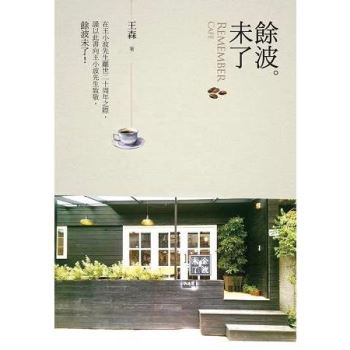駱以軍
我是在臺北一家叫YABOO鴉埠的咖啡屋認識王森的。
那是一家在綠樹密覆小弄裡的咖啡屋,店主是一對可愛標緻的姊妹,我因為抽菸,總在它小院的一張小桌寫稿。我在這裡寫了許多稿子,有兩隻店貓,一隻叫虎面,一隻叫豹頭,牠們時不時跳上我的桌子,喝水杯裡的水。店裡的工讀生都是些年輕怪咖,他們在客人少時,會跑到這小院抽菸,打打鬧鬧,說些屁話。這些怪咖們臥虎藏龍,有拍電影的,這個拍電影的年輕導演,有次和我聊臺灣六○年代女性壓抑的情慾,他們好像要拍個那樣時空背景的電視劇,當時我建議他去看瓊瑤的《窗外》;有兩個合作開一間設計公司,其中一個跑來跟我哈啦,說他是洪秀全的後代,他們家家譜真的有記載,應是當年被李鴻章剿滅後,離散逃亡來臺灣;另一個則跟我說些他父親在南部開神壇的故事;另有一個看去很像手塚治蟲的怪人,我看過幾次他在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還有卡夫卡的《城堡》。
這間咖啡屋很像我的「看不見的城市」,它既是臺北的縮影又不是真正的臺北。他有種頹廢,有種收容各路流浪漢不驚不怪的自由;一種「未來文明芻議」的發想之地;有點像旋轉中的魔方,許多個「另一個」並置、重疊、跳動的場所。我在這裡遇過張懸,遇過舒國治,遇過許多電影導演、音樂人、作家,我在那寫稿的時候,一旁那店主姊妹的妹妹再用機器烘咖啡,空氣中全是那焦苦的香味。
我是在某個下午,在這YABOO咖啡屋的小院,和王森聊起來。很奇妙的,我們聊得非常契合,我知道他在大陸推廣開咖啡屋,他也支持一些年輕人開咖啡屋,我們可能都有一些對這文明未來的擔憂或牢騷,且各自有一定人生閱歷,對人世的複雜百感交集,可以談論某些結構背後的暗影,且說起那荒謬難解之處,會悲傷的笑。很奇妙的是,我相信小說,而他相信咖啡屋,我們相信我們在認真實現的,至少都可以一小刻度的給予這文明甚麼:情感的想像力,人對他人空間的尊重和自由,對異端的包容,對精緻的不休止追求,還有,昆德拉說的,笑的能力。
這次,王森寫了本談王小波的書,我非常驚喜,說來我也是個王小波迷啊。時空的錯置,當年我在讀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驚為天書,但也缺乏背景脈絡的理解,只知道他是個早逝的天才。已經許多年了,我記得《黃金時代》裡,那被集體排除尊嚴,人間失格的兩人,男主角還提議女主角「我們來敦一敦我們偉大的友誼」,我覺得那是我讀過的小說,昆德拉《玩笑》的呂德維克之外,最倒楣、最灰敗的男主人公。但王小波給予我一個中文書寫活蹦亂跳,毛羽賁張,想像力無比自由無遠弗屆的啟發。我是在對大陸小說之語境,缺乏足夠理解的狀況下,讀了王小波這些調戲、憂鬱、自遊魂被剝解之冷酷喜劇、狂想的文字。時日久遠,這個陰鬱的印象,成了我這些年,較多跑大陸,多認識些大陸哥們,一種後設的、抓不住那不可思議存在情境的比對幻燈片。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笑,不那麼西方戲劇的笑,一種穿過《儒林外史》,《紅樓夢》,在那艱難之境找一絲絲浪漫小苗的,疊加層層領會的笑。就像你讀了波拉尼奧《荒野追尋》便瞭墨西哥人,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就懂俄羅斯人,王小波是一個在紙面上的中國小說,更浮凸、立體出來的這個民族心靈的某種多維投影。後來我在YOUTUBE上流連忘返的看一些大陸綜藝:《金星秀》、《愛情保衛戰》、《中國好聲音》、《中國達人秀》、郭德剛的相聲、《東北一家人》……,我感覺那是一個王小波預言的世界。一種外邊人看,不理解那結構如何如此錯綜複雜、群體性大於個體小小的密室,而能夠不崩塌-的疊加態。作為一個外部的觀察者,沒有置身其中,這樣的情感學習,因為數據太龐大了,無從領會其周期表、排序、以及音階。
這次讀了王森的《餘波未了》,我有一種借用余華的話「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感觸:王森真的是王小波鐵粉,我真是自嘆不如,但我想像著我和他在咖啡屋秉燭夜談,談我們不同切面體會的王小波。我談我感受的王小波的陰鬱和瘋狂,他談他看到的王小波的清醒和真實。而他對王小波的熱愛,可以比附他對咖啡屋推廣的同一種情感:對這個文明的一種未來學的可能,可以不麻木,不虛無,不冷酷,任何一種陌生的感受都可以有情感的想像力。這本書其實就是王森的「王小波絮語」,一種「知識份子論」的跨時空對話,從獨立性、誠實、經驗、人性的逆轉、網路、電影與愛情、思維的樂趣……,半引半侃,夾議夾敘,他可能是在王小波不在了之後的這二十年,活在這個水波湍流的中國,他是個實踐者,行動者,他當然不是梁文道、許知遠那樣的公知,但你會看到他這樣和我算同代人,苦口婆心,脣乾舌燥的想和年輕人說說,那些不該被遺忘的,那些隱藏在細節中的現代人的價值。他是活在新事物、新氣息的世界裡的人。我讀了這本書更覺得王森是個溫厚的人,木訥的人,如果中國的未來有更多這樣的,從不安、疑惑中,仍願意一點一滴的保存那獨立思考之人,那這個文明會是個美麗的文明。
祝福這本書。
我是在臺北一家叫YABOO鴉埠的咖啡屋認識王森的。
那是一家在綠樹密覆小弄裡的咖啡屋,店主是一對可愛標緻的姊妹,我因為抽菸,總在它小院的一張小桌寫稿。我在這裡寫了許多稿子,有兩隻店貓,一隻叫虎面,一隻叫豹頭,牠們時不時跳上我的桌子,喝水杯裡的水。店裡的工讀生都是些年輕怪咖,他們在客人少時,會跑到這小院抽菸,打打鬧鬧,說些屁話。這些怪咖們臥虎藏龍,有拍電影的,這個拍電影的年輕導演,有次和我聊臺灣六○年代女性壓抑的情慾,他們好像要拍個那樣時空背景的電視劇,當時我建議他去看瓊瑤的《窗外》;有兩個合作開一間設計公司,其中一個跑來跟我哈啦,說他是洪秀全的後代,他們家家譜真的有記載,應是當年被李鴻章剿滅後,離散逃亡來臺灣;另一個則跟我說些他父親在南部開神壇的故事;另有一個看去很像手塚治蟲的怪人,我看過幾次他在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還有卡夫卡的《城堡》。
這間咖啡屋很像我的「看不見的城市」,它既是臺北的縮影又不是真正的臺北。他有種頹廢,有種收容各路流浪漢不驚不怪的自由;一種「未來文明芻議」的發想之地;有點像旋轉中的魔方,許多個「另一個」並置、重疊、跳動的場所。我在這裡遇過張懸,遇過舒國治,遇過許多電影導演、音樂人、作家,我在那寫稿的時候,一旁那店主姊妹的妹妹再用機器烘咖啡,空氣中全是那焦苦的香味。
我是在某個下午,在這YABOO咖啡屋的小院,和王森聊起來。很奇妙的,我們聊得非常契合,我知道他在大陸推廣開咖啡屋,他也支持一些年輕人開咖啡屋,我們可能都有一些對這文明未來的擔憂或牢騷,且各自有一定人生閱歷,對人世的複雜百感交集,可以談論某些結構背後的暗影,且說起那荒謬難解之處,會悲傷的笑。很奇妙的是,我相信小說,而他相信咖啡屋,我們相信我們在認真實現的,至少都可以一小刻度的給予這文明甚麼:情感的想像力,人對他人空間的尊重和自由,對異端的包容,對精緻的不休止追求,還有,昆德拉說的,笑的能力。
這次,王森寫了本談王小波的書,我非常驚喜,說來我也是個王小波迷啊。時空的錯置,當年我在讀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驚為天書,但也缺乏背景脈絡的理解,只知道他是個早逝的天才。已經許多年了,我記得《黃金時代》裡,那被集體排除尊嚴,人間失格的兩人,男主角還提議女主角「我們來敦一敦我們偉大的友誼」,我覺得那是我讀過的小說,昆德拉《玩笑》的呂德維克之外,最倒楣、最灰敗的男主人公。但王小波給予我一個中文書寫活蹦亂跳,毛羽賁張,想像力無比自由無遠弗屆的啟發。我是在對大陸小說之語境,缺乏足夠理解的狀況下,讀了王小波這些調戲、憂鬱、自遊魂被剝解之冷酷喜劇、狂想的文字。時日久遠,這個陰鬱的印象,成了我這些年,較多跑大陸,多認識些大陸哥們,一種後設的、抓不住那不可思議存在情境的比對幻燈片。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笑,不那麼西方戲劇的笑,一種穿過《儒林外史》,《紅樓夢》,在那艱難之境找一絲絲浪漫小苗的,疊加層層領會的笑。就像你讀了波拉尼奧《荒野追尋》便瞭墨西哥人,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就懂俄羅斯人,王小波是一個在紙面上的中國小說,更浮凸、立體出來的這個民族心靈的某種多維投影。後來我在YOUTUBE上流連忘返的看一些大陸綜藝:《金星秀》、《愛情保衛戰》、《中國好聲音》、《中國達人秀》、郭德剛的相聲、《東北一家人》……,我感覺那是一個王小波預言的世界。一種外邊人看,不理解那結構如何如此錯綜複雜、群體性大於個體小小的密室,而能夠不崩塌-的疊加態。作為一個外部的觀察者,沒有置身其中,這樣的情感學習,因為數據太龐大了,無從領會其周期表、排序、以及音階。
這次讀了王森的《餘波未了》,我有一種借用余華的話「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感觸:王森真的是王小波鐵粉,我真是自嘆不如,但我想像著我和他在咖啡屋秉燭夜談,談我們不同切面體會的王小波。我談我感受的王小波的陰鬱和瘋狂,他談他看到的王小波的清醒和真實。而他對王小波的熱愛,可以比附他對咖啡屋推廣的同一種情感:對這個文明的一種未來學的可能,可以不麻木,不虛無,不冷酷,任何一種陌生的感受都可以有情感的想像力。這本書其實就是王森的「王小波絮語」,一種「知識份子論」的跨時空對話,從獨立性、誠實、經驗、人性的逆轉、網路、電影與愛情、思維的樂趣……,半引半侃,夾議夾敘,他可能是在王小波不在了之後的這二十年,活在這個水波湍流的中國,他是個實踐者,行動者,他當然不是梁文道、許知遠那樣的公知,但你會看到他這樣和我算同代人,苦口婆心,脣乾舌燥的想和年輕人說說,那些不該被遺忘的,那些隱藏在細節中的現代人的價值。他是活在新事物、新氣息的世界裡的人。我讀了這本書更覺得王森是個溫厚的人,木訥的人,如果中國的未來有更多這樣的,從不安、疑惑中,仍願意一點一滴的保存那獨立思考之人,那這個文明會是個美麗的文明。
祝福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