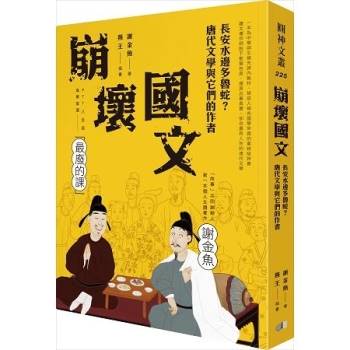壹部曲
人有離合,月有圓缺
──那些永不在生活中缺席的情感之事
第一章 韓愈的生猛海鮮宴
學習把嚥不下喉的吞入腹中
「韓柳元白」是國文與歷史課本上很常讀到的四個人—韓愈、柳宗元、元稹和白居易,他們被奉為一代文壇宗師、傑出的詩人與散文家。他們若不是道貌岸然,就是憂國懷鄉,似乎生來就帶著崇高的使命,就連他們的挫折,也都是為了更長遠的理想而做出犧牲,他們是聖賢,而不是「人」。
如果我們穿越回唐代,可能會對這四人的印象截然不同。在這四人之中,韓愈最為年長,他和柳宗元是忘年之交,但是對於元白,就不這麼交心。他們經歷過同樣的時代、同一事件,他們各自做出不同的抉擇,也承擔不同的結果。 某個人的飛黃騰達,或許代表著另一人的失意落寞。在仕途浮沉之間,長安成了唯一的目標,這座象徵著最高權力的城市,寄託著他們對於仕途的念想。長安之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飲食,就成為他們從帝國的中心前往邊境時,最難以適應又不得不適應的問題。
兩個貶謫到南方的吃貨
韓愈與柳宗元相知很早,不過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截然不同。永貞年間(A.D. 805-806),站在革新派的柳宗元,雖一度與保守派的韓愈鬧得不太愉快,但無損於他們真摯的友情。一向被認為個性偏激的韓愈,後來仍殷殷地寫詩、寫信安慰處境比他更慘的柳宗元,甚至在柳宗元死後收養了他的孩子。許多人以韓愈的詩作〈永貞行〉和他修史時臭罵永貞黨人的紀錄,批評他對老朋友刻薄、不厚道,卻忽略了他和柳宗元一封封往來的書信。 對柳宗元而言,他在貶謫人生中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人情冷暖,他不可能無感。不過他和韓愈的來往依然真誠,甚至是可以直接反駁的交情。如果不是出於友情和尊重,也沒有必要到這份上還要來往。這樣的交情,不亞於一直和他站錯隊的難兄難弟劉禹錫。柳宗元的悲劇與其個性有直接的關聯,而事實上,韓愈也不完全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聖人,因此這兩人的感情能超越政治,確實是很難得的。 柳宗元的政治汙點,跟了他一輩子。他曾一度被召回長安,以為否極泰來,正高興著,沒想到朝廷裡有人惡整他,明升暗降,把他送到了更遙遠的柳州(今廣西省境內)當刺史。元和(A.D. 806-820)十四年,當唐廷正為了憲宗的「元和中興」大肆慶祝時,韓愈卻因諫阻皇帝迎佛骨舍利的靡費行為上了〈諫迎佛骨表〉,觸怒皇帝而被趕出長安,發往今日廣東的潮州為官。 潮州與柳州都是唐帝國的南方邊疆,韓愈與柳宗元兩人可說是陷入人生的嚴重低潮。不過在他們往來的詩文中,除了談人生、談環境、談挫折、談思想等種種偉大理想和抱負之外,也不忘談吃⋯⋯
他們吃什麼呢?羊肉?牛肉?豬肉?魚肉?
都不是,他們談的是蛙肉!
在我看到這則記載時,柳宗元在我心中冷豔高貴的形象完全破滅。他不僅吃青蛙,還很愛吃!甚至寫信勸剛貶往南方的韓愈說:「這東西很好吃,你試試看。」 於是,韓愈就寫了一首〈答柳柳州食蝦蟆〉回應他的好朋友: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
這六句詩的意思大致就是:「我一開始也不是很喜歡吃,最近稍微可以吃一些了,但是怕這種東西吃多了會染上南方的蠻夷之氣,只好暫時放下這個喜好。不過你也太愛吃蛙肉了吧?竟然把它當作豹子胎這種高級的美食來吃?」
如果換作是現代人吃豹胎,可能會鬧上新聞被罵不愛護動物,但中古時代並沒有這種規矩,當時的人還覺得豹胎是美味珍饈。說到這裡,各位或許對於韓柳二人的印象又更崩壞了一些,不過,大家其實可以放心,在唐代只有親王、公主以上的貴族才有資格擁有豹子,所以沒多少人真的吃得起豹胎,豹胎可能只是一種傳說中的食物,就像龍髓鳳肝一樣,只是個指代。
雖然吃青蛙這件事很難和韓柳二人聯想在一起,不過青蛙在南方是很常見的食物,到了北方反是罕見的食材,甚至能端上唐代的「國宴」菜單。各位應該會好奇,他們到底怎麼吃蛙?是三杯嗎?還是油炸?很可惜,雖然外皮酥脆、肉質滑嫩的炸蛙腿是現代人的下酒菜,但唐代還沒有出現炒和炸的技術。因此,長安的高級吃法就是把青蛙剝皮之後,從中間剖半,像分開的豆莢一樣兩片平貼在盤子上蒸熟了吃,叫「雪嬰兒」,聽起來有點嚇人。
但是到了南方,可就不是這樣了。唐代的《南楚新聞》說,南方的一些部族(百越)會先煮一鍋滾水,丟入小芋頭或小筍子,接著把蛙類丟進去,蛙類就會抱住水中的芋頭或筍子,煮好之後,就統統撈起來吃。這些百越民眾尤其喜歡吃皮上有疙瘩的蟾蜍,他們主張先丟進滾水、燙掉蟾蜍的皮,然後再煮,但也有些人就愛吃蟾蜍皮,這顯然是特殊的個人愛好。
韓愈和柳宗元的吃法,可能是蒸、清燙或煮湯。從中醫的理論來說,蛙肉是補氣治脾虛的食物,對於身體一直不好的柳宗元來說,應該是很不錯的滋補食品。
潮州的海鮮大餐
在長安城,除了蒸蛙肉之外,還有一樣高級的食物只屬於士族與貴族,那就是「魚膾」。千萬不要以為唐代人都吃熟食,他們也喜歡把新鮮的鯉魚去骨後切成條狀,拌上佐料生吃。因此,韓愈和柳宗元可能在長安時就曾經嚐過了生魚片的美味。
不過,新鮮的魚並不常見。儘管韓愈幼年曾經短暫在南方生活,但是他所習慣的食物,應該大多還是麵食類或雞肉、羊肉。為什麼沒有牛肉或豬肉呢?這是因為唐代不能隨便宰殺耕田的牛,而豬在當時的北方又比較少。因此,當韓愈從長安風塵僕僕、心如死灰地抵達南方,有人邀他參加一場宴會時,他一踏入現場就嚇壞了! 案上有一大堆他沒看過的食物,韓愈在吃完這頓飯後,就寫了首詩〈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這首詩是給長安的朋友元集虛,除了寫下自己看到的奇怪食物,順便給朋友補充一下生物知識: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首先是鱟。鱟長得很像好萊塢電影裡會出現的外星生物,被稱為地球的活化石,由於繁殖時雌雄會黏在一起,很容易抓得到。現在因為被列為保育類動物,所以比較不吃了,不過在韓愈的時代,潮州人才不會管這麼多,抓起來就宰。
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
接著是蠔,也就是牡蠣。潮州的牡蠣黏在礁石上,不像現代養殖牡蠣那樣串成一串放進海裡。吃牡蠣在現代人看來,真是超級生猛有勁的好東西呀!不過韓愈從來沒見過這生物,請各位不要怪他見識少,因為在那個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海的時代,牡蠣並不常見。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
第三種是蒲魚,也就是魟魚。這種在淺海生活的軟骨魚,現代也常看到,體型可以長到非常大。我曾經在東石港邊看到人們分切大概有餐桌這麼大的巨大魟魚,但說實在的,我不是很喜歡牠的味道。不過還是再強調一次,雖然韓愈小時候曾住過南方,但是他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北方,所以他對魟魚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一條蛇一樣的尾巴⋯⋯畢竟他比較熟悉蛇。
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
第四種就是青蛙了。韓愈在這裡告訴現代人一個重點,在唐代的南方,「蛤」不是現在我們吃的蚌殼文蛤,而是蛙類的統稱。雖然名字和北方不同,不過是一樣的東西。
章舉馬甲柱,鬥以怪自呈。
最後,章舉和馬甲柱,其實就是章魚和帆立貝(扇貝)。在現代人看來,章魚現燙現切、加上剛撬開的新鮮扇貝,滿口海味鮮美無比,實在是無上享受。但是不懂得欣賞的韓愈,竟然嫌這兩樣東西長得怪!絲毫沒提到牠們的滋味。
其餘還有數十種,韓愈就懶得解釋了。那麼他怎麼吃呢?他只好暫時按照南方的習慣來食用,「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也就是用酸和鹹來調味,並加了橙汁和椒拌著吃。這裡的椒絕對不是辣椒(辣椒在唐代還沒進入中國),有可能是花椒,也有可能是胡椒。
雖然在他的詩中,把這些海鮮介紹得很難吃,但是各位不妨把它想像成淋了五味醬那樣的酸酸鹹鹹,正好襯托出海鮮的滋味。然而,在這裡又顯現了唐代與現代的不同,我們想像的美味,韓愈卻說:「腥臊始發越,嘴吞面汗騂。」意思是:「我吃下去之後發現更腥更臭了,嘴巴雖然已經吞下,臉上卻狂冒汗而且臉色發紅。」 這狼狽的樣子,讓韓愈把目光從海鮮上轉開,看向了⋯⋯ 蛇⋯⋯ 是的,就在此時,韓愈看見了活生生、在籠子裡的蛇。 為什麼吃飯的時候會看到活蛇?因為唐人也知道現宰現煮最新鮮呀!韓愈和這蛇你看我我看你,雖然認得蛇是什麼,卻覺得蛇長得真是面目猙獰啊⋯⋯
於是,他打開籠子,把蛇放走,但是這蛇竟然不知感激,繼續對韓愈示威。 韓愈只好對蛇說:「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意思是:「賣掉你不是我的錯,沒殺你也算是有情分吧,我也不求你拿顆靈珠來報答我,只希望我們之間別有什麼怨恨哪!」 韓愈的這頓生猛海鮮歡迎宴,到這裡告一個段落。這是在他初抵潮州時的詩作,當他寫下那首吃青蛙詩的時候,他已經在潮州過了些日子,原先不能接受的青蛙,也稍稍能夠入口,並懂得了南方食物的美味。
千里宦遊是唐代官員政治生涯的常態,或在天子腳下、吃著長安口味的駝峰、魚膾、雪嬰兒;或在山海邊緣、吞著一生從未見過的山產海鮮。 宦海中浮浮沉沉,誰都不得不學會忍耐,學習把嚥不下喉的吞入腹中,即便是韓愈,即便是柳宗元,即便是今日的你、今日的我。第二章
柳宗元的檳榔
我得了一種叫作寂寞的病
我小時候讀到「柳宗元」三個字時,腦中總會浮現一個高䠷纖瘦、如柳樹般的身影,又或是一身道袍、凜然昂首。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小時候的印象只對了一半。
中唐文學神主牌韓柳元白四人遭遇各異,雖然都經過貶謫的失意,但其他三人的結局還稱得上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然而出身最好、又最早成為人生勝利組的柳宗元,卻只是猜到了開頭、猜不著結局,怎麼說呢?這就要從柳氏一門說起了。 柳氏一家有個不太好的門風,就是他們超級死腦筋又聰明絕頂。柳宗元的父親柳鎮,以博學多聞和剛直不屈出名,遭受冤屈被貶也死不掉一滴淚,是個硬漢中的硬漢。柳媽媽盧氏也是博學的名門閨秀。這樣優秀的家庭教育和端正不阿的品格養成下,正常來說是一個偉大名臣的搖籃,可惜,事情從來不是小時候媽媽教你的那麼簡單。
在唐帝國,一個理想的人生勝利組需要有好的開始。當時的身分制度分成兩大類:下層社會是廣大的平民與賤民,上層社會則是皇族與士族。皇族容易理解,而士族有點模糊,廣義地說,就是家族有人當過官、是讀書人;但狹義地說,誰屬於士族是需要考察祖譜的,能夠被列入紀錄的家族,通常都有長達百年以上的歷史、有顯赫的祖先或雄厚的地方勢力。也只有士族才能擔任握有政治實權的某些官職,這種稱為「清官」;其他不重要、純技術性的就可以讓非士族的人擔任,這些則稱為「濁官」。清濁之間,自然就顯出了高下之分。
投胎成功、順利長大之後,要開始求官,當然有不同的管道,但最棒的一種就是「進士科」。這需要先取得鄉貢進士的資格,才能去考試,考上進士就保證有工作,但要等多久才有缺、會在哪裡工作,則還是未知數,有時候一等就是三五年。如果不想等,那就要再去考更難的「制科」,也稱「制舉」。困難的原因是,來考試的人基本上不限鄉貢進士資格,只要你出身合格,不管你是現任的官員或是成名已久的大才子,都可以來考試,所以什麼骨灰級的神獸霸者傳說人物都可能出現。如果通過制科,就能晉升唐帝國新秀菁英,不但工作會更好,也會更接近京師。
少年柳宗元二十幾歲就進士加制舉雙料冠軍、青雲直上,那時白居易還在吃土呢⋯⋯恐怕當時唐帝國的人都不會懷疑他將是下一個政治明星。更加人生勝利組的是,他娶了名門楊家的女兒,這下子父族、母族和妻族的各種政治資源,當然都是他的籌碼了。 意氣風發、聰明絕頂的柳宗元,理所當然地氣焰囂張,所以討厭他的人不少。不過,他一點也不在意,說句粗俗的話:「人一屌,就任性。」柳宗元就是這樣一個任性的男人。
順風順水的前半生,在八○五年攀上了人生新高峰,這一年,因為老皇帝駕崩、新君上台,史稱「永貞革新」的變革正式展開。在當時唐帝國的人看來,這場變革由於政治影響而評價低下,但是隔著一千三百年來看,除了政治鬥爭的現實外,還有著近乎傻氣的天真。
永貞是新皇帝的年號,雖是新君,但這位新皇帝就像今日英國的查爾斯王子一樣,當了幾十年的太子,眼見國家衰落而亟欲於有生之年有一番作為。而他身旁的親信,其實就是兩個出身民間、被高級官僚看不起的技藝官,以及一群像柳宗元這樣出身良好、資歷優秀、急著想改變國家的青年菁英,組成一個唐吉軻德式的團隊,也就是後來人稱的「二王八司馬」。
永貞革新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對內處理內侍、對外處理藩鎮。大家可能都在課本上讀過,唐代宦官勢力猖獗,因此,新君先斷除下級內侍收取賄賂與強取豪奪的宮市,除掉宮中的異己派內侍,再以親信奪取神策軍這支由內侍長期掌握的軍隊。對於藩鎮,則先從皇帝己身做起,叫藩鎮不要一天到晚送禮物賄賂朝廷,同時壓制遠在江南、武力較弱卻很有錢的藩鎮,純粹殺雞給猴看,順便再拔幾個貪官來收買人心。
永貞革新的內容,其實以宣示的政治意義居多。發動這場革新的核心,是兩個王姓官員,他們來自帝國中下層階級,雖然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卻無法贏得士族官僚的認可。他們的不懂禮儀、出身低下,甚至是一口不夠優雅正確的官話,都被當成取笑的對象。不過平心而論,要說他們沒有私心是不可能的;但如其他菁英官僚一般說他們是奸佞小人,也未必是真,只是他們沒有時間可以證明自己對國家救亡圖存的決心。
除此之外,皇帝又突然中風、不能言語,於是一百多天的革新,成為一場煙花。中風的皇帝無法阻擋由內侍、藩鎮與高級菁英官僚組成的政變,黯然退位,眼睜睜地看著二十八歲的長子在眾人簇擁下登上寶座。皇帝只多活了半年,在所謂「西宮南內多秋草」的「南內」興慶宮中,靜靜地去世,諡號「順宗」。此時,二王已成泉下亡魂,八司馬也被新君逐出長安,前往唐帝國的絕域。 永貞時代的政策並非一無可取,尤其在處理藩鎮這件事上被後來的繼任者延續下來,甚至不惜發動了長達十餘年的戰爭—攻打各地藩鎮。
一樣的事,永貞時代沒能取得官僚們的認同,完全地失敗,而繼任的皇帝與官僚們借取經驗,一步一步地把路走好,而被稱為「元和中興」。 「二王八司馬」,是新政府上台後處理永貞時代舊臣的舉措。唐帝國有身分階級,一般而言,除非大逆不道,否則士族通常不太容易被處死,二王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們終究不是士族,而出身士族的八個朝臣則被貶為州司馬,也就是一州的副官。其實,一開始他們是被發出去當刺史,也就是一州的長官,結果在路上再貶一級、被發得更遠,柳宗元就被送到現在湖南和廣西交界的永州當司馬,而且還不是正式的司馬,是「員外同正員」。簡單說,他是個冗員。 這一年,柳宗元三十三歲,從萬眾仰慕的高級官僚,被踢到湖南的山裡當冗員,用肚臍想也知道他不開心。事實上,從三十三歲之後,他的人生像卡到陰一樣衰到極點,媽媽、女兒、姊夫、外甥、姪女、堂弟⋯⋯幾乎稱得上至親的人都去世了。
最慘的是,他堂弟跑來永州看他,路上生了小病,但還能和柳宗元一起出去玩,回來後也有說有笑的,隔天早上卻叫不起來,這才發現斷了氣⋯⋯ 我無法理解,柳宗元到底是命帶天煞孤星還是被草人插針,人生痛苦到這種程度,衰運卻不只如此,他還遇過找不到房子暫居寺廟(可能因為他是冗員或被刻意打壓,永州一開始沒有配宿舍給他)、家裡失火,還一直生病,甚至昏迷三天沒醒。
這麼悲慘的人生,同時造成他在婚姻上的重大挫折。在他二十七歲時,出身名門的妻子去世了,後來二十年都沒有再娶。不是他不想娶,而是娶不到⋯⋯關鍵就在於他是士族,唐帝國中不同階級的人不能結婚,士族男性可以納庶民女性為妾、卻不能為妻,但是以柳宗元的處境,也沒有士族女性要嫁給他。 如果說三十三歲之前的柳宗元是翩翩公子,三十三歲之後的柳宗元就徹底是個魯蛇。他很焦慮自己娶不到老婆又生不出兒子,因此在永貞事件的影響稍微平息、開始有故舊寫信和他聯絡時,他忍不住告訴一位長輩:「我真的好想娶老婆、好怕絕後啊⋯⋯」
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寄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的悲慘自敘讀起來是很可憐啦,但我有時候覺得柳宗元也是神經頗大條,前面說自己好慘、都沒有女孩想跟我一起生寶寶,後面又說自己吃東西也不知道滋味,而且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每次讀到這裡,都讓我有點不舒服—一個不洗澡的男人,誰會介紹長安的白富美給他呢?!有事嗎! * * *
在痛苦的人生中,飲食對柳宗元來說只是拿來苟延殘喘的工具,所以關於吃,他留下的紀錄很少很少,造成我很大的困擾。他和當時的士人們一樣,對南方充滿了恐懼,在他們筆下,南方的夜晚黑壓壓一片,到處都是藤蔓、奇怪的生物,以及吃著噁心食物的土人。
(平衡報導,我認為南方的平民可能也覺得這群官員是一群沒見過世面的城市俗,但很可惜地,南方視角的文字並沒有留下來。) 話雖如此,其實柳宗元很怕自己被南方同化,事實上,他可能還真的已經慢慢被南方給同化了。在前一章,我說過他告訴韓愈自己喜歡吃青蛙,在永州也可能吃過鷓鴣,因為他說口感「甘且腴」,而且很容易就抓得到。
某一天,他家的廚子抓了一籠鷓鴣正準備宰殺,柳宗元經過,想起了自己有如籠中鳥一般的生活,於是,他放走了鷓鴣,並寫詩告訴鷓鴣: 破籠展翅當遠去, 同類相呼莫相顧。 這個情景和韓愈放走那條蛇有點像,或許都是他們在感嘆自己命運,卻也意外留下了飲食史的證據。
柳宗元究竟後來還吃不吃鷓鴣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樣東西,倒是他從元和初年貶到永州之後,就一路吃到柳州⋯⋯ 那就是檳榔。 是的,我想寫到這裡,柳宗元在諸位心中冷豔高貴的形象已經完全毀了—不洗澡、一騷癢滿手汙垢,然後還吃檳榔?!誰要嫁給他呢!
不過,不講衛生這件事雖然不受妹子青睞,但吃檳榔在當時並非惡習,反而是一種高級享受!在漢魏時代,北方朝廷的勢力還沒能完全控制南方時,生長在南方的檳榔是超夢幻的果實,只有皇帝和高官才能看到那麼少少幾顆。直到三國與南朝,北方下來的政權掌控南方,才把檳榔從深山老林裡挖出來,千里迢迢地送到建康城(今南京),用超高級的盤子貢獻給皇帝,皇帝再賜給大臣當作禮物。
也因此南朝的世家大族,開始把吃檳榔當成高級享受,飯後來一顆,健胃整腸助消化。曾經有個魯蛇,在落魄時去老婆娘家求檳榔吃,結果被妻舅嘲笑,後來魯蛇搖身一變成大官,把妻舅叫來,用金盤盛了一堆檳榔請他們吃,完全是打臉打很大;另外有個南朝的親王,平時實在是太愛吃檳榔了,於是過世前特別交代子孫,以後一定要用檳榔祭拜他;還有一個南朝官員,臨死前兒子問他:「老爸,你有什麼心願未了嗎?」他只說:「我要吃一口好檳榔⋯⋯」於是,兒子買了一大堆檳榔現剖,結果剖了一百多顆都不夠好,眼見老爸含恨而終,兒子也從此發誓戒掉檳榔。 除了貴族們,高級的檳榔也可作為供養品送給高僧。不過由於檳榔吃多了人會有點醉,所以佛教僧團內部也曾討論吃檳榔是否合適,結論就是:「因為檳榔可以讓人口氣芬芳,如果吃少少當口香糖沒關係。」
那麼,南朝人怎麼吃檳榔呢?史書上說,他們用扶留藤夾牡蠣殼灰包在一起吃。扶留藤就類似荖葉,而牡蠣灰其實就是石灰⋯⋯等等!這不就是巷口檳榔攤賣的包葉仔白灰檳榔嗎?所以,各位讀者如果想要體驗南朝時尚,不要猶豫,快去檳榔攤享受千年傳統吧。
隋唐之後,因為主要的政治重心被拉回北方,檳榔沒那麼容易取得,所以無法持續高級口香糖的地位,變成一種南方來的藥材,長安的官員們沒事的時候是不會集體在都城吃檳榔的。但是南方的百姓還是繼續開心地吃著檳榔,然後嘲笑從北方來的官員水土不服、上吐下瀉,我想,他們心中可能這麼想:「這群長安俗,我們都是吃檳榔以毒攻毒!所以完全沒事呢!」
接著,北方來的官員們為了在南方活下去,也開始吃起檳榔了⋯⋯
人有離合,月有圓缺
──那些永不在生活中缺席的情感之事
第一章 韓愈的生猛海鮮宴
學習把嚥不下喉的吞入腹中
「韓柳元白」是國文與歷史課本上很常讀到的四個人—韓愈、柳宗元、元稹和白居易,他們被奉為一代文壇宗師、傑出的詩人與散文家。他們若不是道貌岸然,就是憂國懷鄉,似乎生來就帶著崇高的使命,就連他們的挫折,也都是為了更長遠的理想而做出犧牲,他們是聖賢,而不是「人」。
如果我們穿越回唐代,可能會對這四人的印象截然不同。在這四人之中,韓愈最為年長,他和柳宗元是忘年之交,但是對於元白,就不這麼交心。他們經歷過同樣的時代、同一事件,他們各自做出不同的抉擇,也承擔不同的結果。 某個人的飛黃騰達,或許代表著另一人的失意落寞。在仕途浮沉之間,長安成了唯一的目標,這座象徵著最高權力的城市,寄託著他們對於仕途的念想。長安之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飲食,就成為他們從帝國的中心前往邊境時,最難以適應又不得不適應的問題。
兩個貶謫到南方的吃貨
韓愈與柳宗元相知很早,不過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截然不同。永貞年間(A.D. 805-806),站在革新派的柳宗元,雖一度與保守派的韓愈鬧得不太愉快,但無損於他們真摯的友情。一向被認為個性偏激的韓愈,後來仍殷殷地寫詩、寫信安慰處境比他更慘的柳宗元,甚至在柳宗元死後收養了他的孩子。許多人以韓愈的詩作〈永貞行〉和他修史時臭罵永貞黨人的紀錄,批評他對老朋友刻薄、不厚道,卻忽略了他和柳宗元一封封往來的書信。 對柳宗元而言,他在貶謫人生中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人情冷暖,他不可能無感。不過他和韓愈的來往依然真誠,甚至是可以直接反駁的交情。如果不是出於友情和尊重,也沒有必要到這份上還要來往。這樣的交情,不亞於一直和他站錯隊的難兄難弟劉禹錫。柳宗元的悲劇與其個性有直接的關聯,而事實上,韓愈也不完全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聖人,因此這兩人的感情能超越政治,確實是很難得的。 柳宗元的政治汙點,跟了他一輩子。他曾一度被召回長安,以為否極泰來,正高興著,沒想到朝廷裡有人惡整他,明升暗降,把他送到了更遙遠的柳州(今廣西省境內)當刺史。元和(A.D. 806-820)十四年,當唐廷正為了憲宗的「元和中興」大肆慶祝時,韓愈卻因諫阻皇帝迎佛骨舍利的靡費行為上了〈諫迎佛骨表〉,觸怒皇帝而被趕出長安,發往今日廣東的潮州為官。 潮州與柳州都是唐帝國的南方邊疆,韓愈與柳宗元兩人可說是陷入人生的嚴重低潮。不過在他們往來的詩文中,除了談人生、談環境、談挫折、談思想等種種偉大理想和抱負之外,也不忘談吃⋯⋯
他們吃什麼呢?羊肉?牛肉?豬肉?魚肉?
都不是,他們談的是蛙肉!
在我看到這則記載時,柳宗元在我心中冷豔高貴的形象完全破滅。他不僅吃青蛙,還很愛吃!甚至寫信勸剛貶往南方的韓愈說:「這東西很好吃,你試試看。」 於是,韓愈就寫了一首〈答柳柳州食蝦蟆〉回應他的好朋友: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
這六句詩的意思大致就是:「我一開始也不是很喜歡吃,最近稍微可以吃一些了,但是怕這種東西吃多了會染上南方的蠻夷之氣,只好暫時放下這個喜好。不過你也太愛吃蛙肉了吧?竟然把它當作豹子胎這種高級的美食來吃?」
如果換作是現代人吃豹胎,可能會鬧上新聞被罵不愛護動物,但中古時代並沒有這種規矩,當時的人還覺得豹胎是美味珍饈。說到這裡,各位或許對於韓柳二人的印象又更崩壞了一些,不過,大家其實可以放心,在唐代只有親王、公主以上的貴族才有資格擁有豹子,所以沒多少人真的吃得起豹胎,豹胎可能只是一種傳說中的食物,就像龍髓鳳肝一樣,只是個指代。
雖然吃青蛙這件事很難和韓柳二人聯想在一起,不過青蛙在南方是很常見的食物,到了北方反是罕見的食材,甚至能端上唐代的「國宴」菜單。各位應該會好奇,他們到底怎麼吃蛙?是三杯嗎?還是油炸?很可惜,雖然外皮酥脆、肉質滑嫩的炸蛙腿是現代人的下酒菜,但唐代還沒有出現炒和炸的技術。因此,長安的高級吃法就是把青蛙剝皮之後,從中間剖半,像分開的豆莢一樣兩片平貼在盤子上蒸熟了吃,叫「雪嬰兒」,聽起來有點嚇人。
但是到了南方,可就不是這樣了。唐代的《南楚新聞》說,南方的一些部族(百越)會先煮一鍋滾水,丟入小芋頭或小筍子,接著把蛙類丟進去,蛙類就會抱住水中的芋頭或筍子,煮好之後,就統統撈起來吃。這些百越民眾尤其喜歡吃皮上有疙瘩的蟾蜍,他們主張先丟進滾水、燙掉蟾蜍的皮,然後再煮,但也有些人就愛吃蟾蜍皮,這顯然是特殊的個人愛好。
韓愈和柳宗元的吃法,可能是蒸、清燙或煮湯。從中醫的理論來說,蛙肉是補氣治脾虛的食物,對於身體一直不好的柳宗元來說,應該是很不錯的滋補食品。
潮州的海鮮大餐
在長安城,除了蒸蛙肉之外,還有一樣高級的食物只屬於士族與貴族,那就是「魚膾」。千萬不要以為唐代人都吃熟食,他們也喜歡把新鮮的鯉魚去骨後切成條狀,拌上佐料生吃。因此,韓愈和柳宗元可能在長安時就曾經嚐過了生魚片的美味。
不過,新鮮的魚並不常見。儘管韓愈幼年曾經短暫在南方生活,但是他所習慣的食物,應該大多還是麵食類或雞肉、羊肉。為什麼沒有牛肉或豬肉呢?這是因為唐代不能隨便宰殺耕田的牛,而豬在當時的北方又比較少。因此,當韓愈從長安風塵僕僕、心如死灰地抵達南方,有人邀他參加一場宴會時,他一踏入現場就嚇壞了! 案上有一大堆他沒看過的食物,韓愈在吃完這頓飯後,就寫了首詩〈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這首詩是給長安的朋友元集虛,除了寫下自己看到的奇怪食物,順便給朋友補充一下生物知識: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首先是鱟。鱟長得很像好萊塢電影裡會出現的外星生物,被稱為地球的活化石,由於繁殖時雌雄會黏在一起,很容易抓得到。現在因為被列為保育類動物,所以比較不吃了,不過在韓愈的時代,潮州人才不會管這麼多,抓起來就宰。
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
接著是蠔,也就是牡蠣。潮州的牡蠣黏在礁石上,不像現代養殖牡蠣那樣串成一串放進海裡。吃牡蠣在現代人看來,真是超級生猛有勁的好東西呀!不過韓愈從來沒見過這生物,請各位不要怪他見識少,因為在那個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海的時代,牡蠣並不常見。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
第三種是蒲魚,也就是魟魚。這種在淺海生活的軟骨魚,現代也常看到,體型可以長到非常大。我曾經在東石港邊看到人們分切大概有餐桌這麼大的巨大魟魚,但說實在的,我不是很喜歡牠的味道。不過還是再強調一次,雖然韓愈小時候曾住過南方,但是他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北方,所以他對魟魚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一條蛇一樣的尾巴⋯⋯畢竟他比較熟悉蛇。
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
第四種就是青蛙了。韓愈在這裡告訴現代人一個重點,在唐代的南方,「蛤」不是現在我們吃的蚌殼文蛤,而是蛙類的統稱。雖然名字和北方不同,不過是一樣的東西。
章舉馬甲柱,鬥以怪自呈。
最後,章舉和馬甲柱,其實就是章魚和帆立貝(扇貝)。在現代人看來,章魚現燙現切、加上剛撬開的新鮮扇貝,滿口海味鮮美無比,實在是無上享受。但是不懂得欣賞的韓愈,竟然嫌這兩樣東西長得怪!絲毫沒提到牠們的滋味。
其餘還有數十種,韓愈就懶得解釋了。那麼他怎麼吃呢?他只好暫時按照南方的習慣來食用,「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也就是用酸和鹹來調味,並加了橙汁和椒拌著吃。這裡的椒絕對不是辣椒(辣椒在唐代還沒進入中國),有可能是花椒,也有可能是胡椒。
雖然在他的詩中,把這些海鮮介紹得很難吃,但是各位不妨把它想像成淋了五味醬那樣的酸酸鹹鹹,正好襯托出海鮮的滋味。然而,在這裡又顯現了唐代與現代的不同,我們想像的美味,韓愈卻說:「腥臊始發越,嘴吞面汗騂。」意思是:「我吃下去之後發現更腥更臭了,嘴巴雖然已經吞下,臉上卻狂冒汗而且臉色發紅。」 這狼狽的樣子,讓韓愈把目光從海鮮上轉開,看向了⋯⋯ 蛇⋯⋯ 是的,就在此時,韓愈看見了活生生、在籠子裡的蛇。 為什麼吃飯的時候會看到活蛇?因為唐人也知道現宰現煮最新鮮呀!韓愈和這蛇你看我我看你,雖然認得蛇是什麼,卻覺得蛇長得真是面目猙獰啊⋯⋯
於是,他打開籠子,把蛇放走,但是這蛇竟然不知感激,繼續對韓愈示威。 韓愈只好對蛇說:「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意思是:「賣掉你不是我的錯,沒殺你也算是有情分吧,我也不求你拿顆靈珠來報答我,只希望我們之間別有什麼怨恨哪!」 韓愈的這頓生猛海鮮歡迎宴,到這裡告一個段落。這是在他初抵潮州時的詩作,當他寫下那首吃青蛙詩的時候,他已經在潮州過了些日子,原先不能接受的青蛙,也稍稍能夠入口,並懂得了南方食物的美味。
千里宦遊是唐代官員政治生涯的常態,或在天子腳下、吃著長安口味的駝峰、魚膾、雪嬰兒;或在山海邊緣、吞著一生從未見過的山產海鮮。 宦海中浮浮沉沉,誰都不得不學會忍耐,學習把嚥不下喉的吞入腹中,即便是韓愈,即便是柳宗元,即便是今日的你、今日的我。第二章
柳宗元的檳榔
我得了一種叫作寂寞的病
我小時候讀到「柳宗元」三個字時,腦中總會浮現一個高䠷纖瘦、如柳樹般的身影,又或是一身道袍、凜然昂首。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小時候的印象只對了一半。
中唐文學神主牌韓柳元白四人遭遇各異,雖然都經過貶謫的失意,但其他三人的結局還稱得上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然而出身最好、又最早成為人生勝利組的柳宗元,卻只是猜到了開頭、猜不著結局,怎麼說呢?這就要從柳氏一門說起了。 柳氏一家有個不太好的門風,就是他們超級死腦筋又聰明絕頂。柳宗元的父親柳鎮,以博學多聞和剛直不屈出名,遭受冤屈被貶也死不掉一滴淚,是個硬漢中的硬漢。柳媽媽盧氏也是博學的名門閨秀。這樣優秀的家庭教育和端正不阿的品格養成下,正常來說是一個偉大名臣的搖籃,可惜,事情從來不是小時候媽媽教你的那麼簡單。
在唐帝國,一個理想的人生勝利組需要有好的開始。當時的身分制度分成兩大類:下層社會是廣大的平民與賤民,上層社會則是皇族與士族。皇族容易理解,而士族有點模糊,廣義地說,就是家族有人當過官、是讀書人;但狹義地說,誰屬於士族是需要考察祖譜的,能夠被列入紀錄的家族,通常都有長達百年以上的歷史、有顯赫的祖先或雄厚的地方勢力。也只有士族才能擔任握有政治實權的某些官職,這種稱為「清官」;其他不重要、純技術性的就可以讓非士族的人擔任,這些則稱為「濁官」。清濁之間,自然就顯出了高下之分。
投胎成功、順利長大之後,要開始求官,當然有不同的管道,但最棒的一種就是「進士科」。這需要先取得鄉貢進士的資格,才能去考試,考上進士就保證有工作,但要等多久才有缺、會在哪裡工作,則還是未知數,有時候一等就是三五年。如果不想等,那就要再去考更難的「制科」,也稱「制舉」。困難的原因是,來考試的人基本上不限鄉貢進士資格,只要你出身合格,不管你是現任的官員或是成名已久的大才子,都可以來考試,所以什麼骨灰級的神獸霸者傳說人物都可能出現。如果通過制科,就能晉升唐帝國新秀菁英,不但工作會更好,也會更接近京師。
少年柳宗元二十幾歲就進士加制舉雙料冠軍、青雲直上,那時白居易還在吃土呢⋯⋯恐怕當時唐帝國的人都不會懷疑他將是下一個政治明星。更加人生勝利組的是,他娶了名門楊家的女兒,這下子父族、母族和妻族的各種政治資源,當然都是他的籌碼了。 意氣風發、聰明絕頂的柳宗元,理所當然地氣焰囂張,所以討厭他的人不少。不過,他一點也不在意,說句粗俗的話:「人一屌,就任性。」柳宗元就是這樣一個任性的男人。
順風順水的前半生,在八○五年攀上了人生新高峰,這一年,因為老皇帝駕崩、新君上台,史稱「永貞革新」的變革正式展開。在當時唐帝國的人看來,這場變革由於政治影響而評價低下,但是隔著一千三百年來看,除了政治鬥爭的現實外,還有著近乎傻氣的天真。
永貞是新皇帝的年號,雖是新君,但這位新皇帝就像今日英國的查爾斯王子一樣,當了幾十年的太子,眼見國家衰落而亟欲於有生之年有一番作為。而他身旁的親信,其實就是兩個出身民間、被高級官僚看不起的技藝官,以及一群像柳宗元這樣出身良好、資歷優秀、急著想改變國家的青年菁英,組成一個唐吉軻德式的團隊,也就是後來人稱的「二王八司馬」。
永貞革新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對內處理內侍、對外處理藩鎮。大家可能都在課本上讀過,唐代宦官勢力猖獗,因此,新君先斷除下級內侍收取賄賂與強取豪奪的宮市,除掉宮中的異己派內侍,再以親信奪取神策軍這支由內侍長期掌握的軍隊。對於藩鎮,則先從皇帝己身做起,叫藩鎮不要一天到晚送禮物賄賂朝廷,同時壓制遠在江南、武力較弱卻很有錢的藩鎮,純粹殺雞給猴看,順便再拔幾個貪官來收買人心。
永貞革新的內容,其實以宣示的政治意義居多。發動這場革新的核心,是兩個王姓官員,他們來自帝國中下層階級,雖然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卻無法贏得士族官僚的認可。他們的不懂禮儀、出身低下,甚至是一口不夠優雅正確的官話,都被當成取笑的對象。不過平心而論,要說他們沒有私心是不可能的;但如其他菁英官僚一般說他們是奸佞小人,也未必是真,只是他們沒有時間可以證明自己對國家救亡圖存的決心。
除此之外,皇帝又突然中風、不能言語,於是一百多天的革新,成為一場煙花。中風的皇帝無法阻擋由內侍、藩鎮與高級菁英官僚組成的政變,黯然退位,眼睜睜地看著二十八歲的長子在眾人簇擁下登上寶座。皇帝只多活了半年,在所謂「西宮南內多秋草」的「南內」興慶宮中,靜靜地去世,諡號「順宗」。此時,二王已成泉下亡魂,八司馬也被新君逐出長安,前往唐帝國的絕域。 永貞時代的政策並非一無可取,尤其在處理藩鎮這件事上被後來的繼任者延續下來,甚至不惜發動了長達十餘年的戰爭—攻打各地藩鎮。
一樣的事,永貞時代沒能取得官僚們的認同,完全地失敗,而繼任的皇帝與官僚們借取經驗,一步一步地把路走好,而被稱為「元和中興」。 「二王八司馬」,是新政府上台後處理永貞時代舊臣的舉措。唐帝國有身分階級,一般而言,除非大逆不道,否則士族通常不太容易被處死,二王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們終究不是士族,而出身士族的八個朝臣則被貶為州司馬,也就是一州的副官。其實,一開始他們是被發出去當刺史,也就是一州的長官,結果在路上再貶一級、被發得更遠,柳宗元就被送到現在湖南和廣西交界的永州當司馬,而且還不是正式的司馬,是「員外同正員」。簡單說,他是個冗員。 這一年,柳宗元三十三歲,從萬眾仰慕的高級官僚,被踢到湖南的山裡當冗員,用肚臍想也知道他不開心。事實上,從三十三歲之後,他的人生像卡到陰一樣衰到極點,媽媽、女兒、姊夫、外甥、姪女、堂弟⋯⋯幾乎稱得上至親的人都去世了。
最慘的是,他堂弟跑來永州看他,路上生了小病,但還能和柳宗元一起出去玩,回來後也有說有笑的,隔天早上卻叫不起來,這才發現斷了氣⋯⋯ 我無法理解,柳宗元到底是命帶天煞孤星還是被草人插針,人生痛苦到這種程度,衰運卻不只如此,他還遇過找不到房子暫居寺廟(可能因為他是冗員或被刻意打壓,永州一開始沒有配宿舍給他)、家裡失火,還一直生病,甚至昏迷三天沒醒。
這麼悲慘的人生,同時造成他在婚姻上的重大挫折。在他二十七歲時,出身名門的妻子去世了,後來二十年都沒有再娶。不是他不想娶,而是娶不到⋯⋯關鍵就在於他是士族,唐帝國中不同階級的人不能結婚,士族男性可以納庶民女性為妾、卻不能為妻,但是以柳宗元的處境,也沒有士族女性要嫁給他。 如果說三十三歲之前的柳宗元是翩翩公子,三十三歲之後的柳宗元就徹底是個魯蛇。他很焦慮自己娶不到老婆又生不出兒子,因此在永貞事件的影響稍微平息、開始有故舊寫信和他聯絡時,他忍不住告訴一位長輩:「我真的好想娶老婆、好怕絕後啊⋯⋯」
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寄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的悲慘自敘讀起來是很可憐啦,但我有時候覺得柳宗元也是神經頗大條,前面說自己好慘、都沒有女孩想跟我一起生寶寶,後面又說自己吃東西也不知道滋味,而且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每次讀到這裡,都讓我有點不舒服—一個不洗澡的男人,誰會介紹長安的白富美給他呢?!有事嗎! * * *
在痛苦的人生中,飲食對柳宗元來說只是拿來苟延殘喘的工具,所以關於吃,他留下的紀錄很少很少,造成我很大的困擾。他和當時的士人們一樣,對南方充滿了恐懼,在他們筆下,南方的夜晚黑壓壓一片,到處都是藤蔓、奇怪的生物,以及吃著噁心食物的土人。
(平衡報導,我認為南方的平民可能也覺得這群官員是一群沒見過世面的城市俗,但很可惜地,南方視角的文字並沒有留下來。) 話雖如此,其實柳宗元很怕自己被南方同化,事實上,他可能還真的已經慢慢被南方給同化了。在前一章,我說過他告訴韓愈自己喜歡吃青蛙,在永州也可能吃過鷓鴣,因為他說口感「甘且腴」,而且很容易就抓得到。
某一天,他家的廚子抓了一籠鷓鴣正準備宰殺,柳宗元經過,想起了自己有如籠中鳥一般的生活,於是,他放走了鷓鴣,並寫詩告訴鷓鴣: 破籠展翅當遠去, 同類相呼莫相顧。 這個情景和韓愈放走那條蛇有點像,或許都是他們在感嘆自己命運,卻也意外留下了飲食史的證據。
柳宗元究竟後來還吃不吃鷓鴣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樣東西,倒是他從元和初年貶到永州之後,就一路吃到柳州⋯⋯ 那就是檳榔。 是的,我想寫到這裡,柳宗元在諸位心中冷豔高貴的形象已經完全毀了—不洗澡、一騷癢滿手汙垢,然後還吃檳榔?!誰要嫁給他呢!
不過,不講衛生這件事雖然不受妹子青睞,但吃檳榔在當時並非惡習,反而是一種高級享受!在漢魏時代,北方朝廷的勢力還沒能完全控制南方時,生長在南方的檳榔是超夢幻的果實,只有皇帝和高官才能看到那麼少少幾顆。直到三國與南朝,北方下來的政權掌控南方,才把檳榔從深山老林裡挖出來,千里迢迢地送到建康城(今南京),用超高級的盤子貢獻給皇帝,皇帝再賜給大臣當作禮物。
也因此南朝的世家大族,開始把吃檳榔當成高級享受,飯後來一顆,健胃整腸助消化。曾經有個魯蛇,在落魄時去老婆娘家求檳榔吃,結果被妻舅嘲笑,後來魯蛇搖身一變成大官,把妻舅叫來,用金盤盛了一堆檳榔請他們吃,完全是打臉打很大;另外有個南朝的親王,平時實在是太愛吃檳榔了,於是過世前特別交代子孫,以後一定要用檳榔祭拜他;還有一個南朝官員,臨死前兒子問他:「老爸,你有什麼心願未了嗎?」他只說:「我要吃一口好檳榔⋯⋯」於是,兒子買了一大堆檳榔現剖,結果剖了一百多顆都不夠好,眼見老爸含恨而終,兒子也從此發誓戒掉檳榔。 除了貴族們,高級的檳榔也可作為供養品送給高僧。不過由於檳榔吃多了人會有點醉,所以佛教僧團內部也曾討論吃檳榔是否合適,結論就是:「因為檳榔可以讓人口氣芬芳,如果吃少少當口香糖沒關係。」
那麼,南朝人怎麼吃檳榔呢?史書上說,他們用扶留藤夾牡蠣殼灰包在一起吃。扶留藤就類似荖葉,而牡蠣灰其實就是石灰⋯⋯等等!這不就是巷口檳榔攤賣的包葉仔白灰檳榔嗎?所以,各位讀者如果想要體驗南朝時尚,不要猶豫,快去檳榔攤享受千年傳統吧。
隋唐之後,因為主要的政治重心被拉回北方,檳榔沒那麼容易取得,所以無法持續高級口香糖的地位,變成一種南方來的藥材,長安的官員們沒事的時候是不會集體在都城吃檳榔的。但是南方的百姓還是繼續開心地吃著檳榔,然後嘲笑從北方來的官員水土不服、上吐下瀉,我想,他們心中可能這麼想:「這群長安俗,我們都是吃檳榔以毒攻毒!所以完全沒事呢!」
接著,北方來的官員們為了在南方活下去,也開始吃起檳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