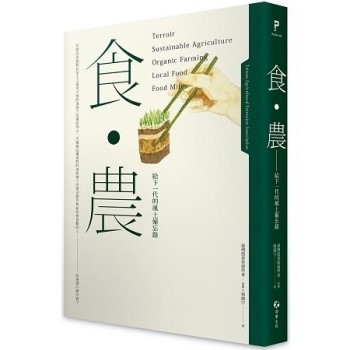推薦序
補上一堂遲到的故鄉學——食.農.風土
陳玠廷(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副研究員)
自有記憶以來,我便是一個在嘉義鄉間踩著泥土長大的小孩;然而,在這個「阮欲來去臺北打拼」價值當道的世代,我也是被從農村推向都市的芸芸眾生中的一分子。由於來自農村,我永遠記得小時候陪著阿公在門口埕曬穀,因散逸在空氣中的稃毛所導致的全身發癢,以及為了躲避西北雨而忙著拉帆布覆蓋稻穀的緊張。這些經驗,也順理成章成了長輩「教誡」我們不好好念書就只能務農的最好素材。但大人們多慮了,逐漸地你會發現整個求學的歷程,像極了一個為了脫離農村的前置作業:為了考上好學校,你得熟記中國各省的物產,以及那些只有在地球儀見過的國家的風土民情。
這樣的劇情與場景,想來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的記憶。如果掉點兒書袋,也就是晚近學術討論對於高度現代發展下,所進行反思最常出現的關鍵詞「斷裂」——人與土地斷裂、都市與鄉村斷裂、文化傳承的斷裂……等。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與家鄉的斷裂並非在空間上我到了臺北求學、工作,而是對於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一無所知。在撰寫論文埋首圖書館蒐集文獻期間,偶然在某期《鄉間小路》的封面上,看到介紹老家鹿草鄉的特產——黃秋葵;在一次不經意的田野經驗中,詫異地發現原來每到冬天,家裡附近田地滿種的芥菜,是全臺最大榨菜廠商的契作,也是在地農民增加從農收入的來源。對於家鄉的物產,我一直停留在小時候看著阿公種水稻、種芭樂、種香瓜、種玉米的印象,幾次的經驗撞擊,才開始讓書本中關於臺灣農糧體制的變遷、農村發展的政策更迭,從平面文字變得立體鮮明。直到多年後接觸了日本食農教育的實踐經驗,才知曉原來認識故鄉的物產、了解父執輩、祖父關於農業的工作經驗,進而對家鄉、對農業建立認同感,是食農教育的重要成效之一。
日本政府於二○○五年公布了〈食育基本法〉後,在文部省、農林水產省、全國農協與各地公私部門的推動下,食育與食農教育一時成為日本各地的全民運動;在臺灣,食農教育也在許多學界、實務界先進的引介下,應著近年來頻仍爆發的食安議題,在臺灣形成浪潮。面對這股看似風起雲湧的食農教育熱潮,我們所關心的,不僅是食農教育該怎麼做,或是如何在猶如盲人摸象的情境下,拼湊出食農教育的全貌。從根本上來說,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是一味跟風,抑或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臺灣推動食農教育的目的為何、欲往何處?為了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成為本書誕生的濫觴。
我與鎮宇相識多年,但一直到了本書的合作,才知道他是一位如此拚命的作者。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鎮宇對歷史經驗資料的爬梳,簡直是前臺大校長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精神的再現。透過他的努力,有系統地在歷史的縱深中抓出臺灣農業之於臺灣社會發展的獨特意義;而晚近各主要國家關於農食議題的實踐經驗,在鎮宇筆下也出現了精彩的對話與交鋒。
在農業領域中,有幾句看似老派卻值得玩味的雋永句子,像是「吾人日進三餐,誰云與農業無關」(If you eat, you a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等等。面對斷裂持續擴大的時代,該如何理解農業的社會價值、連結人與土地的關係?本書以農糧體制與飲食習慣的變遷作為中介,省視日常生活細微處變化積累所產生的影響,絕對是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臺灣這塊土地的重要讀本。
最後,時值我國農業結構調整、重建新農業典範、推動全民農業之際,期盼本書的出版,可以扮演城鄉交流、產消互助的重要媒介。然而,「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這堂遲來的故鄉學該如何上、如何走出後續的實踐,就是本書策劃團隊、作者留給各位讀者的回家作業了。
是為推薦序!
前言
從自己土地上長出來的食農教育
「校外的體驗有其地理、藝術、文學、科學,以及歷史各方面的因素。所有的研究都源自一片土地,以及根植於這片土地上的生命。」——杜威(John Dewey)
我的老家在新竹市香山區的樹下腳,小時候家裡的三合院還沒拆除,午後陽光灑在稻埕上,稻穀日曬後散發出來的香氣,是我最難忘的童年氣味。後來,三合院拆了,老家後的稻田也早已休耕多年。
國小時我隨父母搬到新竹縣竹北市,爸媽開打字行,我則在竹北就讀新社國小。每天上下學我都會經過一家位於中正西路上的新社農藥種子行,店門口常擺些蔬果盆栽,但我從沒進去過,也不曾聽聞學校老師、同學談過這間種子行的事情。直到後來我當了記者,接觸教育、農業領域後,才知道我兒時每天經過的新社種子行大有來頭,他們費心保留及販售在地品種。
現在已經退休的臺大農藝學系教授郭華仁說,這間新社種子行收集的在地品種,非常適合農民市集發展有在地特色的農產品。像是做客家料理的「芋冬瓜」、做雪裡紅的「竹北扁甲刈菜」、做長年菜的「甜大菜」,都是地方特色品種。還有白蘿蔔的地方品種「金交」,客家人用來曬蘿蔔乾,但因為這品種體型小,市面上不容易看到。
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還有一棟黑黑舊舊的老房子,上頭寫著「采田福地」,小時候我只聽過那是間土地公廟。長大才知道「采田福地」是平埔族竹塹社人的祖祠,奉祀竹塹社七姓歷代祖先,而且是清乾隆皇欽賜興建,全臺僅只一家。這是竹塹社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見證。根據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習俗,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與十一月十六日是祭祖的日子,由頭目準備麻糬、酒,以及豬、雞、鴨的生肉為祭品,進行走田(類似賽跑的競技活動)等習俗,跑完後大家聚餐,各吃一片薄生豬肉。但近年來,這些道卡斯族的傳統祭祖儀式已經逐漸式微。
我在撰寫本書時,讀文史工作者劉還月寫恆春半島的故事,裡頭也提到平埔族文化的祭品特色。恆春鎮墾丁路文化巷尾有間「龍鳳鎮寶座」小廟,拜「八寶公主」。這位八寶公主跟白人乘船上岸後被當地的平埔族龜仔甪社殺害有關,傳說八寶公主是登陸船隻船長的太太,遭殺害後身上的八樣寶物被取走,因此被稱為八寶公主。據說八寶公主顯靈託夢給當地漁民,說要留在臺灣,地方上因而蓋小祠恭奉她。每年七月普渡,龍鳳鎮寶座的祭品中有用酒醃的生肉,便可能是受到當地平埔族馬卡道族文化的影響。
新社農藥種子行與采田福地,都在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但我兒時渾然不知它們有什麼特別,直到長大後採訪食農教育主題時才驚覺,原來在地就有珍寶啊!在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最好的資源正是在地的文化傳統及社區居民!
國小階段我沒上過安親班或補習班,只有在小學六年級時,跟朋友去過一堂英文試聽課。當時我的四個堂哥都讀新竹市區的三民國中,因為那所國中剛成立,很注重升學,於是我也被送去那就讀。
剛上國中時,英文老師第一堂課是這麼開場的:「你們小學時應該都去補習班學過KK音標和英文字母,我就不教這些了。」可是我當時完全不會KK音標和英文字母,只好用注音符號強記英文發音。我當時很痛恨英文老師那份「理所當然」的姿態,現在回頭來看,那也是種城鄉差距下的文化衝擊吧。因為課業跟不上進度,我開始補習,國高中生活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補習班度過。
如果受教育讓人跟生長環境變得疏離,到頭來仍得要花上好長一段時間,重新尋回自己的「本色」。假使孩子天天總是往返在上學和補習的途中,那麼對生長環境無所感、對土地沒有眷戀,也就不是太難想像的事情了。
臺灣說大不大,親近大海原野並不算太難,教育的方向應在於維護孩子的「本色化」。臺灣教育改革先驅黃武雄所寫的《童年與解放》和《學校在窗外》,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要維護孩子的主體性,給孩子留白的時空環境,呵護他們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拓展他們的經驗知識。大人的角色應是多帶孩子接觸在地環境,包括飲食、農業、生態、文化傳統等,都是讓孩子成長、豐厚的最佳養分。從自己的生活周遭學習起,也是食農教育的一項目標。
補上一堂遲到的故鄉學——食.農.風土
陳玠廷(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副研究員)
自有記憶以來,我便是一個在嘉義鄉間踩著泥土長大的小孩;然而,在這個「阮欲來去臺北打拼」價值當道的世代,我也是被從農村推向都市的芸芸眾生中的一分子。由於來自農村,我永遠記得小時候陪著阿公在門口埕曬穀,因散逸在空氣中的稃毛所導致的全身發癢,以及為了躲避西北雨而忙著拉帆布覆蓋稻穀的緊張。這些經驗,也順理成章成了長輩「教誡」我們不好好念書就只能務農的最好素材。但大人們多慮了,逐漸地你會發現整個求學的歷程,像極了一個為了脫離農村的前置作業:為了考上好學校,你得熟記中國各省的物產,以及那些只有在地球儀見過的國家的風土民情。
這樣的劇情與場景,想來是我們這個世代共同的記憶。如果掉點兒書袋,也就是晚近學術討論對於高度現代發展下,所進行反思最常出現的關鍵詞「斷裂」——人與土地斷裂、都市與鄉村斷裂、文化傳承的斷裂……等。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與家鄉的斷裂並非在空間上我到了臺北求學、工作,而是對於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一無所知。在撰寫論文埋首圖書館蒐集文獻期間,偶然在某期《鄉間小路》的封面上,看到介紹老家鹿草鄉的特產——黃秋葵;在一次不經意的田野經驗中,詫異地發現原來每到冬天,家裡附近田地滿種的芥菜,是全臺最大榨菜廠商的契作,也是在地農民增加從農收入的來源。對於家鄉的物產,我一直停留在小時候看著阿公種水稻、種芭樂、種香瓜、種玉米的印象,幾次的經驗撞擊,才開始讓書本中關於臺灣農糧體制的變遷、農村發展的政策更迭,從平面文字變得立體鮮明。直到多年後接觸了日本食農教育的實踐經驗,才知曉原來認識故鄉的物產、了解父執輩、祖父關於農業的工作經驗,進而對家鄉、對農業建立認同感,是食農教育的重要成效之一。
日本政府於二○○五年公布了〈食育基本法〉後,在文部省、農林水產省、全國農協與各地公私部門的推動下,食育與食農教育一時成為日本各地的全民運動;在臺灣,食農教育也在許多學界、實務界先進的引介下,應著近年來頻仍爆發的食安議題,在臺灣形成浪潮。面對這股看似風起雲湧的食農教育熱潮,我們所關心的,不僅是食農教育該怎麼做,或是如何在猶如盲人摸象的情境下,拼湊出食農教育的全貌。從根本上來說,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是一味跟風,抑或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臺灣推動食農教育的目的為何、欲往何處?為了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成為本書誕生的濫觴。
我與鎮宇相識多年,但一直到了本書的合作,才知道他是一位如此拚命的作者。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鎮宇對歷史經驗資料的爬梳,簡直是前臺大校長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精神的再現。透過他的努力,有系統地在歷史的縱深中抓出臺灣農業之於臺灣社會發展的獨特意義;而晚近各主要國家關於農食議題的實踐經驗,在鎮宇筆下也出現了精彩的對話與交鋒。
在農業領域中,有幾句看似老派卻值得玩味的雋永句子,像是「吾人日進三餐,誰云與農業無關」(If you eat, you a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等等。面對斷裂持續擴大的時代,該如何理解農業的社會價值、連結人與土地的關係?本書以農糧體制與飲食習慣的變遷作為中介,省視日常生活細微處變化積累所產生的影響,絕對是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臺灣這塊土地的重要讀本。
最後,時值我國農業結構調整、重建新農業典範、推動全民農業之際,期盼本書的出版,可以扮演城鄉交流、產消互助的重要媒介。然而,「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這堂遲來的故鄉學該如何上、如何走出後續的實踐,就是本書策劃團隊、作者留給各位讀者的回家作業了。
是為推薦序!
前言
從自己土地上長出來的食農教育
「校外的體驗有其地理、藝術、文學、科學,以及歷史各方面的因素。所有的研究都源自一片土地,以及根植於這片土地上的生命。」——杜威(John Dewey)
我的老家在新竹市香山區的樹下腳,小時候家裡的三合院還沒拆除,午後陽光灑在稻埕上,稻穀日曬後散發出來的香氣,是我最難忘的童年氣味。後來,三合院拆了,老家後的稻田也早已休耕多年。
國小時我隨父母搬到新竹縣竹北市,爸媽開打字行,我則在竹北就讀新社國小。每天上下學我都會經過一家位於中正西路上的新社農藥種子行,店門口常擺些蔬果盆栽,但我從沒進去過,也不曾聽聞學校老師、同學談過這間種子行的事情。直到後來我當了記者,接觸教育、農業領域後,才知道我兒時每天經過的新社種子行大有來頭,他們費心保留及販售在地品種。
現在已經退休的臺大農藝學系教授郭華仁說,這間新社種子行收集的在地品種,非常適合農民市集發展有在地特色的農產品。像是做客家料理的「芋冬瓜」、做雪裡紅的「竹北扁甲刈菜」、做長年菜的「甜大菜」,都是地方特色品種。還有白蘿蔔的地方品種「金交」,客家人用來曬蘿蔔乾,但因為這品種體型小,市面上不容易看到。
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還有一棟黑黑舊舊的老房子,上頭寫著「采田福地」,小時候我只聽過那是間土地公廟。長大才知道「采田福地」是平埔族竹塹社人的祖祠,奉祀竹塹社七姓歷代祖先,而且是清乾隆皇欽賜興建,全臺僅只一家。這是竹塹社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見證。根據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習俗,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與十一月十六日是祭祖的日子,由頭目準備麻糬、酒,以及豬、雞、鴨的生肉為祭品,進行走田(類似賽跑的競技活動)等習俗,跑完後大家聚餐,各吃一片薄生豬肉。但近年來,這些道卡斯族的傳統祭祖儀式已經逐漸式微。
我在撰寫本書時,讀文史工作者劉還月寫恆春半島的故事,裡頭也提到平埔族文化的祭品特色。恆春鎮墾丁路文化巷尾有間「龍鳳鎮寶座」小廟,拜「八寶公主」。這位八寶公主跟白人乘船上岸後被當地的平埔族龜仔甪社殺害有關,傳說八寶公主是登陸船隻船長的太太,遭殺害後身上的八樣寶物被取走,因此被稱為八寶公主。據說八寶公主顯靈託夢給當地漁民,說要留在臺灣,地方上因而蓋小祠恭奉她。每年七月普渡,龍鳳鎮寶座的祭品中有用酒醃的生肉,便可能是受到當地平埔族馬卡道族文化的影響。
新社農藥種子行與采田福地,都在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但我兒時渾然不知它們有什麼特別,直到長大後採訪食農教育主題時才驚覺,原來在地就有珍寶啊!在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最好的資源正是在地的文化傳統及社區居民!
國小階段我沒上過安親班或補習班,只有在小學六年級時,跟朋友去過一堂英文試聽課。當時我的四個堂哥都讀新竹市區的三民國中,因為那所國中剛成立,很注重升學,於是我也被送去那就讀。
剛上國中時,英文老師第一堂課是這麼開場的:「你們小學時應該都去補習班學過KK音標和英文字母,我就不教這些了。」可是我當時完全不會KK音標和英文字母,只好用注音符號強記英文發音。我當時很痛恨英文老師那份「理所當然」的姿態,現在回頭來看,那也是種城鄉差距下的文化衝擊吧。因為課業跟不上進度,我開始補習,國高中生活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補習班度過。
如果受教育讓人跟生長環境變得疏離,到頭來仍得要花上好長一段時間,重新尋回自己的「本色」。假使孩子天天總是往返在上學和補習的途中,那麼對生長環境無所感、對土地沒有眷戀,也就不是太難想像的事情了。
臺灣說大不大,親近大海原野並不算太難,教育的方向應在於維護孩子的「本色化」。臺灣教育改革先驅黃武雄所寫的《童年與解放》和《學校在窗外》,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要維護孩子的主體性,給孩子留白的時空環境,呵護他們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拓展他們的經驗知識。大人的角色應是多帶孩子接觸在地環境,包括飲食、農業、生態、文化傳統等,都是讓孩子成長、豐厚的最佳養分。從自己的生活周遭學習起,也是食農教育的一項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