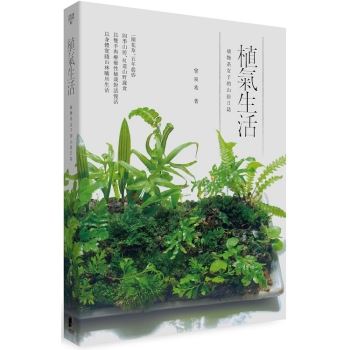居山心願(節錄)
夏季,清晨五點多的朝陽,柔細地,斜射入窗,窗外木瓜樹已競速突破頂框,木瓜大粗葉頂天,把光線篩了一層,多角形的光塊,慢速爬上了床尾,印上了棉鋪,微微聚起熱來。樹蘭的花香味與七里花香,綿密濃郁地隨著風穿進紗窗孔隙,漫進屋內,兩種花香煙霧般嬌嬈互纏(如果它們有形體的話),彼此以味參滲,揉合出了刺鼻的豔香,逸噴滿室,空氣亦突然轉了頻波似的,輕振鼻腔,微觸沉睡系統。
鳥鳴遠近,青空薄雲,大好天色都在試圖喚醒我,而我常是半夢半醒,還在床寐間卻硬是撐開眼眶,想無時差地接收眼前美奐景象,以無遺群覽。青冷灰色調,是夏季清晨溫度的顯色,綿綿灰團透隙著亮光,家中景物隨著我平移的視線,漸漸甦醒、逐一清晰。20℃,是夏季攀升至鎮日高溫的最低起始點,爽涼適溫,沁人肺腑,成為一日的開端,身體頓時化為一具蓄能槽體,大氣能量縈繞,啟動體內各處感應節點,連動、鏈結、通電般的,觸發原有感官認知為高敏度,晨昏持勉,接隙運作。而溼氣潤圍,陽光曳曳灑灑,芭蕉葉揚顫了幾下,幡然如幟旗,裂葉如多足蟲獸,乘著光邁邁飛行。
在海拔540公尺高度,稍稍將人為世界的朦度篩淡了一些,淨抽後的清澄,曝出了朗朗光譜,空氣透晰,頓時將人與物拋擲騰空。稍遠一端,粉色蒜香藤攀上了八米高的南洋杉,細柔飄忽,輕盈置頂,這是我初入住山裡時,每日早晨所感受到的光景。
2011年,因一次訪友之行,來到陽明山竹子湖名為猴崁的山區,在一家野菜餐廳看到對面房子門口掛了張出租貼條,前去探知,一問有兩間獨棟平房要出租,立即敲門入內探視,屋況尚可,便邀了也喜歡居山環境的好友一起入住,一人一棟,一週後把市區房子退租後,就入住猴崁。平時沒常往山裡跑,森林步道也沒走幾條,對於住在非都市的環境裡,還未形成具體的想望,不過,幾次往郊區採集草花、蕨類的經驗,以及在中部山區行走荒山,至今猶存一個人體驗「單獨」的深刻性感受,潛埋體內。再者,在當時租賃地方的後陽台晾衣處,失心瘋似的大肆種了多種盆栽植物;垂花茉莉、玫瑰、育木瓜苗、蕃茄苗與九層塔苗,雖居小盆小土,卻也茂茂然地盎然出苗。其中,種在九吋盆的小棵紫藤也狂奔似的,一路攀到接近天花板的晒衣架上,渴望種植的願力,強烈濃厚到像紫藤一樣戮力往天窗的縫隙裡鑽,滲進骨子裡似的,對應當時生活環境的狹小侷促,想要栽種植物的格局有限,意念卻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到山野之地,願念便從窄小之口傾倒而出,明白唯有居住在更妥適的生長環境,更多自然天候的滋養,植物跟人,才能得以同時快活,自在奔長。
於是,離開了便利的城市生活,入住到竹子湖區的內山小屋,正式成為居山人。一開始原以為交通是最大的問題,身為公車族的我,沒有任何交通工具,要如何進出山區與城市呢?離住家最近的公車站需要穿越野林,一路上坡十幾分鐘,或者連續下坡走林間小道才會到,兩條小路風景實在迷人,我一度以為可以這樣興致高昂沿途賞景,穿越森林去坐公車,但,山區的小巴班次並不多,跟人相約在山下時間時常掐不準,後來,一同居住的鄰居給了我一台摩托車,縮短了交通往來時間,亦開啟了我探尋的旅程。在山路上騎車,沿著彎道沿著樹叢,繞來轉去,爽快無比,尤其在春夏秋三季,山林圍覆、樹林庇蔭下的沁涼溫度,著實讓人身心暢快奔騰,而機動性的行駛,也讓我大致熟悉附近區域環境;騎到頂湖,騎到巴拉卡公路,騎到陽金公路,繞整個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及大屯山系;也騎到文大、平等里、行義路、北投,以住家為中心,把方圓10-20公里的環境內圈繞過一遍,之後的日子,便開始慢慢行腳,一步步走入山中的每一條小路。到了冬季,溫度驟降,時不時就五度以下,覺得需要一台汽車以獲得更大的行動便利,於是入山第二年購入了一台二手福斯,住家內圈腹地也開始往東、往北再擴展到八煙、金山、北海岸,往南也更快速抵達市區了。車拉開了視野空間,幫助身體感受山的幅度與維度,但是車到不了的地方,才是精彩。走路,閒散的走路,走入每一條叢林小徑,走入每一處荒野與未知,那是隔著車窗欣賞群山大景、叢林遍野所觸及不到的細微尺度,就像葉子的纖維脈絡,你必須貼近,貼得非常近,才有辦法一探究竟的領地。
住在山區共五年多,很多時間都在看天看雲,與花草樹木共處,更多時間在散步與探路,五年的時光殖留在小山徑上,塵囂與繁雜思緒似乎也被叢叢樹林阻隔了,像是在進行封印城市記憶般的,偶爾下山才暫時打開一下腦內的海馬迴體,回到家,再封起來。可以試著想像,活在一個生態瓶裡,生態瓶裡面的風光水火土自成一系統,春夏秋三季風光明媚,草花接序而生,冬季嚴寒冷冽,蕭瑟凝凍了萬物,四季分明,晨昏歷歷,依著天候,生息起落有其律則。感覺時間的流動,像煙霧吞吐、稀薄的形貌,簌地忽現忽隱,想要用力辨識其存在感,又一溜煙似蛇形或散霧狀從窗口奔漩而出。
時間,不再追趕我,我也不再視時間為生命唯一的度量衡。
這是我入住山內才慢慢點滴聚合的感知;抽離時間與空間的約制,弛放了自我設定,垮鬆了的生活步調裡,呼吸吐納躍上了存在的軸心。沒有設定目標,也不是從景仰山林奧妙或環抱偉大的田園夢開始的,我唯一有的願力只想要接觸花草並大量種植,雖然後來也沒有成為一個相當專業的種植人就是了,但確定的是,我跟植物終於可以做朋友,用一種看不見的溝通語言;照料,關注,成長,變化,並不時回相予我,我擁有前所未有對生命的欣喜感,要由衷地感激它們長期且始終無聲的存在與陪伴。
務食主義 (節錄)
住在山區,關於食的部分,最不缺的就是民家種植的蔬菜,以及自然生長在山邊的野菜。民家專門種植的蔬菜主要是為了賣給從城市、山下來的觀光客,或是爬山偶然經過的登山客們,友人問我説:「現在有機的品質也堪慮,哪裡還找得到沒有農藥的菜呢?」
我就住在山上的農人圈裡,很明白農友們有很大的收成壓力,因此,或多或少都會施些肥料(動物性居多),或者怕野草過於茂盛,噴點除草劑之類的總是在所難免,如果要在山上吃到沒有農藥味的菜,那麼,我建議可以去摘食山中的野菜。因為,蔓生的野菜,無須照料便可以茂茂然地一直生長,代表的是,它們適合在地的氣候與土壤,也代表著,無須人為的過度照料(施肥、除蟲、移植),也能在這樣的環境內,自成系統、自己找地繁衍,百年生而不滅,這可說是天在賞食啊!
既然天來賞餉,我只有滿懷欣喜地接旨了!
山邊菜市集:六家菜攤
菜攤一號
白太太
攤販年資:三十餘年
擺攤地點:入頂湖的十字路口旁
自家推薦:梅花種白蘿蔔、高麗菜
白太太,從年輕時嫁入山內,脫離城市生活運作後,便開始過著耕種與賣菜的生活,至今已逾三十多年。她跟她先生的菜攤設置地點很巧妙,位居竹子湖要入更高海拔――頂湖的入口處馬路旁,所有入竹子湖的車輛與人群,必定經過此攤,可謂古時候重要的交通驛口。每次散步經過,常看到各大廠牌進口名車一輛輛停在路邊,搖下車窗對著白太太遙指點菜,或者下車親臨菜攤,彎著腰,對著一堆堆白菜蘿蔔青菜,賞玩似的挑選,也順道應景似的殺起價,要菜販多送一把蔥蒜。一條彎曲的白線區劃了白太太攤位的長度與寬度,倒置的塑膠方形菜籃,成了菜攤子的主要架構,上面直排羅列著90%自己栽種的應季蔬果,以及醃漬物,如菜脯、鳳梨豆腐乳、乾刈菜等,主要賣給常常來山上爬山運動與吃飯的熟客、部分觀光客;很多住在山上,在電視上看得到的明星,也都會不時出現在這裡,身著休閒服,素顏,帽簷低低,野趣似的問著哪樣蔬菜怎麼烹煮,有沒有其他的吃法之類的,像下了鄉的貴族,不知民間在時興著什麼樣的食物。
頭戴長版遮陽帽、手套、雨鞋,全副武裝緊緊包裹,以對應炎熱的太陽,或者時不時的濃霧襲來,水氣氤氳 ,將菜攤團團包圍的潮溼天候。白太太 ,除了刮颱風之外,一年四季,每天早上十點前就會出現在這裡,直到傍晚收攤。下雨就用幾支雨傘遮就好了啊,濃霧來了更好,讓客人撥著霧氣挑菜,好像打開家裡的冷凍庫般,有著迎面而來,新鮮的滋味。白太太丹田飽滿的大聲笑著,一邊手不停的把今天從田裡拔起來的刈菜、龍鬚菜捆成一束束,有序的攤開擺放。我是她的常客,第一年搬來山上住的時候,第一次買菜就跟她打熟了,她說她有在蘋果日報看過我,是個她叫不出名字的作家,還因此獲贈了一把紅鳳菜。她與人交談的切入方式很有趣,隨性的問候有著打探你是誰的意味,卻讓人毫無防衛的回應,也許是太多城市來的人們原本意圖遮掩的面紗,被山區自然的氣味給掀開了,重要的是――白太太,一個與大家毫無關聯性的菜販身分,及其敞朗的招呼與笑容,讓人暫時忘了身上原有大大小小賦持的符號。
時值六月天,太陽很大,照著攤子上的菜都在發亮,鮮綠的豐富層次從白太太身後的樟樹與南洋杉,疊迭到前排的菜組來,我最喜歡買她的長豆、山苦瓜與山藥,還有冬天必買的白蘿蔔與高麗菜。她說白山藥要選皮薄、好削皮好處理的,不然整支滑溜溜的,會讓人感到不方便而放棄這道菜,殊不知光是生吃就很營養了耶。與之交易數年後,冬季的某一天,白太太突然授予選高麗菜與梅花蘿蔔的祕訣:高麗菜要選外葉凍到發紫的那種,高麗菜非常喜歡寒冷的環境,因此,越凍越是將其甜度凝結起來,越是可口。而又短又圓的白蘿蔔,則是自家培育留種的梅花品種,30年的梅花種所種出的白蘿蔔,外面可沒得買,全世界只有這攤有。
她私授予我挑菜祕訣,可能是因為我早已是她心中認定的農友。而吾人認為與農家人交誼的玄妙之處與最高峰,不只是起床時打開門,門前攤著一堆他們好意堆疊起來的菜,而是,農家人願意將自家研發的獨門祕種,不藏私的交給我這個年資尚淺的農友來栽種。
夏季,清晨五點多的朝陽,柔細地,斜射入窗,窗外木瓜樹已競速突破頂框,木瓜大粗葉頂天,把光線篩了一層,多角形的光塊,慢速爬上了床尾,印上了棉鋪,微微聚起熱來。樹蘭的花香味與七里花香,綿密濃郁地隨著風穿進紗窗孔隙,漫進屋內,兩種花香煙霧般嬌嬈互纏(如果它們有形體的話),彼此以味參滲,揉合出了刺鼻的豔香,逸噴滿室,空氣亦突然轉了頻波似的,輕振鼻腔,微觸沉睡系統。
鳥鳴遠近,青空薄雲,大好天色都在試圖喚醒我,而我常是半夢半醒,還在床寐間卻硬是撐開眼眶,想無時差地接收眼前美奐景象,以無遺群覽。青冷灰色調,是夏季清晨溫度的顯色,綿綿灰團透隙著亮光,家中景物隨著我平移的視線,漸漸甦醒、逐一清晰。20℃,是夏季攀升至鎮日高溫的最低起始點,爽涼適溫,沁人肺腑,成為一日的開端,身體頓時化為一具蓄能槽體,大氣能量縈繞,啟動體內各處感應節點,連動、鏈結、通電般的,觸發原有感官認知為高敏度,晨昏持勉,接隙運作。而溼氣潤圍,陽光曳曳灑灑,芭蕉葉揚顫了幾下,幡然如幟旗,裂葉如多足蟲獸,乘著光邁邁飛行。
在海拔540公尺高度,稍稍將人為世界的朦度篩淡了一些,淨抽後的清澄,曝出了朗朗光譜,空氣透晰,頓時將人與物拋擲騰空。稍遠一端,粉色蒜香藤攀上了八米高的南洋杉,細柔飄忽,輕盈置頂,這是我初入住山裡時,每日早晨所感受到的光景。
2011年,因一次訪友之行,來到陽明山竹子湖名為猴崁的山區,在一家野菜餐廳看到對面房子門口掛了張出租貼條,前去探知,一問有兩間獨棟平房要出租,立即敲門入內探視,屋況尚可,便邀了也喜歡居山環境的好友一起入住,一人一棟,一週後把市區房子退租後,就入住猴崁。平時沒常往山裡跑,森林步道也沒走幾條,對於住在非都市的環境裡,還未形成具體的想望,不過,幾次往郊區採集草花、蕨類的經驗,以及在中部山區行走荒山,至今猶存一個人體驗「單獨」的深刻性感受,潛埋體內。再者,在當時租賃地方的後陽台晾衣處,失心瘋似的大肆種了多種盆栽植物;垂花茉莉、玫瑰、育木瓜苗、蕃茄苗與九層塔苗,雖居小盆小土,卻也茂茂然地盎然出苗。其中,種在九吋盆的小棵紫藤也狂奔似的,一路攀到接近天花板的晒衣架上,渴望種植的願力,強烈濃厚到像紫藤一樣戮力往天窗的縫隙裡鑽,滲進骨子裡似的,對應當時生活環境的狹小侷促,想要栽種植物的格局有限,意念卻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到山野之地,願念便從窄小之口傾倒而出,明白唯有居住在更妥適的生長環境,更多自然天候的滋養,植物跟人,才能得以同時快活,自在奔長。
於是,離開了便利的城市生活,入住到竹子湖區的內山小屋,正式成為居山人。一開始原以為交通是最大的問題,身為公車族的我,沒有任何交通工具,要如何進出山區與城市呢?離住家最近的公車站需要穿越野林,一路上坡十幾分鐘,或者連續下坡走林間小道才會到,兩條小路風景實在迷人,我一度以為可以這樣興致高昂沿途賞景,穿越森林去坐公車,但,山區的小巴班次並不多,跟人相約在山下時間時常掐不準,後來,一同居住的鄰居給了我一台摩托車,縮短了交通往來時間,亦開啟了我探尋的旅程。在山路上騎車,沿著彎道沿著樹叢,繞來轉去,爽快無比,尤其在春夏秋三季,山林圍覆、樹林庇蔭下的沁涼溫度,著實讓人身心暢快奔騰,而機動性的行駛,也讓我大致熟悉附近區域環境;騎到頂湖,騎到巴拉卡公路,騎到陽金公路,繞整個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及大屯山系;也騎到文大、平等里、行義路、北投,以住家為中心,把方圓10-20公里的環境內圈繞過一遍,之後的日子,便開始慢慢行腳,一步步走入山中的每一條小路。到了冬季,溫度驟降,時不時就五度以下,覺得需要一台汽車以獲得更大的行動便利,於是入山第二年購入了一台二手福斯,住家內圈腹地也開始往東、往北再擴展到八煙、金山、北海岸,往南也更快速抵達市區了。車拉開了視野空間,幫助身體感受山的幅度與維度,但是車到不了的地方,才是精彩。走路,閒散的走路,走入每一條叢林小徑,走入每一處荒野與未知,那是隔著車窗欣賞群山大景、叢林遍野所觸及不到的細微尺度,就像葉子的纖維脈絡,你必須貼近,貼得非常近,才有辦法一探究竟的領地。
住在山區共五年多,很多時間都在看天看雲,與花草樹木共處,更多時間在散步與探路,五年的時光殖留在小山徑上,塵囂與繁雜思緒似乎也被叢叢樹林阻隔了,像是在進行封印城市記憶般的,偶爾下山才暫時打開一下腦內的海馬迴體,回到家,再封起來。可以試著想像,活在一個生態瓶裡,生態瓶裡面的風光水火土自成一系統,春夏秋三季風光明媚,草花接序而生,冬季嚴寒冷冽,蕭瑟凝凍了萬物,四季分明,晨昏歷歷,依著天候,生息起落有其律則。感覺時間的流動,像煙霧吞吐、稀薄的形貌,簌地忽現忽隱,想要用力辨識其存在感,又一溜煙似蛇形或散霧狀從窗口奔漩而出。
時間,不再追趕我,我也不再視時間為生命唯一的度量衡。
這是我入住山內才慢慢點滴聚合的感知;抽離時間與空間的約制,弛放了自我設定,垮鬆了的生活步調裡,呼吸吐納躍上了存在的軸心。沒有設定目標,也不是從景仰山林奧妙或環抱偉大的田園夢開始的,我唯一有的願力只想要接觸花草並大量種植,雖然後來也沒有成為一個相當專業的種植人就是了,但確定的是,我跟植物終於可以做朋友,用一種看不見的溝通語言;照料,關注,成長,變化,並不時回相予我,我擁有前所未有對生命的欣喜感,要由衷地感激它們長期且始終無聲的存在與陪伴。
務食主義 (節錄)
住在山區,關於食的部分,最不缺的就是民家種植的蔬菜,以及自然生長在山邊的野菜。民家專門種植的蔬菜主要是為了賣給從城市、山下來的觀光客,或是爬山偶然經過的登山客們,友人問我説:「現在有機的品質也堪慮,哪裡還找得到沒有農藥的菜呢?」
我就住在山上的農人圈裡,很明白農友們有很大的收成壓力,因此,或多或少都會施些肥料(動物性居多),或者怕野草過於茂盛,噴點除草劑之類的總是在所難免,如果要在山上吃到沒有農藥味的菜,那麼,我建議可以去摘食山中的野菜。因為,蔓生的野菜,無須照料便可以茂茂然地一直生長,代表的是,它們適合在地的氣候與土壤,也代表著,無須人為的過度照料(施肥、除蟲、移植),也能在這樣的環境內,自成系統、自己找地繁衍,百年生而不滅,這可說是天在賞食啊!
既然天來賞餉,我只有滿懷欣喜地接旨了!
山邊菜市集:六家菜攤
菜攤一號
白太太
攤販年資:三十餘年
擺攤地點:入頂湖的十字路口旁
自家推薦:梅花種白蘿蔔、高麗菜
白太太,從年輕時嫁入山內,脫離城市生活運作後,便開始過著耕種與賣菜的生活,至今已逾三十多年。她跟她先生的菜攤設置地點很巧妙,位居竹子湖要入更高海拔――頂湖的入口處馬路旁,所有入竹子湖的車輛與人群,必定經過此攤,可謂古時候重要的交通驛口。每次散步經過,常看到各大廠牌進口名車一輛輛停在路邊,搖下車窗對著白太太遙指點菜,或者下車親臨菜攤,彎著腰,對著一堆堆白菜蘿蔔青菜,賞玩似的挑選,也順道應景似的殺起價,要菜販多送一把蔥蒜。一條彎曲的白線區劃了白太太攤位的長度與寬度,倒置的塑膠方形菜籃,成了菜攤子的主要架構,上面直排羅列著90%自己栽種的應季蔬果,以及醃漬物,如菜脯、鳳梨豆腐乳、乾刈菜等,主要賣給常常來山上爬山運動與吃飯的熟客、部分觀光客;很多住在山上,在電視上看得到的明星,也都會不時出現在這裡,身著休閒服,素顏,帽簷低低,野趣似的問著哪樣蔬菜怎麼烹煮,有沒有其他的吃法之類的,像下了鄉的貴族,不知民間在時興著什麼樣的食物。
頭戴長版遮陽帽、手套、雨鞋,全副武裝緊緊包裹,以對應炎熱的太陽,或者時不時的濃霧襲來,水氣氤氳 ,將菜攤團團包圍的潮溼天候。白太太 ,除了刮颱風之外,一年四季,每天早上十點前就會出現在這裡,直到傍晚收攤。下雨就用幾支雨傘遮就好了啊,濃霧來了更好,讓客人撥著霧氣挑菜,好像打開家裡的冷凍庫般,有著迎面而來,新鮮的滋味。白太太丹田飽滿的大聲笑著,一邊手不停的把今天從田裡拔起來的刈菜、龍鬚菜捆成一束束,有序的攤開擺放。我是她的常客,第一年搬來山上住的時候,第一次買菜就跟她打熟了,她說她有在蘋果日報看過我,是個她叫不出名字的作家,還因此獲贈了一把紅鳳菜。她與人交談的切入方式很有趣,隨性的問候有著打探你是誰的意味,卻讓人毫無防衛的回應,也許是太多城市來的人們原本意圖遮掩的面紗,被山區自然的氣味給掀開了,重要的是――白太太,一個與大家毫無關聯性的菜販身分,及其敞朗的招呼與笑容,讓人暫時忘了身上原有大大小小賦持的符號。
時值六月天,太陽很大,照著攤子上的菜都在發亮,鮮綠的豐富層次從白太太身後的樟樹與南洋杉,疊迭到前排的菜組來,我最喜歡買她的長豆、山苦瓜與山藥,還有冬天必買的白蘿蔔與高麗菜。她說白山藥要選皮薄、好削皮好處理的,不然整支滑溜溜的,會讓人感到不方便而放棄這道菜,殊不知光是生吃就很營養了耶。與之交易數年後,冬季的某一天,白太太突然授予選高麗菜與梅花蘿蔔的祕訣:高麗菜要選外葉凍到發紫的那種,高麗菜非常喜歡寒冷的環境,因此,越凍越是將其甜度凝結起來,越是可口。而又短又圓的白蘿蔔,則是自家培育留種的梅花品種,30年的梅花種所種出的白蘿蔔,外面可沒得買,全世界只有這攤有。
她私授予我挑菜祕訣,可能是因為我早已是她心中認定的農友。而吾人認為與農家人交誼的玄妙之處與最高峰,不只是起床時打開門,門前攤著一堆他們好意堆疊起來的菜,而是,農家人願意將自家研發的獨門祕種,不藏私的交給我這個年資尚淺的農友來栽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