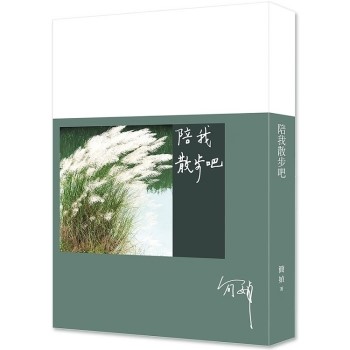散步到芒花深處
有風吹來,眼前一條河堤往雲空的地方蜿蜒而去,望不見盡頭。
埋沒在生活當中,日日像磨坊裡的騾子團團轉,也是望不見盡頭的。柴米油鹽的空隙,塞的是疲憊,難以栽種悠閒。所以,旅行的第一層意義就是把自己綁架出去,脫離軌道,去新的時空變成另一種動物;磨坊騾子變成草原上花蝴蝶,一肩扛家一肩馱負業務的人,變成蹦跳小兔。旅行,通常有個潛藏的傾向,把自己變小,小到像蝌蚪、瓢蟲,不被找到。
誰有用不完的福氣,能常常把自己丟到海角天邊?被數條繩索綁手綁腳的人,南北一日遊都是奢侈的。但疲憊的心需要雨露潤澤,心花才能含苞待放;至於腦,像籠子關滿騷動鳥類,必須找個天高地寬之處打開柵門,讓老鷹、烏鴉說不定也有雲雀一般的思緒,振翅飛出,以免憎恨意識兇猛的獵鷹啄死那隻仁慈的小雲雀。
散步,是自我解救的最佳小路徑,不必訂票無須行李,帶上鑰匙就好。若不幸是從跟人噴火爆油的地方甩門而出,忘了帶鑰匙,回頭去拿會破壞剛剛甩門的戲劇效果,乾脆不回頭好似一個不打算回家的人,也是一種小小的氣魄。
最好有一條長長的樹街,兩邊大樹枝條在半空交握形成隧道,只擋醜陋建築不擋春花秋月;最好有幾條可喜的小巷,經過咖啡小鋪聞到誘人的咖啡香,經過公園,曬太陽的老人依然高聲談笑,走到固定地點,抬頭欣賞愛種花的那戶人家,陽台上豔色九重葛開得像造勢大會……。但這些都比不上離家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河堤。
我與河有緣,童年時沿冬山河騎車追風逐日,落籍台北後,住內湖時民權大橋下是基隆河,住深坑時每日過昇高大橋,常見景美溪畔釣客與白鷺鷥同在,如今移居文山區,景美溪也來到寬闊可親的下游,不像其上游「石碇」、中游「深坑」因河川作用得名那般驚險,河之流程與人的成長有異曲同工之妙,世面見多、年歲夠久,越來越顯得和藹可親。
台灣將近有一百三十條河系,以此張開的水性網絡遍佈全島,浪漫地想,每個人的童年都應該在河邊長大才對,如果沒有,不是河拋棄我們,是我們背叛河。一塊土地,從農耕開發成都市,首先鏟除的必然是山丘與河川,不懂得保留大自然資產的城市,醜得驚人。台灣一直犯這種錯,是以,三十多年前我雖臨基隆河而居,卻無法親近那條又黑又亂的河,移住深坑山莊歲月,山下景美溪常飄來養豬戶排放廢水之臭,後來雖取締,但雜樹叢草掩蓋河灘,亦不易親近。直到十多年前搬來此地,拜自然意識抬頭,台北開始尋找「河川親情」,公部門提撥經費整治河堤,民眾才擁有一條可以騎車、慢跑、散步的堤岸小徑。可嘆,等得都老了。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前四句,曾出現在我中學時一度著迷收集的風景書籤上;一條小河蜿蜒著,兩岸楓林轉紅,天空有飛鳥。配合低迴的詩情,這張紙上風景伴我苦讀,當心緒疲累時便幻想自己躺在岸邊小睡,河水潺潺,楓葉飄落我身。曾經這麼依賴一條想像中的河,或許啟動了冥冥之中的緣法,現實上也有一條河在我最疲累的時候安慰了我。
那是寫《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期間,侍親陪病與案頭寫作衝突,心力交瘁。某日,興之所至散步,走到小巷盡頭見一樓梯,心想應該是堤岸,搬來數年都未走到,不妨一探。
文山區曾淹水,應是為了防洪才修築高堤,堤下便是景美溪,溪畔再修一條河岸小路,如此形成堤頂小徑、河岸小路同行的地貌。這一條有名的單車道,從動物園起程一路可延伸至淡水,騎程約兩三小時。我家附近這段,堤頂僅供步行,岸路較寬可以跑步、騎車。河岸邊為了提供暴雨時河水宣洩之用,相隔甚遠只種幾棵茄冬樹或水黃皮,此外即是草地及河灘零星分佈的芒叢。至於高處堤道,一邊有長條花圃可栽花,另一邊靠大馬路的緩降坡,各色樹木蓊鬱,自成綠雲帶。
有一日,書寫陷入困頓;要採取輕鬆作法將已完成篇章收攏成書,還是拆掉小格局拉出大架構重寫?我坐在河岸,面對晚霞倒映水面,彷彿看著自己的心湖;有陰沉處也有絢爛部分,有潦草處,也有耐得住寂寞的地方,身旁高大的芒叢隨風發出忽強忽弱的窸窣聲,彷彿安慰我︰「撐下去,撐下去,最困難的路段快要過去了……」我領受這不知是來自內心深處的自我鼓舞或是河流贈言,竟有被理解、被擁抱的感動。沉思︰「每本書如同一個人,都是一生僅此一會啊,既然如此,就選擇困難卻輝煌的,好好地與他戀愛、廝守一場吧。」我對著河流許願,讓我完成這本困難之書,出版後我會再來,朗誦給河流聽。書出,再次坐在芒叢邊,為一條河朗讀。「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往日情懷再現,這時躺臥在河邊聽我朗讀的,應該是年少以來陪伴我的那位河流精靈吧。
平靜日常,堤頂散步也是愉悅的。有一次,我專程為認識植物而去,帶一壺咖啡、筆記本,凡不認識的,利用手機軟體查詢。樹群種類頗豐,有︰小葉欖仁、櫻、樟、松、柏、茄冬、海桐、欖仁、水黃皮、白雞油、水杉、烏桕、苦楝、朴樹……,遇一叢十多齡梔子花尤其驚喜。至於植花,堤頂棚架栽著山牽牛,淡紫色垂吊花串像爬屋頂的小頑童,除此之外,零星草花欠缺照料,不多時即出現敗象,頗為遺憾。
大約就在醞釀《我為你灑下月光》期間,又發作了,寫或不寫拉扯著,隨著散步的步伐起落,後來決定寫,書的模樣卻不知從何構思起,宛若大海撈針,常坐在石墩仰望星空,對著月亮釋放思潮。「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之語引我深思;第二次踏入,河已不是之前的河,人也非之前的人。然而,人之所以想再次踏入,不正是因為前一次「未了」嗎?未了的又是什麼?我自行剖析,層層剝去,流露初心。或許,對夜風而言這些藏在頭顱內的思緒都是可吹揚的絮,吹落河面,吹到花圃。不久,發覺堤頂花圃有幾株欠缺照料的玫瑰開花了,我回程時特別會去深深嗅聞其芬芳,得到片刻歡愉。隨著書寫進入如火如荼階段,那條荒廢花圃竟然種著不知自何處移來的含苞玫瑰與百合,一百多株各色品種玫瑰開出盛況,成排的百合花也昂揚綻放,風中香氛流動。某晚,坐在花前椅上,問這條河︰「這是為我種的嗎?」心情甜美至極。蘇東坡<念奴嬌>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原意是「應笑我多情早生華髮」,人生實難,自作多情又何妨,玫瑰呼應書寫,解我疲乏,一路才有月光。
我重新思索旅行與散步有何不同。旅行去到異國他鄉,急於認識新奇環境,自我變小,家常散步只在熟悉地方,感官凝縮,自我放大;一路上處於大腦放空狀態無所思慮,或是思慮甚深沉浸在某項主題之中,步伐起落僅是依照本能而行,像在幫思緒伴奏。是以,旅行適合結伴交換驚奇,散步適合獨行,若要結伴,除非兩人腳步速度合拍,言談主題相同、思緒漣漪交融,若是一人滔滔不絕宣洩其感受,另一人不得不聽,便會壞了散步興致。旅行昂貴,人不會把時間用來訴苦訴冤訴怨,散步免費,常會落入此井。
最讓我嚮往的結伴散步,當屬柏拉圖《費德羅篇》(注)。蘇格拉底偶遇費德羅,問他往哪裡去,費德羅答︰「我在呂西亞斯家坐了整個上午,現在要去城牆外散步。」多美的開始,他們往城外一起散步,打算找個地方好好聽費德羅朗讀呂西亞斯的演說稿。兩人沿著伊利索斯河走,打赤腳,相中一棵大松樹,涉水過河,稱讚溪水清澈透明。以下這一段很迷人,值得引述。
蘇格拉底說︰「這棵松樹如此開枝散葉,高大參天,而一旁的牡荊樹,也如此高大,提供這麼好的樹蔭。況且,眼下正值牡荊花盛開,在這些花的點綴下,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美了。除此之外,松樹旁還潺潺流著令人無法抗拒的溪水,我剛剛用腳試了水溫,想不到溪水如此沁涼。……這條溪流根本是獻給水仙子與阿奇羅(指星河之神)的供品。看!請看看,這裡的空氣如此舒爽。這就是夏天的樂曲啊!溪水與蟬的心聲相互呼應……這片草地實屬當中極品︰坡上草地天然的柔軟讓我們得以伸展全身,讓頭處於最舒適的狀態。」
費德羅讚許他︰「你啊,令人仰慕的男人,你真是這世上最令人費解的人。」
讓我不禁想起《論語》中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再也沒有比倘佯大自然之中更能呼應豐饒的精神世界了,形上國度與自然美景互證,讓我嚮往。讀柏拉圖,發現場景大多在生活中、自然裡,並非正襟危坐在課堂裡辯論,顯示哲思乃在行住坐臥之間,是生活需求的一種,也是自然運行的一部分。來到草坡,蘇格拉底對費德羅說︰「我打算全身舒展開來,躺在這片草地上。而你呢,你就選個你覺得朗讀最舒適的姿勢,等你安頓好,就唸吧。」如此生動,恨不得身在其中,旁聽朗誦。
河岸散步,要是挑剔的毛病犯了,一路上看到的規劃模式不是愛智而是反智;橋邊拉一條很長的LED燈線,晚間變換各色霓虹光,沒有故事,認為河只是水與土石組合而已,民眾只須有平坦的地面追趕跑跳,不須知道一條河的身世。寧願把大片空地切割成各種兒童遊戲區塊,忘了給附近學校佈置一個可以當戶外教室的空間,讓學生有機會在明亮春天來這裡上一堂國文課。
走著走著,不免幻想,如果眼前這一條河的左岸風景屬哲學、歷史,右岸屬詩與藝術,不僅只是步道車道而已,該有多好。如果溪流能夠再度清澈,允許赤腳涉水,還能保留大片原生芒叢,讓沉思者散步到芒花深處,被白鷺鷥、黑冠麻鷺、紅頭綠鳩驚醒,領取一片白茫茫的秋天氣息,那當下的觸動或許能讓疲憊的心恢復元氣,像旭日初升一般。
這是喜愛散步的人不可救藥的幻想吧。慢著,說不定不是幻想,是用另一種樣態存在的情景。有一天,我走到芒花盡處,看見邊坡上三隻喜鵲排成一列,頻頻點頭不知在討論什麼?忽想,是蘇格拉底與費德羅在辯論愛與慾、美與智,僵持不下,找來第三人評評理嗎?那個人是誰?
天啊,難道是我嗎?
注︰引自《論美,論愛︰柏拉圖《費德羅篇》譯註》,孫有蓉著。
end
有風吹來,眼前一條河堤往雲空的地方蜿蜒而去,望不見盡頭。
埋沒在生活當中,日日像磨坊裡的騾子團團轉,也是望不見盡頭的。柴米油鹽的空隙,塞的是疲憊,難以栽種悠閒。所以,旅行的第一層意義就是把自己綁架出去,脫離軌道,去新的時空變成另一種動物;磨坊騾子變成草原上花蝴蝶,一肩扛家一肩馱負業務的人,變成蹦跳小兔。旅行,通常有個潛藏的傾向,把自己變小,小到像蝌蚪、瓢蟲,不被找到。
誰有用不完的福氣,能常常把自己丟到海角天邊?被數條繩索綁手綁腳的人,南北一日遊都是奢侈的。但疲憊的心需要雨露潤澤,心花才能含苞待放;至於腦,像籠子關滿騷動鳥類,必須找個天高地寬之處打開柵門,讓老鷹、烏鴉說不定也有雲雀一般的思緒,振翅飛出,以免憎恨意識兇猛的獵鷹啄死那隻仁慈的小雲雀。
散步,是自我解救的最佳小路徑,不必訂票無須行李,帶上鑰匙就好。若不幸是從跟人噴火爆油的地方甩門而出,忘了帶鑰匙,回頭去拿會破壞剛剛甩門的戲劇效果,乾脆不回頭好似一個不打算回家的人,也是一種小小的氣魄。
最好有一條長長的樹街,兩邊大樹枝條在半空交握形成隧道,只擋醜陋建築不擋春花秋月;最好有幾條可喜的小巷,經過咖啡小鋪聞到誘人的咖啡香,經過公園,曬太陽的老人依然高聲談笑,走到固定地點,抬頭欣賞愛種花的那戶人家,陽台上豔色九重葛開得像造勢大會……。但這些都比不上離家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河堤。
我與河有緣,童年時沿冬山河騎車追風逐日,落籍台北後,住內湖時民權大橋下是基隆河,住深坑時每日過昇高大橋,常見景美溪畔釣客與白鷺鷥同在,如今移居文山區,景美溪也來到寬闊可親的下游,不像其上游「石碇」、中游「深坑」因河川作用得名那般驚險,河之流程與人的成長有異曲同工之妙,世面見多、年歲夠久,越來越顯得和藹可親。
台灣將近有一百三十條河系,以此張開的水性網絡遍佈全島,浪漫地想,每個人的童年都應該在河邊長大才對,如果沒有,不是河拋棄我們,是我們背叛河。一塊土地,從農耕開發成都市,首先鏟除的必然是山丘與河川,不懂得保留大自然資產的城市,醜得驚人。台灣一直犯這種錯,是以,三十多年前我雖臨基隆河而居,卻無法親近那條又黑又亂的河,移住深坑山莊歲月,山下景美溪常飄來養豬戶排放廢水之臭,後來雖取締,但雜樹叢草掩蓋河灘,亦不易親近。直到十多年前搬來此地,拜自然意識抬頭,台北開始尋找「河川親情」,公部門提撥經費整治河堤,民眾才擁有一條可以騎車、慢跑、散步的堤岸小徑。可嘆,等得都老了。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前四句,曾出現在我中學時一度著迷收集的風景書籤上;一條小河蜿蜒著,兩岸楓林轉紅,天空有飛鳥。配合低迴的詩情,這張紙上風景伴我苦讀,當心緒疲累時便幻想自己躺在岸邊小睡,河水潺潺,楓葉飄落我身。曾經這麼依賴一條想像中的河,或許啟動了冥冥之中的緣法,現實上也有一條河在我最疲累的時候安慰了我。
那是寫《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期間,侍親陪病與案頭寫作衝突,心力交瘁。某日,興之所至散步,走到小巷盡頭見一樓梯,心想應該是堤岸,搬來數年都未走到,不妨一探。
文山區曾淹水,應是為了防洪才修築高堤,堤下便是景美溪,溪畔再修一條河岸小路,如此形成堤頂小徑、河岸小路同行的地貌。這一條有名的單車道,從動物園起程一路可延伸至淡水,騎程約兩三小時。我家附近這段,堤頂僅供步行,岸路較寬可以跑步、騎車。河岸邊為了提供暴雨時河水宣洩之用,相隔甚遠只種幾棵茄冬樹或水黃皮,此外即是草地及河灘零星分佈的芒叢。至於高處堤道,一邊有長條花圃可栽花,另一邊靠大馬路的緩降坡,各色樹木蓊鬱,自成綠雲帶。
有一日,書寫陷入困頓;要採取輕鬆作法將已完成篇章收攏成書,還是拆掉小格局拉出大架構重寫?我坐在河岸,面對晚霞倒映水面,彷彿看著自己的心湖;有陰沉處也有絢爛部分,有潦草處,也有耐得住寂寞的地方,身旁高大的芒叢隨風發出忽強忽弱的窸窣聲,彷彿安慰我︰「撐下去,撐下去,最困難的路段快要過去了……」我領受這不知是來自內心深處的自我鼓舞或是河流贈言,竟有被理解、被擁抱的感動。沉思︰「每本書如同一個人,都是一生僅此一會啊,既然如此,就選擇困難卻輝煌的,好好地與他戀愛、廝守一場吧。」我對著河流許願,讓我完成這本困難之書,出版後我會再來,朗誦給河流聽。書出,再次坐在芒叢邊,為一條河朗讀。「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往日情懷再現,這時躺臥在河邊聽我朗讀的,應該是年少以來陪伴我的那位河流精靈吧。
平靜日常,堤頂散步也是愉悅的。有一次,我專程為認識植物而去,帶一壺咖啡、筆記本,凡不認識的,利用手機軟體查詢。樹群種類頗豐,有︰小葉欖仁、櫻、樟、松、柏、茄冬、海桐、欖仁、水黃皮、白雞油、水杉、烏桕、苦楝、朴樹……,遇一叢十多齡梔子花尤其驚喜。至於植花,堤頂棚架栽著山牽牛,淡紫色垂吊花串像爬屋頂的小頑童,除此之外,零星草花欠缺照料,不多時即出現敗象,頗為遺憾。
大約就在醞釀《我為你灑下月光》期間,又發作了,寫或不寫拉扯著,隨著散步的步伐起落,後來決定寫,書的模樣卻不知從何構思起,宛若大海撈針,常坐在石墩仰望星空,對著月亮釋放思潮。「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之語引我深思;第二次踏入,河已不是之前的河,人也非之前的人。然而,人之所以想再次踏入,不正是因為前一次「未了」嗎?未了的又是什麼?我自行剖析,層層剝去,流露初心。或許,對夜風而言這些藏在頭顱內的思緒都是可吹揚的絮,吹落河面,吹到花圃。不久,發覺堤頂花圃有幾株欠缺照料的玫瑰開花了,我回程時特別會去深深嗅聞其芬芳,得到片刻歡愉。隨著書寫進入如火如荼階段,那條荒廢花圃竟然種著不知自何處移來的含苞玫瑰與百合,一百多株各色品種玫瑰開出盛況,成排的百合花也昂揚綻放,風中香氛流動。某晚,坐在花前椅上,問這條河︰「這是為我種的嗎?」心情甜美至極。蘇東坡<念奴嬌>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原意是「應笑我多情早生華髮」,人生實難,自作多情又何妨,玫瑰呼應書寫,解我疲乏,一路才有月光。
我重新思索旅行與散步有何不同。旅行去到異國他鄉,急於認識新奇環境,自我變小,家常散步只在熟悉地方,感官凝縮,自我放大;一路上處於大腦放空狀態無所思慮,或是思慮甚深沉浸在某項主題之中,步伐起落僅是依照本能而行,像在幫思緒伴奏。是以,旅行適合結伴交換驚奇,散步適合獨行,若要結伴,除非兩人腳步速度合拍,言談主題相同、思緒漣漪交融,若是一人滔滔不絕宣洩其感受,另一人不得不聽,便會壞了散步興致。旅行昂貴,人不會把時間用來訴苦訴冤訴怨,散步免費,常會落入此井。
最讓我嚮往的結伴散步,當屬柏拉圖《費德羅篇》(注)。蘇格拉底偶遇費德羅,問他往哪裡去,費德羅答︰「我在呂西亞斯家坐了整個上午,現在要去城牆外散步。」多美的開始,他們往城外一起散步,打算找個地方好好聽費德羅朗讀呂西亞斯的演說稿。兩人沿著伊利索斯河走,打赤腳,相中一棵大松樹,涉水過河,稱讚溪水清澈透明。以下這一段很迷人,值得引述。
蘇格拉底說︰「這棵松樹如此開枝散葉,高大參天,而一旁的牡荊樹,也如此高大,提供這麼好的樹蔭。況且,眼下正值牡荊花盛開,在這些花的點綴下,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美了。除此之外,松樹旁還潺潺流著令人無法抗拒的溪水,我剛剛用腳試了水溫,想不到溪水如此沁涼。……這條溪流根本是獻給水仙子與阿奇羅(指星河之神)的供品。看!請看看,這裡的空氣如此舒爽。這就是夏天的樂曲啊!溪水與蟬的心聲相互呼應……這片草地實屬當中極品︰坡上草地天然的柔軟讓我們得以伸展全身,讓頭處於最舒適的狀態。」
費德羅讚許他︰「你啊,令人仰慕的男人,你真是這世上最令人費解的人。」
讓我不禁想起《論語》中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再也沒有比倘佯大自然之中更能呼應豐饒的精神世界了,形上國度與自然美景互證,讓我嚮往。讀柏拉圖,發現場景大多在生活中、自然裡,並非正襟危坐在課堂裡辯論,顯示哲思乃在行住坐臥之間,是生活需求的一種,也是自然運行的一部分。來到草坡,蘇格拉底對費德羅說︰「我打算全身舒展開來,躺在這片草地上。而你呢,你就選個你覺得朗讀最舒適的姿勢,等你安頓好,就唸吧。」如此生動,恨不得身在其中,旁聽朗誦。
河岸散步,要是挑剔的毛病犯了,一路上看到的規劃模式不是愛智而是反智;橋邊拉一條很長的LED燈線,晚間變換各色霓虹光,沒有故事,認為河只是水與土石組合而已,民眾只須有平坦的地面追趕跑跳,不須知道一條河的身世。寧願把大片空地切割成各種兒童遊戲區塊,忘了給附近學校佈置一個可以當戶外教室的空間,讓學生有機會在明亮春天來這裡上一堂國文課。
走著走著,不免幻想,如果眼前這一條河的左岸風景屬哲學、歷史,右岸屬詩與藝術,不僅只是步道車道而已,該有多好。如果溪流能夠再度清澈,允許赤腳涉水,還能保留大片原生芒叢,讓沉思者散步到芒花深處,被白鷺鷥、黑冠麻鷺、紅頭綠鳩驚醒,領取一片白茫茫的秋天氣息,那當下的觸動或許能讓疲憊的心恢復元氣,像旭日初升一般。
這是喜愛散步的人不可救藥的幻想吧。慢著,說不定不是幻想,是用另一種樣態存在的情景。有一天,我走到芒花盡處,看見邊坡上三隻喜鵲排成一列,頻頻點頭不知在討論什麼?忽想,是蘇格拉底與費德羅在辯論愛與慾、美與智,僵持不下,找來第三人評評理嗎?那個人是誰?
天啊,難道是我嗎?
注︰引自《論美,論愛︰柏拉圖《費德羅篇》譯註》,孫有蓉著。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