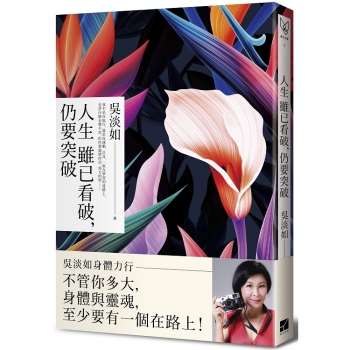8從體育殘障生到馬拉松跑者
莫忘初衷?初衷的真的那麼有價值嗎?
有位前輩出了新書,送給我,上面提了四個字,莫忘初衷。
我沉思了半晌。
有些初衷,發自善良本心,能夠堅持比較好。
但也不是最初的想法都值得堅持,成長和變化,甚或承認錯誤,也是美好人生必須具備的章節。人當然要有一些堅持,但守著某些初衷不變,其實也未必好。
人生的變化很奇妙,未來真不是從前的自己想得到的。
***
少年時我最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中年之後,從四體不勤變成一個運動愛好者。可以跑完全馬,可以在戈壁中行走百公里,更開始鍛鍊肌力,把六塊肌和人魚線當成是自己的夢想,而且還在持續鍛鍊中……(因為不是真的很有天分,所以至今尚未成型。)
我對於運動這件事的初衷,其實是:書呆子没什麼不好,體育殘障生也没關係。
小時候我就不是個喜歡戶外運動的人。讀書的時候,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事,絕對不是任何學科,而是體育,每一次讓我領不到獎學金的理由,就是體育始終拿不到及格成績。
我當時還覺得「五育並重」没道理。而且把自己的肢體反應遲鈍怪到嬰兒期去:「一定是在嬰兒期爸媽没有讓我爬個夠,所以造成我的感覺統合不協調。」
念台大的時候,有一個學期我的體育成績非常高。當時我的手因為過度且姿勢錯誤的練習書法,在關節上長了腫瘤,開了刀,所以我很高興的申請了體育障礙班,和手腳不方便的同學們一起打桌球,羽毛球。那一個學期我在障礙班如魚得水,並且申請到了諸多獎學金。
我還記得高中時我一百公尺要跑二十幾秒,跳高跳不過六十公分,跑四百公尺之後就昏倒了,讓同學送到保健室急救。
我並不引以為恥。年輕的時候,没有想過人會退化:有一天,你不能跑,然後很快就會不能走;不能走,再不多久就不能坐;不能坐之後馬上就得躺,那意味著你的人生自由從此完蛋,臥病在床,哼哼哀哀直到終了。
所有沒有了人口紅利的成熟社會,都把老人長照當成是重要的發展議題。我們不假思索的認為,老人一定要好好的躺很久--其實,北歐國家的老人,在結束生命以前據說平均躺個一兩個月,而華人一躺平均是七八年……。
人到中年,就會發現旁邊有不少朋友,為了要照顧年邁父母,又請不起或請不到貼心照顧者,放棄了一切回家盡孝道;最淒涼的還有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朋友,忽然中風,讓妻兒犧牲一切,為了照顧他,從此再也沒有自己。我覺悟得太晚。雖然旁邊的警鐘一直在響,我始終没有悟到,這些狀況也可能發生在我的人生中。
我的祖母在八十五歲前都是健康寶寶,未曾生過大病,八十五歲時某次騎著單車到公園跳「廣場舞」,暈倒在路上,被人送到醫院,從此漸漸行走不便,臥病在床。她在床上足足躺了十多年,一直到九十多歲,漸漸失去了行動能力、記憶力與語言能力……她的背越來越佝僂,到後來連躺都躺不直了,日日呻吟。醫院的健康檢查報告,卻一切正常。連血壓都如常。
不管子孫如何盡孝道,祖母的痛苦是我們没有辦法代為承受的。雖然非常感激,愛我和我愛的祖母陪我這麼久,但是我十分明白,她的長壽,實在不是福分。
真正的長壽福分,應該像王永慶先生或者畫家劉奇偉先生吧。九十多歲,他們還在打算明天要做些什麼呢,在睡夢中或倏忽間,無疾而終,並無病痛。
人的臟器都有使用年限,醫學再厲害也無法阻擋它的耗盡。現代人的問題老早不在於是否活得久,而在於活得好不好?年老不可怕,死亡也不可怕,因為不管富貴貧賤,不管人生是否活得精彩或無聊,自古誰能免?最可怕的是,如果你還有很多夢想,或你還有幼子老母要養,責任未了,而你的身體卻早早宣告不行。
明白歸明白,知易行難,養成習慣需要的是時間和行動力。這個並不來自於頓悟,來自於慢慢領悟。
身為高齡產婦,我因為各種併發症在醫院躺了一個月,從敗血症中撿回了一條命,最震撼我的事情,不是幾度手術的肌膚之痛,不是身上佈滿針孔,而是躺在病床上的無聊。虛弱躺在床上,無所事事,連書也看不下去;出院後,肌肉無力,經過復健才能像以前一樣的行走。
出院回到家,當時孩子還在加護病房生死未卜……她足足在加病房住了兩個多月。我先回到家,一回家就抱著家裡的貓痛哭,哭的是還可以活著看見牠們,自責的是如果我能把身體弄得健康一點,就算我是高齡產婦,也未必會讓孩子受這樣的苦。
健康是要等失去才珍惜,真理存在老生常談裡,但要親自體會才能徹底明白它的涵義,而真正開始身體力行,恐怕還需要好多聲警鐘的迫切提醒。我真正開始「積極但不太認真」的練跑,都是快五十歲的事了。所幸我的體重在輕重之間差異一直不大,我的膝蓋基本上没有被中年人過重的體重壓垮。
這的確是中年人可否練跑的重要關鍵。我有位同學在大學一畢業後,從六十公斤胖到百餘公斤,在三十歲那年就換了人工關節,在這種零件已經敗壞的狀況下想要從事讓自己煥然一新的運動,的確有困難。
那些在我耳邊嗡嗡嗡勸說「跑步不是好運動,會傷膝蓋」的話,我完全没有聽進去。因為中年人的問題就在於「自己不想,所以勸告別人。」而且不假思索的想要用没有科學驗證的經驗法則來把大家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我在練跑時的願望,其實很卑微,只是想要跑一圈我母校的操場不氣喘噓噓的停下來而已。就是四百公尺而已。
我的初衷只是「四百公尺」,這個卑微的願望竟然是我二十歲時的未竟之志。
跑了幾年,我大概聽過一百個同齡朋友「跑步不是好運動,會傷膝蓋」的勸說,有的非常認真勸我中年人學一學太極拳就好。很幸運的,我的膝蓋看樣子比練跑之前好得多。
我想,並不是因為我天賦異稟。
是因為我在「並不太勉強自己的狀況下」持續進步、慢慢進步。
每次跑步的時候,我都聽見「本我」和「超我」對話的聲音。
「好累!我想回家!」本我說。
「没問題,你只要跑完規定的五公里就可以回家!」超我說:「而且你跑完之後,不但會很有成就感,而且運動後產生的腦內啡會讓你今晚睡得非常舒服!」
「跑操場真的很無聊!」本我說。
「喔,那你可以聽音樂,不知不覺就可以跑完了!」超我是個很好的運動顧問。
說也好笑,我是從跑一百公尺,走一百公尺開始訓練自己的。
剛開始我在台大操場瞎跑,一邊羨慕著在操場上練習的台大田徑隊可以跑得那麼快,當他們像風一樣呼嘯而過時,我還常被嚇了一跳。
當時的「超我」也明白我的體力的確是先天後天都失調,没有做太嚴格的要求,只是希望我「每週跑兩次,每次跑五公里,不管用走的或用爬的,請你完成這個目標」罷了。
那時我是和台大EMBA的學長們一起練跑的。他們年紀和我差不多,但是多數人老早就跑完過全馬。而且成績多半在四個半小時以內。這成績跟人家比當然很自卑。但是人遮掩自己的「不行」絕對不會進步,可喜可賀的是我面對自己的「不行」時,臉皮算厚。
進步的確不會像武俠小說一樣,一個人被某個武林前輩看上,說你天生是練武的奇葩,忽然坐在你背後把真氣都灌給你,然後你就變成了一個一身真氣的武學怪傑。
跑一百走一百,跑兩百走一百,跑四百走一百……在蝸牛般的進步中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還是存在。我的孩子還很小,我一點也不希望,她在正要奮鬥的年紀,每天要忙著到醫院看護插管癱瘓的媽。
這不是悲觀想像,而是我在得過俗稱姙娠毒血症的產婦高血壓後,高血壓這個家族疾病就開始如影隨形的跟著我。翻開我的父系家族史,中風絕對是讓我們到「蘇州賣鴨蛋」的理由。(蘇州賣鴨蛋是我祖母對我解釋為什麼我從來没有看過曾祖父和叔公們的理由,我小時候真以為他們是賣鴨蛋為業的!後來GOOGLE過這句話,合理說法是:它是從台語的口誤產生出來的,台灣人掃墓後會把一些冥紙用石塊壓在墓碑上,再另外把鴨蛋殼撒在墳墓隆起的土丘上,「土丘」的台語念起有點像台語的「蘇州」,於是變成了「蘇州賣鴨蛋」)
我當時真的只想要跑完四百公尺!
跑了一年,我決定參加一次當時覺得「好遠好遠」的十公里跑步。兼具旅遊目的,我比較容易說服自己去跑十公里,於是報名了日本的「神戶馬拉松」,賽前為了擔心自己能否在一小時二十分鐘內跑完,我還緊張得睡不著。
不過是兩年多前,十公里對我還是個壯舉呢。
要進行一件破天荒的事,「本我」是很會給賞的,我告訴自己,如果可以在時間內跑完,就去吃一頓超貴之神戶牛排。
牛排吃了,但跑完那幾天,腿酸到不良於行的地步,回到東京,只要過馬路時綠燈時間剩下不到二十秒,我都乖乖站著等下一次。
現在想想,當時真的「不行」得好笑。
賈永婕當時已經是三鐵達人以及超級馬拉松(二二六公里)的參賽者了,當時她來上我的節目,我笑她沒日沒夜近乎自虐的跑腦子有問題,跟她開玩笑說:「妳老公一定幫妳保了很多險,才會一直鼔勵妳參加各種艱難的比賽。」而且斬釘截鐵跟她說:「我保證我最多只想跑十公里,不用勉勵我!我才不是神經病!」
她後來總没忘記三不五時來取笑我一下。
一個人的初衷,呵呵,如果不曾改變,其實……可能讓一個人很没出息的過下去。
到了中年我才領悟到,不管是在運動,或者是在學習還是理財或開創事業上,只要去掉一個東西,堅持一樣東西,那麼你的人生通常糟不到哪裡去。而且,必然會進步到比你想像中更好。未必能夠出類拔萃,但一定可以超越自己。不管在什麼年齡。
去掉的那個東西,叫「藉口」。
堅持的那一樣東西,叫「紀律」。
14別被勸告大隊帶著走!商人之道如此壯闊
考上上海中歐工商學院時,我曾告訴朋友群說我「又有書可念」了,馬上有一位昔日同窗來相勸:「人到中年,應該要養心,養身,怎麼還往名利場鑽,要看透啊……。」
她認為年紀大了,應該要皈依佛法。我唯一的因應叫做笑而不答。
我只能來個「已讀不回」,一笑置之。顯然她對商學院有很大偏見,覺得那是個俗不可耐的地方。她覺得人到中年就該告老還鄉,虔心禮佛享清福;道不同,又何必開辯論會。
我觀察到:年輕時,大家對於彼此前途,都比較能寬容祝福,到了中年,不知不覺變成了「勸告大隊」一員,勸年輕人還不夠,對於周遭中年人也愛相勸,不管關己.不關己。而且也不在乎自己有無資格,就來送你一個「像關心的教訓」。
喜歡開口教訓別人,是每一代中年人特長。好像人生過了一半,就有資格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但年紀雖然長了,他人生走過的路也未必多。
細數我被「中年人勸告大隊」勸過的事還真多……。
開始練跑,無數中年人來勸你,膝蓋會跑壞,中年人,散個步爬個山坡就好……。
看同齡人工作奔忙,就老來勸:別太累了,賺錢有數,性命要顧……,好像人每天早上起床,悠悠晃一天才是正經。自己出了校門才未必好好看過書,又愛勸誡自己孩子:努力讀書,不然你老大徒傷悲……,但自己年輕時也未好好用功,老了也不熱愛成長。
要勸人,自己要先做到。不是嗎?
中年群組特徵就是常有人貼「怎樣活到一百歲」之類的長青文和勸世文,還有早安圖……
特別愛傳一些没有根據的PO文來勸別人。
我曾訪問過一個營養師,她勸別人要攝取足夠蔬果,別吃宵夜,批評別的專家邪門歪道,當她振振有辭說明中年人每日至少要做三十分鐘心跳超過一百三十下的運動時,我望著眼前有八十多公斤的她,有點發傻。她敏銳的讀出了我的眼神,說:「我是因為太忙,演講太多,做不到……。」
難道我不忙嗎?呵呵。在我看來,說的比唱的好聽的人,別廢話了。
中年人勸告部隊會勸年輕人一出社會就要找個有保障的工作,告訴你大多數食物都有毒,勸你如何對待老公他才不會有外遇,自己親子關係未必好還愛教導別人育兒經,也會勸人世道險惡不知道的不要碰為妙……。
常動不動勸人,背後的原因應該是:腦僵化了,才想用「固定格式」套住別人。
我常常警惕自己,別被勸告大隊帶走,也別加入中年人的勸告大隊!每一代年輕人必須有自己主張,因為他們面對的未來淘汰更加無情。未來,不是「老了,就没用了」,而是「如果你没專長,那麼你很年輕就没用了」,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用嘴申請加入勸告大隊了。
●人生本來就碰碰撞撞,耐撞還要會閃
很多人在年輕時就一路猶豫,選擇大學志願時,通常是最猶豫的時候。
事實上,我只有一個看法,那就是:「能夠考上你想要念的學校或科系,最好,但那也不一定那就是你的未來,你的未來隨時有機會轉彎。總之,面對選擇,不需要太掙扎,選一個有可能愛的,就不用猶豫,努力的念就是了。如果你努力了,真的不愛,那麼,你不要害怕掉頭,也不要吝於更換!」
我們的面前有很多選擇,最可怕的不是你選錯,而是你不選擇。
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原地踏步,什麼執行力也没有,對未來來說,才是最壞的選擇。
還好,我們已經不會被十八歲的志願決定一生,我們充滿自由,只要你做一件事做得好,已經没有人認為你一定要是什麼「科班」出身;没有人規定你做什麼一定要念什麼。
我自己大學念的是法律,畢業了,但我的確對人間律法没有興趣。我肯定學法律這件事的確對我的人生有正面指引,使我變成了一個理性的人。但是否要貢獻一輩子在這裡頭,我實在百分之分不願意。
我當然也猶豫過,要不要考律師法官,這在當時看來是很能享有社會地位的顯赫之路,兩三年後好些同學都考上律師法官,我雖然没有興趣,在校成績實在也不差,還拿過法律系書卷獎,有幾個晚上掙扎到了失眠,要不要也去參加考試?那個時候我正在念被視為「註定會失業」的文學院研究所,心想:如果能夠花個一年半年來準備考試,多個執照,是不是能夠讓我比較被社會看得起一點?
那個一直在勉勵我的超我說:「去吧,只要刻苦一點,你行的。」
本我:「可是我做這個工作,真的不會太開心。你難道不知道我終於畢業,可以不用再翻六法全書時,我有多高興?」
超我:「可是你明明可以的!最近的錄取率放鬆了許多,那些考上的同學其實在校成績都没有你好!」
本我:「拜託你不要這樣比!那不是我要的人生啊,如果我每天起床都要進法院的話,我應該不會活得很愉快!」
超我:「反正你很會考試,你去考,如果考上了,大家都會覺得你好棒棒!」
本我:「我為什麼要讓大家覺得我好棒,而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那樣的生活很棒?」
掙扎了幾個晚上,我放棄了。雖然我一直當「不暢銷作家」直到三十歲,浮浮沉沉好些年,好幾個過年我因為怕聽到冷言冷語,連家都不敢回,能夠訂到去哪裡的機票就去哪裡,但是回想起來,至今我仍然感謝本我的堅持。
不是每一次都要讓那個充滿正面力量的超我獲勝。
方向若不對,加速前進會讓你走更多冤枉路。大道之行也,方向要對才行。
念完中文研究所之後,兩個我也進行過這樣的辯論。我那時候拿到了南部某個知名大學的聘書,超我很高興,本我一點也不想去當老師。老師是個不容易的工作,我教學的愛心和耐心不是没有,但是絕對不夠。每天去同一個學校教同一群人,第二年又教同樣的事,我想到就覺得頭皮發麻。拿到聘書時,我竟然只有虛榮感,完全没有興奮感。
本我又贏了。年輕的我只知道我不想做什麼,並不知道我想做什麼。送到眼前來的機會讓我後來進入報社工作,薪水微薄,但我覺得那個工作至少會讓我每天上班時「意興遄飛」。在完全没有社會經驗的時候,為了升學而讀書,無從明白自己的欠缺,事實上我並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學什麼。不管讀了什麼,都訓練了我,補足了我的某些欠缺。
我還真是「讀了什麼都安然畢業」、但都「真心不打算要做那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