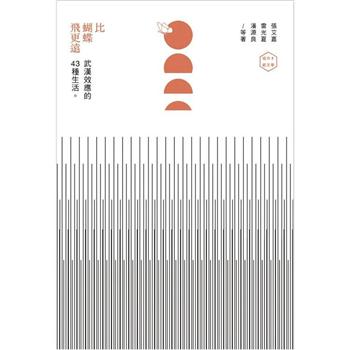<在我記憶中武漢市從來沒有這麼安靜過>
武漢 李繼開
在我記憶中武漢市從來沒有這麼安靜過,最近出門街頭空無一人,前些日子裡微信在傳東湖的野豬都下山了,在二環線上狂奔,也不知是真是假。隨著這次疫情的加重,人們也都習慣了很多事情:比如時常滿天飛的謠言。這段日子裡武漢時不時會出一下冬日的暖陽,溫暖的照在這個世界,仿佛什麼壞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由於人們大都窩在家裡,戶外活動減少,可以看得到天上的鳥明顯多了起來,待在屋子裡的人們看著成群的鳥飛過,多少也會想起這個世界也是屬於牠們的。
一進二0二0年就遇上了這場疫情,之前我足足寫了一個月的論文。人便是這個樣子,真正明白走投無路時心便開始靜了下來,就像這場疫情之初,人們先是由不太在乎到全面恐慌,從最初關在屋裡一星期的沉悶和無處發洩,到習慣於自我保護的長時間足不出戶……這既是沒有辦法,也是在限制中的一種適應。同時知道的是,一方面是安安靜靜待在家裡的人們,另一方面是外邊兒已經亂了套的世界。
想起一月二十三號凌晨打開手機,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方知這次疫情的嚴重,我本打算可以趁春節開車外出轉轉風景,也就全泡湯了。那封城的一兩天也許是比較混亂的時刻,以至於我擔心加油站加不到油,超市會搶購一空,但這一切並沒有發生。至少到目前為止,日常物資供應是充足的。封城通知發布後的一個多星期後的夜晚九點多,我聽到了四周樓房裡傳出的此起彼伏的嘶吼聲,那是很多人在網上約好打開窗戶喊「加油」,這也是一種發洩吧,人們終於被自己關進了各自的籠子裡了。
如此又過了許多天,時而天陰下雨降溫,時而豔陽高照,每天都有壞消息和一些好消息。由於是春節假期的緣故,人們待在家裡也就漸漸習慣了,總比不幸中招躺在醫院或求醫而不得四處奔走的人們幸運。人們很多打算中斷了,很多事情停擺了。武漢三鎮相接連的各個大橋上橋面空空,公汽地鐵全面停運。整個城市空前的安靜,連下雨的唦唦聲都聽得清楚。外出的人們戴著口罩,遠遠看到一個路人也會有意回避,不想給自己和給別人添麻煩。是的,這個事情已經足夠糟糕了。
我每天刷微信朋友圈時覺得這真是一個壞世界,身處日常生活時又覺得和從前相比,只是變安靜和空曠了,少有極端的事情發生被我目睹。當然,我基本上也是足不出戶,因為總是有事情不停在幹,先是繼續修改文章,之後又是開始了被中斷一段時間的繪畫。好在年前囤了不少東西,在物流快遞暫時停擺的現在,還不需要保持以往網上頻繁購物的習慣。
我搬到了我從前的一個工作室去,這裡綠地面積很大,還有南湖環繞,工作室空間也足夠大。我最開始每日晝夜顛倒,漸漸輪回般又倒了回來,現在作息正常且規律。每天看著菜地裡的青菜在生長,好多肥胖的野貓在遊蕩,布穀鳥在不遠處「布穀布穀」的叫,那聲音可以傳得很遠。晴天時黃昏樹林裡麻雀一群一群的嘰嘰喳喳聊天,這可愛的大自然,和從前一樣。
於是在天氣好的時候我開始每天就著陽光畫畫,畫了戴口罩囤貨的人的形象,這年月大家都需要囤點貨,我院子周邊地裡有的白菜青菜胡蘿蔔。有時我想如果蘿蔔葉是豬尾巴,一拽拽出一頭豬來該多好。二0一九年豬肉漲價太厲害了,這場疫情生豬肉價格就更高了。人在物價面前,也是隨波逐流。
每天勞動一下,持續畫畫也是一種充實,想太多也要落在實處去動筆,自己認定的好壞也不太重要了,就當自己是一個勞動的農夫吧。我每天晚上看一兩部電影,這段時間補看了不少從前沒看的影片,電視節目是多少年沒有看過了。想想這段疫情的非常時期也是一個教訓和一次演練,人們已經習慣待在一個安居樂業的世界很長時間了,但世事無常才是恒常之態,當遇到不習慣的事物來臨時還要有吃苦耐勞的準備,這些波動都是每一代人命運的一部分。另外自己也覺得中國人真是天性善良,是易於管理的群族,龐大數字的人群就這樣聽眾號召全窩在家裡,社會的基本面也沒出現大的動盪跡象,客觀來說這真是很難得的表現。這二0二0年一開頭這個世界就不順,澳洲大火、美伊衝突、連科比也離奇去世了……像是夢一樣。
我住的地方離鐵路近,那是一段老鐵路,安安靜靜時經常聽到火車駛過鐵軌的聲音,開得遠了還鳴幾聲笛,聲音和院子裡布穀鳥的「布穀布穀」叫聲一樣傳很遠去,像是這些火車載著過去世界的人和事,經過了我安靜的畫室,然後奔向到未知未來的某個地方去了似的。我一邊聽火車經過的「咣咣噹噹」聲音一邊攪弄著畫筆上的顏料,這讓我覺得有些事情地老天荒,就像人餓了要做飯吃一樣。這些日子由於不能點外賣,外面餐館也關了門,自己簡簡單單弄點一日三餐竟也能耐得下心來了:米飯餃子湯圓麵條……這樣子也挺好的,每天幹這麼多周而復始事情,一件不拉下的話一天竟也滿滿當當,白天一晃而過。我本也是不愛熱鬧的人,有時雖然也不喜歡這樣的日子,但臨到頭也沒有什麼選擇,還是依照習慣去過自己重複日子。畫畫作為勞動可以讓人感到踏實,所以這段時間的繪畫我就直截了當、不假思索的去畫,不去作過多的思考,依靠這副肉身形成的工作習慣只當一種勞動而己,懶得去想那麼多了。每天和筆和顏料打交道,我就是自己小廚房裡的那個不合格的廚子。
這一下子天又黑了下來,一天又要過去了,現在武漢封城已是二十天過去了,全國各地別的城市也都處在嚴控狀況之中,剛剛我從窗戶望出去,看見樹林裡一個人在散步,當他遠遠看到另外一邊走過來一個人時,默默靜悄悄地隱身了。一時間我看得恍恍惚惚的,這些在外透一口氣的遊蕩影子連同這前所未有、無限安靜的天地,竟是我進入二0二0年面臨的最初景象。
〈二月的夢〉
台北 張永霖
這個二月感覺很煩躁,有點與眾不同,但細看分明,這二月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同,人們依舊為生存而爭搶,只是搶取之物,現在多了口罩。
而我依然佛系,不爭不搶不排隊,煩悶時就走到外面抓個寶,感覺日子也沒什麼不同,該發生的依然發生,該不安的還是不安,比較不同的是,這個二月做了比較多的夢,奇奇怪怪的夢。
第一個奇怪的夢是關於螻蟻,一群螻蟻在大地辛勤的工作,為每天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靜的過日子,但突然有一天,一些螻蟻們開始躁動。
螻蟻:「我們為何要當螻蟻,把命運交給老天來決定,我們要反抗,我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就這樣,在這些螻蟻的煽動下,其他的螻蟻也跟著展開行動,他們長出了翅膀,一隻一隻的飛起來,一眨眼間,幾乎就要把天空遮住一半。
就在他們快要把天空遮住,感覺自己不用在看老天臉色時,老天出手了。說出手還真是只有出手,一隻巨大的手突然出現在天上,而特別的是這隻手上竟然還戴著一支手套,手套上有六顆閃亮亮的寶石,看起來就像是《復仇者聯盟》薩諾斯手上的那支無限手套,就這樣這隻手輕輕一握,滿天的螻蟻邊開始紛紛墜落,一群接著一群。
就這樣第一個夢醒了,在一群群紛紛掉落不只是螞蟻還是蝗蟲的夢中醒來。
第二個奇怪的夢,是在離第一個夢沒幾天發生的。夢中我來到一個漆黑的山洞,而不知為何,在這不見五指的漆黑中,我還能看見兩隻黑色的蝙蝠,但也可能我就是兩隻蝙蝠中的一隻,但不管我是怎樣的身分,存在這個夢境中,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蝙蝠一:「我們要不要來搞一下?」
蝙蝠二:「不太好吧!」
蝙蝠一:「為什麼?」
蝙蝠二:「我發現我有愛滋!」
蝙蝠一:「你是跑去森林跟狐猴亂搞嗎?」
蝙蝠二:「不是,是我白天睡覺時,有人來搞我。」
蝙蝠一:「人真是亂來啊!什麼都能搞。」
蝙蝠二:「是啊!人類什麼都能搞。」
而我就在「人類什麼都能搞……。」這句話不斷REPEAT的回音中醒來,這是我做的第二個夢。
第三個夢,是我在看完一部歐美的愛情電影後做的,為何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這個夢就是電影裡的男女主角主演的,他們就這樣在我的夢裡出現,在他們電影中的那個公園,女主角依然穿著綠色精靈的衣服,兩人坐在公園長椅上,而男主角深情款款地看著女主角。
男主角:「我愛你,我願意把我的一切都給你。」
女主角:「我不要你的一切,我只要你臉上的口罩。」
就在這刻男主角的臉上突然多出了一副口罩,而在女主角的要求說出要求時,男主角瞬間起身轉身,落荒而逃。
就這樣第三個夢醒了,我依稀記得那天的日子,二月十四日,是情人節,一個特別的日子。
第四個夢,則是關於排隊,這個夢我之所以會記得清楚,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排隊的人,但我發現我在夢中排隊時,我便把這個夢記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在排隊,而且這個隊伍很長,感覺怎麼排都排不完,前面好像不停地有人插隊,怎麼排前面都是長長的人龍,我問我自己為何要在這排隊,突然聽見了自己對自己的回答:「你是想要知道前面到底發生什麼而排隊。」
就這樣不知排了多久,我終於看見大家在排什麼,前面有一個火葬場的大火爐,而這些前面排隊的人,正一個一個的自動跳進火爐中,眼看很快就要輪到我,我著急地想要從隊伍中逃脫,卻發現自己被前後的人夾得緊緊的,就這樣,我一步步地靠進火爐,我拼命的掙扎,就這樣我醒了過來,滿身的大汗。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都祈禱自己不要再做這樣的夢,最好不要再作夢,但沒想到幾天後還是夢了。
但這次夢的開場很歡樂,是在一個色彩繽紛的童話王國,一個隊伍正在遊行,
遊行的主角是一個沒穿衣服但戴著王冠的國王,國王所到之處民眾都熱烈的鼓掌歡迎,國王的身材有點胖,臉長得有像包子,但他顯然很滿意自己的身材,一邊走一邊擺出健美選手的姿勢,群眾們也不停的熱烈鼓掌。就在不知何時,國王的身旁突然多了一個袋子,國王伸手從袋子裡抓東西丟向群眾,群眾紛紛伸手搶接,接到手發現,竟然是一個個王冠,剛接的手的群眾開始很開心,但接著一個個開始口吐白沫臉發黑的倒在地上,四下的群眾開始驚叫奔跑,想躲開丟過來的王冠,但王冠太密集了,沒人躲得掉,大家紛紛倒地,這時我感覺一個皇冠正丟向我,我想躲開,但還是被扔到,我再度驚叫地從夢中醒來,滿頭大汗。
就這樣,整個二月都在做些莫名其妙的夢,只是有的記得清,有些記不清,但是醒來時都會有一種共同的情緒,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憤怒,覺得自己好像回到青春叛逆期時的自己,覺得這世界早該毀滅,人就是這地球的癌細胞。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中二,但我覺得自己的這個二月很中二。
想寫這篇文章的昨晚,我其實又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詩人,在一片雪白的大地,伸出雙手,迎接一片片從天上飄落的雪花,他認為那一片片的雪花,是倉促離開人世,來不及跟親人告別的人的靈魂,而同時遠方南方的島嶼上,一個穿著國中生制服的老人,看著陽光普照的窗外,想像著遠方那一場大雪,而身邊老舊的收音機正播放著氣象預告:「天氣預報!天氣預報!暴雪將至,暴雪將至,之後慎防烈日灼身。」
武漢 李繼開
在我記憶中武漢市從來沒有這麼安靜過,最近出門街頭空無一人,前些日子裡微信在傳東湖的野豬都下山了,在二環線上狂奔,也不知是真是假。隨著這次疫情的加重,人們也都習慣了很多事情:比如時常滿天飛的謠言。這段日子裡武漢時不時會出一下冬日的暖陽,溫暖的照在這個世界,仿佛什麼壞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由於人們大都窩在家裡,戶外活動減少,可以看得到天上的鳥明顯多了起來,待在屋子裡的人們看著成群的鳥飛過,多少也會想起這個世界也是屬於牠們的。
一進二0二0年就遇上了這場疫情,之前我足足寫了一個月的論文。人便是這個樣子,真正明白走投無路時心便開始靜了下來,就像這場疫情之初,人們先是由不太在乎到全面恐慌,從最初關在屋裡一星期的沉悶和無處發洩,到習慣於自我保護的長時間足不出戶……這既是沒有辦法,也是在限制中的一種適應。同時知道的是,一方面是安安靜靜待在家裡的人們,另一方面是外邊兒已經亂了套的世界。
想起一月二十三號凌晨打開手機,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方知這次疫情的嚴重,我本打算可以趁春節開車外出轉轉風景,也就全泡湯了。那封城的一兩天也許是比較混亂的時刻,以至於我擔心加油站加不到油,超市會搶購一空,但這一切並沒有發生。至少到目前為止,日常物資供應是充足的。封城通知發布後的一個多星期後的夜晚九點多,我聽到了四周樓房裡傳出的此起彼伏的嘶吼聲,那是很多人在網上約好打開窗戶喊「加油」,這也是一種發洩吧,人們終於被自己關進了各自的籠子裡了。
如此又過了許多天,時而天陰下雨降溫,時而豔陽高照,每天都有壞消息和一些好消息。由於是春節假期的緣故,人們待在家裡也就漸漸習慣了,總比不幸中招躺在醫院或求醫而不得四處奔走的人們幸運。人們很多打算中斷了,很多事情停擺了。武漢三鎮相接連的各個大橋上橋面空空,公汽地鐵全面停運。整個城市空前的安靜,連下雨的唦唦聲都聽得清楚。外出的人們戴著口罩,遠遠看到一個路人也會有意回避,不想給自己和給別人添麻煩。是的,這個事情已經足夠糟糕了。
我每天刷微信朋友圈時覺得這真是一個壞世界,身處日常生活時又覺得和從前相比,只是變安靜和空曠了,少有極端的事情發生被我目睹。當然,我基本上也是足不出戶,因為總是有事情不停在幹,先是繼續修改文章,之後又是開始了被中斷一段時間的繪畫。好在年前囤了不少東西,在物流快遞暫時停擺的現在,還不需要保持以往網上頻繁購物的習慣。
我搬到了我從前的一個工作室去,這裡綠地面積很大,還有南湖環繞,工作室空間也足夠大。我最開始每日晝夜顛倒,漸漸輪回般又倒了回來,現在作息正常且規律。每天看著菜地裡的青菜在生長,好多肥胖的野貓在遊蕩,布穀鳥在不遠處「布穀布穀」的叫,那聲音可以傳得很遠。晴天時黃昏樹林裡麻雀一群一群的嘰嘰喳喳聊天,這可愛的大自然,和從前一樣。
於是在天氣好的時候我開始每天就著陽光畫畫,畫了戴口罩囤貨的人的形象,這年月大家都需要囤點貨,我院子周邊地裡有的白菜青菜胡蘿蔔。有時我想如果蘿蔔葉是豬尾巴,一拽拽出一頭豬來該多好。二0一九年豬肉漲價太厲害了,這場疫情生豬肉價格就更高了。人在物價面前,也是隨波逐流。
每天勞動一下,持續畫畫也是一種充實,想太多也要落在實處去動筆,自己認定的好壞也不太重要了,就當自己是一個勞動的農夫吧。我每天晚上看一兩部電影,這段時間補看了不少從前沒看的影片,電視節目是多少年沒有看過了。想想這段疫情的非常時期也是一個教訓和一次演練,人們已經習慣待在一個安居樂業的世界很長時間了,但世事無常才是恒常之態,當遇到不習慣的事物來臨時還要有吃苦耐勞的準備,這些波動都是每一代人命運的一部分。另外自己也覺得中國人真是天性善良,是易於管理的群族,龐大數字的人群就這樣聽眾號召全窩在家裡,社會的基本面也沒出現大的動盪跡象,客觀來說這真是很難得的表現。這二0二0年一開頭這個世界就不順,澳洲大火、美伊衝突、連科比也離奇去世了……像是夢一樣。
我住的地方離鐵路近,那是一段老鐵路,安安靜靜時經常聽到火車駛過鐵軌的聲音,開得遠了還鳴幾聲笛,聲音和院子裡布穀鳥的「布穀布穀」叫聲一樣傳很遠去,像是這些火車載著過去世界的人和事,經過了我安靜的畫室,然後奔向到未知未來的某個地方去了似的。我一邊聽火車經過的「咣咣噹噹」聲音一邊攪弄著畫筆上的顏料,這讓我覺得有些事情地老天荒,就像人餓了要做飯吃一樣。這些日子由於不能點外賣,外面餐館也關了門,自己簡簡單單弄點一日三餐竟也能耐得下心來了:米飯餃子湯圓麵條……這樣子也挺好的,每天幹這麼多周而復始事情,一件不拉下的話一天竟也滿滿當當,白天一晃而過。我本也是不愛熱鬧的人,有時雖然也不喜歡這樣的日子,但臨到頭也沒有什麼選擇,還是依照習慣去過自己重複日子。畫畫作為勞動可以讓人感到踏實,所以這段時間的繪畫我就直截了當、不假思索的去畫,不去作過多的思考,依靠這副肉身形成的工作習慣只當一種勞動而己,懶得去想那麼多了。每天和筆和顏料打交道,我就是自己小廚房裡的那個不合格的廚子。
這一下子天又黑了下來,一天又要過去了,現在武漢封城已是二十天過去了,全國各地別的城市也都處在嚴控狀況之中,剛剛我從窗戶望出去,看見樹林裡一個人在散步,當他遠遠看到另外一邊走過來一個人時,默默靜悄悄地隱身了。一時間我看得恍恍惚惚的,這些在外透一口氣的遊蕩影子連同這前所未有、無限安靜的天地,竟是我進入二0二0年面臨的最初景象。
〈二月的夢〉
台北 張永霖
這個二月感覺很煩躁,有點與眾不同,但細看分明,這二月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同,人們依舊為生存而爭搶,只是搶取之物,現在多了口罩。
而我依然佛系,不爭不搶不排隊,煩悶時就走到外面抓個寶,感覺日子也沒什麼不同,該發生的依然發生,該不安的還是不安,比較不同的是,這個二月做了比較多的夢,奇奇怪怪的夢。
第一個奇怪的夢是關於螻蟻,一群螻蟻在大地辛勤的工作,為每天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靜的過日子,但突然有一天,一些螻蟻們開始躁動。
螻蟻:「我們為何要當螻蟻,把命運交給老天來決定,我們要反抗,我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就這樣,在這些螻蟻的煽動下,其他的螻蟻也跟著展開行動,他們長出了翅膀,一隻一隻的飛起來,一眨眼間,幾乎就要把天空遮住一半。
就在他們快要把天空遮住,感覺自己不用在看老天臉色時,老天出手了。說出手還真是只有出手,一隻巨大的手突然出現在天上,而特別的是這隻手上竟然還戴著一支手套,手套上有六顆閃亮亮的寶石,看起來就像是《復仇者聯盟》薩諾斯手上的那支無限手套,就這樣這隻手輕輕一握,滿天的螻蟻邊開始紛紛墜落,一群接著一群。
就這樣第一個夢醒了,在一群群紛紛掉落不只是螞蟻還是蝗蟲的夢中醒來。
第二個奇怪的夢,是在離第一個夢沒幾天發生的。夢中我來到一個漆黑的山洞,而不知為何,在這不見五指的漆黑中,我還能看見兩隻黑色的蝙蝠,但也可能我就是兩隻蝙蝠中的一隻,但不管我是怎樣的身分,存在這個夢境中,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蝙蝠一:「我們要不要來搞一下?」
蝙蝠二:「不太好吧!」
蝙蝠一:「為什麼?」
蝙蝠二:「我發現我有愛滋!」
蝙蝠一:「你是跑去森林跟狐猴亂搞嗎?」
蝙蝠二:「不是,是我白天睡覺時,有人來搞我。」
蝙蝠一:「人真是亂來啊!什麼都能搞。」
蝙蝠二:「是啊!人類什麼都能搞。」
而我就在「人類什麼都能搞……。」這句話不斷REPEAT的回音中醒來,這是我做的第二個夢。
第三個夢,是我在看完一部歐美的愛情電影後做的,為何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這個夢就是電影裡的男女主角主演的,他們就這樣在我的夢裡出現,在他們電影中的那個公園,女主角依然穿著綠色精靈的衣服,兩人坐在公園長椅上,而男主角深情款款地看著女主角。
男主角:「我愛你,我願意把我的一切都給你。」
女主角:「我不要你的一切,我只要你臉上的口罩。」
就在這刻男主角的臉上突然多出了一副口罩,而在女主角的要求說出要求時,男主角瞬間起身轉身,落荒而逃。
就這樣第三個夢醒了,我依稀記得那天的日子,二月十四日,是情人節,一個特別的日子。
第四個夢,則是關於排隊,這個夢我之所以會記得清楚,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排隊的人,但我發現我在夢中排隊時,我便把這個夢記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在排隊,而且這個隊伍很長,感覺怎麼排都排不完,前面好像不停地有人插隊,怎麼排前面都是長長的人龍,我問我自己為何要在這排隊,突然聽見了自己對自己的回答:「你是想要知道前面到底發生什麼而排隊。」
就這樣不知排了多久,我終於看見大家在排什麼,前面有一個火葬場的大火爐,而這些前面排隊的人,正一個一個的自動跳進火爐中,眼看很快就要輪到我,我著急地想要從隊伍中逃脫,卻發現自己被前後的人夾得緊緊的,就這樣,我一步步地靠進火爐,我拼命的掙扎,就這樣我醒了過來,滿身的大汗。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都祈禱自己不要再做這樣的夢,最好不要再作夢,但沒想到幾天後還是夢了。
但這次夢的開場很歡樂,是在一個色彩繽紛的童話王國,一個隊伍正在遊行,
遊行的主角是一個沒穿衣服但戴著王冠的國王,國王所到之處民眾都熱烈的鼓掌歡迎,國王的身材有點胖,臉長得有像包子,但他顯然很滿意自己的身材,一邊走一邊擺出健美選手的姿勢,群眾們也不停的熱烈鼓掌。就在不知何時,國王的身旁突然多了一個袋子,國王伸手從袋子裡抓東西丟向群眾,群眾紛紛伸手搶接,接到手發現,竟然是一個個王冠,剛接的手的群眾開始很開心,但接著一個個開始口吐白沫臉發黑的倒在地上,四下的群眾開始驚叫奔跑,想躲開丟過來的王冠,但王冠太密集了,沒人躲得掉,大家紛紛倒地,這時我感覺一個皇冠正丟向我,我想躲開,但還是被扔到,我再度驚叫地從夢中醒來,滿頭大汗。
就這樣,整個二月都在做些莫名其妙的夢,只是有的記得清,有些記不清,但是醒來時都會有一種共同的情緒,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憤怒,覺得自己好像回到青春叛逆期時的自己,覺得這世界早該毀滅,人就是這地球的癌細胞。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中二,但我覺得自己的這個二月很中二。
想寫這篇文章的昨晚,我其實又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詩人,在一片雪白的大地,伸出雙手,迎接一片片從天上飄落的雪花,他認為那一片片的雪花,是倉促離開人世,來不及跟親人告別的人的靈魂,而同時遠方南方的島嶼上,一個穿著國中生制服的老人,看著陽光普照的窗外,想像著遠方那一場大雪,而身邊老舊的收音機正播放著氣象預告:「天氣預報!天氣預報!暴雪將至,暴雪將至,之後慎防烈日灼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