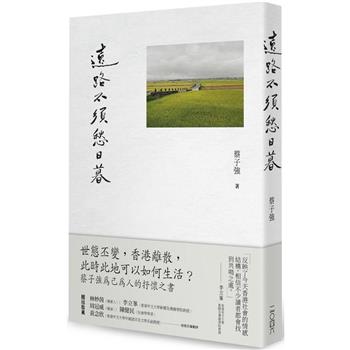序:躺平.儒道互補
曾經有高官批評社會出現「躺平主義」,說是消極心態,令人萎靡不振,長遠窒礙社會進步云云。
但我又記得,中學時的中文課,有收錄陶淵明的〈 歸園田居〉,其實這不就是古時的「躺平」嗎?
「躺平」原是內地網絡潮語,指有年輕人在經濟下滑、階級上流困難下,與其跟從社會期望奮發向上,倒不如「躺平」,無欲無求,「不買房、不買車、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剝削的奴隸」。
其實在日本,亦有類似說法,稱之為「草食男」。
「躺平」原本指的是一種經濟和生活上的態度,但逐漸,它也成了一種政治態度。
二〇二二年五月,上海因疫情封城個多月,民眾怨聲載道,一段網上流傳視頻,引發廣泛熱議。視頻上看見,一對據說核酸檢測屬陰性的年輕夫婦,被一群衣服印有「警察」二字的「大白」圍着,要強拉他們往方艙隔離,兩人不肯,「大白」威脅說:「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治安處罰。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
豈料,男子卻平靜地回答,說:「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近年香港政局驟變,很多年輕人,不單是買不起樓,且就算想發聲、想有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想爭取民主自由,卻發現處處紅線。於是,也就罷了,索性「躺平」。
二〇二三年八月尾,日本即將排放福島核污水,本地電視新聞作街頭訪問, 問市民會否擔心日本水產安全,年輕男子林先生說他一直有買刺身等日本水產, 但完全不擔心。
「點解唔擔心?」(為何不擔心?)
「我哋唔諗住有下一代。」(我們不打算有下一代。)
莫非這就是「終極躺平」?我不知道。
不單年輕人,就算我們知識份子,彼此都苦笑說,時局如斯,難有作為,當下也只能選擇「躺平」,先避其鋒,做一下「竹林七賢」。
其實這也是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行徑,這種逆境時的調整,有學者稱之為「儒道互補」,說的是,雖然儒和道在處世態度和精神面貌上,看似相反,前者主張入世、有為、積極;後者則主張出世、無為、順其自然,但兩者卻能並存, 且成讀書人的精神支柱。
由儒入道,再由道入儒,得志時是儒家,失意時是道家,成了中國讀書人的雙重性格,也是他們調整自己、適應時局的方法,讓他們多了韌力。
時局有可為時,信的是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當時局崩壞,仕途失意,無能為力時,則改信道家,以至退隱山林,就像陶淵明一樣。
就是這樣,道家(也就是「躺平」)成了那些失意、無力改變現實的讀書人, 精神上的避風港,也只有這樣的調整,他們才在逆境下仍能自處。
以前我在《 明報》寫政論,如今在《 明報》改寫副刊,多少也是這樣的心態。
但後來我又發現,身處困厄的朋友,能夠見見家人朋友,以及好好讀報,已經是他們日常僅有的寄託。見面時,不少都說有看我的專欄,鼓勵我要好好寫下去。
我做不到每週去探望他們,於是寫好《 明報》內這個專欄,也成了義不容辭之舉,希望能夠給朋友點點撫慰。
過去幾年,社會氣氛低迷,自己也愁腸百結,鬱悶難解,把自己寫在這個年代的文章結集,也把自己的心境、情懷、鬱結記下,也算是為一個時代留下註腳。
一、一蓑煙雨任平生
下次你路過,人間已無我
「下次你路過,人間已無我」,這是余光中先生寫給哈雷彗星的兩句詩,第一次讀到時,只覺一份穿透時空的蒼涼。
哈雷是顆週期彗星,每隔約七十五年路經地球一次,它的璀璨,讓人類從地球上用肉眼也可直接看到。哈雷下次崔護重來,估計將會是二O六一年,而上次, 則是一九八六年。那年我剛巧「上莊」,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學生會,風華正茂,志氣昂揚,對香港回歸、非殖、民主化,都充滿憧憬。
上了年紀,總愛懷緬過去。近日,約了幾位昔日學生會、學生報好友,重遊中大。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為各自事業和理想打拼,雖然偶有見面,但再在校園內聚首一堂,今趟卻是頭一次。我帶他們看中大的「新」景點,如新亞書院的天人合一池、聯合書院的校史館、和聲書院的無敵靚景咖啡館……但他們最想去的,還是昔日大家並肩作戰、過了無數晨昏顛倒日子的學生會和學生報舊址。
過去幾年,歷盡風波,學生會和學生報都已經被迫解散,如今人去樓空,只剩一堆遺棄雜物。撫今追昔,大家都有說不出的感慨。在這堆遺物中,我們意外發現了一些資料冊和錄影帶,是當年我們製作來向同學介紹政制改革,如爭取八八直選、《 基本法》草擬等,一時間,大家百感交集。我相信其它記錄了近年抗爭的遺物,早已被人檢走,唯獨是這些物件,卻無人問津,或甚至棄如敝屣, 那是一個大家對回歸、非殖、民主化,都充滿憧憬的年代。
(順帶一提,當時《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委員是戴耀廷,那時他被一些同學批評「走入中方建制」。)
離開中大前,我們去了二號橋一趟,無語。
一九八六年,我出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一年後再出任會長),那年香港大學(港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是葉健民。早前,他辭去城市大學(城大)教席, 移居英國,在彼邦延續其學術路,盼為研究留住點香火。臨行前,他接受《 明報》 專訪,被問到香港民主前景,他答:「我不覺得我這代人會看到。」
同意,就如哈雷彗星一樣。
最不幸是無聊一生甚麼也沒信過
近日鄭海泉逝世,享年七十四歲。鄭是我中大學長,我跟他並不相識,但對他卻有一份敬意,不在於他曾經位極人臣,是首位匯豐銀行華人大班,事實上飛黃騰達的師兄多的是,我敬他,是因為他也是學運出身,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 更重要的是,他出人頭地後,始終不忘初心,對學運仍舊肯定。他說:「最不幸的是無無聊聊過了一生,甚麼也沒信過。」
十一年前,《 中大通訊》(第382 期)曾對這首位出任中大校董會主席的校友, 作了一個專訪,當中憶述到在大學「火紅的年代」之學運生涯時,他說:
「年輕人只道這個世界有不公義,我們便要鬥爭。我們有時(……)學生就是這樣的,正義感掩蓋了一切,非黑即白。這類衝擊是人生寶貴的一課。找到自己的信念,或曾經追尋過你的信念,是最有福的。最不幸的是無無聊聊過了一生, 甚麼也沒信過。我是無悔的,不過,作為過來人,我仍想指出無論從事任何運動,無須用侮辱對方作為表達意見或爭取的手段,也無須妨礙他人的權利。必須多點聆聽你的『敵人』,細心觀察或從別人的角度去審視問題,尊重對方。侮辱性的言語或行動會適得其反,令本來同情你的因而不接受你的意見。」
這段話今天聽來依然擲地有聲。
因為並無交往,所以上星期其喪禮我並沒有去,但事後卻有看悼念特刊,當中有各界人士憶述其生平點滴,看後,對這位師兄又多了點認識和尊敬。
其中一篇提到,鄭早年曾教過義務中學,純屬義工,並無薪水,但卻不減其教學熱誠,學生說鄭待他們如弟妹,課餘,請他們到戲院看電影,到生果檔吃水果。
此外,鄭向學生解釋為何要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學生受到感召,冒著大雨,隨他在尖沙咀碼頭派傳單,雖然那個年代派傳單比較敏感(唉,今天竟落得又再如此),但他們信任老師,覺得應該去做。另外一次,則是保護釣魚台,在深水埗和李鄭屋一帶派。
今時今日看到這些,是否教大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呢?
記憶與遺忘
讀大學時比較文青,慕名讀了好些殿堂級小說,如《 百年孤寂》、《 生命不能承受的輕》、《 笑忘書》等。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是米蘭.昆德拉所寫的《 笑忘書》。
書中說到,捷克共產政權上台,要消滅這個國家的記憶,首先做的,便是放逐當地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等。失明歷史學家赫布(Hübl),悲慟地說:「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記憶,毀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重新製造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他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
當獨裁者在台上高喊「孩子,你們就是國家的未來」時,其實他真正的意思, 並不是真的要把社稷交託給他們,而只不過是,他會將人民和民智逐步推向幼年化發展。
獨裁者最喜歡孩子,因為孩子的最大特徵,就是並沒有太多記憶。
作者透過小說裡異見人士麥瑞克(Mirek)口中,更道出擲地有聲的不朽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也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故事女主角塔美娜(Tamina),一直思念她被政權迫害而流亡國外,最後客死異鄉的亡夫。起初,她力抗遺忘,希望留住對亡夫的寶貴回憶,但無奈丈夫的形象卻在她腦海裡日趨模糊,這讓她感到絕望和痛苦。
直到一天,一個年輕男人走來找她,並說如果她想遠離這一切痛苦,訣竅便是把記憶放下,並跟他到另一處地方:「那裡沒有悔恨,一切都沒有重量,像微風一樣輕盈。」結果,塔美娜跟他走了。
她來到一個只有孩子(沒有記憶的人?)的小島,她感到:「在這一刻, 她的丈夫既不在記憶裡,也不在思念中存在,因此,他既不感到壓抑,也不感到悔恨。」從此,她更與孩子,陷入激烈的性愛當中,「她重新閉上眼睛, 體會著肉體的快樂。有生以來,這是她第一次在靈魂遠去的時候,享受肉體的快感。她的靈魂既沒有想像甚麼,也沒有記憶甚麼,早已悄悄地離開了那間屋子。」
但隨著時間過去,重複使一切快感都失去了光采,更沒有幫她抓住靈魂。最後,她決定游水離開這個小島。但當她跳進水裡後,才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拚命划水,都已經無法離開這個小島了。最終,只能往下沉,無聲無息在水中湮沒。
於是,大家看到原本如斯美麗的一位佳人,就在這樣的一個遺忘之島上,在縱慾的狂歡和麻醉中,慢慢凋零。到一天驀然覺醒,想擺脫這種狀態,卻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失去了力量,只能往下沉淪,無聲無息的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