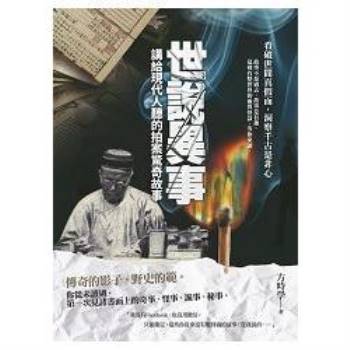徐貢元
徐貢元,字孔賜,別號紫嵐,繁昌縣彎子店接官亭小興湖人。明嘉靖(明世宗朱厚熜,西元一五二一~一五六七年在位)辛丑(西元一五四一年)進士。他學識淵博,為官清廉,為人正直,不屑阿諛。為官三十載,遷任十四次。當時,與夏言、海瑞、鄧元標被稱為天下四君子。嘉靖帝賜「徐公書院」正八間正方形亭式建築一座,海瑞贈:「天下一君子紫嵐君子居」匾額一塊。萬曆甲戌(西元一五七四年)在家中逝世,在生前住處大路旁有涼亭一座,稱「接官亭」,該地名即由此而來,還有牌坊五座。這些建築,都在後來的戰亂中毀壞。
徐貢元以刑官比部郎出任江西德安府時,遇太監運送壽藩梓輿(皇帝的棺木)進京,一路上敲詐勒索,強迫沿途官府送禮。徐貢元不僅不送禮,還揚言要把太監勒索錢財的惡行報告給皇帝,太監聽後收斂了許多。在該任上時,遭遇水災,他組織百姓抗災,按工發糧,拯救了數萬人。
德安府任期滿後,調任順天府尹,欽賜誥命,掌管後宮。由於受當朝太師嚴嵩的讒言與干擾,轉大理卿待命(即閒置)兩年。
徐貢元在朝中常常看見一些大臣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製造種種假象,糊弄皇帝。浙江一位官員在天井裡放個大缽子,裡面裝上泥土,種上稻子,又用毛竹筒子將稻子逼著向上長,居然長出了天井。一天,這位官員將特別培育的稻子運到朝中,指著稻子向皇帝奏本說:「我們浙江,地肥人勤,種出了特別好的稻子來,這是我皇洪福齊天的預兆。」皇帝見了這樣的稻子,非常高興,立刻加封了他的官職,同時也給浙江百姓增加了稅賦。
徐貢元對這種為了自己榮華富貴,弄虛作假,不惜犧牲勞動人民利益的行為,不屑一顧。可是,他從中也知道了皇帝容易被糊弄的性格。於是,他也想方設法來糊弄皇帝。不過,他想的是為官處世,應該為民謀福。
如何能為民謀福呢?徐貢元想了許久,終於讓他想了個辦法出來。第二天,他上朝奏本說:「我主萬歲,大事不好,我繁昌倒掉了一座飯籮山,把繁昌縣的農田全部壓掉了,繁昌的老百姓,別說繳錢糧,就連自己飯也沒得吃了!」皇帝聽了果然大吃一驚,說道:「愛卿,這樣一來,如何是好?」貢元說:「皇上愛民如子,百姓遭遇天災,皇上只有免除他們全部錢糧,發放救濟才是。」於是,當年繁昌農民不僅沒繳錢糧,還享受了皇恩救濟。
第二年,繁昌雖然沒有大災,卻也沒什麼收成。相信正統,並且唯心的貢元以為,農民種田,應該向皇上繳納錢糧,不然老天將不容許。於是,他又向皇上奏本說:「我主萬歲,繁昌飯籮山倒掉後,承蒙皇上救濟,繁昌人民感恩戴德不盡。近年來全力以赴,又開出一些田地了。這開出來的田地,應該上繳錢糧才是。」皇上聽了說:「准奏。」於是繁昌縣農民又向皇帝繳納錢糧了。不過,繳的數量很少。
為了對外講得通,他把繁昌田畝的數字減少了。按照實際田畝平均下去,繁昌田的面積被弄大了,每一畝六分六厘才算一畝。這種辦法,使繁昌農民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交差使役的義務。在那「有田須當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的社會裡,為繁昌農民減輕了許多負擔。如今,繁昌的田地,有老畝和市畝之分,每六分老畝,才是市畝一畝,其原因便在這裡。
徐貢元在大理卿閒待兩年後,被任命為戶部侍郎兼總督糧儲的職務。期間,他又遭嚴嵩陷害,說他在鑄造國幣時偷工減料,製造假錢。因為嚴嵩的搗鬼,在檢查國庫時,果然發現了假幣。嘉靖帝本來非常信任徐貢元,可是當他見了這些「證據」後,信以為真,大失所望,憤憤地說道:「徐貢元是朕最信任的貪官!」加上西宮娘娘一再慫恿,嘉靖帝決定殺掉徐貢元。
皇帝與娘娘的對話,讓身邊的宮女聽得清清楚楚。這個宮女與服侍貢元的丫鬟熟悉,因為她非常敬佩徐貢元的人格,便偷偷地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服侍徐貢元的丫鬟。徐貢元的丫鬟每天早上在給主人打來洗臉水、沏來早茶時,總要給徐貢元請安。這天早上送來這些東西後,居然什麼話也沒說,轉身就走了。徐貢元覺得奇怪,仔細看了看茶碗,發現裡面有三粒紅棗,碗蓋上還有天香。貢元聯想到這些天來,在嚴嵩老賊的唆使下,朝中正在檢查自己管理的錢庫,大約已經被他捏造出了證據,自己的大難就要來了——今天丫鬟這個意思,是叫我:「早早還鄉!」他們坐著簡陋的椅子,桌子也缺乏皇族該有的格調。父親被殺當天,「K」在家裡大肆破壞,毓峍只好臨時添購撐得起日常的傢俱。這時,她站在男人面前,用盡全力才忍住悲憤。這男人沒同情心嗎?她已經夠無助了,他怎能拒絕她?但愛新覺羅一族的驕傲不許她示弱。即使她臉已脹紅,眼淚卻硬是沒落下。
這位男子叫法務主獺槻。他生得俊美迷人,與當代影星上原謙有幾分相似,光微笑便能打動多少少女的心。與這張臉不稱,法務主是臺北州裡的名偵探,一開始毓峍對「獺槻」這名字感到好奇,因為發音與「騙子」相同,真難想像是偵探的名字,但為何取這個名字,恐怕得問他父母。七年前,法務主為愛新覺羅父女偵破一個案件,那是法務主偵探社開張經手的最初事件,毓峍本以為這段淵源會讓他出手相助──他們可不是毫無關係!何況愛新覺羅家不缺錢,至少現在不缺。
眼見法務主沉默不語,毓峍忍不住說:「您在猶豫什麼?若偵破殺人鬼『K』案,您的大名立刻威震全國,甚至海外都會讚揚您。若您失敗了,又有什麼好怕的?反正警察失敗了、總督府失敗了,再多一位法務主又何妨?或您是害怕?怕自己成為『K』的目標,被他所殺?」
她刻意激他一激。男人最受不得激,她至少知道這點。但法務主只是微微苦笑:「我對揚名天下沒興趣。會當偵探,只是善用我為數不多的才能。不過愛新覺羅小姐,請你見諒,我在經營偵探社之初,便為自己設下一些規則。有些案子,我是不會接的,而『K』的案子,不巧便是其中之一。」
這答案在毓峍的意料之外。她問:「什麼意思?哪些案子您不會接?」
「這是機密,無可奉告。」
「但您會這樣說,表示您對『K』的案子,已知道了些什麼吧!所以才能判斷這案子能不能接。到底是什麼?法務主先生,請您告訴我!」
她幾乎要跪下來求他了。法務主嘆了口氣:「我確實知道一些事。但我若告訴你,便不是機密了。請你相信,我知道的事,對你絕對沒幫助,甚至無法讓我們更瞭解『K』……你還有我的名片嗎?除了調查『K』,你需要什麼幫助,我盡力而為。但我不會接下你的委託。」法務主取出名片放在桌上,拒絕的意思算是明顯了。他本就只是來憑弔這位最初委託人,沒義務接受毓峍的委託。毓峍低下頭,感到沉沉的黑暗壓在自己身上。她見法務主來憑弔,忽然想起這麼一號人物;他這麼有心,甚至親自來一趟,一定會接受她的委託吧!誰知法務主只是將她朝絕望再推一步。要落井下石,何必親自來?她幾乎便要說出難聽話,總算是忍住了。
法務主見她的樣子,於心不忍。他點了根菸:「姑且問一下好了。若我不接這個案子,愛新覺羅小姐打算怎麼辦?會將一切交給警察,靜待他們破案嗎?」
毓峍吸了口氣,咬牙切齒:「不會。警察要是能破案,早就破案了,還會等到家父遇害嗎!」
「還是你會去委託其他偵探?」
「不,我……可能會,但他們都沒有法務主先生這麼值得信賴。」毓峍快速抹去正要落下的淚水。她想起父親的「秘密」,如果是法務主,也許值得她說出口,法務主有自己的堅持。其他偵探……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委託他們也沒有意義。她微微顫抖著說:「我會自己調查『K』的事。」
「你自己?」法務主吃了一驚:「請恕我直言,愛新覺羅小姐,你毫無經驗,而且……」
「難道我沒想過嗎?」毓峍冷笑:「但我心意已決。坦白說,在法務主先生來之前,我便是這麼打算──根本不能信賴警察。」
她站起身,從客廳角落堆著的東西裡拿出一本冊子:「至今為止的案件,我蒐集了全部的剪報,就連八卦小報上莫名其妙的推測都蒐集了。法務主先生應該知道吧?居然有人懷疑我是殺人鬼『K』,只因我正巧出國,逃過一劫……」她說著說著,情緒又冒上來,表情也扭曲了。
但法務主只是冷酷地指出:「你能找到的資料,警察也找得到。我看不出你哪裡能做得比警察好。」
「不錯,但有件事,警察確實不知道,而我知道。」
「你確定嗎?」
「當然!我知道家父被殺的真正原因!」
「什麼?」法務主抬起頭,一臉意外。毓峍心裡有種報復般的快感,因為法務主彷彿把她當成小孩。但有這麼一瞬間,不只是報復,她想全盤抖出;她實在無法一個人背負這些,可她最後只是冷笑:「不錯,如果法務主先生接下這個案子,我便告訴你。無關的人是沒資格知道的。」徐貢元本無什麼財產,只是將自己常穿的衣服收拾了一下,便動身回鄉。可是,當他走到城門口,卻見戒備森嚴,自己根本出不去了。這樣一來,他更加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徐貢元迅速來到海瑞家,坐上海瑞的轎子出城。因為海瑞是經過皇帝的特許,無論到了哪裡,都有不受檢查的特權。這樣,徐貢元才算出了京城,逃了回來。
徐貢元回到家鄉後,他想嚴嵩絕不會就此甘休,一定會派兵前來逮捕他。於是,他穿著青衣小帽,整日在紫嵐嶺路邊茶館裡等著朝中的兵來。當時,正值炎天六月,他將遮陽傘傘柄竹節打通,裝了一傘柄的清水,準備應付突發事件。
果然,嚴嵩見徐貢元不辭而別,就上書嘉靖帝,再三說若此人不除,有損萬歲的聖威。於是,嘉靖帝便下了聖旨,派御林軍到徐貢元家來抄斬他家滿門。這天,隊伍到了紫嵐嶺上,已是巳時,人人熱得滿頭大汗,就來到茶館休息。他們見這裡有個人在一旁悠然自得地品茶,領隊的頭目問道:「喂,喝茶的,這裡有個叫徐貢元的,你知道嗎?」
徐貢元說:「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清官,哪會不知道啊!」那頭目又問他認不認得到徐貢元的家,徐貢元說:「家鄉熟人,怎會不認得呢?」這頭目聽後,便吩咐這位「茶客」為他們帶路,貢元欣然答應。
他們出了茶館,徐貢元騎上毛驢,撐上遮陽傘,帶著這些兵丁,往平鋪方向的長山頭上走來。
大熱天,驕陽似火,走在青蓬柴夾道、高低起伏的山路上,熱浪襲人。徐貢元渴了,將傘柄往嘴上湊一下,喝點水。
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這些在皇城裡驕養慣了的兵丁,汗水溼透了衣裳,又沒有水喝,都口渴心焦,疲憊不堪。頭目問道:「徐貢元家在哪裡,還有多少路啊?」
徐貢貢元說:「怎麼?才走了這麼點路,就問起他家在哪裡了?還遠得很呢!我捨得時間給你們帶路,你們急什麼!」說著,催驢又走。
走了一程,頭目實在熱得受不了,很不耐煩地問道:「徐貢元家到底還有多遠?」徐貢元這才勒驢駐足說:「從這裡到徐貢元家,十里長山跑死馬,十里團山轉死馬;還有十里陷馬灘,再過十里大興湖,走過小興湖中的十里梅花樁,才能看到徐貢元家的莊園。這些雖說都是十里路,其實只是個約數,我們走了這麼長時間,十里長山還沒走到一半呢!」此時,日當正午,火熱的太陽當頂照著,熱得這班兵丁像是蒸籠裡的烏龜,實在吃不消。本來,徐貢元在朝中口碑很好,這頭目也沒有冤仇一定要去殺他。於是,頭目說道:「算了,算了。徐貢元家這麼難走,就算到了他家,我們也沒命了。」說完,沒再理會徐貢元,便回馬轉程了。
可是,這班御林兵為了回京能夠交差,路過三山街道時,卻殺掉了三山的一門無辜的徐姓。徐貢元知道後,大哭了一場。而後,遷徙自己住處的徐姓到三山,填補了三山徐家。
徐貢元為官清廉,因此家道並不富裕。逃過了皇上追殺後,他與地方紳士、百姓來往,也還怡然自樂。這一年的六月十九,他與眾紳士去九華山做觀音會。這時候,廟裡正籌備建築觀音閣。住持見他們都是名流,特別設宴招待。可是廟裡設宴是有規矩的,喝酒的人應該捐款;特別是坐首席的,要帶頭多捐。因此喝酒時,眾紳士都不肯上首就坐。徐貢元見了,大大方方地坐了上去。
席間,住持捧著化緣簿請眾紳士施捨。因為徐貢元坐在首席,理所當然地首先捐贈。徐貢元清清嗓子,說:「我徐貢元見錢捐一百挑,見鹽捐一百挑,見油捐一百挑。」
在位眾紳士聽了,雖然不相信徐貢元會有這麼多財產可捐,可是他們虔誠地篤信,在佛事上是不可打誑語的;加上徐貢元到底是當過朝中大官的,以為他會有另外的財產。於是,各要面子,盡力捐贈。之後,廟裡化緣時,總捧著這些紳士捐贈數字的簿子昭示施主,施主們見了他們捐贈的數目,都不甘小氣,使九華山觀音閣順利地建了起來。在收集捐款時,住持知道徐貢元的用意,最後才收他的。徐貢元只是拿著湯匙,將錢、鹽、油各舀了一百給廟裡。並且說:「這湯匙,我們地方上叫做挑子。我所說的各捐一百挑,就是指這樣的『挑』子。我徐貢元哪來那麼多的財產,能捐得出挑擔的『挑』呢?當時所以那麼說,只是為了想大家都能多捐贈一些!」法務主苦笑:「為何不告訴警察?」
「剛剛我說過,如果警察的能力值得信賴,就不會輪到家父被殺。」
「也許警察就是缺這一個關鍵線索。」
「那也與我無關。既然家父已經死了,無能的警察能不能偵破就不關我的事,誰叫他們無能?」
「愛新覺羅小姐。」法務主嚴肅地說:「即使你真的循著這個只有你知道的線索找到『K』,結果也很可能只是你成為下一位受害者。這不是你該承擔的。」
毓峍一時無言,接著她淒然一笑:「那什麼才是我該承擔的?法務主先生。就坐在這裡,只是無助地活下去?」
「至少令尊不希望你死。」
「也許真是如此,但我卻不冀望活著。您能瞭解嗎?能讓我依賴的人,一個也沒有了。滿洲國的那些皇親貴族,我快十年沒見過他們的臉,何況當初父親搬來臺灣,便是因為跟他們處得不好。現在,他們寫信來要我回去,我太清楚了,他們只是要我在滿洲國扮好受害者的角色,整天只要我哭哭啼啼,拿我作為對付日本帝國的王牌,幾個月之後,就會把我丟在一旁。」
她越說越激動,彷彿要將滿腔痛苦宣洩而出:「您說的沒錯,若我找到殺人鬼『K』,也許會被他所殺,但那至少是讓我滿足的死法!我想過自殺,就用這根樑上吊,但我太不甘心。對現在的我來說……找到『K』,與他面對面,然後我們其中一人會死,便是我最大的願望,也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她的聲音在宅子裡迴響。毓峍喘著氣,滿臉通紅,腦中激動到一片混亂,淚水悄然滑下。法務主靜靜吐了口煙,眼裡帶著同情,卻沒表現在聲音上。他漠然說:「我知道了。我只想確定一件事,您是認真的嗎?」
「當然!有什麼好懷疑的?」
「不。」法務主閉上眼,他看來何其俊美,這一瞬間若是停格,大概會成為影史上永垂不朽的劇照。偵探站起身:「若您的意志如此明確,我要是再阻止你,便不尊重了。很抱歉,這案子我幫不上忙,我只能祝福你。」
「我已經知道了,不用一說再說。」毓峍將臉上的淚水抹去:「若您不介意,我希望靜一靜。」
「當然。」法務主戴上帽子,走出大宅。毓峍送他到門邊。法務主回頭:「愛新覺羅小姐,雖然我不會阻止你,但如果你找到願意幫忙的同伴,像是其他偵探,你可以將那件事告訴他們,這樣他們才幫得上忙……」「請別再說了。」毓峍厲聲打斷:「這本是我會帶進棺材的秘密,對誰都沒打算說。我不會再告訴任何人,也請您當成沒聽過。我是見您來了,一時軟弱起來才說出口,我本來以為您會幫忙。現在看來,我真是笨蛋。」
法務主還要再說,毓峍卻已把門關上。她用背抵著門,終於無法克制地啜泣起來,身子一軟,沿著門慢慢滑下。時間過去,夕陽的光線射進宅裡,染上一層薄薄的哀愁;毓峍不知自己哭了多久,等她止住淚,一個深切的體會悄然降臨。
會來安慰自己的人,都已不在了。
這座宅子已是失去靈魂的空殼,是搖搖欲墜的殘跡。過去她傷心時,父親會來摸摸她的背,墨冬會舔她的手──墨冬是她養的北極狼,一身白毛如雪般純淨,附近的人都以為牠是狗,她也懶得解釋。臺灣沒有北極狼,墨冬是父親的露西亞友人贈送的,牠陪毓峍渡過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就像她的家人。
她多希望父親、墨冬還在啊。但她想起父親的屍體──警察帶她去看,讓她領回──父親咽喉上的傷口,就像連她的心一同刺穿。「死」本是虛無飄渺的,卻在那瞬間降臨,結結實實地提醒她父親已死。
雖然沒發現墨冬的屍體,但墨冬若活著,一定會回來。何況「K」殺死父親時,墨冬不可能不捨身護主。所以墨冬必是死了,只是發生什麼事,讓牠的屍體不在現場。荒謬的是,家裡反而出現一具貓屍!一開始毓峍不知道,後來聽鄰居說,才知被警察清理了。墨冬失蹤,卻出現一隻貓,這是什麼惡質玩笑?若這是「K」的惡作劇,毓峍真會氣到發抖。
那些被「K」大鬧一番破壞的傢俱,有些還堆在牆角,不知該怎麼辦。父親收藏的書畫,有些被破壞,只能打開看看有沒有救。說是這麼說,她也不知能不能修復。這是真正的人事全非。「K」不只殺了人,還將能供她回憶的物也破壞了。但不可能完全破壞,她感到記憶陰魂不散地在每個角落低語,喃喃訴說逝去的溫暖。
每個地方都有父親的表情、墨冬的低鳴。
毓峍默然回到房裡,腳步飄忽,彷彿化為死者的陰影。她點起電燈,造型典雅的賽璐璐燈罩融融地亮了,在她臉上勾出金色的筆畫。她從抽屜底層翻出紋飾精緻的琺瑯盒,打開一看,裡面是半滿的黑墨,在燈光下閃閃發光,像沉著一彎金月。毓峍盯著墨沉思,從旁拿起毛筆,沾了點墨。
接下來發生的事,或許稱得上「不可思議」。儘管這樣,住持還是感謝徐貢元帶了個好頭,決定贈送他一對旗杆。徐貢元說:「我本無功勞,承蒙住持錯愛,這旗杆就不能樹在外面了,因為會丟人現眼。只好放在大樑上架著,每一百年拿出來出一回新。等到哪一年,我繁昌縣能有一百炷『華山會』朝九華山時,我的旗杆再樹出來,以表示紀念。」
住持知道,繁昌是不可能一次有一百炷香會朝九華的。徐貢元這麼說,分明是不肯將旗杆樹在外面,讓風吹雨淋而腐朽。於是,他也順勢說了句相襯的話:「等到你繁昌能有百炷會朝九華時,我從青陽結絡子,一直結到我九華山上來,表示歡迎。」青陽城離九華山六十里路,從那裡結絡子上九華山,也是不可能的。於是,徐貢元的旗杆總是架在觀音閣的大樑上,每一百年才給出一回新。
這樣,旗杆永遠不會壞,拜觀音菩薩的人,同時也拜謁了徐貢元的旗杆。嘉靖帝逝世後,他的兒子朱載垕當了皇帝,是為穆宗(西元一五六七 一五七二年在位)。
穆宗殺了嚴嵩,嚴嵩的女兒西宮娘娘也被貶出了皇宮。一日,徐貢元在九華山看見一位尼姑在井邊洗衣,覺得面熟,走近一看,原來卻是西宮娘娘。出於禮貌,他問候道:「娘娘,一向可好?緣何削髮為尼?」西宮娘娘回首一看,見是徐貢元,自愧無顏相見,又覺無地自容,衣也不洗了,一頭鑽進了井裡。
貢元急忙呼救,待人們把娘娘打撈上來時,已經嚥了氣。徐貢元嘆息了一番,將她安葬起來。
如今,西宮娘娘洗衣自盡的水井,還叫「娘娘井」。
徐貢元博學多才,機智敏捷,為官清廉,為民謀福,逝世四百多年了,可是關於他的故事還依舊流傳在人間。毓峍並沒有在紙上作畫,她的筆在空中一點,墨跡竟附上虛空,有如墨色的煙被收束起來,只是微微暈開──她竟直接在「世界」上作畫。同時,她身邊飄起墨色的細雨,點滴濕潤了她的頭髮、衣衫。那是溫柔異常的雨,但室內怎會下雨?事實上,不只室內下起了雨,在她作畫的方圓百尺裡,都籠罩在墨色的雨中。
「墨冬,回來吧。」毓峍低語。
一聲狼嚎,雪白的北極狼竟從墨雲中穿出,輕飄飄地踏落地面。毓峍將筆放下,輕輕抱住北極狼,她摸著「墨冬」的毛皮,感到牠的溫暖,忍不住又流下淚。她知道這是幻影,只是透過「驀霢墨」創造出來的幻覺。牠不是墨冬,甚至不能持續存在一整天。
但已能溫暖她的心靈。
在淚光中,她是帶著恨的。她清楚明白,驀霢墨就是父親被殺的原因。
驀霢墨──她不知父親怎麼會有這種不科學的事物。本來她也不信,但她還是少女時,墨冬曾死過一次;對北極狼來說,臺灣還是太炎熱。毓峍抱著墨冬的屍體痛哭,怎樣都不肯給墨冬收屍。
那時父親問她,她要讓墨冬活過來嗎?願意承擔墨冬活過來的後果嗎?毓峍哪管什麼後果,連連答應,於是溥儲便用金色的驀霢墨讓墨冬復甦。毓峍看著墨冬重新呼吸,大為驚奇。父親諄諄告誡,驀霢墨的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因為這是能動搖天命運轉的事物。
她記得父親說過,驀霢墨有三色,分別是黑、紅、金,都能翻轉陰陽變化,混淆黑白虛實。黑驀霢墨能描繪幻境、從無化虛,紅驀霢墨則用途萬端、變化無方,金驀霢墨更能顛倒日夜、無中生有、起死回生。讓墨冬復生,已悖離天理,將有報應,絕不能任意為之,更不能因擁有驀霢墨而得意。
父親的死,是否便是多年前復活墨冬的報應,毓峍不得而知。但她不信命運。畢竟,是她堅持要墨冬復活,死的怎不是她?能確定的是,父親死後,她翻遍整個家都找不到金色與紅色的驀霢墨,只剩下父親在她十六歲時送她,被她藏在抽屜夾層裡的黑驀霢墨。
驀霢墨沒道理消失。所以,「K」一定是為了驀霢墨而來。這便是父親為何會死。直到此時,毓峍仍不敢相信,有著金驀霢墨的父親居然會死。金驀霢墨的能耐,她再清楚不過了。「K」那傢伙一定用了卑鄙的手段。但問題是,「K」是怎麼知道驀霢墨存在的?父親不會到處亂說,但有很小的可能,父親基於同情──就像墨冬死去時──透露了驀霢墨的事。那麼,知情者只可能限於與父親有交流的人。
這就是警察不知道的情報,「K」極可能就是愛新覺羅溥儲認識的人!
雖說如此,毓峍她四處調查,比照之前的被害人,卻怎麼也找不到與父親的交集。能與父親相交,多半是文化界的人,被害者幾乎與此無關,這是怎麼回事?
但愛新覺羅毓峍不急。
繼續等下去,「K」一定會露出馬腳。那時,毓峍會站在「K」面前。她確實不在乎自己生命,卻不是有勇無謀;她猜想,「K」沒找到黑驀霢墨,卻沒燒掉他們家,以防萬一,是否表示「K」不知道黑驀霢墨存在?
雖然黑驀霢墨是驀霢墨中最無力的,但若「K」對此毫無防備的話──
在他們交鋒的一瞬間,毓峍或許是能活下來的一方。
徐貢元,字孔賜,別號紫嵐,繁昌縣彎子店接官亭小興湖人。明嘉靖(明世宗朱厚熜,西元一五二一~一五六七年在位)辛丑(西元一五四一年)進士。他學識淵博,為官清廉,為人正直,不屑阿諛。為官三十載,遷任十四次。當時,與夏言、海瑞、鄧元標被稱為天下四君子。嘉靖帝賜「徐公書院」正八間正方形亭式建築一座,海瑞贈:「天下一君子紫嵐君子居」匾額一塊。萬曆甲戌(西元一五七四年)在家中逝世,在生前住處大路旁有涼亭一座,稱「接官亭」,該地名即由此而來,還有牌坊五座。這些建築,都在後來的戰亂中毀壞。
徐貢元以刑官比部郎出任江西德安府時,遇太監運送壽藩梓輿(皇帝的棺木)進京,一路上敲詐勒索,強迫沿途官府送禮。徐貢元不僅不送禮,還揚言要把太監勒索錢財的惡行報告給皇帝,太監聽後收斂了許多。在該任上時,遭遇水災,他組織百姓抗災,按工發糧,拯救了數萬人。
德安府任期滿後,調任順天府尹,欽賜誥命,掌管後宮。由於受當朝太師嚴嵩的讒言與干擾,轉大理卿待命(即閒置)兩年。
徐貢元在朝中常常看見一些大臣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製造種種假象,糊弄皇帝。浙江一位官員在天井裡放個大缽子,裡面裝上泥土,種上稻子,又用毛竹筒子將稻子逼著向上長,居然長出了天井。一天,這位官員將特別培育的稻子運到朝中,指著稻子向皇帝奏本說:「我們浙江,地肥人勤,種出了特別好的稻子來,這是我皇洪福齊天的預兆。」皇帝見了這樣的稻子,非常高興,立刻加封了他的官職,同時也給浙江百姓增加了稅賦。
徐貢元對這種為了自己榮華富貴,弄虛作假,不惜犧牲勞動人民利益的行為,不屑一顧。可是,他從中也知道了皇帝容易被糊弄的性格。於是,他也想方設法來糊弄皇帝。不過,他想的是為官處世,應該為民謀福。
如何能為民謀福呢?徐貢元想了許久,終於讓他想了個辦法出來。第二天,他上朝奏本說:「我主萬歲,大事不好,我繁昌倒掉了一座飯籮山,把繁昌縣的農田全部壓掉了,繁昌的老百姓,別說繳錢糧,就連自己飯也沒得吃了!」皇帝聽了果然大吃一驚,說道:「愛卿,這樣一來,如何是好?」貢元說:「皇上愛民如子,百姓遭遇天災,皇上只有免除他們全部錢糧,發放救濟才是。」於是,當年繁昌農民不僅沒繳錢糧,還享受了皇恩救濟。
第二年,繁昌雖然沒有大災,卻也沒什麼收成。相信正統,並且唯心的貢元以為,農民種田,應該向皇上繳納錢糧,不然老天將不容許。於是,他又向皇上奏本說:「我主萬歲,繁昌飯籮山倒掉後,承蒙皇上救濟,繁昌人民感恩戴德不盡。近年來全力以赴,又開出一些田地了。這開出來的田地,應該上繳錢糧才是。」皇上聽了說:「准奏。」於是繁昌縣農民又向皇帝繳納錢糧了。不過,繳的數量很少。
為了對外講得通,他把繁昌田畝的數字減少了。按照實際田畝平均下去,繁昌田的面積被弄大了,每一畝六分六厘才算一畝。這種辦法,使繁昌農民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交差使役的義務。在那「有田須當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的社會裡,為繁昌農民減輕了許多負擔。如今,繁昌的田地,有老畝和市畝之分,每六分老畝,才是市畝一畝,其原因便在這裡。
徐貢元在大理卿閒待兩年後,被任命為戶部侍郎兼總督糧儲的職務。期間,他又遭嚴嵩陷害,說他在鑄造國幣時偷工減料,製造假錢。因為嚴嵩的搗鬼,在檢查國庫時,果然發現了假幣。嘉靖帝本來非常信任徐貢元,可是當他見了這些「證據」後,信以為真,大失所望,憤憤地說道:「徐貢元是朕最信任的貪官!」加上西宮娘娘一再慫恿,嘉靖帝決定殺掉徐貢元。
皇帝與娘娘的對話,讓身邊的宮女聽得清清楚楚。這個宮女與服侍貢元的丫鬟熟悉,因為她非常敬佩徐貢元的人格,便偷偷地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服侍徐貢元的丫鬟。徐貢元的丫鬟每天早上在給主人打來洗臉水、沏來早茶時,總要給徐貢元請安。這天早上送來這些東西後,居然什麼話也沒說,轉身就走了。徐貢元覺得奇怪,仔細看了看茶碗,發現裡面有三粒紅棗,碗蓋上還有天香。貢元聯想到這些天來,在嚴嵩老賊的唆使下,朝中正在檢查自己管理的錢庫,大約已經被他捏造出了證據,自己的大難就要來了——今天丫鬟這個意思,是叫我:「早早還鄉!」他們坐著簡陋的椅子,桌子也缺乏皇族該有的格調。父親被殺當天,「K」在家裡大肆破壞,毓峍只好臨時添購撐得起日常的傢俱。這時,她站在男人面前,用盡全力才忍住悲憤。這男人沒同情心嗎?她已經夠無助了,他怎能拒絕她?但愛新覺羅一族的驕傲不許她示弱。即使她臉已脹紅,眼淚卻硬是沒落下。
這位男子叫法務主獺槻。他生得俊美迷人,與當代影星上原謙有幾分相似,光微笑便能打動多少少女的心。與這張臉不稱,法務主是臺北州裡的名偵探,一開始毓峍對「獺槻」這名字感到好奇,因為發音與「騙子」相同,真難想像是偵探的名字,但為何取這個名字,恐怕得問他父母。七年前,法務主為愛新覺羅父女偵破一個案件,那是法務主偵探社開張經手的最初事件,毓峍本以為這段淵源會讓他出手相助──他們可不是毫無關係!何況愛新覺羅家不缺錢,至少現在不缺。
眼見法務主沉默不語,毓峍忍不住說:「您在猶豫什麼?若偵破殺人鬼『K』案,您的大名立刻威震全國,甚至海外都會讚揚您。若您失敗了,又有什麼好怕的?反正警察失敗了、總督府失敗了,再多一位法務主又何妨?或您是害怕?怕自己成為『K』的目標,被他所殺?」
她刻意激他一激。男人最受不得激,她至少知道這點。但法務主只是微微苦笑:「我對揚名天下沒興趣。會當偵探,只是善用我為數不多的才能。不過愛新覺羅小姐,請你見諒,我在經營偵探社之初,便為自己設下一些規則。有些案子,我是不會接的,而『K』的案子,不巧便是其中之一。」
這答案在毓峍的意料之外。她問:「什麼意思?哪些案子您不會接?」
「這是機密,無可奉告。」
「但您會這樣說,表示您對『K』的案子,已知道了些什麼吧!所以才能判斷這案子能不能接。到底是什麼?法務主先生,請您告訴我!」
她幾乎要跪下來求他了。法務主嘆了口氣:「我確實知道一些事。但我若告訴你,便不是機密了。請你相信,我知道的事,對你絕對沒幫助,甚至無法讓我們更瞭解『K』……你還有我的名片嗎?除了調查『K』,你需要什麼幫助,我盡力而為。但我不會接下你的委託。」法務主取出名片放在桌上,拒絕的意思算是明顯了。他本就只是來憑弔這位最初委託人,沒義務接受毓峍的委託。毓峍低下頭,感到沉沉的黑暗壓在自己身上。她見法務主來憑弔,忽然想起這麼一號人物;他這麼有心,甚至親自來一趟,一定會接受她的委託吧!誰知法務主只是將她朝絕望再推一步。要落井下石,何必親自來?她幾乎便要說出難聽話,總算是忍住了。
法務主見她的樣子,於心不忍。他點了根菸:「姑且問一下好了。若我不接這個案子,愛新覺羅小姐打算怎麼辦?會將一切交給警察,靜待他們破案嗎?」
毓峍吸了口氣,咬牙切齒:「不會。警察要是能破案,早就破案了,還會等到家父遇害嗎!」
「還是你會去委託其他偵探?」
「不,我……可能會,但他們都沒有法務主先生這麼值得信賴。」毓峍快速抹去正要落下的淚水。她想起父親的「秘密」,如果是法務主,也許值得她說出口,法務主有自己的堅持。其他偵探……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委託他們也沒有意義。她微微顫抖著說:「我會自己調查『K』的事。」
「你自己?」法務主吃了一驚:「請恕我直言,愛新覺羅小姐,你毫無經驗,而且……」
「難道我沒想過嗎?」毓峍冷笑:「但我心意已決。坦白說,在法務主先生來之前,我便是這麼打算──根本不能信賴警察。」
她站起身,從客廳角落堆著的東西裡拿出一本冊子:「至今為止的案件,我蒐集了全部的剪報,就連八卦小報上莫名其妙的推測都蒐集了。法務主先生應該知道吧?居然有人懷疑我是殺人鬼『K』,只因我正巧出國,逃過一劫……」她說著說著,情緒又冒上來,表情也扭曲了。
但法務主只是冷酷地指出:「你能找到的資料,警察也找得到。我看不出你哪裡能做得比警察好。」
「不錯,但有件事,警察確實不知道,而我知道。」
「你確定嗎?」
「當然!我知道家父被殺的真正原因!」
「什麼?」法務主抬起頭,一臉意外。毓峍心裡有種報復般的快感,因為法務主彷彿把她當成小孩。但有這麼一瞬間,不只是報復,她想全盤抖出;她實在無法一個人背負這些,可她最後只是冷笑:「不錯,如果法務主先生接下這個案子,我便告訴你。無關的人是沒資格知道的。」徐貢元本無什麼財產,只是將自己常穿的衣服收拾了一下,便動身回鄉。可是,當他走到城門口,卻見戒備森嚴,自己根本出不去了。這樣一來,他更加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徐貢元迅速來到海瑞家,坐上海瑞的轎子出城。因為海瑞是經過皇帝的特許,無論到了哪裡,都有不受檢查的特權。這樣,徐貢元才算出了京城,逃了回來。
徐貢元回到家鄉後,他想嚴嵩絕不會就此甘休,一定會派兵前來逮捕他。於是,他穿著青衣小帽,整日在紫嵐嶺路邊茶館裡等著朝中的兵來。當時,正值炎天六月,他將遮陽傘傘柄竹節打通,裝了一傘柄的清水,準備應付突發事件。
果然,嚴嵩見徐貢元不辭而別,就上書嘉靖帝,再三說若此人不除,有損萬歲的聖威。於是,嘉靖帝便下了聖旨,派御林軍到徐貢元家來抄斬他家滿門。這天,隊伍到了紫嵐嶺上,已是巳時,人人熱得滿頭大汗,就來到茶館休息。他們見這裡有個人在一旁悠然自得地品茶,領隊的頭目問道:「喂,喝茶的,這裡有個叫徐貢元的,你知道嗎?」
徐貢元說:「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清官,哪會不知道啊!」那頭目又問他認不認得到徐貢元的家,徐貢元說:「家鄉熟人,怎會不認得呢?」這頭目聽後,便吩咐這位「茶客」為他們帶路,貢元欣然答應。
他們出了茶館,徐貢元騎上毛驢,撐上遮陽傘,帶著這些兵丁,往平鋪方向的長山頭上走來。
大熱天,驕陽似火,走在青蓬柴夾道、高低起伏的山路上,熱浪襲人。徐貢元渴了,將傘柄往嘴上湊一下,喝點水。
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這些在皇城裡驕養慣了的兵丁,汗水溼透了衣裳,又沒有水喝,都口渴心焦,疲憊不堪。頭目問道:「徐貢元家在哪裡,還有多少路啊?」
徐貢貢元說:「怎麼?才走了這麼點路,就問起他家在哪裡了?還遠得很呢!我捨得時間給你們帶路,你們急什麼!」說著,催驢又走。
走了一程,頭目實在熱得受不了,很不耐煩地問道:「徐貢元家到底還有多遠?」徐貢元這才勒驢駐足說:「從這裡到徐貢元家,十里長山跑死馬,十里團山轉死馬;還有十里陷馬灘,再過十里大興湖,走過小興湖中的十里梅花樁,才能看到徐貢元家的莊園。這些雖說都是十里路,其實只是個約數,我們走了這麼長時間,十里長山還沒走到一半呢!」此時,日當正午,火熱的太陽當頂照著,熱得這班兵丁像是蒸籠裡的烏龜,實在吃不消。本來,徐貢元在朝中口碑很好,這頭目也沒有冤仇一定要去殺他。於是,頭目說道:「算了,算了。徐貢元家這麼難走,就算到了他家,我們也沒命了。」說完,沒再理會徐貢元,便回馬轉程了。
可是,這班御林兵為了回京能夠交差,路過三山街道時,卻殺掉了三山的一門無辜的徐姓。徐貢元知道後,大哭了一場。而後,遷徙自己住處的徐姓到三山,填補了三山徐家。
徐貢元為官清廉,因此家道並不富裕。逃過了皇上追殺後,他與地方紳士、百姓來往,也還怡然自樂。這一年的六月十九,他與眾紳士去九華山做觀音會。這時候,廟裡正籌備建築觀音閣。住持見他們都是名流,特別設宴招待。可是廟裡設宴是有規矩的,喝酒的人應該捐款;特別是坐首席的,要帶頭多捐。因此喝酒時,眾紳士都不肯上首就坐。徐貢元見了,大大方方地坐了上去。
席間,住持捧著化緣簿請眾紳士施捨。因為徐貢元坐在首席,理所當然地首先捐贈。徐貢元清清嗓子,說:「我徐貢元見錢捐一百挑,見鹽捐一百挑,見油捐一百挑。」
在位眾紳士聽了,雖然不相信徐貢元會有這麼多財產可捐,可是他們虔誠地篤信,在佛事上是不可打誑語的;加上徐貢元到底是當過朝中大官的,以為他會有另外的財產。於是,各要面子,盡力捐贈。之後,廟裡化緣時,總捧著這些紳士捐贈數字的簿子昭示施主,施主們見了他們捐贈的數目,都不甘小氣,使九華山觀音閣順利地建了起來。在收集捐款時,住持知道徐貢元的用意,最後才收他的。徐貢元只是拿著湯匙,將錢、鹽、油各舀了一百給廟裡。並且說:「這湯匙,我們地方上叫做挑子。我所說的各捐一百挑,就是指這樣的『挑』子。我徐貢元哪來那麼多的財產,能捐得出挑擔的『挑』呢?當時所以那麼說,只是為了想大家都能多捐贈一些!」法務主苦笑:「為何不告訴警察?」
「剛剛我說過,如果警察的能力值得信賴,就不會輪到家父被殺。」
「也許警察就是缺這一個關鍵線索。」
「那也與我無關。既然家父已經死了,無能的警察能不能偵破就不關我的事,誰叫他們無能?」
「愛新覺羅小姐。」法務主嚴肅地說:「即使你真的循著這個只有你知道的線索找到『K』,結果也很可能只是你成為下一位受害者。這不是你該承擔的。」
毓峍一時無言,接著她淒然一笑:「那什麼才是我該承擔的?法務主先生。就坐在這裡,只是無助地活下去?」
「至少令尊不希望你死。」
「也許真是如此,但我卻不冀望活著。您能瞭解嗎?能讓我依賴的人,一個也沒有了。滿洲國的那些皇親貴族,我快十年沒見過他們的臉,何況當初父親搬來臺灣,便是因為跟他們處得不好。現在,他們寫信來要我回去,我太清楚了,他們只是要我在滿洲國扮好受害者的角色,整天只要我哭哭啼啼,拿我作為對付日本帝國的王牌,幾個月之後,就會把我丟在一旁。」
她越說越激動,彷彿要將滿腔痛苦宣洩而出:「您說的沒錯,若我找到殺人鬼『K』,也許會被他所殺,但那至少是讓我滿足的死法!我想過自殺,就用這根樑上吊,但我太不甘心。對現在的我來說……找到『K』,與他面對面,然後我們其中一人會死,便是我最大的願望,也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她的聲音在宅子裡迴響。毓峍喘著氣,滿臉通紅,腦中激動到一片混亂,淚水悄然滑下。法務主靜靜吐了口煙,眼裡帶著同情,卻沒表現在聲音上。他漠然說:「我知道了。我只想確定一件事,您是認真的嗎?」
「當然!有什麼好懷疑的?」
「不。」法務主閉上眼,他看來何其俊美,這一瞬間若是停格,大概會成為影史上永垂不朽的劇照。偵探站起身:「若您的意志如此明確,我要是再阻止你,便不尊重了。很抱歉,這案子我幫不上忙,我只能祝福你。」
「我已經知道了,不用一說再說。」毓峍將臉上的淚水抹去:「若您不介意,我希望靜一靜。」
「當然。」法務主戴上帽子,走出大宅。毓峍送他到門邊。法務主回頭:「愛新覺羅小姐,雖然我不會阻止你,但如果你找到願意幫忙的同伴,像是其他偵探,你可以將那件事告訴他們,這樣他們才幫得上忙……」「請別再說了。」毓峍厲聲打斷:「這本是我會帶進棺材的秘密,對誰都沒打算說。我不會再告訴任何人,也請您當成沒聽過。我是見您來了,一時軟弱起來才說出口,我本來以為您會幫忙。現在看來,我真是笨蛋。」
法務主還要再說,毓峍卻已把門關上。她用背抵著門,終於無法克制地啜泣起來,身子一軟,沿著門慢慢滑下。時間過去,夕陽的光線射進宅裡,染上一層薄薄的哀愁;毓峍不知自己哭了多久,等她止住淚,一個深切的體會悄然降臨。
會來安慰自己的人,都已不在了。
這座宅子已是失去靈魂的空殼,是搖搖欲墜的殘跡。過去她傷心時,父親會來摸摸她的背,墨冬會舔她的手──墨冬是她養的北極狼,一身白毛如雪般純淨,附近的人都以為牠是狗,她也懶得解釋。臺灣沒有北極狼,墨冬是父親的露西亞友人贈送的,牠陪毓峍渡過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就像她的家人。
她多希望父親、墨冬還在啊。但她想起父親的屍體──警察帶她去看,讓她領回──父親咽喉上的傷口,就像連她的心一同刺穿。「死」本是虛無飄渺的,卻在那瞬間降臨,結結實實地提醒她父親已死。
雖然沒發現墨冬的屍體,但墨冬若活著,一定會回來。何況「K」殺死父親時,墨冬不可能不捨身護主。所以墨冬必是死了,只是發生什麼事,讓牠的屍體不在現場。荒謬的是,家裡反而出現一具貓屍!一開始毓峍不知道,後來聽鄰居說,才知被警察清理了。墨冬失蹤,卻出現一隻貓,這是什麼惡質玩笑?若這是「K」的惡作劇,毓峍真會氣到發抖。
那些被「K」大鬧一番破壞的傢俱,有些還堆在牆角,不知該怎麼辦。父親收藏的書畫,有些被破壞,只能打開看看有沒有救。說是這麼說,她也不知能不能修復。這是真正的人事全非。「K」不只殺了人,還將能供她回憶的物也破壞了。但不可能完全破壞,她感到記憶陰魂不散地在每個角落低語,喃喃訴說逝去的溫暖。
每個地方都有父親的表情、墨冬的低鳴。
毓峍默然回到房裡,腳步飄忽,彷彿化為死者的陰影。她點起電燈,造型典雅的賽璐璐燈罩融融地亮了,在她臉上勾出金色的筆畫。她從抽屜底層翻出紋飾精緻的琺瑯盒,打開一看,裡面是半滿的黑墨,在燈光下閃閃發光,像沉著一彎金月。毓峍盯著墨沉思,從旁拿起毛筆,沾了點墨。
接下來發生的事,或許稱得上「不可思議」。儘管這樣,住持還是感謝徐貢元帶了個好頭,決定贈送他一對旗杆。徐貢元說:「我本無功勞,承蒙住持錯愛,這旗杆就不能樹在外面了,因為會丟人現眼。只好放在大樑上架著,每一百年拿出來出一回新。等到哪一年,我繁昌縣能有一百炷『華山會』朝九華山時,我的旗杆再樹出來,以表示紀念。」
住持知道,繁昌是不可能一次有一百炷香會朝九華的。徐貢元這麼說,分明是不肯將旗杆樹在外面,讓風吹雨淋而腐朽。於是,他也順勢說了句相襯的話:「等到你繁昌能有百炷會朝九華時,我從青陽結絡子,一直結到我九華山上來,表示歡迎。」青陽城離九華山六十里路,從那裡結絡子上九華山,也是不可能的。於是,徐貢元的旗杆總是架在觀音閣的大樑上,每一百年才給出一回新。
這樣,旗杆永遠不會壞,拜觀音菩薩的人,同時也拜謁了徐貢元的旗杆。嘉靖帝逝世後,他的兒子朱載垕當了皇帝,是為穆宗(西元一五六七 一五七二年在位)。
穆宗殺了嚴嵩,嚴嵩的女兒西宮娘娘也被貶出了皇宮。一日,徐貢元在九華山看見一位尼姑在井邊洗衣,覺得面熟,走近一看,原來卻是西宮娘娘。出於禮貌,他問候道:「娘娘,一向可好?緣何削髮為尼?」西宮娘娘回首一看,見是徐貢元,自愧無顏相見,又覺無地自容,衣也不洗了,一頭鑽進了井裡。
貢元急忙呼救,待人們把娘娘打撈上來時,已經嚥了氣。徐貢元嘆息了一番,將她安葬起來。
如今,西宮娘娘洗衣自盡的水井,還叫「娘娘井」。
徐貢元博學多才,機智敏捷,為官清廉,為民謀福,逝世四百多年了,可是關於他的故事還依舊流傳在人間。毓峍並沒有在紙上作畫,她的筆在空中一點,墨跡竟附上虛空,有如墨色的煙被收束起來,只是微微暈開──她竟直接在「世界」上作畫。同時,她身邊飄起墨色的細雨,點滴濕潤了她的頭髮、衣衫。那是溫柔異常的雨,但室內怎會下雨?事實上,不只室內下起了雨,在她作畫的方圓百尺裡,都籠罩在墨色的雨中。
「墨冬,回來吧。」毓峍低語。
一聲狼嚎,雪白的北極狼竟從墨雲中穿出,輕飄飄地踏落地面。毓峍將筆放下,輕輕抱住北極狼,她摸著「墨冬」的毛皮,感到牠的溫暖,忍不住又流下淚。她知道這是幻影,只是透過「驀霢墨」創造出來的幻覺。牠不是墨冬,甚至不能持續存在一整天。
但已能溫暖她的心靈。
在淚光中,她是帶著恨的。她清楚明白,驀霢墨就是父親被殺的原因。
驀霢墨──她不知父親怎麼會有這種不科學的事物。本來她也不信,但她還是少女時,墨冬曾死過一次;對北極狼來說,臺灣還是太炎熱。毓峍抱著墨冬的屍體痛哭,怎樣都不肯給墨冬收屍。
那時父親問她,她要讓墨冬活過來嗎?願意承擔墨冬活過來的後果嗎?毓峍哪管什麼後果,連連答應,於是溥儲便用金色的驀霢墨讓墨冬復甦。毓峍看著墨冬重新呼吸,大為驚奇。父親諄諄告誡,驀霢墨的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因為這是能動搖天命運轉的事物。
她記得父親說過,驀霢墨有三色,分別是黑、紅、金,都能翻轉陰陽變化,混淆黑白虛實。黑驀霢墨能描繪幻境、從無化虛,紅驀霢墨則用途萬端、變化無方,金驀霢墨更能顛倒日夜、無中生有、起死回生。讓墨冬復生,已悖離天理,將有報應,絕不能任意為之,更不能因擁有驀霢墨而得意。
父親的死,是否便是多年前復活墨冬的報應,毓峍不得而知。但她不信命運。畢竟,是她堅持要墨冬復活,死的怎不是她?能確定的是,父親死後,她翻遍整個家都找不到金色與紅色的驀霢墨,只剩下父親在她十六歲時送她,被她藏在抽屜夾層裡的黑驀霢墨。
驀霢墨沒道理消失。所以,「K」一定是為了驀霢墨而來。這便是父親為何會死。直到此時,毓峍仍不敢相信,有著金驀霢墨的父親居然會死。金驀霢墨的能耐,她再清楚不過了。「K」那傢伙一定用了卑鄙的手段。但問題是,「K」是怎麼知道驀霢墨存在的?父親不會到處亂說,但有很小的可能,父親基於同情──就像墨冬死去時──透露了驀霢墨的事。那麼,知情者只可能限於與父親有交流的人。
這就是警察不知道的情報,「K」極可能就是愛新覺羅溥儲認識的人!
雖說如此,毓峍她四處調查,比照之前的被害人,卻怎麼也找不到與父親的交集。能與父親相交,多半是文化界的人,被害者幾乎與此無關,這是怎麼回事?
但愛新覺羅毓峍不急。
繼續等下去,「K」一定會露出馬腳。那時,毓峍會站在「K」面前。她確實不在乎自己生命,卻不是有勇無謀;她猜想,「K」沒找到黑驀霢墨,卻沒燒掉他們家,以防萬一,是否表示「K」不知道黑驀霢墨存在?
雖然黑驀霢墨是驀霢墨中最無力的,但若「K」對此毫無防備的話──
在他們交鋒的一瞬間,毓峍或許是能活下來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