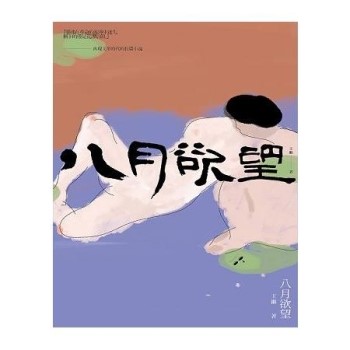師父王繼
1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2
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3
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4
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
師父王繼
1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2
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3
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4
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
1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2
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3
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4
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
師父王繼
1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2
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3
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4
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