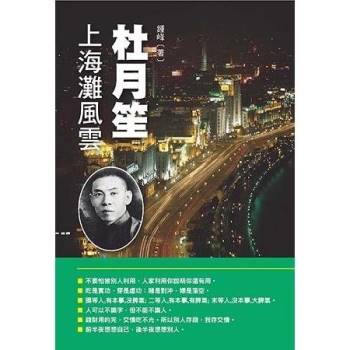貧苦童年鄉間夢
降臨人世
上海縣高橋鎮(當時官稱江蘇川沙)地處黃浦江以東,是一個不大的鎮子。其最早之雛形起之於一一○二年的宋朝,算是有近千年歷史的一座古鎮。高橋,又名翁家橋,而高橋鎮鎮東北一公里處原有清浦鎮,由於清朝初年清浦港淤積,集市便南移至高橋鎮,遂使高橋鎮擁有了商業面貌。而就在這上海縣高橋鎮的南面,則有一個小村子,當時人們都叫它杜家宅。
西元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這天,一名男嬰就在這裡出生了,而這個出生的男嬰,就是日後聞名於整個上海灘的青幫大亨―—杜月笙。
當然這個時候,剛剛出生的這個嬰兒是不知道他後來會怎樣的,更不知道自己日後會成為上海灘有名的大亨。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其他剛出生的嬰兒一樣,咧著小嘴,哇哇嚎哭,聲震屋頂。
按照中國的舊曆,農曆七月十五日這天是中元節,又俗稱「鬼節」或「盂蘭盆會」。中元節是道教的說法,「中元」之名則起於北魏時期。根據古書記載:「道經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中元節與除夕、清明節、重陽節等三節,可以說都是中國傳統節日裡祭祖的四大節日。《道藏》載:「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選眾人,分別善惡,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當時解脫。」而在民間,中元節則多在此節日懷念親人,並對未來寄予美好的祝願。
但由於杜家的這個嬰兒是在「鬼節」這天出生的,所以當村裡的人們聞知後,便一個個紛紛議論,有的說:「這個孩子將來的壽命一定不長,不是被鬼捉了去,就是沒等成年便會夭折。」也有的說:「即使不是這樣,將來這個孩子也是一身鬼氣,非奸即盜,肯定不會有什麼大出息。」
但不管別人怎樣議論,孩子終歸是自己的好,作為新生嬰兒的父親,杜文卿卻視這個孩子如珍寶。當接生婆把嬰兒包裹完畢,杜文卿就走上前來,左看右看自己兒子的模樣,最後還在孩子的小臉上親了一口。由於這個嬰兒是七月十五日的晚上所生,時當天上掛著一輪明月,因此,杜文卿便給自己剛出生的這個兒子取名「月生」,其意是指月半而生。
在中國,對於沒有文化的人來說,為孩子取名字常常都習慣於走捷徑,往往看見什麼,就為孩子取個什麼。比如在孩子出生時,如果看見一棵樹,常常就會起個「樹森」或「森林、樹林」。倘若沒看見什麼,卻聞見了鐘聲,那麼十有八九,就會為自己的新生孩子取名不是「楊樹聲」,就會是「李樹聲」。總之,沒有聲音的名字,就絕對不會為孩子取的。杜文卿這次,當然也不能例外,好在當時他看見的是一輪十五的月亮,為兒子起名「月生」。
但在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的是,由於當時杜文卿為兒子起名「月生」,自然他兒子的全名就叫「杜月生」,而非「杜月笙」。有關「杜月笙」這個名字,還是因為日後杜月生發跡了,才由當時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給改的,將原來的「月生」,變成了「月笙」,雖只一字之差,卻也頗有出處,在後文中將做詳解。在這裡,根據當時實際,也不想篡改歷史,故在行文中依然用原來杜文卿為兒子所起的「杜月生」這個名字。
再有,西元一八八八年,這個數字看著很吉利,如果用今天人們的想法來解釋,那就是「要發發發」。可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卻是多事之秋,先是在京城、山東、東北奉天等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震,使很多住戶房倒屋塌。繼而,安徽懷寧等地又發生了水災,大水汪洋四溢,令許多家庭殘受水災的迫害,失去家園。
當然,這一年多少也是有些好事的,那就是在這一年,臺灣首次建省,且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上任。再者,就是這年的12月17日,北洋水師在山東威海衛的劉公島正式成立,使得清朝有了一支海軍隊伍。
然可悲的卻是,北洋水師名義上是建立了,但很多用於軍事建設的經費,卻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了,她拿著用於建設北洋水師的一大筆錢軍費,去興建供她消暑度假的頤和園。
一個國家,如果最高的實權領導者為了自己玩得高興、玩得開心,而拿自己的國家命運開玩笑,那麼,這個國家注定就會被別的國家所欺負,也注定不會在軍事上強大,甚至還會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
當時慈禧太后想:「我一個女人家,眼瞅就快六十的人了,我還能玩幾年?我不就是挪用點兒軍事建設的經費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這些年扶持清朝的兩個皇帝,可謂嘔心氣血,我容易嗎我!」但不管慈禧太后是什麼心態,反正她這個女人後來是把北洋水師給害慘了,不僅全軍覆沒,而且由她這個女人當政的清朝,還要向日本侵略者賠款。
而作為平民百姓,才不管什麼國家大事呢!只要自己一家人活得好,不愁吃,不愁穿,再有些錢花,那就知足了。
可杜月生出生後的命運很不好,情形就像當時的清朝一樣,命運多艱。因為自他一生下來,母親就缺少奶水,只能拿米糊糊來餵食。同時,他母親的身體也變得非常虛弱,大有風一吹,人就倒的情形。還有,以往當富貴人家添人進口生了小孩子時,往往都有親朋好友前來登門祝賀,以示恭喜。而作為主家,再擺上幾桌或者幾十桌酒席,然後相互推杯把盞,彼此熱鬧一番。但杜家不是名門望族,更不是達官顯貴,就在杜月生出生之時,他的父親杜文卿也只不過算個小商人,與人合夥開了一個小米店,藉以維持生計養家糊口罷了。
杜文卿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地處上海楊樹浦,杜家宅距離那裡有二十餘里之遙。眼見自己有了兒子,當時的杜文卿的心裡很是歡喜,但喜過之後,便是憂。喜的是自己有了個兒子,等自己將來老了,也就有了依靠,至少養老送終的人有了。而憂的是,自己與人合夥在楊樹浦開的那個小米店,經營得並不景氣,真可以說是世事維艱。儘管如此,但為了維持家庭的生計,於是杜文卿沒等孩子滿月便又去了楊樹浦,打理小米店的生意。杜文卿一走,家中便只剩妻子朱氏不但要照顧自己,同時也要擔負起照顧剛剛出生不久的兒子。
在中國,無論哪朝哪代,對於平常百姓而言,吃飯問題歷來是首要問題。只要能吃飽肚子,他們便甘願無錢可花,甘願被有錢有權有勢的人欺負。而作為杜月生的父親杜文卿,就是這樣百姓中的一個分子。
在與人合夥開小米店之前,杜月生的父親曾在茶館裡當「茶博士」,所謂的「茶博士」,也就是個在茶館裡當跑堂的,沏茶倒水,幹著伺候人的營生且被人呼來喚去。後來,他又在碼頭上幹過「扦子手」,負責檢驗貨物,職務形如碼頭上的一種丁役,也是沒有什麼身分和地位的,常常還要受當頭的氣。
當然作為一個人,除了安分守己討生活外,都是渴望自家的衣食無憂,渴望闔家能夠經常團聚在一起的。然而渴望終究是渴望,畢竟不是現實。也就是說,現實距渴望的那種場景太遠了,使你無法觸及。
為了生存,為了剛剛出生的兒子,這時候的杜文卿回到楊樹浦後,唯一的想法就是趁自己還有體力,還能摸爬滾打,要下力氣把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經營得好起來,能攢下幾個錢,以便支應家裡的開銷,和兒子日後的讀書所用花費。
可是杜文卿回到楊樹浦的小米店沒多久,上海一帶就開始鬧旱災,旱得土地裂出一道道口子,就連黃浦江的水位也下退許多。但令人沒有到的是,當旱災剛剛過去,時間到了一八八九年的夏秋之際,上海地區又鬧起了水災,接連幾十天都是大雨連綿,使去年旱裂的土地又變成了水鄉澤國。那時節放眼一望,到處是白亮亮的水,汪洋得令人心中膽寒。面對這種自然災害,平民百姓是無能為力的,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外出逃荒,就是在家中忍饑受餓,為此還出現了賣兒賣女度艱難的現象。可即使這樣,災難還沒有結束,緊跟著又發生了瘟疫。
當時在上海高橋鎮一帶,十里八村餓殍遍地,真可謂在人們寒冷苦難的心上,憑空又給添加上了一層冰霜。見此情狀,杜月生的母親朱氏害怕兒子也染上這種瘟疫,因此在無奈之下,只好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杜月生離開杜家宅,徒步行走二十餘里前往楊樹浦,去投奔那裡的丈夫杜文卿。可當朱氏見到丈夫之後才知道,杜文卿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在天災之下,因米價暴漲已無力進貨,守著的已是一個空攤子。
如此生活際遇,愁得杜文卿整日眉目不展,唉聲歎氣。好在合夥人還算通情達理,災難之下沒有撤股,反倒勸慰杜文卿說:「老杜,你想開些,天災也不是咱們所能左右的,只要人無災有個好身體,就是活人的本錢。」
朱氏本是個很要強的女人,眼見丈夫整日愁眉苦臉,就提出自己去做工。當時,楊樹浦有兩家絲廠,因缺人手正在招工,所以朱氏就想到絲廠裡去。初始杜文卿一聽,很不贊同這事,認為朱氏出去做工掙錢會使自己很沒有面子。朱氏見丈夫反對,於是就氣了,對杜文卿說:「面子,面子,面子能值幾個錢?沒有錢花沒有飯吃,那才是真正的沒有面子。」結果朱氏一狠心,便給剛滿周歲的杜月生斷了奶,進了一家絲廠當女工。
杜文卿所以反對妻子朱氏去做工,除了看重自己的面子外,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這時候的妻子朱氏,又懷有了身孕。他認為這時的朱氏,理應在家休養,不該再去勞累自己的身體。
朱氏剛進了絲廠時,心情是很激動的,也猜想如果自己一年這麼做下來,雖不能攢下什麼錢,但至少自家的日子會比原來要好得多。可朱氏沒料到的是,她在這家絲廠只做了幾個月的工,吃力的勞動就把身懷六甲的她,累出了病來了,使她不得不回家休養。
在朱氏養病的時候,瘟疫雖然已經過去,可人們的苦難卻沒有過去。由於缺少吃的,朱氏的身影常常出現在村外的野地裡,像其他村裡還活著的人一樣,在野地裡尋挖野菜,回來煮熟當飯吃。
一天,杜月生的外婆來了,眼見自己的女兒形銷骨瘦,而自己又無法接濟,不覺母女兩個便抱頭痛哭起來。她們這麼一哭,小小的杜月生便也哭。當然他們彼此哭的原因不同,大人們哭的原因是因為老天太不長眼睛了,為何在災難之上,還要增添災難。而小孩子杜月生哭則是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而且母親每日餵給自己的飯食,有一半都是苦苦的野菜。
日後,當杜月生八歲時,外婆曾經給他講起過這個時候的事情說,孩子,你小時候都是吃野菜活過來的,你怎麼不記得了?整日你就知道在外面瘋跑,你什麼時候才能懂事呢?
但是,這個時候的杜月生,剛要牙牙學語,根本還不懂得什麼是野菜,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中的磨難與蒼涼。可接下來,更大的磨難又光臨在了杜月生的身上,雖然他依然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降臨人世
上海縣高橋鎮(當時官稱江蘇川沙)地處黃浦江以東,是一個不大的鎮子。其最早之雛形起之於一一○二年的宋朝,算是有近千年歷史的一座古鎮。高橋,又名翁家橋,而高橋鎮鎮東北一公里處原有清浦鎮,由於清朝初年清浦港淤積,集市便南移至高橋鎮,遂使高橋鎮擁有了商業面貌。而就在這上海縣高橋鎮的南面,則有一個小村子,當時人們都叫它杜家宅。
西元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這天,一名男嬰就在這裡出生了,而這個出生的男嬰,就是日後聞名於整個上海灘的青幫大亨―—杜月笙。
當然這個時候,剛剛出生的這個嬰兒是不知道他後來會怎樣的,更不知道自己日後會成為上海灘有名的大亨。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其他剛出生的嬰兒一樣,咧著小嘴,哇哇嚎哭,聲震屋頂。
按照中國的舊曆,農曆七月十五日這天是中元節,又俗稱「鬼節」或「盂蘭盆會」。中元節是道教的說法,「中元」之名則起於北魏時期。根據古書記載:「道經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中元節與除夕、清明節、重陽節等三節,可以說都是中國傳統節日裡祭祖的四大節日。《道藏》載:「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選眾人,分別善惡,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當時解脫。」而在民間,中元節則多在此節日懷念親人,並對未來寄予美好的祝願。
但由於杜家的這個嬰兒是在「鬼節」這天出生的,所以當村裡的人們聞知後,便一個個紛紛議論,有的說:「這個孩子將來的壽命一定不長,不是被鬼捉了去,就是沒等成年便會夭折。」也有的說:「即使不是這樣,將來這個孩子也是一身鬼氣,非奸即盜,肯定不會有什麼大出息。」
但不管別人怎樣議論,孩子終歸是自己的好,作為新生嬰兒的父親,杜文卿卻視這個孩子如珍寶。當接生婆把嬰兒包裹完畢,杜文卿就走上前來,左看右看自己兒子的模樣,最後還在孩子的小臉上親了一口。由於這個嬰兒是七月十五日的晚上所生,時當天上掛著一輪明月,因此,杜文卿便給自己剛出生的這個兒子取名「月生」,其意是指月半而生。
在中國,對於沒有文化的人來說,為孩子取名字常常都習慣於走捷徑,往往看見什麼,就為孩子取個什麼。比如在孩子出生時,如果看見一棵樹,常常就會起個「樹森」或「森林、樹林」。倘若沒看見什麼,卻聞見了鐘聲,那麼十有八九,就會為自己的新生孩子取名不是「楊樹聲」,就會是「李樹聲」。總之,沒有聲音的名字,就絕對不會為孩子取的。杜文卿這次,當然也不能例外,好在當時他看見的是一輪十五的月亮,為兒子起名「月生」。
但在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的是,由於當時杜文卿為兒子起名「月生」,自然他兒子的全名就叫「杜月生」,而非「杜月笙」。有關「杜月笙」這個名字,還是因為日後杜月生發跡了,才由當時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給改的,將原來的「月生」,變成了「月笙」,雖只一字之差,卻也頗有出處,在後文中將做詳解。在這裡,根據當時實際,也不想篡改歷史,故在行文中依然用原來杜文卿為兒子所起的「杜月生」這個名字。
再有,西元一八八八年,這個數字看著很吉利,如果用今天人們的想法來解釋,那就是「要發發發」。可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卻是多事之秋,先是在京城、山東、東北奉天等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震,使很多住戶房倒屋塌。繼而,安徽懷寧等地又發生了水災,大水汪洋四溢,令許多家庭殘受水災的迫害,失去家園。
當然,這一年多少也是有些好事的,那就是在這一年,臺灣首次建省,且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上任。再者,就是這年的12月17日,北洋水師在山東威海衛的劉公島正式成立,使得清朝有了一支海軍隊伍。
然可悲的卻是,北洋水師名義上是建立了,但很多用於軍事建設的經費,卻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了,她拿著用於建設北洋水師的一大筆錢軍費,去興建供她消暑度假的頤和園。
一個國家,如果最高的實權領導者為了自己玩得高興、玩得開心,而拿自己的國家命運開玩笑,那麼,這個國家注定就會被別的國家所欺負,也注定不會在軍事上強大,甚至還會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
當時慈禧太后想:「我一個女人家,眼瞅就快六十的人了,我還能玩幾年?我不就是挪用點兒軍事建設的經費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這些年扶持清朝的兩個皇帝,可謂嘔心氣血,我容易嗎我!」但不管慈禧太后是什麼心態,反正她這個女人後來是把北洋水師給害慘了,不僅全軍覆沒,而且由她這個女人當政的清朝,還要向日本侵略者賠款。
而作為平民百姓,才不管什麼國家大事呢!只要自己一家人活得好,不愁吃,不愁穿,再有些錢花,那就知足了。
可杜月生出生後的命運很不好,情形就像當時的清朝一樣,命運多艱。因為自他一生下來,母親就缺少奶水,只能拿米糊糊來餵食。同時,他母親的身體也變得非常虛弱,大有風一吹,人就倒的情形。還有,以往當富貴人家添人進口生了小孩子時,往往都有親朋好友前來登門祝賀,以示恭喜。而作為主家,再擺上幾桌或者幾十桌酒席,然後相互推杯把盞,彼此熱鬧一番。但杜家不是名門望族,更不是達官顯貴,就在杜月生出生之時,他的父親杜文卿也只不過算個小商人,與人合夥開了一個小米店,藉以維持生計養家糊口罷了。
杜文卿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地處上海楊樹浦,杜家宅距離那裡有二十餘里之遙。眼見自己有了兒子,當時的杜文卿的心裡很是歡喜,但喜過之後,便是憂。喜的是自己有了個兒子,等自己將來老了,也就有了依靠,至少養老送終的人有了。而憂的是,自己與人合夥在楊樹浦開的那個小米店,經營得並不景氣,真可以說是世事維艱。儘管如此,但為了維持家庭的生計,於是杜文卿沒等孩子滿月便又去了楊樹浦,打理小米店的生意。杜文卿一走,家中便只剩妻子朱氏不但要照顧自己,同時也要擔負起照顧剛剛出生不久的兒子。
在中國,無論哪朝哪代,對於平常百姓而言,吃飯問題歷來是首要問題。只要能吃飽肚子,他們便甘願無錢可花,甘願被有錢有權有勢的人欺負。而作為杜月生的父親杜文卿,就是這樣百姓中的一個分子。
在與人合夥開小米店之前,杜月生的父親曾在茶館裡當「茶博士」,所謂的「茶博士」,也就是個在茶館裡當跑堂的,沏茶倒水,幹著伺候人的營生且被人呼來喚去。後來,他又在碼頭上幹過「扦子手」,負責檢驗貨物,職務形如碼頭上的一種丁役,也是沒有什麼身分和地位的,常常還要受當頭的氣。
當然作為一個人,除了安分守己討生活外,都是渴望自家的衣食無憂,渴望闔家能夠經常團聚在一起的。然而渴望終究是渴望,畢竟不是現實。也就是說,現實距渴望的那種場景太遠了,使你無法觸及。
為了生存,為了剛剛出生的兒子,這時候的杜文卿回到楊樹浦後,唯一的想法就是趁自己還有體力,還能摸爬滾打,要下力氣把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經營得好起來,能攢下幾個錢,以便支應家裡的開銷,和兒子日後的讀書所用花費。
可是杜文卿回到楊樹浦的小米店沒多久,上海一帶就開始鬧旱災,旱得土地裂出一道道口子,就連黃浦江的水位也下退許多。但令人沒有到的是,當旱災剛剛過去,時間到了一八八九年的夏秋之際,上海地區又鬧起了水災,接連幾十天都是大雨連綿,使去年旱裂的土地又變成了水鄉澤國。那時節放眼一望,到處是白亮亮的水,汪洋得令人心中膽寒。面對這種自然災害,平民百姓是無能為力的,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外出逃荒,就是在家中忍饑受餓,為此還出現了賣兒賣女度艱難的現象。可即使這樣,災難還沒有結束,緊跟著又發生了瘟疫。
當時在上海高橋鎮一帶,十里八村餓殍遍地,真可謂在人們寒冷苦難的心上,憑空又給添加上了一層冰霜。見此情狀,杜月生的母親朱氏害怕兒子也染上這種瘟疫,因此在無奈之下,只好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杜月生離開杜家宅,徒步行走二十餘里前往楊樹浦,去投奔那裡的丈夫杜文卿。可當朱氏見到丈夫之後才知道,杜文卿與人合夥開的這個小米店在天災之下,因米價暴漲已無力進貨,守著的已是一個空攤子。
如此生活際遇,愁得杜文卿整日眉目不展,唉聲歎氣。好在合夥人還算通情達理,災難之下沒有撤股,反倒勸慰杜文卿說:「老杜,你想開些,天災也不是咱們所能左右的,只要人無災有個好身體,就是活人的本錢。」
朱氏本是個很要強的女人,眼見丈夫整日愁眉苦臉,就提出自己去做工。當時,楊樹浦有兩家絲廠,因缺人手正在招工,所以朱氏就想到絲廠裡去。初始杜文卿一聽,很不贊同這事,認為朱氏出去做工掙錢會使自己很沒有面子。朱氏見丈夫反對,於是就氣了,對杜文卿說:「面子,面子,面子能值幾個錢?沒有錢花沒有飯吃,那才是真正的沒有面子。」結果朱氏一狠心,便給剛滿周歲的杜月生斷了奶,進了一家絲廠當女工。
杜文卿所以反對妻子朱氏去做工,除了看重自己的面子外,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這時候的妻子朱氏,又懷有了身孕。他認為這時的朱氏,理應在家休養,不該再去勞累自己的身體。
朱氏剛進了絲廠時,心情是很激動的,也猜想如果自己一年這麼做下來,雖不能攢下什麼錢,但至少自家的日子會比原來要好得多。可朱氏沒料到的是,她在這家絲廠只做了幾個月的工,吃力的勞動就把身懷六甲的她,累出了病來了,使她不得不回家休養。
在朱氏養病的時候,瘟疫雖然已經過去,可人們的苦難卻沒有過去。由於缺少吃的,朱氏的身影常常出現在村外的野地裡,像其他村裡還活著的人一樣,在野地裡尋挖野菜,回來煮熟當飯吃。
一天,杜月生的外婆來了,眼見自己的女兒形銷骨瘦,而自己又無法接濟,不覺母女兩個便抱頭痛哭起來。她們這麼一哭,小小的杜月生便也哭。當然他們彼此哭的原因不同,大人們哭的原因是因為老天太不長眼睛了,為何在災難之上,還要增添災難。而小孩子杜月生哭則是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而且母親每日餵給自己的飯食,有一半都是苦苦的野菜。
日後,當杜月生八歲時,外婆曾經給他講起過這個時候的事情說,孩子,你小時候都是吃野菜活過來的,你怎麼不記得了?整日你就知道在外面瘋跑,你什麼時候才能懂事呢?
但是,這個時候的杜月生,剛要牙牙學語,根本還不懂得什麼是野菜,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中的磨難與蒼涼。可接下來,更大的磨難又光臨在了杜月生的身上,雖然他依然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