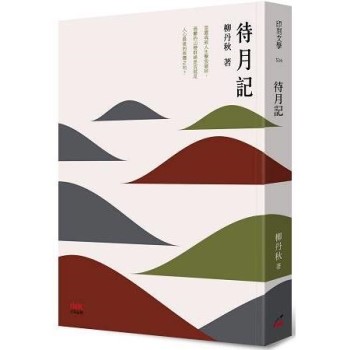溯洄行
No.85日文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2.11 │徒然
我在日文補習班認識凜,算起來也不過兩年多。那時候還在讀研究所,論文幾乎完成,已篤定自己可以畢業,也和教授談妥會繼續留在學校當助理,但除此之外,我沒有任何目標,不曉得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日子過得渾渾噩噩。學日文是少數我還能感到有趣的事物,至少給我動力重新打開書本。自從論文完成後,我的眼睛似乎對文字產生排斥力,我已很少碰漫畫或雜誌以外的書籍。
補習班的常設日文班,幾乎全數學員都是女性,特別是上班族。每個人的目的都不同。有上班族為了通過檢定以便升職加薪,有日文系的學生,也有不少人剛畢業或正考慮未來出路,而日本導遊執照向來相當熱門。組成人員經常改變,不過凜似乎待得相當久。上課時總是坐到最後一排,遙遙觀望班上的動靜,顯得懶洋洋。老師好像也已習慣她這副模樣。偶爾我會坐在凜旁邊,聽她相當熟稔的議論課堂狀況。這時教室看起來格外遙遠,就像走在夜晚的街道上,瞥見櫥窗裡有個亮著綠光的水族箱。
「老師又在講名牌了。」凜說。
「嗯。」我答道。
「提到日本的名牌皮包就沒完沒了。」
「是喔。」
「可以趁機休息一下。」
「工作很辛苦喔?」
「我還是學生。」
「是喔。課那麼重啊?」
「我修教育學程,這學期三十學分。」說著趴倒在桌上。
諸如此類。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一直是這樣的點頭之交。
班上若有人到日本去,總會帶回成包的糖果餅乾請客,或者是把在當地購買的紀念品帶到課堂上,讓大家傳看,意思大概和高中學測前,拜過文昌帝君的同學分送香灰的舉動雷同。有一回,班上同學帶回來的土產是東京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帽。
我照例坐在最後一排的凜旁邊,遙望前排光景。凜照例懶洋洋地開口:「老鼠耳啊……其實貓耳才是王道吧。」
「當然了。」
「而且要裝在少年身上。」
「真的。」
「有尾巴的話更好。」
「是嗎?我對尾巴倒不怎麼執著,有或沒有都沒差,重點還是在耳朵吧,一定要三角形的獸耳。」
「妳……」凜轉過臉來,好像第一次意識到有我這個人存在:「真的聽得懂我在說什麼耶。」
「聽得懂啊,不就在講貓耳少年?」
「御宅族同士?」
「御宅族同士。」
「妳該不會……妳看BL嗎?」「怎麼不看呢,那種好東西。」
我們熱烈握住彼此的手。綠光隱退,水族箱般的補習班教室頓時繁花盛開。儘管看漫畫的風氣目前相當普遍,真正沉迷其中、熟悉各項術語的御宅族其實沒那麼多。要碰見連閱聽口味都相近的同好,更是難上加難。有時當我回想此事,會惱恨凜為何要挑中我,似乎這麼想就可以把責任歸咎於她。
事實是如此:我們之間沒有誰搭上誰,而是一拍即合。錯的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合稱宿命。
火山──間狂言。A Teatime Play
人物:一對男女
地點:台北
(天空是黑色的,雨也是。黑雨滂沱。女提手提袋,撐傘,靜止站立,像走到一半忽然停格)
女:喂─!救命啊!幫幫忙啊!
(撐傘背背包的男,快步經過,在離女一段距離處停下)
男:不能停下腳步!這是硫酸雨,一旦停下超過三秒,鞋底就會融解黏在地上。
女:為什麼突然下起硫酸雨?
男:妳不知道?為減緩溫室效應,聯合國呼籲所有擁有活火山或休火山的國家引爆火山,讓火山灰阻斷太陽輻射,所以政府引爆大屯山,然後就下起硫酸雨啦。
女:我們又不是聯合國成員。
男:但我們很想加入,所以總是默默照做,以為只要付出夠多不求回報的愛,哪天終究還是會有回報。知道了就快逃。
(想要離開,突然發現動彈不得)
女:……對不起,看來你跟我一樣了。
(相對無言)
女:為什麼鞋子會融化,雨傘不會?
男:新一代的抗UV塗層可以暫時抵擋一陣子。
女:看來我們應該感謝太陽輻射。
男:有時候敵人和朋友一體兩面。
女:(頓)你知道這故事嗎?
男:不知道。
女:我還沒說。
男:所以啊。這是個邏輯問題─妳還沒說出口的事,我怎麼可能知道?
女:不要打岔嘛!這是現場氣氛的問題。我不是真想知道你知不知道,而是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我都要說,OK?
男:我了,就像記者採訪前都會說「可以耽誤你一下嗎?」而你還來不及說「不可以,沒空」,他們就擅自開始了。他們根本不想聽你答覆。(女,瞪視)歹勢,請講。
女:有個攀岩高手,獨自攀岩的時候被落石壓住手臂。他被困在那五天都沒人經過,最後自己鋸斷手臂下山求救。如果我們的鞋子被黏住,也許應該脫掉鞋子,光腳……
男:走進硫酸裡嗎?這招還是等沒別的辦法的時候再用吧。如果我是那個攀岩高手,我寧可死在山上。(頓)妳袋子裡裝了什麼?
女:怎樣?男:我在想我們帶的東西,不知道夠不夠拿來墊腳走到沒雨的地方。
(男和女各自翻看背包,女拿出塑膠保鮮盒放到地上,脫鞋子踏上)
女:(環保標語語氣)「人類會消失,塑膠會留下」。(保鮮盒開始逐漸融化)
男:看樣子連塑膠也不會留下了。
(女從手提袋拿出半打裝的啤酒)
男:為什麼帶著這個?
女:你說前陣子引爆火山嘛。這幾天一直有地震,天空又那麼黑,我以為世界要毀滅了,所以帶啤酒去找我男朋友,打算一起醉死算了。
男:那為什麼還在?
女:我們不愧是情侶,心意相通,他也以為是世界末日。只是他約了劈腿對象一塊喝酒。
男:你們應該多看新聞。
女:我早把電視砸了,當我曉得新聞是一場陰謀的時候。
男:什麼陰謀?
女:培養冷血戰士的陰謀啊。新聞每天播出那麼多悲慘消息,一定是個陰謀,為了讓我們逐漸麻木,變成冷血戰士,為國打仗。
男:在妳考慮將來之前,先解決眼前吧。(看向斜前方)我們如果沿著同一條路線前進,就可以把兩人的東西加起來用。
女: 就這麼辦。(將啤酒罐放在往男方向的地上,改踏到啤酒罐上。保鮮盒完全融化。兩人距離稍近)前進第二步。
(男從背包裡拿出糕餅禮盒,擺在朝女的方向,脫下鞋子踏上)
男:我也前進一步。
女:隨身帶著禮盒是怎樣?
男:巴結教授用的。我今天要送論文,但我覺得不會過。
女:沒那麼糟吧。你做什麼的?
男:《論松果果鱗左旋排列與以松葉為食之高山旋角羊右旋角間之相似或相反性狀》。
女:……喔。
男:生物學。
女:什麼意思啊這題目?
男:吃松葉的山羊,牠角上的螺旋紋旋轉方向,跟松果的鱗片排列方向有沒有關係。
女:結果呢?
男:實驗證明它們毫不相關。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每次吃雞翅都只吃左翅,就會變左撇子嗎?並不會。
女:那你幹嘛還研究啊!
待月記
楓按地址來到公寓前。沒有管理員的七層樓建築,玻璃門深鎖。她停妥車子,在公寓外頭等候一陣,不見有住戶往來。
這倒是意想不到的難題。
她轉向對講機,找到經岳住的那戶,試著按幾下電鈴。毫無反應。
要是一切只是她小題大作,要是她按錯門鈴,要是有好事者路過問她在做什麼……。負面想法一如往常湧現,她努力甩開它們。搞錯的下場,大不了只是丟臉而已。丟人現眼的事,至今她做得可夠多了。她不是老早便經歷過最糟的嗎?楓如此自我催眠,吸了一口氣,開始猛拍電鈴,同時仰頭向上大喊:
「喂──!李經岳──!隊長,你聽見沒?是我,是梅伯啦──!我知道你在家,開門讓我上去!」
毫無反應。
「你不開我就繼續喊,喊到讓你鄰居叫警察!」
這招似乎奏效,門噠一聲打開。楓進公寓,按下電梯鈕上四樓,把輪椅留在電梯裡,暗自祈求一切順利。
她來到那人住處門口。
對方已把門打開一條縫,等著。
「喲,隊長。」楓說。見對方悶聲不響,她又補了句:「好久不見。」
「……梅伯。妳搞成這樣是在幹嘛?」
「誰教你不快開門,我想說不知是不是晚了。你為什麼不回我信?」
「妳說那串爆長的訊息?最好我還有力氣理妳的玩笑。」
「那不是玩笑,是關心。」
「事到如今,關心有用嗎?」
「你就是欠人關心,否則你幹嘛把細節都寫在臉書裡。」
「妳也跟其他人一樣,認為我在作秀?」經岳的語氣森森然:「這回我是不是作秀,大可走著瞧。」
「當然不是這樣。我知道木炭和火盆都是真的,不然我幹嘛來?」
「好吧,那妳就關心吧。盡量關心,看妳要用什麼理由說服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他讓到一邊去。
楓踏入室內,頓時被黑暗包圍。
她首次踏進這位經常自殺未遂的朋友家,立刻明白他做事挺賣力。割開的瓦楞紙箱遮蔽窗戶,沒開的日光燈似乎裹著玻璃紙,只有筆電螢幕大亮。透過那絲微光,她辨認出茶几上散亂著膠帶、剪刀、手機、泡麵碗、墨鏡、蛙鏡和多副眼鏡。
地上有木炭、撕成條狀的毛巾和不鏽鋼盆。
「那是以前登山社煮菜的大盆。」她說。
「是又怎樣。」
「很懷念。」
「現在是我洗鞋子用的。」
楓換了個話題。
「我沒要說服你,也沒想要改變你的想法,我來是為了之前的約定。就跟我信上說的一樣,我們約好要去北一段。」
「所以?」
「你口口聲聲嚷說要去死,所以我希望你先實踐諾言。裝備我都準備了,你跟我上車就是。如果我們好端端回來,要死要活隨你的便。」
經岳吁了一口長氣。
「跟醫生或諮商師比起來,這說法是有點新意,不過妳想拿這理由說服一個燒炭的人?如果妳來是為了一塊燒炭,我還比較有興趣。看到妳傳訊息過來,還沒讀之前,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個。」經岳露出一抹古怪微笑:「原本覺得可能性蠻大的,我現在比較可以了解妳以前在搞什麼……」「我今天是、是來邀你爬山的!一起來吧!」楓打斷他。
「妳還要囉嗦的話就算了。回去吧。」
「我、我還帶了以前爬山的相片來。說不定你看了,會想起一些爬山的樂趣之類……」她伸手在背包裡翻找。
「那妳擱桌上,然後就回去吧。」
下一瞬間,一陣突如其來的劇痛令經岳倒在地上,四肢不由自主地抽搐。
楓手上拿著電擊棒。她因緊張而大口喘氣。
接著,她迅速執行計畫好的動作:往他嘴上貼膠帶,雙手雙腳也用膠帶綑好。確定他動彈不得後,她抖著手找東西卡住門縫,出到外頭按電梯。幸好電梯還在同一樓,輪椅也還在。
她展開摺疊輪椅,把經岳拖上去。她已許久不曾拖人。從前在登山社,她幫忙扛過幾個高山症的學弟妹,以及父親復健時把他翻來搬去,都不覺得有這麼重,不過總算七手八腳把人弄上椅子。她給他戴上口罩、墨鏡、鴨舌帽、抓了雙看來還像樣的球鞋。腿部蓋上外套,遮住綑手的膠帶。
檢查家中窗戶、瓦斯、水龍頭是否確實關好,還找到他的處方藥。這並不困難,家裡到處丟著成排藥錠和眼藥,她來不及細看,姑且把它們通通收攏起來。
最後是電腦。雖然看了經岳一如往常的自殺宣言,會行動的大概只有她,不過以防萬一,楓打開他的臉書,照擬好的稿子打字──
這陣子頭腦不很清楚,但我改變主意了,打算一個人好好想下。要是聯絡不上,別擔心,我只是打算去他媽的來趟忘我之旅,放空一下。
運下樓的過程大致順利,沒撞見任何人,只是電梯口離門口的兩個台階,以及把經岳弄上汽車前座,又是一陣折騰。她實際體會到,無障礙設施的不完備多令人痛苦。
當她終於用膠帶把他像木乃伊似的黏在椅子上,自己也汗流浹背,渾身濕透,筋疲力盡地癱倒在駕駛座。
然後她拍拍他的肩膀。
「別擔心,你完全曉得我們要去哪。」楓說。
「走吧。」
那則私訊是這麼寫的──
哈囉,好久不見,我梅伯啦。場面話就省略。看你最近這樣子,我想問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北一段有個約?我們覺得那是世上最適合埋骨的所在,所以留下來的要幫先走的從山頂撒骨灰。如果你忘了,我也趁機說服你:橫豎都是不行,何不到那裡來場真正的生存遊戲?以前我們不是對《荒野求生祕技》很感興趣,說有機會一定要親身求證,看它到底是不是胡謅。現在就是機會。在我看來,你不是真想結束,只是想脫胎換骨,把現在的自己狠狠砸碎,卻苦無辦法。我覺得求生遊戲是好主意。如果你有興趣,我奉陪。
要不因為是你,我也不敢這麼提議。你是老手,即便搞砸也比現在來得好,畢竟那是你選定的最終之地。現在這樣,替你收拾的人很可憐,房子也很可憐。這只會讓你更痛恨自己。
我知道晚上很難熬,不容易思考,因此我希望你:選個心情還算平靜、天氣也不錯的早上,好好考慮,給我答覆。
我說話算話,會奉陪到底。翻遍好友名單你也找不到這麼有義氣的。
No.85日文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12.11 │徒然
我在日文補習班認識凜,算起來也不過兩年多。那時候還在讀研究所,論文幾乎完成,已篤定自己可以畢業,也和教授談妥會繼續留在學校當助理,但除此之外,我沒有任何目標,不曉得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日子過得渾渾噩噩。學日文是少數我還能感到有趣的事物,至少給我動力重新打開書本。自從論文完成後,我的眼睛似乎對文字產生排斥力,我已很少碰漫畫或雜誌以外的書籍。
補習班的常設日文班,幾乎全數學員都是女性,特別是上班族。每個人的目的都不同。有上班族為了通過檢定以便升職加薪,有日文系的學生,也有不少人剛畢業或正考慮未來出路,而日本導遊執照向來相當熱門。組成人員經常改變,不過凜似乎待得相當久。上課時總是坐到最後一排,遙遙觀望班上的動靜,顯得懶洋洋。老師好像也已習慣她這副模樣。偶爾我會坐在凜旁邊,聽她相當熟稔的議論課堂狀況。這時教室看起來格外遙遠,就像走在夜晚的街道上,瞥見櫥窗裡有個亮著綠光的水族箱。
「老師又在講名牌了。」凜說。
「嗯。」我答道。
「提到日本的名牌皮包就沒完沒了。」
「是喔。」
「可以趁機休息一下。」
「工作很辛苦喔?」
「我還是學生。」
「是喔。課那麼重啊?」
「我修教育學程,這學期三十學分。」說著趴倒在桌上。
諸如此類。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一直是這樣的點頭之交。
班上若有人到日本去,總會帶回成包的糖果餅乾請客,或者是把在當地購買的紀念品帶到課堂上,讓大家傳看,意思大概和高中學測前,拜過文昌帝君的同學分送香灰的舉動雷同。有一回,班上同學帶回來的土產是東京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帽。
我照例坐在最後一排的凜旁邊,遙望前排光景。凜照例懶洋洋地開口:「老鼠耳啊……其實貓耳才是王道吧。」
「當然了。」
「而且要裝在少年身上。」
「真的。」
「有尾巴的話更好。」
「是嗎?我對尾巴倒不怎麼執著,有或沒有都沒差,重點還是在耳朵吧,一定要三角形的獸耳。」
「妳……」凜轉過臉來,好像第一次意識到有我這個人存在:「真的聽得懂我在說什麼耶。」
「聽得懂啊,不就在講貓耳少年?」
「御宅族同士?」
「御宅族同士。」
「妳該不會……妳看BL嗎?」「怎麼不看呢,那種好東西。」
我們熱烈握住彼此的手。綠光隱退,水族箱般的補習班教室頓時繁花盛開。儘管看漫畫的風氣目前相當普遍,真正沉迷其中、熟悉各項術語的御宅族其實沒那麼多。要碰見連閱聽口味都相近的同好,更是難上加難。有時當我回想此事,會惱恨凜為何要挑中我,似乎這麼想就可以把責任歸咎於她。
事實是如此:我們之間沒有誰搭上誰,而是一拍即合。錯的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合稱宿命。
火山──間狂言。A Teatime Play
人物:一對男女
地點:台北
(天空是黑色的,雨也是。黑雨滂沱。女提手提袋,撐傘,靜止站立,像走到一半忽然停格)
女:喂─!救命啊!幫幫忙啊!
(撐傘背背包的男,快步經過,在離女一段距離處停下)
男:不能停下腳步!這是硫酸雨,一旦停下超過三秒,鞋底就會融解黏在地上。
女:為什麼突然下起硫酸雨?
男:妳不知道?為減緩溫室效應,聯合國呼籲所有擁有活火山或休火山的國家引爆火山,讓火山灰阻斷太陽輻射,所以政府引爆大屯山,然後就下起硫酸雨啦。
女:我們又不是聯合國成員。
男:但我們很想加入,所以總是默默照做,以為只要付出夠多不求回報的愛,哪天終究還是會有回報。知道了就快逃。
(想要離開,突然發現動彈不得)
女:……對不起,看來你跟我一樣了。
(相對無言)
女:為什麼鞋子會融化,雨傘不會?
男:新一代的抗UV塗層可以暫時抵擋一陣子。
女:看來我們應該感謝太陽輻射。
男:有時候敵人和朋友一體兩面。
女:(頓)你知道這故事嗎?
男:不知道。
女:我還沒說。
男:所以啊。這是個邏輯問題─妳還沒說出口的事,我怎麼可能知道?
女:不要打岔嘛!這是現場氣氛的問題。我不是真想知道你知不知道,而是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我都要說,OK?
男:我了,就像記者採訪前都會說「可以耽誤你一下嗎?」而你還來不及說「不可以,沒空」,他們就擅自開始了。他們根本不想聽你答覆。(女,瞪視)歹勢,請講。
女:有個攀岩高手,獨自攀岩的時候被落石壓住手臂。他被困在那五天都沒人經過,最後自己鋸斷手臂下山求救。如果我們的鞋子被黏住,也許應該脫掉鞋子,光腳……
男:走進硫酸裡嗎?這招還是等沒別的辦法的時候再用吧。如果我是那個攀岩高手,我寧可死在山上。(頓)妳袋子裡裝了什麼?
女:怎樣?男:我在想我們帶的東西,不知道夠不夠拿來墊腳走到沒雨的地方。
(男和女各自翻看背包,女拿出塑膠保鮮盒放到地上,脫鞋子踏上)
女:(環保標語語氣)「人類會消失,塑膠會留下」。(保鮮盒開始逐漸融化)
男:看樣子連塑膠也不會留下了。
(女從手提袋拿出半打裝的啤酒)
男:為什麼帶著這個?
女:你說前陣子引爆火山嘛。這幾天一直有地震,天空又那麼黑,我以為世界要毀滅了,所以帶啤酒去找我男朋友,打算一起醉死算了。
男:那為什麼還在?
女:我們不愧是情侶,心意相通,他也以為是世界末日。只是他約了劈腿對象一塊喝酒。
男:你們應該多看新聞。
女:我早把電視砸了,當我曉得新聞是一場陰謀的時候。
男:什麼陰謀?
女:培養冷血戰士的陰謀啊。新聞每天播出那麼多悲慘消息,一定是個陰謀,為了讓我們逐漸麻木,變成冷血戰士,為國打仗。
男:在妳考慮將來之前,先解決眼前吧。(看向斜前方)我們如果沿著同一條路線前進,就可以把兩人的東西加起來用。
女: 就這麼辦。(將啤酒罐放在往男方向的地上,改踏到啤酒罐上。保鮮盒完全融化。兩人距離稍近)前進第二步。
(男從背包裡拿出糕餅禮盒,擺在朝女的方向,脫下鞋子踏上)
男:我也前進一步。
女:隨身帶著禮盒是怎樣?
男:巴結教授用的。我今天要送論文,但我覺得不會過。
女:沒那麼糟吧。你做什麼的?
男:《論松果果鱗左旋排列與以松葉為食之高山旋角羊右旋角間之相似或相反性狀》。
女:……喔。
男:生物學。
女:什麼意思啊這題目?
男:吃松葉的山羊,牠角上的螺旋紋旋轉方向,跟松果的鱗片排列方向有沒有關係。
女:結果呢?
男:實驗證明它們毫不相關。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每次吃雞翅都只吃左翅,就會變左撇子嗎?並不會。
女:那你幹嘛還研究啊!
待月記
楓按地址來到公寓前。沒有管理員的七層樓建築,玻璃門深鎖。她停妥車子,在公寓外頭等候一陣,不見有住戶往來。
這倒是意想不到的難題。
她轉向對講機,找到經岳住的那戶,試著按幾下電鈴。毫無反應。
要是一切只是她小題大作,要是她按錯門鈴,要是有好事者路過問她在做什麼……。負面想法一如往常湧現,她努力甩開它們。搞錯的下場,大不了只是丟臉而已。丟人現眼的事,至今她做得可夠多了。她不是老早便經歷過最糟的嗎?楓如此自我催眠,吸了一口氣,開始猛拍電鈴,同時仰頭向上大喊:
「喂──!李經岳──!隊長,你聽見沒?是我,是梅伯啦──!我知道你在家,開門讓我上去!」
毫無反應。
「你不開我就繼續喊,喊到讓你鄰居叫警察!」
這招似乎奏效,門噠一聲打開。楓進公寓,按下電梯鈕上四樓,把輪椅留在電梯裡,暗自祈求一切順利。
她來到那人住處門口。
對方已把門打開一條縫,等著。
「喲,隊長。」楓說。見對方悶聲不響,她又補了句:「好久不見。」
「……梅伯。妳搞成這樣是在幹嘛?」
「誰教你不快開門,我想說不知是不是晚了。你為什麼不回我信?」
「妳說那串爆長的訊息?最好我還有力氣理妳的玩笑。」
「那不是玩笑,是關心。」
「事到如今,關心有用嗎?」
「你就是欠人關心,否則你幹嘛把細節都寫在臉書裡。」
「妳也跟其他人一樣,認為我在作秀?」經岳的語氣森森然:「這回我是不是作秀,大可走著瞧。」
「當然不是這樣。我知道木炭和火盆都是真的,不然我幹嘛來?」
「好吧,那妳就關心吧。盡量關心,看妳要用什麼理由說服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他讓到一邊去。
楓踏入室內,頓時被黑暗包圍。
她首次踏進這位經常自殺未遂的朋友家,立刻明白他做事挺賣力。割開的瓦楞紙箱遮蔽窗戶,沒開的日光燈似乎裹著玻璃紙,只有筆電螢幕大亮。透過那絲微光,她辨認出茶几上散亂著膠帶、剪刀、手機、泡麵碗、墨鏡、蛙鏡和多副眼鏡。
地上有木炭、撕成條狀的毛巾和不鏽鋼盆。
「那是以前登山社煮菜的大盆。」她說。
「是又怎樣。」
「很懷念。」
「現在是我洗鞋子用的。」
楓換了個話題。
「我沒要說服你,也沒想要改變你的想法,我來是為了之前的約定。就跟我信上說的一樣,我們約好要去北一段。」
「所以?」
「你口口聲聲嚷說要去死,所以我希望你先實踐諾言。裝備我都準備了,你跟我上車就是。如果我們好端端回來,要死要活隨你的便。」
經岳吁了一口長氣。
「跟醫生或諮商師比起來,這說法是有點新意,不過妳想拿這理由說服一個燒炭的人?如果妳來是為了一塊燒炭,我還比較有興趣。看到妳傳訊息過來,還沒讀之前,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個。」經岳露出一抹古怪微笑:「原本覺得可能性蠻大的,我現在比較可以了解妳以前在搞什麼……」「我今天是、是來邀你爬山的!一起來吧!」楓打斷他。
「妳還要囉嗦的話就算了。回去吧。」
「我、我還帶了以前爬山的相片來。說不定你看了,會想起一些爬山的樂趣之類……」她伸手在背包裡翻找。
「那妳擱桌上,然後就回去吧。」
下一瞬間,一陣突如其來的劇痛令經岳倒在地上,四肢不由自主地抽搐。
楓手上拿著電擊棒。她因緊張而大口喘氣。
接著,她迅速執行計畫好的動作:往他嘴上貼膠帶,雙手雙腳也用膠帶綑好。確定他動彈不得後,她抖著手找東西卡住門縫,出到外頭按電梯。幸好電梯還在同一樓,輪椅也還在。
她展開摺疊輪椅,把經岳拖上去。她已許久不曾拖人。從前在登山社,她幫忙扛過幾個高山症的學弟妹,以及父親復健時把他翻來搬去,都不覺得有這麼重,不過總算七手八腳把人弄上椅子。她給他戴上口罩、墨鏡、鴨舌帽、抓了雙看來還像樣的球鞋。腿部蓋上外套,遮住綑手的膠帶。
檢查家中窗戶、瓦斯、水龍頭是否確實關好,還找到他的處方藥。這並不困難,家裡到處丟著成排藥錠和眼藥,她來不及細看,姑且把它們通通收攏起來。
最後是電腦。雖然看了經岳一如往常的自殺宣言,會行動的大概只有她,不過以防萬一,楓打開他的臉書,照擬好的稿子打字──
這陣子頭腦不很清楚,但我改變主意了,打算一個人好好想下。要是聯絡不上,別擔心,我只是打算去他媽的來趟忘我之旅,放空一下。
運下樓的過程大致順利,沒撞見任何人,只是電梯口離門口的兩個台階,以及把經岳弄上汽車前座,又是一陣折騰。她實際體會到,無障礙設施的不完備多令人痛苦。
當她終於用膠帶把他像木乃伊似的黏在椅子上,自己也汗流浹背,渾身濕透,筋疲力盡地癱倒在駕駛座。
然後她拍拍他的肩膀。
「別擔心,你完全曉得我們要去哪。」楓說。
「走吧。」
那則私訊是這麼寫的──
哈囉,好久不見,我梅伯啦。場面話就省略。看你最近這樣子,我想問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北一段有個約?我們覺得那是世上最適合埋骨的所在,所以留下來的要幫先走的從山頂撒骨灰。如果你忘了,我也趁機說服你:橫豎都是不行,何不到那裡來場真正的生存遊戲?以前我們不是對《荒野求生祕技》很感興趣,說有機會一定要親身求證,看它到底是不是胡謅。現在就是機會。在我看來,你不是真想結束,只是想脫胎換骨,把現在的自己狠狠砸碎,卻苦無辦法。我覺得求生遊戲是好主意。如果你有興趣,我奉陪。
要不因為是你,我也不敢這麼提議。你是老手,即便搞砸也比現在來得好,畢竟那是你選定的最終之地。現在這樣,替你收拾的人很可憐,房子也很可憐。這只會讓你更痛恨自己。
我知道晚上很難熬,不容易思考,因此我希望你:選個心情還算平靜、天氣也不錯的早上,好好考慮,給我答覆。
我說話算話,會奉陪到底。翻遍好友名單你也找不到這麼有義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