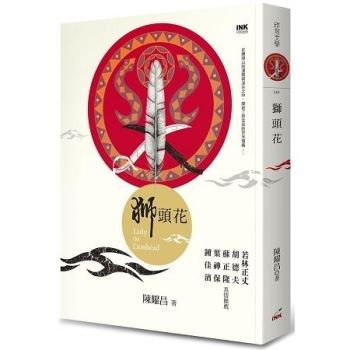楔子
楓港德隆宮外,鑼鼓聲喧天價響,圍觀的不但有大批民眾,還有電視台的衛星轉播車,把小小廟口圍得水泄不通。
寺廟內,穿著湖綠色夾克的女性總統候選人,捧著大束鮮花,向神明恭恭敬敬行禮。在幕僚及隨扈的簇擁之下,她緩緩自廟裡走出,站在廟口台階上,一臉自信,接受群眾歡呼。披著紅色布條的寺廟主委站在她身旁,高舉雙手,興奮呼喊:「五府千歲降旨,我們這次一定當選!」民眾馬上也跟著興奮高呼:「凍蒜!凍蒜!」
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與響徹雲霄的歡呼聲中,女性總統候選人滿臉笑容,接過麥克風,向群眾揮手致詞。她的語氣卻是出奇平靜:「我們誓言要點亮台灣。總統競選的最後一里路,現在,自楓港,我最愛的故鄉-出-發-!」
離楓港幾十公里外的台東安朔,白髮蒼蒼卻依然壯碩挺拔的他,滿意地看著這個電視的實況轉播鏡頭,眼眶微濕。他自一大早就守著電視,終於讓他等到這一刻。去年年底,這位女性總統候選人來到屏東獅子鄉,公開向群眾及媒體宣布,她有來自獅子鄉的四分之一排灣血統,並且親筆在表格上寫下她的族別是「排灣」。從那一刻開始,他就成為她的死忠支持者。他沒想到,在他有生之年,有幸目睹這樣的鏡頭。排灣出頭了,大龜文出頭了。這個明年很可能成為總統的小女生,公開表示以擁有排灣血統為榮,他感動了。儘管只有四分之一,或是有些人說的八分之一,他已無憾。
「大龜文」或「大龜紋」(註1:大龜文:Tjaquvuquvulj。)這個名稱,在十七世紀荷蘭時代文獻即有記載。大龜文的祖先們經過漫長的遷徙與整合,數百年來在率芒溪以南,楓港溪以北之間的枋山溪(大龜文溪)的山林與河谷,再加上東部太平洋岸阿塱衛溪流域,建立了一個超級部落聯合體,被稱為「大龜文十八社」或「上琅嶠十八社」,事實上已具有族邦,甚至小王國的雛型。
回憶歷史,讓他痛心。因為但大龜文之名在最近一百年已不復見於官方文書,也在民間消失。幾十年來,他一直自稱為「大龜文王國國王」。其實,他的真意不在國王或王國,而是為了保存「大龜文」這個祖靈留下來的寶貴稱號。
荷蘭時代,大龜文和熱蘭遮城總督的關係時好時壞。大龜文雖有時也參加荷蘭長官召開的地方會議,但大半時間相應不理。惱羞成怒的荷蘭人終於在一六六一年進攻大龜文,結果不但未能得勝,反讓外來的鄭成功漁翁得利,順勢圍攻熱蘭遮城。鄭氏東寧時期,雖有少數閩粵移民開始進入琅嶠,東寧部隊也在獅頭山下沿海一帶進出,但大抵兩邊相安無事。
清國自康熙至同治年間,把治台範圍自限在枋寮、加祿堂以北,因此大龜文屬於「治理不及,化外之地」。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國改弦易轍,「開山撫番」成為新政策,於是一八七五年爆發了台灣第一場原住民對抗清國的大戰。這是大龜文命運的轉捩點。
到了日本據台,一九一四年的「南蕃事件」,更造成了大龜文諸部落的大遷徙。更不堪的是,「大龜文」竟自此被矮化成「內文」。自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到來,過去的大龜文溪,現在稱枋山溪的流域被劃歸為「屏東縣獅子鄉」;阿塱衛溪流域則成為「台東縣達仁鄉」。大龜文不但名號不見了,連地域都被切割分屬兩個不同的縣。這令身為大龜文領導家族後人的他,更加憂心「大龜文」或從此永遠走入歷史。他終日念念在茲,希望「大龜文」的榮光能夠重現台灣;他不甘心大龜文被遺忘,於是開始自稱「大龜文國王」。
自加祿到楓港海邊,山海交接,景觀雄偉,遠望像是一群巨獅雄踞海邊,獅頭遙望大海,獅身與獅尾則成為那雲深不知處的大龜文地域。海邊的漢人墾民,稱獅頭山這一帶的部落族群「獅頭社群」。後來的獅子鄉也因此得名。獅頭社群因為與海邊漢人移民村落非常接近,雙方常有來往。這位女總統候選人的排灣血統,聽說就是來自獅頭社一帶。雖然這只是大家的傳聞,女總統候選人本人一直沒有出面證實。
「獅頭社…」老人不禁咧嘴笑了出來。這太有趣了。常被合稱為獅頭社的外獅(Uwaljudj)及內獅(Acedas),正是當年對抗清國最英勇的部落。
在他支持這位女總統候選人之前,他對這些海邊平地人,也就是在過去二百年來一直欺凌大龜文的「白浪」,其實相當不滿,甚至有恨意的。他們大龜文人,不,整個島嶼的原住民,因為大批白浪移民排山倒海而來,失去了祖靈留下來的大部分土地,失去了祖靈留下來的悠久傳統。所有姓名、家系、服飾、制度、習俗…,甚至語言,一切都白浪化了。他一直好痛心,好反感。諷刺的是,為了反制,他反必須去唸白浪的大學與研究所,拿白浪的學位,比當年先人上「番學堂」還更投入。這一切,太無奈又太荒謬了。
然而,他的努力始終孤掌難鳴。一直沒有幾個白浪知道「大龜文」這個名字,連學界都不重視。一直要到這幾年,大家開始強調這個島嶼的主體性,白浪後代開始認真回顧這個島嶼的歷史,對這個島嶼的原始主人才慢慢尊重起來,也開始以自己能擁有「番仔」DNA為榮。原住民文化與藝術也開始被重視。這位女性候選人還公開表示,她如果當選,會以總統身分公開向原住民致歉者。這讓他的眼淚差點掉下來。
終於,他的「大龜文王國」可以慢慢撥雲見日了。大家已漸漸體認,最好的方向是這個島的多元原住民族群和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多元移民族群,來共組彩虹般的多元文化。他很高興看到原、漢由對立霸凌而漸漸走上合作共榮的路,雖然離理想還相當非常遙遠。更遺憾的是,原住民社會許多失去的傳統已經回不來了。
電視上又出現這位女性總統候選人的鏡頭。
他對她的身世,當然極為好奇。由地緣關係看來,她的祖先不只是來自排灣,而且應該是來自大龜文。
依家族的口述歷史,他的祖先就是在一八七五年那場歷史性戰役中,率領大龜文族人與「官兵」奮勇作戰了好幾個月的大頭目。後來更被清廷冊封為大龜文「總目」,等於是清廷所正式敕封的大龜文領導人。因為隱然已有國家或族邦的雛型,所以才有「總目」之稱。這位女性總統候選人與他那位曾任大龜文國王的祖先可能正是血脈相連。
那場一八七五年的戰爭,一直是他們大龜文的傷痛。那是一個小族邦對一個大帝國的不對稱戰爭。雖然白浪官兵摧毀了五個大龜文部落,大龜文有許多勇士犧牲了。相對的,大龜文也讓官兵付出超乎預期的慘痛代價。但是令人氣憤的是,後來白浪的文字記載讓戰爭的真相被扭曲了。在歷史文獻中,所謂大龜文人的「歸順」、「投降」都是厚顏白浪的片面之詞。一百四十年來,大龜文人受盡委屈。
時代巨輪不停轉動,如今大龜文終於時來運轉,進入一個新局面了。
在新局面中,這位女性總統候選人已經承認了她的大龜文血統。如果她真能成為這個島嶼前所未有的女總統,那麼他相信,祖靈在天,一定會感到無比欣慰。百年之前,一位女性祖靈當年勇敢地嫁入白浪社會,竟在多年以後,讓大龜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在台灣找回了往日的榮光及嶄新的希望。他希望,這位未來的女總統不僅是泛泛對原住民道歉而已,他期許這位擁有大龜文DNA的準總統,除緬懷她的原住民祖先,更能協助原住民文化的再建立。
他心中滿懷感動,熱淚盈眶。這是否是一種火鳥先浴火再重生的救贖?
他舉頭望天。他在心中默問當年嫁入白浪的大龜文女性祖靈,您是否在教導我們,要與過去敵對的白浪和解攜手,才能讓大龜文之名永傳於世,讓大龜文的榮耀不再侷限於琅嶠一隅,而名揚台灣。時代已變,百年來高高在上的白浪後人,現在不是也正有著遲來的自省與醒悟,向原民攜手,以擁有「番仔」血統為榮。如果下任總統能以元首之尊,國家名義向原住民道歉,這將是一個新里程碑的開始。這不能只是絢麗儀式,雖然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他突然意識到,這個島嶼,早已不是單一族群所擁有,各族群通過和解及了解,反省與寬容,互相尊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觀,族群共榮」,是這個島嶼居民的未來方向,也是宿命。
第一部 日本兵:揮刀牡丹望風港
第一章
自從媽祖生日前一天的三月二十二日開始,王媽守(註1:當時清朝官方文書內皆作諧音之「王馬首」,後來方更正為「王媽守」(見本書第二十章)。)和風港(註2:今屏東楓港。)的海邊居民,三不五時就抬頭望著海面,看看是否有掛著紅白太陽旗的巨大鐵殼船駛過。
眾人不是沒有看過這種會冒煙,會鳴笛的新式鐵殼船。這一、二年,鐵殼船慢慢多了,取代了過去的三桅大帆船。但是,像這樣頻頻出現,又幾乎沿著海岸行駛,自岸上看,船員制服清清楚楚,是從來沒有的事。這些鐵船冒著白煙,鳴著長笛,可以看到船舷大砲,又載著軍隊,令大家既好奇又害怕。
在德隆宮的廟口,王媽守以老大的口吻告訴風港的墾民:「一定有大事發生了。」果然馬上有消息傳來,有好幾百名日本兵在三十里外的社寮(註3:今屏東射寮。)上了岸。他們配著新式的連發槍,聽說還有大砲,開始紮營,顯然會停留一段時間。日本人以重金招募大批幫工,連柴城、保力、後灣的居民都趨之若鶩,好多人都去賺外快。
接著,有兩位官爺也自枋寮來到風港。一位是巡檢周有基(註4:依《甲戌公牘鈔存》,此時枋寮巡檢為王懋功,但此後幾乎都是周有基。在本小說中為求一貫性,在此易為周有基。),一位是千總郭占鰲。他們向民眾打聽日本人的消息,以及社寮、龜山、後灣那一帶的狀況。這些官府爺們平時都駐停在枋寮或加祿的官府衙門,很少到琅嶠來。風港已經有七年沒有軍爺光臨了。上次台灣府總兵劉明燈大人帶著九百兵士,浩浩蕩蕩路過,又浩浩蕩蕩離去,把這一帶的人搞得雞飛狗跳,大家印象猶新。一旦被蛇咬,看到草繩都怕。大家對清國官員都心存戒心。
王媽守說,在社寮及後灣地區陸陸續續登陸的日本兵已超過一千人,聽說是準備攻打牡丹番社。理由是牡丹社生番殺害了好幾十個琉球人船員。
王媽守搖頭擺腦,自言自語:「奇了。那不是已經三、四年前的舊事了嗎?日本人若要來,怎麼現在才來?其中必有緣故。」
有人問:「官爺們來探聽些什麼?」
王媽守回答:「那位周巡檢說,任何和日本人相關的消息都可以。特別是如果有日本人來到風港,一定要向他們報告。那位郭千總特別強調,只要訊息重要,必有賞賜。」
有人說:「要坐船去枋寮向他們報告?那可是一件麻煩事,去的時候是西南風還好,要回來可沒那麼順暢了。」
幾天後,又有消息傳來。七年前與台灣府劉總兵帶領大軍一起經過此地的那位獨眼白人,聽說現在到了日本,幫忙日本籌畫這次的出兵行動。風港人都清楚記得七年前那件事(註5:指同治六年(1867)的羅妹號事件。劉總兵為台灣總兵劉明燈。獨眼白人為當時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李讓禮)(Charles Le Gendre),後來在1872年跳船橫濱,為日本人籌劃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請參見作者2016年出版的《傀儡花》。)。劉總兵劉鎮台帶著上千人馬,說是要到南邊的龜鼻山征討生番。聽到要殺生番,風港、崩山(註6:今屏東枋山。)、莿桐腳的墾民都轟動了。庄民們主動幫忙清軍開路搭橋,備水獻糧,大家都希望官兵把生番打敗,因為大家都被生番欺負怕了。生番在山邊林中出沒,風港、崩山這一帶的福佬墾民每年都有人被生番突襲。運氣不好的連頭顱都保不住,被割下帶走,死狀極慘。
沒想到,後來劉總兵與生番達成和議。還沒有打仗,官兵就撤走了。居民不但期待落空,反而因幫忙官兵而得罪了生番。後來村民為了平息生番之怒,還宰豬獻糧。這件事,大家還耿耿於心。
周有基來到風港,向王媽守等人表示,日本兵來此是為了懲罰牡丹生番濫殺漂流到東部後山的琉球船員。
這句話聽在王媽守及風港人心中特別有感。因為就在去年,王媽守嫁到莿桐腳的姪女,丈夫就在耕作時無緣無故被山上下來的大龜文番出草殺了。風港、崩山、莿桐腳這些離大龜文較近的新開闢地區,每年都會有倒霉村民被生番馘首。而在枋寮的官府從來不管到他們死活,推託說枋寮以南,不在有司責任範圍。居民既未向官府繳稅,也就不能要官府支援什麼。官府的說法反讓王媽守等人暗自盤算,期待日本人可能比官府會保護人民。
王媽守的王姓家族是二十多年前集體自柴城遷徙過來的。王姓在風港算是大家族。王媽守的姪女在五年前嫁到莿桐腳,夫妻兩人胼手胝足,開墾了一塊田地,每年也按規矩向大龜文繳租。但不幸幾個月前,丈夫死在崩山溪谷,屍體泡在水中,頭被割走,留下孤兒寡婦。王媽守費了一番功夫才將她安頓下來。
第二章
風港人還在注意社寮那邊有什麼新消息,也在猜測台灣府這次是否會再度派兵南下時,出乎意料之外的,反而是二、三十位日本兵先來到了風港。
那是日本人在社寮登陸後的第九天或第十天,周有基等離開風港以後的第四天,有一隊日本兵來到風港。令王媽守很驚訝的是,日本兵雖然語言不通,但懂得一些漢字,可以筆談。而且日本兵還帶來了一位柴城人的福佬通譯。於是風港的福佬墾民公推了王媽守去和日本軍人交談。
日本兵的頭目,是一位叫橫田棄的大尉。王媽守很高興,竟然有機會見到日本兵,而且還是一位中級頭目。王媽守的兩顆小眼珠骨碌碌轉著,望著橫田棄。橫田棄雖然有些矮小,但合身的軍服與腰際的佩刀,讓他看起來甚是威風。他在心中比較著橫田棄與幾天前來過的周有基。兩人除了打扮不同外,周有基對他們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橫田棄則有禮貌多了。
那一天周有基來的時候,王媽守向他訴苦,說他的妹婿被大龜文番殺了,頭顱也被取走,希望周有基為民眾出頭,至少派幾位軍爺上山去警告大龜文人,不可再濫殺民眾。周有基不但不表同情,反而有些不以為然,不耐煩地說:「這個你們自求多福吧。官府一向的原則是不介入生番的事。再說,現在又有日本人來惹事生非,官府應付日本人都來不及了。」
王媽守正在打量橫田棄腰際的佩刀時,橫田棄透過那位柴城福佬問了第一個問題:「你們風港有多少住戶啊?」
「不多,一百多戶而已。」
「這裡到牡丹人的地方,有幾里路?」
「自這裡到牡丹番社大約三十多里,山高嶺險。」
「有道路可以通嗎?」
「穿山而過,沒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