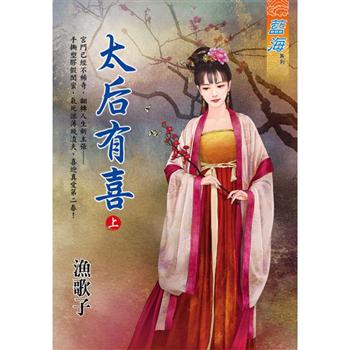第一章 陛下真該死 五黃六月,京師赤炎。 午時末,正是一日之中暑氣蒸騰最盛之時,那金碧輝煌的龍樓鳳殿亦不能倖免被滔天熱浪席捲。 夏日可畏,蟬鳴聲聲陣陣,不絕於耳,巍峨禁宮也被蟬鳴所充斥,擾得人燥意更甚。 然內廷正殿附近卻是一片寂靜,聞不到一聲蟬鳴,帝王寢宮前歷來禁栽大樹,而附近一片的夏蟬早在半月之前第一聲鳴響起之時便被小內侍們捕了個乾淨,生怕擾了天子的清淨。 帝寢重地,四周靜得連一丁點兒響動都不曾有,靜得讓人心慌。 此時的寢宮四周皆被身披鐵甲手持利刃的禁軍層層圍住,密不透風。 華麗沉重的殿門「吱呀」一聲緩緩打開,從裡魚貫而出三個手持空托盤的小宮女。 她們自殿裡出來,在夾道兩邊渾身煞氣的禁衛軍銳利注視下,個個都將自己的腦袋埋得低低的,連呼吸都不敢放重了,加快腳步匆匆退下。 內侍們三日前早已將承乾宮殿外廊前地磚上濺滿的血給擦拭乾淨,那鋪地金磚依舊如往常那般光可鑒人,但沖人的血腥之氣卻猶在鼻腔縈繞,怎麼也散不去…… 帝寢暖閣內的陳設奢華氣派,盡顯天子威嚴氣勢。 雲頂檀木作梁,金磚鋪地絨衣,紫檀燈架擱放羊角琉璃燈,一盞又一盞,偌大寢宮,即使關窗閉門卻依舊能亮堂堂,殿內各個角落皆置了冰盆,正散著眼見白煙的寒氣,殿外燥熱得叫人心浮氣躁,殿內卻是絲絲縷縷的涼氣,卻也平靜不了心氣,反倒生了些透骨的陰冷之感。 金狻猊獸香爐正燃著裊裊青煙,殿裡一片寂寧。 「叮噹。」 一聲輕響在靜謐之中尤為明顯,是玉石鐲子不小心碰到黃花梨木案面時發出的清脆響聲。 一隻嫩白纖長的素手輕輕端起來案桌上陳放著的那一碗黑褐色藥汁,湯藥已放置了些時候,溫熱不燙手。 面貌瞧著約莫雙十出頭的年輕女人身著一襲月白緞百褶暗鳳紋月裙,一頭墨緞的青絲只用髮帶束著,一根素簪綰了一個鬆散的髻,瞧著倒是一派愜意閒適。 她端著湯碗,步子輕緩,踩在厚重的絨地衣上也不曾發出什麼響動。 女人行至那張奢華的龍床前,抬手撩起垂下的帳幔,踩上腳踏,在床邊施施然坐定。 龍床之上直挺挺平躺一人,男人約莫三十逾半的年紀,雙目緊閉,眼下一片青黑,面頰枯瘦顴骨高突,面色灰敗,分明早已是一副油盡燈枯之相,露於錦被之外的手蒼白僵瘦,只餘皮包骨,青筋脈絡於皮膚之下清晰可見,若非胸膛偶有細微起伏,乍看之下已然是一具死屍。 這男人便是如今大召王朝第五代君王仲德帝趙韞。 只可惜萬歲不萬歲,仲德帝趙韞分明才三十過六,哪怕是高高在上掌控千萬人生死的天子帝王,亦無法擺脫自己生死輪回的宿命。 女人坐在床榻邊,端著藥碗怔怔地看著床上昏睡的趙韞,雖已是垂死之相,但還是依稀能瞧出曾經俊逸的輪廓。 女人盯著趙韞出了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而後兀自一聲輕笑,果然哪,都道風流亦無情,最是帝王家。 她回過神,換一隻手端藥碗,微俯下身,在昏迷中的趙韞耳邊輕聲道:「陛下……陛下醒醒,該吃藥了,陛下……」 女人一派閒適,似乎有得是耐心,輕聲喚著「陛下」,一聲接一聲,直到將陷入深度昏睡中的趙韞生生喊醒。 趙韞似從噩夢之中掙扎轉醒過來,吃力地動了好久的眼皮後才艱難地睜開了一條縫,他呼吸粗重,舔了舔乾裂蒼白的唇,渾濁的目光掃到了坐在他邊上的女人。 在看清女人面容後趙韞驀地睜圓了雙眼,胸膛開始劇烈起伏,呼吸也越發急促,喉間像是被堵住一般發出「呵哧呵哧」嘶啞聲。 「妳……溫溫溪……妳這個……這個毒婦!皇后、皇后……妳好好得很……呵——咳咳咳……」 短促的一句話才說完,過於激動之下急促喘氣,喉嚨聚攏濁痰,發出一陣咕嚕聲,緊接著便是驚天動地的咳嗽。 被罵作毒婦的女人卻依舊氣定神閒,杏眼之中盛著賢淑溫柔的盈盈笑意,她將藥碗擱在床邊矮櫃上,捏著帕子,蜻蜓點水般在趙韞胸口囫圇拍了兩下,算作替他順氣,「陛下可莫要再動怒火,本就沒幾日活頭了,再如此盛怒,指不定立時便伸腿瞪眼駕鶴西去了呢!」 趙韞被這一句話氣得眼中瞬間爬滿了紅血絲,但還真將她滿含戲謔的話語聽了進去,強逼自己穩下情緒,緩下呼吸,可雙眼卻是狠狠盯住她,那刻骨的恨意似要血淋淋地撕下她的面皮。 女人薄施粉黛卻依舊姿容嬌妍,面色白皙透紅、光滑潤澤,朱唇紅潤飽滿,眸中水光微斂,那是寓意年輕康健的生機活力…… 似是相當滿意趙韞這般反應,她又端起矮櫃上的藥碗,此時的湯藥已經完全涼透了,女人用湯匙叮叮噹噹地攪了幾下,舀起一勺褐色的藥汁遞送到他嘴邊,「來,陛下,莫氣了,還是先進些湯藥吧,也好多活些日頭,罵人的時候也能有些力氣。」 趙韞盯著這勺藥汁良久,顫巍巍抬起一隻枯瘦如柴的手一把揮開面前的湯勺,連同女人手上的藥碗皆被揮掃出去。 藥汁揮灑開來,落在錦被上、女人月白色的宮裝上,碗勺叮噹一聲輕響,而後跌落在厚實的絨毯裡,剩餘的藥汁滲入地衣中,只餘一聲悶響。 「妳……妳皇后,妳這個毒婦!妳妳……妳這是在禍亂朝綱,妳想……妳想弒君殺夫呵呵——這藥、這藥定有毒,朕不、不吃,滾……滾開……咳咳咳……朕要廢后咳咳咳……」 對於皇帝再次激動的情緒及誅心之語,女人毫不在意,始終表情淡然,她用羅帕慢條斯理地將沾在手上的藥汁拭去,「這罪名可大了,陛下莫要冤枉了臣妾才好,這是徐院使開的百年老參湯,給您吊命用的,如今太醫院庫房裡兩百年以上的老參所剩不多了,全為您熬製了參湯,再者臣妾若真想弒君,何必用下毒這種蠢笨的下三濫招數給自己招惹麻煩,只需再耐心等上幾日便成……」 女人拭完自己手後起身又去遠些的案桌上拿了另一碗一同備好的湯藥,她端著湯藥往回走,聲線溫和恬柔彷彿就是在與自己的丈夫閒話家常,「還有,闔宮的人都可作證,如今陛下躺在此處可與臣妾無一星半點的關係,陛下莫不是忘了,您可是從淑妃的床上被抬下來的,怎到最後反倒怪起了臣妾的不是來?」 趙韞是倒在女人肚皮上的。 雄心壯志的帝王,正是春秋鼎盛之際,還未成就自己的宏圖霸業卻即將英年早逝,想讓自己做個名留青史的千古明君,最終卻只將得到名聲盡毀的死因。 趙韞深深地閉上了眼睛,胸膛劇烈起伏幾下,臉上垂死的灰敗之色更濃了幾分,他認為自己勤政愛民、日理萬機,嘔心瀝血地操勞政事,只偶爾放縱幾次而已…… 為何?為何上天如此不公?為何會落得如今的這番局面? 趙韞強嚥下喉間不斷翻湧的血腥氣,聲音猶如鈍刀刮骨,「淑妃……皇后妳將淑妃如何了?」 女人漫不經心地用湯匙攪動瓷碗裡的湯藥,聞言一聲嗤笑,「看來陛下對淑妃的情誼真真兒是天地可鑒,自個兒都到了這般田地,心裡還念著淑妃。陛下寬心,淑妃沒事,能吃能睡,她應是能比您尚且多活幾日。」 趙韞咬牙,「毒婦!咳咳咳……朕……終究還是小看了妳,竟從不知皇后本事如此之大,朕都不曉得什麼時候起朕的人已經被妳籠絡了泰半,江進忠被妳收買,居然連秦斂都被妳拉入了太子陣營,咳咳咳……好手段啊皇后……」 他昏厥之後中途被太醫救醒過一次,奄奄一息之際,親眼看著他的好皇后號令禁衛軍圍了他的寢宮,捆了淑妃,他的心腹及暗衛不是叛變就是被當場格殺,他甚至親眼見到皇后拿著劍親手捅穿了他大女兒平寧的肩膀,他早已擬好的易儲聖旨則被當場燃成灰燼…… 他目睹了一切,卻連動一下唇的力氣都沒有,他身邊的人都被換成了皇后的,只能那般眼睜睜看著皇后興風作浪,把持全域,而他已無力回天。 女人紅唇微揚,「陛下過獎,夫妻多年,陛下的那些手段臣妾雖學不來精髓倒也能仿了一二,您只當替您辦事的那些人是鞏固你龍椅的工具,卻忘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總會有弱點和私慾,就算臣妾抓不住他們的弱點和私慾,但總歸不是銅皮鐵骨,會疼會死,好手段談不上,只是些小聰明罷了。至於秦閣老,臣妾倒也真是意外,不過這些現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臣妾贏了,不是嗎?」皇帝於淑妃床榻之上突然昏厥,天家這場明爭暗鬥數年之久的奪儲風雲終於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終局之戰,朝中眾官員早已站隊的站隊,只內閣首輔秦斂手握重權卻是純臣,從不偏頗任何一派,深得趙韞器重,也對他頗為忌憚。 從前各皇子黨派都正面側面試圖拉攏其人,但秦斂從未對任何人的示好表露過意動。 直至此次皇帝病危臨死,她本是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只是令她沒想到的是,在平寧公主拿出那張趙韞易儲三皇子的聖旨且被她刺傷後,秦斂竟突然站出來親自將聖旨焚毀,而後步出殿外,向著外間不知真相的眾臣道,平寧公主孝順憂父,憂思過重,重病胡言,還調來了禁衛軍…… 她也方才明白,原來禁衛軍統領是秦斂的人。 她知道,最後關頭,秦斂最終是選擇站在了太子這一邊,那麼這場奪儲之爭她就勝了! 她管不了跟秦斂合作是不是與虎謀皮,她現在退一步便是萬丈深淵,別無選擇,必須贏! 趙韞一時間再說不上話來,只怔怔地看著坐在床頭的髮妻,渾濁的雙眸已經彌漫上了死氣,似是陌生又似是失望,軟化了語調帶著往昔的回憶喃喃道:「阿妧……妳怎會變成如今這般模樣,妳我怎就到了如今這般地步,從前的妳分明不是這般……」 女人卻沒有如此多的感慨,她彷彿是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笑得花枝亂顫。 等笑夠了,她抽出帕子拭了拭眼角笑出的眼淚,然後幽幽地伸出一隻手放在自己眼前細細地看,玉手丹蔻,美如羊脂玉雕。 「臣妾從前是哪般模樣?陛下與臣妾從前又是哪般地步?說不清了……您瞧這雙手,曾經連刀都握不動,可如今竟能在此攪動著這滿城的腥風血雨……臣妾也不想的,可是沒辦法,深宮之中,我的丈夫算計我,豺狼虎豹們想生吞我,我想活命啊! 「我也不想爭的,我明明曾經最是膽小怕事,最怕與人爭執……可我總得活命,總得讓我的兒子活命,總得護我溫家的遺孀幼孤們下半輩子不受人欺凌,我總得為溫家滿門不得安息的忠烈英魂們討一個公道!總得為我的珠珠討一個公平!陛下,您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譴責我變了,在這深宮,誰都可以說我變了,就陛下您沒有資格!」 趙韞還想再言,但顯得蒼白無力,「皇后,太子還年幼……溫家如今只餘一院婦孺和溫六一介殘身白衣,太子根本壓不住朝中林立的黨派之爭、鬥不贏那些牛鬼神蛇……妳……妳只見了易儲聖旨,可未曾想到妳竟與秦斂相謀,連朕都拿他沒辦法,阿妧,妳這是在玩火……朕其實還留了另一道聖旨,朕在時會護妳母子,待朕身去後……咳咳咳,那道遺旨便會令新帝繼續護妳母子周全——」 「呵呵……呵呵呵呵……」趙韞的話被女人一連串的笑打斷,她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待稍稍平復笑聲後說道:「這麼說來陛下為了我們母子倒還真是殫精竭慮啊!臣妾和太子確實沒有了可以依靠作為後盾的娘家,可臣妾是您的皇后,我的兒子是您親封的太子,我們母子是您立在人前的活靶,若我兒子不坐上那個位置,您覺得您這道虛偽的聖旨能保我母子生不如死的日子到幾時?可若太子繼位,那臣妾就不一樣了,雖然該死的還是得死,但能留一命的臣妾會勉強留他們一命的……」 說著女人俯身,湊近了趙韞,眼中的冷笑早已結成了寒冰,「陛下如今倒嫌棄太子無鼎力相助的外家來了,可莫不是忘了,太子本是可以有一群赤膽忠心的好兒郎們替他保家衛國、開疆拓土,可是您呀!是您好算計,將他們的白骨壘築成了白狼城的牆……」 趙韞雙眼霍地睜大,胸膛起起伏伏,喉間帶痰地渾濁喘氣,「妳妳妳……妳呵——」 女人嫣紅的唇微微上挑,她緩緩湊近到趙韞耳畔,面上仍在微笑,卻挾裹了刻骨的恨意,「你以為死一個劉刈就算完了?就算是給我父兄、給五萬溫家軍將士、給白狼城一城的百姓有了交代了嗎?陛下,沒完!到你死都不算完!這筆血債從現在起才真正開始清算呢!」 「妳……妳妳……妳知道,妳知道對不對?妳、妳怎會知曉?」趙韞原本病態蒼白的面色此時已猶如死灰,就像一條離水已久瀕死的魚,艱難地大口喘息。 女人嘴角的弧度一點點消失,直至抿成一條直線,她貼著趙韞的耳朵,吐氣如蘭卻猶如銳利的尖釘一字一句釘入他耳中,「臣妾不光知道這些,臣妾還知道,十年前,圍獵場,臣妾的馬是你送的,臣妾被太后斥責而鬱鬱寡歡的消息也是你故意放出去的,五哥他想在圍獵時找時機近身寬慰我也是你暗中行的『方便』,餵馬的小太監其實是你的人,莊嬪不過是替你背了這罪名……呵!」 在趙韞驚濤駭浪般的目光中,女人緩緩直起身,複又端起那碗早已涼透的參湯用湯勺攪了攪,盯著褐色的湯藥神色淡然,卻是早已心如死灰的悲涼,「臣妾真是可悲又可笑啊,前一晚還在與我耳鬢廝磨溫存纏綿的夫君,卻在一夜醒來後用他蓄謀已久的毒計罔顧我的死活,設計我,利用我,害殘了我兄長的雙腿,毀了他一生!」 趙韞張張嘴想說些什麼,卻被女人截斷。 「我知你要說什麼,無非便是溫家滿門為將,三十萬溫家軍只認帥不識君,溫家兒郎本手握重兵,再有一個從文出仕、驚豔絕塵的溫五公子,你不得不忌憚,你為了大召江山社稷,為了你趙家的祖宗基業,不得不這麼做……呵! 「你總是在為自己找理由,可笑我鐵骨忠膽的父兄為了你趙家的江山,血肉身軀早已在白狼城屍身化枯骨,你卻到現在都沒覺得自己哪裡做錯過!」女人莫名揚起古怪的笑容,彷彿要看穿趙韞的內心,「你果真是一心為了大召嗎?你不想五哥出仕高升有多少別的法子,可偏生用了這最陰毒卑鄙的,陛下,你除了忌憚還有嫉妒,那醜陋的嫉妒,陛下心底住著一隻面目猙獰醜陋不堪的獸!」 女人的話彷彿是戳中了趙韞內心深處最隱祕晦暗的心思,但此時的他連喘息都變得很是費勁,幾乎說不出一句怒斥或反駁的話來,只能一起一伏努力喘息。 殿中一陣窒息的靜默。 女人沉默了很久,終究紅了眼眶,她硬生生忍住不甘和怨恨的淚意,逼近了趙韞,與他對視,「趙四郎啊趙四郎,你可知,同床異夢這些年,我打落了牙齒和著血水將所有的一切吞進肚中,每每午夜夢迴從那些噩夢之中驚醒過來,當看到你就臥在我榻邊,長夜之中,你可知我將那褥枕覆於你的口鼻之上,無數回拿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看著趙韞明顯有些怔忪的眼神,女人扯了一下嘴角繼續道:「因為我的孩子,因為我還有淳哥兒,呵呵呵……可是你呢?陛下你呢?」 女人驀地俯下身,與趙韞面貼面,雙目通紅,近在咫尺的四目相對讓趙韞眼中所有虛弱的情緒都無處藏匿,「趙韞你告訴我,我要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在你心裡,可曾有過對珠珠的半分歉疚,哪怕只是轉瞬即逝的那麼一小會兒?你告訴我你可曾有過!」 「朕……」趙韞艱難地喘口氣,想要說些什麼反駁,但看著女人泛紅的眸子裡刺向他的銳芒讓他無所遁形,他有過傷心,有過盛怒,也有過悔意,卻唯獨沒有歉疚,甚至到了如今這般癱躺在床的地步,他依舊覺得那不是他的錯,至少他從未想過要害死珠珠…… 趙韞的遲疑和語塞女人看得一清二楚,她眸中清晰地映著嘲諷,卻沒有失望,因為這早在她的意料之中。 女人再次直起身,他們之間早已稀碎,都到了這地步其實連樣子都不必再佯裝了,於是她放下那碗端了很久的參湯,與趙韞對視,眼中聚集的厚重恨意用言語化作那最鋒利的劍刃,刺透皮肉傷疤,挑出那附骨膿毒,「趙韞,作為掌控萬千人生死的帝王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世人都得愛你、敬你、怕你,你覺得自己英明睿智,擺弄人心掌控生死,你意氣風發令世人心悅誠服,好成全你河清海晏的賢君美夢。 「呵呵……可如今你兩腳都踏進了棺材,將死之時不知瞧沒瞧明白,這朝堂之上又有幾人是真正的心悅誠服?後宮之中又有誰是真心愛你?我當然早就不愛了,那還有誰?你的淑妃?你真的覺得她愛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