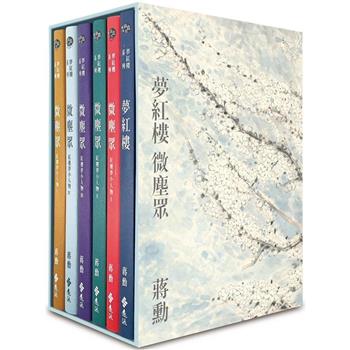〈寶玉和黛玉是情侶嗎?〉
芒種節對今日的讀者已經有些陌生了。
古代每到四月下旬,要向花神餞別,過了芒種節就是夏天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
「送春」的習俗,也說明著人們對春天的不捨、依戀與感謝吧。
芒種節又多由閨中的少女們舉行,有點珍惜青春年華的意味吧。在日本,常有俗稱「女兒節」的,也是由閨中少女告別春天。
《紅樓夢》中的「芒種節」,使得大觀園中所有的女孩子們都早早起來,這一天是四月二十六日。
大觀園的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線繫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搖,花枝招展。」
而在芒種節這一天,心事最多的當然是黛玉。她沒有參加眾人熱鬧的「送春」儀式,她孤獨一人,帶了花鋤,走到僻靜的地方去「葬花」。
黛玉葬花的故事,是所有讀《紅樓夢》的讀者印象深刻的一段。
這一段故事發生在《紅樓夢》的第二十三回。
三月中旬,正是春天百花開到最盛艷的季節。少年的寶玉,瞞著父母家人,偷偷帶了一套《會真記》,跑到沁芳閘橋邊的桃花底下讀書。
《會真記》原來是唐朝元稹寫的《鶯鶯傳》,描寫崔鶯鶯和張君瑞私自戀愛,鶯鶯的侍女紅娘從中穿針引線,撮合二人幽會,被鶯鶯的母親知道,拷打紅娘。
《鶯鶯傳》在金代、元代被改編成戲劇,歌頌青年自由的戀愛,打破封建禮教的約束,很受民間喜愛,成為家喻戶曉的《西廂記》。
賈寶玉這時在春天的桃花樹下讀的,就是元代經王實甫改編的《西廂記》。
這部書因為描寫鶯鶯違反家規,和張君瑞幽會私通,涉及青年的肉體情慾,雖然被民間廣為流傳,卻是書香世家不准子弟閱讀的「禁書」。
賈寶玉便偷偷在春天的花園中讀「禁書」。
春天的花園,像是寶玉這個情慾剛剛萌芽的少年孤獨的內心世界。他看到書上有「落紅成陣」這樣的句子,剛好一陣風過,樹上桃花被風吹下一大片,「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花片」。
這是《紅樓夢》令人著迷的片段,一個少年,一身都是落花,他想走動,又害怕踏壞了地上的落花,便用衣襟兜著花瓣,慢慢走到水池邊,把花瓣抖在水中。那條水是山子野設計的「沁芳閘」,是盛受落花芬芳的園林溪流。
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
寶玉身邊有許許多多的女性,她們美麗、聰明、靈慧、體貼,她們都成為寶玉一生一世忘不掉、也感念不盡的青春伴侶。
但是,在所有的女性中,沒有人能夠取代林黛玉。
寶玉和黛玉沒有任何肉體上的關係,似乎連情慾也沒有。他們有時甚至覺得比他人更疏遠,彼此來往不多,交談也不多。
但是,在寶玉最孤獨的時候,黛玉會出現。寶玉看著一地落花,百感交集的時刻,黛玉走來了,像是生命裡另外一個自己,沒有人會這麼熟悉、這麼親密。
黛玉來了,肩膀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裡拿著掃花的掃帚。
寶玉說:「來的正好,妳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撂在那水裡去吧!」
他們都疼惜花,疼惜美,疼惜生命,他們不同一般的情侶,他們似乎沒有此生的瓜葛,卻是在久遠的前世已經有了緣分。
黛玉卻不贊成把花撂在水裡,她說:「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
黛玉珍惜花,連落花都不願糟蹋。她惋惜花,不要花隨水流去人間,在雜穢的人世仍然要被糟蹋污染。
黛玉說:「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它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寶玉和黛玉因此有了其他人沒有的共同秘密。他們在春天一起惋惜落花,一起埋葬落花,他們的青春有了共同的紀念,共同的哀悼,共同的回憶,共同的眷戀與不捨。
天長地久的不會是肉體,不會是花,而是曾經共同擁有的美麗的記憶吧。
黛玉葬花,把花瓣裝在絲織的絹袋裡,埋在大觀園牆角的花塚下,日久隨土化去,乾乾淨淨,也正是「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主旨。
黛玉葬花一段使許多人感動,變成舞台上美麗的形象,變成仕女圖的主題,甚至變成廣告設計的圖像,對流行消費的大眾文化都產生了影響。
黛玉在葬花之後,走到梨香院,聽到學戲的十二個女孩子正唱著《牡丹亭》的句子:「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又聽到:「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黛玉感悟到葬花其實是埋葬自己,惋惜花的凋零,也就是惋惜青春逝去。
〈秦鐘〉
秦鐘在《紅樓夢》第七回出現,他是秦可卿的弟弟。這兩個姓「秦」的姊弟,諧音「情」,兩人都為「情」所困,為「情」而死。
秦可卿與秦鐘都長得美,可卿是賈寶玉初發育時暗戀的性幻想對象,秦鐘則是賈寶玉第一個同性愛人。異性或同性,對十三歲左右的青少年而言,似乎沒有差別。純粹因為「美」,他們有了宿世緣分,也純粹因為「美」,他們有了不可知的情緣糾纏。
第七回,寶玉和王熙鳳去寧國府看秦可卿,可卿說正巧弟弟秦鐘在,寶玉就吵著要見他。
秦鐘一出場的描寫是:「比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更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兒之態。」
作者寫秦鐘的「美」,沒有強調性別。在性別劃分單一的世界,其實也不容易瞭解秦鐘與寶玉的情感。
王熙鳳一見秦鐘,推寶玉一把,笑著說:「比下去了!」
秦鐘的「美」讀者看不見,王熙鳳一句:「比下去了!」彷彿讓人眼睛一亮。
秦鐘青春的生命有多麼「美」,不是世俗男性陽剛到粗魯的美,也不是女性陰柔到蒼白的美,性別的膚淺兩極劃分無法分析。秦鐘的「美」,不像是肉體,像是一種魂魄。湯瑪斯‧曼(Thomas Mann)《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名著裡的少年「達秋」(Tadzio),很類似秦鐘。他們的美,像是青春本身;他們的美,忽然喚醒每一個人自己生命曾經有過的嚮住。那「美」使王熙鳳驚動,推了寶玉一把,說「比下去了!」
同樣年齡的寶玉,生長在富貴家庭,有一切物質的享受,受一切人寵愛,他沒有拿自己跟秦鐘比。他的反應是「心中若有所失,痴了半日」。
寶玉的「若有所失」,寶玉的「痴了半日」,耐人尋味。一個富貴公子,集天下榮華寵愛於一身,在生命的「美」面前悵然若失。他沒有「忌妒」,沒有「比」的心思,他只是從心底肺腑衷心歡喜讚歎:「天下竟有這等人物!」
秦鐘的「美」會不會反射出了寶玉自身動人的生命情操?在處處競爭比較的社會,在時時因為比較競爭產生忌妒排擠自誇的社會,賈寶玉看到的「美」一清如水,只是歡喜,只是讚歎。
寶玉,一個青少年,在「美」的面前發呆,他心中想著:為什麼我生在侯門公府之家?為什麼他生在寒儒薄宦之家?
「美」沒有性別,「美」也沒有階級,《紅樓夢》的作者要用「美」對抗一切世俗的分類嗎?
王熙鳳、秦可卿要吃茶吃酒,寶玉就借故他和秦鐘不喝酒,兩人就私下離開去講悄悄話了。
寶玉第一次見到秦鐘的「若有所失」,是青春期難以解釋的寂寞嗎?在眾人的寵愛中,他好像一直在尋找另一個自己,像柏拉圖說的那個被神懲罰劈成兩半後失去蹤跡的另一半的自己?
我們如此不完整,我們都在尋找另一半的自己,每次好像找到,卻又覺得不對,那真實的另一半自己到底在哪裡?
寶玉覺得秦鐘是自己劈開來的另外一半,他找到了,他想與秦鐘合而為一。
寶玉問秦鐘課業,秦鐘因父親老邁,家境窮困,正輟學在家。寶玉平日最恨到學校讀書,厭煩所有為了考試做官的虛偽教育,此時他卻熱心邀約秦鐘一起上學,一起做功課。
青少年的中學記憶,常常並不是學校功課,其實是玩伴,同年齡的玩伴,同性別的玩伴。一個在女性世界中長大的寶玉,一個身邊圍滿長輩呵護的寶玉,終於有了第一個同年齡、同性別的「伴侶」秦鐘。
所以,秦鐘是寶玉的第一個同性戀愛人嗎?
許多人討論過他們的關係,有沒有性行為云云。小說留下很大的猜測空間,好的文學畢竟不是八卦,也不會把關心的重點放在揭人隱私的沾沾自喜上吧。
寶玉和秦鐘一起上學了,他們在學校裡做了什麼事,第九回有詳細描述。
《紅樓夢》第九回是精采的青少年寫實文學,比美《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可惜教科書選讀《紅樓夢》,都不(敢)選此回。
秦鐘和寶玉讀的學校是賈府設立的貴族私塾,小到八、九歲,大到十七、八歲,都在這裡讀書。等於今天的小學四、五年級到高一、高二左右。清一色的男學生,假藉讀書,玩起青少年男生大膽的性遊戲。
學校的老師是賈代儒,一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在私塾教書,學生也不愛聽,自己也覺得窩囊,常缺課,要孫子賈瑞代課。賈瑞沒有威嚴,鎮壓不住學生,學生就造起反來了。
班上有一對小學生,長得漂亮,同學給他們取外號,一個「香憐」,一個「玉愛」。同學都想「染指」這兩個男生,但是他們是薛蟠包養的。薛蟠有錢,班上學生圖有錢花,許多成為他的「契弟」(乾弟弟)。香憐和玉愛是薛蟠新歡,別人都不敢碰。
秦鐘來了,有寶玉撐腰,就跟香憐擠眉弄眼,假裝上廁所,兩人就勾搭起來。
有一個叫金榮的,原來也是薛蟠包養的乾弟,但薛蟠有了「香憐」「玉愛」,金榮就被丟棄。過氣愛人心裡當然不爽,趁秦鐘跟香憐勾搭,跟在後面就要報復,金榮一聲張,學堂裡就鬧成一團了。
秦鐘是同性戀嗎?他與寶玉有情,他追求學弟香憐。但是,別太早下結論,看到第十五回,秦鐘姊姊喪禮,在廟裡頭,秦鐘就搞起一個小尼姑智能兒。他把智能兒抱到床上,立刻扯褲子,「才剛入港」,性慾高漲,秦鐘不管場合,也不分性別了。
《紅樓夢》裡的青少年多是今天的「酷兒」,秦鐘是,薛蟠、金榮都是,「酷兒」們應該重看《紅樓夢》。
〈晴雯撕扇〉
晴雯是《紅樓夢》裡寫得極出色的一個角色。
晴雯是賈寶玉的貼身丫頭,地位僅次於襲人。襲人柔順,能夠化大事為小事,處處忍讓包容。晴雯剛好相反,個性剛烈,爭強好勝,遇到與人衝突,口舌上總不饒人,直率自負,犀利尖銳,常不給人留情面。
《紅樓夢》越多讀幾次,越覺得作者有一種平等心。基本上,他不介入書中人物的好惡,只是具體呈現一個人的真相,留下許多餘裕的空間,讓讀者自己去評論判斷。
襲人細心體貼,全部精神都放在照顧賈寶玉身上。寶玉吃什麼,穿什麼,天氣冷了熱了,該添衣服、減衣服,都是襲人的事。通常晴雯總是在一旁,冷眼看著,或者不時說一兩句風涼話。因此初讀《紅樓夢》,容易對這個口舌厲害、卻似乎不熱心做事的丫頭有一點偏見。
晴雯在小說一開始的判詞是「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做為丫頭,出身低微,當然「身為下賤」,但是她養著長長的指甲,整天沒事就慢條斯理用鳳仙花的汁液把蔥管一樣的長指甲染紅。一個丫頭諸事不管,整天調理自己的指甲,換作今天,一個菲傭整天在客廳蹺腳塗指甲油,這樣的畫面,大概許多人也還是不容易接受吧。
晴雯這個心高氣傲的丫頭的真實個性,《紅樓夢》寫到第三十一回,才開始明顯重要起來。
三十一回寫晴雯撕扇,充分表現了晴雯的率性與自負自傲,表現了晴雯「心比天高」的性格本質。
端陽節這天,寶玉的母親王夫人請客過節,因為前一天寶玉與金釧調情,金釧捱了打,被趕出了賈府,這一天寶玉在母親面前當然有點尷尬,其他客人也都不敢造次,飯局匆匆結束,大家就都散了。
寶玉心裡頭悶悶不樂,回到自己房裡,心情不好,正巧碰到晴雯給他換家居的休閒衣服,一不小心把扇子掉在地上,扇骨折斷了,寶玉因此埋怨晴雯,講了兩句難聽的話:「蠢材,蠢材!……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
晴雯很少受寶玉這樣重話,當然不舒服,她立刻反擊,冷笑說:「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
寶玉平日對丫頭特別溫柔和順,甚至低聲下氣,從沒有疾言厲色、粗言粗語,晴雯當然不習慣。她特別指出,以前什麼貴重東西都打破過,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寶玉也從來不會生氣,今天竟然為了一把扇子骨跌斷,要這樣罵人。
晴雯的剛烈個性顯露了出來,她說了決絕的話:「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
兩個人鬧彆扭,互不相讓,氣頭上就都講出難聽的話。襲人趕來勸阻說和,也被晴雯遷怒,冷嘲熱諷一陣子。
寶玉這一天似乎動了真怒,覺得晴雯如此胡鬧,不如打發出去,也真作態要去稟告母親,讓晴雯離開賈府。
襲人看事情鬧大了,跪下相求,要寶玉息怒。連其他丫頭──碧痕、秋紋、麝月,也一起跪了下來求情。這些十幾歲的少男少女,都是一起長大的知己玩伴,寶玉當然也捨不得任何一個離開。看眾人跪下相求,寶玉流下淚來,長嘆一口氣,不再堅持了。
當晚寶玉跟薛蟠等人歡宴,喝了酒回來,看到院中涼榻上睡著一個人,以為是襲人,便在床榻邊坐下,慰問襲人。沒想到床榻上的人一翻身,竟是晴雯。晴雯還在跟寶玉賭氣,罵了一句:「何苦來,又招我!」
寶玉已經氣消了,仍然百般溫順體貼,鬧著要跟晴雯一起洗澡。
寶玉晴雯和好了,寶玉就告訴晴雯,一把扇子原是用來搧的,你愛拿來砸,愛拿來撕著玩兒,也可以。寶玉的哲學是,不要生氣的時候拿它出氣。
寶玉下面一段話很有意思:「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使得,只別在氣頭上拿它出氣。」
這段話似乎完全是為褒姒量身訂做的。幽王寵愛褒姒,要看她笑,褒姒難得一笑。有一次聽到瓷器碎裂的聲音,褒姒笑了,幽王動容,就命令摔碎一個一個瓷器,讓褒姒笑。
褒姒為瓷器破碎的聲音而笑,為絲綢撕裂的聲音而笑,最後在燃起烽火的亡國前夕而笑。這個千古以來一直受詛咒的故事,《紅樓夢》的作者為何把它運用在一個丫頭晴雯身上,也很耐人尋味。
晴雯聽了寶玉的哲學,高興極了,她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
這是「心比天高」的晴雯,她要驚動世人,她要一種決絕義無反顧的毀滅,寧為玉碎的毀滅。
麝月進來,看見晴雯撕扇子,撕完一把,又撕一把,寶玉在旁邊笑著說:「撕得好,再撕響些!」麝月罵了一句:「少做點孽吧。」
麝月罵的話,大概凡世俗中人,也都一樣會罵。然而,《紅樓夢》的作者在寫三十一回晴雯撕扇的時候,是不是想到了歷史上被貼上禍水標籤的美麗女子?是不是想到了褒姒?是不是要為褒姒的故事翻案?
為什麼《紅樓夢》作者要讓晴雯撕扇子?一聲一聲撕裂的聲音,像一種吶喊,彷彿要撕破中國上千年歷史的詛咒,彷彿刻意要再一次回想褒姒的笑傲,在摔碎的瓷器前,在撕破的絲綢前,在燃起熊熊大火的夜晚,大聲狂笑,嘲笑世俗的戰戰兢兢,嘲笑上千年的偽善。寶玉是幽王,他在一旁讚歎,讓晴雯撕掉一張又一張歷史偽善者的面具。
晴雯撕扇,不容易用世俗邏輯看懂,然而民間編成了舞台劇,真心感覺到晴雯撕扇的悲壯快樂。
晴雯的故事還有「補裘」,還有臨死前咬斷指甲交給寶玉,都有裂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