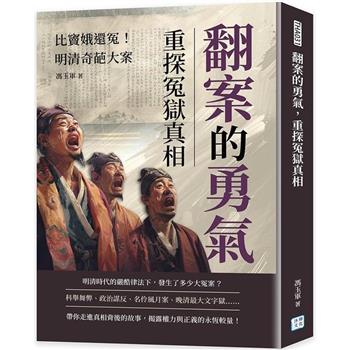「莫須有」的空印案
「莫須有」是宋代權臣秦檜的名言,他在判定驍勇善戰、為國為民的岳飛是否有罪時,實在無法找到實際證據,便用「也許有罪」的名義誅殺了忠臣岳飛。後人痛斥秦檜的這種濫殺無辜的卑劣行徑,並將「莫須有」作為冤案的代名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以主觀態度枉殺臣民的行為仍在繼續著。
出身平民,透過艱苦鬥爭才謀得皇帝之位的朱元璋猜忌多疑,總是懼怕皇位不保。他認為自己正處於亂世,他感覺到政權外部的元朝蒙古貴族還未肅清,政權內部的武將居功,文臣自大,對他的統治造成了很大威脅,於是他便抱著「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態度對一切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加以重懲,明初的空印案便是這種「莫須有」的冤案。該案株連甚廣,獲罪官員累以百計,而在血流成河的諸般慘狀背後,竟是一個並無充分證據證明的貪汙罪名。讀者要想知道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如果看法偏執、見解僵化,將會帶來何等慘烈的結果?「莫須有」的空印案留給了後人一個毛骨悚然的答案。
案情回顧
與前朝各代類似,明代的中央政府牢牢掌控著地方政府的財政大權。法律規定,各布政司、府州縣每年都要對本地的戶口、錢糧、軍需等事項的各種財政收支情況做帳,並用正式的官文在年底時上報給中央主管財政收支的行政機構──戶部核對。地方官員攜帶的文書要加蓋印信,逐級核對無誤方可透過,如發現上下統計數字不符,戶部要予以駁回。即:戶部對各地發來的文書會詳細審閱,如果戶部核查後,認為帳目清楚,並無不合之處就會確認帳目的有效性,將該中央報銷的款項下撥,但如果發現文書中有不能對帳的部分,戶部也會毫不客氣地將文書駁回地方,由地方主管財政的布政使、府州縣吏等官員在原地重新核查做帳、重新填寫、蓋好印信後,再次上報核對。
看到這裡,似乎這一核查體制並無任何不合情理之處,而且這樣嚴格的審核體制的運作也有利於減少甚至杜絕地方官員貪汙錢財、亂用公款現象的發生,是一個來自中央的有效監督機制。然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一個貌似公平合理的制度在真實的運作中卻面臨著操作上的困難。因為按照法律的規定,各級財政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將帳目上報中央並獲得批准,否則便算瀆職,所以各地官員都希望能夠盡快完成帳目的上報和核查工作。但是在實際中,達成這一目標卻面臨著多項困難:
其一,出現帳目錯誤的可能性大,地方每筆財政收支情況都要詳細記錄,內容瑣碎,核查計算工作十分複雜。在沒有現代計算工具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各種錯誤。如果戶部發現所報帳目有矛盾錯誤之處,都會駁回帳目,而不論這種矛盾有多麼微小。
其二,交通的不便。可能有人會問,帳目被駁回,重做一下就可以了,有什麼困難呢?在現今社會,通訊工具發達,聯絡便利。一封電子郵件或是一張傳真就可以聯絡千里之外的人員,將需要完成的事項和工作通告給他們。然而,在幾百年前,快速更改帳目錯誤,並再次發回中央卻成為了一大難題。當時的文書傳送都靠驛站快馬,馬兒跑得再快,也經不住路途太過遙遠。一來一往又費人力、費金錢,更重要的是費時間,附加地方官員需要在指定期限內上報帳目的上述規定,這種駁回體制便足夠讓地方官員頭痛的了。
一方面上報期限不能更改,另一方面帳目錯誤不能避免,而戶部又不會主動更改帳目。地方財政官員為了保證能夠按期完成上報任務,想出了一個變通辦法:他們讓手下吏員拿著已經蓋好地方政府印章的空白文書到中央去報帳。這樣,如果已有的帳目被戶部駁回,吏員們也不用再奔馳回所屬地方重新做帳了,他們只需要用帶去的空白文書重新抄寫一下已有內容,另將有問題的部分重新計算後抄錄上就可以了。這種做法簡單易行,免除了往返之勞,在當時的報帳體制下,既避免了重新做帳帶來的諸多麻煩,又能使戶部的監督職責得到充分的履行。於是,這種做法逐漸變成了一種通行的慣例,幾乎所有的負責上報財政狀況職的地方官員都採用這種做法。在實踐中,這一慣例也得到了戶部的認同。
然而,到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年),事情發生了逆轉。朱元璋在偶然得知這一做法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主觀認定地方官員用空白的蓋印文書再次做帳,深恐他們「以為欺罔」、「其中有奸」(即各地方官大有貪汙矇蔽的嫌疑);而且全國都採用這種做法,可能造成的假帳會有多少?朱元璋越想越氣,認為如果不對這種做法加以嚴懲,「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明史.鄭士利傳》),私下偷懶,擅自蓋印而輕視皇權,難以使之恪盡職守、認真統理帳目。於是大發雷霆,下令嚴懲不貸,將那些掌管官印的地方官都抓了起來,要將主印官一律處死。因為地方官多採用這種辦法做帳,所以為此事獲罪的官員很多,自尚書至守令,署空印書冊的皆坐欺罔論死;佐貳以下杖一百戍邊。據統計,因此案株連殺戮、充軍邊地者達數百人,地方管理田糧的長吏幾乎一殺而空。
案發之後,滿朝大臣看著勃然大怒的皇帝朱元璋,誰也不敢進諫勸說他。這時,有寧海人鄭士元牽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鄭士利──湖廣按察僉事就為哥哥鄭士元冒死上書訴冤。他首先持書到胡惟庸丞相府,由胡惟庸將上書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胡惟庸等人雖然知道空白蓋印文書的做法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是為了作弊瞞上,但他們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冒死強諫的話,豈不是不要自己腦袋了,因此都不敢向朱元璋進諫。鄭士利詳述了空印書冊的來龍去脈,曉以利害,並作證說鄭士元剛直不阿,在地方上做過很多好事,使用空印文書並無過錯,不應治罪。他的奏摺中說:
「陛下想要嚴厲處罰使用空印文書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書,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書必須加蓋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錢糧所用的文書冊,是兩張紙的騎縫印,不能和一張紙上一個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況一般人還得不到呢?各地錢糧之數,府一定要與省相合,省一定要與部相合,經過多次核對,到戶部才最後確定。省府離中央戶部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書冊核對完成後回本地加蓋印信,往返必須要用一年時間。因此,就先加蓋印信而後書寫,這不過是權宜變通的辦法,很久以來都是這樣做的,怎麼能對他們加以追究治罪呢?[1]而且國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規定向天下公開講明,以後有違犯的人就可以治罪了,因為他們是明知故犯。現在的情況是,自立國至今,沒有關於使用空印文書違法的規定,各部門一直按習慣做下來,不知這是犯罪。如今忽然要給他們治罪,怎麼能使受誅殺的人口服心服呢?」
明辯了空印問題的是非之後,鄭士利又說:
「朝廷選拔賢能,把他們安排到各個位子上,這些官員得到這個位子,都十分難得。一個官員能夠當到郡守,都是數十年努力的結果。這些通達廉明之士的頭,並不像野草一樣,割了以後可以再生。陛下為什麼對其不足以治罪的過錯給予治罪,而損壞了那些可用之才呢?臣竊為陛下感到惋惜。」
在為空印問題做辯護之前,鄭士利事先就已料到,給朱元璋上書,必定會招來殺身橫禍,但他仍心存僥倖:「殺我,生數百人」,要以自己的死,換來數百人的生,因此冒死上書。朱元璋看到鄭士利的奏摺後,果然大怒,不僅沒有聽從他的勸解,反而要追究幕後主使者。鄭士利說:「只看我的上書是不是有用就夠了,為什麼要追究主謀呢?我既然為國家上書提意見,就是死也是應當的。哪裡用得著誰為我主謀呢?」
朱元璋不為所動,結果鄭士利最終還是被定罪,與鄭士元一同罰到江浦做苦工。而那些因適用空白文書而獲罪的數百名官員,正印官處死,副職則一律杖責一百,發往遠方當兵戍守,牽連者無一倖免。在這些人中,就連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2](其子就是後來因反對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誅十族的「天下讀書種子」方孝孺)也被牽連在內,方克勤自洪武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勞改將近一年,最終冤屈而死。
皇帝的盛怒與冤獄
空印案是由皇帝的剛愎自用而鑄成的冤案典型。在古代社會,雖然沒有今日社會的法治文明,但在很多時候,還是會遵從當時的法律規定來斷案的。然而皇帝的存在往往會打破已有的法制框架,產生超乎想像的災難性後果。朱元璋是將這些無辜官員送上斷頭台的禍首,他憑藉一己的成見,殺人無忌,如同兒戲,其處斷之堅決,行刑之迅速,誅殺人數之多讓人瞠目結舌。本案在審理、判刑和證據方面存在著很多荒謬之舉,讓生活在法治社會的我們感到難以接受和理解。
一、有悖常規的審理程序
明朝在承襲前朝的基礎上,也設置了三大中央司法機構,專門負責重大案件的審理。刑部是審理重案的機構,大理寺是對已經審理的案件進行再次審核的機構,而御史台則對刑部和大理寺的審判行為進行監督。地方雖沒有專門的司法機構,但也實行行政兼理司法制度,也就是由行政官員負責司法案件的審理。專門和非專門的司法機構都在現實中存在著,就等著審理各種各樣的訴訟案件。但在本案中,由具有皇帝身分的朱元璋個人定案,沒有經過任何司法機構的審理過程,突破了常規的審理程序。在封建社會,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由皇帝對他認為是非常嚴重的案件進行審判,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在空印案發後,皇帝沒有提審任何涉案官員,沒有認真分析案情、也沒有徵詢相關戶部官員的意見、更不聽取臣子的進諫。他在了解到空印事件的那一刻起,便確定了這個案件的性質和基本的處斷方向,即這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涉及各地官員的交結作弊行為,情節嚴重、性質惡劣,非嚴懲不能以儆傚尤。
二、未適用法律定罪量刑
眾所周知,像明朝這樣用嚴刑懲治貪官汙吏,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以《大明律》為例:對於受財枉法的「枉法贓」,從嚴懲處,一貫以下杖七十,八十貫則絞;對於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罪,滿四十貫即處斬刑;對於執行監察職務的「風憲官」的御史,若犯貪汙罪,則比其他官吏加重兩等處刑。考慮到「空印案」的基本情況,最多可以比照最相類似條款,即受財枉法的「枉法贓」進行懲處。但因這些掌管財務印信的官員們並未有實際枉法受財的事實,只能從輕處罰,即在古代五類刑罰(笞、杖、徒、流、死)當中的「笞」或「杖」當中裁處。可是,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僅沒有看到所適用的法律以及確定罪名的內容,更不存在根據罪名確定刑罰的環節。朱元璋在盛怒之下,僅僅將最終的懲處行為模糊地定位為欺騙朝廷,在沒有任何正式的定罪官文的情況下,便直接下令處死所有主管印信的官員,並將所有下屬的佐吏發配流放。古代的流放刑是僅次於死刑的嚴酷刑罰,將罪犯流配到遠離故土、人煙稀少的荒蕪之所,對罪犯來說不僅是身體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佐吏只不過是按慣例行事,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卻受到如此重罰,不能不說是嚴苛過甚。
「莫須有」是宋代權臣秦檜的名言,他在判定驍勇善戰、為國為民的岳飛是否有罪時,實在無法找到實際證據,便用「也許有罪」的名義誅殺了忠臣岳飛。後人痛斥秦檜的這種濫殺無辜的卑劣行徑,並將「莫須有」作為冤案的代名詞。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以主觀態度枉殺臣民的行為仍在繼續著。
出身平民,透過艱苦鬥爭才謀得皇帝之位的朱元璋猜忌多疑,總是懼怕皇位不保。他認為自己正處於亂世,他感覺到政權外部的元朝蒙古貴族還未肅清,政權內部的武將居功,文臣自大,對他的統治造成了很大威脅,於是他便抱著「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態度對一切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加以重懲,明初的空印案便是這種「莫須有」的冤案。該案株連甚廣,獲罪官員累以百計,而在血流成河的諸般慘狀背後,竟是一個並無充分證據證明的貪汙罪名。讀者要想知道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如果看法偏執、見解僵化,將會帶來何等慘烈的結果?「莫須有」的空印案留給了後人一個毛骨悚然的答案。
案情回顧
與前朝各代類似,明代的中央政府牢牢掌控著地方政府的財政大權。法律規定,各布政司、府州縣每年都要對本地的戶口、錢糧、軍需等事項的各種財政收支情況做帳,並用正式的官文在年底時上報給中央主管財政收支的行政機構──戶部核對。地方官員攜帶的文書要加蓋印信,逐級核對無誤方可透過,如發現上下統計數字不符,戶部要予以駁回。即:戶部對各地發來的文書會詳細審閱,如果戶部核查後,認為帳目清楚,並無不合之處就會確認帳目的有效性,將該中央報銷的款項下撥,但如果發現文書中有不能對帳的部分,戶部也會毫不客氣地將文書駁回地方,由地方主管財政的布政使、府州縣吏等官員在原地重新核查做帳、重新填寫、蓋好印信後,再次上報核對。
看到這裡,似乎這一核查體制並無任何不合情理之處,而且這樣嚴格的審核體制的運作也有利於減少甚至杜絕地方官員貪汙錢財、亂用公款現象的發生,是一個來自中央的有效監督機制。然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一個貌似公平合理的制度在真實的運作中卻面臨著操作上的困難。因為按照法律的規定,各級財政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將帳目上報中央並獲得批准,否則便算瀆職,所以各地官員都希望能夠盡快完成帳目的上報和核查工作。但是在實際中,達成這一目標卻面臨著多項困難:
其一,出現帳目錯誤的可能性大,地方每筆財政收支情況都要詳細記錄,內容瑣碎,核查計算工作十分複雜。在沒有現代計算工具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各種錯誤。如果戶部發現所報帳目有矛盾錯誤之處,都會駁回帳目,而不論這種矛盾有多麼微小。
其二,交通的不便。可能有人會問,帳目被駁回,重做一下就可以了,有什麼困難呢?在現今社會,通訊工具發達,聯絡便利。一封電子郵件或是一張傳真就可以聯絡千里之外的人員,將需要完成的事項和工作通告給他們。然而,在幾百年前,快速更改帳目錯誤,並再次發回中央卻成為了一大難題。當時的文書傳送都靠驛站快馬,馬兒跑得再快,也經不住路途太過遙遠。一來一往又費人力、費金錢,更重要的是費時間,附加地方官員需要在指定期限內上報帳目的上述規定,這種駁回體制便足夠讓地方官員頭痛的了。
一方面上報期限不能更改,另一方面帳目錯誤不能避免,而戶部又不會主動更改帳目。地方財政官員為了保證能夠按期完成上報任務,想出了一個變通辦法:他們讓手下吏員拿著已經蓋好地方政府印章的空白文書到中央去報帳。這樣,如果已有的帳目被戶部駁回,吏員們也不用再奔馳回所屬地方重新做帳了,他們只需要用帶去的空白文書重新抄寫一下已有內容,另將有問題的部分重新計算後抄錄上就可以了。這種做法簡單易行,免除了往返之勞,在當時的報帳體制下,既避免了重新做帳帶來的諸多麻煩,又能使戶部的監督職責得到充分的履行。於是,這種做法逐漸變成了一種通行的慣例,幾乎所有的負責上報財政狀況職的地方官員都採用這種做法。在實踐中,這一慣例也得到了戶部的認同。
然而,到洪武九年(西元一三七六年),事情發生了逆轉。朱元璋在偶然得知這一做法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主觀認定地方官員用空白的蓋印文書再次做帳,深恐他們「以為欺罔」、「其中有奸」(即各地方官大有貪汙矇蔽的嫌疑);而且全國都採用這種做法,可能造成的假帳會有多少?朱元璋越想越氣,認為如果不對這種做法加以嚴懲,「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明史.鄭士利傳》),私下偷懶,擅自蓋印而輕視皇權,難以使之恪盡職守、認真統理帳目。於是大發雷霆,下令嚴懲不貸,將那些掌管官印的地方官都抓了起來,要將主印官一律處死。因為地方官多採用這種辦法做帳,所以為此事獲罪的官員很多,自尚書至守令,署空印書冊的皆坐欺罔論死;佐貳以下杖一百戍邊。據統計,因此案株連殺戮、充軍邊地者達數百人,地方管理田糧的長吏幾乎一殺而空。
案發之後,滿朝大臣看著勃然大怒的皇帝朱元璋,誰也不敢進諫勸說他。這時,有寧海人鄭士元牽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鄭士利──湖廣按察僉事就為哥哥鄭士元冒死上書訴冤。他首先持書到胡惟庸丞相府,由胡惟庸將上書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胡惟庸等人雖然知道空白蓋印文書的做法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是為了作弊瞞上,但他們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冒死強諫的話,豈不是不要自己腦袋了,因此都不敢向朱元璋進諫。鄭士利詳述了空印書冊的來龍去脈,曉以利害,並作證說鄭士元剛直不阿,在地方上做過很多好事,使用空印文書並無過錯,不應治罪。他的奏摺中說:
「陛下想要嚴厲處罰使用空印文書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書,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書必須加蓋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錢糧所用的文書冊,是兩張紙的騎縫印,不能和一張紙上一個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況一般人還得不到呢?各地錢糧之數,府一定要與省相合,省一定要與部相合,經過多次核對,到戶部才最後確定。省府離中央戶部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書冊核對完成後回本地加蓋印信,往返必須要用一年時間。因此,就先加蓋印信而後書寫,這不過是權宜變通的辦法,很久以來都是這樣做的,怎麼能對他們加以追究治罪呢?[1]而且國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規定向天下公開講明,以後有違犯的人就可以治罪了,因為他們是明知故犯。現在的情況是,自立國至今,沒有關於使用空印文書違法的規定,各部門一直按習慣做下來,不知這是犯罪。如今忽然要給他們治罪,怎麼能使受誅殺的人口服心服呢?」
明辯了空印問題的是非之後,鄭士利又說:
「朝廷選拔賢能,把他們安排到各個位子上,這些官員得到這個位子,都十分難得。一個官員能夠當到郡守,都是數十年努力的結果。這些通達廉明之士的頭,並不像野草一樣,割了以後可以再生。陛下為什麼對其不足以治罪的過錯給予治罪,而損壞了那些可用之才呢?臣竊為陛下感到惋惜。」
在為空印問題做辯護之前,鄭士利事先就已料到,給朱元璋上書,必定會招來殺身橫禍,但他仍心存僥倖:「殺我,生數百人」,要以自己的死,換來數百人的生,因此冒死上書。朱元璋看到鄭士利的奏摺後,果然大怒,不僅沒有聽從他的勸解,反而要追究幕後主使者。鄭士利說:「只看我的上書是不是有用就夠了,為什麼要追究主謀呢?我既然為國家上書提意見,就是死也是應當的。哪裡用得著誰為我主謀呢?」
朱元璋不為所動,結果鄭士利最終還是被定罪,與鄭士元一同罰到江浦做苦工。而那些因適用空白文書而獲罪的數百名官員,正印官處死,副職則一律杖責一百,發往遠方當兵戍守,牽連者無一倖免。在這些人中,就連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2](其子就是後來因反對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誅十族的「天下讀書種子」方孝孺)也被牽連在內,方克勤自洪武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勞改將近一年,最終冤屈而死。
皇帝的盛怒與冤獄
空印案是由皇帝的剛愎自用而鑄成的冤案典型。在古代社會,雖然沒有今日社會的法治文明,但在很多時候,還是會遵從當時的法律規定來斷案的。然而皇帝的存在往往會打破已有的法制框架,產生超乎想像的災難性後果。朱元璋是將這些無辜官員送上斷頭台的禍首,他憑藉一己的成見,殺人無忌,如同兒戲,其處斷之堅決,行刑之迅速,誅殺人數之多讓人瞠目結舌。本案在審理、判刑和證據方面存在著很多荒謬之舉,讓生活在法治社會的我們感到難以接受和理解。
一、有悖常規的審理程序
明朝在承襲前朝的基礎上,也設置了三大中央司法機構,專門負責重大案件的審理。刑部是審理重案的機構,大理寺是對已經審理的案件進行再次審核的機構,而御史台則對刑部和大理寺的審判行為進行監督。地方雖沒有專門的司法機構,但也實行行政兼理司法制度,也就是由行政官員負責司法案件的審理。專門和非專門的司法機構都在現實中存在著,就等著審理各種各樣的訴訟案件。但在本案中,由具有皇帝身分的朱元璋個人定案,沒有經過任何司法機構的審理過程,突破了常規的審理程序。在封建社會,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由皇帝對他認為是非常嚴重的案件進行審判,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在空印案發後,皇帝沒有提審任何涉案官員,沒有認真分析案情、也沒有徵詢相關戶部官員的意見、更不聽取臣子的進諫。他在了解到空印事件的那一刻起,便確定了這個案件的性質和基本的處斷方向,即這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涉及各地官員的交結作弊行為,情節嚴重、性質惡劣,非嚴懲不能以儆傚尤。
二、未適用法律定罪量刑
眾所周知,像明朝這樣用嚴刑懲治貪官汙吏,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以《大明律》為例:對於受財枉法的「枉法贓」,從嚴懲處,一貫以下杖七十,八十貫則絞;對於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罪,滿四十貫即處斬刑;對於執行監察職務的「風憲官」的御史,若犯貪汙罪,則比其他官吏加重兩等處刑。考慮到「空印案」的基本情況,最多可以比照最相類似條款,即受財枉法的「枉法贓」進行懲處。但因這些掌管財務印信的官員們並未有實際枉法受財的事實,只能從輕處罰,即在古代五類刑罰(笞、杖、徒、流、死)當中的「笞」或「杖」當中裁處。可是,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僅沒有看到所適用的法律以及確定罪名的內容,更不存在根據罪名確定刑罰的環節。朱元璋在盛怒之下,僅僅將最終的懲處行為模糊地定位為欺騙朝廷,在沒有任何正式的定罪官文的情況下,便直接下令處死所有主管印信的官員,並將所有下屬的佐吏發配流放。古代的流放刑是僅次於死刑的嚴酷刑罰,將罪犯流配到遠離故土、人煙稀少的荒蕪之所,對罪犯來說不僅是身體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佐吏只不過是按慣例行事,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卻受到如此重罰,不能不說是嚴苛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