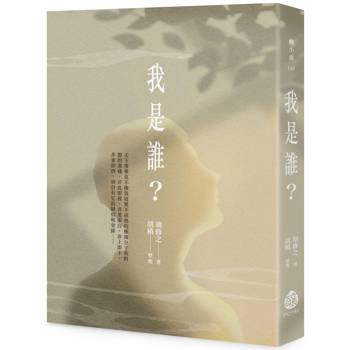第一章 第十三節(節錄)
這時候,我對什麼叫新聞、如何當記者,確實也是茫無頭緒的。新聞教科書說,新聞有三個要素,即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和什麼內容,未免過於簡單,說了等於沒說。書上舉例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表示三要素以外,還有離奇的成分。然而登在報上的,不僅僅只有離奇一類,而且狂犬咬人還是當作新聞發表的。《泰晤士報》以「本報刊登一切適宜刊載的新聞」為口號,但是何者適宜?何者不適宜?這標準它又祕而不宣。我就此向陸先生請教,陸先生說:「很難用一兩句話就向你說得一清二楚。依我看,『新聞』二字,一個是新,要新鮮的,不要陳舊的,別人說過的事你就不必再說;一個是聞,那就是喜聞樂見的聞,你寫的消息讀者要愛看。至於『記者』兩字,要緊的是個『記』字。你記下來就行,不要改,不能添枝加葉,也不許胡編亂造,所貴者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新聞有大小,有可登,有不可登,這要靠記者去識別、挑選,而後寫好。一個記者的好壞,就在這上頭。你新來乍到,不要急,慢慢摸索起來就是。有個一年半載時間,你就通了。」
果然,不久以後,我慢慢地摸到了一些門道。醫院天天死人,死人在醫院裡就不成為新聞,但是如果有人死後又活過來,那就成為新聞。與此理相同,活人在街上走路,不成其為新聞。但是行人忽然被汽車碾死或者被人群毆斃、殺死,立刻就成為新聞。以此類推,汽車在馬路上跑、飛機在天空裡飛、輪船在江河裡開,都不是新聞。然而汽車忽然墜入深溝、火車忽然出軌傾覆、輪船忽然遇難沉沒、飛機忽然失事墜毀,則又成為新聞。在人事方面,普通人今天到東、明天到西都不是新聞,但是蔣介石上廬山、馮玉祥去蘇聯、宋子文到開羅、孔祥熙赴紐約、魏德邁抵張家口、馬歇爾來南京城,乃至梅蘭芳北上、程硯秋南下,卻不僅僅是新聞,而且有時是最重要的一版頭條新聞。吳國楨到美國留學,在上海賣過領帶,從沒有報紙為他發過新聞,然而他被宋美齡看中當上上海市長後,偶爾陪個美國人到龍華看看桃花會成為「花邊新聞」。商店賣出一隻籃球,毫無新聞價值,但是一場球賽後這隻籃球由電影明星李麗華或者王丹鳳支持拍賣,最後由某名人出鉅資買下,款項移作公益之用,成了「義球」,就又成了極大新聞。不過話無法說得太死、太絕對。一個小人物安分守己、循規蹈矩,本來是不會成為新聞人物的,然而要是他忽然殺人越貨、強姦劫獄,或者服毒上吊、投河臥軌,則將酌情成為大小不等的新聞中的角色。
新聞這麼多,而報紙的篇幅卻有限,登什麼?不登什麼?就要由編者來決定。但是在編者決定以前,記者已擔當了首輪挑選的任務。記者把估計「擠」不進版面的新聞、價值不大的新聞都放棄了。「擠」,當然就是大而重要的擠掉小而次要的,但這也並不一定就是天經地義,小而次要的擠掉大而重要的事,偶爾也會發生。因為新聞的絕大部分都牽涉到人,而人和人總不一樣。有的人有權有勢有錢,有的人有此三者中的一項、兩項,有的人則三者俱無。這樣一來,牽涉到某一類人的新聞,登與不登,要由記者、編輯、主筆、當事人以及與當事人相關各方的人上下縱橫、錯綜複雜的關係來決定,常常發生報社要登、當事人不讓登或者當事人要登、報社又不讓登的情事。偶爾,報社記者、編輯、主筆等人員的稟賦、質地、性格、脾氣甚至當天心情愉快與否,也會影響到某一新聞的登與不登。舉個例說,夫妻睡覺,不屬於新聞範圍,但是夫妻中的一方,姑且假定為女方,同丈夫以外的男人睡覺,不幸被人發覺,捉到警察局,就構成了新聞。這是大而重要還是小而次要的新聞,不取決於這對野鴛鴦睡覺的情節,而取決於野鴛鴦及其本夫是什麼人,權、勢、財的程度如何。刊登與否,也不簡單地取決於當事人三方的願望和報紙的篇幅,而取決於當事人的地位、背景和各方的關係,有時又和報紙方面的金錢利益有關。總而言之,複雜得很,或如陸先生所言,一兩句話無法說得清楚。
決定刊登之後,接著就發生怎麼寫這條新聞的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同是《春秋》,傳分《左》、《公羊》、《穀梁》三種。官府稱宋江為賊,宋江自稱則是義士,這天下事本來就難說定,寫新聞亦然如此。仍以上例為例,記者可以不偏袒任何一方,做就事論事的純客觀記敘,也可以為本夫鳴不平,或可以為女方做辯解,甚至可以為姦夫開脫,暗示姦夫姦婦睡覺有其必要與必然。到底為誰寫這條新聞,往往不取決於記者的認識和好惡,而要取決於微妙、複雜的各方之間的利害。這裡不妨用畫家畫茶壺做個比喻,同是一把茶壺,畫家以壺嘴為基準,從左面、右面、正中、上方、下方、背面六個角度觀察,可以畫出六個各不相同的畫面。這些畫面都如實反映出這是一把茶壺,觀眾看後也獲得了是茶壺而不是茶杯的印象。
因此這也是一門比較複雜的學問,不是阿貓阿狗都能充當記者的。開始我還想別出蹊徑,獨樹一幟,憑良知來寫新聞,旋即發覺,這根本行不通、辦不到。因為我是作為社會人而不僅僅是自然人而存在的,社會人需要依靠某一集團的利益而生活。良知只對主觀世界亦即自然人起作用,在變幻不定的客觀世界亦即社會人面前,卻一籌莫展。人們常說:「良心值幾個錢?」道理大約就在這裡。
這時候,我對什麼叫新聞、如何當記者,確實也是茫無頭緒的。新聞教科書說,新聞有三個要素,即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和什麼內容,未免過於簡單,說了等於沒說。書上舉例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表示三要素以外,還有離奇的成分。然而登在報上的,不僅僅只有離奇一類,而且狂犬咬人還是當作新聞發表的。《泰晤士報》以「本報刊登一切適宜刊載的新聞」為口號,但是何者適宜?何者不適宜?這標準它又祕而不宣。我就此向陸先生請教,陸先生說:「很難用一兩句話就向你說得一清二楚。依我看,『新聞』二字,一個是新,要新鮮的,不要陳舊的,別人說過的事你就不必再說;一個是聞,那就是喜聞樂見的聞,你寫的消息讀者要愛看。至於『記者』兩字,要緊的是個『記』字。你記下來就行,不要改,不能添枝加葉,也不許胡編亂造,所貴者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新聞有大小,有可登,有不可登,這要靠記者去識別、挑選,而後寫好。一個記者的好壞,就在這上頭。你新來乍到,不要急,慢慢摸索起來就是。有個一年半載時間,你就通了。」
果然,不久以後,我慢慢地摸到了一些門道。醫院天天死人,死人在醫院裡就不成為新聞,但是如果有人死後又活過來,那就成為新聞。與此理相同,活人在街上走路,不成其為新聞。但是行人忽然被汽車碾死或者被人群毆斃、殺死,立刻就成為新聞。以此類推,汽車在馬路上跑、飛機在天空裡飛、輪船在江河裡開,都不是新聞。然而汽車忽然墜入深溝、火車忽然出軌傾覆、輪船忽然遇難沉沒、飛機忽然失事墜毀,則又成為新聞。在人事方面,普通人今天到東、明天到西都不是新聞,但是蔣介石上廬山、馮玉祥去蘇聯、宋子文到開羅、孔祥熙赴紐約、魏德邁抵張家口、馬歇爾來南京城,乃至梅蘭芳北上、程硯秋南下,卻不僅僅是新聞,而且有時是最重要的一版頭條新聞。吳國楨到美國留學,在上海賣過領帶,從沒有報紙為他發過新聞,然而他被宋美齡看中當上上海市長後,偶爾陪個美國人到龍華看看桃花會成為「花邊新聞」。商店賣出一隻籃球,毫無新聞價值,但是一場球賽後這隻籃球由電影明星李麗華或者王丹鳳支持拍賣,最後由某名人出鉅資買下,款項移作公益之用,成了「義球」,就又成了極大新聞。不過話無法說得太死、太絕對。一個小人物安分守己、循規蹈矩,本來是不會成為新聞人物的,然而要是他忽然殺人越貨、強姦劫獄,或者服毒上吊、投河臥軌,則將酌情成為大小不等的新聞中的角色。
新聞這麼多,而報紙的篇幅卻有限,登什麼?不登什麼?就要由編者來決定。但是在編者決定以前,記者已擔當了首輪挑選的任務。記者把估計「擠」不進版面的新聞、價值不大的新聞都放棄了。「擠」,當然就是大而重要的擠掉小而次要的,但這也並不一定就是天經地義,小而次要的擠掉大而重要的事,偶爾也會發生。因為新聞的絕大部分都牽涉到人,而人和人總不一樣。有的人有權有勢有錢,有的人有此三者中的一項、兩項,有的人則三者俱無。這樣一來,牽涉到某一類人的新聞,登與不登,要由記者、編輯、主筆、當事人以及與當事人相關各方的人上下縱橫、錯綜複雜的關係來決定,常常發生報社要登、當事人不讓登或者當事人要登、報社又不讓登的情事。偶爾,報社記者、編輯、主筆等人員的稟賦、質地、性格、脾氣甚至當天心情愉快與否,也會影響到某一新聞的登與不登。舉個例說,夫妻睡覺,不屬於新聞範圍,但是夫妻中的一方,姑且假定為女方,同丈夫以外的男人睡覺,不幸被人發覺,捉到警察局,就構成了新聞。這是大而重要還是小而次要的新聞,不取決於這對野鴛鴦睡覺的情節,而取決於野鴛鴦及其本夫是什麼人,權、勢、財的程度如何。刊登與否,也不簡單地取決於當事人三方的願望和報紙的篇幅,而取決於當事人的地位、背景和各方的關係,有時又和報紙方面的金錢利益有關。總而言之,複雜得很,或如陸先生所言,一兩句話無法說得清楚。
決定刊登之後,接著就發生怎麼寫這條新聞的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同是《春秋》,傳分《左》、《公羊》、《穀梁》三種。官府稱宋江為賊,宋江自稱則是義士,這天下事本來就難說定,寫新聞亦然如此。仍以上例為例,記者可以不偏袒任何一方,做就事論事的純客觀記敘,也可以為本夫鳴不平,或可以為女方做辯解,甚至可以為姦夫開脫,暗示姦夫姦婦睡覺有其必要與必然。到底為誰寫這條新聞,往往不取決於記者的認識和好惡,而要取決於微妙、複雜的各方之間的利害。這裡不妨用畫家畫茶壺做個比喻,同是一把茶壺,畫家以壺嘴為基準,從左面、右面、正中、上方、下方、背面六個角度觀察,可以畫出六個各不相同的畫面。這些畫面都如實反映出這是一把茶壺,觀眾看後也獲得了是茶壺而不是茶杯的印象。
因此這也是一門比較複雜的學問,不是阿貓阿狗都能充當記者的。開始我還想別出蹊徑,獨樹一幟,憑良知來寫新聞,旋即發覺,這根本行不通、辦不到。因為我是作為社會人而不僅僅是自然人而存在的,社會人需要依靠某一集團的利益而生活。良知只對主觀世界亦即自然人起作用,在變幻不定的客觀世界亦即社會人面前,卻一籌莫展。人們常說:「良心值幾個錢?」道理大約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