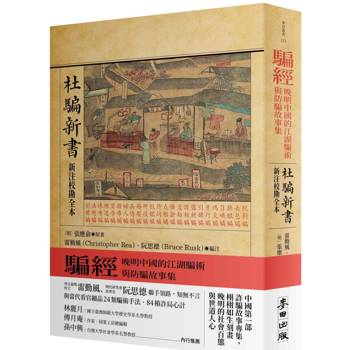導論 原來皆為騙中騙——重讀明代「騙經」
我們生活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言語和外觀誤導好人;行騙高手坑害粗心大意之人;官場中充滿了偽君子;市場上放眼皆是掛羊頭賣狗肉。每個陌生人都是潛在的敵人,走出家門就得自擔風險。在這個騙子橫行的世界,必須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生存。然而,怎樣提防笑裡藏刀?留心你的親屬,保管好自己的財物,絕不要相信任何人。
但是,首先,看官請讀這本書。
據所知,《杜騙新書》是中國第一部欺詐故事專集。書中匯集八十四則故事,依照欺詐的方法、地點或行凶者分為二十四類。每一則故事後頭都有作者張應俞(約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在世)的按語,另有五則額外的故事見於作者的按語中。整體而言,此故事集呈現當時社會欺詐行為的全景式觀察,作者是一位對普通人,尤其是行商之人,所面對的危險饒有興趣的評論家。
《杜騙新書》中所敘述的犯罪與欺詐行為,主要發生在明代晚期。在此時期,中國國內與國際商業貿易的蓬勃發展,創造了大筆橫財。這些流動的貨幣帶來新的風險和社會變動,張氏此書即把握住了由此而生的偏差風氣。財富在繁榮帝國南部的道路、運河與街市小巷中流動,故事主要關心的是從中獲富的策略。騙子與受害者來自北至北京、西至四川、南至廣東、廣西的地區,但大部分的詐騙行為發生在陪都南京(北京是實質上的首都)與福建之間。
張應俞稱非法侵占財產者為「棍」,本義是「棍棒」,但可用來指代任何靠犯罪為生的人。這些「棍」所使用的方法有時候是暴力,但故事中總是帶有欺騙與狡猾的元素。 張氏稱他們的策略為「騙」,主要關注這些棍在擺布受害者方面的聰明才智和創意。
總之,《杜騙新書》呈現當時社會的暗淡景象。看官,你是否喜歡鄰居背叛、配偶賣淫、旅行者被殺、誠實的商人被騙、有前途的學生墮落、良家婦女放蕩、寡婦被下藥的故事?你是否喜歡那些篡改司法制度、違背宗教誓言、矇騙信徒、金銀攙假、慫恿賭博和酗酒、虐待兒童、使用巫術、煽動叛亂,以及趁人不備進行搶劫的惡棍故事?
如果是的話,這本書非讀不可。
《杜騙新書》呈現一系列的詐騙場景、動機和原型。行商假冒親屬偷竊對方的貨物;搬運工和船工騙取不知情旅客的財物,有時甚至謀害他們的性命;貨幣兌換商和來客習慣用攙假的銀子互相欺騙;江湖術士催眠無辜的孩童、煽動遊手好閒的富人造反;一遊方道士假扮成白無常騙取財物,另一人則佯稱能煉丹以撈取小錢;一人強姦其兒媳,而後在其妻的精心策畫下,又騙姦了兒媳的母親;不止一個流動詐騙犯開設了二十世紀美國騙徒所謂的「大店面」,這種看似合法的生意會令人放鬆警惕進而受騙。 鄰居、官吏、店主、工匠、友善的女子、和尚——無人值得信任。
名義上,書中原標題表明,本書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讀者免受欺詐之害。本書第一版大約刻於一六一七年或略晚,其書名頁標《江湖歷覽杜騙新書》。誠然,關於詐騙的知識可以幫助讀者對抗江湖上的騙術。然而,杜騙之書同時也可以是教人行騙的手冊。若單純作娛樂之用,本書提供豐富的故事細節,刻畫了一般讀者不大可能遭遇的犯罪行為,比如被太監烹食。張應俞為故事附上的按語,在堅定反對棍的罪行與帶有鑒賞眼光欣賞其足智多謀兩方面,搖擺不定。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瀰漫於全書,既肯定人的行為應以普世道德標準來評斷,卻又對此觀念產生動搖,這也許是當代版本之所以同時被稱為《防騙經》和《騙經》的原因。
「經」在古代,專門用來指稱特定知識領域的核心文本:作為正統儒學基礎的古代哲學經典、佛道兩家的宗教經典,或者後來傳入的《聖經》。這個術語最後被用於不那麼嚴肅的領域,有《茶經》、《棋經》以及《嫖經》 等。如同這些「經」,《杜騙新書》被認為是一部「經」,是由於針對特定領域提供了力求確定、具權威性、全面性的深入闡述。
在這篇導論中,我們將以不同角度來欣賞這部中國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為處於危險中的世界提出了警示。
作者和他的聲音
張應俞,字夔衷,生平不詳。《杜騙新書》是目前所知他名下唯一的作品,各類傳記性材料中也沒有任何關於張氏的記載。他生活於明代萬曆年間(一五六三|一六二〇)。據本書一六一七年的序,他生於福建省建陽縣。此記載看似較為可信,因本書現存的最早版本就刻印於此地,書中地名可考的故事一半都發生在福建,而且故事中偶爾出現閩北方言。 然而,此生平資訊卻與《杜騙新書》本身的內容有所牴牾:明代版本的每卷卷頭表明張氏來自浙江省。其中一種可能是,張應俞祖籍浙江,但定居福建。
張氏的按語是《杜騙新書》的一大亮點之一。評論,包括作者的自注或按語,在中國古代許多文學體裁(包括明代通俗小說)中都很常見。早期的史學家創立此作法,他們在所著述的傳記和時文中附上評論,以自己的口吻表達對正文所敘事件的意見。在這之後的作者、編者和評論者往往熱中於藉其澄清故事情節或者解釋詞句,以便故事的寓意能為讀者所理解。
通過評論自己所寫的故事,張應俞扮演了多個角色。他像道學家一般追究騙局中各方的責任,有時他把過錯歸咎於受害者的愚笨天真,而非棍的唯利是圖——受害者本應當知道得更多一點以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他像欺詐與犯罪領域的權威,評價騙子欺騙的技巧、詐騙對象的反擊及警覺、司法干預者的行為以及審判官員的明察。評論的目標之一,就是區分技能和無能。一項特定的能力、洞察力,對世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作者甚至寫了一個根本沒有欺瞞或詐騙的故事──〈行李誤挑往別船〉,其標題不言自明,這個故事揭示了無能在一般商業行為中的影響。他也作為見證人發言,根據所謂的一手資料來證實、反駁和提供實際情事,例如〈詐學道書報好夢〉、〈婦嫁淘街而害命〉和〈地理寄婦脫好種〉的故事。幾乎在所有例子中,他不僅會評論一個獨立的案例,也推斷出一則普世的道德教訓或一條實用的建議。有時他的按語會包含額外的材料,甚至完整的故事:〈冒州接著漂白鏪〉與〈地理寄婦脫好種〉包含篇幅最長、內容最複雜的按語。後一則故事的按語中嵌入了三個附加的故事;張氏在前一則故事的按語中讓我們了解了晚明商業的主要貨幣——白銀——為眾多騙局的目標,有時也是工具。僅有〈因蛙露出謀娶情〉和〈船載家人行李逃〉這兩個故事不附作者的按語。
要讀懂《杜騙新書》中的故事,一個明代的讀者應當只須具備閱讀簡易文言的能力並且熟悉基本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受過教育的商人應該會掌握的知識。而張應俞的按語則經常使用較為正式的語言,並且引用受過高級古典教育的讀者才能理解的文史典故。張應俞經常提及《易經》,看來他曾在科舉考試中學習這本儒家經典的古代占卜書籍。(熊振驥在其〈序〉中將《易經》當作《杜騙新書》的榜樣之一。)這些典故,有的並沒有明說出處,反而要求讀者自己辨認出來。《易經》由六十四個被稱為「卦」的圖像構成,每個圖像由六條橫線(爻)由下到上排列而成。在占卜過程中,通常會使用拋擲蓍草或者硬幣來得出一卦,並根據結果對應特定的爻象。《易經》的文本包括簡短而隱晦的卦辭、爻辭和多層附加的注解。占卜者為決定如何對待某種狀況來翻看《易經》,並且使用占卜中產生的卦爻辭來解釋它。張應俞也把《易經》看作智慧與見識的寶庫,引用其詞句來指導各式各樣道德與現實的決策。比如,〈帶鏡船中引謀害〉講述忠誠的家僕保護紈绔公子的故事,這位紈绔將商旅變為浪遊。在故事後的按語,張應俞引用了《易經》第五十六卦「旅」卦的爻辭,講述好童僕的重要性。張並未提到《易經》的名稱,他要麼認為讀者應該了解這個沒有注明出處的引用,要麼不關心讀者是否知道這一點。
(以上摘自本書〈導論:原來皆為騙中騙——重讀明代「騙經」〉)
我們生活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言語和外觀誤導好人;行騙高手坑害粗心大意之人;官場中充滿了偽君子;市場上放眼皆是掛羊頭賣狗肉。每個陌生人都是潛在的敵人,走出家門就得自擔風險。在這個騙子橫行的世界,必須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生存。然而,怎樣提防笑裡藏刀?留心你的親屬,保管好自己的財物,絕不要相信任何人。
但是,首先,看官請讀這本書。
據所知,《杜騙新書》是中國第一部欺詐故事專集。書中匯集八十四則故事,依照欺詐的方法、地點或行凶者分為二十四類。每一則故事後頭都有作者張應俞(約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在世)的按語,另有五則額外的故事見於作者的按語中。整體而言,此故事集呈現當時社會欺詐行為的全景式觀察,作者是一位對普通人,尤其是行商之人,所面對的危險饒有興趣的評論家。
《杜騙新書》中所敘述的犯罪與欺詐行為,主要發生在明代晚期。在此時期,中國國內與國際商業貿易的蓬勃發展,創造了大筆橫財。這些流動的貨幣帶來新的風險和社會變動,張氏此書即把握住了由此而生的偏差風氣。財富在繁榮帝國南部的道路、運河與街市小巷中流動,故事主要關心的是從中獲富的策略。騙子與受害者來自北至北京、西至四川、南至廣東、廣西的地區,但大部分的詐騙行為發生在陪都南京(北京是實質上的首都)與福建之間。
張應俞稱非法侵占財產者為「棍」,本義是「棍棒」,但可用來指代任何靠犯罪為生的人。這些「棍」所使用的方法有時候是暴力,但故事中總是帶有欺騙與狡猾的元素。 張氏稱他們的策略為「騙」,主要關注這些棍在擺布受害者方面的聰明才智和創意。
總之,《杜騙新書》呈現當時社會的暗淡景象。看官,你是否喜歡鄰居背叛、配偶賣淫、旅行者被殺、誠實的商人被騙、有前途的學生墮落、良家婦女放蕩、寡婦被下藥的故事?你是否喜歡那些篡改司法制度、違背宗教誓言、矇騙信徒、金銀攙假、慫恿賭博和酗酒、虐待兒童、使用巫術、煽動叛亂,以及趁人不備進行搶劫的惡棍故事?
如果是的話,這本書非讀不可。
《杜騙新書》呈現一系列的詐騙場景、動機和原型。行商假冒親屬偷竊對方的貨物;搬運工和船工騙取不知情旅客的財物,有時甚至謀害他們的性命;貨幣兌換商和來客習慣用攙假的銀子互相欺騙;江湖術士催眠無辜的孩童、煽動遊手好閒的富人造反;一遊方道士假扮成白無常騙取財物,另一人則佯稱能煉丹以撈取小錢;一人強姦其兒媳,而後在其妻的精心策畫下,又騙姦了兒媳的母親;不止一個流動詐騙犯開設了二十世紀美國騙徒所謂的「大店面」,這種看似合法的生意會令人放鬆警惕進而受騙。 鄰居、官吏、店主、工匠、友善的女子、和尚——無人值得信任。
名義上,書中原標題表明,本書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讀者免受欺詐之害。本書第一版大約刻於一六一七年或略晚,其書名頁標《江湖歷覽杜騙新書》。誠然,關於詐騙的知識可以幫助讀者對抗江湖上的騙術。然而,杜騙之書同時也可以是教人行騙的手冊。若單純作娛樂之用,本書提供豐富的故事細節,刻畫了一般讀者不大可能遭遇的犯罪行為,比如被太監烹食。張應俞為故事附上的按語,在堅定反對棍的罪行與帶有鑒賞眼光欣賞其足智多謀兩方面,搖擺不定。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瀰漫於全書,既肯定人的行為應以普世道德標準來評斷,卻又對此觀念產生動搖,這也許是當代版本之所以同時被稱為《防騙經》和《騙經》的原因。
「經」在古代,專門用來指稱特定知識領域的核心文本:作為正統儒學基礎的古代哲學經典、佛道兩家的宗教經典,或者後來傳入的《聖經》。這個術語最後被用於不那麼嚴肅的領域,有《茶經》、《棋經》以及《嫖經》 等。如同這些「經」,《杜騙新書》被認為是一部「經」,是由於針對特定領域提供了力求確定、具權威性、全面性的深入闡述。
在這篇導論中,我們將以不同角度來欣賞這部中國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為處於危險中的世界提出了警示。
作者和他的聲音
張應俞,字夔衷,生平不詳。《杜騙新書》是目前所知他名下唯一的作品,各類傳記性材料中也沒有任何關於張氏的記載。他生活於明代萬曆年間(一五六三|一六二〇)。據本書一六一七年的序,他生於福建省建陽縣。此記載看似較為可信,因本書現存的最早版本就刻印於此地,書中地名可考的故事一半都發生在福建,而且故事中偶爾出現閩北方言。 然而,此生平資訊卻與《杜騙新書》本身的內容有所牴牾:明代版本的每卷卷頭表明張氏來自浙江省。其中一種可能是,張應俞祖籍浙江,但定居福建。
張氏的按語是《杜騙新書》的一大亮點之一。評論,包括作者的自注或按語,在中國古代許多文學體裁(包括明代通俗小說)中都很常見。早期的史學家創立此作法,他們在所著述的傳記和時文中附上評論,以自己的口吻表達對正文所敘事件的意見。在這之後的作者、編者和評論者往往熱中於藉其澄清故事情節或者解釋詞句,以便故事的寓意能為讀者所理解。
通過評論自己所寫的故事,張應俞扮演了多個角色。他像道學家一般追究騙局中各方的責任,有時他把過錯歸咎於受害者的愚笨天真,而非棍的唯利是圖——受害者本應當知道得更多一點以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他像欺詐與犯罪領域的權威,評價騙子欺騙的技巧、詐騙對象的反擊及警覺、司法干預者的行為以及審判官員的明察。評論的目標之一,就是區分技能和無能。一項特定的能力、洞察力,對世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作者甚至寫了一個根本沒有欺瞞或詐騙的故事──〈行李誤挑往別船〉,其標題不言自明,這個故事揭示了無能在一般商業行為中的影響。他也作為見證人發言,根據所謂的一手資料來證實、反駁和提供實際情事,例如〈詐學道書報好夢〉、〈婦嫁淘街而害命〉和〈地理寄婦脫好種〉的故事。幾乎在所有例子中,他不僅會評論一個獨立的案例,也推斷出一則普世的道德教訓或一條實用的建議。有時他的按語會包含額外的材料,甚至完整的故事:〈冒州接著漂白鏪〉與〈地理寄婦脫好種〉包含篇幅最長、內容最複雜的按語。後一則故事的按語中嵌入了三個附加的故事;張氏在前一則故事的按語中讓我們了解了晚明商業的主要貨幣——白銀——為眾多騙局的目標,有時也是工具。僅有〈因蛙露出謀娶情〉和〈船載家人行李逃〉這兩個故事不附作者的按語。
要讀懂《杜騙新書》中的故事,一個明代的讀者應當只須具備閱讀簡易文言的能力並且熟悉基本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受過教育的商人應該會掌握的知識。而張應俞的按語則經常使用較為正式的語言,並且引用受過高級古典教育的讀者才能理解的文史典故。張應俞經常提及《易經》,看來他曾在科舉考試中學習這本儒家經典的古代占卜書籍。(熊振驥在其〈序〉中將《易經》當作《杜騙新書》的榜樣之一。)這些典故,有的並沒有明說出處,反而要求讀者自己辨認出來。《易經》由六十四個被稱為「卦」的圖像構成,每個圖像由六條橫線(爻)由下到上排列而成。在占卜過程中,通常會使用拋擲蓍草或者硬幣來得出一卦,並根據結果對應特定的爻象。《易經》的文本包括簡短而隱晦的卦辭、爻辭和多層附加的注解。占卜者為決定如何對待某種狀況來翻看《易經》,並且使用占卜中產生的卦爻辭來解釋它。張應俞也把《易經》看作智慧與見識的寶庫,引用其詞句來指導各式各樣道德與現實的決策。比如,〈帶鏡船中引謀害〉講述忠誠的家僕保護紈绔公子的故事,這位紈绔將商旅變為浪遊。在故事後的按語,張應俞引用了《易經》第五十六卦「旅」卦的爻辭,講述好童僕的重要性。張並未提到《易經》的名稱,他要麼認為讀者應該了解這個沒有注明出處的引用,要麼不關心讀者是否知道這一點。
(以上摘自本書〈導論:原來皆為騙中騙——重讀明代「騙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