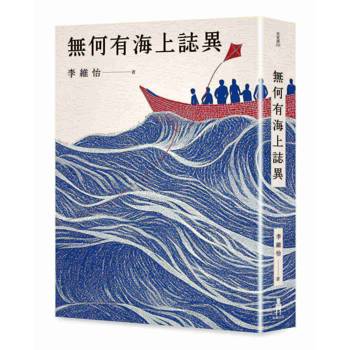【卷四 月啞光,水流梳】
1
天上一勾下弦月,等待著什麼上鉤。
鉤月白光啞啞,倒讓星群滿天嘈吵著。盛夏夜海,風微微碎,浪浮浮晃,艇上的二人卻連飆冷汗,搖櫓聲異常急速。耳朵塞滿了些隨身帶備的碎布,卻又思疑自己是否仍聽到那些不知是嗯嗯哼哼?還是尖聲細叫?還是海水謠?還是石頭刮石頭,好似姑姐打紫菜的聲音……
那些白色的什麼在孤島崖邊跳落水,高速向他們游過來的殘影,還在鄭福鄭洪兩兄弟腦裡不斷閃現。二人都極其安靜,一心盡快搖船埋岸,眼睛也不敢往水裡看,彷彿大家都不說話便可當作無事發生。心急如焚,時間自然過得慢,到終於遙望到雙連島上零散的昏黃燈光,撲撲跳的心才開始漸漸踏實下來,以後還是盡量避免晚上停泊在那些無人島,以免又遇上什麼髒東西。
眼看要埋岸,弟弟鄭洪正準備繩子,忽然船哐啷一聲劇烈搖擺了一下,彷佛有條超大魚在船底經過,不經意與船底磨擦了一下似的,二人嚇得心差點沒跳出來,蹲著抓緊船邊。可是,過不一會,又靜下來了……
終於腳踏實地,綁好船隻。
「下次都是聽阿爸話,請個海娘娘放船頭啦,好邪。」弟弟鄭洪道。「阿母話放蛇神。」哥哥鄭福道。
「唉兩個都放啦!」
鄭洪提起漁籮,看著好幾條肥石斑,好幾斤重,還有幾條紅鸚鵡魚、油錐,也不乏一些雜魚。已忘了幾多年前的墟期,有個白突國的人上岸做買賣,一見那紅鸚鵡魚七彩斑爛的顏色,高興得不得了,出了個高價,足交了半季的稅收。那白突人皮膚白滑滑,衣服閃閃亮,說話像個大姑娘,幾個官府的師爺跟在旁邊唯唯諾諾,必恭必敬。聽講遙遠的無何有城主都怕了他們,只是面對面實在看不出什麼厲害之處。哥哥鄭福卻心不在焉:「可能這正是人家的厲害之處呢……」鄭洪視線從魚望向阿哥,卻見平時木訥的阿哥竟在與一個少女眉目傳情……
此時的鄭福拎著漁籮,心裡一陣冷一陣熱,還在疑惑是否見到了熟悉的身影……
走到半路,前方不遠處的巷口,走出來一隊心口有個「勇」字制服的兵丁,提著燈背著行裝,不快不慢地,往泊大船那邊的碼頭走過去。人那麼多不似出來巡邏,閑閑散散的也不似列隊,又不似捉賊,更不似應戰,倒更像……搬家……
在無何有的久遠年代,經常在黑墨墨夜海作業的漁民,都養了雙貓眼。鄭福仔細看了看,有幾個熟口熟面的,心裡震了一震。那幾個就是之前指控西邊村村長郭成田「煮私鹽」,捉去打個半死那幾個。全島都知,那不過是王氏大族的老爺王大勝看上了郭成田的孫女春苗,想納個妾,兩爺孫不乖乖聽命而已……
鄭洪知道阿哥一見那班人便被刺中痛處。雖然阿哥膽子不大,打架也不行,但也怕不小心捅出亂子,便趕緊低聲道:「別管了,先回家,別讓官兵大人看中了石斑,我們就白白驚險一場了。」二人便緊靠著岸邊一整排木麻黃、水黃皮和細葉榕的掩護,盡量安靜地快步走回家。
這麼晚了,屋裡還點著一盞暗油燈。一入屋,阿爸、阿母、鄭洪的老婆小竹、岳父胡七、梁九、白老鬼,還有幾個兄弟都在。大家一見二人,驚呼直出,倒像二人是七七回魂夜的新鬼。
「不過去了兩晚,一向捉石斑都兩晚啦!」鄭洪笑道。
「兩晚整整七日啦!」平時鬼主意最多的小竹哭叫道。
「兄弟你們嚇死你阿母呀,搞到你阿爸發散兄弟去尋!」梁九道。「不聽話去釣鬼頭斑,結果釣到油錐?!」父親鄭虹帶喝問。
兄弟二人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母親石蘭馬上喝令二人把漁獲倒出來,提燈檢驗。一看,哪有什麼石斑、鸚鵡魚?只有一堆一堆糾纏不清的黑髮白髮和幾把女人用的梳子。兄弟二人都呆了,剛才上岸明明還是魚!
「姑姐呢?」鄭福忽然警誡地問。
「有幾個細路發燒,阿玉去照顧了,不過走前有交代怎做!」鄭虹帶便命二人用左腳踩住頭髮和梳子,齊齊面向東方雙手合十向海娘娘廟求庇祐,再齊齊面向南方雙手合十向蛇神木牌祈求庇祐。那邊廂石蘭已點起一個火盆,命二人向神明祈求後,把頭髮和梳子都丟進火盆中,再把雙手放在火的上空,並恭送頭髮和梳子的主人,早日超渡,往福樂之地。
兩兄弟當晚睡在父母屋裡,夫婦二人輪番爬起來提著燈察看,見二人面色沒有死灰,呼吸均勻,才鬆口氣。日出前最黯,前半夜的一鉤月已沉到山後,滿天的星,閃耀著寒光,似千把隱藏的小刀被拔出的一剎。石蘭其實睡不著,走出屋外,面南向著蛇神木牌,點起香爐⋯⋯
1
天上一勾下弦月,等待著什麼上鉤。
鉤月白光啞啞,倒讓星群滿天嘈吵著。盛夏夜海,風微微碎,浪浮浮晃,艇上的二人卻連飆冷汗,搖櫓聲異常急速。耳朵塞滿了些隨身帶備的碎布,卻又思疑自己是否仍聽到那些不知是嗯嗯哼哼?還是尖聲細叫?還是海水謠?還是石頭刮石頭,好似姑姐打紫菜的聲音……
那些白色的什麼在孤島崖邊跳落水,高速向他們游過來的殘影,還在鄭福鄭洪兩兄弟腦裡不斷閃現。二人都極其安靜,一心盡快搖船埋岸,眼睛也不敢往水裡看,彷彿大家都不說話便可當作無事發生。心急如焚,時間自然過得慢,到終於遙望到雙連島上零散的昏黃燈光,撲撲跳的心才開始漸漸踏實下來,以後還是盡量避免晚上停泊在那些無人島,以免又遇上什麼髒東西。
眼看要埋岸,弟弟鄭洪正準備繩子,忽然船哐啷一聲劇烈搖擺了一下,彷佛有條超大魚在船底經過,不經意與船底磨擦了一下似的,二人嚇得心差點沒跳出來,蹲著抓緊船邊。可是,過不一會,又靜下來了……
終於腳踏實地,綁好船隻。
「下次都是聽阿爸話,請個海娘娘放船頭啦,好邪。」弟弟鄭洪道。「阿母話放蛇神。」哥哥鄭福道。
「唉兩個都放啦!」
鄭洪提起漁籮,看著好幾條肥石斑,好幾斤重,還有幾條紅鸚鵡魚、油錐,也不乏一些雜魚。已忘了幾多年前的墟期,有個白突國的人上岸做買賣,一見那紅鸚鵡魚七彩斑爛的顏色,高興得不得了,出了個高價,足交了半季的稅收。那白突人皮膚白滑滑,衣服閃閃亮,說話像個大姑娘,幾個官府的師爺跟在旁邊唯唯諾諾,必恭必敬。聽講遙遠的無何有城主都怕了他們,只是面對面實在看不出什麼厲害之處。哥哥鄭福卻心不在焉:「可能這正是人家的厲害之處呢……」鄭洪視線從魚望向阿哥,卻見平時木訥的阿哥竟在與一個少女眉目傳情……
此時的鄭福拎著漁籮,心裡一陣冷一陣熱,還在疑惑是否見到了熟悉的身影……
走到半路,前方不遠處的巷口,走出來一隊心口有個「勇」字制服的兵丁,提著燈背著行裝,不快不慢地,往泊大船那邊的碼頭走過去。人那麼多不似出來巡邏,閑閑散散的也不似列隊,又不似捉賊,更不似應戰,倒更像……搬家……
在無何有的久遠年代,經常在黑墨墨夜海作業的漁民,都養了雙貓眼。鄭福仔細看了看,有幾個熟口熟面的,心裡震了一震。那幾個就是之前指控西邊村村長郭成田「煮私鹽」,捉去打個半死那幾個。全島都知,那不過是王氏大族的老爺王大勝看上了郭成田的孫女春苗,想納個妾,兩爺孫不乖乖聽命而已……
鄭洪知道阿哥一見那班人便被刺中痛處。雖然阿哥膽子不大,打架也不行,但也怕不小心捅出亂子,便趕緊低聲道:「別管了,先回家,別讓官兵大人看中了石斑,我們就白白驚險一場了。」二人便緊靠著岸邊一整排木麻黃、水黃皮和細葉榕的掩護,盡量安靜地快步走回家。
這麼晚了,屋裡還點著一盞暗油燈。一入屋,阿爸、阿母、鄭洪的老婆小竹、岳父胡七、梁九、白老鬼,還有幾個兄弟都在。大家一見二人,驚呼直出,倒像二人是七七回魂夜的新鬼。
「不過去了兩晚,一向捉石斑都兩晚啦!」鄭洪笑道。
「兩晚整整七日啦!」平時鬼主意最多的小竹哭叫道。
「兄弟你們嚇死你阿母呀,搞到你阿爸發散兄弟去尋!」梁九道。「不聽話去釣鬼頭斑,結果釣到油錐?!」父親鄭虹帶喝問。
兄弟二人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母親石蘭馬上喝令二人把漁獲倒出來,提燈檢驗。一看,哪有什麼石斑、鸚鵡魚?只有一堆一堆糾纏不清的黑髮白髮和幾把女人用的梳子。兄弟二人都呆了,剛才上岸明明還是魚!
「姑姐呢?」鄭福忽然警誡地問。
「有幾個細路發燒,阿玉去照顧了,不過走前有交代怎做!」鄭虹帶便命二人用左腳踩住頭髮和梳子,齊齊面向東方雙手合十向海娘娘廟求庇祐,再齊齊面向南方雙手合十向蛇神木牌祈求庇祐。那邊廂石蘭已點起一個火盆,命二人向神明祈求後,把頭髮和梳子都丟進火盆中,再把雙手放在火的上空,並恭送頭髮和梳子的主人,早日超渡,往福樂之地。
兩兄弟當晚睡在父母屋裡,夫婦二人輪番爬起來提著燈察看,見二人面色沒有死灰,呼吸均勻,才鬆口氣。日出前最黯,前半夜的一鉤月已沉到山後,滿天的星,閃耀著寒光,似千把隱藏的小刀被拔出的一剎。石蘭其實睡不著,走出屋外,面南向著蛇神木牌,點起香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