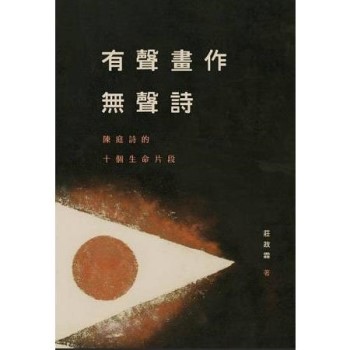第一篇 離家‧流離 來臺以前的陳庭詩
一九七八年的年節,詩人曹介直邀他的老友周夢蝶、以及周夢蝶的摯友陳庭詩兩位到家中,和家人一起吃團圓飯,沾沾年味。一道道擺出的菜餚均由曹介直指定點選、周夢蝶暗中授意,曹夫人邱照蘭女士掌廚,計有:海參、螃蟹、黃魚、腰子、紅棗燉雞……等等。三個大男人就著這些菜餚配酒,但沒有一般人聚會時那種大聲談笑。他們也笑,笑得不比別人小聲,只是他們的交談都寫在一疊便條紙上──「信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便條紙──寫滿一頁就翻到下一頁、下一頁、再下一頁。有限的媒介限制了他們的語言,卻沒有限制住他們的談興和酒興。曹介直喝高粱,陳庭詩飲曹介直特意為他準備的紹興。周夢蝶不擅飲酒,兩人也就不勸他,任他按照自己的節奏喝去,只分配給他「扶醉」的任務。眾人喝完了一瓶再開一瓶,聊到興致高昂處,乾脆把「混酒易醉」的大忌拋到一邊去,酒來了,喝掉便是。
他們聊菜餚。
他們聊曹介直的妻子兒女。
他們聊這年初三在李錫奇家中的畫界聚會。
他們聊性格執拗孤高又富才氣的周棄子。
他們聊《肉蒲團》,說那不過是小學讀物。
他們要不醉不休。
期間,陳庭詩還得抽出心思和曹介直的女兒在紙上應對一番:
「陳伯伯,我是曹家玥,是興隆國小二年三班的學生。」
「我知道。」
小曹家玥畫了一個畫:「這是大畫家陳伯伯。」
「太嫵媚,頭髮太多。」
「陳伯伯,畫一條魚給我看好不好?」
陳庭詩畫下三條魚。
家玥畫了蘭花:「陳伯伯,我會畫蘭花,您會畫嗎?」
陳庭詩也畫一盆蘭花。
家玥畫了一個女娃娃:「陳伯伯,您看我畫的娃娃好嗎?您也畫一個好嗎?」
陳庭詩也畫下一個娃娃,在娃娃旁邊寫上:「很好!」
後來,不知是誰提起「離家」二字,挑動了潛伏在他們三個人心底共有的,卻又不盡相同的心事。
一九四八年七月,時年二十八的周夢蝶離開河南淅川,赴湖北漢口,再轉往武昌黃鶴樓投考國軍二O六師補充團,來臺後被編入工兵營第三連。
同年,曹介直也離開湖北大治的老家,同樣在黃鶴樓投考進青年軍二O六師,來臺後編入工兵營第一連。那一年,曹介直還未滿十八歲。陳庭詩離鄉背井的時間點,足足早了他倆十年。一九三八年,他二十三歲,隨身只帶著輕便的行囊,從位於福建海濱的福州,趕赴兩百多公里之遙的路程,前往位於內陸山區的沙縣就職。而這一步走出,尚留在福州黃巷陳家宅邸內的人們,便從此失去陳庭詩的音訊,長達半世紀之久。沒有人能確切地說出:陳家的長子這一去是為了什麼,而這些年,他又去了哪裡?
確切地說,陳庭詩的初次離家,又再更早一些。一九三O年代,本來受到家學薰染浸淫於中國傳統書畫的陳庭詩,逐漸將他的心思轉往西畫。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新舊文化劇烈碰撞的年代,無論知識份子還是平民老百姓都想、也必須在這團巨大的混沌中摸索著前進,期望能在漫長漆黑的甬道裡,尋出也許存在,又也許並不存在的,閃耀著希望光芒的彼端。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張新舊思想兼容並蓄,並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希望美術教育能夠普及全國。在蔡元培的鼓勵下,曾在海外留學的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等藝術家回國後皆進入學院之中,準備一展身手,為中國藝術的教育、改革與推廣做出貢獻。他們的做法在細節上雖有不同,但其主張大底不脫「引進西洋繪畫,改革中國畫,融合中西,創造屬於中國的新文化藝術」這樣的方向。
在歸國藝術家各色各樣的主張之中,徐悲鴻倡導的做法引起了陳庭詩的注意。徐悲鴻認為,改良中國畫,應當從引進西方的寫實主義做起,以素描作為改良中國畫的造形基礎。受到這一觀念的啟發,陳庭詩開始自學起素描和油畫,對寫實技法有了一定的掌握。稍後,他更前往上海,由旅居在此的叔叔照顧,進入劉海粟於一九一二年創立的上海私立美專就讀國畫科。上海美專可說是中國第一所具規模的現代化美術專業學校,當時如一塊海綿般亟欲吸收各種藝術新知的青年陳庭詩,對此處自然懷有憧憬和嚮往。可惜的是,在他正入學之際,中國對日八年抗戰旋即爆發,八月十三日上海更發生了慘烈的淞滬戰役,別無選擇的陳庭詩,只能中斷學業,返回福建家中。
抗戰第一年,陳庭詩待在家中的日子並不好過。抗戰初期,由於日本主力在長江流域和國軍對峙,抽不出足夠軍力南下福建,戰火並未直接在福建沿海地區大肆延燒。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清末民初數十年間名人輩出的福州三坊七巷,陳庭詩的家族也還足以和當地的其他名門望族平起平坐。他的祖父陳君耀是晚清進士,祖母是沈葆楨第七個女兒,父親陳忠園是清末秀才,並在一九O七年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校前身)就讀,與蔣介石同學,母親許鶴儒則來自杭州的書香名門。有這樣的家世,在太平之日當然是衣食無虞,戰時,要是沒有遭受到無理的欺壓掠奪,陳家的境況也應較平常人家好上許多。
他的不好過,並不是來自於物質上的缺乏。
陳庭詩在五歲那年,遭逢了母親過世的打擊。八歲時,在自家院子裡遊玩的陳庭詩不慎從樹上摔下,起先他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麼異樣,後來漸漸地就聽不到了。自此以後,父親對他日漸冷淡,更在不久之後納了妾,生了幾個孩子,使得家中人口更為繁多。喪母、失聰、失寵,迫使一個原先應該是世家公子的孩子提前熟成,比常人更加敏感纖細。
家且如此,國又如何?雖然他無法聽到隆隆的砲火聲,可是雙眼所見,莫不使他坐立難安。他看著書報上的字字句句,寫著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國家是如何在日本一步步的侵略下逐漸滑進絕望的深淵。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滬之役。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事變同年十月,上海淪陷(就在這稍早之前,陳庭詩便因上海情勢危急,無奈自上海美專返家)。十二月,南京陷落,數十萬人被屠殺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中國。
青年陳庭詩要如何在家中安坐,自外於這場戰爭?耳不能聽、口不能言,除了詩詞書畫篆刻外什麼都不會的他,在一場戰爭中又能發揮什麼作用?
更何況,他所待的這個家,並不是一個全然友善的庇護所。
他用力地想,他能做什麼?
第一個想起的,是他曾在魯迅的《南腔北調集》裡看到的幾段話:
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裡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要注意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嘆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花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花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這實在是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在寫就這幾篇關於木刻、漫畫文章的前後,魯迅同時在一九二九年播下第一顆種子。魯迅以藝苑朝華這個名字印行四本畫集,其中有兩本是木刻集,是中國首度引進西方木刻的創舉。為了培養這顆種子,魯迅於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辦了一個木刻講習班,請一位日本版畫家內山嘉吉擔任教授,使愛好木刻的藝術青年有學習刻作的機會。自此以後,「捏刀向木」的藝術青年一天天地增多,成為呼應魯迅所大力提倡以藝術批判現實、形同「戰鬥」的木刻版畫運動的生力軍──運用木刻取材快速且易於複印的特性,以當時的社會現象為題材,抨擊時弊、反映民生。
近一點的,是發生在去年,一九三七年的事。
一九三七年,魯迅去世隔年,在全國一致的抗日聲浪中,上海漫畫界成立了「漫畫救亡協會」,並創辦刊物《救亡漫畫》。漫畫宣傳隊伍在各地展開抗日漫畫展,魯迅生前大力提倡的具有戰鬥性質的木刻版畫,自此在社會上廣泛地普及開來。
木刻、漫畫是不是藝術?
是。
自幼至今的所學所聞用不用得上?
可以。
從事木刻版畫需要很多錢嗎?
不用。
想不想繼續做藝術創作?
想。
想不想讓別人看見自己的作品?
當然更想。在經過一番思索,並且問完自己所有該問的問題之後,陳庭詩堅定地執起畫筆,完成了自己生平所作的第一幅漫畫,就近投稿至福建省抗敵後援會辦的《抗敵漫畫》旬刊。稿件一經登用,他同時被《抗敵漫畫》聘為編輯,不久升任主編。他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耳氏」,為幾乎和他的人生等長的藝術生涯揭開序幕。
陳庭詩在福州新開展的藝術抗日事業持續不過數月,便被迫宣告中止。一九三八年春,日軍為了配合進攻武漢,決定佔領廈門和廣州,企圖切斷國際間對中國提供支援的補給線。五月,廈門、福州先後失守,福建省政府自福州內遷至永安。與此同時,陳庭詩也離開了福州,到達距永安八十多公里的沙縣另起爐灶,和宋秉恆共同主編起另一份純刊載木刻作品的月刊雜誌,《大眾畫刊》。
《大眾畫刊》是一份隸屬於福建軍管區國民軍訓處的機關刊物,主要由宋秉恆、陳庭詩、荒煙、薩一佛等版畫家編印,推行抗戰木刻運動。陳庭詩在此時冠上了一個新的職稱,「國民軍訓處及政治部中尉科員」,一個因應戰時國軍政工系統對於美術編輯人才的需求而設立的職位。早前,陳庭詩並未參與魯迅發起的木刻版畫運動。在福州,他所發表的漫畫則是用他先前所熟悉的媒材進行創作,木刻版畫的刻作則尚在自學摸索的階段。直到他結識宋秉恆,才在宋的指導下真正地和木刻版畫結緣。
在當時,考慮起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這樣一個隸屬於軍方政工系統的文藝宣傳機關難免份子複雜。一心想要為國家做點事、想要在有良師指導的環境裡儘快精進木刻技藝的陳庭詩,反而因為他耳朵不方便的緣故,得以遠離各種暗中流動的矛盾和詭譎,在木板上專注地刻、挖。一九三一年畢業於上海美專的宋秉恆,算得上是陳庭詩的大學長,有宋這樣一個典範行走在前,進一步加深了陳庭詩對上海美專、對木刻版畫救國的嚮往。
從事抗敵宣傳活動的期間,陳庭詩是學習者、是創作者,同時也是認真的主編。在他所編的刊物中,他不僅採用名家的稿件。即便是名不見經傳的創作者,只要作品夠好,他也照刊不誤。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陳庭詩除上述身份外,更是一個值得信賴、值得一生想念的好朋友。還在福州《抗敵漫畫》工作期間的某日,編務進行到一半,陳庭詩突然察覺周遭的氛圍有些異樣。同事和前來洽公的訪客紛紛交頭接耳,神色凝重。主編張玳蛹的表情交織著憂慮與慌張,看來正為了某事焦急著,不知如何是好。
「發生什麼事了?」陳庭詩以紙筆寫下疑問,遞給張玳蛹。
「去漳州的戰地工作隊被調回來,張人希差點被抓去關!」
前不久,陳庭詩注意到,有位新來的、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輕人,經常來到《抗敵漫畫》的編輯室交稿。一經攀談,才知道這個叫張人希的年經人來自泉州,是主編張玳蛹的舊友,在《福州日報》當記者。張玳蛹知道張人希能畫,便經常向他邀稿。由於年齡相近、性情興趣也投合,彼時青春年少的陳庭詩和張人希很快便成為了莫逆之交。
廈門淪陷後不久,某日,張人希來到《抗敵漫畫》,卻不像往常和陳庭詩縱聲談笑,只安靜地坐在那兒。雖然沒有過於戲劇性的長吁短嘆,但善於察言觀色的陳庭詩看得出,在張人希的表情裡,除了悲嘆外,更多了一份不知所措的抑鬱。
「怎麼回事?」陳庭詩遞了張紙條過去。
「廈門淪陷,整個福建……不,整個中國都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只是在想,區區一個記者,在這種時候能為國家做的事竟然這樣地少……。」
「記者也很重要啊。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你們這些記者的努力奔波,中國會變成個什麼樣子。」
「我知道這份工作有它的作用,但我受不了只是在一旁觀看,總想靠這雙手再多做點什麼。」
「不然,」陳庭詩沉吟了一下:「這陣子省抗敵後援會正在招考戰地工作隊員,聽說是要去漳州做抗敵宣傳,你是否要去考考看?」
「真的嗎?」張人希見之大喜,隨即又擔憂起來:「報考隊員需要哪些資格?怕是我不符合他們需要的條件。」
陳庭詩看了只是一笑:「擔心什麼?《抗敵漫畫》是後援會底下的刊物啊!我不就是後援會的嗎?我來介紹你給負責招考的那些人認識認識,問清楚不就好了?」
那樣具備愛國熱情,甘願辭去報社工作,為國付出的張人希,怎麼會被入罪,以至於差一點被抓去關?「工作隊的組成分子複雜,聽說他們才剛到漳州沒多久,就有人在內部蓄意破壞。」張玳蛹緊接著往下交代:「他們全隊被調回福州,不知何故,張人希竟遭到清算,被冠上『亂黨』的罪名。幸好他在福州這邊認識的人多,有朋友幫了他一把,只是從工作隊除名,不用坐牢。他這幾天住進一間破廟,好像在等同鄉的朋友開車送他回泉州……。」
問清破廟所在,陳庭詩趕忙前去探望。一見到廟宇破敗如斯,身在其中的張人希只能以石板為床,陳庭詩問,為什麼不去住旅社?
「我現在是身無分文哪。」張人希只能苦笑:「《福州日報》記者收入微薄,工作隊又不給薪,只管吃住。還好前兩天遇到同鄉,他剛好明天要開車回泉州,可以順道載我一趟。沒被關進監牢,有地方可以暫住,又有車能送我回鄉,我的境遇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眼見張人希如此落魄,自己又幫不上什麼忙。陳庭詩無語,只有無聲的眼淚代替文字表達他心中的悲傷。
往後數十年,陳庭詩和張人希於分隔的兩岸各自在藝術領域中耕耘,陳庭詩的藝術家身分自不用多提,張人希也成了中國大陸著名的書畫家。待到兩岸關係稍有鬆動,陳庭詩和其他幾位臺灣畫家的作品於北京展出,張人希這才知道好友仍健在,隨即修書信一封,透過層層關係轉交到陳庭詩手上。陳庭詩收到後很快地就回信了:「……你棲身在破廟的情景猶歷歷在目,每當想起,我一生的眼淚都流盡了。這證明我時時在想念你……」
加入教育部巡迴戲劇教育部隊,是陳庭詩在抗戰時期另一個特別的經歷。
在一九四O年春天裡的某日,陳庭詩留意到,幾個公家機關的公佈欄都張貼著一張新的海報,內容是「劇教二隊」來到了沙縣,並準備在此辦一個訓練班,廣招有愛國熱忱的各界人士一同投入劇教隊的工作。早在此前,陳庭詩便見聞過劇教隊的名頭。戰時,教育部一共有兩個演劇隊:「一隊」在西南省份活動,主要活躍於湖南、廣西等地,由魯迅的學生、戲劇家向培良出任隊長;「二隊」的活動範圍則是在東南,隊長為戲劇家谷劍塵。出於好奇,陳庭詩和其他木刻家便利用工作的閒暇跑去湊熱鬧。同為戰時為國家服務的文化人,這麼做,當然也有彼此鼓勵的意味。在沙縣工作的文化人不算太多,看幾次戲、碰幾次面以後,很容易便攀談起來。知道陳庭詩等人是做木刻的,谷劍塵便大力邀約木刻家們加入劇教二隊的行列。於是,在《大眾畫刊》之外,陳庭詩同時也進入劇教二隊工作,負責繪畫與舞臺設計。
一九四一年,早已廢棄的馬尾軍港及船廠成為日軍大舉攻擊的目標,福州首次為日軍所佔領(抗戰期間福州共淪陷兩次,中間有一段平靜時期)。陳庭詩與宋秉恆合編的《大眾畫刊》也在本年發行完最後一期(二十四期)後,宣告停刊。
此時,劇教二隊接到命令,準備開拔移往贛南,歸到當時擔任江西省第四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區司令的蔣經國轄下。由於福建情勢十分緊張,畫刊的編輯工作也結束了,考量各種因素,陳庭詩便決定於一九四二年隨著劇教二隊開拔移往贛南,駐在贛州城邊的東溪寺。在當時,陳庭詩大概也沒有太多別的選項可選。另一方面,「蔣太子」在贛南的作風和政績聲名遠傳,陳庭詩身在和江西接鄰的閩北地區,自然時有所聞。考慮到父親陳忠園和蔣介石的同學關係,對這染有不少傳奇色彩的父親的同學之子,在這亂世中為贛南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自然,陳庭詩也抱有些許的好奇心。
一九三九年,方屆而立之年、自蘇聯歸國不久的蔣經國,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安排下來到贛州,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接下來的六年,蔣經國在此大張旗鼓地推行「建設新贛南」,為他一生的政治事業揭開序幕。
蔣經國召開全行政區的擴大行政會議的那天是在一九四O年十月一日,以此做為建設新贛南的序曲。大會開完不久,蔣經國就在贛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發動了除四害的戰鬥,查禁煙、賭、娼,懲辦貪汙,並槍斃了一批煙犯和貪汙犯。接連而來的大動作像地震一樣,震動了贛南乃至於全江西,甚至鄰近的省份。緊接著,蔣經國又採取了許多新的措施,朝著他在行政會議提出的「五有」目標前進,即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他在此時,真正貫徹了吃苦、冒險、創造的精神,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使得長期為土豪軍閥盤據的贛南出現了嶄新的氣象,在中國內外都獲得了一定的聲望。如此便創造出一種社會評價:贛南是一塊光明地帶,「新贛南」推行的是一種全新且充滿希望的政治模式。加上贛南地勢複雜,對外交通困難,日軍不易攻克,因而形成了在重慶之外的另一大文藝重鎮。看到蔣經國的人們,在他們眼裡,贛南儼然是「小重慶」。另外,對於東南各省想投奔國民黨的各界人士來說,重慶實在太過遙遠,贛南正好在必行之路的中間,無論停留在此或做為中繼站都是個理想的選項。於是,贛南吸引了許多愛國青年、知名學者、書畫名家前來投奔,在此謀職,有些就在蔣經國支持興辦的《正氣日報》、《新贛南月刊》、《中華正氣出版社》(陳庭詩曾任出版社藝術編輯)等文化出版機構工作。以這樣的背景作為前提,原先就在東南省份活動的劇教二隊,也就順理成章地來到贛州,歸在蔣經國的轄下。
跟著劇教二隊來到贛南的陳庭詩,在日軍尚未進犯贛南以前,於此度過了一、兩年相對太平的日子。偶爾福建戰事稍歇,他還有餘裕能回去處理一些公務私事,數度往返於贛州、福州之間。這段時期,因為在劇教二隊工作的關係,陳庭詩和蔣經國時有接觸,也使他親眼見識到蔣經國易於親近的一面。
在陳庭詩和劇教二隊同仁的眼裡,蔣經國、緯國當時樸素得動人。哥哥經常到二隊看排戲,弟弟也來過幾回,但次數不多。多年後蔣緯國給人的印象大抵是健談、幽默,當時卻不是如此,魁梧、英俊,但嚴肅莊重,不怎麼有趣。
某日,陳庭詩在隊上忙碌時,正好碰上蔣經國的來訪。這本來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做為劇教二隊的直屬上司,蔣經國本來就時常到二隊看排戲。奇的是,這天蔣經國像是專程來找隊長曾也魯(原劇教二隊副隊長,谷劍塵離開後接任隊長),一尋到曾也魯便纏著不放,似乎是在拜託他什麼事。曾也魯一臉難色,卻不敢直接回絕。幾經考量後,曾也魯點了點頭,似乎允諾了些什麼,蔣經國這才放過曾也魯,歡天喜地地離去。後來陳庭詩才知道,蔣經國這次來訪,起因是他不知為何突然來了靈感,慫恿少女時期曾是烏拉爾機械廠歌舞團臺柱的蔣方良和他一起學京戲。極有行動力的蔣經國探聽到幾個其時正在贛州的京劇演員,想方設法延聘到家中當他和蔣方良的家庭教師。出乎意料的是,這些京劇名角不是間接婉拒,就是乾脆直指蔣經國不是那塊料,碰了幾根軟釘子硬釘子後,接下來實際開始學戲的只有蔣方良一人。蔣經國也不以為忤,而是轉了一圈想:「京劇不行,我演話劇總可以吧?」便又興沖沖地跑到劇教二隊,纏著曾也魯分派個角色給他演。
忙碌的蔣經國不見得有時間排戲、演出,也曾經在正式演出時把戲演砸。但平常在臺上作報告時一本正經、道貌岸然的蔣經國,一到二隊就變了樣,跟著演員們一塊在毯子上翻、滾、吼叫,什麼鬼臉都做得出來,天真得像個孩子。
正因為這樣,二隊的大家跟蔣經國都很要好。逢年過節,他會和二隊的人約個時間,到隊上吃飯喝酒,胡鬧說笑。陳庭詩還記得,蔣經國初次到隊上過節時,很快地就和隊員們笑鬧在一塊。在這類場合中,陳庭詩早已習慣將自己安放在一旁,靜靜地看著眾人喧鬧。和隊員們吆喝划拳到一半,蔣經國留意到陳庭詩始終待在一旁,似是無法融入,便主動趨前和他攀談:
「怎麼不一塊來划拳喝酒?」見陳庭詩沒有反應,蔣經國以為他沒聽清楚,便提高音量,大聲地又說了一遍。
人群中傳出一個聲音:「蔣專員,他是個聾子,聽不見,怎麼跟您划拳?」
蔣經國愣了一下,念頭一轉,笑說:「這好辦。」他回到陳庭詩面前,比了個寫字的動作,和陳庭詩借了紙筆,寫下:「以後我們一起合作,我喊拳,你喝酒!」
自此,蔣經國果然總是力邀口不能言的陳庭詩跟他通力合作。每當氣氛熱烈到最高點,興致一到,大家都喝得多了、醉了,開始唱歌、唱戲、拉小提琴、變魔術時,蔣經國也會跟著用俄文唱幾段〈三套馬車〉等俄國歌謠,不管成不成調,就是要和大家在一起盡情笑鬧。有時,蔣經國也邀請二隊的成員到他家作客、吃飯。如果那天說好要包餃子,女隊員們就和蔣方良一起在廚房內和麵、擀皮。忙到不可開交時,廚房內外呼來喊去,蔣經國和蔣方良也跟著喊起隊員們的諢名,儼然像個熱鬧的大家庭。飯後,學習京戲已有一段時日的蔣方良興致一來,便會粉墨登場。聽著蔣方良一口俄國腔官話的二隊隊員,只能在席間忍著笑,分不清她唱的究竟是《玉堂春》還是《茶花女》、是蘇三還是從家裡私奔出來的安娜‧卡列妮娜……。
在苦難的時節裡,笑容和喧鬧是如此珍貴,以至於身在其中的他們無不張開全身的毛孔,盡情承接歡樂。一時之間,彷彿只有這裡的歡笑是真實,而外頭連綿不絕的烽火,是假的。好像只要明朝酒醒,就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場漫長的噩夢,夢醒便不復存在。
一九四四年,企圖打通江西、廣東全線的日本軍隊,為了癱瘓贛南的制空、防空能力,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對贛州的空襲行動。當時的人們自然無法得知,無論是蔣經國的建設新贛南,或是延燒大半個中國的漫長戰事,都已接近尾聲。對他們來說,日軍三天兩頭從頭頂上丟下來的無數炸彈,才是眼前最迫切的、生死交關的現實。對此,除了無用的咒罵宣洩外,最令贛州城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日軍要炸的明明是機場,卻老是遺害到街坊、居民,有時連荒無人跡的山頭也炸,炸飛了許多野草樹木,甚至把野墳炸得給掀了起來。
如同其他的贛州城民一般,「跑警報」成了令陳庭詩和二隊隊員們每晚提心吊膽的不固定「節目」。聽不見警報聲的陳庭詩經常在睡夢中被「捅醒」,這一捅,他便知道大事不妙,立刻清醒過來,趕緊跟著在前頭領路的隊員們拔足飛奔。贛州府城是章江和貢江匯流成贛江的地方,章江在城西,貢江在城東。因為東溪寺所在地理位置的緣故,劇教二隊一行人得一路越過章江、貢江的兩座浮橋,才能直上山坡,躲進墳洞或是任何可以提供掩蔽的地方。等到他們確定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安全的,才紛紛走出藏身處,一起在月亮繁星之下,感受贛州城內外冒著濃煙火光的傷痛。
聽不見爆炸聲的陳庭詩和另一位同樣耳朵不方便的隊員,漫畫家陸志庠,則是用身體去感覺大地的震動,然後扳動手指,計算著落彈的數目。一九四四年底,廣東北部的日軍竄犯贛南,贛北日軍也配合進擾贛中,互相策應,企圖夾擊贛州,並揚言要掃蕩三南(龍南、定南、虔南),打通粵贛全線,局勢立刻緊張起來,劇教二隊便在此時自贛州撤退,陳庭詩也跟著撤走。一段時間後,他才聽說了贛州城陷落的始末。
贛南局勢吃緊之時,蔣經國為了安定民心,發表了「誓與贛南共存亡」的講話。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日軍即將兵臨贛州城下,重慶突然來了一架由空軍大隊長衣復恩親自駕駛的「美齡號」專機,奉命來接蔣經國和眷屬到重慶。蔣經國不走,只讓蔣方良和兩個孩子,以及蔣緯國的生母先行離開。
「重慶派飛機來接,蔣專員都不走」的消息立刻傳遍了贛南,人心也更加安定。當有人想逃難時,甚至還會有人說:「蔣專員都不走,你怕什麼呀!」
二月六日,美齡號第二次出現在贛州上空,同樣是由衣復恩大隊長親自駕駛。不同的是,這次衣隊長手上拿著蔣介石的手諭。蔣經國還在猶豫之時,顧祝同、上官雲相、劉多荃等高級將官一同前來促駕。最後是劉多荃的一句話補上臨門一腳:「你不走,我們還要保護你,為你的安全負責,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今天如果不走,明天就走不了了!」
蔣專員到底還是飛走了。
二月七日,贛州城在雨雪朔風中淪陷敵手,蔣經國賠上了他在贛南經營的一切,包括他的名聲。沒有心理準備的贛州人民連夜在風雨中倉皇逃離,沿途盡在咒罵言而無信的蔣經國。
自此,陳庭詩為了逃難,在贛南、贛東之間輾轉流離,無法持續創作,整整一年間沒有任何作品發表。直到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結束這場漫長的戰爭,陳庭詩仍舊沒有安定下來,也沒有回到福州黃巷的家中。對於這段時期,陳庭詩自己絕口不提,也就無人能得知:為何戰爭結束了,他還不回家,而這些日子,他又去了哪裡。
直到他下了一個決心,手持一張到臺灣的船票,開啟他下一階段的人生。
一九七八年的年節,詩人曹介直邀他的老友周夢蝶、以及周夢蝶的摯友陳庭詩兩位到家中,和家人一起吃團圓飯,沾沾年味。一道道擺出的菜餚均由曹介直指定點選、周夢蝶暗中授意,曹夫人邱照蘭女士掌廚,計有:海參、螃蟹、黃魚、腰子、紅棗燉雞……等等。三個大男人就著這些菜餚配酒,但沒有一般人聚會時那種大聲談笑。他們也笑,笑得不比別人小聲,只是他們的交談都寫在一疊便條紙上──「信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便條紙──寫滿一頁就翻到下一頁、下一頁、再下一頁。有限的媒介限制了他們的語言,卻沒有限制住他們的談興和酒興。曹介直喝高粱,陳庭詩飲曹介直特意為他準備的紹興。周夢蝶不擅飲酒,兩人也就不勸他,任他按照自己的節奏喝去,只分配給他「扶醉」的任務。眾人喝完了一瓶再開一瓶,聊到興致高昂處,乾脆把「混酒易醉」的大忌拋到一邊去,酒來了,喝掉便是。
他們聊菜餚。
他們聊曹介直的妻子兒女。
他們聊這年初三在李錫奇家中的畫界聚會。
他們聊性格執拗孤高又富才氣的周棄子。
他們聊《肉蒲團》,說那不過是小學讀物。
他們要不醉不休。
期間,陳庭詩還得抽出心思和曹介直的女兒在紙上應對一番:
「陳伯伯,我是曹家玥,是興隆國小二年三班的學生。」
「我知道。」
小曹家玥畫了一個畫:「這是大畫家陳伯伯。」
「太嫵媚,頭髮太多。」
「陳伯伯,畫一條魚給我看好不好?」
陳庭詩畫下三條魚。
家玥畫了蘭花:「陳伯伯,我會畫蘭花,您會畫嗎?」
陳庭詩也畫一盆蘭花。
家玥畫了一個女娃娃:「陳伯伯,您看我畫的娃娃好嗎?您也畫一個好嗎?」
陳庭詩也畫下一個娃娃,在娃娃旁邊寫上:「很好!」
後來,不知是誰提起「離家」二字,挑動了潛伏在他們三個人心底共有的,卻又不盡相同的心事。
一九四八年七月,時年二十八的周夢蝶離開河南淅川,赴湖北漢口,再轉往武昌黃鶴樓投考國軍二O六師補充團,來臺後被編入工兵營第三連。
同年,曹介直也離開湖北大治的老家,同樣在黃鶴樓投考進青年軍二O六師,來臺後編入工兵營第一連。那一年,曹介直還未滿十八歲。陳庭詩離鄉背井的時間點,足足早了他倆十年。一九三八年,他二十三歲,隨身只帶著輕便的行囊,從位於福建海濱的福州,趕赴兩百多公里之遙的路程,前往位於內陸山區的沙縣就職。而這一步走出,尚留在福州黃巷陳家宅邸內的人們,便從此失去陳庭詩的音訊,長達半世紀之久。沒有人能確切地說出:陳家的長子這一去是為了什麼,而這些年,他又去了哪裡?
確切地說,陳庭詩的初次離家,又再更早一些。一九三O年代,本來受到家學薰染浸淫於中國傳統書畫的陳庭詩,逐漸將他的心思轉往西畫。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新舊文化劇烈碰撞的年代,無論知識份子還是平民老百姓都想、也必須在這團巨大的混沌中摸索著前進,期望能在漫長漆黑的甬道裡,尋出也許存在,又也許並不存在的,閃耀著希望光芒的彼端。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張新舊思想兼容並蓄,並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希望美術教育能夠普及全國。在蔡元培的鼓勵下,曾在海外留學的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等藝術家回國後皆進入學院之中,準備一展身手,為中國藝術的教育、改革與推廣做出貢獻。他們的做法在細節上雖有不同,但其主張大底不脫「引進西洋繪畫,改革中國畫,融合中西,創造屬於中國的新文化藝術」這樣的方向。
在歸國藝術家各色各樣的主張之中,徐悲鴻倡導的做法引起了陳庭詩的注意。徐悲鴻認為,改良中國畫,應當從引進西方的寫實主義做起,以素描作為改良中國畫的造形基礎。受到這一觀念的啟發,陳庭詩開始自學起素描和油畫,對寫實技法有了一定的掌握。稍後,他更前往上海,由旅居在此的叔叔照顧,進入劉海粟於一九一二年創立的上海私立美專就讀國畫科。上海美專可說是中國第一所具規模的現代化美術專業學校,當時如一塊海綿般亟欲吸收各種藝術新知的青年陳庭詩,對此處自然懷有憧憬和嚮往。可惜的是,在他正入學之際,中國對日八年抗戰旋即爆發,八月十三日上海更發生了慘烈的淞滬戰役,別無選擇的陳庭詩,只能中斷學業,返回福建家中。
抗戰第一年,陳庭詩待在家中的日子並不好過。抗戰初期,由於日本主力在長江流域和國軍對峙,抽不出足夠軍力南下福建,戰火並未直接在福建沿海地區大肆延燒。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清末民初數十年間名人輩出的福州三坊七巷,陳庭詩的家族也還足以和當地的其他名門望族平起平坐。他的祖父陳君耀是晚清進士,祖母是沈葆楨第七個女兒,父親陳忠園是清末秀才,並在一九O七年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校前身)就讀,與蔣介石同學,母親許鶴儒則來自杭州的書香名門。有這樣的家世,在太平之日當然是衣食無虞,戰時,要是沒有遭受到無理的欺壓掠奪,陳家的境況也應較平常人家好上許多。
他的不好過,並不是來自於物質上的缺乏。
陳庭詩在五歲那年,遭逢了母親過世的打擊。八歲時,在自家院子裡遊玩的陳庭詩不慎從樹上摔下,起先他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麼異樣,後來漸漸地就聽不到了。自此以後,父親對他日漸冷淡,更在不久之後納了妾,生了幾個孩子,使得家中人口更為繁多。喪母、失聰、失寵,迫使一個原先應該是世家公子的孩子提前熟成,比常人更加敏感纖細。
家且如此,國又如何?雖然他無法聽到隆隆的砲火聲,可是雙眼所見,莫不使他坐立難安。他看著書報上的字字句句,寫著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國家是如何在日本一步步的侵略下逐漸滑進絕望的深淵。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滬之役。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事變同年十月,上海淪陷(就在這稍早之前,陳庭詩便因上海情勢危急,無奈自上海美專返家)。十二月,南京陷落,數十萬人被屠殺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全中國。
青年陳庭詩要如何在家中安坐,自外於這場戰爭?耳不能聽、口不能言,除了詩詞書畫篆刻外什麼都不會的他,在一場戰爭中又能發揮什麼作用?
更何況,他所待的這個家,並不是一個全然友善的庇護所。
他用力地想,他能做什麼?
第一個想起的,是他曾在魯迅的《南腔北調集》裡看到的幾段話:
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裡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要注意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嘆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花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花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這實在是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在寫就這幾篇關於木刻、漫畫文章的前後,魯迅同時在一九二九年播下第一顆種子。魯迅以藝苑朝華這個名字印行四本畫集,其中有兩本是木刻集,是中國首度引進西方木刻的創舉。為了培養這顆種子,魯迅於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辦了一個木刻講習班,請一位日本版畫家內山嘉吉擔任教授,使愛好木刻的藝術青年有學習刻作的機會。自此以後,「捏刀向木」的藝術青年一天天地增多,成為呼應魯迅所大力提倡以藝術批判現實、形同「戰鬥」的木刻版畫運動的生力軍──運用木刻取材快速且易於複印的特性,以當時的社會現象為題材,抨擊時弊、反映民生。
近一點的,是發生在去年,一九三七年的事。
一九三七年,魯迅去世隔年,在全國一致的抗日聲浪中,上海漫畫界成立了「漫畫救亡協會」,並創辦刊物《救亡漫畫》。漫畫宣傳隊伍在各地展開抗日漫畫展,魯迅生前大力提倡的具有戰鬥性質的木刻版畫,自此在社會上廣泛地普及開來。
木刻、漫畫是不是藝術?
是。
自幼至今的所學所聞用不用得上?
可以。
從事木刻版畫需要很多錢嗎?
不用。
想不想繼續做藝術創作?
想。
想不想讓別人看見自己的作品?
當然更想。在經過一番思索,並且問完自己所有該問的問題之後,陳庭詩堅定地執起畫筆,完成了自己生平所作的第一幅漫畫,就近投稿至福建省抗敵後援會辦的《抗敵漫畫》旬刊。稿件一經登用,他同時被《抗敵漫畫》聘為編輯,不久升任主編。他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耳氏」,為幾乎和他的人生等長的藝術生涯揭開序幕。
陳庭詩在福州新開展的藝術抗日事業持續不過數月,便被迫宣告中止。一九三八年春,日軍為了配合進攻武漢,決定佔領廈門和廣州,企圖切斷國際間對中國提供支援的補給線。五月,廈門、福州先後失守,福建省政府自福州內遷至永安。與此同時,陳庭詩也離開了福州,到達距永安八十多公里的沙縣另起爐灶,和宋秉恆共同主編起另一份純刊載木刻作品的月刊雜誌,《大眾畫刊》。
《大眾畫刊》是一份隸屬於福建軍管區國民軍訓處的機關刊物,主要由宋秉恆、陳庭詩、荒煙、薩一佛等版畫家編印,推行抗戰木刻運動。陳庭詩在此時冠上了一個新的職稱,「國民軍訓處及政治部中尉科員」,一個因應戰時國軍政工系統對於美術編輯人才的需求而設立的職位。早前,陳庭詩並未參與魯迅發起的木刻版畫運動。在福州,他所發表的漫畫則是用他先前所熟悉的媒材進行創作,木刻版畫的刻作則尚在自學摸索的階段。直到他結識宋秉恆,才在宋的指導下真正地和木刻版畫結緣。
在當時,考慮起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這樣一個隸屬於軍方政工系統的文藝宣傳機關難免份子複雜。一心想要為國家做點事、想要在有良師指導的環境裡儘快精進木刻技藝的陳庭詩,反而因為他耳朵不方便的緣故,得以遠離各種暗中流動的矛盾和詭譎,在木板上專注地刻、挖。一九三一年畢業於上海美專的宋秉恆,算得上是陳庭詩的大學長,有宋這樣一個典範行走在前,進一步加深了陳庭詩對上海美專、對木刻版畫救國的嚮往。
從事抗敵宣傳活動的期間,陳庭詩是學習者、是創作者,同時也是認真的主編。在他所編的刊物中,他不僅採用名家的稿件。即便是名不見經傳的創作者,只要作品夠好,他也照刊不誤。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陳庭詩除上述身份外,更是一個值得信賴、值得一生想念的好朋友。還在福州《抗敵漫畫》工作期間的某日,編務進行到一半,陳庭詩突然察覺周遭的氛圍有些異樣。同事和前來洽公的訪客紛紛交頭接耳,神色凝重。主編張玳蛹的表情交織著憂慮與慌張,看來正為了某事焦急著,不知如何是好。
「發生什麼事了?」陳庭詩以紙筆寫下疑問,遞給張玳蛹。
「去漳州的戰地工作隊被調回來,張人希差點被抓去關!」
前不久,陳庭詩注意到,有位新來的、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輕人,經常來到《抗敵漫畫》的編輯室交稿。一經攀談,才知道這個叫張人希的年經人來自泉州,是主編張玳蛹的舊友,在《福州日報》當記者。張玳蛹知道張人希能畫,便經常向他邀稿。由於年齡相近、性情興趣也投合,彼時青春年少的陳庭詩和張人希很快便成為了莫逆之交。
廈門淪陷後不久,某日,張人希來到《抗敵漫畫》,卻不像往常和陳庭詩縱聲談笑,只安靜地坐在那兒。雖然沒有過於戲劇性的長吁短嘆,但善於察言觀色的陳庭詩看得出,在張人希的表情裡,除了悲嘆外,更多了一份不知所措的抑鬱。
「怎麼回事?」陳庭詩遞了張紙條過去。
「廈門淪陷,整個福建……不,整個中國都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只是在想,區區一個記者,在這種時候能為國家做的事竟然這樣地少……。」
「記者也很重要啊。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你們這些記者的努力奔波,中國會變成個什麼樣子。」
「我知道這份工作有它的作用,但我受不了只是在一旁觀看,總想靠這雙手再多做點什麼。」
「不然,」陳庭詩沉吟了一下:「這陣子省抗敵後援會正在招考戰地工作隊員,聽說是要去漳州做抗敵宣傳,你是否要去考考看?」
「真的嗎?」張人希見之大喜,隨即又擔憂起來:「報考隊員需要哪些資格?怕是我不符合他們需要的條件。」
陳庭詩看了只是一笑:「擔心什麼?《抗敵漫畫》是後援會底下的刊物啊!我不就是後援會的嗎?我來介紹你給負責招考的那些人認識認識,問清楚不就好了?」
那樣具備愛國熱情,甘願辭去報社工作,為國付出的張人希,怎麼會被入罪,以至於差一點被抓去關?「工作隊的組成分子複雜,聽說他們才剛到漳州沒多久,就有人在內部蓄意破壞。」張玳蛹緊接著往下交代:「他們全隊被調回福州,不知何故,張人希竟遭到清算,被冠上『亂黨』的罪名。幸好他在福州這邊認識的人多,有朋友幫了他一把,只是從工作隊除名,不用坐牢。他這幾天住進一間破廟,好像在等同鄉的朋友開車送他回泉州……。」
問清破廟所在,陳庭詩趕忙前去探望。一見到廟宇破敗如斯,身在其中的張人希只能以石板為床,陳庭詩問,為什麼不去住旅社?
「我現在是身無分文哪。」張人希只能苦笑:「《福州日報》記者收入微薄,工作隊又不給薪,只管吃住。還好前兩天遇到同鄉,他剛好明天要開車回泉州,可以順道載我一趟。沒被關進監牢,有地方可以暫住,又有車能送我回鄉,我的境遇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眼見張人希如此落魄,自己又幫不上什麼忙。陳庭詩無語,只有無聲的眼淚代替文字表達他心中的悲傷。
往後數十年,陳庭詩和張人希於分隔的兩岸各自在藝術領域中耕耘,陳庭詩的藝術家身分自不用多提,張人希也成了中國大陸著名的書畫家。待到兩岸關係稍有鬆動,陳庭詩和其他幾位臺灣畫家的作品於北京展出,張人希這才知道好友仍健在,隨即修書信一封,透過層層關係轉交到陳庭詩手上。陳庭詩收到後很快地就回信了:「……你棲身在破廟的情景猶歷歷在目,每當想起,我一生的眼淚都流盡了。這證明我時時在想念你……」
加入教育部巡迴戲劇教育部隊,是陳庭詩在抗戰時期另一個特別的經歷。
在一九四O年春天裡的某日,陳庭詩留意到,幾個公家機關的公佈欄都張貼著一張新的海報,內容是「劇教二隊」來到了沙縣,並準備在此辦一個訓練班,廣招有愛國熱忱的各界人士一同投入劇教隊的工作。早在此前,陳庭詩便見聞過劇教隊的名頭。戰時,教育部一共有兩個演劇隊:「一隊」在西南省份活動,主要活躍於湖南、廣西等地,由魯迅的學生、戲劇家向培良出任隊長;「二隊」的活動範圍則是在東南,隊長為戲劇家谷劍塵。出於好奇,陳庭詩和其他木刻家便利用工作的閒暇跑去湊熱鬧。同為戰時為國家服務的文化人,這麼做,當然也有彼此鼓勵的意味。在沙縣工作的文化人不算太多,看幾次戲、碰幾次面以後,很容易便攀談起來。知道陳庭詩等人是做木刻的,谷劍塵便大力邀約木刻家們加入劇教二隊的行列。於是,在《大眾畫刊》之外,陳庭詩同時也進入劇教二隊工作,負責繪畫與舞臺設計。
一九四一年,早已廢棄的馬尾軍港及船廠成為日軍大舉攻擊的目標,福州首次為日軍所佔領(抗戰期間福州共淪陷兩次,中間有一段平靜時期)。陳庭詩與宋秉恆合編的《大眾畫刊》也在本年發行完最後一期(二十四期)後,宣告停刊。
此時,劇教二隊接到命令,準備開拔移往贛南,歸到當時擔任江西省第四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區司令的蔣經國轄下。由於福建情勢十分緊張,畫刊的編輯工作也結束了,考量各種因素,陳庭詩便決定於一九四二年隨著劇教二隊開拔移往贛南,駐在贛州城邊的東溪寺。在當時,陳庭詩大概也沒有太多別的選項可選。另一方面,「蔣太子」在贛南的作風和政績聲名遠傳,陳庭詩身在和江西接鄰的閩北地區,自然時有所聞。考慮到父親陳忠園和蔣介石的同學關係,對這染有不少傳奇色彩的父親的同學之子,在這亂世中為贛南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自然,陳庭詩也抱有些許的好奇心。
一九三九年,方屆而立之年、自蘇聯歸國不久的蔣經國,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安排下來到贛州,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接下來的六年,蔣經國在此大張旗鼓地推行「建設新贛南」,為他一生的政治事業揭開序幕。
蔣經國召開全行政區的擴大行政會議的那天是在一九四O年十月一日,以此做為建設新贛南的序曲。大會開完不久,蔣經國就在贛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發動了除四害的戰鬥,查禁煙、賭、娼,懲辦貪汙,並槍斃了一批煙犯和貪汙犯。接連而來的大動作像地震一樣,震動了贛南乃至於全江西,甚至鄰近的省份。緊接著,蔣經國又採取了許多新的措施,朝著他在行政會議提出的「五有」目標前進,即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他在此時,真正貫徹了吃苦、冒險、創造的精神,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使得長期為土豪軍閥盤據的贛南出現了嶄新的氣象,在中國內外都獲得了一定的聲望。如此便創造出一種社會評價:贛南是一塊光明地帶,「新贛南」推行的是一種全新且充滿希望的政治模式。加上贛南地勢複雜,對外交通困難,日軍不易攻克,因而形成了在重慶之外的另一大文藝重鎮。看到蔣經國的人們,在他們眼裡,贛南儼然是「小重慶」。另外,對於東南各省想投奔國民黨的各界人士來說,重慶實在太過遙遠,贛南正好在必行之路的中間,無論停留在此或做為中繼站都是個理想的選項。於是,贛南吸引了許多愛國青年、知名學者、書畫名家前來投奔,在此謀職,有些就在蔣經國支持興辦的《正氣日報》、《新贛南月刊》、《中華正氣出版社》(陳庭詩曾任出版社藝術編輯)等文化出版機構工作。以這樣的背景作為前提,原先就在東南省份活動的劇教二隊,也就順理成章地來到贛州,歸在蔣經國的轄下。
跟著劇教二隊來到贛南的陳庭詩,在日軍尚未進犯贛南以前,於此度過了一、兩年相對太平的日子。偶爾福建戰事稍歇,他還有餘裕能回去處理一些公務私事,數度往返於贛州、福州之間。這段時期,因為在劇教二隊工作的關係,陳庭詩和蔣經國時有接觸,也使他親眼見識到蔣經國易於親近的一面。
在陳庭詩和劇教二隊同仁的眼裡,蔣經國、緯國當時樸素得動人。哥哥經常到二隊看排戲,弟弟也來過幾回,但次數不多。多年後蔣緯國給人的印象大抵是健談、幽默,當時卻不是如此,魁梧、英俊,但嚴肅莊重,不怎麼有趣。
某日,陳庭詩在隊上忙碌時,正好碰上蔣經國的來訪。這本來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做為劇教二隊的直屬上司,蔣經國本來就時常到二隊看排戲。奇的是,這天蔣經國像是專程來找隊長曾也魯(原劇教二隊副隊長,谷劍塵離開後接任隊長),一尋到曾也魯便纏著不放,似乎是在拜託他什麼事。曾也魯一臉難色,卻不敢直接回絕。幾經考量後,曾也魯點了點頭,似乎允諾了些什麼,蔣經國這才放過曾也魯,歡天喜地地離去。後來陳庭詩才知道,蔣經國這次來訪,起因是他不知為何突然來了靈感,慫恿少女時期曾是烏拉爾機械廠歌舞團臺柱的蔣方良和他一起學京戲。極有行動力的蔣經國探聽到幾個其時正在贛州的京劇演員,想方設法延聘到家中當他和蔣方良的家庭教師。出乎意料的是,這些京劇名角不是間接婉拒,就是乾脆直指蔣經國不是那塊料,碰了幾根軟釘子硬釘子後,接下來實際開始學戲的只有蔣方良一人。蔣經國也不以為忤,而是轉了一圈想:「京劇不行,我演話劇總可以吧?」便又興沖沖地跑到劇教二隊,纏著曾也魯分派個角色給他演。
忙碌的蔣經國不見得有時間排戲、演出,也曾經在正式演出時把戲演砸。但平常在臺上作報告時一本正經、道貌岸然的蔣經國,一到二隊就變了樣,跟著演員們一塊在毯子上翻、滾、吼叫,什麼鬼臉都做得出來,天真得像個孩子。
正因為這樣,二隊的大家跟蔣經國都很要好。逢年過節,他會和二隊的人約個時間,到隊上吃飯喝酒,胡鬧說笑。陳庭詩還記得,蔣經國初次到隊上過節時,很快地就和隊員們笑鬧在一塊。在這類場合中,陳庭詩早已習慣將自己安放在一旁,靜靜地看著眾人喧鬧。和隊員們吆喝划拳到一半,蔣經國留意到陳庭詩始終待在一旁,似是無法融入,便主動趨前和他攀談:
「怎麼不一塊來划拳喝酒?」見陳庭詩沒有反應,蔣經國以為他沒聽清楚,便提高音量,大聲地又說了一遍。
人群中傳出一個聲音:「蔣專員,他是個聾子,聽不見,怎麼跟您划拳?」
蔣經國愣了一下,念頭一轉,笑說:「這好辦。」他回到陳庭詩面前,比了個寫字的動作,和陳庭詩借了紙筆,寫下:「以後我們一起合作,我喊拳,你喝酒!」
自此,蔣經國果然總是力邀口不能言的陳庭詩跟他通力合作。每當氣氛熱烈到最高點,興致一到,大家都喝得多了、醉了,開始唱歌、唱戲、拉小提琴、變魔術時,蔣經國也會跟著用俄文唱幾段〈三套馬車〉等俄國歌謠,不管成不成調,就是要和大家在一起盡情笑鬧。有時,蔣經國也邀請二隊的成員到他家作客、吃飯。如果那天說好要包餃子,女隊員們就和蔣方良一起在廚房內和麵、擀皮。忙到不可開交時,廚房內外呼來喊去,蔣經國和蔣方良也跟著喊起隊員們的諢名,儼然像個熱鬧的大家庭。飯後,學習京戲已有一段時日的蔣方良興致一來,便會粉墨登場。聽著蔣方良一口俄國腔官話的二隊隊員,只能在席間忍著笑,分不清她唱的究竟是《玉堂春》還是《茶花女》、是蘇三還是從家裡私奔出來的安娜‧卡列妮娜……。
在苦難的時節裡,笑容和喧鬧是如此珍貴,以至於身在其中的他們無不張開全身的毛孔,盡情承接歡樂。一時之間,彷彿只有這裡的歡笑是真實,而外頭連綿不絕的烽火,是假的。好像只要明朝酒醒,就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場漫長的噩夢,夢醒便不復存在。
一九四四年,企圖打通江西、廣東全線的日本軍隊,為了癱瘓贛南的制空、防空能力,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對贛州的空襲行動。當時的人們自然無法得知,無論是蔣經國的建設新贛南,或是延燒大半個中國的漫長戰事,都已接近尾聲。對他們來說,日軍三天兩頭從頭頂上丟下來的無數炸彈,才是眼前最迫切的、生死交關的現實。對此,除了無用的咒罵宣洩外,最令贛州城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日軍要炸的明明是機場,卻老是遺害到街坊、居民,有時連荒無人跡的山頭也炸,炸飛了許多野草樹木,甚至把野墳炸得給掀了起來。
如同其他的贛州城民一般,「跑警報」成了令陳庭詩和二隊隊員們每晚提心吊膽的不固定「節目」。聽不見警報聲的陳庭詩經常在睡夢中被「捅醒」,這一捅,他便知道大事不妙,立刻清醒過來,趕緊跟著在前頭領路的隊員們拔足飛奔。贛州府城是章江和貢江匯流成贛江的地方,章江在城西,貢江在城東。因為東溪寺所在地理位置的緣故,劇教二隊一行人得一路越過章江、貢江的兩座浮橋,才能直上山坡,躲進墳洞或是任何可以提供掩蔽的地方。等到他們確定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安全的,才紛紛走出藏身處,一起在月亮繁星之下,感受贛州城內外冒著濃煙火光的傷痛。
聽不見爆炸聲的陳庭詩和另一位同樣耳朵不方便的隊員,漫畫家陸志庠,則是用身體去感覺大地的震動,然後扳動手指,計算著落彈的數目。一九四四年底,廣東北部的日軍竄犯贛南,贛北日軍也配合進擾贛中,互相策應,企圖夾擊贛州,並揚言要掃蕩三南(龍南、定南、虔南),打通粵贛全線,局勢立刻緊張起來,劇教二隊便在此時自贛州撤退,陳庭詩也跟著撤走。一段時間後,他才聽說了贛州城陷落的始末。
贛南局勢吃緊之時,蔣經國為了安定民心,發表了「誓與贛南共存亡」的講話。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日軍即將兵臨贛州城下,重慶突然來了一架由空軍大隊長衣復恩親自駕駛的「美齡號」專機,奉命來接蔣經國和眷屬到重慶。蔣經國不走,只讓蔣方良和兩個孩子,以及蔣緯國的生母先行離開。
「重慶派飛機來接,蔣專員都不走」的消息立刻傳遍了贛南,人心也更加安定。當有人想逃難時,甚至還會有人說:「蔣專員都不走,你怕什麼呀!」
二月六日,美齡號第二次出現在贛州上空,同樣是由衣復恩大隊長親自駕駛。不同的是,這次衣隊長手上拿著蔣介石的手諭。蔣經國還在猶豫之時,顧祝同、上官雲相、劉多荃等高級將官一同前來促駕。最後是劉多荃的一句話補上臨門一腳:「你不走,我們還要保護你,為你的安全負責,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今天如果不走,明天就走不了了!」
蔣專員到底還是飛走了。
二月七日,贛州城在雨雪朔風中淪陷敵手,蔣經國賠上了他在贛南經營的一切,包括他的名聲。沒有心理準備的贛州人民連夜在風雨中倉皇逃離,沿途盡在咒罵言而無信的蔣經國。
自此,陳庭詩為了逃難,在贛南、贛東之間輾轉流離,無法持續創作,整整一年間沒有任何作品發表。直到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結束這場漫長的戰爭,陳庭詩仍舊沒有安定下來,也沒有回到福州黃巷的家中。對於這段時期,陳庭詩自己絕口不提,也就無人能得知:為何戰爭結束了,他還不回家,而這些日子,他又去了哪裡。
直到他下了一個決心,手持一張到臺灣的船票,開啟他下一階段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