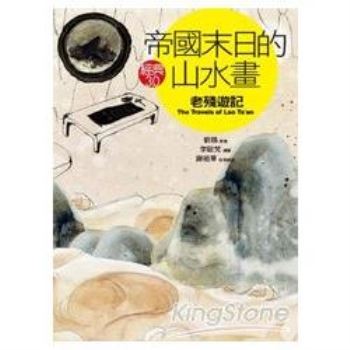歷史可以是實的,也可以是虛的,端看一個文學家怎麼寫。我們熟悉的晚清小說,如《孽海花》和《官場現形記》都是「野史」,是根據當時的現實情況演繹出來的,唯有《老殘遊記》不然,它用一種抒情手法,把當時的現實「美化」,變成一幅歷史的山水畫。如果是在漢唐盛世,這種山水畫可以拿來共享,但到了十八世紀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己經是在追憶似水年華,但大觀園中的那個抒情意境還是完美的。然而到了清末的《老殘遊記》,這個抒情意境本身已經殘缺了,這個殘缺意境的背後,是一個歷史的陰影,小說愈抒情,陰影愈大,但劉鶚並沒有把當時的歷史危機的現實──諸如拳匪之亂、八國聯軍、戊戍變法、孫中山的革命──寫出來,只是從一首詩中略作影射,這並不表示作者會全置身度外,因為我們知道劉鶚本人熟悉鐵路、採礦、鍊鹽之術,也參加過這一類的工作,只不過是他後來生意失敗了,被流放到新疆,鬱鬱而死。正因為在文本中他不寫,這個亂局的陰影反而和抒情的意境之間形成一種緊張,表面上越平和,你越覺得背後的亂性越大。有時我想到同一時期的奧匈帝國和世紀末的維也納文化,可謂頹廢之美達到極點,也更危機四伏,這個比較,恐怕須要進一步探討才行。
最後,我想做一個小小的結論。也回到王德威的意見,他引用了捷克學者(也是我的老師)普宗克(Jaroslav Pråšek)關於「抒情」和「史詩」的兩模式並將之引伸,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到了廿世紀,已經進入一個史詩式的文學時代,也就是革命時代,這個大時代是須要投入的,小說是寫實的,社會性的,似乎是繼「抒情」時代以後的東西,二者互相取代,王德威再三探討論證的是,在這個史詩時代,抒情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還要抒情?我對王德威的看法的感覺是:其實抒情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學藝術傳統,即使山水畫也有它永恒的美學意義,是不容取代的,甚至可以超越歷史和現實,譬如曹植的詩中所達到的最高意境。照另一位名學者高友工的說法,這是一種「美典」。我又覺得,反而在史詩時代,危機四伏時,抒情的作用才更珍貴,它甚至可以變成表現歷史危機的另一種方式,猶如頹廢是現代性的另一面一樣。
最後,我想做一個小小的結論。也回到王德威的意見,他引用了捷克學者(也是我的老師)普宗克(Jaroslav Pråšek)關於「抒情」和「史詩」的兩模式並將之引伸,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到了廿世紀,已經進入一個史詩式的文學時代,也就是革命時代,這個大時代是須要投入的,小說是寫實的,社會性的,似乎是繼「抒情」時代以後的東西,二者互相取代,王德威再三探討論證的是,在這個史詩時代,抒情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還要抒情?我對王德威的看法的感覺是:其實抒情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學藝術傳統,即使山水畫也有它永恒的美學意義,是不容取代的,甚至可以超越歷史和現實,譬如曹植的詩中所達到的最高意境。照另一位名學者高友工的說法,這是一種「美典」。我又覺得,反而在史詩時代,危機四伏時,抒情的作用才更珍貴,它甚至可以變成表現歷史危機的另一種方式,猶如頹廢是現代性的另一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