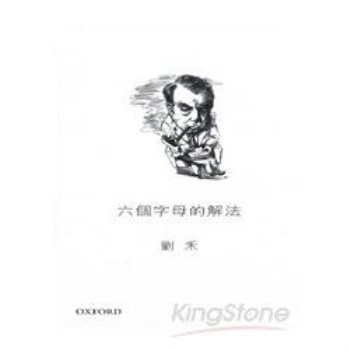六個字母的解法
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的小說《洛麗塔》大約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納博科夫一生搬過無數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戰期間,他從歐洲遠渡美國,幾年輾轉,最後在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定居下來——這也是胡適早年留學的地方。納博科夫在那裏教了十幾年書,他從不買房,只租房。大學有上千名教授,總有人休長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納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這種做法,在精於盤算的美國人眼裏,自然是極不明智的。後來,小說《洛麗塔》一砲打響,成為暢銷書,版稅收入源源不斷,納博科夫從此衣食無憂,但他依舊不買房,依舊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歐洲,索性和妻子住進一家瑞士小城的賓館,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離開人世。
一個作家一輩子租別人的房子住,實在少見,尤其放在歐美作家的行列裏,就更顯突出。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納博科夫為什麼這樣做?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過什麼創傷,造成了不為人所知的心理障礙?
工作之餘,我開始零星地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各種資料,想從他的人生蹤跡中找出某種心理邏輯,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古怪的行為後面都隱藏著一個真實的理由。但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資料彙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變得撲簌迷離,枝杈叢生,而且愈偏離主題,到後來,竟然放棄了原先的想法,沿.另一條路越走越遠。
仔細回想,最初使我偏離主題的導因,可能還是一封不期而至的電子郵件。
1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電郵,一封來自瑞士的巴塞爾大學的普通會議邀請信。這些年來,我對於參加這一類的學術會,變得興趣日淡,經常找些藉口,推辭了事。可是這一回我實在難於推辭,會議地點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Interlaken)──它是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歐洲的滑雪勝地。從這裏乘小火車,坐纜車,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歐洲巔峰爭盛譽的少女峰,上面有長達二十三公里的阿萊齊冰川,據說它是阿爾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從紐約飛到歐洲共要六個多小時,抵達日內瓦國際機場後,再乘兩個半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瑞士小城英特拉肯。臨行之前,我順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塞進旅行袋,預備在路上打發時間。這是納博科夫的小說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譯名是《塞‧納特的真實生活》───我自己則願意把它譯成《塞‧納特的人生真相》。書名平淡無奇,但它屬於讓我著迷的那一類作品,是納博科夫用英文撰寫的第一部小說。在我看來,比後來在商業上聲明大噪的《洛麗塔》,這部《塞‧納特的人生真相》讀起來更加耐人尋味,技巧上也許更勝一籌。不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這本書,這裏面是不是有更隱秘的因素,在當時,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運有時很詭異。有的人足不出戶,就無所不通,實際上一輩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裏。比如哲學家康德,他從未離開過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學裏長期講授人類學,這在後來的人類學家看來,即使不算犯規犯忌,也不大靠譜──不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那算什麼人類學?好在康德講授人類學和撰寫人類學著作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記,也很少有人追究。
與足不出戶的哲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另一類人,他們浪跡天下,一生漂泊,始終找不到歸宿,最後說不定客死他鄉。他們都是一些失去家園的流亡者。
生於孰地,來自何方?這樣的人在二十世紀頗多,以後會越來越多。
其實,這種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圍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我不是指禿常意義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見者,而是一些靈魂深處不安份的人,他們不切實際、耽於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則,這種人為什麼總是與文學會思想多少有些緣份?納博科夫的《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就寫了這樣的一個流亡者,不過,這本書的不尋常之處在於,主人公塞‧納特的下場預示了作者自己後來的命運,因為小說發表四十年後,納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鄉,選擇的地方就是我提到的瑞士賓館。
火車上的廣播說,英特拉肯站馬上就到了,我趕忙向窗外望去,殘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車窗的視野。第一眼看上去,這個小城就像歐洲的任何一處旅遊勝地一樣,美麗而不真實。我把眼鏡摘下來,呵了口氣,仔細擦拭鏡片,再抬頭看時,重重疊疊的阿爾卑斯山脈已經赫然矗在眼前,幾座高峰在霧中小城的背後平地拔起,高聳入雲,巍巍峨峨。我車停靠英特拉肯東站的時候,天色變得陰沉起來,旋即飄起了雪花,雪花裏參和著一些細小的冰粒,大約就是古人所說的雪霰。我因出發時沒有帶傘,下車後,凌空飛舞的冰粒砸在臉上,有點隱隱作痛,幸好打聽到,賓館的位置離車站不遠。
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兩旁的店舖緊閉大門,這光景似乎不像一個度假勝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兩三家餐館,似乎還在營業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館外賣店,生意蕭條,毫無人氣。不論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會碰到這種千篇一律的、裝潢俗氣的廉價中餐外賣店,我在早先還有些奇怪,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幾乎叫人睜不開眼,抬頭一看,雲層又加厚了,偶爾露出狹窄的縫隙,讓人瞥見藏在後面黑壓壓的山峰。幾乎在一秒鐘的瞬間裏,山峰像魔術般地閃現出來,即刻又融化在雲霧背後,教人看不清這雲霧後面的真實情形。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悵惘的情緒,說不清是為了什麼,這時,一個遙遠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誰在那邊踏雪,終生不曾歸來?
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的小說《洛麗塔》大約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納博科夫一生搬過無數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戰期間,他從歐洲遠渡美國,幾年輾轉,最後在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定居下來——這也是胡適早年留學的地方。納博科夫在那裏教了十幾年書,他從不買房,只租房。大學有上千名教授,總有人休長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納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這種做法,在精於盤算的美國人眼裏,自然是極不明智的。後來,小說《洛麗塔》一砲打響,成為暢銷書,版稅收入源源不斷,納博科夫從此衣食無憂,但他依舊不買房,依舊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歐洲,索性和妻子住進一家瑞士小城的賓館,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離開人世。
一個作家一輩子租別人的房子住,實在少見,尤其放在歐美作家的行列裏,就更顯突出。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納博科夫為什麼這樣做?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過什麼創傷,造成了不為人所知的心理障礙?
工作之餘,我開始零星地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各種資料,想從他的人生蹤跡中找出某種心理邏輯,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古怪的行為後面都隱藏著一個真實的理由。但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資料彙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變得撲簌迷離,枝杈叢生,而且愈偏離主題,到後來,竟然放棄了原先的想法,沿.另一條路越走越遠。
仔細回想,最初使我偏離主題的導因,可能還是一封不期而至的電子郵件。
1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電郵,一封來自瑞士的巴塞爾大學的普通會議邀請信。這些年來,我對於參加這一類的學術會,變得興趣日淡,經常找些藉口,推辭了事。可是這一回我實在難於推辭,會議地點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Interlaken)──它是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歐洲的滑雪勝地。從這裏乘小火車,坐纜車,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歐洲巔峰爭盛譽的少女峰,上面有長達二十三公里的阿萊齊冰川,據說它是阿爾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從紐約飛到歐洲共要六個多小時,抵達日內瓦國際機場後,再乘兩個半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瑞士小城英特拉肯。臨行之前,我順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塞進旅行袋,預備在路上打發時間。這是納博科夫的小說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譯名是《塞‧納特的真實生活》───我自己則願意把它譯成《塞‧納特的人生真相》。書名平淡無奇,但它屬於讓我著迷的那一類作品,是納博科夫用英文撰寫的第一部小說。在我看來,比後來在商業上聲明大噪的《洛麗塔》,這部《塞‧納特的人生真相》讀起來更加耐人尋味,技巧上也許更勝一籌。不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這本書,這裏面是不是有更隱秘的因素,在當時,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運有時很詭異。有的人足不出戶,就無所不通,實際上一輩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裏。比如哲學家康德,他從未離開過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學裏長期講授人類學,這在後來的人類學家看來,即使不算犯規犯忌,也不大靠譜──不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那算什麼人類學?好在康德講授人類學和撰寫人類學著作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記,也很少有人追究。
與足不出戶的哲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另一類人,他們浪跡天下,一生漂泊,始終找不到歸宿,最後說不定客死他鄉。他們都是一些失去家園的流亡者。
生於孰地,來自何方?這樣的人在二十世紀頗多,以後會越來越多。
其實,這種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圍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我不是指禿常意義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見者,而是一些靈魂深處不安份的人,他們不切實際、耽於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則,這種人為什麼總是與文學會思想多少有些緣份?納博科夫的《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就寫了這樣的一個流亡者,不過,這本書的不尋常之處在於,主人公塞‧納特的下場預示了作者自己後來的命運,因為小說發表四十年後,納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鄉,選擇的地方就是我提到的瑞士賓館。
火車上的廣播說,英特拉肯站馬上就到了,我趕忙向窗外望去,殘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車窗的視野。第一眼看上去,這個小城就像歐洲的任何一處旅遊勝地一樣,美麗而不真實。我把眼鏡摘下來,呵了口氣,仔細擦拭鏡片,再抬頭看時,重重疊疊的阿爾卑斯山脈已經赫然矗在眼前,幾座高峰在霧中小城的背後平地拔起,高聳入雲,巍巍峨峨。我車停靠英特拉肯東站的時候,天色變得陰沉起來,旋即飄起了雪花,雪花裏參和著一些細小的冰粒,大約就是古人所說的雪霰。我因出發時沒有帶傘,下車後,凌空飛舞的冰粒砸在臉上,有點隱隱作痛,幸好打聽到,賓館的位置離車站不遠。
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兩旁的店舖緊閉大門,這光景似乎不像一個度假勝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兩三家餐館,似乎還在營業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館外賣店,生意蕭條,毫無人氣。不論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會碰到這種千篇一律的、裝潢俗氣的廉價中餐外賣店,我在早先還有些奇怪,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幾乎叫人睜不開眼,抬頭一看,雲層又加厚了,偶爾露出狹窄的縫隙,讓人瞥見藏在後面黑壓壓的山峰。幾乎在一秒鐘的瞬間裏,山峰像魔術般地閃現出來,即刻又融化在雲霧背後,教人看不清這雲霧後面的真實情形。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悵惘的情緒,說不清是為了什麼,這時,一個遙遠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誰在那邊踏雪,終生不曾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