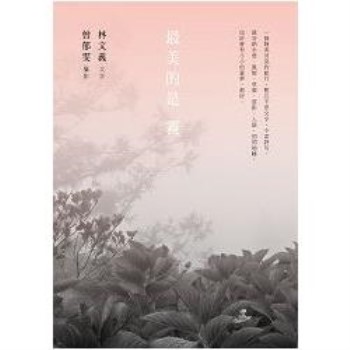(選自卷一「擬態山水」)
最美的,是霧
花崗岩堆疊的聚落,初夏竟如秋……
餐鋪落地窗外一叢百合花,在這北方島群竟然綻放出頑強的意志,那靜謐的瘦長枝莖遂有青竹的錯覺,異常美麗之凜冽。無語的呼喚,喇叭形態昂揚著高音的挺拔,花呼喚著這條鋪著型式不一的岩片小徑,巷道轉角處,就是潮汐接岸的,海。
我必須坐困在這霧鎖雨濕的島嶼邊緣,喝著老酒,些微躁慮地等著船期渡海到南方的另一島鄉;這裡的老朋友們倒是氣定神閒的邀酒勸食:安心,他們在那兒不缺陳高和海鮮,您就隔海對酌吧。五月霧季,船不開,臺灣飛機不來本是尋常啊!老朋友唇留小鬍,像極了:魯迅。
去年(二○一三)九月初,詩酒節在離此七十公里外,稱之「國之北疆」的東引島;我和一群詩人老友,就從入夜微雨的基隆港西岸碼頭登上臺馬輪,夜航北上。太平洋全然在無邊無涯的黑暗中,五千噸的交通船低吼著沉定的輪機聲響,猶若百人大樂團不歇地賣力演奏,何以成眠?向來就是夜醒者之我,索性半坐半臥於下甲板的舷畔,看著船體下端的浪潮……堅硬的鋼鐵切割過柔軟卻強韌的海流,黑暗中軋軋然裂帛般的白浪……
單調、純粹的渡海夜航。
濛濛亮的黎明,彤色漸褪夜暗……小小的島我時而思念,浮海隱約地挪近了。
詩酒節之夜,意外地有幸和秀異詩人李進文交換吟詠對方的詩作,詩題:東引。貼心的他明白此地於我是長年的親炙與些許情怯,就在入晚歌者胡德夫幽雅的鍵琴伴奏下,我唸起李進文之詩──
如果島上八月就落葉
該不會秋天對什麼誤解
小油菊花漫山遍野
像愛,綻放最前線
東湧陳高搖晃今夜
黑尾燕鷗叫著沒醉沒醉
野薔薇是孤高的仙
站在國之北疆舉杯
遠的是東引,近的是東莒。我所殷切等待的是船渡東莒,相知疼惜,久未相見的作家老友二人亦是隔海召喚我之前去。很多年未詩之人反而寫了一本:《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彷彿一段時間的放逐自我,身心安頓;去年方從日本福岡西南學院大學退休的前輩作家,就在初秋季節的異國歡聚時,言之能否翌年相約:馬祖同旅?果真應諾,卻是一水之隔,浪激霧困,暫難與會。念及他的名著:《船過水無痕》此時潮湧無船,徒然矣!
島那方來簡訊:他們夜見有「藍眼淚」美稱的星砂海景,猶如極地光流……我所困身的南竿只見霧氣一朵一朵飄過民宿前方磊峻的山壁稜線,灰濛濛的銀亮,像一首詩完成前突兀的折斷思緒……。留著魯迅般鬍子的老友笑說與詩人前輩向明先生酒聚,曾在一九六六年駐防此間的詩人形容:
最美的,是霧。
最美的,是霧……詩人向明如是說。雨和霧的夜晚,留學習畫於西班牙的夫婦遂開著休旅車帶我們環繞整個南竿島,那般決絕的斷言:一定可以看見「藍眼淚」星砂夜海……沒有看見,倒是抵達了靜美的津沙古厝聚落,畫家幽然地提及這是他的誕生地。
畫家夫人也是畫家。牛角村民宿的夜讀爾雅版的詩畫集:《向島嶼靠近》。窗外微雨卻不沾衣,推門外出到可眺遠海的大露臺,夜霧綿纏的絲帛觸感;一種清新的、潔淨的輕寒,女詩人著筆的是這羅列的島鄉,女畫家顏彩深邃著潮汐與貝殼的情愫……多少美麗的組合。
明日是第三天了,如果依然船不開航,飛機不從臺灣來,是否我們依然要隔海一水,相互等待?霧鎖島群,如何向島靠近?十里之隔竟比天涯海角還要遙遠……最美的,是霧。我又想起向明先生的句子,只是形容,不是完成的詩行,卻比詩更像詩。那麼請容我踰越的試筆延伸──
困我於島不是大海
一枚乾涸貝殼
眠間傾聽的耳朵
那是隔水思念
耽美的從前早遺忘
最美的現在還是霧……
(選自卷二「隱匿應答」)
最初的陳列
越過花蓮木瓜溪,地上歲月又老去幾分?隔離千山萬水的中央山脈,嘉南平原的原鄉和此時花東縱谷的家園,前是記憶今是安頓;祈願靜謐的,沉定的,文字如種植般堅貞。
臺北外雙溪一九八一
作家妻子是音樂家,主修提琴和作曲。
三十年前的臺北士林福林路還是近郊,眷村群落在幾條狹隘、迂迴的窄巷兩邊,據說是總統官邸侍衛隊的宿舍所在;內外雙溪的小河從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那端清淺地流了過來,走過橫跨河上水泥橋就是雨農路。
雨農。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路名,想像:勤耕的農夫穿著沉甸的蓑衣,在濕濡的雨中弓身插秧或施肥,為生民培育糧食的勞苦,美麗而勇健的大地之子……彼時,少人知悉「雨農」二字根本不是向農夫致敬,而是紀念一位在四○年代中國抗日戰爭時,善於剷除異己、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首腦:戴笠,另號:雨農。
年輕時蒙難的作家住在附近,不知道心裡是否五味雜陳?初訪他的家居前通了電話,福林路幾號?說了地址後,特別聲明門口掛著畫上小提琴標記的牌子──妻子在家教音樂。抵達時,這才發現此地並不陌生,高中年代曾在對面的私立學校混過,那時何等叛逆,故意與極力反對我習畫的父親過不去,插班考試明明能夠唸公立高中,卻拿著成績單到私中報到;很感性的,因為依山傍水的校園開滿杜鵑花。
時報文學散文首獎,原題〈獄中書〉被要求改名為〈無怨〉……作家淡然地說,微笑著燃起菸來。我們閒散漫遊在夜市沸騰的鍋氣與食味、店家吆喝和食客喧語之間,常常就是這般地相約閒散漫遊市井,少談文學,彷彿心有靈犀的直覺:文字是生活的必然而非偶然,書寫和閱讀吧,抵達靈魂最深邃的某個角落,猶若作家曾經引用過卡夫卡的名言──
是一隻從黑暗中伸出,向美探索的手。
有一次的夜酒,倒是談到他在散文之前的譯書:《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原著者是匈牙利猶太裔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小說彷彿自傳,敘述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歐洲從事祕密活動,被逮捕受審判的經歷……曾經蒙難過的作家翻譯比他早生四十年一樣蒙難過的作家,譯筆的過程中是否多少因感身受而沉鬱、悲涼?敬他一杯酒,其實是不捨的怕引起他昔憶重返的憂傷;只是純粹的一本書,譯者和作者竟宿命等同。
我還清晰記得初訪時,小提琴標記的指路,想是妻子的琴弦,安頓了作家的美麗與哀愁。
花蓮一九九四
彼此約定,午後四時的花蓮機場。他從臺中過來,我從臺北過去,我臆測的航程是從蘭陽平原出海,沿著海岸線飛行,他則要穿越大甲溪直至源頭接立霧溪東飛,皆是三千米的峰頂。
他說:我沒去過花蓮。
沒去過花蓮,卻一直關心那位不曾見過面的散文作家。能夠寫出雄渾氣勢,運筆如大河山巒的秀異作家,卻去參選省議員了?這個九○年代的臺灣是怎麼回事?作家逐漸棄筆?
塞車的臺北市區,計程車插滿了市長候選人的小旗幟,司機老大連珠炮一樣的抨擊執政黨,我則由於時間緊迫,腹間隱隱作痛,索性閉上雙眼,左手抓著的皮包滾到座椅下端。
塞到民權東路、敦化北路口綠燈一下子換成紅燈,耐不住性子,我說要下車,司機老大說:我幫你趕吧!用力踩油門。兩側湧上的車子緊急煞車。喇叭聲大作,交通警察的臉很長。
喘過長長的氣,航機已穿過雨雲,在無涯的棉絮上水平飛行。我也很久不曾去花蓮了,想到花蓮總是多少會怦然心動,好像一種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負荷、絞痛之時,就會想去花蓮……。
把這種想法告訴住在花蓮的作家,他回信說:花蓮治療了你們的負荷、絞痛,那麼誰來治療創痕累累的花蓮?
作家帶領群眾去包圍紙漿廠,抗議水泥廠,被指為「有心分子」。我在報紙的地方版上見到作家,心中總是一種溫熱卻又摻雜著辛酸。
機窗外是蘇花公路,迂迴如細髮般的銀線,顯然逐漸降低高度,後座兩個日本人指著壯麗的清水斷崖,不禁輕呼的讚美:真是綺麗啊!航機猛然急墜,所有的乘客有所騷動,機長把航機拉平,忙說:剛通過一段不穩定氣流……五分鐘後在花蓮北埔機場落地。
在花蓮長住的作家,今晚的募款餐會,要替花蓮爭取、說話。忽然想到他所寫的兩本散文:《地上歲月》、《永遠的山》那份令人感心的暖熱。如果作家只是一直守住書房,也許這就不再是作家特有的質性了,夢終究不能只是文字。
太平洋灰茫蒼鬱的海水拍擊著花蓮海岸,航機在海灣上繚繞了個大圈,然後筆直地降落長長的跑道,穿過兩旁停駐的虎鯊型戰機以及微霧。
臺中來的朋友已經在機場外抽菸、等我。
(選自卷四「子夜貓頭鷹」)
今生
曾經書寫過的文字,其實早就遺忘。
最初是如何立意書寫,應該啟蒙於閱讀。
湮遠的七○年代,表面噤聲、沉寂,內裡花開絢爛的副刊、雜誌、書籍,哲學、藝術、文學……悄然、靜謐地,水似抒情地開始潛移默化的浸潤少年孤獨之心,比起凝滯、死板的國家主義唯尚的學校教育,為我推開一扇窗,窗外竟是無垠的大山大海,充滿無限的想像。
少年愚痴、天真的開始試圖習繪、作文,是對毫無創意的教育體制一種無由的主觀抗拒亦或是私己家庭的壓力所引致的故意叛逆?許是自我倦於勤讀,服膺於現實裡必然遵循的學校養成體制,卻替代以深愛的文學和藝術做為此後的人生,榮辱相與的過往終是值得感謝。
近時有人慎重問及可曾悔憾?我答以:不會後悔,只是多少有著遺憾。遺憾的是現實人生,不悔的是眷戀至今的文學一生;這也可能是自我認定是僅有做好的一件事,現實諸般一片荒蕪。言之「文學一生」自有些微感慨,終究六十初度已是事實,不必神傷亦不須自棄,歲月曾經美麗、肉身曾經青春已然足夠。
●
是誰,將我遺忘的最初招魂般喚回?蓄意忘卻的以及實質遺忘的,竟被重新復刻、檢視、出土……猶若千年前樓蘭古國的乾屍或者是非洲第一高峰頂上那隻被冰河凝凍的花豹。此時遺體被送上解剖檯,他們切開我的肌理,小心翼翼地分離胸前橫隔膜,搜尋到還在怦然跳動的心臟,他們可知道這心的某部分早已壞死。
值得探究我的內心嗎?我早以文字留下。不曾隱瞞,少於虛構(除了小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沒有灰色地帶;四十年就定義在「我手寫我心」,不須揣臆、勞神。每一個文字,每一則段落皆是我主觀的人生說法,或有偏執,或有朦昧,都是個人由衷的一廂情願。
偏執或朦昧的一廂情願。他者怎麼看,如何評比就由之自去,作者書寫、發表、合集出版之後,作品自然告別作者,陌路不再回首。文字的敗筆、失分都是種種過程,過程比完成還要美麗,其間的思索也許艱辛,就讓識者知心的各自體會,同感或異見皆是生命的圓滿。
他們奮力剖析我文字的內在,用以寫就豐實的碩士論文(注),如若願意的話,學位領受之外,我多麼祈望他們能真正讀懂我的內心,我面對殘酷、冰冷的現實,凜冽地應答。
●
無可救藥的浪漫嗎?確然如此。
偏執的相信理想與真情,多少自困自苦。
沒有浪漫與理想,試問:文學意義何在?
當然因之抵觸現實。那是一種人類社會與歷史長久以降形塑的固有定律,說是叢林法則、適者生存自是先哲群儒飽經苦難所深切領悟的智慧;如若明知現實中文學與藝術可能僅是稀微的心靈慰安,不必然成為生命的美感知覺生活的大部分,其實可以理解。抉擇是一座天秤,現實和理想如何找到平衡正是人類苦思、尋索的與生大病,後者永遠是一枚寒夜孤星。
愚痴、天真之我,似乎永遠不馴於現實,早就洞悉理想如此稀微、薄弱,依然眷愛不渝地試圖以文學書寫及閱讀保存一絲絲的理想信仰。於是有時我自問自答,編織文字情境並且從中獲得純淨的生命救贖。他們奮力剖析我文字的內在,年少初期十年的濫情,再十年的著力土地人民,又十年的回歸寧謐,而近十年他們洞悉了現在之我又是怎般地人生晚晴……
樓蘭古國的乾屍千年前想是青春美麗。
冰河封存的花豹怎會登臨五千米頂峰?
人與獸究竟要證明什麼?理想還是現實?
而我,卻一再以文學印證某種不馴對抗。
●
賽萬提斯不朽小說筆下的「夢幻騎士」,以為那轉動的風車是歌利亞巨人,如是嗎?
散文是心影錄,小說乃虛構演劇,詩是音樂和舞姿……我是讀者也是作者,閱讀他人書寫自己,前者冷靜後者狂熱,傾聽與爭辯、民主和獨裁,論文假以手術刀與明鏡,解剖之後真正發現什麼,豐饒或是空蕪還是心理學上的「人格分裂」?如果生在數百年之前,自己曾是遁山種植的農夫亦或是征戰逐野的霸主?
前世茫茫,今生逐然沉定。自嘲千年昔時也許就是佛座足下蓮花池裡一尾偷偷聽經的金魚,田田圓葉,花開如燭焰,這尾金魚莫非凡思想蛻化為人,佛陀令之以文字刑懲之今生。
猶若靜水一方,如同天光雲影,如此清晰、明澈,今生逐時留在文字中,你定能通透。
最美的,是霧
花崗岩堆疊的聚落,初夏竟如秋……
餐鋪落地窗外一叢百合花,在這北方島群竟然綻放出頑強的意志,那靜謐的瘦長枝莖遂有青竹的錯覺,異常美麗之凜冽。無語的呼喚,喇叭形態昂揚著高音的挺拔,花呼喚著這條鋪著型式不一的岩片小徑,巷道轉角處,就是潮汐接岸的,海。
我必須坐困在這霧鎖雨濕的島嶼邊緣,喝著老酒,些微躁慮地等著船期渡海到南方的另一島鄉;這裡的老朋友們倒是氣定神閒的邀酒勸食:安心,他們在那兒不缺陳高和海鮮,您就隔海對酌吧。五月霧季,船不開,臺灣飛機不來本是尋常啊!老朋友唇留小鬍,像極了:魯迅。
去年(二○一三)九月初,詩酒節在離此七十公里外,稱之「國之北疆」的東引島;我和一群詩人老友,就從入夜微雨的基隆港西岸碼頭登上臺馬輪,夜航北上。太平洋全然在無邊無涯的黑暗中,五千噸的交通船低吼著沉定的輪機聲響,猶若百人大樂團不歇地賣力演奏,何以成眠?向來就是夜醒者之我,索性半坐半臥於下甲板的舷畔,看著船體下端的浪潮……堅硬的鋼鐵切割過柔軟卻強韌的海流,黑暗中軋軋然裂帛般的白浪……
單調、純粹的渡海夜航。
濛濛亮的黎明,彤色漸褪夜暗……小小的島我時而思念,浮海隱約地挪近了。
詩酒節之夜,意外地有幸和秀異詩人李進文交換吟詠對方的詩作,詩題:東引。貼心的他明白此地於我是長年的親炙與些許情怯,就在入晚歌者胡德夫幽雅的鍵琴伴奏下,我唸起李進文之詩──
如果島上八月就落葉
該不會秋天對什麼誤解
小油菊花漫山遍野
像愛,綻放最前線
東湧陳高搖晃今夜
黑尾燕鷗叫著沒醉沒醉
野薔薇是孤高的仙
站在國之北疆舉杯
遠的是東引,近的是東莒。我所殷切等待的是船渡東莒,相知疼惜,久未相見的作家老友二人亦是隔海召喚我之前去。很多年未詩之人反而寫了一本:《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彷彿一段時間的放逐自我,身心安頓;去年方從日本福岡西南學院大學退休的前輩作家,就在初秋季節的異國歡聚時,言之能否翌年相約:馬祖同旅?果真應諾,卻是一水之隔,浪激霧困,暫難與會。念及他的名著:《船過水無痕》此時潮湧無船,徒然矣!
島那方來簡訊:他們夜見有「藍眼淚」美稱的星砂海景,猶如極地光流……我所困身的南竿只見霧氣一朵一朵飄過民宿前方磊峻的山壁稜線,灰濛濛的銀亮,像一首詩完成前突兀的折斷思緒……。留著魯迅般鬍子的老友笑說與詩人前輩向明先生酒聚,曾在一九六六年駐防此間的詩人形容:
最美的,是霧。
最美的,是霧……詩人向明如是說。雨和霧的夜晚,留學習畫於西班牙的夫婦遂開著休旅車帶我們環繞整個南竿島,那般決絕的斷言:一定可以看見「藍眼淚」星砂夜海……沒有看見,倒是抵達了靜美的津沙古厝聚落,畫家幽然地提及這是他的誕生地。
畫家夫人也是畫家。牛角村民宿的夜讀爾雅版的詩畫集:《向島嶼靠近》。窗外微雨卻不沾衣,推門外出到可眺遠海的大露臺,夜霧綿纏的絲帛觸感;一種清新的、潔淨的輕寒,女詩人著筆的是這羅列的島鄉,女畫家顏彩深邃著潮汐與貝殼的情愫……多少美麗的組合。
明日是第三天了,如果依然船不開航,飛機不從臺灣來,是否我們依然要隔海一水,相互等待?霧鎖島群,如何向島靠近?十里之隔竟比天涯海角還要遙遠……最美的,是霧。我又想起向明先生的句子,只是形容,不是完成的詩行,卻比詩更像詩。那麼請容我踰越的試筆延伸──
困我於島不是大海
一枚乾涸貝殼
眠間傾聽的耳朵
那是隔水思念
耽美的從前早遺忘
最美的現在還是霧……
(選自卷二「隱匿應答」)
最初的陳列
越過花蓮木瓜溪,地上歲月又老去幾分?隔離千山萬水的中央山脈,嘉南平原的原鄉和此時花東縱谷的家園,前是記憶今是安頓;祈願靜謐的,沉定的,文字如種植般堅貞。
臺北外雙溪一九八一
作家妻子是音樂家,主修提琴和作曲。
三十年前的臺北士林福林路還是近郊,眷村群落在幾條狹隘、迂迴的窄巷兩邊,據說是總統官邸侍衛隊的宿舍所在;內外雙溪的小河從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那端清淺地流了過來,走過橫跨河上水泥橋就是雨農路。
雨農。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路名,想像:勤耕的農夫穿著沉甸的蓑衣,在濕濡的雨中弓身插秧或施肥,為生民培育糧食的勞苦,美麗而勇健的大地之子……彼時,少人知悉「雨農」二字根本不是向農夫致敬,而是紀念一位在四○年代中國抗日戰爭時,善於剷除異己、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首腦:戴笠,另號:雨農。
年輕時蒙難的作家住在附近,不知道心裡是否五味雜陳?初訪他的家居前通了電話,福林路幾號?說了地址後,特別聲明門口掛著畫上小提琴標記的牌子──妻子在家教音樂。抵達時,這才發現此地並不陌生,高中年代曾在對面的私立學校混過,那時何等叛逆,故意與極力反對我習畫的父親過不去,插班考試明明能夠唸公立高中,卻拿著成績單到私中報到;很感性的,因為依山傍水的校園開滿杜鵑花。
時報文學散文首獎,原題〈獄中書〉被要求改名為〈無怨〉……作家淡然地說,微笑著燃起菸來。我們閒散漫遊在夜市沸騰的鍋氣與食味、店家吆喝和食客喧語之間,常常就是這般地相約閒散漫遊市井,少談文學,彷彿心有靈犀的直覺:文字是生活的必然而非偶然,書寫和閱讀吧,抵達靈魂最深邃的某個角落,猶若作家曾經引用過卡夫卡的名言──
是一隻從黑暗中伸出,向美探索的手。
有一次的夜酒,倒是談到他在散文之前的譯書:《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原著者是匈牙利猶太裔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小說彷彿自傳,敘述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歐洲從事祕密活動,被逮捕受審判的經歷……曾經蒙難過的作家翻譯比他早生四十年一樣蒙難過的作家,譯筆的過程中是否多少因感身受而沉鬱、悲涼?敬他一杯酒,其實是不捨的怕引起他昔憶重返的憂傷;只是純粹的一本書,譯者和作者竟宿命等同。
我還清晰記得初訪時,小提琴標記的指路,想是妻子的琴弦,安頓了作家的美麗與哀愁。
花蓮一九九四
彼此約定,午後四時的花蓮機場。他從臺中過來,我從臺北過去,我臆測的航程是從蘭陽平原出海,沿著海岸線飛行,他則要穿越大甲溪直至源頭接立霧溪東飛,皆是三千米的峰頂。
他說:我沒去過花蓮。
沒去過花蓮,卻一直關心那位不曾見過面的散文作家。能夠寫出雄渾氣勢,運筆如大河山巒的秀異作家,卻去參選省議員了?這個九○年代的臺灣是怎麼回事?作家逐漸棄筆?
塞車的臺北市區,計程車插滿了市長候選人的小旗幟,司機老大連珠炮一樣的抨擊執政黨,我則由於時間緊迫,腹間隱隱作痛,索性閉上雙眼,左手抓著的皮包滾到座椅下端。
塞到民權東路、敦化北路口綠燈一下子換成紅燈,耐不住性子,我說要下車,司機老大說:我幫你趕吧!用力踩油門。兩側湧上的車子緊急煞車。喇叭聲大作,交通警察的臉很長。
喘過長長的氣,航機已穿過雨雲,在無涯的棉絮上水平飛行。我也很久不曾去花蓮了,想到花蓮總是多少會怦然心動,好像一種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負荷、絞痛之時,就會想去花蓮……。
把這種想法告訴住在花蓮的作家,他回信說:花蓮治療了你們的負荷、絞痛,那麼誰來治療創痕累累的花蓮?
作家帶領群眾去包圍紙漿廠,抗議水泥廠,被指為「有心分子」。我在報紙的地方版上見到作家,心中總是一種溫熱卻又摻雜著辛酸。
機窗外是蘇花公路,迂迴如細髮般的銀線,顯然逐漸降低高度,後座兩個日本人指著壯麗的清水斷崖,不禁輕呼的讚美:真是綺麗啊!航機猛然急墜,所有的乘客有所騷動,機長把航機拉平,忙說:剛通過一段不穩定氣流……五分鐘後在花蓮北埔機場落地。
在花蓮長住的作家,今晚的募款餐會,要替花蓮爭取、說話。忽然想到他所寫的兩本散文:《地上歲月》、《永遠的山》那份令人感心的暖熱。如果作家只是一直守住書房,也許這就不再是作家特有的質性了,夢終究不能只是文字。
太平洋灰茫蒼鬱的海水拍擊著花蓮海岸,航機在海灣上繚繞了個大圈,然後筆直地降落長長的跑道,穿過兩旁停駐的虎鯊型戰機以及微霧。
臺中來的朋友已經在機場外抽菸、等我。
(選自卷四「子夜貓頭鷹」)
今生
曾經書寫過的文字,其實早就遺忘。
最初是如何立意書寫,應該啟蒙於閱讀。
湮遠的七○年代,表面噤聲、沉寂,內裡花開絢爛的副刊、雜誌、書籍,哲學、藝術、文學……悄然、靜謐地,水似抒情地開始潛移默化的浸潤少年孤獨之心,比起凝滯、死板的國家主義唯尚的學校教育,為我推開一扇窗,窗外竟是無垠的大山大海,充滿無限的想像。
少年愚痴、天真的開始試圖習繪、作文,是對毫無創意的教育體制一種無由的主觀抗拒亦或是私己家庭的壓力所引致的故意叛逆?許是自我倦於勤讀,服膺於現實裡必然遵循的學校養成體制,卻替代以深愛的文學和藝術做為此後的人生,榮辱相與的過往終是值得感謝。
近時有人慎重問及可曾悔憾?我答以:不會後悔,只是多少有著遺憾。遺憾的是現實人生,不悔的是眷戀至今的文學一生;這也可能是自我認定是僅有做好的一件事,現實諸般一片荒蕪。言之「文學一生」自有些微感慨,終究六十初度已是事實,不必神傷亦不須自棄,歲月曾經美麗、肉身曾經青春已然足夠。
●
是誰,將我遺忘的最初招魂般喚回?蓄意忘卻的以及實質遺忘的,竟被重新復刻、檢視、出土……猶若千年前樓蘭古國的乾屍或者是非洲第一高峰頂上那隻被冰河凝凍的花豹。此時遺體被送上解剖檯,他們切開我的肌理,小心翼翼地分離胸前橫隔膜,搜尋到還在怦然跳動的心臟,他們可知道這心的某部分早已壞死。
值得探究我的內心嗎?我早以文字留下。不曾隱瞞,少於虛構(除了小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沒有灰色地帶;四十年就定義在「我手寫我心」,不須揣臆、勞神。每一個文字,每一則段落皆是我主觀的人生說法,或有偏執,或有朦昧,都是個人由衷的一廂情願。
偏執或朦昧的一廂情願。他者怎麼看,如何評比就由之自去,作者書寫、發表、合集出版之後,作品自然告別作者,陌路不再回首。文字的敗筆、失分都是種種過程,過程比完成還要美麗,其間的思索也許艱辛,就讓識者知心的各自體會,同感或異見皆是生命的圓滿。
他們奮力剖析我文字的內在,用以寫就豐實的碩士論文(注),如若願意的話,學位領受之外,我多麼祈望他們能真正讀懂我的內心,我面對殘酷、冰冷的現實,凜冽地應答。
●
無可救藥的浪漫嗎?確然如此。
偏執的相信理想與真情,多少自困自苦。
沒有浪漫與理想,試問:文學意義何在?
當然因之抵觸現實。那是一種人類社會與歷史長久以降形塑的固有定律,說是叢林法則、適者生存自是先哲群儒飽經苦難所深切領悟的智慧;如若明知現實中文學與藝術可能僅是稀微的心靈慰安,不必然成為生命的美感知覺生活的大部分,其實可以理解。抉擇是一座天秤,現實和理想如何找到平衡正是人類苦思、尋索的與生大病,後者永遠是一枚寒夜孤星。
愚痴、天真之我,似乎永遠不馴於現實,早就洞悉理想如此稀微、薄弱,依然眷愛不渝地試圖以文學書寫及閱讀保存一絲絲的理想信仰。於是有時我自問自答,編織文字情境並且從中獲得純淨的生命救贖。他們奮力剖析我文字的內在,年少初期十年的濫情,再十年的著力土地人民,又十年的回歸寧謐,而近十年他們洞悉了現在之我又是怎般地人生晚晴……
樓蘭古國的乾屍千年前想是青春美麗。
冰河封存的花豹怎會登臨五千米頂峰?
人與獸究竟要證明什麼?理想還是現實?
而我,卻一再以文學印證某種不馴對抗。
●
賽萬提斯不朽小說筆下的「夢幻騎士」,以為那轉動的風車是歌利亞巨人,如是嗎?
散文是心影錄,小說乃虛構演劇,詩是音樂和舞姿……我是讀者也是作者,閱讀他人書寫自己,前者冷靜後者狂熱,傾聽與爭辯、民主和獨裁,論文假以手術刀與明鏡,解剖之後真正發現什麼,豐饒或是空蕪還是心理學上的「人格分裂」?如果生在數百年之前,自己曾是遁山種植的農夫亦或是征戰逐野的霸主?
前世茫茫,今生逐然沉定。自嘲千年昔時也許就是佛座足下蓮花池裡一尾偷偷聽經的金魚,田田圓葉,花開如燭焰,這尾金魚莫非凡思想蛻化為人,佛陀令之以文字刑懲之今生。
猶若靜水一方,如同天光雲影,如此清晰、明澈,今生逐時留在文字中,你定能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