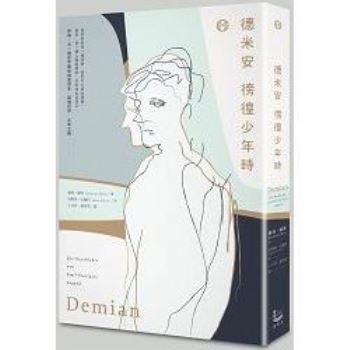我想要的,
只不過是想努力活得與我內在渴望的生活一致而已。
但為什麼竟如此艱難?
我的故事得從最初的時刻說起。若是可能的話,我得追憶到童年的懵懂時代,乃至童年的久遠之前,從我的家族淵源開始。
寫小說時,許多作家彷彿將自己尊為上帝,高高俯瞰,洞穿凡人的歷史,講述故事的方式也如同上帝的敘述方式,沒有任何粉飾,一切都是其本真面目。可我卻沒有這樣的能耐,就像作家也沒有這種能耐一樣。但我的故事對我之重要遠甚於作家的故事之於作家,因為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一個人的故事――不是一個虛假的、可能的、理想的或非現實的人,而是一個真切、獨一、鮮活的人,可惜現在世人對此的理解卻不如往昔,雖然每一個人都是自然獨一無二的寶貴造物,人們卻依然對彼此大開殺戒。如果我們並非獨一無二的人,如果我們真能用槍炮任意將他人從世上抹殺,那麼講故事將是多此一舉。然而人並非僅僅作為個人而存在,他同時也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個體,永遠是一個關鍵而奇妙的點,在這個點上,世界的萬千現象縱橫交錯,充滿不可重複的偶然。因此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恆的、神聖的,只要以某種方式活於世上,只要順應了自然的意願,每一個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們關注。在每一個人身上,精神都已化成了形貌,在每一個人身上,造物都在蒙受苦楚,在每一個人身上,救世主都被釘上了十字架。
今天很少有人懂得什麼是人。很多人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死得更從容,當我寫完這個故事之後,我也會同樣從容地死去。
我不能自詡洞明世事。從過去到今天,我一直是一個尋覓者,但我已不再尋求於星辰和書本之間,而是開始聆聽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語。我的故事並不令人暢懷,也不像杜撰的故事那樣甜美和諧,它味如癡語、混亂、癲狂和夢幻,就像所有那些不願再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樣。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對一條道路的嘗試,是一條小徑的悄然召喚。人們從來都無法以絕對的自我之相存在,每一個人都在努力變成絕對自我,有人遲鈍,有人更洞明,但無一不是自己的方式。人人都背負著誕生之時的殘餘,背負著來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殼,直到生命的終點。很多人都未能成人,只能繼續做青蛙、蜥蜴、螞蟻之輩。有些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然而每個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擲。所有人都擁有同一個起源和母親,我們來自同一個深淵,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試圖躍出深淵。我們可以彼此理解,然而每個人能夠詮釋的,只有他自己。
第一章 兩個世界
故事開始時,我大約十到十一歲,正在我所在小城的拉丁文學校讀書,那時的經歷便是故事的開端。
那時,世界朝我撲面而來,痛楚和愜意的戰慄叩擊著我的內心,隱祕的小巷,明淨的房屋和鐘塔,鐘聲,面孔,舒適暖和的房間,神祕詭異的房間。那裡有溫馨的親密,有兔子和女僕的味道,有家用藥材和乾菜的味道。在那裡,兩個世界迎面相逢,日和夜從兩個極點冉冉升起。
一個世界是父親主持的家,是個親密的小世界,裡面只有我的父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我已熟識,它的名字便是父親和母親,愛戀和嚴厲,模範和學校。這個世界散發著溫情的光,清淨而整潔,這裡有絮絮軟語,潔淨的雙手,整潔的衣裝和文雅的舉動。這裡有早晨的禱歌和聖誕的喜樂。這個世界中,通向未來的路途平坦筆直,這裡有義務和罪責,愧疚和懺悔,饒恕和善舉,愛慕和敬意,《聖經》和箴言。這個世界的秩序需要我們去遵守,這樣生命才會變得明朗而豐富,美好而規矩整齊。
另一個世界也從我們的家中延伸出來,卻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它的味道、語言、承諾和要求都大相迥異。第二個世界中有女僕和小工匠,有鬼怪和奇譚,那裡流溢著無數恐怖卻又魅力無窮的神祕事物,有屠場和監獄、醉鬼和潑婦、產小牛的母牛和失足的馬,有關於偷竊、兇殺和自縊的故事。這些美妙而可怕、野蠻而殘酷的事件無處不在。在咫尺之遙的街巷或庭院中,員警和流浪漢隨處可見,醉醺醺的男人打老婆,夜晚時分,少女紡的線團從工廠中汩汩滾出來,老婦能對人施咒致病,強盜藏身在森林中,縱火者被鄉警逮捕――濃烈逼人的第二個世界四處奔湧,襲面不息,無處不在,卻惟獨沒有滲入父母居住的房間。不過這樣也好。我們能夠擁有和睦、秩序和靜謐,義務和良知、饒恕和愛慕,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而截然不同的那些事物的存在,那些喧囂和尖叫、陰暗而殘酷的一切,也是非常美妙的,因為只一步之遙,我們就能回歸母親的懷抱。然而最奇妙的是,這兩個世界竟如此密切地彼此銜接,相生相伴!比如說我們的女僕莉娜,每到傍晚,她坐在大門邊的客廳裡祈禱,清亮的歌喉唱著禱歌,洗淨的雙手攤在平整的圍裙上,此時,她完全屬於父親和母親,屬於我們,屬於光明和真理的一方。這一刻結束之後,她卻在廚房或馬廄裡為我說無頭侏儒的故事;有時,她還在屠夫的肉店裡和鄰家婦人潑口對罵,此時,她已是另一個人,屬於另一個世界,渾身藏著祕密。一切都是這樣,尤其在我身上。毫無疑問,我自然站在光明和真理的一方,我是父母的孩子,然而我又無時不在見聞另外一個世界,雖然那裡於我如此陰森而陌生,經常喚起我的內疚和驚懼,但我同時也生長在那裡。某些時候,我甚至情願自己活在那個禁忌之國中,每次返回光明的一方時――雖然這一回歸是不可抗拒的正道――這裡的世界似乎顯得更冷清乏味。某些時刻,我明白,我生命的目標便是以父母為榜樣,長成光明而純淨的人,成熟和規矩的人,然而在此之前,我還要跋涉一段遠路,要上小學、大學,參加各種實習考試,而這條道路的路邊便是那另一個黑暗的國度,我必須穿越這個世界,一不小心,我就會駐留其中,無法拔身。我心潮澎湃地讀過一些故事,故事中的少年遭遇了類似的經歷,墮入迷途。此時,回歸父親的真理世界令人感覺如釋重負,我覺得這才是惟一的真善之舉,是我應謀求的路途,然而即便如此,那個關於邪道和迷途的故事依然更顯誘人,平心而論,失足者的受罰和回歸有時甚至令人心生遺憾。人們不會這樣說,也不會如此去思考,然而它依然盤踞在人的心中,埋在情感的深處,是一種微妙的暗示和可能。在我的幻想中,魔鬼可能會在樓下的街面上,或藏頭露尾,或以真面示人,或在年末的集市中,或在客棧中,但魔鬼永遠不會出現在我的家中。
我的姊妹也是光明世界的一員。我一向覺得,她們離父母更近一些,她們更端莊文雅,也更純淨。當然她們也有缺陷和瑕疵,但在我看來,她們的問題並非深伏於心,不像我,對邪惡之物難以釋懷,受其吸引。姊妹和父母一樣,天生受人呵護和尊重,若有人和她們發生爭執,事後必然會覺得良心有愧,認為錯在自身,需要乞求她們的原諒,因為侮辱她們就意味著侮辱了她們的父母,而他們是備受尊敬的善人。有些祕密,我寧可告訴那些放蕩的街頭浪子,也不願透露給我的姊妹。在好日子裡――一切安好,心思端正時――我也喜歡與姊妹做伴,殷勤相對,表現得乖巧端正。身為天使,就得這麼做!這是我們所知的最高境界,我們甜蜜而驚詫地想像自己身為天使,渾身被聖潔的吟唱和芬芳縈繞,享受聖誕和幸福的滋味。可歎的是,這樣的時刻多麼難得!常常在正常的遊戲之間,我會突然激動莽撞,令姊妹不滿,造成爭執和不快,當她們氣憤地指責我時,我竟變得不可理喻,行為和言語極為邪惡,甚至我自己在那一刻都能感到這種邪惡讓我痛徹心扉。之後我又會滿心懊悔,咬牙切齒地度過一段沮喪的時光,然後痛苦地道歉,此時,一線光明又會顯現,一種寧靜而感恩的純粹幸福――刹那間的幸福。
我去拉丁文學校上學,市長和森林警備主任的兒子也在我的班中,他們是不羈少年,但依然屬於正派的世界。有時他們也會和我接觸,但我依然和鄰家的一些男孩走得更近,這些孩子讀國民學校,一向為我們所輕視。我的故事就從某一個鄰家男孩開始。
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當時我剛過十歲――我和兩個鄰家的男孩正在閒逛。這時,一個大男孩也走過來,他年約十三歲,體格健壯,性格粗魯,是一個裁縫的兒子,讀國民學校,父親是酒鬼,家庭名聲很不好。我認識他――法蘭茲.克羅默,在他面前我很害怕,因此很不願意他加入我們。他已漸有成年男人的味道,舉止言談時時模仿年輕小工。他帶我們從橋邊下到河畔,然後躲進第一個橋孔中。拱曲的橋身和遲緩的水流間只有一道窄窄的河岸,上面全是垃圾――破瓦爛磚,生鏽纏結的鐵絲等玩意兒。有時那裡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在法蘭茲.克羅默的命令下,我們在垃圾裡翻來找去,把自己的發現給他看。有些東西他奪過去,有些則徑直扔到水裡。他讓我們留心鉛銅錫製的東西,這些他都會留著,連一把舊牛角梳也不例外。他在一旁時,我總覺得十分壓抑,不是因為我知道父親若是知情會嚴禁我和他來往,而是因為他令我恐懼。然而他對待我的方式和對別人並無不同,這倒令我開心。他下令,我們遵從,彷彿這是老規矩,雖然我和他只是初次見面。
完事後,我們坐在地上,法蘭茲朝水中吐唾沫,看起來像是一個男人。他從牙縫中吐痰,彈無虛發。我們開始閒聊,男孩們大贊或吹噓學校裡的各種英雄事蹟和惡作劇。我沉默著,但又擔心沉默會引起注意,使克羅默對我不滿。我的兩位同伴從一開始就疏遠了我,轉而向他示好,在他們當中,我是個異類,我的衣裝和風格在他們眼中是一種挑釁。我出身良好,上拉丁文學校,法蘭茲不可能會喜歡我,我也知道,只要機會到了,另外兩個男孩會立刻對我出言不遜,讓我出醜。
在強烈的恐懼中,我終於也不得不開口,編造了一個刺激的強盜故事,把自己變成主角之一。我說,在埃克磨坊邊的一個花園中,我曾和一個夥伴乘夜偷了一袋蘋果,那可不是普通蘋果,而是金色的萊茵特蘋果,最好的品種。由於一時緊張,我逃進了這個故事,杜撰是我的強項。為了不讓故事過早結束――或為了讓事情演變得更糟糕――我使出了全身解數。我說,我們一人放哨,另一人在樹上扔蘋果,結果袋子太沉,我們只好開袋留下一半後離開,半小時後又回來扛走了這一半。
講完後,我以為他們會喝彩。說故事令我的身體漸漸溫暖,我沉浸在臆想的樂趣中。兩個小男孩默不作聲地等法蘭茲表態,法蘭茲.克羅默瞇著眼睛,眼神似乎要穿透我,他以一種恐嚇的口氣問:「是真的嗎?」
「是的。」我說。
「千真萬確?」
「是的,千真萬確。」我硬著頭皮保證。
「你能發誓?」
我很害怕,但立即表示肯定。
「那你說:以上帝和幸福的名義!」
我就說:「以上帝和幸福的名義。」
「好吧。」他咕噥道,轉過身去。
我以為這事就這麼結束了,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開始往回走,我很高興。走到橋上時,我羞怯地表示自己要回家。
「不用著急,」法蘭茲大笑道,「我們同路。」
他慢慢地踱著步子走,我不敢溜開,他走的的確是我家的方向。走到我家附近,我看見大門,看見門上厚實的銅把手和窗戶的陽光,看見母親臥房的窗簾,於是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哦,回家!回家,回到光明寧靜世界的極樂之路!
我飛快開門溜進家,正當我要合上身後的門時,法蘭茲.克羅默竟跟著我擠了進來。地磚走廊幽暗陰涼,只有後院的光才透得進來,他貼在我身旁,握住我的胳膊,悄聲說:「別這麼著急!」
我驚恐萬分地瞪著他。他握我胳膊的手勁像鐵一樣結實。我在心中猜測他的意圖,擔心他會不會打我。我心想,如果此時大聲呼叫,會有人及時跑出來救我嗎?然而我終究沒有喊。
「怎麼?」我問,「你要幹嗎?」
「沒什麼。我只是有事要問你。其他人沒必要知道。」
「是嗎?你還要知道什麼?我得上去了,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法蘭茲輕聲道,「埃克磨坊邊的果園是誰家的?」
「我不知道。磨坊主的?」
法蘭茲用胳膊圈住我,將我拉到他身邊,他的臉逼近我的眼前,眼神邪惡,笑容不懷好意,臉上充滿了殘忍和力量。
「好吧,孩子,我告訴你果園是誰家的。我早就知道那些蘋果被偷了,我還知道,那個園主說過,只要有人能告訴他小偷是誰,他就給那人兩馬克。」
「上帝啊!」我喊道,「你不會向他舉報吧?」
我覺得寄望於他的自尊完全是徒勞。他來自另一個世界,對他而言,背叛並不是犯罪。我非常明白這一點。在這些事上,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和我們不同。
「不舉報?」克羅默大笑,「親愛的朋友,你以為我是假幣商,能給自己造出兩馬克來?我是窮鬼,不像你有個富爸爸,既然有兩馬克可賺,我肯定要賺到。說不定他還能給更多錢呢。」
他突然鬆開了我。家的門廊不再散發著靜謐安寧的氣息,世界在我身旁轟然崩潰。他會舉報我,我是一個犯人,別人會告訴父親,員警可能會來抓我。混沌世界的恐怖撲面而來,所有醜陋險惡之事都會奔我而來。我根本沒有偷竊的事實已經不重要了。何況我還發了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我的眼淚奔湧而出。我想,一定要買回自己的清白,於是絕望地在所有口袋裡搜索。沒有蘋果,沒有小刀,什麼都沒有。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錶。那是一隻古老的銀錶,早就不走了,我戴著它只是「裝裝樣子」。那是祖母的錶,我立刻將錶脫下來。
「克羅默,」我說,「聽著,你不用告發我,這樣做不好。我把我的錶送給你,你看看,我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這個你拿著,是銀的,這是好東西,只是有點小毛病,得修一修。」
他笑著,大手接過了錶。我盯著這隻手,心想它多麼粗糙,多麼心懷不軌,要奪走我的生活和寧靜。
「它是銀的――」我怯生生地說。
「我對你的銀貨和爛錶不感興趣!」他鄙夷地說道,「你自己去修吧!」
「法蘭茲!」我顫抖地叫道,擔心他跑走,「等等!把這支錶拿走!真是銀的,不騙你。我沒有別的東西。」
他冷漠而鄙夷地盯著我。
「你也知道我會去找誰。我也可以跟員警說,我跟巡警很熟。」
他轉身要離開。我扯住他的袖子,將他拉回來。絕對不能讓他走。他要是走了,我就得遭殃,那種痛苦我寧死也不要忍受。
「法蘭茲,」我乞求他,激動得聲音嘶啞,「不要做傻事!就當開個玩笑,好不好?」
「是,一個玩笑,對於你,這個玩笑代價有點昂貴。」
「法蘭茲,你說,你要我怎麼做?我什麼都答應!」
他那雙小眼睛上下打量著我,又笑了。
「不要這麼傻!」他偽善地說,「你和我一樣明白。我能賺兩馬克,你也知道,我既然是個窮人,就不會放著這筆錢不賺。可你是有錢人,甚至還有支錶。你只要給我兩馬克,這事就一筆勾銷。」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兩馬克!對我而言,兩馬克和十馬克、一百馬克、一千馬克一樣,是筆天文數字。我沒有錢。我有一個儲錢罐放在母親那裡,裡面有一些十分五分的硬幣,大都是親友們來訪時給的。此外我一分錢都沒有。我當時還沒到領零用錢的年紀。
「我沒錢。」我悲傷地說,「一分錢都沒有。除此之外,我什麼都能給你。我有一本講印第安人的書,還有士兵玩具,還有一個羅盤。我這就給你拿來。」
克羅默撇了撇邪惡的大嘴,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少廢話!」他不容分辯地說,「那些破玩意兒你自己留著吧。羅盤,哼!別把我當傻子,你聽著,拿錢給我!」
「可我沒有錢,我從來沒領過零用錢。這我也沒辦法!」
「那這樣,你明天把兩馬克給我送過來。放學後我在集市等,給錢就算了,拿不來錢,你就等著看好戲!」
「我答應你,可我從哪兒去弄錢呢?天哪,我真的沒錢――」
「你家裡多得是錢。這是你的事。明天放學後見。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帶錢來――」他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吐了一口唾沫,然後像幽靈一樣消失了。
我連上樓的力氣都沒有。我的生活完蛋了。我起了離家出走再也不回來的念頭,甚至想跳河自盡。可那些想法都很模糊。黑暗中我坐在樓梯間的底層臺階上,緊緊蜷成一團,沉浸在痛苦中。莉娜拎著籃子下樓取柴火時,才發現泣不成聲的我。
我請求她不要對家裡人提這件事,然後走上樓。玻璃門邊的衣鉤上掛著父親的禮帽和母親的陽傘,家園和柔情的氣息從這些物品中汩汩流出,向我溢來,我的心滿懷乞求和感激向它們致意,就像迷途的孩子看見故鄉小屋,聞見故鄉的味道一樣。然而這些都已不再屬於我,那是父母的光明世界,而我已罪惡地深陷在陌生的洪流中,敵人在伺機,危險、恐懼和恥辱已候在門外。禮帽和陽傘,砂石鋪的地面,廊櫃上的大幅油畫,還有起居室裡傳來姊妹的話語聲,一切都顯得比任何時候更可親可愛,然而這些已不再是撫慰,不再是奪不走的財富,而是嚴厲的呵斥。這些已不再屬於我,它們的純淨和安逸已與我無緣。我的腳上沾上了污穢,而這些污點已無法在地毯上擦脫,我瞞著家裡帶回了一片陰霾。我曾有過無數祕密,曾多次擔憂不安,可和今天帶回的陰影相比,那些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兒戲。厄運追在我身後,無數手正向我伸來,母親也已無法保護我免受其害,我絕不能讓她知道這件事。不管我的罪過是偷竊還是撒謊(我不是以上帝的名義起誓了嗎?),結果都一樣。我的罪不在這些,而在於讓魔鬼登堂入室。我為什麼要和他們一起呢?為什麼我遵從克羅默更甚於遵從父親呢?我為什麼要杜撰那個偷竊的故事呢?為什麼要吹噓自己犯過罪,彷彿那是英雄事蹟一樣?現在,魔鬼握住了我的手,敵人已跟隨在我身後。
某一瞬間,我忘記了對明天的恐懼,我所擔心的,是一種毛骨悚然的明確性――自己的路從今而後將急轉直下,墮入黑暗。我心裡明白,這一過錯將會勾出更多的過錯,我在姊妹面前的舉止、對父母的問候和親吻將成為謊言,我將隱瞞起自己的命運和祕密。
只不過是想努力活得與我內在渴望的生活一致而已。
但為什麼竟如此艱難?
我的故事得從最初的時刻說起。若是可能的話,我得追憶到童年的懵懂時代,乃至童年的久遠之前,從我的家族淵源開始。
寫小說時,許多作家彷彿將自己尊為上帝,高高俯瞰,洞穿凡人的歷史,講述故事的方式也如同上帝的敘述方式,沒有任何粉飾,一切都是其本真面目。可我卻沒有這樣的能耐,就像作家也沒有這種能耐一樣。但我的故事對我之重要遠甚於作家的故事之於作家,因為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一個人的故事――不是一個虛假的、可能的、理想的或非現實的人,而是一個真切、獨一、鮮活的人,可惜現在世人對此的理解卻不如往昔,雖然每一個人都是自然獨一無二的寶貴造物,人們卻依然對彼此大開殺戒。如果我們並非獨一無二的人,如果我們真能用槍炮任意將他人從世上抹殺,那麼講故事將是多此一舉。然而人並非僅僅作為個人而存在,他同時也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個體,永遠是一個關鍵而奇妙的點,在這個點上,世界的萬千現象縱橫交錯,充滿不可重複的偶然。因此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恆的、神聖的,只要以某種方式活於世上,只要順應了自然的意願,每一個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們關注。在每一個人身上,精神都已化成了形貌,在每一個人身上,造物都在蒙受苦楚,在每一個人身上,救世主都被釘上了十字架。
今天很少有人懂得什麼是人。很多人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死得更從容,當我寫完這個故事之後,我也會同樣從容地死去。
我不能自詡洞明世事。從過去到今天,我一直是一個尋覓者,但我已不再尋求於星辰和書本之間,而是開始聆聽自己血液的簌簌低語。我的故事並不令人暢懷,也不像杜撰的故事那樣甜美和諧,它味如癡語、混亂、癲狂和夢幻,就像所有那些不願再自欺欺人的生活一樣。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對一條道路的嘗試,是一條小徑的悄然召喚。人們從來都無法以絕對的自我之相存在,每一個人都在努力變成絕對自我,有人遲鈍,有人更洞明,但無一不是自己的方式。人人都背負著誕生之時的殘餘,背負著來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殼,直到生命的終點。很多人都未能成人,只能繼續做青蛙、蜥蜴、螞蟻之輩。有些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然而每個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擲。所有人都擁有同一個起源和母親,我們來自同一個深淵,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試圖躍出深淵。我們可以彼此理解,然而每個人能夠詮釋的,只有他自己。
第一章 兩個世界
故事開始時,我大約十到十一歲,正在我所在小城的拉丁文學校讀書,那時的經歷便是故事的開端。
那時,世界朝我撲面而來,痛楚和愜意的戰慄叩擊著我的內心,隱祕的小巷,明淨的房屋和鐘塔,鐘聲,面孔,舒適暖和的房間,神祕詭異的房間。那裡有溫馨的親密,有兔子和女僕的味道,有家用藥材和乾菜的味道。在那裡,兩個世界迎面相逢,日和夜從兩個極點冉冉升起。
一個世界是父親主持的家,是個親密的小世界,裡面只有我的父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我已熟識,它的名字便是父親和母親,愛戀和嚴厲,模範和學校。這個世界散發著溫情的光,清淨而整潔,這裡有絮絮軟語,潔淨的雙手,整潔的衣裝和文雅的舉動。這裡有早晨的禱歌和聖誕的喜樂。這個世界中,通向未來的路途平坦筆直,這裡有義務和罪責,愧疚和懺悔,饒恕和善舉,愛慕和敬意,《聖經》和箴言。這個世界的秩序需要我們去遵守,這樣生命才會變得明朗而豐富,美好而規矩整齊。
另一個世界也從我們的家中延伸出來,卻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它的味道、語言、承諾和要求都大相迥異。第二個世界中有女僕和小工匠,有鬼怪和奇譚,那裡流溢著無數恐怖卻又魅力無窮的神祕事物,有屠場和監獄、醉鬼和潑婦、產小牛的母牛和失足的馬,有關於偷竊、兇殺和自縊的故事。這些美妙而可怕、野蠻而殘酷的事件無處不在。在咫尺之遙的街巷或庭院中,員警和流浪漢隨處可見,醉醺醺的男人打老婆,夜晚時分,少女紡的線團從工廠中汩汩滾出來,老婦能對人施咒致病,強盜藏身在森林中,縱火者被鄉警逮捕――濃烈逼人的第二個世界四處奔湧,襲面不息,無處不在,卻惟獨沒有滲入父母居住的房間。不過這樣也好。我們能夠擁有和睦、秩序和靜謐,義務和良知、饒恕和愛慕,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而截然不同的那些事物的存在,那些喧囂和尖叫、陰暗而殘酷的一切,也是非常美妙的,因為只一步之遙,我們就能回歸母親的懷抱。然而最奇妙的是,這兩個世界竟如此密切地彼此銜接,相生相伴!比如說我們的女僕莉娜,每到傍晚,她坐在大門邊的客廳裡祈禱,清亮的歌喉唱著禱歌,洗淨的雙手攤在平整的圍裙上,此時,她完全屬於父親和母親,屬於我們,屬於光明和真理的一方。這一刻結束之後,她卻在廚房或馬廄裡為我說無頭侏儒的故事;有時,她還在屠夫的肉店裡和鄰家婦人潑口對罵,此時,她已是另一個人,屬於另一個世界,渾身藏著祕密。一切都是這樣,尤其在我身上。毫無疑問,我自然站在光明和真理的一方,我是父母的孩子,然而我又無時不在見聞另外一個世界,雖然那裡於我如此陰森而陌生,經常喚起我的內疚和驚懼,但我同時也生長在那裡。某些時候,我甚至情願自己活在那個禁忌之國中,每次返回光明的一方時――雖然這一回歸是不可抗拒的正道――這裡的世界似乎顯得更冷清乏味。某些時刻,我明白,我生命的目標便是以父母為榜樣,長成光明而純淨的人,成熟和規矩的人,然而在此之前,我還要跋涉一段遠路,要上小學、大學,參加各種實習考試,而這條道路的路邊便是那另一個黑暗的國度,我必須穿越這個世界,一不小心,我就會駐留其中,無法拔身。我心潮澎湃地讀過一些故事,故事中的少年遭遇了類似的經歷,墮入迷途。此時,回歸父親的真理世界令人感覺如釋重負,我覺得這才是惟一的真善之舉,是我應謀求的路途,然而即便如此,那個關於邪道和迷途的故事依然更顯誘人,平心而論,失足者的受罰和回歸有時甚至令人心生遺憾。人們不會這樣說,也不會如此去思考,然而它依然盤踞在人的心中,埋在情感的深處,是一種微妙的暗示和可能。在我的幻想中,魔鬼可能會在樓下的街面上,或藏頭露尾,或以真面示人,或在年末的集市中,或在客棧中,但魔鬼永遠不會出現在我的家中。
我的姊妹也是光明世界的一員。我一向覺得,她們離父母更近一些,她們更端莊文雅,也更純淨。當然她們也有缺陷和瑕疵,但在我看來,她們的問題並非深伏於心,不像我,對邪惡之物難以釋懷,受其吸引。姊妹和父母一樣,天生受人呵護和尊重,若有人和她們發生爭執,事後必然會覺得良心有愧,認為錯在自身,需要乞求她們的原諒,因為侮辱她們就意味著侮辱了她們的父母,而他們是備受尊敬的善人。有些祕密,我寧可告訴那些放蕩的街頭浪子,也不願透露給我的姊妹。在好日子裡――一切安好,心思端正時――我也喜歡與姊妹做伴,殷勤相對,表現得乖巧端正。身為天使,就得這麼做!這是我們所知的最高境界,我們甜蜜而驚詫地想像自己身為天使,渾身被聖潔的吟唱和芬芳縈繞,享受聖誕和幸福的滋味。可歎的是,這樣的時刻多麼難得!常常在正常的遊戲之間,我會突然激動莽撞,令姊妹不滿,造成爭執和不快,當她們氣憤地指責我時,我竟變得不可理喻,行為和言語極為邪惡,甚至我自己在那一刻都能感到這種邪惡讓我痛徹心扉。之後我又會滿心懊悔,咬牙切齒地度過一段沮喪的時光,然後痛苦地道歉,此時,一線光明又會顯現,一種寧靜而感恩的純粹幸福――刹那間的幸福。
我去拉丁文學校上學,市長和森林警備主任的兒子也在我的班中,他們是不羈少年,但依然屬於正派的世界。有時他們也會和我接觸,但我依然和鄰家的一些男孩走得更近,這些孩子讀國民學校,一向為我們所輕視。我的故事就從某一個鄰家男孩開始。
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當時我剛過十歲――我和兩個鄰家的男孩正在閒逛。這時,一個大男孩也走過來,他年約十三歲,體格健壯,性格粗魯,是一個裁縫的兒子,讀國民學校,父親是酒鬼,家庭名聲很不好。我認識他――法蘭茲.克羅默,在他面前我很害怕,因此很不願意他加入我們。他已漸有成年男人的味道,舉止言談時時模仿年輕小工。他帶我們從橋邊下到河畔,然後躲進第一個橋孔中。拱曲的橋身和遲緩的水流間只有一道窄窄的河岸,上面全是垃圾――破瓦爛磚,生鏽纏結的鐵絲等玩意兒。有時那裡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在法蘭茲.克羅默的命令下,我們在垃圾裡翻來找去,把自己的發現給他看。有些東西他奪過去,有些則徑直扔到水裡。他讓我們留心鉛銅錫製的東西,這些他都會留著,連一把舊牛角梳也不例外。他在一旁時,我總覺得十分壓抑,不是因為我知道父親若是知情會嚴禁我和他來往,而是因為他令我恐懼。然而他對待我的方式和對別人並無不同,這倒令我開心。他下令,我們遵從,彷彿這是老規矩,雖然我和他只是初次見面。
完事後,我們坐在地上,法蘭茲朝水中吐唾沫,看起來像是一個男人。他從牙縫中吐痰,彈無虛發。我們開始閒聊,男孩們大贊或吹噓學校裡的各種英雄事蹟和惡作劇。我沉默著,但又擔心沉默會引起注意,使克羅默對我不滿。我的兩位同伴從一開始就疏遠了我,轉而向他示好,在他們當中,我是個異類,我的衣裝和風格在他們眼中是一種挑釁。我出身良好,上拉丁文學校,法蘭茲不可能會喜歡我,我也知道,只要機會到了,另外兩個男孩會立刻對我出言不遜,讓我出醜。
在強烈的恐懼中,我終於也不得不開口,編造了一個刺激的強盜故事,把自己變成主角之一。我說,在埃克磨坊邊的一個花園中,我曾和一個夥伴乘夜偷了一袋蘋果,那可不是普通蘋果,而是金色的萊茵特蘋果,最好的品種。由於一時緊張,我逃進了這個故事,杜撰是我的強項。為了不讓故事過早結束――或為了讓事情演變得更糟糕――我使出了全身解數。我說,我們一人放哨,另一人在樹上扔蘋果,結果袋子太沉,我們只好開袋留下一半後離開,半小時後又回來扛走了這一半。
講完後,我以為他們會喝彩。說故事令我的身體漸漸溫暖,我沉浸在臆想的樂趣中。兩個小男孩默不作聲地等法蘭茲表態,法蘭茲.克羅默瞇著眼睛,眼神似乎要穿透我,他以一種恐嚇的口氣問:「是真的嗎?」
「是的。」我說。
「千真萬確?」
「是的,千真萬確。」我硬著頭皮保證。
「你能發誓?」
我很害怕,但立即表示肯定。
「那你說:以上帝和幸福的名義!」
我就說:「以上帝和幸福的名義。」
「好吧。」他咕噥道,轉過身去。
我以為這事就這麼結束了,過了一會兒,他站起身,開始往回走,我很高興。走到橋上時,我羞怯地表示自己要回家。
「不用著急,」法蘭茲大笑道,「我們同路。」
他慢慢地踱著步子走,我不敢溜開,他走的的確是我家的方向。走到我家附近,我看見大門,看見門上厚實的銅把手和窗戶的陽光,看見母親臥房的窗簾,於是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哦,回家!回家,回到光明寧靜世界的極樂之路!
我飛快開門溜進家,正當我要合上身後的門時,法蘭茲.克羅默竟跟著我擠了進來。地磚走廊幽暗陰涼,只有後院的光才透得進來,他貼在我身旁,握住我的胳膊,悄聲說:「別這麼著急!」
我驚恐萬分地瞪著他。他握我胳膊的手勁像鐵一樣結實。我在心中猜測他的意圖,擔心他會不會打我。我心想,如果此時大聲呼叫,會有人及時跑出來救我嗎?然而我終究沒有喊。
「怎麼?」我問,「你要幹嗎?」
「沒什麼。我只是有事要問你。其他人沒必要知道。」
「是嗎?你還要知道什麼?我得上去了,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法蘭茲輕聲道,「埃克磨坊邊的果園是誰家的?」
「我不知道。磨坊主的?」
法蘭茲用胳膊圈住我,將我拉到他身邊,他的臉逼近我的眼前,眼神邪惡,笑容不懷好意,臉上充滿了殘忍和力量。
「好吧,孩子,我告訴你果園是誰家的。我早就知道那些蘋果被偷了,我還知道,那個園主說過,只要有人能告訴他小偷是誰,他就給那人兩馬克。」
「上帝啊!」我喊道,「你不會向他舉報吧?」
我覺得寄望於他的自尊完全是徒勞。他來自另一個世界,對他而言,背叛並不是犯罪。我非常明白這一點。在這些事上,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和我們不同。
「不舉報?」克羅默大笑,「親愛的朋友,你以為我是假幣商,能給自己造出兩馬克來?我是窮鬼,不像你有個富爸爸,既然有兩馬克可賺,我肯定要賺到。說不定他還能給更多錢呢。」
他突然鬆開了我。家的門廊不再散發著靜謐安寧的氣息,世界在我身旁轟然崩潰。他會舉報我,我是一個犯人,別人會告訴父親,員警可能會來抓我。混沌世界的恐怖撲面而來,所有醜陋險惡之事都會奔我而來。我根本沒有偷竊的事實已經不重要了。何況我還發了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我的眼淚奔湧而出。我想,一定要買回自己的清白,於是絕望地在所有口袋裡搜索。沒有蘋果,沒有小刀,什麼都沒有。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錶。那是一隻古老的銀錶,早就不走了,我戴著它只是「裝裝樣子」。那是祖母的錶,我立刻將錶脫下來。
「克羅默,」我說,「聽著,你不用告發我,這樣做不好。我把我的錶送給你,你看看,我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這個你拿著,是銀的,這是好東西,只是有點小毛病,得修一修。」
他笑著,大手接過了錶。我盯著這隻手,心想它多麼粗糙,多麼心懷不軌,要奪走我的生活和寧靜。
「它是銀的――」我怯生生地說。
「我對你的銀貨和爛錶不感興趣!」他鄙夷地說道,「你自己去修吧!」
「法蘭茲!」我顫抖地叫道,擔心他跑走,「等等!把這支錶拿走!真是銀的,不騙你。我沒有別的東西。」
他冷漠而鄙夷地盯著我。
「你也知道我會去找誰。我也可以跟員警說,我跟巡警很熟。」
他轉身要離開。我扯住他的袖子,將他拉回來。絕對不能讓他走。他要是走了,我就得遭殃,那種痛苦我寧死也不要忍受。
「法蘭茲,」我乞求他,激動得聲音嘶啞,「不要做傻事!就當開個玩笑,好不好?」
「是,一個玩笑,對於你,這個玩笑代價有點昂貴。」
「法蘭茲,你說,你要我怎麼做?我什麼都答應!」
他那雙小眼睛上下打量著我,又笑了。
「不要這麼傻!」他偽善地說,「你和我一樣明白。我能賺兩馬克,你也知道,我既然是個窮人,就不會放著這筆錢不賺。可你是有錢人,甚至還有支錶。你只要給我兩馬克,這事就一筆勾銷。」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兩馬克!對我而言,兩馬克和十馬克、一百馬克、一千馬克一樣,是筆天文數字。我沒有錢。我有一個儲錢罐放在母親那裡,裡面有一些十分五分的硬幣,大都是親友們來訪時給的。此外我一分錢都沒有。我當時還沒到領零用錢的年紀。
「我沒錢。」我悲傷地說,「一分錢都沒有。除此之外,我什麼都能給你。我有一本講印第安人的書,還有士兵玩具,還有一個羅盤。我這就給你拿來。」
克羅默撇了撇邪惡的大嘴,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少廢話!」他不容分辯地說,「那些破玩意兒你自己留著吧。羅盤,哼!別把我當傻子,你聽著,拿錢給我!」
「可我沒有錢,我從來沒領過零用錢。這我也沒辦法!」
「那這樣,你明天把兩馬克給我送過來。放學後我在集市等,給錢就算了,拿不來錢,你就等著看好戲!」
「我答應你,可我從哪兒去弄錢呢?天哪,我真的沒錢――」
「你家裡多得是錢。這是你的事。明天放學後見。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帶錢來――」他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吐了一口唾沫,然後像幽靈一樣消失了。
我連上樓的力氣都沒有。我的生活完蛋了。我起了離家出走再也不回來的念頭,甚至想跳河自盡。可那些想法都很模糊。黑暗中我坐在樓梯間的底層臺階上,緊緊蜷成一團,沉浸在痛苦中。莉娜拎著籃子下樓取柴火時,才發現泣不成聲的我。
我請求她不要對家裡人提這件事,然後走上樓。玻璃門邊的衣鉤上掛著父親的禮帽和母親的陽傘,家園和柔情的氣息從這些物品中汩汩流出,向我溢來,我的心滿懷乞求和感激向它們致意,就像迷途的孩子看見故鄉小屋,聞見故鄉的味道一樣。然而這些都已不再屬於我,那是父母的光明世界,而我已罪惡地深陷在陌生的洪流中,敵人在伺機,危險、恐懼和恥辱已候在門外。禮帽和陽傘,砂石鋪的地面,廊櫃上的大幅油畫,還有起居室裡傳來姊妹的話語聲,一切都顯得比任何時候更可親可愛,然而這些已不再是撫慰,不再是奪不走的財富,而是嚴厲的呵斥。這些已不再屬於我,它們的純淨和安逸已與我無緣。我的腳上沾上了污穢,而這些污點已無法在地毯上擦脫,我瞞著家裡帶回了一片陰霾。我曾有過無數祕密,曾多次擔憂不安,可和今天帶回的陰影相比,那些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兒戲。厄運追在我身後,無數手正向我伸來,母親也已無法保護我免受其害,我絕不能讓她知道這件事。不管我的罪過是偷竊還是撒謊(我不是以上帝的名義起誓了嗎?),結果都一樣。我的罪不在這些,而在於讓魔鬼登堂入室。我為什麼要和他們一起呢?為什麼我遵從克羅默更甚於遵從父親呢?我為什麼要杜撰那個偷竊的故事呢?為什麼要吹噓自己犯過罪,彷彿那是英雄事蹟一樣?現在,魔鬼握住了我的手,敵人已跟隨在我身後。
某一瞬間,我忘記了對明天的恐懼,我所擔心的,是一種毛骨悚然的明確性――自己的路從今而後將急轉直下,墮入黑暗。我心裡明白,這一過錯將會勾出更多的過錯,我在姊妹面前的舉止、對父母的問候和親吻將成為謊言,我將隱瞞起自己的命運和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