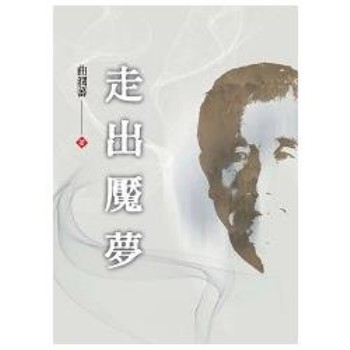5、四個黑點
母親在父親和四叔、五叔離開以後,坐立不安,天剛黑她就沉不住氣,抱著妹妹領著我跑到大街上去,看到從田裡回家的人就問,看到我父親和四叔、五叔沒有?怎麼這麼晚了還不見他們回來?其實那時候正是大部分的人從田裡回家的時刻,一點也不算晚。母親本來的目的是要向別人顯示,對於父親和四叔、五叔的逃走她完全不知情,可是這樣一來反而弄巧成拙,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這令人起疑的問話,果然被一個回家的幹部聽了出來,他咬牙切齒地對母親罵道:「妳這個屄養的!妳把他們弟兄打發走了,還在這裡裝糊塗,妳等著吧!斬草一定會除根!」母親嚇得放下妹妹跑去跳井,我和妹妹跟著在後面哭叫,井邊有人在挑水,把母親攔了下來。
那天晚上還不到吃飯的時間,幾個幹部背著磨得雪亮的大刀片,來勢洶洶地跑到我們住的三爺家裡來,嚇得所有住在三爺家裡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吃得下晚飯。不知道幹部跟母親說了些什麼,母親認為她活不成了,在炕上翻來覆去地想了一夜,認為與其等著被吊起來活活地打死,或是被活埋了慢慢地憋死,不如先自我了斷,上吊死了來得痛快。一大早不知道母親從哪裡找到了一根繩子,她拿了繩子走到前院原先三爺家長工住的夥計屋裡去,找了一個凳子,踩在上面正要往樑上拋繩子,我跟了進來,看到母親要上吊,我大哭大叫抱住她的腿不放,三爺家的三姑在後院聽到了,忙跑過來把繩子從母親的手裡搶了過去。
斧頭落下來了,第二天早晨幹部來把母親帶了去。中午幹部要三姑來帶我去問話,在路上三姑跟我說:「等一下幹部問你爹走的時候你媽知道不知道,你要說你媽不知道。記住了嗎?」我說:「記住了!」其實三姑不告訴我,我也知道該怎麼回答。
跟三姑去到一間屋子裡,看到母親直挺地站在一條長凳子上,腳上沒穿鞋子,兩隻胳膊各被一根繩子從腋窩下吊到樑上,眼睛被布摀了起來。一個女幹部把我領到那條凳子的頭上,在母親的腳旁邊她蹲下來問我說:「你爹走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媽?」我哭著說:「沒有!」幹部教三姑把我帶回去。我跟三姑回去後,不肯進到屋子裡去,站在大門口兩眼遠遠地盯著母親被吊起來的那間屋子,動也不肯動。太陽都快下山了,終於看到母親從那屋裡頭走了出來,我很高興地迎向前去拉著母親的手往家裡走,母親有些不耐煩,甩開了我的手說:「不能回家,要去找保。」我跟著母親挨家挨戶地求人作保,等找到了足夠的保數,告訴了幹部,早就到點燈的時候了。
往後的日子母親沒有活一天算一天的奢侈,只能是活一口氣算一口氣。家裡沒有了男人,她必須自己上山、下田來養活妹妹和我,以及被關起來的婆婆。時時都在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幹部會想起來要我們的命。
我們家在村西北頭山上有塊包穀地,地已經被鬥走了,因為地上的包穀是我父親原先種的,所以幹部允許我們等地上的作物收成了以後,再把地交給他們。地頭上種了些南瓜,那年南瓜豐收,好像整個夏天我們都在吃南瓜。
秋天包穀成熟了以後,我跟隨母親去那塊地上摘包穀穗,她在一行行茂密的包穀叢間邊摘邊往前走,我緊跟隨在她的後頭幫她忙,忽然我抬起頭來,母親不見了,高大的包穀桿和葉子擋住了我四周的視線,我驚嚇得大哭大叫,以為母親又丟下我去上吊了。聽到母親在前頭高聲對我說:「我在這裡,你哭什麼?」有如抓住我的死神突然鬆了手,我又掉回了原地。我用胳臂擦擦淚,撥開前面的包穀葉子,跑上前去緊緊抱住母親的腿。
一個炎熱的下午母親帶了網包,要到地裡去背包穀稭回家燒火煮飯,她要我留在家裡陪妹妹,我怕她去上吊,不放心,不肯。上山的路上,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哭哭啼啼地跟著。母親真被我煩透了,她快步走到前頭轉彎的路上,在一座小橋底下躲了起來。我繼續往前走,到了轉彎的路口看不到了母親,我又驚嚇地大哭大叫,這時候母親突然從橋底下鑽了出來,她怒氣沖沖地向我衝過來,我嚇得往回跑,她抓住我,把我按在地上,用網包使勁地抽打我。有個村裡的人路過,看了心酸,求母親不要再打我了。其實當時我一點也不感覺到痛,因為所有的心思全放在慶幸母親沒有丟下我。幹部命令母親接替父親為參軍的家屬代耕。那時節主要的工作是翻地瓜蔓,一壟一壟的地瓜長了茂盛的地瓜蔓(藤),為了不讓地瓜蔓的鬚根長到土裡去分散了地瓜的養分,必須用一根長長的棍子把地瓜蔓從壟的左邊翻到右邊去,過一段時間再從壟的右邊翻回左邊來,反覆地左右翻動。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母親既無力氣又無經驗,翻得不好常引起參軍家屬的不滿,遭到責難。要翻地瓜蔓的時候,母親帶著妹妹和我一起到田裡去。在大太陽底下晒,流很多汗,四歲不到的妹妹常常口渴要水喝,母親要我到地頭上摘片芋頭葉,拿到山澗底下去盛水給妹妹喝。芋頭葉不沾水,水包在裡頭很滑溜,一不小心就灑光了。經常我在山澗裡包得滿滿的一包水,等爬上來到了妹妹面前一滴也不剩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乾脆帶妹妹直接去山澗底下喝水。六歲不到的我背著妹妹一道梯田一道梯田地往山澗底下爬,又一道一道地爬上來,不時望望母親在翻地瓜蔓的側影,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
在婆婆遇害後,駐煙台李彌將軍的國軍部隊,和在牟平縣西北反抗共產黨的游擊隊,不時地從北邊下鄉來掃蕩。他們要來的時候,幹部不許我們留在村子裡,命令我們母子跟隨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往南邊的山上或村莊裡去躲避。在往南的大路上,母親一手抱著妹妹,一手拐個籃子,我跟在她旁邊,孤伶伶地跟隨著大隊往前走。人們像躲瘟似的遠遠地躲著我們。一次突然有人趁幹部不注意向我們飛快地跑過來,丟下一塊東西在母親的籃子裡,又飛快地跑回去。丟下的是塊白麵做的餅。在糧食極端缺乏的當時,這塊連他們自己老人和孩子都捨不得給吃的珍貴食品,竟然冒險送給了我們。我幫母親拉一拉籃子上蓋的那塊布,把餅藏在布底下,裝著若無其事,繼續跟著隊伍往前走。
有一天幹部要我們到南河對岸一個叫「峴上」的村莊去開會,那裡集合了附近幾個村莊被清算鬥爭過的地主,人數不少,擠滿了整個會場。一個共產黨上面派下來的年輕幹部走到台上來,向我們解釋新的罪行積點制度。他說,每家最多只能積到四個黑點,第五個黑點一到馬上就要處死。散會後可以到隔壁的辦公室去查看檔案,看看自己家目前有幾個黑點。母親不認識字,問幹部,幹部說我們已經有四個黑點,原因是我們家是地主,這是第一個黑點;我爺爺當過村長(只要在共產黨來之前當過村長,不管對村子做過多少貢獻,個人做過多少犧牲,一律劃為惡霸),是第二個黑點;我爺爺先逃走了,是第三個黑點;我父親和我四叔、五叔後來逃走了,是第四個黑點。母親向幹部提出抗議,認為我爺爺的逃走和我父親、四叔、五叔的逃走應該合在一起算一個黑點,不應該分開來算兩個黑點,那個年輕幹部不同意。
不等到第五個黑點的到來,我們村裡的幹部就迫不及待地要處置我們母子。傳出來的消息是他們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活埋我們,洞已經挖好了;另一個是把母親配給村東頭的一個窮無賴,綽號叫「驢痀腿」的瘸子。他們可能內部有所爭議,所以遲遲沒有執行。
有一天晚上開會散會以後,一個人來找母親,對母親說在村東北角上有一個四十來歲叫魏某的鰥夫,他願意娶母親並收養妹妹和我,幹部已經同意了,如果母親願意,今天晚上就過去。母親說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早晨再過去。
6、堅持地活下去
我年紀太小,不知道母親前一天夜裡有沒有合上眼,也無法理解母親當時的感受,不記得她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了一個小包袱,領了妹妹和我走完那一小段山坡路。我們到了魏家已經快中午了,魏某正在擀麵條。因為家鄉有「起腳的餃子,落腳的麵」的習俗,新媳婦進門要吃麵條。母親接過手把麵條擀好。麵還沒有來得及吃,就有幾個幹部說是來鬧洞房,哪裡有人大白天鬧洞房的,分明是來羞辱母親,他們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母親低著頭坐在那裡,一句話也沒有說,一根麵條也沒有吃。
共產黨把農民分為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四個等級。魏家屬於中農,有幾畝地、一棟房子和一頭驢。房子建在山坡上一塊整平的台地上,坐北朝南一排,總共只有三個房間,中間進門的是廚房,廚房的兩旁是臥房,臥房的門通廚房。房子的前面有一長溜溜沒有圍牆的院子,院子的左邊是驢欄,栓那頭驢的地方,右邊種了一棵大槐樹,槐樹的右邊台階下是一條南北向,直通村南的斜坡路,我們就是從這條路走上來的。沿著房子的後頭是一條小路,往東能通到村東頭的大路。魏家只有兩個人,魏某和他的一個十來歲,腦筋有些遲鈍,名叫小喜子的女兒。
要堅持地活下去,嫁到魏家來總比被強迫配給「驢痀腿」好多了。我們母子不再有隨時死亡的威脅和恐懼,我不用再怕母親去自殺而時刻盯住她不放。我們更多了一層新的活動空間,可以拿到路行條去探望外婆和大姨。對外有了交通,有事情可以找親戚商量,不再感到那可怕的孤立和無援。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從此就可以太平無事。第一個警訊發生在過來魏家沒有多久的一天晚上,村裡開會,像往常一樣按階級成分不同分開來坐,幹部命令我們母子去跟地主們坐在一起,能再看到大爺和三爺家的親人自然很高興,但這分明是要告訴我們:我們母子的命運仍然跟過去脫不了關係。
全村的人都在瘋狂地搞清算鬥爭、窮人翻身。那些翻了身,分到了土地的窮人,很少人有心思去種地,因為那要流汗和出力,不如去拿地主現成的來得便捷。加上許多年輕人被迫參了軍,造成種地勞力的不足。更由於共產黨在打仗,戰費浩繁,稅捐極重,收刮走了不成比例的農民收成。這些原因給我們村子裡帶來了空前的饑荒。放眼所及大多數的家庭都在靠野菜(如嫩的蒲公英)、樹葉(如楊柳、榆樹的葉)和樹皮(如楊柳樹皮)充饑。野菜挖光了,連陳年晒黑了的乾地瓜蔓也拿出來用熱水泡開煮來吃。村裡有人餓死。
比較起來我們要好多了。魏某是個典型的勤奮農民,早已過了參軍的年齡,現在有了年輕的母親為他洗衣燒飯料理家務,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地去種他那幾畝地,加上人口簡單,因而有足夠的地瓜、地瓜乾和包穀可以讓我們吃飽。
為了節省過日子,母親也學著別人把野菜摻在包穀餅裡當飯吃。
在趕集的時候,魏某把自己種的,數量有限的花生和麥子馱在他那頭驢背上,到市場上賣了換成錢。回來的時候總會買點煮熟的豬頭肉或其他好吃、好用的小東西帶給我們。有一次他買了一件小男孩的舊上衣帶回來給我。母親堅決不讓我穿,和魏某爭吵了起來,因為她怕那是從死人身上剝下來的,死人的怨魂會附在衣服上不散。母親的顧慮看起來有些不近情理,事實上那時候有非常多冤死的大人和小孩,尤其是從前地主家的大人和小孩。
大人都說小喜子的腦筋有些遲鈍,但是當時才六歲的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或許由於她的智商不高所以沒有壞心眼,我覺得她的心地特別善良,跟她相處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秋天過後,山上的闊葉樹如養柞蠶的柞木落了葉,窮人家的半大孩子們都要到山上去扒樹葉,用網包背回家堆積起來,作為爾後煮飯或燒炕的燃料。午飯後太陽晒乾了落葉上的露水,孩子們紛紛上山去扒樹葉,魏某擔心小喜子一個人去會受到壞男孩子的欺負,母親要我陪她一起去。山林裡遍地的紅葉,煞是美麗。我幫小喜子塞滿了網包後,我們到樹叢中去找鳥蛋,在野地裡追兔子,在山上玩夠了,才快樂地踩著夕陽循著下山的路回家,從遠處村裡飄來燃燒樹葉的陣陣炊煙,有一股醉人的芬芳。
母親迫不及待地要到了路行條,到下雨村去探望外婆。記得上一次到外婆家是在一年多以前小姨出嫁的時候,那時候外婆的日子還過得去。這次再看到外婆,她的情況糟透了,外公完全倒向了他姨太太的那一邊去,和外婆分開來吃飯,不再養活外婆了。外婆只好日夜紡紗,賺一點點包穀麵摻合著大部分的野菜來養活自己。我們能活著看到外婆,外婆自然很高興,但是她窮得連管我們一頓飯的能力都沒有。母親料想不到外婆竟會潦倒到這步田地,傷心透了,對外公表示了極度的不滿。
母親對外公的不滿還包括了她認為外公對我們母子的死活漠不關心。原因是由於外公沒有多少土地,加上要養活的人口又多,在下雨村這個比較大的村莊裡,很多人都比他富裕,因而在農民等級劃分的時候,他被評為中農。由於成分良好,他姨太太的一個女兒當上了下雨村「青婦會」的副會長,大小是個幹部。母親抱怨的是,在我們母子遭到極端迫害的時候,外公並沒有利用他的影響力,向我們伸出任何絲毫的援手。
其實外公沒有來營救我們,對我們來說不見得是件壞事情。與我們情況相似,在離我們村不遠的一個村莊裡就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有一家人的丈夫逃跑了,該村子裡的幹部要活埋他的太太和三個女兒。太太娘家的哥哥得到了消息,跑來向幹部求情,希望能讓他帶走一個女兒,幹部滿口答應,問他要哪個女兒,請他在屋裡等等,這就去帶他要的女兒來。幹部出了門,把門從外頭反鎖了起來,立即去把四個人都活埋了,才回來開門放他出去。以我們村裡的幹部之壞、之狠、之毒,同樣的事情很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母子身上。
要過年了,母親忙著清潔屋子,準備過年的食物。她蒸了一籠一半白麵、一半包穀麵的年糕,做了一籠屜的豆腐,蒸了幾籠普通的餑餑,炸了一些用麵粉裹的肥肉,俗稱酥肉,燉了一盆包含豆腐、酥肉、大白菜和粉條在一起的隔年菜。過年期間能吃到餑餑和年糕配隔年菜,對於平時餐餐蔬菜雜糧,絕少油水的我們來說,有勝於滿漢全席。對了,還有包子,年三十的早晨一定吃包子。
正月裡天冷,風雪不斷,外公還是冒著大雪來女兒家作客。母親雖然心裡對外公不滿,仍然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款待他。一直處於半饑餓狀態下的外公能有酒有肉地飽餐一頓,非常的滿意,算是過了一個難得的好年。過完了年的春天,母親把外婆接過來住了一段時間。那時候小姨婆家的情況也不好,小姨丈被徵參軍去了,家裡窮,沒有什麼東西吃,大人和小孩都營養不良,小姨頭胎生下來的孩子沒活多久就夭折了。小姨在家跟她公婆處不好,常來探望外婆和母親。外婆和小姨的到來,帶給母親很多的關懷和慰藉,母親的日子好過得多了。最興奮的是我,老纏著小姨問東問西地不放。晚飯後小姨帶我坐在屋旁的大槐樹下,給我講故事,教我數數,我能輕易地從一數到一百,這讓我後來上學的算術成績比別的同學都好,因為大多數的同學剛開始只能從一數到十。
外婆和小姨回去後,我們的日子又靜了下來。母親和我有很多的時間單獨在一起,母親又禁不住一再重複地問我:「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你爹?」因為母親相信傳說:小孩子能預知未來。我也一再重複地給母親同樣的回答:「過了年。」母親很失望,去年我告訴她過了年,怎麼今年又說過了年?到底要過幾個年?
母親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母親懷孕了。
母親在父親和四叔、五叔離開以後,坐立不安,天剛黑她就沉不住氣,抱著妹妹領著我跑到大街上去,看到從田裡回家的人就問,看到我父親和四叔、五叔沒有?怎麼這麼晚了還不見他們回來?其實那時候正是大部分的人從田裡回家的時刻,一點也不算晚。母親本來的目的是要向別人顯示,對於父親和四叔、五叔的逃走她完全不知情,可是這樣一來反而弄巧成拙,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這令人起疑的問話,果然被一個回家的幹部聽了出來,他咬牙切齒地對母親罵道:「妳這個屄養的!妳把他們弟兄打發走了,還在這裡裝糊塗,妳等著吧!斬草一定會除根!」母親嚇得放下妹妹跑去跳井,我和妹妹跟著在後面哭叫,井邊有人在挑水,把母親攔了下來。
那天晚上還不到吃飯的時間,幾個幹部背著磨得雪亮的大刀片,來勢洶洶地跑到我們住的三爺家裡來,嚇得所有住在三爺家裡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吃得下晚飯。不知道幹部跟母親說了些什麼,母親認為她活不成了,在炕上翻來覆去地想了一夜,認為與其等著被吊起來活活地打死,或是被活埋了慢慢地憋死,不如先自我了斷,上吊死了來得痛快。一大早不知道母親從哪裡找到了一根繩子,她拿了繩子走到前院原先三爺家長工住的夥計屋裡去,找了一個凳子,踩在上面正要往樑上拋繩子,我跟了進來,看到母親要上吊,我大哭大叫抱住她的腿不放,三爺家的三姑在後院聽到了,忙跑過來把繩子從母親的手裡搶了過去。
斧頭落下來了,第二天早晨幹部來把母親帶了去。中午幹部要三姑來帶我去問話,在路上三姑跟我說:「等一下幹部問你爹走的時候你媽知道不知道,你要說你媽不知道。記住了嗎?」我說:「記住了!」其實三姑不告訴我,我也知道該怎麼回答。
跟三姑去到一間屋子裡,看到母親直挺地站在一條長凳子上,腳上沒穿鞋子,兩隻胳膊各被一根繩子從腋窩下吊到樑上,眼睛被布摀了起來。一個女幹部把我領到那條凳子的頭上,在母親的腳旁邊她蹲下來問我說:「你爹走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媽?」我哭著說:「沒有!」幹部教三姑把我帶回去。我跟三姑回去後,不肯進到屋子裡去,站在大門口兩眼遠遠地盯著母親被吊起來的那間屋子,動也不肯動。太陽都快下山了,終於看到母親從那屋裡頭走了出來,我很高興地迎向前去拉著母親的手往家裡走,母親有些不耐煩,甩開了我的手說:「不能回家,要去找保。」我跟著母親挨家挨戶地求人作保,等找到了足夠的保數,告訴了幹部,早就到點燈的時候了。
往後的日子母親沒有活一天算一天的奢侈,只能是活一口氣算一口氣。家裡沒有了男人,她必須自己上山、下田來養活妹妹和我,以及被關起來的婆婆。時時都在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幹部會想起來要我們的命。
我們家在村西北頭山上有塊包穀地,地已經被鬥走了,因為地上的包穀是我父親原先種的,所以幹部允許我們等地上的作物收成了以後,再把地交給他們。地頭上種了些南瓜,那年南瓜豐收,好像整個夏天我們都在吃南瓜。
秋天包穀成熟了以後,我跟隨母親去那塊地上摘包穀穗,她在一行行茂密的包穀叢間邊摘邊往前走,我緊跟隨在她的後頭幫她忙,忽然我抬起頭來,母親不見了,高大的包穀桿和葉子擋住了我四周的視線,我驚嚇得大哭大叫,以為母親又丟下我去上吊了。聽到母親在前頭高聲對我說:「我在這裡,你哭什麼?」有如抓住我的死神突然鬆了手,我又掉回了原地。我用胳臂擦擦淚,撥開前面的包穀葉子,跑上前去緊緊抱住母親的腿。
一個炎熱的下午母親帶了網包,要到地裡去背包穀稭回家燒火煮飯,她要我留在家裡陪妹妹,我怕她去上吊,不放心,不肯。上山的路上,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哭哭啼啼地跟著。母親真被我煩透了,她快步走到前頭轉彎的路上,在一座小橋底下躲了起來。我繼續往前走,到了轉彎的路口看不到了母親,我又驚嚇地大哭大叫,這時候母親突然從橋底下鑽了出來,她怒氣沖沖地向我衝過來,我嚇得往回跑,她抓住我,把我按在地上,用網包使勁地抽打我。有個村裡的人路過,看了心酸,求母親不要再打我了。其實當時我一點也不感覺到痛,因為所有的心思全放在慶幸母親沒有丟下我。幹部命令母親接替父親為參軍的家屬代耕。那時節主要的工作是翻地瓜蔓,一壟一壟的地瓜長了茂盛的地瓜蔓(藤),為了不讓地瓜蔓的鬚根長到土裡去分散了地瓜的養分,必須用一根長長的棍子把地瓜蔓從壟的左邊翻到右邊去,過一段時間再從壟的右邊翻回左邊來,反覆地左右翻動。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母親既無力氣又無經驗,翻得不好常引起參軍家屬的不滿,遭到責難。要翻地瓜蔓的時候,母親帶著妹妹和我一起到田裡去。在大太陽底下晒,流很多汗,四歲不到的妹妹常常口渴要水喝,母親要我到地頭上摘片芋頭葉,拿到山澗底下去盛水給妹妹喝。芋頭葉不沾水,水包在裡頭很滑溜,一不小心就灑光了。經常我在山澗裡包得滿滿的一包水,等爬上來到了妹妹面前一滴也不剩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乾脆帶妹妹直接去山澗底下喝水。六歲不到的我背著妹妹一道梯田一道梯田地往山澗底下爬,又一道一道地爬上來,不時望望母親在翻地瓜蔓的側影,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
在婆婆遇害後,駐煙台李彌將軍的國軍部隊,和在牟平縣西北反抗共產黨的游擊隊,不時地從北邊下鄉來掃蕩。他們要來的時候,幹部不許我們留在村子裡,命令我們母子跟隨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往南邊的山上或村莊裡去躲避。在往南的大路上,母親一手抱著妹妹,一手拐個籃子,我跟在她旁邊,孤伶伶地跟隨著大隊往前走。人們像躲瘟似的遠遠地躲著我們。一次突然有人趁幹部不注意向我們飛快地跑過來,丟下一塊東西在母親的籃子裡,又飛快地跑回去。丟下的是塊白麵做的餅。在糧食極端缺乏的當時,這塊連他們自己老人和孩子都捨不得給吃的珍貴食品,竟然冒險送給了我們。我幫母親拉一拉籃子上蓋的那塊布,把餅藏在布底下,裝著若無其事,繼續跟著隊伍往前走。
有一天幹部要我們到南河對岸一個叫「峴上」的村莊去開會,那裡集合了附近幾個村莊被清算鬥爭過的地主,人數不少,擠滿了整個會場。一個共產黨上面派下來的年輕幹部走到台上來,向我們解釋新的罪行積點制度。他說,每家最多只能積到四個黑點,第五個黑點一到馬上就要處死。散會後可以到隔壁的辦公室去查看檔案,看看自己家目前有幾個黑點。母親不認識字,問幹部,幹部說我們已經有四個黑點,原因是我們家是地主,這是第一個黑點;我爺爺當過村長(只要在共產黨來之前當過村長,不管對村子做過多少貢獻,個人做過多少犧牲,一律劃為惡霸),是第二個黑點;我爺爺先逃走了,是第三個黑點;我父親和我四叔、五叔後來逃走了,是第四個黑點。母親向幹部提出抗議,認為我爺爺的逃走和我父親、四叔、五叔的逃走應該合在一起算一個黑點,不應該分開來算兩個黑點,那個年輕幹部不同意。
不等到第五個黑點的到來,我們村裡的幹部就迫不及待地要處置我們母子。傳出來的消息是他們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活埋我們,洞已經挖好了;另一個是把母親配給村東頭的一個窮無賴,綽號叫「驢痀腿」的瘸子。他們可能內部有所爭議,所以遲遲沒有執行。
有一天晚上開會散會以後,一個人來找母親,對母親說在村東北角上有一個四十來歲叫魏某的鰥夫,他願意娶母親並收養妹妹和我,幹部已經同意了,如果母親願意,今天晚上就過去。母親說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早晨再過去。
6、堅持地活下去
我年紀太小,不知道母親前一天夜裡有沒有合上眼,也無法理解母親當時的感受,不記得她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了一個小包袱,領了妹妹和我走完那一小段山坡路。我們到了魏家已經快中午了,魏某正在擀麵條。因為家鄉有「起腳的餃子,落腳的麵」的習俗,新媳婦進門要吃麵條。母親接過手把麵條擀好。麵還沒有來得及吃,就有幾個幹部說是來鬧洞房,哪裡有人大白天鬧洞房的,分明是來羞辱母親,他們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母親低著頭坐在那裡,一句話也沒有說,一根麵條也沒有吃。
共產黨把農民分為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四個等級。魏家屬於中農,有幾畝地、一棟房子和一頭驢。房子建在山坡上一塊整平的台地上,坐北朝南一排,總共只有三個房間,中間進門的是廚房,廚房的兩旁是臥房,臥房的門通廚房。房子的前面有一長溜溜沒有圍牆的院子,院子的左邊是驢欄,栓那頭驢的地方,右邊種了一棵大槐樹,槐樹的右邊台階下是一條南北向,直通村南的斜坡路,我們就是從這條路走上來的。沿著房子的後頭是一條小路,往東能通到村東頭的大路。魏家只有兩個人,魏某和他的一個十來歲,腦筋有些遲鈍,名叫小喜子的女兒。
要堅持地活下去,嫁到魏家來總比被強迫配給「驢痀腿」好多了。我們母子不再有隨時死亡的威脅和恐懼,我不用再怕母親去自殺而時刻盯住她不放。我們更多了一層新的活動空間,可以拿到路行條去探望外婆和大姨。對外有了交通,有事情可以找親戚商量,不再感到那可怕的孤立和無援。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從此就可以太平無事。第一個警訊發生在過來魏家沒有多久的一天晚上,村裡開會,像往常一樣按階級成分不同分開來坐,幹部命令我們母子去跟地主們坐在一起,能再看到大爺和三爺家的親人自然很高興,但這分明是要告訴我們:我們母子的命運仍然跟過去脫不了關係。
全村的人都在瘋狂地搞清算鬥爭、窮人翻身。那些翻了身,分到了土地的窮人,很少人有心思去種地,因為那要流汗和出力,不如去拿地主現成的來得便捷。加上許多年輕人被迫參了軍,造成種地勞力的不足。更由於共產黨在打仗,戰費浩繁,稅捐極重,收刮走了不成比例的農民收成。這些原因給我們村子裡帶來了空前的饑荒。放眼所及大多數的家庭都在靠野菜(如嫩的蒲公英)、樹葉(如楊柳、榆樹的葉)和樹皮(如楊柳樹皮)充饑。野菜挖光了,連陳年晒黑了的乾地瓜蔓也拿出來用熱水泡開煮來吃。村裡有人餓死。
比較起來我們要好多了。魏某是個典型的勤奮農民,早已過了參軍的年齡,現在有了年輕的母親為他洗衣燒飯料理家務,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地去種他那幾畝地,加上人口簡單,因而有足夠的地瓜、地瓜乾和包穀可以讓我們吃飽。
為了節省過日子,母親也學著別人把野菜摻在包穀餅裡當飯吃。
在趕集的時候,魏某把自己種的,數量有限的花生和麥子馱在他那頭驢背上,到市場上賣了換成錢。回來的時候總會買點煮熟的豬頭肉或其他好吃、好用的小東西帶給我們。有一次他買了一件小男孩的舊上衣帶回來給我。母親堅決不讓我穿,和魏某爭吵了起來,因為她怕那是從死人身上剝下來的,死人的怨魂會附在衣服上不散。母親的顧慮看起來有些不近情理,事實上那時候有非常多冤死的大人和小孩,尤其是從前地主家的大人和小孩。
大人都說小喜子的腦筋有些遲鈍,但是當時才六歲的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或許由於她的智商不高所以沒有壞心眼,我覺得她的心地特別善良,跟她相處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秋天過後,山上的闊葉樹如養柞蠶的柞木落了葉,窮人家的半大孩子們都要到山上去扒樹葉,用網包背回家堆積起來,作為爾後煮飯或燒炕的燃料。午飯後太陽晒乾了落葉上的露水,孩子們紛紛上山去扒樹葉,魏某擔心小喜子一個人去會受到壞男孩子的欺負,母親要我陪她一起去。山林裡遍地的紅葉,煞是美麗。我幫小喜子塞滿了網包後,我們到樹叢中去找鳥蛋,在野地裡追兔子,在山上玩夠了,才快樂地踩著夕陽循著下山的路回家,從遠處村裡飄來燃燒樹葉的陣陣炊煙,有一股醉人的芬芳。
母親迫不及待地要到了路行條,到下雨村去探望外婆。記得上一次到外婆家是在一年多以前小姨出嫁的時候,那時候外婆的日子還過得去。這次再看到外婆,她的情況糟透了,外公完全倒向了他姨太太的那一邊去,和外婆分開來吃飯,不再養活外婆了。外婆只好日夜紡紗,賺一點點包穀麵摻合著大部分的野菜來養活自己。我們能活著看到外婆,外婆自然很高興,但是她窮得連管我們一頓飯的能力都沒有。母親料想不到外婆竟會潦倒到這步田地,傷心透了,對外公表示了極度的不滿。
母親對外公的不滿還包括了她認為外公對我們母子的死活漠不關心。原因是由於外公沒有多少土地,加上要養活的人口又多,在下雨村這個比較大的村莊裡,很多人都比他富裕,因而在農民等級劃分的時候,他被評為中農。由於成分良好,他姨太太的一個女兒當上了下雨村「青婦會」的副會長,大小是個幹部。母親抱怨的是,在我們母子遭到極端迫害的時候,外公並沒有利用他的影響力,向我們伸出任何絲毫的援手。
其實外公沒有來營救我們,對我們來說不見得是件壞事情。與我們情況相似,在離我們村不遠的一個村莊裡就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有一家人的丈夫逃跑了,該村子裡的幹部要活埋他的太太和三個女兒。太太娘家的哥哥得到了消息,跑來向幹部求情,希望能讓他帶走一個女兒,幹部滿口答應,問他要哪個女兒,請他在屋裡等等,這就去帶他要的女兒來。幹部出了門,把門從外頭反鎖了起來,立即去把四個人都活埋了,才回來開門放他出去。以我們村裡的幹部之壞、之狠、之毒,同樣的事情很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母子身上。
要過年了,母親忙著清潔屋子,準備過年的食物。她蒸了一籠一半白麵、一半包穀麵的年糕,做了一籠屜的豆腐,蒸了幾籠普通的餑餑,炸了一些用麵粉裹的肥肉,俗稱酥肉,燉了一盆包含豆腐、酥肉、大白菜和粉條在一起的隔年菜。過年期間能吃到餑餑和年糕配隔年菜,對於平時餐餐蔬菜雜糧,絕少油水的我們來說,有勝於滿漢全席。對了,還有包子,年三十的早晨一定吃包子。
正月裡天冷,風雪不斷,外公還是冒著大雪來女兒家作客。母親雖然心裡對外公不滿,仍然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款待他。一直處於半饑餓狀態下的外公能有酒有肉地飽餐一頓,非常的滿意,算是過了一個難得的好年。過完了年的春天,母親把外婆接過來住了一段時間。那時候小姨婆家的情況也不好,小姨丈被徵參軍去了,家裡窮,沒有什麼東西吃,大人和小孩都營養不良,小姨頭胎生下來的孩子沒活多久就夭折了。小姨在家跟她公婆處不好,常來探望外婆和母親。外婆和小姨的到來,帶給母親很多的關懷和慰藉,母親的日子好過得多了。最興奮的是我,老纏著小姨問東問西地不放。晚飯後小姨帶我坐在屋旁的大槐樹下,給我講故事,教我數數,我能輕易地從一數到一百,這讓我後來上學的算術成績比別的同學都好,因為大多數的同學剛開始只能從一數到十。
外婆和小姨回去後,我們的日子又靜了下來。母親和我有很多的時間單獨在一起,母親又禁不住一再重複地問我:「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你爹?」因為母親相信傳說:小孩子能預知未來。我也一再重複地給母親同樣的回答:「過了年。」母親很失望,去年我告訴她過了年,怎麼今年又說過了年?到底要過幾個年?
母親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母親懷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