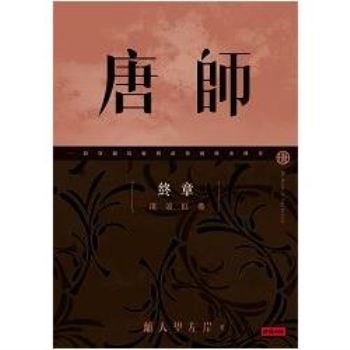第二百四十一章 被困黑獄神秘老者
都說宰相難及獄吏貴,落難的宰相到了牢獄之中,也只能忍氣吞聲,然而徐真不是尋常的大唐使節,他是一個神話,無論在天竺、泥婆羅或是吐蕃,他的事蹟直至今日仍舊在不斷傳唱。
哪怕這些獄吏都是喬邦色的人,也不敢虧待徐真,更漫說這些獄吏乃是邏些城的公人。
徐真不解刀,也不受縛,單獨關押,不與其他囚徒混居,日常飲食按使節規格來供給,並未受到任何的刁難與虐待,只是不准任何人來探視。
負責看守徐真的獄吏是個六十餘歲的老者,徐真從未見過他開口說話,也未見過任何人與之交談,想來是個啞巴。
老啞巴只是笑,對誰都是一臉的和氣,以致於誰也不忍心欺負他,據說他在邏些城當獄吏已經有很多個年頭了,獄吏人來人往,據說當年和他入職的一位獄吏,早兩年才從政務大臣的位置上退下來,而他卻仍舊守著這座牢獄。
吐蕃只有青稞酒和馬奶酒,不似大唐,有三勒漿、劍南燒春等諸多名酒,小案几上擺著幾樣小菜,還有幾張酥脆的胡餅,徐真朝啞巴招了招手,後者嘿嘿咧嘴笑,朝外面掃了幾眼,這才坐在了徐真的對面。
徐真不好酒,與這個老啞巴也沒辦法交談,他也不知道啞巴能不能聽懂他的話,他甚至懷疑啞巴還是聾的,但這並不妨礙他佩服這個老啞巴。
人生最難之事,莫過於從一而終,無論這位老啞巴是生活所迫,還是其他原因,能夠當大半輩子的獄吏,已經足夠贏得徐真的敬意。
老啞巴也不客氣,該吃吃,該喝喝,無論徐真說什麼,他就只是笑,徐真曾經開玩笑地問他喜歡吃些什麼,好讓人下次送點來,那老啞巴也只是笑。
不過無論徐真吃什麼,都預留了老啞巴一份,而老啞巴也是無論什麼都喜歡吃,這段時間徐真的酒水,可都便宜了這老啞巴。
「老黑,看你面相輪廓,該是中原人士,可又生了一雙碧眼,髮色看似枯黃,實則該是赤紅之色才對,你到底是哪裡人?」
徐真吃得不多,只是想讓老啞巴作陪,消遣一些寂寞,他知道自己的問題從來就得不到回答,但他還是忍不住問起,希望能夠從老啞巴的表情反應之中得出答案來,可惜老啞巴只是笑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比劃著示意自己聽不到也說不了。徐真也毫不介意,他不是覺得老啞巴有何特別之處,而是整座牢獄,也就只有這個老啞巴能夠接觸得到,能夠說話的也只有這個老啞巴。
用了飯之後,老啞巴收拾東西出去了,徐真就坐下來,修練《增演易經洗髓內功心法》,小半個時辰之後,氣息和經脈調和平穩,就開始在草榻上擺出各種超乎常理的姿勢,關節反張扭曲,練起瑜伽術和七聖刀秘法。
他已經讓祿東贊將密信送交給凱薩,若他們能夠按照密信上的囑託,準備充足,徐真根本就不需要擔心喬邦色會對他下毒手,不過這畢竟是初次嘗試,他心裡也是沒底。
好在這些功法他每日勤練不輟,並非臨時抱佛腳,多少也生出一些自信來,修練完畢之後已經是兩個時辰之後了,牢獄裡火光長明,卻不見天日,無人滴漏打更,老啞巴又無法開口說話,徐真只能用炭條在牆上計算時日。
牢中無事,早先他還翻來覆去的思考分析吐蕃的局勢,過得兩日已經弄得透徹,也就不再去想這種事情,也睡不了多少,其餘時間都用來修練。
這兩年雖然少了征戰,但並未能夠靜下心來鑽研自己的身手和刀法以及幻術,這些時日正好用來修習。
看著精神還足,他就解下腰間的長刀,在牢中練起刀法來。
他的刀法得過李德獎和周滄的指點,而後又得了李靖的真傳,李德獎的刀法大氣磅礴,充滿了江湖人的灑脫豪氣;周滄的刀法霸道至極,大開大合,毫無花哨,只求殺傷;李靖的刀法卻張弛有度,蒼涼而不失儒雅。
反正有的是時間,徐真一遍一遍練著,居然有些集百家精華於一身的意思,慢慢將三種刀法精髓凝聚提煉,於刀法一道,又有了新的領悟。
正練著刀,門鎖卻輕微響動,若是平日裡,徐真定然會第一時間發現,可如今他沉浸在刀法的領悟當中,居然沒有停下來。
老啞巴如墓穴之中躺了幾百年的乾屍,悄然無聲走了進來,他的臉上仍舊帶著憨厚之極的笑容,可當他看到徐真手中那柄刀的時候,笑容卻凝固了起來,雙眸陡然亮起一團火,而後又很快消失,只剩下臉上那標誌性的笑容。
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徐真練刀,也第一次見到徐真將這柄長刀拔出鞘來,徐真雖然對他沒有任何戒心,但修練秘法和刀術,都是夜深人靜的時候,若非老啞巴收到公文,見得上頭要押徐真赴刑場,他也不會趁夜來支會徐真。他在牢獄之中呆了太久,這座牢獄就是他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對於這個老人來說,實在太過陌生。
然而徐真的坦誠相待,讓他看到了一個人的影子,而徐真練刀的時候,讓他更加確定,徐真跟那個人有著莫大的關聯,因為徐真所練刀術,蘊含著那人刀術的精髓!
而讓老啞巴更加吃驚的是,徐真的手中握著的,是另一個人的長刀,這長刀和徐真的刀術,讓他回到了極為遙遠的記憶之中,回到了那個兵荒馬亂、英豪與梟雄四起並出的年代,是徐真,讓他再次回想起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或許是因為心神受到了衝擊,他的腳步也變得有些沉重,腳步聲吸引了徐真的注意,徐真停下動作,見得老啞巴去而複返,不由疑惑問道。
「老黑,這麼晚了,來找我有事?」
老黑嘴唇翕動了幾下,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的笑容消失了,用手指了指徐真,又將手刀在自己的脖頸上抹了幾下,徐真知道,這老黑是來提醒自己,喬邦色終於要殺他徐真了。
徐真的眼眸陡然黯淡下去,但很快又明亮了起來,苦笑著搖了搖頭,向老黑拱了拱手表示感謝。
見老黑沒走,而是好奇地盯著自己的長刀,徐真遂將長刀倒轉過來,刀柄遞了過去。
「給你看看?這可是我機緣巧合得到的寶刀,後來得了大唐皇帝陛下的刻字,這可是殷開山公的刀,那是一位大英雄哦,不過我對他的事蹟也不是很瞭解,只是到現在我還記得,當大唐的太宗文皇帝見到這把刀的時候,他可是偷偷掉眼淚的咧......」
徐真還在叨叨著這把刀的來歷,老黑卻將刀捧在手中,伸出二指來彈了彈刀刃,又撫摸著狹長的鋒刃,摩挲著刀柄上的刻字,心頭湧起無盡的感傷,表面上卻保持著一個異域老獄吏該有的好奇表情。
「老黑,我突然想喝酒了,你能搞點好酒小菜來,咱爺兒倆好好喝一場嗎?」徐真咂了砸嘴,朝老黑狡黠一笑,這才想起老黑聽不到,就做了個仰脖飲酒的動作。
老黑回過神來,將長刀還給徐真,嘿嘿一笑,點點頭就出去找酒菜去了。
徐真與老啞巴在黑獄之中喝斷頭酒之時,司法大臣琴梭羅正在紅山腳下指揮工匠搭建行刑台。
自從喬邦色挾持芒松芒贊而攝政之後,琴梭羅也成為了重臣,一應主和派被他誣以各種罪名,紛紛斬除,領主們擁兵自重,圍剿之時少不了一番血戰,整個吐蕃烏煙瘴氣,血雨腥風攪動不止。而經過這段時間的清剿和拉攏、威逼利誘和安撫之後,吐蕃的局勢也趨於平定,喬邦色也終於等到了機會,殺死徐真,以激起大唐的怒火!
他很清楚,徐真並非殺死安兒喬的元兇,殺不殺徐真,其實並不重要,按理說,他已經掌控了吐蕃的局勢,主動交好大唐,這才是明智之舉。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他雖然利用兒子之死,成功掀起了內戰,琴梭羅又利用宮裡的內應,害死了器宗弄贊,成功將芒松芒贊推到了王位之上,自己則獨攬大權,可民心卻不在他這一邊。
若他不殺徐真,則自己當初起兵反叛就沒有正當的名義,而且與大唐友好往來之後,吐蕃就會步入正軌,民生得以恢復,沒有外患之後,吐蕃國內的派系和領主力量,就會再次對他發動挑戰。
是故他需要與大唐發生衝突,在大唐的強大軍事力量震懾之下,吐蕃各部族的領主才會凝聚在他的手下,一同抗擊大唐,這樣他才能趁機奪取這些力量。
從這個層面來看,徐真這個大唐的鎮軍大將軍、上柱國,就必須要被殺死,而且還要死得很轟動,死得人盡皆知!
自從當上了司法大臣之後,琴梭羅也算是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昨夜才有一位西北領主送了兩名天竺孿生少女,春風一度並蒂蓮,滋味不足為外人道也,見得刑場搭建得差不多了,他就在五名衛士的簇擁之下,坐車回府去了。
這五名衛士都是從王城禁軍之中抽調出來的精銳,乘騎大馬,披掛鐵甲,既能護衛周全,也能權當依仗,可謂威風十分。
領頭的衛士長乃喬邦色的嫡系人馬,從藏藩調到王城來的,趾高氣揚,臉上帶著不可一世的冷笑,似乎自己比車裡的琴梭羅還要威風。
車隊從紅山腳下繞了過去,再拐幾個彎就能夠進入街道,兩邊的楓林窸窸窣窣,夜風習習,驅散了白日的悶熱,讓人有些發涼。
一片鵝掌一般的葉子從衛士長的眼前飄落,他的目光發自本能被吸引到葉子之上,待得葉子悠悠落下,他才看到一點寒芒,如夜空之中的暗星一般,在他的視野之中慢慢變大!
第二百四十二章 悲情神子押赴刑場
左黯心中很是愧疚,因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師父,直到師娘凱薩從祿東贊的手中得到了師父的密信,他才生出一股動力來。他很清楚師父的能力,但對於師父的壓箱底絕學,仍舊有些看不透,密信分為兩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只有師娘凱薩才知曉內容,因為那是用祆教密文寫的。
師娘交給他的任務不算太簡單,但卻是左黯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帶著寶珠來了。
他們二人早早就隱藏在了楓林之中,如同行走於人間的鬼魅一般,入夜一直潛伏到現在這一刻,讓他們彷彿與楓樹融為一體,連自己都能夠感受到楓樹的根在吸收水分,楓葉正在吐露芳香一般!
目標車隊緩緩而來,五名衛士都是禁軍精銳,雖然他跟寶珠都深諳刺殺之道,但仍舊不敢大意。
當那片楓葉落下去,正好遮擋了衛士長視野之時,左黯開始動手了!
他如靈猴一般從樹上倒吊下來,借助落勢,激發出一柄飛刀,他的飛刀深得徐真的傳承,雖然不如徐真那般充滿了隨手而就的靈性,但卻是千錘百鍊,例無虛發!
「噗嗤!」
飛刀瞬間洞穿衛士長的眉心,那人的手還按在刀柄之上!
正因為飛刀能夠做到無聲無息,左黯才選擇用飛刀,而不用威力更大的暗弩,為了今夜的計畫,他和寶珠研究了好幾套刺殺方案,今夜若失手,師父就會性命不保,如此關鍵時刻,他又豈敢大意。
衛士長還未落馬,左黯就已經鬆開倒吊在樹上的腳背,身子如俯衝到水面又爬升起來的翠鳥,在衛士長的頭頂一撐,落到了車廂頂部,腳尖一點,整個人平平掠過,雙刃在手中如風輪一般旋轉,而後倏然交叉,車廂後面左邊的護衛已經被雙刃剪掉了人頭!
右邊那一名剛剛抽出腰刀來,左黯的腳掌已經踢到了他的心窩,那人也是機警到了極點,慌忙拍在馬鞍上,整個人不顧形象地摔落馬下,扭頭看時,車廂右側的馬背上,那名禁軍袍澤耷拉著腦袋,鮮血卻蓄滿了鹿皮靴子,而後溢出來,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上!
他反手按在地面上,撐著泥地,身子整個彈了起來,緊握刀柄,抽出狹長的寬背窄刃大刀,然而剛剛抽出刀來,那刀卻掉落在地,連同他的半截手臂!
這人還未來得及喊痛,半截刀頭已經從他的口中穿刺出來,直到刀刃抽走,他噗通悶響著落地,露出身後那少女宜嗔宜喜的調皮臉蛋來。琴梭羅正微微閉目,蓄養一下精氣神,以便回府之後好好疼一疼那對天竺姐妹花,他下意識地摸了摸手袖裡的胡僧藥丸子,想起這丸子的驚人功效,一顆邪惡的心頓時火熱難耐。
正走著,車子突然顫了一下,而後又繼續往前,他皺了皺眉頭,拉開車簾子,不耐煩地問了一句:「怎麼回事!」
沒有回應,前後左右五匹馬的馬背上,空空如也,他的心頭頓時一緊,空氣中瀰散著濃濃的血腥味,他下意識就要衝出車廂,然而剛剛有所動作,卻又無奈坐了回去,因為他的咽喉之上,正頂著寒芒閃閃的刀尖!
「嘿嘿嘿......」
眼前的少年郎露出人畜無害的笑容,一如鄰家的大小子,這個臉上有疤的小子,不正是祿東贊府上,阻撓他擒拿徐真,還將捕頭的手指切下來的那個小子嗎?
他想大聲呼救,可根本就沒有那個機會,因為他能夠感受到左黯眼中的殺意,若自己開口,哪怕只是吞一吞驚駭的口水,說不得都要被一刀刺死。
寶珠跳上車來,與左黯相視一笑,二人如同配合默契的雌雄大盜,嘿嘿笑著,相互擊掌,若非剛剛他們才殺死了五名禁軍精銳,琴梭羅還以為這兩位只不過是稚氣未脫的小情侶罷了。
車子很快就停了下來,中途又上來了一個更加清麗可人的大唐娘子,只聽左黯對那小娘子說道:「小師娘,這人就交給你了......」
來者正是張素靈,只見她打量了琴梭羅一番,又用眉筆在他的臉上勾勒出一些長短線條來,琴梭羅心頭忌憚,不敢開口,因為雖然車裡這幾個都是活生生的俊男美女,但他們看著琴梭羅的目光,似乎都像在看一件死物!
過得片刻,一個黑壯的帶刀大漢帶著四個人從道旁鑽了出來,他們的身上穿著的,正是被殺死的那些禁軍精銳的衣甲!
其中一人身材高挑,讓人印象深刻的,卻是一頭遮不住的金髮,一雙碧眼在夜色之中如貓一般熠熠生輝。
「師娘,都準備好了...」左黯對凱薩如此說道。
凱薩看了看車廂內的情況,對偽裝成衛士長的周滄說道:「回刑場!」
徐真的人手幾乎全部都出動了,就除了深宮之中的李無雙,此時的她也是憂心忡忡,她無法直接參與計畫,心裡對徐真頗感愧疚。她嫁給器宗弄贊的時候,這位吐蕃英主已經垂垂老矣,對尺尊公主又最是寵愛,還有另外兩位吐蕃王妃等著寵幸,是故對李無雙從來都是不冷不熱,到了後來,吐蕃流行疫病,尺尊公主將疫病傳染給了器宗弄贊,後者更不敢與其他王妃親近,終究沒有動李無雙的身子。
如今器宗弄贊莫名其妙死在了叛亂之中,李無雙對此也沒有過多的憂傷,以她的身份地位,喬邦色自然不敢亂來,若無喬邦色的攝政,或許她還能夠在宮中保有一絲地位,然而以現今之形勢,估計她就只能守著藏王陵,餘生都在守活寡之中度過了。
當然了,如果大唐帝國要將她接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她不過是個宗室女,李治又怎麼可能特意召她回大唐?
若徐真此次能夠逃脫生天,或許施以妙計,來個偷天換日,說不定真的能夠將她和孩子帶回長安,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若凱薩他們的計畫不成功,徐真連這次劫難都逃不過,又何來以後?
她雖然不接觸政務,但從宮中傳聞也可以知道,這一次對徐真行刑,可謂聲勢浩大,而且喬邦色為了使行刑更具威懾力,居然放棄了斬首和絞刑,而是沿用古法,對徐真實行車裂,也就是五馬分屍!
以往極為難熬的寂寞深夜,就在李無雙的擔憂之中悄悄溜了過去,待得天亮之時,有宮人來傳召,說是贊普要她隨駕觀看行刑,李無雙一顆心都懸了起來。
芒松芒贊不過是兩三歲的孩童,連說話走路都不太順溜,所謂傳召,不過是喬邦色的意思罷了。
若只帶芒松芒贊出面,他喬邦色還怕民眾說他獨斷專權,是故將李無雙和另外兩位王妃都帶上了。
器宗弄贊死後,尺尊公主病情急劇惡化,如今也是奄奄一息,所剩時日無多,瀕臨彌留,就算喬邦色想帶上她,也不太可能做得到了。
布達拉宮的紅山腳下,行刑台極為高大,周圍遍佈禁軍,估計是擔心有人來劫法場,而台下人頭湧動,用人山人海已經無法形容當時的盛況。
喬邦色刻意宣揚,徐真在民眾之中有有著如同神子一般的聲望,非但整個邏些城的人,連諸多領主的領土上的人們都提前趕了過來,其中更是出現了諸多他國使節,諸如泥婆羅和天竺等國的使節團,以及一些宗教團體的教眾,全部都到場圍觀。徐真這位祆教葉爾博,阿胡拉之子,在宗教界可謂名聲鼎沸,作為大唐帝國的將軍,他雖然受到了朝堂文官們的傾軋,但在海外諸國,他的威名卻不曾黯淡,關於他的事蹟和戰功仍舊傳唱不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今日的行刑可謂震驚天下,使得前來觀看的人擠滿了整個紅山的山腳。
好在喬邦色和琴梭羅提前做了準備,將行刑台搭建得高大無比,天氣又晴朗,縱使遠隔二三裡,都能夠清楚地看到行刑的場景。
喬邦色高坐於行刑台的上方,贊普依仗就在身側,芒松芒贊由吐谷渾妃蒙潔墀嘎抱在懷中,如李無雙等三名先王的王妃,卻只能稍稍靠後,這使得喬邦色的權勢欲望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高昂著頭顱,微微抬起手來,身邊的人就吩咐了下去。
一輛囚車嘎吱嘎吱的碾壓著地面,從黑牢的方向遠遠而來,沿途的民眾紛紛發出驚嘆的聲浪,而後又很快沉寂下來。
他們,在用沉默,向徐真致敬。
在吐蕃這樣一個虔誠的國度,連徐真自己都無法想像得到,自己的事蹟擁有著多麼巨大的影響力,就如同贊普的化身都能夠擁有極高的人望一般,就如同有人相信器宗弄贊死後,化為一道光芒,融入到了大昭寺的佛像之中一般。
連如同安兒喬這樣的化身都有人信服,更何況是展現過「神跡」的徐真。
在他們的眼中,徐真就是行走於人間的神使,雖然他們並非祆教的信徒,但他們卻同樣膜拜著徐真,因為有徐真,才讓他們看到,自己所信仰的東西,並非虛無縹緲的。
祆教能夠擁有徐真這樣的大神力者,佛宗為何就不能有?
全場數萬人靜悄悄地注視著那輛緩緩而上的囚車,囚車很高大,徐真能夠站立起來,但他選擇了盤膝靜坐。
他將自己的東西全部都交托給了老黑,因為老黑是他被押走之前,唯一能見到的一個人,他不知以後還能不能找得著老黑,但他發自內心地感到安心。
第二百四十三章 祆教神子浴火重生
人生自古誰無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將軍百戰得了馬革裹屍,文臣大士口誅筆伐固是青史留名,皇家貴胄多少彪炳春秋,而販夫走卒碌碌終老,一如秋蟬無人知曉。
老黑終覺死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活著才艱難,這些年來若非他還心有所執,早已老死山林了。此時他捧著手中的包囊,遠遠跟在囚車的後面,看著囚車之中那傲然而立的身影,心裡卻想著極其遙遠的年歲裡,同樣見過如此臨危而不亂的泰然之人。
當喬邦色遣人詢問徐真死前有何要求之時,徐真並無特別的要求,只說自己乃祆教的使者,需要穿上祆教的聖袍,死後希望能夠受到祆教式樣的葬禮。
這樣的要求簡直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祆教之人並非只是拜火,他們崇拜風火水土,是故死後只能舉行天葬,讓兀鷹吃掉自己的屍體,徐真被五馬分屍之後,這葬禮也省事多了。
「給他做一件風光華麗一些的聖袍,我就是要讓他死得體面,死得轟動!」喬邦色如是吩咐。
於是,翌日的早晨,王宮裡的尚衣織娘就命人將這套聖袍送到了黑獄裡來。
吐蕃人喜紅黃之色,不似大唐以玄黑為貴,徐真這件聖袍呈現極為難得的火紅之色,上面用金線紋繡烈焰飛天紋路,善神阿胡拉馬茲達的雙翼也改成了烈焰一般的凰鳥樣式。
古時染料多取自於天然,色澤偏淡,染色技術並不高明,想要豔麗一些的顏色極為不易,徐真這套火紅色的聖袍,可是賺足了眼球。
加上他身材高挑挺拔,豐神俊朗,長髮隨意披散下來,只用一個軟絲繩隨意挽著,一字鬍修剪得乾爽整齊,哪怕立於囚車之中,都似頂天立地,讓人覺著,漫說囚車,就算是房屋宮殿,連那天上的雲朵,都無法壓挨他半寸。
在場的祆教徒紛紛跪拜下來,而後張開雙臂,高聲唱著祆教的聖經,用這樣的方式,送別他們的阿胡拉之子。
囚車來到高臺之下,護送的禁軍打開囚車,徐真下車之後,還報以微笑,點頭表示感謝,那禁軍微微一愕,慌忙回了徐真一禮,這一幕落在所有人的眼中,就彷似那禁軍也被徐真的氣節所折服一般。
臺上的喬邦色冷笑一聲,擺手示意自己的親信蒙多兒魁可以開始行刑了。
蒙多兒魁本是喬邦色領地的小頭人,他本以為喬邦色攝政之後,自己能夠當上大臣,可沒想到卻讓琴梭羅搶了先,正鬱悶之際,喬邦色遣人來召,說是琴梭羅染了疫病,已經在府邸隔離,無法主持行刑,是故讓蒙多兒魁代為行事。
在這樣的大場面上露臉,處死一名傳奇人物,對於蒙多兒魁而言,自是好事一樁,他素知喬邦色的心性,既然要辦得天下轟動,他自然用心做事,於是將琴梭羅原先裝備的五匹駿馬,改成了五頭戰象!用大唐使節徐真帶來的戰象,處決大唐使節徐真,這樣才夠轟動,才足夠激怒大唐!
他往台下掃了一眼,徐真的那些唐國護軍都聚在了一起,但他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仇恨目光,他們的悲憤,他們的無奈,都落入諸多圍觀者的眼中,這讓行刑變得更加的悲壯。
「徐大將軍,請吧。」蒙多兒魁陰冷著聲音,皮笑肉不笑地做了一個請的姿勢,徐真微微點頭,帶著微笑走到了高臺中央。
他的腳步很穩重,皮靴在木板上磕出聲響,似乎每一步都直接敲擊在所有圍觀者的心頭一般,他似有意無意地掃了一眼自己腳下的位置,而後站定,張開雙臂,一副大義凜然,任由宰割的姿態。
人們多麼希望徐真能夠說些什麼,振臂高呼也罷,輕聲告誡,留下隻言片語也好,他們之所以如此安靜,就是希望徐真在死之前,能夠留下一些神啟,或許過了千百年之後,仍舊有人會談起這場不應該出現的處刑。
然而徐真沒有說半句話,他只是保持著有些冷漠卻又有些詭異的微笑,似乎死亡,是他嚮往的最好歸宿。
他緩緩張開了雙臂,而後昂起頭來,笑容凝固了,眉頭開始緊鎖,變得悲傷,似乎為了這人世間數不清的無知人們而悲憫,他的嘴唇在翕動,低聲哭訴,似乎在與天上的善神對話。
所有人都側耳傾聽,希望能夠聽到他在說些什麼,人們的情緒開始躁動起來,他們開始慢慢往高臺這邊湧來,有序而安靜。
喬邦色臉色一變,生怕台下的群眾會發生暴亂,也生怕有人會趁亂劫法場,禁軍們稍稍後退,緊握刀柄的手掌開始冒汗。
都說宰相難及獄吏貴,落難的宰相到了牢獄之中,也只能忍氣吞聲,然而徐真不是尋常的大唐使節,他是一個神話,無論在天竺、泥婆羅或是吐蕃,他的事蹟直至今日仍舊在不斷傳唱。
哪怕這些獄吏都是喬邦色的人,也不敢虧待徐真,更漫說這些獄吏乃是邏些城的公人。
徐真不解刀,也不受縛,單獨關押,不與其他囚徒混居,日常飲食按使節規格來供給,並未受到任何的刁難與虐待,只是不准任何人來探視。
負責看守徐真的獄吏是個六十餘歲的老者,徐真從未見過他開口說話,也未見過任何人與之交談,想來是個啞巴。
老啞巴只是笑,對誰都是一臉的和氣,以致於誰也不忍心欺負他,據說他在邏些城當獄吏已經有很多個年頭了,獄吏人來人往,據說當年和他入職的一位獄吏,早兩年才從政務大臣的位置上退下來,而他卻仍舊守著這座牢獄。
吐蕃只有青稞酒和馬奶酒,不似大唐,有三勒漿、劍南燒春等諸多名酒,小案几上擺著幾樣小菜,還有幾張酥脆的胡餅,徐真朝啞巴招了招手,後者嘿嘿咧嘴笑,朝外面掃了幾眼,這才坐在了徐真的對面。
徐真不好酒,與這個老啞巴也沒辦法交談,他也不知道啞巴能不能聽懂他的話,他甚至懷疑啞巴還是聾的,但這並不妨礙他佩服這個老啞巴。
人生最難之事,莫過於從一而終,無論這位老啞巴是生活所迫,還是其他原因,能夠當大半輩子的獄吏,已經足夠贏得徐真的敬意。
老啞巴也不客氣,該吃吃,該喝喝,無論徐真說什麼,他就只是笑,徐真曾經開玩笑地問他喜歡吃些什麼,好讓人下次送點來,那老啞巴也只是笑。
不過無論徐真吃什麼,都預留了老啞巴一份,而老啞巴也是無論什麼都喜歡吃,這段時間徐真的酒水,可都便宜了這老啞巴。
「老黑,看你面相輪廓,該是中原人士,可又生了一雙碧眼,髮色看似枯黃,實則該是赤紅之色才對,你到底是哪裡人?」
徐真吃得不多,只是想讓老啞巴作陪,消遣一些寂寞,他知道自己的問題從來就得不到回答,但他還是忍不住問起,希望能夠從老啞巴的表情反應之中得出答案來,可惜老啞巴只是笑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比劃著示意自己聽不到也說不了。徐真也毫不介意,他不是覺得老啞巴有何特別之處,而是整座牢獄,也就只有這個老啞巴能夠接觸得到,能夠說話的也只有這個老啞巴。
用了飯之後,老啞巴收拾東西出去了,徐真就坐下來,修練《增演易經洗髓內功心法》,小半個時辰之後,氣息和經脈調和平穩,就開始在草榻上擺出各種超乎常理的姿勢,關節反張扭曲,練起瑜伽術和七聖刀秘法。
他已經讓祿東贊將密信送交給凱薩,若他們能夠按照密信上的囑託,準備充足,徐真根本就不需要擔心喬邦色會對他下毒手,不過這畢竟是初次嘗試,他心裡也是沒底。
好在這些功法他每日勤練不輟,並非臨時抱佛腳,多少也生出一些自信來,修練完畢之後已經是兩個時辰之後了,牢獄裡火光長明,卻不見天日,無人滴漏打更,老啞巴又無法開口說話,徐真只能用炭條在牆上計算時日。
牢中無事,早先他還翻來覆去的思考分析吐蕃的局勢,過得兩日已經弄得透徹,也就不再去想這種事情,也睡不了多少,其餘時間都用來修練。
這兩年雖然少了征戰,但並未能夠靜下心來鑽研自己的身手和刀法以及幻術,這些時日正好用來修習。
看著精神還足,他就解下腰間的長刀,在牢中練起刀法來。
他的刀法得過李德獎和周滄的指點,而後又得了李靖的真傳,李德獎的刀法大氣磅礴,充滿了江湖人的灑脫豪氣;周滄的刀法霸道至極,大開大合,毫無花哨,只求殺傷;李靖的刀法卻張弛有度,蒼涼而不失儒雅。
反正有的是時間,徐真一遍一遍練著,居然有些集百家精華於一身的意思,慢慢將三種刀法精髓凝聚提煉,於刀法一道,又有了新的領悟。
正練著刀,門鎖卻輕微響動,若是平日裡,徐真定然會第一時間發現,可如今他沉浸在刀法的領悟當中,居然沒有停下來。
老啞巴如墓穴之中躺了幾百年的乾屍,悄然無聲走了進來,他的臉上仍舊帶著憨厚之極的笑容,可當他看到徐真手中那柄刀的時候,笑容卻凝固了起來,雙眸陡然亮起一團火,而後又很快消失,只剩下臉上那標誌性的笑容。
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徐真練刀,也第一次見到徐真將這柄長刀拔出鞘來,徐真雖然對他沒有任何戒心,但修練秘法和刀術,都是夜深人靜的時候,若非老啞巴收到公文,見得上頭要押徐真赴刑場,他也不會趁夜來支會徐真。他在牢獄之中呆了太久,這座牢獄就是他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對於這個老人來說,實在太過陌生。
然而徐真的坦誠相待,讓他看到了一個人的影子,而徐真練刀的時候,讓他更加確定,徐真跟那個人有著莫大的關聯,因為徐真所練刀術,蘊含著那人刀術的精髓!
而讓老啞巴更加吃驚的是,徐真的手中握著的,是另一個人的長刀,這長刀和徐真的刀術,讓他回到了極為遙遠的記憶之中,回到了那個兵荒馬亂、英豪與梟雄四起並出的年代,是徐真,讓他再次回想起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或許是因為心神受到了衝擊,他的腳步也變得有些沉重,腳步聲吸引了徐真的注意,徐真停下動作,見得老啞巴去而複返,不由疑惑問道。
「老黑,這麼晚了,來找我有事?」
老黑嘴唇翕動了幾下,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的笑容消失了,用手指了指徐真,又將手刀在自己的脖頸上抹了幾下,徐真知道,這老黑是來提醒自己,喬邦色終於要殺他徐真了。
徐真的眼眸陡然黯淡下去,但很快又明亮了起來,苦笑著搖了搖頭,向老黑拱了拱手表示感謝。
見老黑沒走,而是好奇地盯著自己的長刀,徐真遂將長刀倒轉過來,刀柄遞了過去。
「給你看看?這可是我機緣巧合得到的寶刀,後來得了大唐皇帝陛下的刻字,這可是殷開山公的刀,那是一位大英雄哦,不過我對他的事蹟也不是很瞭解,只是到現在我還記得,當大唐的太宗文皇帝見到這把刀的時候,他可是偷偷掉眼淚的咧......」
徐真還在叨叨著這把刀的來歷,老黑卻將刀捧在手中,伸出二指來彈了彈刀刃,又撫摸著狹長的鋒刃,摩挲著刀柄上的刻字,心頭湧起無盡的感傷,表面上卻保持著一個異域老獄吏該有的好奇表情。
「老黑,我突然想喝酒了,你能搞點好酒小菜來,咱爺兒倆好好喝一場嗎?」徐真咂了砸嘴,朝老黑狡黠一笑,這才想起老黑聽不到,就做了個仰脖飲酒的動作。
老黑回過神來,將長刀還給徐真,嘿嘿一笑,點點頭就出去找酒菜去了。
徐真與老啞巴在黑獄之中喝斷頭酒之時,司法大臣琴梭羅正在紅山腳下指揮工匠搭建行刑台。
自從喬邦色挾持芒松芒贊而攝政之後,琴梭羅也成為了重臣,一應主和派被他誣以各種罪名,紛紛斬除,領主們擁兵自重,圍剿之時少不了一番血戰,整個吐蕃烏煙瘴氣,血雨腥風攪動不止。而經過這段時間的清剿和拉攏、威逼利誘和安撫之後,吐蕃的局勢也趨於平定,喬邦色也終於等到了機會,殺死徐真,以激起大唐的怒火!
他很清楚,徐真並非殺死安兒喬的元兇,殺不殺徐真,其實並不重要,按理說,他已經掌控了吐蕃的局勢,主動交好大唐,這才是明智之舉。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他雖然利用兒子之死,成功掀起了內戰,琴梭羅又利用宮裡的內應,害死了器宗弄贊,成功將芒松芒贊推到了王位之上,自己則獨攬大權,可民心卻不在他這一邊。
若他不殺徐真,則自己當初起兵反叛就沒有正當的名義,而且與大唐友好往來之後,吐蕃就會步入正軌,民生得以恢復,沒有外患之後,吐蕃國內的派系和領主力量,就會再次對他發動挑戰。
是故他需要與大唐發生衝突,在大唐的強大軍事力量震懾之下,吐蕃各部族的領主才會凝聚在他的手下,一同抗擊大唐,這樣他才能趁機奪取這些力量。
從這個層面來看,徐真這個大唐的鎮軍大將軍、上柱國,就必須要被殺死,而且還要死得很轟動,死得人盡皆知!
自從當上了司法大臣之後,琴梭羅也算是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昨夜才有一位西北領主送了兩名天竺孿生少女,春風一度並蒂蓮,滋味不足為外人道也,見得刑場搭建得差不多了,他就在五名衛士的簇擁之下,坐車回府去了。
這五名衛士都是從王城禁軍之中抽調出來的精銳,乘騎大馬,披掛鐵甲,既能護衛周全,也能權當依仗,可謂威風十分。
領頭的衛士長乃喬邦色的嫡系人馬,從藏藩調到王城來的,趾高氣揚,臉上帶著不可一世的冷笑,似乎自己比車裡的琴梭羅還要威風。
車隊從紅山腳下繞了過去,再拐幾個彎就能夠進入街道,兩邊的楓林窸窸窣窣,夜風習習,驅散了白日的悶熱,讓人有些發涼。
一片鵝掌一般的葉子從衛士長的眼前飄落,他的目光發自本能被吸引到葉子之上,待得葉子悠悠落下,他才看到一點寒芒,如夜空之中的暗星一般,在他的視野之中慢慢變大!
第二百四十二章 悲情神子押赴刑場
左黯心中很是愧疚,因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師父,直到師娘凱薩從祿東贊的手中得到了師父的密信,他才生出一股動力來。他很清楚師父的能力,但對於師父的壓箱底絕學,仍舊有些看不透,密信分為兩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只有師娘凱薩才知曉內容,因為那是用祆教密文寫的。
師娘交給他的任務不算太簡單,但卻是左黯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帶著寶珠來了。
他們二人早早就隱藏在了楓林之中,如同行走於人間的鬼魅一般,入夜一直潛伏到現在這一刻,讓他們彷彿與楓樹融為一體,連自己都能夠感受到楓樹的根在吸收水分,楓葉正在吐露芳香一般!
目標車隊緩緩而來,五名衛士都是禁軍精銳,雖然他跟寶珠都深諳刺殺之道,但仍舊不敢大意。
當那片楓葉落下去,正好遮擋了衛士長視野之時,左黯開始動手了!
他如靈猴一般從樹上倒吊下來,借助落勢,激發出一柄飛刀,他的飛刀深得徐真的傳承,雖然不如徐真那般充滿了隨手而就的靈性,但卻是千錘百鍊,例無虛發!
「噗嗤!」
飛刀瞬間洞穿衛士長的眉心,那人的手還按在刀柄之上!
正因為飛刀能夠做到無聲無息,左黯才選擇用飛刀,而不用威力更大的暗弩,為了今夜的計畫,他和寶珠研究了好幾套刺殺方案,今夜若失手,師父就會性命不保,如此關鍵時刻,他又豈敢大意。
衛士長還未落馬,左黯就已經鬆開倒吊在樹上的腳背,身子如俯衝到水面又爬升起來的翠鳥,在衛士長的頭頂一撐,落到了車廂頂部,腳尖一點,整個人平平掠過,雙刃在手中如風輪一般旋轉,而後倏然交叉,車廂後面左邊的護衛已經被雙刃剪掉了人頭!
右邊那一名剛剛抽出腰刀來,左黯的腳掌已經踢到了他的心窩,那人也是機警到了極點,慌忙拍在馬鞍上,整個人不顧形象地摔落馬下,扭頭看時,車廂右側的馬背上,那名禁軍袍澤耷拉著腦袋,鮮血卻蓄滿了鹿皮靴子,而後溢出來,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上!
他反手按在地面上,撐著泥地,身子整個彈了起來,緊握刀柄,抽出狹長的寬背窄刃大刀,然而剛剛抽出刀來,那刀卻掉落在地,連同他的半截手臂!
這人還未來得及喊痛,半截刀頭已經從他的口中穿刺出來,直到刀刃抽走,他噗通悶響著落地,露出身後那少女宜嗔宜喜的調皮臉蛋來。琴梭羅正微微閉目,蓄養一下精氣神,以便回府之後好好疼一疼那對天竺姐妹花,他下意識地摸了摸手袖裡的胡僧藥丸子,想起這丸子的驚人功效,一顆邪惡的心頓時火熱難耐。
正走著,車子突然顫了一下,而後又繼續往前,他皺了皺眉頭,拉開車簾子,不耐煩地問了一句:「怎麼回事!」
沒有回應,前後左右五匹馬的馬背上,空空如也,他的心頭頓時一緊,空氣中瀰散著濃濃的血腥味,他下意識就要衝出車廂,然而剛剛有所動作,卻又無奈坐了回去,因為他的咽喉之上,正頂著寒芒閃閃的刀尖!
「嘿嘿嘿......」
眼前的少年郎露出人畜無害的笑容,一如鄰家的大小子,這個臉上有疤的小子,不正是祿東贊府上,阻撓他擒拿徐真,還將捕頭的手指切下來的那個小子嗎?
他想大聲呼救,可根本就沒有那個機會,因為他能夠感受到左黯眼中的殺意,若自己開口,哪怕只是吞一吞驚駭的口水,說不得都要被一刀刺死。
寶珠跳上車來,與左黯相視一笑,二人如同配合默契的雌雄大盜,嘿嘿笑著,相互擊掌,若非剛剛他們才殺死了五名禁軍精銳,琴梭羅還以為這兩位只不過是稚氣未脫的小情侶罷了。
車子很快就停了下來,中途又上來了一個更加清麗可人的大唐娘子,只聽左黯對那小娘子說道:「小師娘,這人就交給你了......」
來者正是張素靈,只見她打量了琴梭羅一番,又用眉筆在他的臉上勾勒出一些長短線條來,琴梭羅心頭忌憚,不敢開口,因為雖然車裡這幾個都是活生生的俊男美女,但他們看著琴梭羅的目光,似乎都像在看一件死物!
過得片刻,一個黑壯的帶刀大漢帶著四個人從道旁鑽了出來,他們的身上穿著的,正是被殺死的那些禁軍精銳的衣甲!
其中一人身材高挑,讓人印象深刻的,卻是一頭遮不住的金髮,一雙碧眼在夜色之中如貓一般熠熠生輝。
「師娘,都準備好了...」左黯對凱薩如此說道。
凱薩看了看車廂內的情況,對偽裝成衛士長的周滄說道:「回刑場!」
徐真的人手幾乎全部都出動了,就除了深宮之中的李無雙,此時的她也是憂心忡忡,她無法直接參與計畫,心裡對徐真頗感愧疚。她嫁給器宗弄贊的時候,這位吐蕃英主已經垂垂老矣,對尺尊公主又最是寵愛,還有另外兩位吐蕃王妃等著寵幸,是故對李無雙從來都是不冷不熱,到了後來,吐蕃流行疫病,尺尊公主將疫病傳染給了器宗弄贊,後者更不敢與其他王妃親近,終究沒有動李無雙的身子。
如今器宗弄贊莫名其妙死在了叛亂之中,李無雙對此也沒有過多的憂傷,以她的身份地位,喬邦色自然不敢亂來,若無喬邦色的攝政,或許她還能夠在宮中保有一絲地位,然而以現今之形勢,估計她就只能守著藏王陵,餘生都在守活寡之中度過了。
當然了,如果大唐帝國要將她接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她不過是個宗室女,李治又怎麼可能特意召她回大唐?
若徐真此次能夠逃脫生天,或許施以妙計,來個偷天換日,說不定真的能夠將她和孩子帶回長安,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若凱薩他們的計畫不成功,徐真連這次劫難都逃不過,又何來以後?
她雖然不接觸政務,但從宮中傳聞也可以知道,這一次對徐真行刑,可謂聲勢浩大,而且喬邦色為了使行刑更具威懾力,居然放棄了斬首和絞刑,而是沿用古法,對徐真實行車裂,也就是五馬分屍!
以往極為難熬的寂寞深夜,就在李無雙的擔憂之中悄悄溜了過去,待得天亮之時,有宮人來傳召,說是贊普要她隨駕觀看行刑,李無雙一顆心都懸了起來。
芒松芒贊不過是兩三歲的孩童,連說話走路都不太順溜,所謂傳召,不過是喬邦色的意思罷了。
若只帶芒松芒贊出面,他喬邦色還怕民眾說他獨斷專權,是故將李無雙和另外兩位王妃都帶上了。
器宗弄贊死後,尺尊公主病情急劇惡化,如今也是奄奄一息,所剩時日無多,瀕臨彌留,就算喬邦色想帶上她,也不太可能做得到了。
布達拉宮的紅山腳下,行刑台極為高大,周圍遍佈禁軍,估計是擔心有人來劫法場,而台下人頭湧動,用人山人海已經無法形容當時的盛況。
喬邦色刻意宣揚,徐真在民眾之中有有著如同神子一般的聲望,非但整個邏些城的人,連諸多領主的領土上的人們都提前趕了過來,其中更是出現了諸多他國使節,諸如泥婆羅和天竺等國的使節團,以及一些宗教團體的教眾,全部都到場圍觀。徐真這位祆教葉爾博,阿胡拉之子,在宗教界可謂名聲鼎沸,作為大唐帝國的將軍,他雖然受到了朝堂文官們的傾軋,但在海外諸國,他的威名卻不曾黯淡,關於他的事蹟和戰功仍舊傳唱不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今日的行刑可謂震驚天下,使得前來觀看的人擠滿了整個紅山的山腳。
好在喬邦色和琴梭羅提前做了準備,將行刑台搭建得高大無比,天氣又晴朗,縱使遠隔二三裡,都能夠清楚地看到行刑的場景。
喬邦色高坐於行刑台的上方,贊普依仗就在身側,芒松芒贊由吐谷渾妃蒙潔墀嘎抱在懷中,如李無雙等三名先王的王妃,卻只能稍稍靠後,這使得喬邦色的權勢欲望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高昂著頭顱,微微抬起手來,身邊的人就吩咐了下去。
一輛囚車嘎吱嘎吱的碾壓著地面,從黑牢的方向遠遠而來,沿途的民眾紛紛發出驚嘆的聲浪,而後又很快沉寂下來。
他們,在用沉默,向徐真致敬。
在吐蕃這樣一個虔誠的國度,連徐真自己都無法想像得到,自己的事蹟擁有著多麼巨大的影響力,就如同贊普的化身都能夠擁有極高的人望一般,就如同有人相信器宗弄贊死後,化為一道光芒,融入到了大昭寺的佛像之中一般。
連如同安兒喬這樣的化身都有人信服,更何況是展現過「神跡」的徐真。
在他們的眼中,徐真就是行走於人間的神使,雖然他們並非祆教的信徒,但他們卻同樣膜拜著徐真,因為有徐真,才讓他們看到,自己所信仰的東西,並非虛無縹緲的。
祆教能夠擁有徐真這樣的大神力者,佛宗為何就不能有?
全場數萬人靜悄悄地注視著那輛緩緩而上的囚車,囚車很高大,徐真能夠站立起來,但他選擇了盤膝靜坐。
他將自己的東西全部都交托給了老黑,因為老黑是他被押走之前,唯一能見到的一個人,他不知以後還能不能找得著老黑,但他發自內心地感到安心。
第二百四十三章 祆教神子浴火重生
人生自古誰無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將軍百戰得了馬革裹屍,文臣大士口誅筆伐固是青史留名,皇家貴胄多少彪炳春秋,而販夫走卒碌碌終老,一如秋蟬無人知曉。
老黑終覺死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活著才艱難,這些年來若非他還心有所執,早已老死山林了。此時他捧著手中的包囊,遠遠跟在囚車的後面,看著囚車之中那傲然而立的身影,心裡卻想著極其遙遠的年歲裡,同樣見過如此臨危而不亂的泰然之人。
當喬邦色遣人詢問徐真死前有何要求之時,徐真並無特別的要求,只說自己乃祆教的使者,需要穿上祆教的聖袍,死後希望能夠受到祆教式樣的葬禮。
這樣的要求簡直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祆教之人並非只是拜火,他們崇拜風火水土,是故死後只能舉行天葬,讓兀鷹吃掉自己的屍體,徐真被五馬分屍之後,這葬禮也省事多了。
「給他做一件風光華麗一些的聖袍,我就是要讓他死得體面,死得轟動!」喬邦色如是吩咐。
於是,翌日的早晨,王宮裡的尚衣織娘就命人將這套聖袍送到了黑獄裡來。
吐蕃人喜紅黃之色,不似大唐以玄黑為貴,徐真這件聖袍呈現極為難得的火紅之色,上面用金線紋繡烈焰飛天紋路,善神阿胡拉馬茲達的雙翼也改成了烈焰一般的凰鳥樣式。
古時染料多取自於天然,色澤偏淡,染色技術並不高明,想要豔麗一些的顏色極為不易,徐真這套火紅色的聖袍,可是賺足了眼球。
加上他身材高挑挺拔,豐神俊朗,長髮隨意披散下來,只用一個軟絲繩隨意挽著,一字鬍修剪得乾爽整齊,哪怕立於囚車之中,都似頂天立地,讓人覺著,漫說囚車,就算是房屋宮殿,連那天上的雲朵,都無法壓挨他半寸。
在場的祆教徒紛紛跪拜下來,而後張開雙臂,高聲唱著祆教的聖經,用這樣的方式,送別他們的阿胡拉之子。
囚車來到高臺之下,護送的禁軍打開囚車,徐真下車之後,還報以微笑,點頭表示感謝,那禁軍微微一愕,慌忙回了徐真一禮,這一幕落在所有人的眼中,就彷似那禁軍也被徐真的氣節所折服一般。
臺上的喬邦色冷笑一聲,擺手示意自己的親信蒙多兒魁可以開始行刑了。
蒙多兒魁本是喬邦色領地的小頭人,他本以為喬邦色攝政之後,自己能夠當上大臣,可沒想到卻讓琴梭羅搶了先,正鬱悶之際,喬邦色遣人來召,說是琴梭羅染了疫病,已經在府邸隔離,無法主持行刑,是故讓蒙多兒魁代為行事。
在這樣的大場面上露臉,處死一名傳奇人物,對於蒙多兒魁而言,自是好事一樁,他素知喬邦色的心性,既然要辦得天下轟動,他自然用心做事,於是將琴梭羅原先裝備的五匹駿馬,改成了五頭戰象!用大唐使節徐真帶來的戰象,處決大唐使節徐真,這樣才夠轟動,才足夠激怒大唐!
他往台下掃了一眼,徐真的那些唐國護軍都聚在了一起,但他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仇恨目光,他們的悲憤,他們的無奈,都落入諸多圍觀者的眼中,這讓行刑變得更加的悲壯。
「徐大將軍,請吧。」蒙多兒魁陰冷著聲音,皮笑肉不笑地做了一個請的姿勢,徐真微微點頭,帶著微笑走到了高臺中央。
他的腳步很穩重,皮靴在木板上磕出聲響,似乎每一步都直接敲擊在所有圍觀者的心頭一般,他似有意無意地掃了一眼自己腳下的位置,而後站定,張開雙臂,一副大義凜然,任由宰割的姿態。
人們多麼希望徐真能夠說些什麼,振臂高呼也罷,輕聲告誡,留下隻言片語也好,他們之所以如此安靜,就是希望徐真在死之前,能夠留下一些神啟,或許過了千百年之後,仍舊有人會談起這場不應該出現的處刑。
然而徐真沒有說半句話,他只是保持著有些冷漠卻又有些詭異的微笑,似乎死亡,是他嚮往的最好歸宿。
他緩緩張開了雙臂,而後昂起頭來,笑容凝固了,眉頭開始緊鎖,變得悲傷,似乎為了這人世間數不清的無知人們而悲憫,他的嘴唇在翕動,低聲哭訴,似乎在與天上的善神對話。
所有人都側耳傾聽,希望能夠聽到他在說些什麼,人們的情緒開始躁動起來,他們開始慢慢往高臺這邊湧來,有序而安靜。
喬邦色臉色一變,生怕台下的群眾會發生暴亂,也生怕有人會趁亂劫法場,禁軍們稍稍後退,緊握刀柄的手掌開始冒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