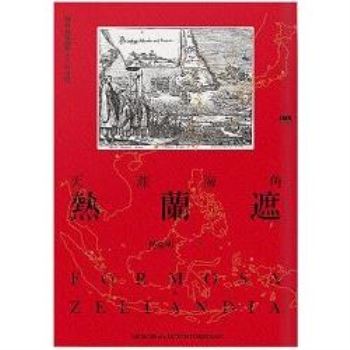楔子 愛上鬱金香
1
一個人的一生裡,到底能有幾次那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個新的自己,周遭的世界也同時就變得更有色彩、更有生機?每當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就馬上會想到我初到萊頓的那一年,尤其是那永生難忘的一個早晨。那一年起初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整個冬季,暴風雪一波一波來襲,連續好幾個月不見天日。除了上課,我幾乎把自己完全困在臨時租來的地下斗室裡,沒有想到費盡心思才得來的獎學金,竟把自己帶到這天寒地凍、昏天暗地的地方。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一個清晨,當我終於整裝就緒,爬出那地窖也似的住處,預備去迎接又一個沒有色彩的一天,迎面而來的卻是明亮耀眼的陽光和萬里無雲的藍天時,我真的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僅如此,路旁、運河兩旁高大的椴樹,也忽然都冒出了新芽。再走過幾條街,原來空曠荒蕪,被厚厚的積雪層層覆蓋的空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然幻化成一片花海,紅白紫黃,五顏六色,一行一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彷彿要一直延伸到天邊。鬱金香!全部都是鬱金香!後來我才聽說。
然後就是瑪琳娜,那健步如飛、笑容燦然、滿頭火紅長髮的瑪琳娜。那一天早晨,她彷彿就從那花叢裡蹦出來,直直地走入我的心坎裡、走入我生命的底層。看到她的那一刻,陽光灑在她那一頭飄逸的長髮上,宛如一把烈火,燒得我心慌。更讓我心慌意亂的,是她那燦然的笑容。我呆呆地看著她擦身而過,忘了呼吸。我轉身癡癡地望著,直到她消逝在街角。
那一整天,她的身影不停地在我腦海裡翻騰,胸腔裡空蕩蕩的,好像掉了什麼東西。那頭長髮、那個笑靨、那鮮豔的花圃、那溫煦的陽光,完完全全交融在一起,占據了我分分秒秒的思緒。多年來我常懷疑小說裡提到的一見鍾情是否真有可能,那一天我霍然發現,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覺得有多荒謬,愛戀之情說來就來,擋也別想擋住。
所幸那些鬱金香不是海市蜃樓,瑪琳娜也不是我心裡的幻影。她是個轉學生,剛到萊頓不久。我們很快就認識,成了朋友、好朋友,後來就不只是朋友了。2
那一年我為什麼會在萊頓?說來也許難以置信,但是我去萊頓,的的確確是為了要尋找我自己。我來自台南新化,在那個小鎮長大,媽媽在附近的高中教英文。印象中她總是那麼溫柔、漂亮,但是她少言寡語,也總是讓人摸不定她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她是小鎮裡知名醫生的獨生女,而我又是她唯一的小孩。我沒有父親,從來不知道他是誰;到了我十歲的時候,媽媽得了白血病,竟然沒多久也就過世了。幸好阿公阿嬤從小照顧我,無微不至,家裡經濟又寬裕、衣食無憂,所以我對我的童年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抱怨的。
我的問題在學校──我的長相、性格,從來就跟其他的同學很不一樣。我又高又瘦、內向畏縮、笨手笨腳、運動神經不好,難以跟人打成一片。我的一頭鬈髮、深陷的眼眶、黝黑的皮膚,又不免讓人側目。小學、中學,年復一年,同學們取笑我,叫我「番仔」。我有時不免想像,也許他們說得沒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媽媽還在的時候,從來不曾提到他,而我大概也從小就知道這是個禁忌,是個不能碰的問題。
這個天大的疑問,一直到了我高中畢業,才開始有了一點眉目。那天阿公難得休診,和阿嬤一起,帶我到台南市區一家新開的日本餐廳,去慶祝我的長大成人。飯後天色還亮,我們慢慢地走到附近的赤崁樓。到達的時候,夏日向晚火紅的太陽正緩緩地沉入大海,映照出滿天絢麗的彩霞。平常滴酒不沾的阿公,那天破例連喝了兩杯,眼睛開始有些迷茫,話也多了起來。閒談著市區市容的變化,他忽然說,「你能想像嗎?從前這裡的海岸線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恰恰就在這裡,就在這赤崁樓的邊緣。」阿嬤笑著說,「別聽他胡扯了,不都是老掉牙的事了嗎?快四百年了吧!」但是微醺的外公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從這裡一直到安平,直徑差不多五公里,整個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時就叫做台江(大港)內海、大員內海。現在全都填平了,到處都是樓房,滄海的確會變成桑田。我們管它叫番仔城的安平古堡本來叫做熱蘭遮堡,我們市中心的赤崁樓,本地人稱之為番仔樓,那時則是荷蘭人的普羅民遮城堡,『普羅文西亞』,就是省的意思;兩個城堡的名字和在一起,就是熱蘭遮省。熱蘭遮的意思是海中之地,這『熱蘭遮省』位於荷蘭的最南邊,正是由許多海島組成的。如果不知道這兩個城堡間隔著這麼大的一片內海,就很難瞭解它們為什麼會建在那裡。」
「你能想像當荷蘭人初到這裡時,他們看到的是什麼嗎?」阿公繼續說,「從這裡往東,一直到中央山脈山腳下,綿延七、八十公里,就是一整片的樹林,中間稀稀疏疏住的是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當初就被荷蘭人叫做福爾摩沙人。其中最早與荷蘭人接觸的,就是住在這大員內海四周的『四大社』—新港社、蔴荳社、蕭壟社和目加溜灣社。這其中新港社受到的衝擊最深。他們原本住在現在我們面前的赤崁城附近,後來被迫往東遷移到新市,二、三百年來又逐漸被擠了出去,繼續往東,搬到山腳下。他們的後代,有些還住在那裡,你的父親就是從那裡來的。你可以說他就正是個道道地地的福爾摩沙人。可惜他沒有那個福分看著你長大,他可真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啊!家裡那麼窮,整個村子那麼窮,大部分的小孩從小念的就是放牛班,他居然一路成績優秀,進了我們全島最頂尖的醫學院,還彈著一手好吉他!你的媽媽在大學裡認識他,他們可真是愛得轟轟烈烈!我滿心期望他畢業後到新化來,接我這個診所,可是他卻選擇到他家鄉附近的衛生所。你一歲的那個夏天,颱風之後山溪暴漲,土石流切斷了他的村子和外界唯一的道路,斷水斷糧。你爸爸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條小船,載滿了藥物米糧,衝進去救援,從此就消逝得無影無蹤。」等了那麼多年,我心裡最大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這也許就是阿公特地要給我的畢業禮物吧!原來我的確是個雜種,我父系的祖先在荷蘭人和漢人還沒來到這個島嶼之前,早就已在這一片肥沃的平原闖蕩。難怪我長得有點像菲律賓人、薩摩亞人、大溪地人、夏威夷人。我後來特地到父親的村子去探望了好幾次,但是每一趟行程都只有更增加我心裡的悵惘。那真是個貧窮得無以想像的地方。每家都只有那麼小小的一塊農地;庭院內外豬、鵝、雞、火雞,四處亂竄;幾乎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嘴裡都一直不停地嚼著檳榔,還不時隨地噴吐猩紅的檳榔汁。酗酒又是另一個不小的問題,常常一大早就會看到好幾個喝到掛的人,躺在馬路旁,不省人事。也許我的出現勾引起太多傷心往事的記憶吧,父親的爸爸媽媽,雖然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是總還是有點防備、有點疏遠。我試著要去接近他們、瞭解他們,可是我們之間,始終有那麼一條無形的,跨不過去的鴻溝。
就這樣,我變得越來越著迷於我父系先人的歷史,以及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我大概覺得,既然無法接近父親的族人,我只好從書本及古老的文件下手。雖然讓阿公傷心失望,大學醫預科讀了一年之後,我還是硬著心腸轉到歷史系就讀。又過了六年,我意外得到萊頓大學的獎學金,去研究荷蘭殖民時代的福爾摩沙。就這個題目而言,萊頓無疑是研究者的天堂。在荷蘭人統治台灣的那三十九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改革派教會留下來的資料汗牛充棟:日誌、報告、書信等等,事事物物,記載得鉅細靡遺,而且大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供學者挖掘、研究。可笑的是,為了尋根,我竟來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未完)
第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1
初識福仔的時候,我們都還是虛歲七歲的小孩。那時我隨著父親,剛從福爾摩沙搬到安海,住入那宛如城堡的鄭家莊園。安海當時是一個非常繁榮的海港,商船、艦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港岸到處都是醉眼惺忪的水手、兵丁,他們操著各地方言、不同的口音,往往雞同鴨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那一群日本浪人,更是危險,經常不知何故,就在碼頭上真槍實刀決鬥了起來;安息、天方、泰西之人,大街小巷隨處亂撞,嘰哩呱啦,大聲喧鬧,講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鄭家莊園隔著鬧區的酒家、妓院、客棧有蠻長的一段距離,倒是相當安靜。莊園四周,每天十二時辰,不分晝夜,總是有成隊的衛士巡迴守衛。這些衛士個個身材魁梧、身手矯捷,黝黑的皮膚閃閃發亮。他們有些滿臉黑鬍鬚,深陷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大得嚇人,看起來就像佛寺牆壁上常見的達摩祖師像;有些則臉部線條比較柔和,鬍鬚也較少,但是皮膚更黑,頭髮難以想像地鬈曲,一小叢一小叢地,有如佛陀頭上那些為他遮陽的小蝸牛。他們火器精良、武藝高超,日夜巡邏,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鄭家莊園因此可謂固若金湯。莊園牆裡牆外,安靜與喧鬧,仿如兩個世界。
父親的醫院則是唯一的例外。醫院位於莊園邊上,面對通往海港的小河,二十四小時沒日沒夜,隨時有水手、軍士,載著斷腿斷手、血流如注、生命垂危的傷患,溯游而上、直抵醫院。父親有如魔術師,拿出冒著一縷奇香的煙管,給他們抽上幾口,那些哀嚎慘叫的傷患竟然登時就安靜了下來,助手們隨即將之牢牢按在手術桌上。此時父親從炙熱的火爐裡抽出一支火紅的鐵棍,迅速燙上傷口。隨著傷患的聲聲慘叫,烤肉般的焦味瀰漫滿屋,噴灑的血流登時打住。有時面對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的肢體,他從牆上拿下一把大鋸子,用烈酒澆灑抹拭後,毫不遲疑地,三兩下就把該鋸的地方齊根截掉,對病人的哀號充耳不聞。福仔父親的商船、艦隊,在海上經常與海賊、「倭寇」、「佛朗機人」、「紅毛番」戰鬥,傷亡慘重,父親的生意自然也就「門庭若市」。不止如此,他還常常需要隨艦出海,在海戰的現場就近醫治。他的確就這樣子每天從早忙到晚,分身乏術,幾乎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我們的村莊四周用密不透風的刺竹林圍著;在這裡面,雞鵝豬狗,和我們這群小孩們,無憂無慮、無拘無束、四處奔跑。村裡的小孩親如兄弟姊妹,大人們不是姑姨伯叔,就是阿嬤阿公,他們呵護所有的小孩,有如己出。那是個人間樂園,至少在我的記憶裡就是如此。
1
一個人的一生裡,到底能有幾次那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一個新的自己,周遭的世界也同時就變得更有色彩、更有生機?每當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就馬上會想到我初到萊頓的那一年,尤其是那永生難忘的一個早晨。那一年起初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整個冬季,暴風雪一波一波來襲,連續好幾個月不見天日。除了上課,我幾乎把自己完全困在臨時租來的地下斗室裡,沒有想到費盡心思才得來的獎學金,竟把自己帶到這天寒地凍、昏天暗地的地方。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一個清晨,當我終於整裝就緒,爬出那地窖也似的住處,預備去迎接又一個沒有色彩的一天,迎面而來的卻是明亮耀眼的陽光和萬里無雲的藍天時,我真的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僅如此,路旁、運河兩旁高大的椴樹,也忽然都冒出了新芽。再走過幾條街,原來空曠荒蕪,被厚厚的積雪層層覆蓋的空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竟然幻化成一片花海,紅白紫黃,五顏六色,一行一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彷彿要一直延伸到天邊。鬱金香!全部都是鬱金香!後來我才聽說。
然後就是瑪琳娜,那健步如飛、笑容燦然、滿頭火紅長髮的瑪琳娜。那一天早晨,她彷彿就從那花叢裡蹦出來,直直地走入我的心坎裡、走入我生命的底層。看到她的那一刻,陽光灑在她那一頭飄逸的長髮上,宛如一把烈火,燒得我心慌。更讓我心慌意亂的,是她那燦然的笑容。我呆呆地看著她擦身而過,忘了呼吸。我轉身癡癡地望著,直到她消逝在街角。
那一整天,她的身影不停地在我腦海裡翻騰,胸腔裡空蕩蕩的,好像掉了什麼東西。那頭長髮、那個笑靨、那鮮豔的花圃、那溫煦的陽光,完完全全交融在一起,占據了我分分秒秒的思緒。多年來我常懷疑小說裡提到的一見鍾情是否真有可能,那一天我霍然發現,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覺得有多荒謬,愛戀之情說來就來,擋也別想擋住。
所幸那些鬱金香不是海市蜃樓,瑪琳娜也不是我心裡的幻影。她是個轉學生,剛到萊頓不久。我們很快就認識,成了朋友、好朋友,後來就不只是朋友了。2
那一年我為什麼會在萊頓?說來也許難以置信,但是我去萊頓,的的確確是為了要尋找我自己。我來自台南新化,在那個小鎮長大,媽媽在附近的高中教英文。印象中她總是那麼溫柔、漂亮,但是她少言寡語,也總是讓人摸不定她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她是小鎮裡知名醫生的獨生女,而我又是她唯一的小孩。我沒有父親,從來不知道他是誰;到了我十歲的時候,媽媽得了白血病,竟然沒多久也就過世了。幸好阿公阿嬤從小照顧我,無微不至,家裡經濟又寬裕、衣食無憂,所以我對我的童年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抱怨的。
我的問題在學校──我的長相、性格,從來就跟其他的同學很不一樣。我又高又瘦、內向畏縮、笨手笨腳、運動神經不好,難以跟人打成一片。我的一頭鬈髮、深陷的眼眶、黝黑的皮膚,又不免讓人側目。小學、中學,年復一年,同學們取笑我,叫我「番仔」。我有時不免想像,也許他們說得沒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媽媽還在的時候,從來不曾提到他,而我大概也從小就知道這是個禁忌,是個不能碰的問題。
這個天大的疑問,一直到了我高中畢業,才開始有了一點眉目。那天阿公難得休診,和阿嬤一起,帶我到台南市區一家新開的日本餐廳,去慶祝我的長大成人。飯後天色還亮,我們慢慢地走到附近的赤崁樓。到達的時候,夏日向晚火紅的太陽正緩緩地沉入大海,映照出滿天絢麗的彩霞。平常滴酒不沾的阿公,那天破例連喝了兩杯,眼睛開始有些迷茫,話也多了起來。閒談著市區市容的變化,他忽然說,「你能想像嗎?從前這裡的海岸線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恰恰就在這裡,就在這赤崁樓的邊緣。」阿嬤笑著說,「別聽他胡扯了,不都是老掉牙的事了嗎?快四百年了吧!」但是微醺的外公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從這裡一直到安平,直徑差不多五公里,整個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時就叫做台江(大港)內海、大員內海。現在全都填平了,到處都是樓房,滄海的確會變成桑田。我們管它叫番仔城的安平古堡本來叫做熱蘭遮堡,我們市中心的赤崁樓,本地人稱之為番仔樓,那時則是荷蘭人的普羅民遮城堡,『普羅文西亞』,就是省的意思;兩個城堡的名字和在一起,就是熱蘭遮省。熱蘭遮的意思是海中之地,這『熱蘭遮省』位於荷蘭的最南邊,正是由許多海島組成的。如果不知道這兩個城堡間隔著這麼大的一片內海,就很難瞭解它們為什麼會建在那裡。」
「你能想像當荷蘭人初到這裡時,他們看到的是什麼嗎?」阿公繼續說,「從這裡往東,一直到中央山脈山腳下,綿延七、八十公里,就是一整片的樹林,中間稀稀疏疏住的是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當初就被荷蘭人叫做福爾摩沙人。其中最早與荷蘭人接觸的,就是住在這大員內海四周的『四大社』—新港社、蔴荳社、蕭壟社和目加溜灣社。這其中新港社受到的衝擊最深。他們原本住在現在我們面前的赤崁城附近,後來被迫往東遷移到新市,二、三百年來又逐漸被擠了出去,繼續往東,搬到山腳下。他們的後代,有些還住在那裡,你的父親就是從那裡來的。你可以說他就正是個道道地地的福爾摩沙人。可惜他沒有那個福分看著你長大,他可真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啊!家裡那麼窮,整個村子那麼窮,大部分的小孩從小念的就是放牛班,他居然一路成績優秀,進了我們全島最頂尖的醫學院,還彈著一手好吉他!你的媽媽在大學裡認識他,他們可真是愛得轟轟烈烈!我滿心期望他畢業後到新化來,接我這個診所,可是他卻選擇到他家鄉附近的衛生所。你一歲的那個夏天,颱風之後山溪暴漲,土石流切斷了他的村子和外界唯一的道路,斷水斷糧。你爸爸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條小船,載滿了藥物米糧,衝進去救援,從此就消逝得無影無蹤。」等了那麼多年,我心裡最大的疑惑終於有了答案,這也許就是阿公特地要給我的畢業禮物吧!原來我的確是個雜種,我父系的祖先在荷蘭人和漢人還沒來到這個島嶼之前,早就已在這一片肥沃的平原闖蕩。難怪我長得有點像菲律賓人、薩摩亞人、大溪地人、夏威夷人。我後來特地到父親的村子去探望了好幾次,但是每一趟行程都只有更增加我心裡的悵惘。那真是個貧窮得無以想像的地方。每家都只有那麼小小的一塊農地;庭院內外豬、鵝、雞、火雞,四處亂竄;幾乎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嘴裡都一直不停地嚼著檳榔,還不時隨地噴吐猩紅的檳榔汁。酗酒又是另一個不小的問題,常常一大早就會看到好幾個喝到掛的人,躺在馬路旁,不省人事。也許我的出現勾引起太多傷心往事的記憶吧,父親的爸爸媽媽,雖然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是總還是有點防備、有點疏遠。我試著要去接近他們、瞭解他們,可是我們之間,始終有那麼一條無形的,跨不過去的鴻溝。
就這樣,我變得越來越著迷於我父系先人的歷史,以及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我大概覺得,既然無法接近父親的族人,我只好從書本及古老的文件下手。雖然讓阿公傷心失望,大學醫預科讀了一年之後,我還是硬著心腸轉到歷史系就讀。又過了六年,我意外得到萊頓大學的獎學金,去研究荷蘭殖民時代的福爾摩沙。就這個題目而言,萊頓無疑是研究者的天堂。在荷蘭人統治台灣的那三十九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改革派教會留下來的資料汗牛充棟:日誌、報告、書信等等,事事物物,記載得鉅細靡遺,而且大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供學者挖掘、研究。可笑的是,為了尋根,我竟來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未完)
第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1
初識福仔的時候,我們都還是虛歲七歲的小孩。那時我隨著父親,剛從福爾摩沙搬到安海,住入那宛如城堡的鄭家莊園。安海當時是一個非常繁榮的海港,商船、艦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港岸到處都是醉眼惺忪的水手、兵丁,他們操著各地方言、不同的口音,往往雞同鴨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那一群日本浪人,更是危險,經常不知何故,就在碼頭上真槍實刀決鬥了起來;安息、天方、泰西之人,大街小巷隨處亂撞,嘰哩呱啦,大聲喧鬧,講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鄭家莊園隔著鬧區的酒家、妓院、客棧有蠻長的一段距離,倒是相當安靜。莊園四周,每天十二時辰,不分晝夜,總是有成隊的衛士巡迴守衛。這些衛士個個身材魁梧、身手矯捷,黝黑的皮膚閃閃發亮。他們有些滿臉黑鬍鬚,深陷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大得嚇人,看起來就像佛寺牆壁上常見的達摩祖師像;有些則臉部線條比較柔和,鬍鬚也較少,但是皮膚更黑,頭髮難以想像地鬈曲,一小叢一小叢地,有如佛陀頭上那些為他遮陽的小蝸牛。他們火器精良、武藝高超,日夜巡邏,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鄭家莊園因此可謂固若金湯。莊園牆裡牆外,安靜與喧鬧,仿如兩個世界。
父親的醫院則是唯一的例外。醫院位於莊園邊上,面對通往海港的小河,二十四小時沒日沒夜,隨時有水手、軍士,載著斷腿斷手、血流如注、生命垂危的傷患,溯游而上、直抵醫院。父親有如魔術師,拿出冒著一縷奇香的煙管,給他們抽上幾口,那些哀嚎慘叫的傷患竟然登時就安靜了下來,助手們隨即將之牢牢按在手術桌上。此時父親從炙熱的火爐裡抽出一支火紅的鐵棍,迅速燙上傷口。隨著傷患的聲聲慘叫,烤肉般的焦味瀰漫滿屋,噴灑的血流登時打住。有時面對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的肢體,他從牆上拿下一把大鋸子,用烈酒澆灑抹拭後,毫不遲疑地,三兩下就把該鋸的地方齊根截掉,對病人的哀號充耳不聞。福仔父親的商船、艦隊,在海上經常與海賊、「倭寇」、「佛朗機人」、「紅毛番」戰鬥,傷亡慘重,父親的生意自然也就「門庭若市」。不止如此,他還常常需要隨艦出海,在海戰的現場就近醫治。他的確就這樣子每天從早忙到晚,分身乏術,幾乎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父親是我唯一的親人,父親的忙碌,更加深了我的寂寞。剛到安海不久的我,時時刻刻思念著我那福爾摩沙的村莊,以及我在那裡度過的,快樂的童年。父親在福爾摩沙的時候當然也很忙碌:福爾摩沙人打獵或「出草」時常常受傷,漢人們伐林闢地,也都是高危險的工作,在在都需要他的診療。做為島內技術最好的外科醫師,他又常常被請到熱蘭遮城堡,去照顧那裡的長官、兵士、商人們。所以在那裡他實在也沒有什麼時間理我,但是我有我的阿姆。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媽媽是誰,只聽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偶然在海灘上發現被沖上岸的父親,細心照料,讓他起死回生;不幸因我的出生,她竟難產過世。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說一出生就是個孤兒,但是在福爾摩沙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身為孤兒的感覺。阿姆照顧我、呵護我,無微不至;她生性爽朗快樂、渾身是勁、整天總是忙個不停,不是做飯就是洗衣,跟鄰居東家長西家短的,背後卻像又長了一隻眼睛似地,總是知道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她是村子裡的尪姨,知道什麼草藥可以治療哪種病痛,也熟知如何念誦代代相傳的咒語,來驅趕邪靈,祈求豐收及狩獵出草順利。
阿姆的另一個重要的工作,是主持每隔幾個月就要舉行一次的夜祭。夜祭都是在月圓的夜晚舉行,到時她帶領村內老少婦女,身披及地白袍,聚集於公廨前的廣場,圍成一圈,唱起古老哀婉的牽曲。隨著那周而復始的歌聲,她們緩緩起舞,徹夜不休,直至精疲力竭。這時往往就會有兩三位舞者被神明附身,忽然倒下,進入恍惚出神的狀態,開始喃喃自語。她們說的話除了阿姆,沒人聽得懂,所以阿姆就是神明的代言人。但是神明說什麼我們小孩子們並不在意,在那些涼爽的月圓之夜,我們就在舞者圍成的圓圈內,跟著隨興而舞。重複的鼓聲,渾厚悠揚的鼻笛音樂,漸漸讓我們也都感覺到神靈的存在;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居然就開始有了那麼一種感覺,覺得那輪明月一直在向我們靠近,我們就消融在月亮娘娘溫柔的擁抱裡。我們的村莊四周用密不透風的刺竹林圍著;在這裡面,雞鵝豬狗,和我們這群小孩們,無憂無慮、無拘無束、四處奔跑。村裡的小孩親如兄弟姊妹,大人們不是姑姨伯叔,就是阿嬤阿公,他們呵護所有的小孩,有如己出。那是個人間樂園,至少在我的記憶裡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