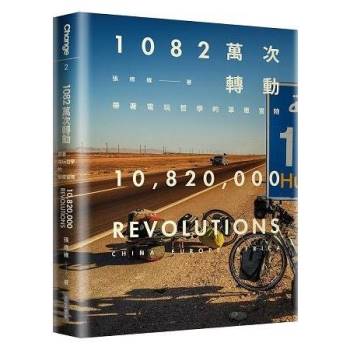〈人跡少的那條路〉
我站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雨依然不停下著,望著眼前似乎永無止境的爛路,滿身泥濘,又冷又餓。怎麼又來了?我開始細數這一生中把自己搞成這麼狼狽的種種蠢事。難道這是我的命嗎?這次又是怎麼發生的?才出發第三天哪!我想起昨天做的那個愚蠢的決定……
從地圖上看,從中甸到稻城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是先沿著路況最好的214國道,再從得榮往東,第二條是必須把Google Map放得很大才看得到的山路,途中得依序翻過海拔三千九百公尺的小雪山、四千三百公尺的大雪山,以及大魔王──四千七百公尺的無名雪山(好像天龍八部的無名僧,最厲害的都沒有名字)。
第二條從地圖上看起來近多了,照里程算好像可以快一天,不如走這條吧。我想起美國詩人羅勃‧佛洛斯特的〈未竟之路〉:「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選擇了人跡較少的一條,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下次如果有人跟你這麼說,請你跟我這樣做:第一,高舉你的左手;第二,用力把他的頭巴下去!走小路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啊……
之前在台灣騎腳踏車最高也只到了三千兩百七十五公尺的武嶺,就連登山也才爬到三千五百公尺左右,這次的行程整個是越級打怪。我也沒想太多,打電話問了公路養護單位,知道這條路沒有受到前幾天的地震影響,照常通行。在路邊的藥局買了盒紅景天膠囊,水果攤買了些香蕉和蘋果,就出發了。只是天氣不太好,陰陰的,一直飄著細雨,氣溫雖在十度以上,但感覺很冷,讓我得把風衣穿上。
這天的計畫是翻過小雪山之後投宿翁水村,看起來高度才增加大概七百公尺而已,就沒有太精實,混到快十點才出發。結果大失算,爬到接近三千六百公尺的高度後,竟然一口氣下降到兩千八百公尺高,才繼續上攻到三千八百,總爬升高達一千八百公尺,爬得我頭昏眼花,大腿幾度瀕臨抽筋。所幸路況還算可以,大部分都是柏油路或水泥路雖然坑坑洞洞,但沒啥大礙。儘管如此,還是比預計時間還晚四小時到達翁水村,天都已經全黑了才在路邊隨便找了間旅店,要了個床位,二十塊人民幣,入住後點了一兩樣炒菜,吃飽喝足,躺在床上拉完筋,沒多久就沉沉睡去。隔天本想早點起床趕路,但是因為太累睡到八點多。目標當然就是翻過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大雪山後下滑,然後直衝稻城。高度才增加五百而已,總里程也才大概八十公里,上山四十公里,時速抓七公里好了,六小時攻頂,下滑時速抓個二十五公里已經很客氣了。這樣算起來八小時左右便可完成今天任務,時間綽綽有餘。
但打開房門一看,心裡一沉,雨勢變大了,看看天空,看樣子會下一整天。但是不出發不行,咬著牙還是上路了。我超級討厭在雨天騎車,天雨路滑增加風險,而且雨水打在臉上真的很痛,水氣加上泥沙黏附在車上以及行李上,本來已經很重的車變得更重,騎起來只有幹。
一邊碎念一邊向前騎,騎了大概快十公里後,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傻眼了,路呢?把手機地圖拿出來看,沒錯啊,方向是正確的,只是柏油路面消失了,變成泥沙和石頭組成的off-road越野路段。沒辦法,只能硬騎了,可能這一段是在修路吧,忍一下就好。沒想到這一忍就是一個多小時,路面不但沒改善,甚至更糟,我下來牽車的頻率越來越高。
有些地方甚至已經變成池塘了,我必須用我穿著拖鞋的雙腳(對,我穿拖鞋,真不知道我腦袋裝啥),走到冰冷的泥水裡牽車通過,更多地方泥巴深達二十公分以上,我一踩就深陷其中,使勁把腳拔起來了,拖鞋卻還黏在泥土裡。我的車又相當重,輪胎像切蛋糕似的陷在裡面,不要說騎了,就連牽車都得花我吃奶力氣。一邊用力推車,後面大卡車不斷經過,有時候會夾雜一台小巴士,車上的乘客對我大聲加油,但我一點也提不起精神。這時候前面來了台四驅休旅車,整車白色的烤漆幾乎被泥水濺成土黃色,我看了心都涼了──到底前面的路是有多慘烈啊?車子停下來,一位大媽探出頭來問我要騎到哪。「我要翻過大雪山到稻城。」我說。
她聽了一臉驚恐:「這一路上八十幾公里都是這種路啊!後面的路還要再爛!」
她接著嘟囔:「真是要命,早知道不走這裡了……」
我聽了幾乎崩潰,天啊,算一算後面還有六十幾公里,如果都是這種路,我是要走上三天三夜嗎?但又安慰自己,中國人有時候說話都比較誇大,應該不會這麼慘吧……又把自己從自暴自棄邊緣拉回來,繼續前進。遇到看起來可以騎的路面就上車,但常常一下子又得下來推車。
就這樣折騰了快四小時,我才前進不到二十公里,途中超過玉山的海拔高度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時還停下來拍個照做紀念,但心裡完全沒有超越極限的喜悅。雨繼續下個不停,我又餓又累又冷,存糧已經全部吃完,全身痠痛又四肢無力,停在路邊動彈不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忽然想到,背包裡好像還有一顆蘋果!伸手一探,果不其然,在背包底部讓我翻出這一顆宛如救命仙丹的蘋果。我顧不得髒了,馬上就大咬個兩口,眼淚差點奪眶而出──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蘋果!正當我要再咬一口時,戴著厚重手套的手一滑,大半顆蘋果就這樣掉到泥巴裡。
我忽然感覺腦子裡好像有條東西斷了,我大吸一口氣,然後用盡丹田之力,大喊了一聲:
「幹!!!!!!」
那聲勢之大,整座山谷為之震動,一群鳥兒從樹林裡受驚飛起,頓時把半片天空遮住。我發洩完,比較冷靜了,自己都覺得好笑,竟然拿出相機來拍了那顆蘋果當作紀念,這以後應該會是個好故事,我心裡想。正在考慮該拿這顆蘋果怎麼辦時,我聽到「喂」的一聲。
見鬼了,這四千多公尺的深山裡,應該不會有人吧?但隨即又聽到一聲:「喂!小伙!」我順著聲音看過去,一位老先生和老婆婆站在不遠處的山坡上,更高處有一座冒著炊煙的帳篷,老先生向我招手示意我過去。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把車隨便丟在路邊,爬上了布滿碎石的山坡,跟著老先生進了帳篷。一陣暖意迎面撲來,我的眼鏡瞬間起霧。老先生示意我坐下,我發抖著把濕透的手套取下,不住地搓著手,已經麻木冰冷的雙手才開始有感覺。
老先生倒了一碗湯給我,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帶點鹹味又充滿奶油的香味,啊,這是酥油嗎,這是藏族招待客人的上品啊。隨著滾燙的湯液滑入喉嚨,到達胃部,我的身體總算開始有暖意,身體也慢慢止住發抖了。「今天才有一群騎摩托車的過去,我沒叫他們,看到你是騎自行車的才叫你。」老先生說得一口不錯的普通話。「你知道這裡是大雪山嗎?冬天是會凍死人的啊。」
我想回答,但嘴巴好像還不大靈光,只能點點頭。
他一邊搖搖頭一邊繼續說:「年輕人真是太瘋狂了,你哪裡的?」
「台……台灣。」
「喔!台灣人啊。」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脫口問道:「請問……這要多少錢啊?」我比了比手中的碗。依我在中國走跳多年的經驗,很多事情還是先講好價錢才不會有麻煩。
「不用錢!大家都是人嘛。」
我忽然愣住了,不知怎麼回應,只能猛點頭說是,臉頰一下子燙了起來,覺得問了這個問題實在很羞愧。「大家都是人。」我猜他想表達的是那種,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所應具備的美德──如果看到其他人需要幫助,不管對方是什麼身分、種族、膚色,就是要伸出援手。
他繼續說:「在這裡養牛養豬辛苦啊,現在都沒有年輕人願意做這種事了。在這山上一待就是好幾個月,要用電還得靠發電機,如果陰天的話,信號塔沒有太陽能給電,手機就沒有訊號。」
一邊講,他一邊盛了一碗糌粑粉給我,說:「加點酥油到碗裡,然後攪一攪,我手髒不好意思幫你弄,對,就是這樣,弄成一團之後就可以吃了,我們藏族都是這樣吃的。」我一邊吃著糌粑,喝著酥油,看著老先生辛苦準備餵豬的飼料,忽然覺得,他活得比很多穿得人模人樣的人都還像個真正的「人」。
我用手托著下巴小睡了片刻,感覺活力一點一滴地回到身體,看看錶,哇,都三點半了,不趕緊出發的話,天黑前可能下不了山了。再次感謝了老先生和老太太,我告別他們繼續前進。
天氣和路況沒有半點改善,即使到山頂只剩六公里的距離,我還是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抵達。終於征服標高四千三百八十六公尺的大雪山了,我的極限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拍了照後,我趕緊把所有保暖擋風的衣物全部穿上,等等溫度可能會降到接近零度,下滑時會更冷。
我以為攻頂後就解脫了,之後就是快樂的下滑了嗎……錯!錯得離譜。才「滑」了幾公尺,我已經被爛路震得四肢骨骼都要散掉,更別說腳踏車了,我真的擔心這樣下去會整台解體。好幾次還因為積水太深看不清楚路,或者不小心輾過大石、陷落大坑而差點摔車。只好又下來牽車了,沒想到比上坡更累,我不僅要隨時讓這部重達六十公斤的車保持平衡,手還得一直按著煞車避免速度太快失控,這時我的手已經冷到麻木,又因為一直用力而頻頻抽筋,才不到半小時,我又被操得幹聲連連。
這時我意識到,在天黑前我是不可能下得了山了。
現在我有兩個選擇,第一是搭便車下山,第二是隨便找個地方露營過一晚。我看看周圍的環境,感覺到處都有機會發生坍方或土石流,實在不適合久待。那攔車吧,我一邊牽車一邊不時往後望,走了快半小時,明明剛剛還有很多貨車經過,現在怎麼半台都沒有?
啊!是了,現在時間已經晚了,該通過這個路段的車早就趁天色還亮著時就走了,在這種路上開夜車簡直就是玩命。
天色慢慢變暗了,我也放棄了搭便車下山的念頭,剛好經過了一座新修的橋墩,和山壁有一段距離,就算有落石應該也砸不到我。
如果真的發生土石流,那也是命吧。
〈貼上價碼之後〉
從Paradise Lodge離開,難度更甚於從卡爾家出發。雖然理智上知道自己得繼續上路,但肉體就是抗拒暴露在毒辣的陽光、永無止境的爬坡和魔音穿腦的屁孩之中。只能安慰自己,我們已經走完百分之八十的路程,只剩最後的兩成,就能離開這個國家了。
今天的目標是往南大概八十公里的康索,德國勇腳伯納已經入境肯亞了,他寫信給我,推薦一個位於康索的「私人」營地,說是他在非洲待過最棒的,能比Paradise Lodge還棒?我們當然得去瞧瞧,於是我寫信給營地主人伯凱,說我們今天會到。
這段其實還挺輕鬆的,一開始就狂下滑個五百公尺,之後繼續上上下下,只是因為今天吃了Mefloquine,不管怎麼喝水都還是口乾舌燥,攜帶的水消耗得相當快。抵達目的地前有個大坡,在這之前尼爾的水已經喝光了,當我們到達康索時,他已經渴得受不了。
路邊有個髮型很酷的年輕人和我們打招呼,英文很流利,原來他就是營地主人伯凱。我們在路邊的餐廳坐下來,連喝兩瓶可樂,之後到附近的飯店吃飯,然後他帶我們去他的營地。
到了一看,我們都傻眼了。說是營地,也只不過是他家的後院而已,我們還得在一個大雞籠旁紮營,和前幾天的Paradise Lodge比起來簡直天差地別,我們大失所望。只是價格還算便宜,一人80 Birr,他又很熱心地騎車載我去換錢、買東西,還提供很多西南路線的建議給我們,是個不錯的年輕人,有志於發展故鄉的觀光。他那邊沒自來水,只從水桶裡裝了六公升的水給我們,不夠洗澡,我們打算用在明天的早餐和路上飲用。晚上他帶我們到村子裡的小店喝啤酒吃晚餐,我們請他喝了三瓶啤酒以示謝意。這裡的小朋友爭相讓我們拍照,之後又迫不及待想看看他們的照片,看了之後互相指指點點、哈哈大笑,可愛極了,遠離觀光區的小孩正常多了。
我不禁好奇,到底這些要錢屁孩的現象是怎麼形成的。其實老一輩的衣索比亞鄉民相當有禮貌,大概四十歲以上的長輩,如果我先點頭問好,他們甚至會脫帽鞠躬還禮。但是三十歲以下的就不是這樣了,我們還看到有媽媽教她小孩向我們喊「Money Money」,那小孩小到應該連Money是什麼意思都不懂。還有些手上捧著書,看起來像是學生的,也衝著我們「Money Money」鬧著玩。
我們猜想這會不會是因為1983到85年的饑荒造成的,這三年衣索比亞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乾旱,將近八百萬人受到影響,一百萬人因此喪生。同時間世界各地的善款湧入,但因為政府的腐敗和內戰頻仍,上千萬美金沒有進到它們應該到的地方,有的甚至被叛軍拿去買武器。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段時間的影響,讓衣索比亞人覺得外國人就是有錢,伸手跟你要錢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呢?尤其中國政府這幾年對非洲的投資力道相當大,到處造橋鋪路,興建基礎建設,所以有些屁孩看到外國人,不管皮膚是什麼顏色,都會「China China」亂喊。我有時候心血來潮,會跟他們說:「Not China. I’m from Taiwan, Taiwan!」他們也似懂非懂地喊起「Taiwan」。
這也讓我覺得慈善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拿著善心人士捐的錢,做得好似乎是應該,做不好一定會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我們常常以為做某些「善事」是為了當地人好,卻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和歷史脈絡去思考。很多歐洲人在非洲做的「善舉」,不但沒有幫到當地人,還改變了當地長久以來的生活型態,甚至永久改變了自然生態的平衡。
想著想著不禁睡著了,晚上睡得挺好,我把耳塞塞上,隔壁的公雞早上五點就開始狂叫,但是吵不到我。
伯凱建議我們從康索往西到達偉托之後,在那邊待一天,隔天前往凱亞佛參觀傳統市場,晚上在阿度巴找個當地人家露營,不用給錢,只要給一個神奇的小禮物就行。什麼小禮物呢?是一種柳橙果汁粉,一包只要5 Birr,可以把兩公升的水變成柳橙汁,伯凱昨天載我去買了一大堆。聽說部落裡的鄉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很愛,如果給他們錢或許只能拍一張照片,給他們一包這個神奇果汁粉,愛拍幾張都行。
於是我們繼續前進,爬了一段小坡之後,迎接我們的是長達四五十公里的長下坡,直接下降了一千公尺之多。這段不只輕鬆而且人少,我們享受了一段難得清靜的旅程。但越下降氣溫越高,再加上坡度太陡,煞車用得太兇,我和尼爾先後都燒框爆胎了。
中午到了偉托,在當地旅館吃了中餐,本想吃完之後繼續前進,但天氣實在太熱,於是決定在這邊露營過一晚,一人50 Birr加淋浴,價格還不錯。只是真的太熱,一直到了凌晨氣溫才降下來,我也才漸漸入睡。
昨天又被熱到了,今天起了個大早,準備挑戰在衣索比亞的最後一段山路,只知道從偉托到凱亞佛有大概十五公里的爬坡,至於爬多高,就不太清楚了。
大概七點左右就出發,天氣還很涼爽,坡度也很平緩,因為終於快要完成衣索比亞了,我們心情都相當不錯,就這樣輕鬆翻過了一個小山丘,騎了二十五公里,想說今天應該就這樣輕鬆吧。
但衣索比亞給我們的挑戰哪那麼容易!接下來的坡應該是此次旅程最硬,有的坡長達一公里,而坡度竟超過十趴甚至到十三趴!很多時候我只能用「之字」騎法迂迴前進。正當你翻過了一個山丘,覺得應該可以休息時,稍微下滑幾秒,又是一個十趴左右的坡在眼前等你。
我一邊踩一邊唱著:「越過山丘,才發現更多山丘,喋喋不休,快要抽筋的哀愁……」就這樣埋頭苦騎,不斷把自己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繼續前進,終於在十點半左右到達凱亞佛。看了里程表,我們在不到十五公里的距離裡竟然爬升了超過一千公尺!
尼爾大概晚我十分鐘到,他看起來也累壞了,我們在路旁的餐廳吃了中餐,連喝三罐汽水,慶祝我們完成衣索比亞最後的挑戰。至於傳統市場,聽說竟然還得花200 Birr找嚮導帶我們進去,我們都興趣缺缺,就在餐廳納涼休息。
我們從凱亞佛往南騎一小段後,找了一個門外有稻草人的農家,想問問主人願不願意讓我們借住一晚。一位婦人看到我們,連忙開門迎接,什麼也沒問就讓我們進門,相當友善,我們比手畫腳問她今天能不能在這裡搭帳篷,她連連點頭,但堅持要我們待在屋裡。她先是用某種瓜殼盛了一些「液體」給我們,作勢要我們喝,我看了一下,我的媽呀,跟泥巴差不多,假裝用嘴唇碰了一下,和她說聲謝謝,我們一人拿了三包神奇柳橙果汁粉給她,她很開心地收下,隨即泡了一包來喝,之後就自己忙自己的去了。
我們也沒事幹,把傢伙拿出來煮晚餐,還多煮了一點準備分給她吃。這裡看起來不像一家子住的地方,倒像是個儲存用的農舍。這時有個瘦瘦的阿伯來了,看樣子是來換班的,這位阿姨看他來了,就和我們告別回家。
這個阿伯也很好客,一面用一點點簡單的英文和比手畫腳,試圖和我們溝通,一面把我們多煮的飯全部吃光光。之後他招呼我們到屋裡睡下,屋裡超熱,我們雖然比較想睡帳篷,但又不好意思拒絕,就在屋裡把睡墊鋪上睡了,他自己跑到屋子的另一邊堆放木柴的地方睡。
依稀聽到他半夜不斷起來,不知道在幹嘛,早上才知道他被成群紅火蟻攻擊,上百隻咬人超痛的紅火蟻就這樣爬滿他的衣服,我們看了都嚇一跳。臨走前我們也給他幾包柳橙汁粉,他收下了,但還是做手勢跟我們要錢,我們給他20 Birr,雖然整個FU都沒了,但看在他昨晚受的煎熬分上,也就比較釋懷了。
也不是因為金額的多寡,只是放上價格標籤後,很多事情都會變質甚至腐化。一晚留宿本來可以是友善和熱情的表現,但放了20 Birr上去,就變成便宜的爛旅館了。
我站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雨依然不停下著,望著眼前似乎永無止境的爛路,滿身泥濘,又冷又餓。怎麼又來了?我開始細數這一生中把自己搞成這麼狼狽的種種蠢事。難道這是我的命嗎?這次又是怎麼發生的?才出發第三天哪!我想起昨天做的那個愚蠢的決定……
從地圖上看,從中甸到稻城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是先沿著路況最好的214國道,再從得榮往東,第二條是必須把Google Map放得很大才看得到的山路,途中得依序翻過海拔三千九百公尺的小雪山、四千三百公尺的大雪山,以及大魔王──四千七百公尺的無名雪山(好像天龍八部的無名僧,最厲害的都沒有名字)。
第二條從地圖上看起來近多了,照里程算好像可以快一天,不如走這條吧。我想起美國詩人羅勃‧佛洛斯特的〈未竟之路〉:「樹林裡有兩條岔路,而我選擇了人跡較少的一條,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下次如果有人跟你這麼說,請你跟我這樣做:第一,高舉你的左手;第二,用力把他的頭巴下去!走小路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啊……
之前在台灣騎腳踏車最高也只到了三千兩百七十五公尺的武嶺,就連登山也才爬到三千五百公尺左右,這次的行程整個是越級打怪。我也沒想太多,打電話問了公路養護單位,知道這條路沒有受到前幾天的地震影響,照常通行。在路邊的藥局買了盒紅景天膠囊,水果攤買了些香蕉和蘋果,就出發了。只是天氣不太好,陰陰的,一直飄著細雨,氣溫雖在十度以上,但感覺很冷,讓我得把風衣穿上。
這天的計畫是翻過小雪山之後投宿翁水村,看起來高度才增加大概七百公尺而已,就沒有太精實,混到快十點才出發。結果大失算,爬到接近三千六百公尺的高度後,竟然一口氣下降到兩千八百公尺高,才繼續上攻到三千八百,總爬升高達一千八百公尺,爬得我頭昏眼花,大腿幾度瀕臨抽筋。所幸路況還算可以,大部分都是柏油路或水泥路雖然坑坑洞洞,但沒啥大礙。儘管如此,還是比預計時間還晚四小時到達翁水村,天都已經全黑了才在路邊隨便找了間旅店,要了個床位,二十塊人民幣,入住後點了一兩樣炒菜,吃飽喝足,躺在床上拉完筋,沒多久就沉沉睡去。隔天本想早點起床趕路,但是因為太累睡到八點多。目標當然就是翻過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大雪山後下滑,然後直衝稻城。高度才增加五百而已,總里程也才大概八十公里,上山四十公里,時速抓七公里好了,六小時攻頂,下滑時速抓個二十五公里已經很客氣了。這樣算起來八小時左右便可完成今天任務,時間綽綽有餘。
但打開房門一看,心裡一沉,雨勢變大了,看看天空,看樣子會下一整天。但是不出發不行,咬著牙還是上路了。我超級討厭在雨天騎車,天雨路滑增加風險,而且雨水打在臉上真的很痛,水氣加上泥沙黏附在車上以及行李上,本來已經很重的車變得更重,騎起來只有幹。
一邊碎念一邊向前騎,騎了大概快十公里後,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傻眼了,路呢?把手機地圖拿出來看,沒錯啊,方向是正確的,只是柏油路面消失了,變成泥沙和石頭組成的off-road越野路段。沒辦法,只能硬騎了,可能這一段是在修路吧,忍一下就好。沒想到這一忍就是一個多小時,路面不但沒改善,甚至更糟,我下來牽車的頻率越來越高。
有些地方甚至已經變成池塘了,我必須用我穿著拖鞋的雙腳(對,我穿拖鞋,真不知道我腦袋裝啥),走到冰冷的泥水裡牽車通過,更多地方泥巴深達二十公分以上,我一踩就深陷其中,使勁把腳拔起來了,拖鞋卻還黏在泥土裡。我的車又相當重,輪胎像切蛋糕似的陷在裡面,不要說騎了,就連牽車都得花我吃奶力氣。一邊用力推車,後面大卡車不斷經過,有時候會夾雜一台小巴士,車上的乘客對我大聲加油,但我一點也提不起精神。這時候前面來了台四驅休旅車,整車白色的烤漆幾乎被泥水濺成土黃色,我看了心都涼了──到底前面的路是有多慘烈啊?車子停下來,一位大媽探出頭來問我要騎到哪。「我要翻過大雪山到稻城。」我說。
她聽了一臉驚恐:「這一路上八十幾公里都是這種路啊!後面的路還要再爛!」
她接著嘟囔:「真是要命,早知道不走這裡了……」
我聽了幾乎崩潰,天啊,算一算後面還有六十幾公里,如果都是這種路,我是要走上三天三夜嗎?但又安慰自己,中國人有時候說話都比較誇大,應該不會這麼慘吧……又把自己從自暴自棄邊緣拉回來,繼續前進。遇到看起來可以騎的路面就上車,但常常一下子又得下來推車。
就這樣折騰了快四小時,我才前進不到二十公里,途中超過玉山的海拔高度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時還停下來拍個照做紀念,但心裡完全沒有超越極限的喜悅。雨繼續下個不停,我又餓又累又冷,存糧已經全部吃完,全身痠痛又四肢無力,停在路邊動彈不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忽然想到,背包裡好像還有一顆蘋果!伸手一探,果不其然,在背包底部讓我翻出這一顆宛如救命仙丹的蘋果。我顧不得髒了,馬上就大咬個兩口,眼淚差點奪眶而出──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蘋果!正當我要再咬一口時,戴著厚重手套的手一滑,大半顆蘋果就這樣掉到泥巴裡。
我忽然感覺腦子裡好像有條東西斷了,我大吸一口氣,然後用盡丹田之力,大喊了一聲:
「幹!!!!!!」
那聲勢之大,整座山谷為之震動,一群鳥兒從樹林裡受驚飛起,頓時把半片天空遮住。我發洩完,比較冷靜了,自己都覺得好笑,竟然拿出相機來拍了那顆蘋果當作紀念,這以後應該會是個好故事,我心裡想。正在考慮該拿這顆蘋果怎麼辦時,我聽到「喂」的一聲。
見鬼了,這四千多公尺的深山裡,應該不會有人吧?但隨即又聽到一聲:「喂!小伙!」我順著聲音看過去,一位老先生和老婆婆站在不遠處的山坡上,更高處有一座冒著炊煙的帳篷,老先生向我招手示意我過去。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把車隨便丟在路邊,爬上了布滿碎石的山坡,跟著老先生進了帳篷。一陣暖意迎面撲來,我的眼鏡瞬間起霧。老先生示意我坐下,我發抖著把濕透的手套取下,不住地搓著手,已經麻木冰冷的雙手才開始有感覺。
老先生倒了一碗湯給我,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帶點鹹味又充滿奶油的香味,啊,這是酥油嗎,這是藏族招待客人的上品啊。隨著滾燙的湯液滑入喉嚨,到達胃部,我的身體總算開始有暖意,身體也慢慢止住發抖了。「今天才有一群騎摩托車的過去,我沒叫他們,看到你是騎自行車的才叫你。」老先生說得一口不錯的普通話。「你知道這裡是大雪山嗎?冬天是會凍死人的啊。」
我想回答,但嘴巴好像還不大靈光,只能點點頭。
他一邊搖搖頭一邊繼續說:「年輕人真是太瘋狂了,你哪裡的?」
「台……台灣。」
「喔!台灣人啊。」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脫口問道:「請問……這要多少錢啊?」我比了比手中的碗。依我在中國走跳多年的經驗,很多事情還是先講好價錢才不會有麻煩。
「不用錢!大家都是人嘛。」
我忽然愣住了,不知怎麼回應,只能猛點頭說是,臉頰一下子燙了起來,覺得問了這個問題實在很羞愧。「大家都是人。」我猜他想表達的是那種,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所應具備的美德──如果看到其他人需要幫助,不管對方是什麼身分、種族、膚色,就是要伸出援手。
他繼續說:「在這裡養牛養豬辛苦啊,現在都沒有年輕人願意做這種事了。在這山上一待就是好幾個月,要用電還得靠發電機,如果陰天的話,信號塔沒有太陽能給電,手機就沒有訊號。」
一邊講,他一邊盛了一碗糌粑粉給我,說:「加點酥油到碗裡,然後攪一攪,我手髒不好意思幫你弄,對,就是這樣,弄成一團之後就可以吃了,我們藏族都是這樣吃的。」我一邊吃著糌粑,喝著酥油,看著老先生辛苦準備餵豬的飼料,忽然覺得,他活得比很多穿得人模人樣的人都還像個真正的「人」。
我用手托著下巴小睡了片刻,感覺活力一點一滴地回到身體,看看錶,哇,都三點半了,不趕緊出發的話,天黑前可能下不了山了。再次感謝了老先生和老太太,我告別他們繼續前進。
天氣和路況沒有半點改善,即使到山頂只剩六公里的距離,我還是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抵達。終於征服標高四千三百八十六公尺的大雪山了,我的極限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拍了照後,我趕緊把所有保暖擋風的衣物全部穿上,等等溫度可能會降到接近零度,下滑時會更冷。
我以為攻頂後就解脫了,之後就是快樂的下滑了嗎……錯!錯得離譜。才「滑」了幾公尺,我已經被爛路震得四肢骨骼都要散掉,更別說腳踏車了,我真的擔心這樣下去會整台解體。好幾次還因為積水太深看不清楚路,或者不小心輾過大石、陷落大坑而差點摔車。只好又下來牽車了,沒想到比上坡更累,我不僅要隨時讓這部重達六十公斤的車保持平衡,手還得一直按著煞車避免速度太快失控,這時我的手已經冷到麻木,又因為一直用力而頻頻抽筋,才不到半小時,我又被操得幹聲連連。
這時我意識到,在天黑前我是不可能下得了山了。
現在我有兩個選擇,第一是搭便車下山,第二是隨便找個地方露營過一晚。我看看周圍的環境,感覺到處都有機會發生坍方或土石流,實在不適合久待。那攔車吧,我一邊牽車一邊不時往後望,走了快半小時,明明剛剛還有很多貨車經過,現在怎麼半台都沒有?
啊!是了,現在時間已經晚了,該通過這個路段的車早就趁天色還亮著時就走了,在這種路上開夜車簡直就是玩命。
天色慢慢變暗了,我也放棄了搭便車下山的念頭,剛好經過了一座新修的橋墩,和山壁有一段距離,就算有落石應該也砸不到我。
如果真的發生土石流,那也是命吧。
〈貼上價碼之後〉
從Paradise Lodge離開,難度更甚於從卡爾家出發。雖然理智上知道自己得繼續上路,但肉體就是抗拒暴露在毒辣的陽光、永無止境的爬坡和魔音穿腦的屁孩之中。只能安慰自己,我們已經走完百分之八十的路程,只剩最後的兩成,就能離開這個國家了。
今天的目標是往南大概八十公里的康索,德國勇腳伯納已經入境肯亞了,他寫信給我,推薦一個位於康索的「私人」營地,說是他在非洲待過最棒的,能比Paradise Lodge還棒?我們當然得去瞧瞧,於是我寫信給營地主人伯凱,說我們今天會到。
這段其實還挺輕鬆的,一開始就狂下滑個五百公尺,之後繼續上上下下,只是因為今天吃了Mefloquine,不管怎麼喝水都還是口乾舌燥,攜帶的水消耗得相當快。抵達目的地前有個大坡,在這之前尼爾的水已經喝光了,當我們到達康索時,他已經渴得受不了。
路邊有個髮型很酷的年輕人和我們打招呼,英文很流利,原來他就是營地主人伯凱。我們在路邊的餐廳坐下來,連喝兩瓶可樂,之後到附近的飯店吃飯,然後他帶我們去他的營地。
到了一看,我們都傻眼了。說是營地,也只不過是他家的後院而已,我們還得在一個大雞籠旁紮營,和前幾天的Paradise Lodge比起來簡直天差地別,我們大失所望。只是價格還算便宜,一人80 Birr,他又很熱心地騎車載我去換錢、買東西,還提供很多西南路線的建議給我們,是個不錯的年輕人,有志於發展故鄉的觀光。他那邊沒自來水,只從水桶裡裝了六公升的水給我們,不夠洗澡,我們打算用在明天的早餐和路上飲用。晚上他帶我們到村子裡的小店喝啤酒吃晚餐,我們請他喝了三瓶啤酒以示謝意。這裡的小朋友爭相讓我們拍照,之後又迫不及待想看看他們的照片,看了之後互相指指點點、哈哈大笑,可愛極了,遠離觀光區的小孩正常多了。
我不禁好奇,到底這些要錢屁孩的現象是怎麼形成的。其實老一輩的衣索比亞鄉民相當有禮貌,大概四十歲以上的長輩,如果我先點頭問好,他們甚至會脫帽鞠躬還禮。但是三十歲以下的就不是這樣了,我們還看到有媽媽教她小孩向我們喊「Money Money」,那小孩小到應該連Money是什麼意思都不懂。還有些手上捧著書,看起來像是學生的,也衝著我們「Money Money」鬧著玩。
我們猜想這會不會是因為1983到85年的饑荒造成的,這三年衣索比亞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乾旱,將近八百萬人受到影響,一百萬人因此喪生。同時間世界各地的善款湧入,但因為政府的腐敗和內戰頻仍,上千萬美金沒有進到它們應該到的地方,有的甚至被叛軍拿去買武器。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段時間的影響,讓衣索比亞人覺得外國人就是有錢,伸手跟你要錢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呢?尤其中國政府這幾年對非洲的投資力道相當大,到處造橋鋪路,興建基礎建設,所以有些屁孩看到外國人,不管皮膚是什麼顏色,都會「China China」亂喊。我有時候心血來潮,會跟他們說:「Not China. I’m from Taiwan, Taiwan!」他們也似懂非懂地喊起「Taiwan」。
這也讓我覺得慈善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拿著善心人士捐的錢,做得好似乎是應該,做不好一定會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我們常常以為做某些「善事」是為了當地人好,卻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和歷史脈絡去思考。很多歐洲人在非洲做的「善舉」,不但沒有幫到當地人,還改變了當地長久以來的生活型態,甚至永久改變了自然生態的平衡。
想著想著不禁睡著了,晚上睡得挺好,我把耳塞塞上,隔壁的公雞早上五點就開始狂叫,但是吵不到我。
伯凱建議我們從康索往西到達偉托之後,在那邊待一天,隔天前往凱亞佛參觀傳統市場,晚上在阿度巴找個當地人家露營,不用給錢,只要給一個神奇的小禮物就行。什麼小禮物呢?是一種柳橙果汁粉,一包只要5 Birr,可以把兩公升的水變成柳橙汁,伯凱昨天載我去買了一大堆。聽說部落裡的鄉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很愛,如果給他們錢或許只能拍一張照片,給他們一包這個神奇果汁粉,愛拍幾張都行。
於是我們繼續前進,爬了一段小坡之後,迎接我們的是長達四五十公里的長下坡,直接下降了一千公尺之多。這段不只輕鬆而且人少,我們享受了一段難得清靜的旅程。但越下降氣溫越高,再加上坡度太陡,煞車用得太兇,我和尼爾先後都燒框爆胎了。
中午到了偉托,在當地旅館吃了中餐,本想吃完之後繼續前進,但天氣實在太熱,於是決定在這邊露營過一晚,一人50 Birr加淋浴,價格還不錯。只是真的太熱,一直到了凌晨氣溫才降下來,我也才漸漸入睡。
昨天又被熱到了,今天起了個大早,準備挑戰在衣索比亞的最後一段山路,只知道從偉托到凱亞佛有大概十五公里的爬坡,至於爬多高,就不太清楚了。
大概七點左右就出發,天氣還很涼爽,坡度也很平緩,因為終於快要完成衣索比亞了,我們心情都相當不錯,就這樣輕鬆翻過了一個小山丘,騎了二十五公里,想說今天應該就這樣輕鬆吧。
但衣索比亞給我們的挑戰哪那麼容易!接下來的坡應該是此次旅程最硬,有的坡長達一公里,而坡度竟超過十趴甚至到十三趴!很多時候我只能用「之字」騎法迂迴前進。正當你翻過了一個山丘,覺得應該可以休息時,稍微下滑幾秒,又是一個十趴左右的坡在眼前等你。
我一邊踩一邊唱著:「越過山丘,才發現更多山丘,喋喋不休,快要抽筋的哀愁……」就這樣埋頭苦騎,不斷把自己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繼續前進,終於在十點半左右到達凱亞佛。看了里程表,我們在不到十五公里的距離裡竟然爬升了超過一千公尺!
尼爾大概晚我十分鐘到,他看起來也累壞了,我們在路旁的餐廳吃了中餐,連喝三罐汽水,慶祝我們完成衣索比亞最後的挑戰。至於傳統市場,聽說竟然還得花200 Birr找嚮導帶我們進去,我們都興趣缺缺,就在餐廳納涼休息。
我們從凱亞佛往南騎一小段後,找了一個門外有稻草人的農家,想問問主人願不願意讓我們借住一晚。一位婦人看到我們,連忙開門迎接,什麼也沒問就讓我們進門,相當友善,我們比手畫腳問她今天能不能在這裡搭帳篷,她連連點頭,但堅持要我們待在屋裡。她先是用某種瓜殼盛了一些「液體」給我們,作勢要我們喝,我看了一下,我的媽呀,跟泥巴差不多,假裝用嘴唇碰了一下,和她說聲謝謝,我們一人拿了三包神奇柳橙果汁粉給她,她很開心地收下,隨即泡了一包來喝,之後就自己忙自己的去了。
我們也沒事幹,把傢伙拿出來煮晚餐,還多煮了一點準備分給她吃。這裡看起來不像一家子住的地方,倒像是個儲存用的農舍。這時有個瘦瘦的阿伯來了,看樣子是來換班的,這位阿姨看他來了,就和我們告別回家。
這個阿伯也很好客,一面用一點點簡單的英文和比手畫腳,試圖和我們溝通,一面把我們多煮的飯全部吃光光。之後他招呼我們到屋裡睡下,屋裡超熱,我們雖然比較想睡帳篷,但又不好意思拒絕,就在屋裡把睡墊鋪上睡了,他自己跑到屋子的另一邊堆放木柴的地方睡。
依稀聽到他半夜不斷起來,不知道在幹嘛,早上才知道他被成群紅火蟻攻擊,上百隻咬人超痛的紅火蟻就這樣爬滿他的衣服,我們看了都嚇一跳。臨走前我們也給他幾包柳橙汁粉,他收下了,但還是做手勢跟我們要錢,我們給他20 Birr,雖然整個FU都沒了,但看在他昨晚受的煎熬分上,也就比較釋懷了。
也不是因為金額的多寡,只是放上價格標籤後,很多事情都會變質甚至腐化。一晚留宿本來可以是友善和熱情的表現,但放了20 Birr上去,就變成便宜的爛旅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