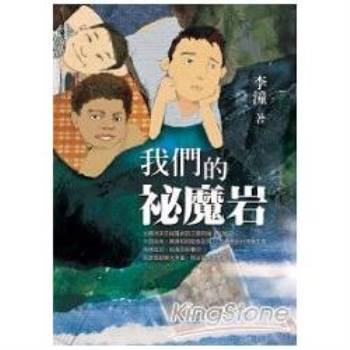第一章
我們又來到祕魔岩。
今天的海風真好,從岩底推捲上來,在祕魔岩的前端,噴出一排淡淡的霧幕,像舞臺前的乾冰霧氣,適時地在主角出場的一刻噴散出來。
我一步步走向岩石平臺的前端。背後,吹拂過蜈蚣草坡的山風,推我向前。
今天,我要將半個腳掌探出岩端,縮起左腳,金雞獨立。我要平伸兩手,像展翅的鷹。
太平洋永遠是遼闊的。
太平洋永遠不太平。太平洋總有颱風和地震。
祕魔岩下的太平洋海潮,天天是這樣澎湃洶湧。我站得再高再遠,腳底一樣感受到它沖刷礁石沙灘,撞擊在祕魔岩底洞穴往上竄的力道;竄過「石頭翁」站的蛇紋石、藍寶石、玫瑰石和時時在鬆塌的頁岩層,直上我們的祕魔岩。
來到祕魔岩,我喜歡脫下鞋襪,讓傳過岩層的海潮勁力,搔刮得腳掌陣陣酥麻。我喜歡。
撲岸的浪花海潮之外,海的色澤是淺碧、青綠、寶藍和靛藍的一層層渲染開來。在我一步步走向祕魔岩前端的時候,我從不低頭看腳掌,我只近看或遠望這兩眼裝不下的海洋!
歐陽臺生哀哀地叫我:「阿遠!阿遠!好了啦!不要再過去,地震來了就糟糕。」(歐陽是蹲著吧?就像那些躲地震的人。他在蜈蚣草坡和祕魔岩的接處,臉色青白,伸出一手,向我哀哀求告。)
毛毛喊:「停!停!阿遠,停!」
每次,我們來到祕魔岩,胖壯的毛毛總盤腿往岩邊一坐,身子往後仰,仿佛憑他的體重,就能把臨海祕魔岩的一端坐翹起來。我愈往前走,他後仰得越厲害,就像和誰在翹翹板拚力氣,拚到身子都躺平。都是孬種!
既然愛跟東跟西,跟我到祕魔岩,又不敢往前多走兩步,歐陽和毛毛是來看熱鬧的?他們是等看我從岩端翻落下去的一?那,好能喊叫得痛快?孬種!他們喊我停止,拿地震嚇我,其實只是警告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向前。
他們都是愛看死亡邊緣,把別人的死亡邊緣當作刺激遊戲的超級大怪胎。他們的叫喊裡,含有多少興奮?
西班牙鬥牛場,那些在圓形看臺欣賞血腥殺戮的人,不也是這樣瘋狂喊叫。馬戲團的圓形帳篷內,那些期待撤走鋼索下的安全網,再為走鋼索捏汗驚叫的人,也是假情假意。拳擊場外、摔角場外和決鬥場外的人,也都是這樣的畸形孬種!有本事,他們為什?不也上場?
歐陽和毛毛,有膽量跟我到祕魔岩,就要有勇氣走到祕魔岩的前端去,去看深崖下的海波,是什?樣的壯麗,去聞聞拂捲上來的海風,是什?樣的氣味。
他們一定要過來感受,感受面對遼闊海洋的無邊美麗和絕望。
父親在生命的盡頭,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景象,也是這種絕望的心情?來到祕魔岩,他是自己走上來,還是套著腳鐐給士兵推過來?父親的雙手是套著手銬,還是給粗麻繩捆綁?
沒有人知道,父親被槍殺那天,是在祕魔岩的清晨、正午、黃昏還是深夜?他看見的是什?時刻的太平洋?海上有船、浪有多高?無論如何,祕魔岩下的潮聲,永遠是澎湃的。
潮聲會掩過父親的哭泣,或者他的?喊?
押解父親到祕魔岩的士兵,曾經對他說過什?話?做過什?動作?他們也像鬥牛場的觀眾,像看著走鋼索的人?
父親消失在祕魔岩的三個月後,我出生。
十四年來,媽媽和阿嬤告訴我:「你爸爸到日本做生意,等他成功,就會回來看你。」
我是個超級大笨蛋,所以從來不懷疑。
直到今年三月,阿嬤過世前,她才告訴我事實的真相。那時,媽媽正好過來,還一再阻止阿嬤說下去。
她們何必要這樣隱瞞我?
這個祕密,她們居然能保守十四年,讓我絲毫沒察覺。保守祕密是很難過的事,而這種事,除了難過,還是痛苦的吧。雖說我知道了事實的真相,不過也只知道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四月,內地來的士兵抓走了父親。父親是個讀書人,是一位醫生。有人在中山橋頭看向祕魔岩,看見父親最後的身影,在他背後有六個士兵。這人是父親診所的患者,他說絕對不會看錯人。
但怎?會找不到父親的屍體?
父親究竟犯了什?大罪,要被槍殺?而槍殺他的地點,為什?又要選在面海高崖上的祕魔岩?
那是個什?時代?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槍殺父親的是內地來的士兵。就像歐陽的爸爸一樣的士兵!
我想知道父親站在祕魔岩,最後一刻的感受。
歐陽和毛毛也應當嘗嘗那樣的滋味!他們不能這樣蹲著,不能仰躺坐著。我也要設法把他們的爸爸引到祕魔岩來,讓他們嘗嘗死亡邊緣的滋味。我一定要。
匍匐在坡地平臺的蜈蚣草,從我們第一次見到,就這樣青綠得發亮,柔軟如毛毯。能在溫鹹的海風和乾爽的山風終年吹襲,又長得這樣平坦而旺茂的青草,它們的生命總是強韌的。這樣的草根,是否也曾滲透過鮮紅的血漬,被一個個終止的生命平躺過?
在祕魔岩眺望大海,若能什?也不想,只是看著;看著湧自海底的浮浪,一波波撲向灘岸;看前浪和後浪激撞起浪花;看浮動如緞帶的海湧,以澄淨的寶藍色澤鋪展向海平線,實在無比暢快。
可是,這陣子,我做不到。即使看到海平線盡頭的濃白浮雲,我也感到悲傷;仰看無際的藍天,只想一聲長呼,飛天而去。看到陽光穿透浮雲的光束,在海面投射得黯一塊、亮一塊,這原該是美麗的景象,居然也引得我氣憤,氣憤它不該以這樣的景象,面對這樣的祕魔岩。
第二章
歐陽和我從小學一年級,便是同班同學。
毛毛在三年級上學期轉到我們中正國小,讀了半學期,就轉走;五年級下學期又轉回來,六上又轉走,六下又轉回來。他真厲害,轉來轉去,都轉回我們這一班,沒轉得頭暈,轉得不見。
我們都不懂,毛毛他家為什麼這樣搬來搬去?搬去臺北、搬去中壢、搬去高雄,好像環島旅行一樣。大概是這樣見識多了,毛毛才不怕生吧?他每次回來,從進教室的第一分鐘,就和大家熟得不得了;交頭接耳找人打招呼、借橡皮擦、借課本,下課還吆喝大家去玩躲避球,而且自願當主攻手。
毛毛每次回來,都長高一些、長胖一圈,小平頭鬈得更厲害,越來越像個黑人。毛毛的厚嘴脣、白牙齒和大屁股,活脫脫是個小黑人。他的力氣大,跑得又快,讓他接到躲避球,場內的「肉餅」,沒人不嚇得腿軟,只有我和歐陽稍稍能對付得了他。
歐陽像他老爸,是個小個頭的湖南佬,但長得更白淨些,這像他客家人的媽媽。歐陽的攻擊力不強,閃躲避球的功夫卻是一流,他蹲、跳、閃、扭腰的柔軟度,好像能跳肚皮舞(沒錯,他在才藝表演時,就男扮女裝跳過夏威夷女郎的草裙舞)。
毛毛的殺手球飆他,再狠再快也碰不著他一根汗毛。
毛毛跑步或丟球,常愛用他的白牙齒咬住厚黑嘴脣,再悶聲加個獅吼助威。是很恐怖,但我怕他什麼?我身高腿長,再強的球路,憑我的長手一伸,大手掌順勢捕接(我才不會去跟他硬碰硬),一旦讓我撈到,對方的場內球員,不成肉餅,至少也得翻幾個跟頭!
毛毛直來直往的強攻,我的柔道接球術和歐陽的軟身閃躲,居然成為三角對手,成了好朋友。我們三人的功課排名,歐陽總是穩居寶座,我還是居中,毛毛比我差一點。我們一起考上好漢坡頂的這所中學,也是這樣的排名順位。
我們又來到祕魔岩。
今天的海風真好,從岩底推捲上來,在祕魔岩的前端,噴出一排淡淡的霧幕,像舞臺前的乾冰霧氣,適時地在主角出場的一刻噴散出來。
我一步步走向岩石平臺的前端。背後,吹拂過蜈蚣草坡的山風,推我向前。
今天,我要將半個腳掌探出岩端,縮起左腳,金雞獨立。我要平伸兩手,像展翅的鷹。
太平洋永遠是遼闊的。
太平洋永遠不太平。太平洋總有颱風和地震。
祕魔岩下的太平洋海潮,天天是這樣澎湃洶湧。我站得再高再遠,腳底一樣感受到它沖刷礁石沙灘,撞擊在祕魔岩底洞穴往上竄的力道;竄過「石頭翁」站的蛇紋石、藍寶石、玫瑰石和時時在鬆塌的頁岩層,直上我們的祕魔岩。
來到祕魔岩,我喜歡脫下鞋襪,讓傳過岩層的海潮勁力,搔刮得腳掌陣陣酥麻。我喜歡。
撲岸的浪花海潮之外,海的色澤是淺碧、青綠、寶藍和靛藍的一層層渲染開來。在我一步步走向祕魔岩前端的時候,我從不低頭看腳掌,我只近看或遠望這兩眼裝不下的海洋!
歐陽臺生哀哀地叫我:「阿遠!阿遠!好了啦!不要再過去,地震來了就糟糕。」(歐陽是蹲著吧?就像那些躲地震的人。他在蜈蚣草坡和祕魔岩的接處,臉色青白,伸出一手,向我哀哀求告。)
毛毛喊:「停!停!阿遠,停!」
每次,我們來到祕魔岩,胖壯的毛毛總盤腿往岩邊一坐,身子往後仰,仿佛憑他的體重,就能把臨海祕魔岩的一端坐翹起來。我愈往前走,他後仰得越厲害,就像和誰在翹翹板拚力氣,拚到身子都躺平。都是孬種!
既然愛跟東跟西,跟我到祕魔岩,又不敢往前多走兩步,歐陽和毛毛是來看熱鬧的?他們是等看我從岩端翻落下去的一?那,好能喊叫得痛快?孬種!他們喊我停止,拿地震嚇我,其實只是警告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向前。
他們都是愛看死亡邊緣,把別人的死亡邊緣當作刺激遊戲的超級大怪胎。他們的叫喊裡,含有多少興奮?
西班牙鬥牛場,那些在圓形看臺欣賞血腥殺戮的人,不也是這樣瘋狂喊叫。馬戲團的圓形帳篷內,那些期待撤走鋼索下的安全網,再為走鋼索捏汗驚叫的人,也是假情假意。拳擊場外、摔角場外和決鬥場外的人,也都是這樣的畸形孬種!有本事,他們為什?不也上場?
歐陽和毛毛,有膽量跟我到祕魔岩,就要有勇氣走到祕魔岩的前端去,去看深崖下的海波,是什?樣的壯麗,去聞聞拂捲上來的海風,是什?樣的氣味。
他們一定要過來感受,感受面對遼闊海洋的無邊美麗和絕望。
父親在生命的盡頭,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景象,也是這種絕望的心情?來到祕魔岩,他是自己走上來,還是套著腳鐐給士兵推過來?父親的雙手是套著手銬,還是給粗麻繩捆綁?
沒有人知道,父親被槍殺那天,是在祕魔岩的清晨、正午、黃昏還是深夜?他看見的是什?時刻的太平洋?海上有船、浪有多高?無論如何,祕魔岩下的潮聲,永遠是澎湃的。
潮聲會掩過父親的哭泣,或者他的?喊?
押解父親到祕魔岩的士兵,曾經對他說過什?話?做過什?動作?他們也像鬥牛場的觀眾,像看著走鋼索的人?
父親消失在祕魔岩的三個月後,我出生。
十四年來,媽媽和阿嬤告訴我:「你爸爸到日本做生意,等他成功,就會回來看你。」
我是個超級大笨蛋,所以從來不懷疑。
直到今年三月,阿嬤過世前,她才告訴我事實的真相。那時,媽媽正好過來,還一再阻止阿嬤說下去。
她們何必要這樣隱瞞我?
這個祕密,她們居然能保守十四年,讓我絲毫沒察覺。保守祕密是很難過的事,而這種事,除了難過,還是痛苦的吧。雖說我知道了事實的真相,不過也只知道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四月,內地來的士兵抓走了父親。父親是個讀書人,是一位醫生。有人在中山橋頭看向祕魔岩,看見父親最後的身影,在他背後有六個士兵。這人是父親診所的患者,他說絕對不會看錯人。
但怎?會找不到父親的屍體?
父親究竟犯了什?大罪,要被槍殺?而槍殺他的地點,為什?又要選在面海高崖上的祕魔岩?
那是個什?時代?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槍殺父親的是內地來的士兵。就像歐陽的爸爸一樣的士兵!
我想知道父親站在祕魔岩,最後一刻的感受。
歐陽和毛毛也應當嘗嘗那樣的滋味!他們不能這樣蹲著,不能仰躺坐著。我也要設法把他們的爸爸引到祕魔岩來,讓他們嘗嘗死亡邊緣的滋味。我一定要。
匍匐在坡地平臺的蜈蚣草,從我們第一次見到,就這樣青綠得發亮,柔軟如毛毯。能在溫鹹的海風和乾爽的山風終年吹襲,又長得這樣平坦而旺茂的青草,它們的生命總是強韌的。這樣的草根,是否也曾滲透過鮮紅的血漬,被一個個終止的生命平躺過?
在祕魔岩眺望大海,若能什?也不想,只是看著;看著湧自海底的浮浪,一波波撲向灘岸;看前浪和後浪激撞起浪花;看浮動如緞帶的海湧,以澄淨的寶藍色澤鋪展向海平線,實在無比暢快。
可是,這陣子,我做不到。即使看到海平線盡頭的濃白浮雲,我也感到悲傷;仰看無際的藍天,只想一聲長呼,飛天而去。看到陽光穿透浮雲的光束,在海面投射得黯一塊、亮一塊,這原該是美麗的景象,居然也引得我氣憤,氣憤它不該以這樣的景象,面對這樣的祕魔岩。
第二章
歐陽和我從小學一年級,便是同班同學。
毛毛在三年級上學期轉到我們中正國小,讀了半學期,就轉走;五年級下學期又轉回來,六上又轉走,六下又轉回來。他真厲害,轉來轉去,都轉回我們這一班,沒轉得頭暈,轉得不見。
我們都不懂,毛毛他家為什麼這樣搬來搬去?搬去臺北、搬去中壢、搬去高雄,好像環島旅行一樣。大概是這樣見識多了,毛毛才不怕生吧?他每次回來,從進教室的第一分鐘,就和大家熟得不得了;交頭接耳找人打招呼、借橡皮擦、借課本,下課還吆喝大家去玩躲避球,而且自願當主攻手。
毛毛每次回來,都長高一些、長胖一圈,小平頭鬈得更厲害,越來越像個黑人。毛毛的厚嘴脣、白牙齒和大屁股,活脫脫是個小黑人。他的力氣大,跑得又快,讓他接到躲避球,場內的「肉餅」,沒人不嚇得腿軟,只有我和歐陽稍稍能對付得了他。
歐陽像他老爸,是個小個頭的湖南佬,但長得更白淨些,這像他客家人的媽媽。歐陽的攻擊力不強,閃躲避球的功夫卻是一流,他蹲、跳、閃、扭腰的柔軟度,好像能跳肚皮舞(沒錯,他在才藝表演時,就男扮女裝跳過夏威夷女郎的草裙舞)。
毛毛的殺手球飆他,再狠再快也碰不著他一根汗毛。
毛毛跑步或丟球,常愛用他的白牙齒咬住厚黑嘴脣,再悶聲加個獅吼助威。是很恐怖,但我怕他什麼?我身高腿長,再強的球路,憑我的長手一伸,大手掌順勢捕接(我才不會去跟他硬碰硬),一旦讓我撈到,對方的場內球員,不成肉餅,至少也得翻幾個跟頭!
毛毛直來直往的強攻,我的柔道接球術和歐陽的軟身閃躲,居然成為三角對手,成了好朋友。我們三人的功課排名,歐陽總是穩居寶座,我還是居中,毛毛比我差一點。我們一起考上好漢坡頂的這所中學,也是這樣的排名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