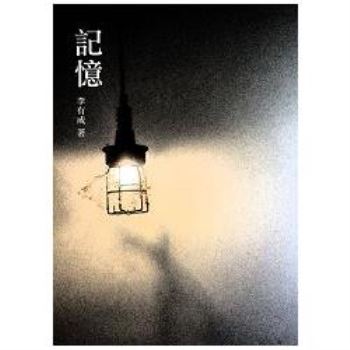召喚過去:石黑一雄的《群山淡景》
每一個尚未被當下視為與己有關的過去
意象都有永遠消失的危險。
—班雅明(Benjamin 2003: 391)
一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一部小說《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榮獲一九八三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的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Memorial Prize)。《群山淡景》是一部完全建立在記憶上的敘事文本,內容敘述一位遲暮之年的寡婦如何回憶她在二戰後長崎的生活。另一方面,這也是一部屬於自我分析的小說,因為她的記憶之旅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透過回憶,她想要理解她所身處的當下。石黑一雄以過去與現在的交錯為其敘事形式,小說敘事空間的轉換也是如此,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長崎;另一個是介於一九七○年代後期或八○年代初期的英國。作者駕輕就熟,將此時與彼時、他方與這方相互交融,織就一張敘事的錦繡。
《群山淡景》所講述的其實是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的敘事者都是悅子(Etsuko)。她是位形象端莊的日裔婦女,歷經喪偶,眼前住在英國鄉下。第一個故事圍繞著悅子與幸子(Sachiko)的交誼發展。這兩位女性年紀相仿,幸子來自富裕家庭,不幸婚後丈夫死於戰火,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幸子的故事發生在長崎,時間約莫在一九四○年代末或五○年代初的某個夏天,那時候「韓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跟以前一樣到處都是美國士兵」(Ishiguro 1990: 11)。悅子跟丈夫次郎(Jiro)住在城東,她當時懷了三、四個月的身孕(懷的是她後來取名為慶子〔Keiko〕的女兒)。她在長崎認識了幸子,一位一心一意撫育女兒真理子(Mariko)的母親。跟其他同年紀的小孩不同的是,真理子並未就學。幸子其時跟一個叫法蘭克(Frank)的美國男子交往,法蘭克答應帶她們母女二人到美國生活,不過卻一再食言。石黑一雄對法蘭克的刻畫顯然諧仿的是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裏的美國軍官平克頓(Pinkerton)(參考 Shaffer 1998:21;Lewis 2000: 22-23)。小說的第二個故事發生在英國,此時悅子已是一位中年寡婦。敘事裏的悅子反覆思忖著大女兒慶子的自殺悲劇:慶子一年前在曼徹斯特的租屋裏上吊自盡。先後失去親人的傷痛似乎還籠罩著悅子,因為在女兒結束其青春生命之前,她的丈夫佘寧漢先生(Mr. Sheringham)才離開人世不久。當她陷入對慶子的回憶時,正好二女兒霓紀(Niki)回家來探望她(霓紀是她與英國丈夫所生的女兒)。這段在英國的敘事以霓紀離家前往倫敦結束。
小說的兩段故事都以悅子的遭遇為主軸,她進入過去的唯一通道是她的記憶。在一開始敘述其故事時,她就表示:「容我自私一點,我不想回憶過去」(Ishiguro 1990: 9),不過她後來卻變成了主動的敘事者,儘管她的敘述未必完全可信。她的回憶無疑經過刻意謹慎的策略性選擇,因此影響到讀者對她的現況的了解。然而她的記憶裏的空缺與疏漏—或許由於過去曾經發生過她不想提起的事—卻反而在回憶的過程中不斷出現。譬如,悅子尚未講完幸子這對母女的結局,故事便戛然而止。至於喪夫的幸子與她舉止怪異的女兒最後的下落為何,或者她們是否順利移民美國,我們都一無所知。甚至悅子的一生也充滿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們無從得知她的日本丈夫次郎為何不再出現。是因為他們離婚了?或者他過世了?為什麼悅子後來嫁給英國人,而且定居英國?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懸而未決。悅子在提到往事時,往往將自己記憶的空缺與疏漏歸咎於時間的流逝。她說:「我的記憶可能隨時間而模糊了,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我現在記得的那樣」(Ishiguro 1990: 41)。她又輕描淡寫地解釋,一個人的處境會影響其回憶的過程,此之所以記憶會紛陳雜亂而不可靠。她說:「記憶往往是不怎麼可靠的。回憶往往把過去染上不同的色彩。我現在敘述的事自然也不例外」(156)。悅子認為記憶會變得模糊,而且有其局限性,這個看法不無道理。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恐怕是她存心排斥某些記憶,尤其是那些與現在無甚關係卻又無法明言的事情。當她提到次郎與慶子的事情時,她迅速一言帶過, 還說:「這些都是陳年往事了, 我無意再去想這些事。……如今多想以前的事也於事無補」(91)。就這點來看,薛佛(Brian W. Shaffer)的說法是對的。他說:「悅子在壓抑記憶」(Shaffer 1998: 17)。因此就小說的書名而言,或許「淡景」 指的不是群山朦朧,而是視線模糊。悅子的過去就如群山,總在遠方,但她有股逃避回想過去某些事件的意念,使得她刻意封閉自己的視野,從而無法清晰地描述自己的一生。
有論者指出,幸子母女的故事與悅子的故事具有平行關係。以欣席雅‧王(Cynthia F. Wong)為例,她嘗試藉白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自我剝奪」(self-dispossession)概念來解讀《群山淡景》。她表示,透過亡女的生命意義,「悅子訴說自己在長崎的故事。故事聚焦在她和一位叫幸子的女人之間怪異的謎樣友誼。而幸子女兒的行為似乎預告著多年後悅子女兒會走向自殺一途」(Wong 1995: 129)。她進一步指出,幸子有意離開日本移民美國的慾望其實是「悅子多年後所重構的故事」(138)。薛佛更認為悅子「過去與慶子有相處上的困難」(Shaffer 1998: 25),因此幸子母女的故事是悅子心理投射下重建的產物。甚至石黑一雄本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在一次與梅森(Gregory Mason)的訪談中,他被問到悅子與幸子「是否為同一人」時,他答道:
我原先的用意是這樣的:的確悅子是在敘述自己的故事,幸子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悅子賦予幸子身上的某些意義,顯然與悅子的一生有關。不管幸子母女的真實情況為何,悅子之所以會關心她們的事,是因為她要藉由談論這對母女來訴說自己。(Mason 1989: 337)
每一個尚未被當下視為與己有關的過去
意象都有永遠消失的危險。
—班雅明(Benjamin 2003: 391)
一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一部小說《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榮獲一九八三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的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Memorial Prize)。《群山淡景》是一部完全建立在記憶上的敘事文本,內容敘述一位遲暮之年的寡婦如何回憶她在二戰後長崎的生活。另一方面,這也是一部屬於自我分析的小說,因為她的記憶之旅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透過回憶,她想要理解她所身處的當下。石黑一雄以過去與現在的交錯為其敘事形式,小說敘事空間的轉換也是如此,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長崎;另一個是介於一九七○年代後期或八○年代初期的英國。作者駕輕就熟,將此時與彼時、他方與這方相互交融,織就一張敘事的錦繡。
《群山淡景》所講述的其實是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的敘事者都是悅子(Etsuko)。她是位形象端莊的日裔婦女,歷經喪偶,眼前住在英國鄉下。第一個故事圍繞著悅子與幸子(Sachiko)的交誼發展。這兩位女性年紀相仿,幸子來自富裕家庭,不幸婚後丈夫死於戰火,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幸子的故事發生在長崎,時間約莫在一九四○年代末或五○年代初的某個夏天,那時候「韓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跟以前一樣到處都是美國士兵」(Ishiguro 1990: 11)。悅子跟丈夫次郎(Jiro)住在城東,她當時懷了三、四個月的身孕(懷的是她後來取名為慶子〔Keiko〕的女兒)。她在長崎認識了幸子,一位一心一意撫育女兒真理子(Mariko)的母親。跟其他同年紀的小孩不同的是,真理子並未就學。幸子其時跟一個叫法蘭克(Frank)的美國男子交往,法蘭克答應帶她們母女二人到美國生活,不過卻一再食言。石黑一雄對法蘭克的刻畫顯然諧仿的是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裏的美國軍官平克頓(Pinkerton)(參考 Shaffer 1998:21;Lewis 2000: 22-23)。小說的第二個故事發生在英國,此時悅子已是一位中年寡婦。敘事裏的悅子反覆思忖著大女兒慶子的自殺悲劇:慶子一年前在曼徹斯特的租屋裏上吊自盡。先後失去親人的傷痛似乎還籠罩著悅子,因為在女兒結束其青春生命之前,她的丈夫佘寧漢先生(Mr. Sheringham)才離開人世不久。當她陷入對慶子的回憶時,正好二女兒霓紀(Niki)回家來探望她(霓紀是她與英國丈夫所生的女兒)。這段在英國的敘事以霓紀離家前往倫敦結束。
小說的兩段故事都以悅子的遭遇為主軸,她進入過去的唯一通道是她的記憶。在一開始敘述其故事時,她就表示:「容我自私一點,我不想回憶過去」(Ishiguro 1990: 9),不過她後來卻變成了主動的敘事者,儘管她的敘述未必完全可信。她的回憶無疑經過刻意謹慎的策略性選擇,因此影響到讀者對她的現況的了解。然而她的記憶裏的空缺與疏漏—或許由於過去曾經發生過她不想提起的事—卻反而在回憶的過程中不斷出現。譬如,悅子尚未講完幸子這對母女的結局,故事便戛然而止。至於喪夫的幸子與她舉止怪異的女兒最後的下落為何,或者她們是否順利移民美國,我們都一無所知。甚至悅子的一生也充滿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們無從得知她的日本丈夫次郎為何不再出現。是因為他們離婚了?或者他過世了?為什麼悅子後來嫁給英國人,而且定居英國?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懸而未決。悅子在提到往事時,往往將自己記憶的空缺與疏漏歸咎於時間的流逝。她說:「我的記憶可能隨時間而模糊了,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我現在記得的那樣」(Ishiguro 1990: 41)。她又輕描淡寫地解釋,一個人的處境會影響其回憶的過程,此之所以記憶會紛陳雜亂而不可靠。她說:「記憶往往是不怎麼可靠的。回憶往往把過去染上不同的色彩。我現在敘述的事自然也不例外」(156)。悅子認為記憶會變得模糊,而且有其局限性,這個看法不無道理。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恐怕是她存心排斥某些記憶,尤其是那些與現在無甚關係卻又無法明言的事情。當她提到次郎與慶子的事情時,她迅速一言帶過, 還說:「這些都是陳年往事了, 我無意再去想這些事。……如今多想以前的事也於事無補」(91)。就這點來看,薛佛(Brian W. Shaffer)的說法是對的。他說:「悅子在壓抑記憶」(Shaffer 1998: 17)。因此就小說的書名而言,或許「淡景」 指的不是群山朦朧,而是視線模糊。悅子的過去就如群山,總在遠方,但她有股逃避回想過去某些事件的意念,使得她刻意封閉自己的視野,從而無法清晰地描述自己的一生。
有論者指出,幸子母女的故事與悅子的故事具有平行關係。以欣席雅‧王(Cynthia F. Wong)為例,她嘗試藉白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自我剝奪」(self-dispossession)概念來解讀《群山淡景》。她表示,透過亡女的生命意義,「悅子訴說自己在長崎的故事。故事聚焦在她和一位叫幸子的女人之間怪異的謎樣友誼。而幸子女兒的行為似乎預告著多年後悅子女兒會走向自殺一途」(Wong 1995: 129)。她進一步指出,幸子有意離開日本移民美國的慾望其實是「悅子多年後所重構的故事」(138)。薛佛更認為悅子「過去與慶子有相處上的困難」(Shaffer 1998: 25),因此幸子母女的故事是悅子心理投射下重建的產物。甚至石黑一雄本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在一次與梅森(Gregory Mason)的訪談中,他被問到悅子與幸子「是否為同一人」時,他答道:
我原先的用意是這樣的:的確悅子是在敘述自己的故事,幸子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悅子賦予幸子身上的某些意義,顯然與悅子的一生有關。不管幸子母女的真實情況為何,悅子之所以會關心她們的事,是因為她要藉由談論這對母女來訴說自己。(Mason 1989: 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