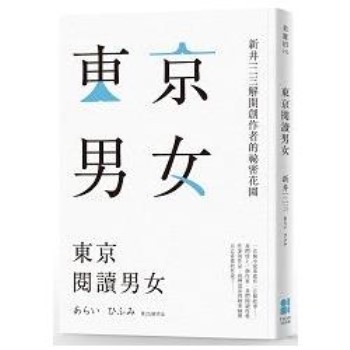痴人和賢者之愛
—─谷崎潤一郎《痴人之愛》與山田詠美《賢者之愛》
說到谷崎潤一郎,外國朋友們一般都當他是《陰翳禮讚》和《細雪》的作者,換句話說是日本傳統審美學的守護神。可是,日本人對他的印象是稍微不一樣的。此間所謂「大谷崎」之所以很「大」,因為他善於把通俗性主題和藝術性形式在崇高的水準上融合為純文學佳作,而他終生拘泥的主題不外是嗜虐和戀物癖。
從一九二四年到二五年,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載的《痴人之愛》,算是谷崎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那是日本短暫的大正摩登時代。二十八歲單身的電氣工程師河合讓治有一個夢想:收養年幼的女孩子而教育成合他口味的情人。果然,老天爺作美,讓治在銀座的酒吧認識了年僅十五歲,外貌似混血兒的奈緒美,從此開始過兩個人的日子。他們之間逐漸演變成奴隸和主人一樣的關係。沒有錯,是讓治心甘情願地淪落為奈緒美的奴隸。
兩個主角的名字讓治和奈緒美,日語發音分別是George和Naomi,加上他們住在位於東京南部大森海岸的出租洋房,整部小說散發著特別洋味的氛圍,可以說跟谷崎後來的作品如《陰翳禮讚》(一九三三年)、《細雪》(一九四八年)的和風世界,相隔十萬八千里。再說,谷崎也公開說《痴人之愛》是「私小說」,至於奈緒美的原型,則一般相信是他第一任夫人的妹妹,當時的電影明星葉山三千子。
將近九十年以前發表的《痴人之愛》,至今在日本仍擁有許多讀者;一說到「奈緒美」就在眾多書迷的腦海中出現共同的形象。於是當二○一五年一月,山田詠美的新作《賢者之愛》問世的時候,書腰上寫的「從正面挑戰文豪谷崎潤一郎」一句話,教大家馬上就領會其含義,以致爭先恐後地購入一本,非得一口氣讀完才痛快了。
我這輩的日本書迷,仍然清楚地記得山田詠美一九八五年以《做愛時的眼神》一書出道時帶來的衝擊。那是年輕日本女孩子和美國黑人逃兵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面上看來,兩者之間只有性愛而沒有靈魂交流似的,卻於存在底層,意外地留下永遠不會消失的烙印。二十世紀後半葉,受到美國的性革命波及,日本的年輕人經驗的,往往就是像她筆下那一對主角那樣的男女關係,因而作品引起了許多同代讀者的強烈共鳴。山田詠美從一開始就善於書寫乍看粗野的男女關係所內含的細膩情感。她以出道作品獲得文藝賞,兩年後又以《戀人才聽得見的靈魂樂》得到直木賞,二○○○年則以《A2Z》獲得讀賣文學賞,二○○五年終於以《無法隨心所欲的愛情,風味絕佳》獲得了谷崎潤一郎賞。另外,出道不久的一九八八年,她也寫過《跪下來舔我的腳》,乃以SM俱樂部的「女皇」為主角的半自傳體小說。果然,她跟谷崎的小說世界頗有重疊之處。但是,這回從正面挑戰「大谷崎」,還是出乎大家意料了;畢竟﹁大谷崎﹂的名氣能跟三島由紀夫等超級大作家相比,可說屬於諾貝爾獎級別的。
山田詠美小說《賢者之愛》的男女主角是,快要四十五歲的出版社編輯真由子和剛過了二十三歲生日的直巳,而「直巳」的日文讀音就是跟奈緒美一樣的Naomi,使讀者以為這是《痴人之愛》的翻版,交換了男女角色,而取名為《賢者之愛》。然而,真由子和直巳其實不是像讓治和奈緒美那樣在風化場所認識的。反之,直巳的母親是真由子從小的朋友百合,他父親又是真由子從小的偶像諒一。也就是說,真由子被百合奪走了諒一,後來就跟他們的孩子發生關係。難道她是為了報復情敵,才把她兒子當性愛寵物培養嗎?實際上,包括真由子的已故父親在內的三代五角關係裡,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奴隸?可見山田詠美創造出來的小說世界,比單純色情的《痴人之愛》複雜得多。
《賢者之愛》的封面和內頁,都配著幻想怪異派漫畫家丸尾末廣畫的繪圖,給作品增添有如二十世紀少女漫畫雜誌上時而出現的恐怖作品一般委婉卻性感的氣味。日本各家報社的書評都給了《賢者之愛》五顆星星。也不奇怪,跟這部刁難讀者的新作相比,古典作品《痴人之愛》的男性中心觀點可說是傻到可愛。山田詠美出道正好三十週年的今天,至少對女性心理的掌握而言,連「大谷崎」都不是她的對手了。
世界級作家與他的老讀者
—村上春樹《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村上春樹的新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於二○一三年四月十二日上市,東京好幾家大書店都比平時早兩個鐘頭開門,至於通宵營業的書店則在深夜零點整就開始出售,據報導鬧區好幾家書店門口都出現了人龍。這種部署,雖然在電腦行業有過不少前例,但是在出版業,除了人氣最高時的《哈利波特》以外,至少在日本是前所未聞的。出版社文藝春秋最初打算首刷三十萬本,然而在亞遜等網路書店的預售量極多,結果商品還沒上市之前,印刷廠已經接到四刷的指示。這則消息一傳出去,愛湊熱鬧的日本人更加爭先恐後地去書店掏腰包,一個星期以內,銷售量達到了一百萬本。
考慮到從二○○九年到二○一○年發表的《1Q84》,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共賣了七百萬本,這次的成績也不算太離譜。只是,在出版業不景氣的日本,前一年最暢銷的小說是三浦紫苑的《啟航吧!編舟計畫》,銷量僅五十六萬本,而在暢銷書榜上頭十名內,那是唯一的小說。就純文學來說,同一年的芥川賞作品是田中慎彌的《共食者》,由於作者在得獎時公開揶揄了文壇大前輩石原慎太郎而成了社會新聞,比近年的同一獎項作品引起較大的注目,可是發行量也才二十萬本。可見村上春樹在日本文壇、出版界所占的地位多麼特別突出。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七天銷量達一百萬本的小說是平時不看書的很多人購買的。他們買了以後到底有沒有看,覺不覺得有意思,則無法得知。同時,對多數行家來說,七天銷量達一百萬本的小說是無法平心評論的。各家報紙的書評人,自己也是寫文章出書的人,對村上一級的大作家,不能不羨慕、不能不嫉妒,結果褒也不是貶也不對,因此至少在短時間裡,不大會出現中肯有分量的評論。
不過,新書出來以後,幾個書評人不約而同地寫道:我們曾熟悉的村上春樹到底去哪兒了?那估計是不少老讀者共同的真實感受。一九七九年,三十歲的村上以《聽風的歌》出道,然後從八○年的《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八二年的《尋羊冒險記》、八五年的《世界末日與冷酷意境》,直到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他著實是一代日本書迷寵愛不已的偶像。回頭看來,那段蜜月的終結和村上的大眾化以及世界化是同時發生的。爆紅的《挪威的森林》賣出破紀錄的四百三十萬本,使得生性內向的作者被嚇壞,之後,他很少出現在日本媒體了。同時,作品的英譯本、中譯本,其他外語本陸續問世,村上春樹的名氣在各國都越來越大。一九九○年,美國《紐約客》雜誌開始刊登他短篇小說的英譯,村上正式進入了世界文學之列。小說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一方面很公然另一方面則很私密。曾經私下寵愛的對象,翻身為全世界的戀人以後,老讀者感到寂寞,雖然沒有道理但是情有可原。尤其,諾貝爾委員會對他有興趣的消息傳播開來以後,不少日本人似乎感到被放棄、出賣,好比親愛的姐妹被外國的老富翁看中了一般。
三十歲出道的村上,如今已經是過了花甲的大作家了。有人看他新書而想起《挪威的森林》或者《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但這次的主人翁多崎作不屬於村上一輩,而屬於他兒子一輩,雖然作者自己沒有孩子。老讀者曾熟悉的村上春樹也許早已不再了,好在作品將一直存在,正如我們對青春的記憶都永遠燦爛。
我如何成為了中文作家
──二○一五年七月十九日,香港書展演講稿
(摘錄)
我當初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寫這麼多中文書的;畢竟我是日本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又全是日本人。在我長大的環境裡,家裡、周圍都沒有人講中國話,更不用說看中文書、寫中文書了。這(照片一)是一九九五年,整整二十年以前,我出的第一本中文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也就是說,我的中文寫作生涯,其實是從香港這個地方開始。
來香港書展演講,我是去年第一次收到的邀請。可是,去年各方面都無法調整,沒能來。今年,又收到香港來的電郵,寫著這次的總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覺得特別巧。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曾有過「從香港閱讀世界」的親身經驗。至於「一讀鍾情」,更不止一次了,好像有過三、四次的「一讀鍾情」促使我用中文寫作。所以,這次,我怎麼也要來講講自己的: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一九八一年上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才開始學中文。中文是我的第二外語。當年在日本,每個大學生除了英語以外,都還得學一門外語。在我們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外語的選擇有:德語、法語、俄語和漢語。大多數學生,要麼選修德語或者選修法語。畢竟,自從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一直向西方學現代化的;民法學法國的,刑法學德國的。另外,法國有沙特、卡繆,德國則有湯瑪斯‧曼、赫曼‧赫塞,因此上大學讀法語、德語,對日本學生來說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選擇。俄語呢,就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語言了,而二十世紀日本的社會科學,在很多方面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所以,大學的社會學科也一定教俄語。
結果,政治經濟學系一年級的學生,分成三十個外語班,其中漢語班只有兩個,一百名學生而已。而在那一百個學生裡面,我偏偏是唯一的女學生,百分之一。這麼一來,老師每次進教室來,都很自然地找找我在不在。班上唯一的女學生是沒辦法曠課,也沒辦法偷偷睡著的。所以,雖然是一個星期只有兩堂課的第二外語,我非得認真學習不可了。
好在我跟漢語普通話, 顯然很有緣分, 從第一次上課開始,我對它很有好感,非常喜歡。最初,我主要覺得有聲調的語言很好玩,聽起來悅耳,說起來又跟唱歌一樣令人高興。可以說,我發現學中文帶來感官上的快樂。那是第一次的「一讀鍾情」,或者說「豔遇」吧。
……
常有人問我: 一個日本人, 為什麼用中文寫作? 我最初說,寫文章就是寫文章,人家要我用日文,我就用日文寫;人家要我用英文,我就用英文寫;人家要我用中文,我就用中文寫罷了。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當初一九八○、九○年代,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人少到幾乎沒有,所以我用中文寫,需求反而最多。另外,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中文是外語,寫起來,不可能像母語那樣流暢快速。反之,需要去找一個接一個合適的詞串下去,猶如串珠鍊,猶如寫詩歌一樣。那感覺,給我帶來創作的樂趣,乃寫日文時感覺不到的。從一九八七年底到九四年初, 我居住於加拿大多倫多。當時那裡共有五個唐人街,有講台山話的老華僑,從香港、台灣去的新移民,也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彼此間,背景不一樣,政治上的認同、說話的口音也各有各的,但是大家吃的都是中國菜,於是都到唐人街買菜,而且順便買中文報紙、雜誌。報紙的話,他們買北美刊行的中文報,因為新聞講新鮮。雜誌呢,則要買香港出版的了。好比是東京的馬來西亞華人買香港雜誌一樣,北美的中國人、華人都看香港雜誌取得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等等的信息。香港報刊的讀者,在南洋、在日本不在話下,遠在北美、歐洲、澳洲、紐西蘭都有,當年簡直分布於全球,因為全球每個地方都有中國人、華人看中文雜誌。
一九九○年代初,我在加拿大每個月寫一篇中文文章,寄到香港去發表。神奇的是,我最初用航空信件郵寄過去,後來用傳真發過去的文章,兩、三個星期以後登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再過幾天,不僅我本人在多倫多公寓的信箱裡收到,而且在唐人街的書店都出售了。當時在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的留學生宿舍裡,一份香港雜誌在好幾十個中國留學生、華人留學生之間傳閱。結果,我在多倫多唐人街,不知幾次遇到過專欄的讀者,是因為我的名字有點特別,很容易被別人發現所致。
另外,香港編輯部轉來的讀者來信,有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漢學家寄來的,也有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裡的華人橡膠園主寄來的。通過一份香港月刊上的小專欄,我說,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擁有了讀者,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九○年代末,網際網路普及之前,那可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直接聽到讀者的反應是無比大的回報。我對中文寫作逐漸上癮,戒不掉,恐怕最大的原因是這一點:到處都有讀者。我離開加拿大以後, 從一九九四年四月到九七年七月,在殖民統治末期的香港居住了三年三個月。在那段時間裡,我除了給日本媒體寫稿件之外,還替《星島日報》、《信報》、《明報》、《蘋果日報》等等香港報紙, 寫過專欄。在全世界,當年香港無疑是報紙種類最多的城市,而且每份報紙每天刊登好多個專欄,所以香港也應該是全世界專欄作家最多的地方了。住在香港的一九九五年,我出了第一本中文書。記得當時有個香港作家告訴我說:香港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是,至少出過兩本書,因為在這裡,出過一本書的舞女、吧女特別多。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同一個月我也回到日本去了。這之後的六、七年時間,我大體上為台灣報紙、雜誌寫中文文章。最初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寫了前後三年的〈三少四壯集〉,後來也在《中央日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聯合報》以及多份雜誌上寫過專欄。並且從社刊行散文集。
由於歷史因素, 台灣讀者對日本事物很有興趣, 而且對日本事物有興趣的台灣讀者又非常多。日本時代過來的老年人有懷舊的心情。戰後長大的一代,則對父母、祖父母時代的台灣抱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恐怕是因為他們曾經被禁止知道日治時期的歷史。例如電影《海角七號》的魏德聖導演,我跟他對談以後才真正明白:他對日本的興趣其實完全來自他對台灣歷史的興趣。我二○一○年出了一本台灣專書《臺灣為何教我哭?》,是獻給魏德聖導演的。
(演講稿全文未完)
—─谷崎潤一郎《痴人之愛》與山田詠美《賢者之愛》
說到谷崎潤一郎,外國朋友們一般都當他是《陰翳禮讚》和《細雪》的作者,換句話說是日本傳統審美學的守護神。可是,日本人對他的印象是稍微不一樣的。此間所謂「大谷崎」之所以很「大」,因為他善於把通俗性主題和藝術性形式在崇高的水準上融合為純文學佳作,而他終生拘泥的主題不外是嗜虐和戀物癖。
從一九二四年到二五年,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載的《痴人之愛》,算是谷崎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那是日本短暫的大正摩登時代。二十八歲單身的電氣工程師河合讓治有一個夢想:收養年幼的女孩子而教育成合他口味的情人。果然,老天爺作美,讓治在銀座的酒吧認識了年僅十五歲,外貌似混血兒的奈緒美,從此開始過兩個人的日子。他們之間逐漸演變成奴隸和主人一樣的關係。沒有錯,是讓治心甘情願地淪落為奈緒美的奴隸。
兩個主角的名字讓治和奈緒美,日語發音分別是George和Naomi,加上他們住在位於東京南部大森海岸的出租洋房,整部小說散發著特別洋味的氛圍,可以說跟谷崎後來的作品如《陰翳禮讚》(一九三三年)、《細雪》(一九四八年)的和風世界,相隔十萬八千里。再說,谷崎也公開說《痴人之愛》是「私小說」,至於奈緒美的原型,則一般相信是他第一任夫人的妹妹,當時的電影明星葉山三千子。
將近九十年以前發表的《痴人之愛》,至今在日本仍擁有許多讀者;一說到「奈緒美」就在眾多書迷的腦海中出現共同的形象。於是當二○一五年一月,山田詠美的新作《賢者之愛》問世的時候,書腰上寫的「從正面挑戰文豪谷崎潤一郎」一句話,教大家馬上就領會其含義,以致爭先恐後地購入一本,非得一口氣讀完才痛快了。
我這輩的日本書迷,仍然清楚地記得山田詠美一九八五年以《做愛時的眼神》一書出道時帶來的衝擊。那是年輕日本女孩子和美國黑人逃兵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面上看來,兩者之間只有性愛而沒有靈魂交流似的,卻於存在底層,意外地留下永遠不會消失的烙印。二十世紀後半葉,受到美國的性革命波及,日本的年輕人經驗的,往往就是像她筆下那一對主角那樣的男女關係,因而作品引起了許多同代讀者的強烈共鳴。山田詠美從一開始就善於書寫乍看粗野的男女關係所內含的細膩情感。她以出道作品獲得文藝賞,兩年後又以《戀人才聽得見的靈魂樂》得到直木賞,二○○○年則以《A2Z》獲得讀賣文學賞,二○○五年終於以《無法隨心所欲的愛情,風味絕佳》獲得了谷崎潤一郎賞。另外,出道不久的一九八八年,她也寫過《跪下來舔我的腳》,乃以SM俱樂部的「女皇」為主角的半自傳體小說。果然,她跟谷崎的小說世界頗有重疊之處。但是,這回從正面挑戰「大谷崎」,還是出乎大家意料了;畢竟﹁大谷崎﹂的名氣能跟三島由紀夫等超級大作家相比,可說屬於諾貝爾獎級別的。
山田詠美小說《賢者之愛》的男女主角是,快要四十五歲的出版社編輯真由子和剛過了二十三歲生日的直巳,而「直巳」的日文讀音就是跟奈緒美一樣的Naomi,使讀者以為這是《痴人之愛》的翻版,交換了男女角色,而取名為《賢者之愛》。然而,真由子和直巳其實不是像讓治和奈緒美那樣在風化場所認識的。反之,直巳的母親是真由子從小的朋友百合,他父親又是真由子從小的偶像諒一。也就是說,真由子被百合奪走了諒一,後來就跟他們的孩子發生關係。難道她是為了報復情敵,才把她兒子當性愛寵物培養嗎?實際上,包括真由子的已故父親在內的三代五角關係裡,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奴隸?可見山田詠美創造出來的小說世界,比單純色情的《痴人之愛》複雜得多。
《賢者之愛》的封面和內頁,都配著幻想怪異派漫畫家丸尾末廣畫的繪圖,給作品增添有如二十世紀少女漫畫雜誌上時而出現的恐怖作品一般委婉卻性感的氣味。日本各家報社的書評都給了《賢者之愛》五顆星星。也不奇怪,跟這部刁難讀者的新作相比,古典作品《痴人之愛》的男性中心觀點可說是傻到可愛。山田詠美出道正好三十週年的今天,至少對女性心理的掌握而言,連「大谷崎」都不是她的對手了。
世界級作家與他的老讀者
—村上春樹《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村上春樹的新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於二○一三年四月十二日上市,東京好幾家大書店都比平時早兩個鐘頭開門,至於通宵營業的書店則在深夜零點整就開始出售,據報導鬧區好幾家書店門口都出現了人龍。這種部署,雖然在電腦行業有過不少前例,但是在出版業,除了人氣最高時的《哈利波特》以外,至少在日本是前所未聞的。出版社文藝春秋最初打算首刷三十萬本,然而在亞遜等網路書店的預售量極多,結果商品還沒上市之前,印刷廠已經接到四刷的指示。這則消息一傳出去,愛湊熱鬧的日本人更加爭先恐後地去書店掏腰包,一個星期以內,銷售量達到了一百萬本。
考慮到從二○○九年到二○一○年發表的《1Q84》,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共賣了七百萬本,這次的成績也不算太離譜。只是,在出版業不景氣的日本,前一年最暢銷的小說是三浦紫苑的《啟航吧!編舟計畫》,銷量僅五十六萬本,而在暢銷書榜上頭十名內,那是唯一的小說。就純文學來說,同一年的芥川賞作品是田中慎彌的《共食者》,由於作者在得獎時公開揶揄了文壇大前輩石原慎太郎而成了社會新聞,比近年的同一獎項作品引起較大的注目,可是發行量也才二十萬本。可見村上春樹在日本文壇、出版界所占的地位多麼特別突出。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七天銷量達一百萬本的小說是平時不看書的很多人購買的。他們買了以後到底有沒有看,覺不覺得有意思,則無法得知。同時,對多數行家來說,七天銷量達一百萬本的小說是無法平心評論的。各家報紙的書評人,自己也是寫文章出書的人,對村上一級的大作家,不能不羨慕、不能不嫉妒,結果褒也不是貶也不對,因此至少在短時間裡,不大會出現中肯有分量的評論。
不過,新書出來以後,幾個書評人不約而同地寫道:我們曾熟悉的村上春樹到底去哪兒了?那估計是不少老讀者共同的真實感受。一九七九年,三十歲的村上以《聽風的歌》出道,然後從八○年的《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八二年的《尋羊冒險記》、八五年的《世界末日與冷酷意境》,直到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他著實是一代日本書迷寵愛不已的偶像。回頭看來,那段蜜月的終結和村上的大眾化以及世界化是同時發生的。爆紅的《挪威的森林》賣出破紀錄的四百三十萬本,使得生性內向的作者被嚇壞,之後,他很少出現在日本媒體了。同時,作品的英譯本、中譯本,其他外語本陸續問世,村上春樹的名氣在各國都越來越大。一九九○年,美國《紐約客》雜誌開始刊登他短篇小說的英譯,村上正式進入了世界文學之列。小說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一方面很公然另一方面則很私密。曾經私下寵愛的對象,翻身為全世界的戀人以後,老讀者感到寂寞,雖然沒有道理但是情有可原。尤其,諾貝爾委員會對他有興趣的消息傳播開來以後,不少日本人似乎感到被放棄、出賣,好比親愛的姐妹被外國的老富翁看中了一般。
三十歲出道的村上,如今已經是過了花甲的大作家了。有人看他新書而想起《挪威的森林》或者《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但這次的主人翁多崎作不屬於村上一輩,而屬於他兒子一輩,雖然作者自己沒有孩子。老讀者曾熟悉的村上春樹也許早已不再了,好在作品將一直存在,正如我們對青春的記憶都永遠燦爛。
我如何成為了中文作家
──二○一五年七月十九日,香港書展演講稿
(摘錄)
我當初怎麼也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寫這麼多中文書的;畢竟我是日本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又全是日本人。在我長大的環境裡,家裡、周圍都沒有人講中國話,更不用說看中文書、寫中文書了。這(照片一)是一九九五年,整整二十年以前,我出的第一本中文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也就是說,我的中文寫作生涯,其實是從香港這個地方開始。
來香港書展演講,我是去年第一次收到的邀請。可是,去年各方面都無法調整,沒能來。今年,又收到香港來的電郵,寫著這次的總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覺得特別巧。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曾有過「從香港閱讀世界」的親身經驗。至於「一讀鍾情」,更不止一次了,好像有過三、四次的「一讀鍾情」促使我用中文寫作。所以,這次,我怎麼也要來講講自己的: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我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一九八一年上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才開始學中文。中文是我的第二外語。當年在日本,每個大學生除了英語以外,都還得學一門外語。在我們早大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外語的選擇有:德語、法語、俄語和漢語。大多數學生,要麼選修德語或者選修法語。畢竟,自從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是一直向西方學現代化的;民法學法國的,刑法學德國的。另外,法國有沙特、卡繆,德國則有湯瑪斯‧曼、赫曼‧赫塞,因此上大學讀法語、德語,對日本學生來說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選擇。俄語呢,就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語言了,而二十世紀日本的社會科學,在很多方面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所以,大學的社會學科也一定教俄語。
結果,政治經濟學系一年級的學生,分成三十個外語班,其中漢語班只有兩個,一百名學生而已。而在那一百個學生裡面,我偏偏是唯一的女學生,百分之一。這麼一來,老師每次進教室來,都很自然地找找我在不在。班上唯一的女學生是沒辦法曠課,也沒辦法偷偷睡著的。所以,雖然是一個星期只有兩堂課的第二外語,我非得認真學習不可了。
好在我跟漢語普通話, 顯然很有緣分, 從第一次上課開始,我對它很有好感,非常喜歡。最初,我主要覺得有聲調的語言很好玩,聽起來悅耳,說起來又跟唱歌一樣令人高興。可以說,我發現學中文帶來感官上的快樂。那是第一次的「一讀鍾情」,或者說「豔遇」吧。
……
常有人問我: 一個日本人, 為什麼用中文寫作? 我最初說,寫文章就是寫文章,人家要我用日文,我就用日文寫;人家要我用英文,我就用英文寫;人家要我用中文,我就用中文寫罷了。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當初一九八○、九○年代,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人少到幾乎沒有,所以我用中文寫,需求反而最多。另外,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中文是外語,寫起來,不可能像母語那樣流暢快速。反之,需要去找一個接一個合適的詞串下去,猶如串珠鍊,猶如寫詩歌一樣。那感覺,給我帶來創作的樂趣,乃寫日文時感覺不到的。從一九八七年底到九四年初, 我居住於加拿大多倫多。當時那裡共有五個唐人街,有講台山話的老華僑,從香港、台灣去的新移民,也有從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彼此間,背景不一樣,政治上的認同、說話的口音也各有各的,但是大家吃的都是中國菜,於是都到唐人街買菜,而且順便買中文報紙、雜誌。報紙的話,他們買北美刊行的中文報,因為新聞講新鮮。雜誌呢,則要買香港出版的了。好比是東京的馬來西亞華人買香港雜誌一樣,北美的中國人、華人都看香港雜誌取得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等等的信息。香港報刊的讀者,在南洋、在日本不在話下,遠在北美、歐洲、澳洲、紐西蘭都有,當年簡直分布於全球,因為全球每個地方都有中國人、華人看中文雜誌。
一九九○年代初,我在加拿大每個月寫一篇中文文章,寄到香港去發表。神奇的是,我最初用航空信件郵寄過去,後來用傳真發過去的文章,兩、三個星期以後登在香港出版的雜誌上,再過幾天,不僅我本人在多倫多公寓的信箱裡收到,而且在唐人街的書店都出售了。當時在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的留學生宿舍裡,一份香港雜誌在好幾十個中國留學生、華人留學生之間傳閱。結果,我在多倫多唐人街,不知幾次遇到過專欄的讀者,是因為我的名字有點特別,很容易被別人發現所致。
另外,香港編輯部轉來的讀者來信,有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漢學家寄來的,也有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裡的華人橡膠園主寄來的。通過一份香港月刊上的小專欄,我說,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擁有了讀者,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九○年代末,網際網路普及之前,那可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直接聽到讀者的反應是無比大的回報。我對中文寫作逐漸上癮,戒不掉,恐怕最大的原因是這一點:到處都有讀者。我離開加拿大以後, 從一九九四年四月到九七年七月,在殖民統治末期的香港居住了三年三個月。在那段時間裡,我除了給日本媒體寫稿件之外,還替《星島日報》、《信報》、《明報》、《蘋果日報》等等香港報紙, 寫過專欄。在全世界,當年香港無疑是報紙種類最多的城市,而且每份報紙每天刊登好多個專欄,所以香港也應該是全世界專欄作家最多的地方了。住在香港的一九九五年,我出了第一本中文書。記得當時有個香港作家告訴我說:香港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是,至少出過兩本書,因為在這裡,出過一本書的舞女、吧女特別多。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同一個月我也回到日本去了。這之後的六、七年時間,我大體上為台灣報紙、雜誌寫中文文章。最初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寫了前後三年的〈三少四壯集〉,後來也在《中央日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聯合報》以及多份雜誌上寫過專欄。並且從社刊行散文集。
由於歷史因素, 台灣讀者對日本事物很有興趣, 而且對日本事物有興趣的台灣讀者又非常多。日本時代過來的老年人有懷舊的心情。戰後長大的一代,則對父母、祖父母時代的台灣抱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恐怕是因為他們曾經被禁止知道日治時期的歷史。例如電影《海角七號》的魏德聖導演,我跟他對談以後才真正明白:他對日本的興趣其實完全來自他對台灣歷史的興趣。我二○一○年出了一本台灣專書《臺灣為何教我哭?》,是獻給魏德聖導演的。
(演講稿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