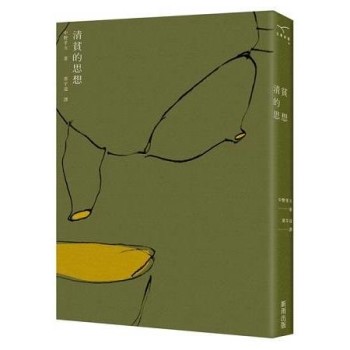三、如果自己心中有愧──本阿彌光德與光甫的鑑刀之眼
一種思想,在一個時期不僅僅侷限於單一個體的生活方式,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生活。因此,我們有必要繞開一下,來觀察妙秀的思想是怎樣被她的後代所繼承。
前面已經說過,本阿彌家族自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將軍足利尊時期開始,即以刀劍鑒賞、研磨作為家業,妙秀和光悅的倫理道德觀同時貫穿於整個家業的流傳過程中。寫作《本阿彌行狀記》的光悅之孫空中齋光甫根據自己的經驗,將此事完整的記載在《本阿彌行狀記》一書中。
光甫滯留在江戶的某一天,被邀至松平安藝守的公館,武士今田四郎左衛門拿出一把插在古鞘中的鏽刀,恭恭敬敬的請求道:
「吾主囑我將此換金幣二枚,故四方求助,找人鑒看。而至今沒一個人看得上眼,奈何!尊駕能幫我鑒定一下嗎?」
光甫接過刀來仔細端詳,刀身上的銘文都已經模糊不清了,且鏽蝕不堪。但光甫立即判定這是一把寶刀。他說:
「不用再找別人了,你想出讓的話,不管什麼價格,我都願意買下,只是,可不許反悔哦。」
在場的寺西將監、淺野數馬等一群重臣見光甫這麼說,都有些疑惑不解:
「哎呀,你好像對這把刀特別中意,我們可怎麼也看不出這刀有什麼好的?」
光甫相信自己的眼光沒錯,斷言這是一把正宗寶刀。眾人都對這意外的情況感到訝異。雖然是武士,如果缺乏鑒賞眼光的話,自然無法透過鏽蝕的刀身,發現其真正的價值。
於是光甫便帶著這刀回到京都。此刀一經研磨,便光芒四射,誰看了都愛不釋手。族長光溫看了光甫拿來請教的此刀後,同樣肯定了光甫的判斷。光溫在刀身上附上價值金幣兩百五十枚的標籤,更嵌刻上「正宗」二字。在那個時代,本阿彌家族的鑒定就是有這樣的權威。
在松平家今田四郎以兩枚金幣的價格出售時,要是別的商人,一定會裝作不知情的樣子,就順勢以兩枚金幣買下。這也算不上什麼大惡事,不過是白撿了一份便宜而已。但在本阿彌家看來,以鑒賞刀劍為業的眼光既已看出真正的價值,而趁對方毫不知情之機去收買,無異於掠奪,是一件令人羞恥的行為。重要的不是金錢,自己家族在鑒賞刀劍方面的權威才令人值得誇耀與自負,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執迷於金錢,使家族的威望受到損害,無疑比死還要可怕。先前妙秀為小袖屋的瀨戶肩衝茶罐一事曾對光悅說:「你拿了那銀子的話,再好的珍品也成了俗物,你這一生也就無法再領略茶道的妙處了。」
這種思想,在他們的家業—刀劍鑒賞中同樣一脈相承。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而是自己內心的原則。哪怕是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自己心中有愧,就無法寬恕自己。這才是他們最為看重的事,和那些見錢眼開,再骯髒的錢也拿得心安理得的人,無疑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光溫的祖父名人光德有這麼一段逸事流傳下來。
有一次,德川家康將一把平日祕不示人的短刀拿給光德看。此刀原為前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的鎮宅之寶,附有足利尊氏本人的親筆字條。是德川家康極為心愛的寶貝。
光德在御前細看了很久,誠實的對家康稟道:「此刀被重新燒鑄過,已是一件廢品。」聽了光德的話,德川家康頓時沉下臉來。
光德進而又說:「雖然附有足利尊氏的字條,但這說明不了問題。足利尊氏本人並不是刀劍鑒賞家,何況在他手上的刀還是新的。」
話說得這麼斬釘截鐵,毫無迴轉餘地,德川家康從此再也沒有召見過他。光德認為即使在最高當權者德川家康面前,要他說出違背自己本心的話,還不如去死。毫不畏懼地直言自己的真實所見,這才是光德。自己才是刀劍鑒賞的絕對權威,這種驕傲哪怕是在最高當權者面前也絕不改變。
《本阿彌行狀記》在這段逸事後解釋道:不管是多麼魯鈍、不善諂媚的人,知道這是將軍的祕藏之寶,又是在御前群臣面前,大概沒有人會純真到會說出這刀是廢品之類的話。
由此可見,本阿彌家族最看重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誠實,對社會有時也要有近乎愚昧的剛直。比起待人接物的圓滑,他們更怕違背自己的本心。這一定是當時日本社會相當珍貴的心靈思想。
他們這麼早就擁有這種近代人的意識,我以為是由於這個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換而言之,正是由於在內心深處有可畏懼的神佛存在,才不須他人的外力規範,能夠自己約束自己。這個家族從第六代幕府將軍足利義教時,本阿彌清信在獄中皈依了日蓮宗的日親上人—因為不屈服於頭戴烤鍋的刑罰,被世人稱為戴鍋日親—改名本光以後,每代人都將頭髮剃光,並以光字命名,是非常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本阿彌家族和京都的本法寺的淵源極深,可稱外護法。此後家族中甚至有人出家皈依佛門,可以說是以本法寺為精神支柱的體現。
光悅自從德川家康賜下鷹峰之地後,就在這片土地上修造了常照寺、妙秀寺、光悅寺、知足庵四座寺廟,每天醉心修行。由於敬畏神佛,即便不為世人所知,也絕不放任自己做出違背信仰的事。這便是本阿彌家族中剛直不阿的精神傳統。
《本阿彌行狀記》在談到光悅的信仰時這麼寫道:
家父光悅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尤信日蓮宗。
先前的光德同樣如此,光悅在這裡更被特別強調「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可見已與日蓮精神結合成為一體了。
光甫在談起自己家族時說:
「本阿彌家族沒有一個具大智慧的人,至今卻仍然得到神佛庇佑,那是由於先祖的品德。因為畏懼天命、相信善惡報應,才不做違反人道的事,更不會擅行惡事。
「尤其在刀劍鑒定方面,因為是家族的頭等大事,必須眼光銳利,心無旁騖者才行。心有陰霾之人是不可能準確鑒定的。這方面有很多例子,現茲舉以下若干事例……」
於是說出光德見德川家康之刀而不阿諛的故事。
換言之,必先有了「畏懼天命」之心,才會恐懼那凡人看不見的存在,才絕對不敢做出違背本心的行為,依從自己本來的意願生活下去。這種心境同樣體現在刀劍鑒賞的家業方面,所以本阿彌家族的眼光才會出乎想像的嚴格。人生信仰和職業倫理就這樣合為一體。我們由此可知,與近代基督新教嚴厲的倫理觀大致相同的意識,已經在這家族中形成。
說得更遠一點,前不久,我在讀菲利普‧梅森的《英國紳士》一書時,發現書中有關紳士的一些論述和《本阿彌行狀記》中的記載非常相似,心裡感到極其愉快。比如在論及名譽時,書中如此敘述:
名譽乃紳士不可或缺的,對威爾來說,名譽不僅是世人對自己的評價,同樣意味著自尊心—從而亦指高潔、圓滿和自足;並且應予輕視金錢。這應是本質的。(略)威爾一文不名,但他確信無形的人格比金錢更重要。這裡說的名譽,即自尊心,也就是無形的人格。如果這段話就這麼換成《本阿彌行狀記》中的人物也絕不奇怪。不,如果在那個時代也有這種語言的話,他們一定也會那樣說的。
由此,我對現代日本商人在海外被認為「滿口都是關於金錢的話題,凡事只知用金錢去衡量」的評語感到十分悲哀。對一個紳士而言,在社交場合絕對應該迴避金錢這個話題,如果在一個崇尚藝術的國度,當人談論起繪畫的美學問題時,卻插言高談此畫的拍賣價格,豈不是太煞風景了嗎?
日本人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以前,他們不願在人面前談論金錢,尊重高潔的行為,把名譽看得至高無上。論天下國家時,我認為日本人討厭那些滿腦子充滿利益算計的傢伙,更重視那些坦率的陳述己見,有頭腦、有見識的人。所以本阿彌家族的故事才會如此詳盡的流傳至今。我相信,日本值得誇耀於世的,並不是躋身經濟大國,也不是成為貿易輸出大國,而是人世間最重要的「無形的人格」。
我知道,現代也有不少人敬畏這種「眼睛看不見的存在」,不會做令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擁有自己價值準則的人。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只熱衷於交易、賺錢,對金額數字之外的事物不感興趣。如果日本人皆是後者,那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我以光悅和妙秀為例,強調日本也還有這樣的人物。
一種思想,在一個時期不僅僅侷限於單一個體的生活方式,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生活。因此,我們有必要繞開一下,來觀察妙秀的思想是怎樣被她的後代所繼承。
前面已經說過,本阿彌家族自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將軍足利尊時期開始,即以刀劍鑒賞、研磨作為家業,妙秀和光悅的倫理道德觀同時貫穿於整個家業的流傳過程中。寫作《本阿彌行狀記》的光悅之孫空中齋光甫根據自己的經驗,將此事完整的記載在《本阿彌行狀記》一書中。
光甫滯留在江戶的某一天,被邀至松平安藝守的公館,武士今田四郎左衛門拿出一把插在古鞘中的鏽刀,恭恭敬敬的請求道:
「吾主囑我將此換金幣二枚,故四方求助,找人鑒看。而至今沒一個人看得上眼,奈何!尊駕能幫我鑒定一下嗎?」
光甫接過刀來仔細端詳,刀身上的銘文都已經模糊不清了,且鏽蝕不堪。但光甫立即判定這是一把寶刀。他說:
「不用再找別人了,你想出讓的話,不管什麼價格,我都願意買下,只是,可不許反悔哦。」
在場的寺西將監、淺野數馬等一群重臣見光甫這麼說,都有些疑惑不解:
「哎呀,你好像對這把刀特別中意,我們可怎麼也看不出這刀有什麼好的?」
光甫相信自己的眼光沒錯,斷言這是一把正宗寶刀。眾人都對這意外的情況感到訝異。雖然是武士,如果缺乏鑒賞眼光的話,自然無法透過鏽蝕的刀身,發現其真正的價值。
於是光甫便帶著這刀回到京都。此刀一經研磨,便光芒四射,誰看了都愛不釋手。族長光溫看了光甫拿來請教的此刀後,同樣肯定了光甫的判斷。光溫在刀身上附上價值金幣兩百五十枚的標籤,更嵌刻上「正宗」二字。在那個時代,本阿彌家族的鑒定就是有這樣的權威。
在松平家今田四郎以兩枚金幣的價格出售時,要是別的商人,一定會裝作不知情的樣子,就順勢以兩枚金幣買下。這也算不上什麼大惡事,不過是白撿了一份便宜而已。但在本阿彌家看來,以鑒賞刀劍為業的眼光既已看出真正的價值,而趁對方毫不知情之機去收買,無異於掠奪,是一件令人羞恥的行為。重要的不是金錢,自己家族在鑒賞刀劍方面的權威才令人值得誇耀與自負,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執迷於金錢,使家族的威望受到損害,無疑比死還要可怕。先前妙秀為小袖屋的瀨戶肩衝茶罐一事曾對光悅說:「你拿了那銀子的話,再好的珍品也成了俗物,你這一生也就無法再領略茶道的妙處了。」
這種思想,在他們的家業—刀劍鑒賞中同樣一脈相承。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而是自己內心的原則。哪怕是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自己心中有愧,就無法寬恕自己。這才是他們最為看重的事,和那些見錢眼開,再骯髒的錢也拿得心安理得的人,無疑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光溫的祖父名人光德有這麼一段逸事流傳下來。
有一次,德川家康將一把平日祕不示人的短刀拿給光德看。此刀原為前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的鎮宅之寶,附有足利尊氏本人的親筆字條。是德川家康極為心愛的寶貝。
光德在御前細看了很久,誠實的對家康稟道:「此刀被重新燒鑄過,已是一件廢品。」聽了光德的話,德川家康頓時沉下臉來。
光德進而又說:「雖然附有足利尊氏的字條,但這說明不了問題。足利尊氏本人並不是刀劍鑒賞家,何況在他手上的刀還是新的。」
話說得這麼斬釘截鐵,毫無迴轉餘地,德川家康從此再也沒有召見過他。光德認為即使在最高當權者德川家康面前,要他說出違背自己本心的話,還不如去死。毫不畏懼地直言自己的真實所見,這才是光德。自己才是刀劍鑒賞的絕對權威,這種驕傲哪怕是在最高當權者面前也絕不改變。
《本阿彌行狀記》在這段逸事後解釋道:不管是多麼魯鈍、不善諂媚的人,知道這是將軍的祕藏之寶,又是在御前群臣面前,大概沒有人會純真到會說出這刀是廢品之類的話。
由此可見,本阿彌家族最看重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誠實,對社會有時也要有近乎愚昧的剛直。比起待人接物的圓滑,他們更怕違背自己的本心。這一定是當時日本社會相當珍貴的心靈思想。
他們這麼早就擁有這種近代人的意識,我以為是由於這個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換而言之,正是由於在內心深處有可畏懼的神佛存在,才不須他人的外力規範,能夠自己約束自己。這個家族從第六代幕府將軍足利義教時,本阿彌清信在獄中皈依了日蓮宗的日親上人—因為不屈服於頭戴烤鍋的刑罰,被世人稱為戴鍋日親—改名本光以後,每代人都將頭髮剃光,並以光字命名,是非常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本阿彌家族和京都的本法寺的淵源極深,可稱外護法。此後家族中甚至有人出家皈依佛門,可以說是以本法寺為精神支柱的體現。
光悅自從德川家康賜下鷹峰之地後,就在這片土地上修造了常照寺、妙秀寺、光悅寺、知足庵四座寺廟,每天醉心修行。由於敬畏神佛,即便不為世人所知,也絕不放任自己做出違背信仰的事。這便是本阿彌家族中剛直不阿的精神傳統。
《本阿彌行狀記》在談到光悅的信仰時這麼寫道:
家父光悅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尤信日蓮宗。
先前的光德同樣如此,光悅在這裡更被特別強調「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可見已與日蓮精神結合成為一體了。
光甫在談起自己家族時說:
「本阿彌家族沒有一個具大智慧的人,至今卻仍然得到神佛庇佑,那是由於先祖的品德。因為畏懼天命、相信善惡報應,才不做違反人道的事,更不會擅行惡事。
「尤其在刀劍鑒定方面,因為是家族的頭等大事,必須眼光銳利,心無旁騖者才行。心有陰霾之人是不可能準確鑒定的。這方面有很多例子,現茲舉以下若干事例……」
於是說出光德見德川家康之刀而不阿諛的故事。
換言之,必先有了「畏懼天命」之心,才會恐懼那凡人看不見的存在,才絕對不敢做出違背本心的行為,依從自己本來的意願生活下去。這種心境同樣體現在刀劍鑒賞的家業方面,所以本阿彌家族的眼光才會出乎想像的嚴格。人生信仰和職業倫理就這樣合為一體。我們由此可知,與近代基督新教嚴厲的倫理觀大致相同的意識,已經在這家族中形成。
說得更遠一點,前不久,我在讀菲利普‧梅森的《英國紳士》一書時,發現書中有關紳士的一些論述和《本阿彌行狀記》中的記載非常相似,心裡感到極其愉快。比如在論及名譽時,書中如此敘述:
名譽乃紳士不可或缺的,對威爾來說,名譽不僅是世人對自己的評價,同樣意味著自尊心—從而亦指高潔、圓滿和自足;並且應予輕視金錢。這應是本質的。(略)威爾一文不名,但他確信無形的人格比金錢更重要。這裡說的名譽,即自尊心,也就是無形的人格。如果這段話就這麼換成《本阿彌行狀記》中的人物也絕不奇怪。不,如果在那個時代也有這種語言的話,他們一定也會那樣說的。
由此,我對現代日本商人在海外被認為「滿口都是關於金錢的話題,凡事只知用金錢去衡量」的評語感到十分悲哀。對一個紳士而言,在社交場合絕對應該迴避金錢這個話題,如果在一個崇尚藝術的國度,當人談論起繪畫的美學問題時,卻插言高談此畫的拍賣價格,豈不是太煞風景了嗎?
日本人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以前,他們不願在人面前談論金錢,尊重高潔的行為,把名譽看得至高無上。論天下國家時,我認為日本人討厭那些滿腦子充滿利益算計的傢伙,更重視那些坦率的陳述己見,有頭腦、有見識的人。所以本阿彌家族的故事才會如此詳盡的流傳至今。我相信,日本值得誇耀於世的,並不是躋身經濟大國,也不是成為貿易輸出大國,而是人世間最重要的「無形的人格」。
我知道,現代也有不少人敬畏這種「眼睛看不見的存在」,不會做令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擁有自己價值準則的人。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只熱衷於交易、賺錢,對金額數字之外的事物不感興趣。如果日本人皆是後者,那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我以光悅和妙秀為例,強調日本也還有這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