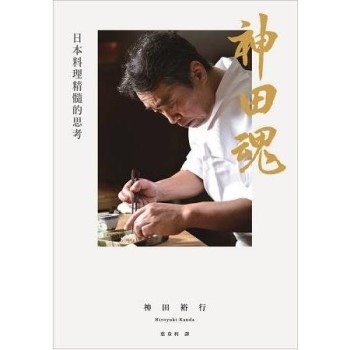日本料理,就像只在日本綻放的花朵。
就像只開在高山上的花,只棲息在清流裡的魚,要是少了日本的水、土壤、空氣就會枯萎、死去,或是將演化成另一種型態。在我心目中,日本料理就是這樣的存在。
年輕時,我曾在巴黎做日本料理。在外國做日本料理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有意義,我也希望能讓西方人了解到日本料理的美好,並且下定決心,將這件事當作我一生的職志。
這個想法在我回國後也持續不變,在我擔任了優秀前輩在海外的料理講習助理,以及在我以工作人員身分參與過巴黎飯店的日本料理祭之後,這份信念益發強烈。
然而,我又忍不住常反問自己。
「其實在外國,是做不出來所謂『真正的日本料理』的吧?」
我認為「日本料理」是由日本本地的食材和日本人的美感為骨架構成的,是一種由食材的新鮮度跟品質直接反映出菜色本質的料理。尋找優質的食材,趁其最為美味之際,以最少的工序將好滋味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料理。烹調的目的不在於將食材妝點得豔麗,而是細細研磨出食材本色,美麗呈現。
以技術和方法論構築出的法國料理,能夠跨海在全球遍地開花。在日本也有很多很棒的法國餐廳,將日本食材運用法國料理的技術和方法論精彩呈現。不過反觀日本料理,不知該說優點或缺點,總之相當倚賴日本本地的食材,而日本特有的食材流通速度才能維持的絕佳鮮度,更是左右成敗的關鍵,因此我認為要在國外做出真正的日本料理,非常困難。
日本是個四季分明的國家,挑選的食材自然也會隨著四季有所變化。
春天,是吃「芽」的季節,像是楤木芽、莢果蕨嫩芽、玉簪芽等。整個冬天在空中飄盪的虛弱太陽,一到春天恢復活力照射地面。土壤的溫度一升高,微生物蠢動,各式各樣的植物也隨之萌芽。無論是莢果蕨嫩芽還是蜂斗菜苗,蕨類、玉簪芽、土當歸、竹筍,所有嫩芽紛紛冒出頭。春天就是食用嫩芽的季節,也是在體內吸取生命力的季節。
夏天是吃瓜果的季節。小黃瓜、茄子、番茄、苦瓜,這些在太陽活力下結果纍纍的蔬果。從藤蔓結實的則有西瓜、瓠瓜、哈密瓜、南瓜之類。從「芽」到「果」,自古人們攝食蔬菜養分移轉的部位,就是這個道理。「葉」也是在夏天吃。在充分吸收陽光下,夏天也是葉片好吃的季節。
到了秋天,植物總算累積能量,為明年留下種子而結實。柿子、梨子等水果,還有銀杏、栗子……蘊含這些種子的果實中都儲存著養分。果實落地,回歸土壤,或是被其他動物吃掉,移動到陌生土地上等待下一個春天來臨。
到了冬天,地上的植物變成枯葉或種子落地,成了土壤中的養分,讓大地中貯藏養分的蔬菜變得更好吃。蘿蔔、蕪菁、紅蘿蔔,這些根莖類蔬菜,都是在寒冷季節於土壤中孕育生命。
日本人的飲食就是依照這個循環,這也是「吃當季時令」的概念。所謂的日本料理,正是品嚐這日本四季不同的時令。日本料理當然有獨特的技術、樣式,及哲學,但這些幾乎全都是為了突顯「時令」食材真正美味而誕生的。
美味的答案就在大自然之中。在不自然的食材裡,是尋不著美味的。
我所謂的「自然」,除了包括四季、天然之外,有時也指在調理科學上或自然法則的意義。
料理在鍋子裡或砧板上顯現的種種不可思議現象,多數以科學的角度來看都只是再自然不過。為什麼用不同形狀的鍋子燉煮,所需的時間也不同?為什麼只是讓鍋蓋開個縫隙,就能做出細緻滑嫩的茶碗蒸?為什麼用炭烤能夠做出散發美好焦香的燒烤料理?超過二十年,每天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廚房裡的我,見識到種種不可思議──但現在看來都是再自然不過的各種現象,我也想趁機在本書之中,一一介紹給大家。
我年輕時很喜歡夏卡爾(Marc Chagall)跟馬諦斯(Henri Matisse)的油畫,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到了法國。現在我喜歡日本畫,其中又以水墨畫這類簡單構圖最吸引我。我最喜歡的畫家是長澤蘆雪。長澤蘆雪是江戶時期中葉,也就是一七○○年代後期的畫家,特色是使用淡色及墨的畫風。日本畫通常以單一線條來描繪出輪廓,或是光以輪廓的曲線來呈現實體。無論臀部的豐滿或是臉頰的盈潤,都不會繁複細塗,而總是試圖用一條簡潔線條來表現。這樣的作業在塑造出空間的同時,也不容許修改。相對來說,西方繪畫則是不斷重複疊色,總之就是要盡量塗滿,總是給人畫面上沒有空白部分的印象。
油畫與水墨畫的差異,令我聯想到這恰巧就像是法國料理高湯「fond」與日本料理高湯「出汁」的不同。日式高湯幾乎都是水。雖然百分之九十九是水,其中卻有淡淡的柴魚鮮味及香氣,昆布的鮮味及香氣。再加入極少量的鹽、極少量的醬油。另一方面,小牛高湯雖然外觀是液狀,其實成分幾乎是膠質與蛋白質,我認為那並不是液體,而是呈現液狀的固體,小牛高湯放涼之後會像肉凍一樣凝固,就是最好的證明。牛骨先烤過,洋蔥先炒過,紅蘿蔔也要炒再放進去,加入香草,疊上一層又一層的鮮味,熬煮所有材料。
相對地,日式高湯是以水為根本,加入淡淡的鮮味與風味,點到為止。
在水墨畫之中,描繪的部分固然重要,而空白之處也不能有多餘的元素。所以我就想到,這套用在日本料理上也是相同的道理,尤其日式高湯更是類似在一張紙上,一邊思索留白的同時揮灑水墨畫筆。
留白之美。
我認為這才是日本人的美學。不加入必要以外的元素,不是去層層堆疊,甚至將所需的要素控制在最低程度。
我自己也一樣,在二、三十歲時,一心一意想做出前所未有的料理,認為非得打破既有觀念才行,否則就失去自我創作的意義。換句話說,我滿腦子在意的都是自我表現。可是,這種料理做得愈多,自己愈感到厭倦,因為有太多不必要的東西。雖然是自己做出來的,卻仍無法接受,因為自己也清楚得很,其中並不真實。不真實的創作,毫無意義。過了四十歲,我開始會這麼想。而這一轉念,才讓我看到了由日本這個國家豐饒自然產出的食材是多麼豐盛,是多麼難能可貴。
就像只開在高山上的花,只棲息在清流裡的魚,要是少了日本的水、土壤、空氣就會枯萎、死去,或是將演化成另一種型態。在我心目中,日本料理就是這樣的存在。
年輕時,我曾在巴黎做日本料理。在外國做日本料理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有意義,我也希望能讓西方人了解到日本料理的美好,並且下定決心,將這件事當作我一生的職志。
這個想法在我回國後也持續不變,在我擔任了優秀前輩在海外的料理講習助理,以及在我以工作人員身分參與過巴黎飯店的日本料理祭之後,這份信念益發強烈。
然而,我又忍不住常反問自己。
「其實在外國,是做不出來所謂『真正的日本料理』的吧?」
我認為「日本料理」是由日本本地的食材和日本人的美感為骨架構成的,是一種由食材的新鮮度跟品質直接反映出菜色本質的料理。尋找優質的食材,趁其最為美味之際,以最少的工序將好滋味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料理。烹調的目的不在於將食材妝點得豔麗,而是細細研磨出食材本色,美麗呈現。
以技術和方法論構築出的法國料理,能夠跨海在全球遍地開花。在日本也有很多很棒的法國餐廳,將日本食材運用法國料理的技術和方法論精彩呈現。不過反觀日本料理,不知該說優點或缺點,總之相當倚賴日本本地的食材,而日本特有的食材流通速度才能維持的絕佳鮮度,更是左右成敗的關鍵,因此我認為要在國外做出真正的日本料理,非常困難。
日本是個四季分明的國家,挑選的食材自然也會隨著四季有所變化。
春天,是吃「芽」的季節,像是楤木芽、莢果蕨嫩芽、玉簪芽等。整個冬天在空中飄盪的虛弱太陽,一到春天恢復活力照射地面。土壤的溫度一升高,微生物蠢動,各式各樣的植物也隨之萌芽。無論是莢果蕨嫩芽還是蜂斗菜苗,蕨類、玉簪芽、土當歸、竹筍,所有嫩芽紛紛冒出頭。春天就是食用嫩芽的季節,也是在體內吸取生命力的季節。
夏天是吃瓜果的季節。小黃瓜、茄子、番茄、苦瓜,這些在太陽活力下結果纍纍的蔬果。從藤蔓結實的則有西瓜、瓠瓜、哈密瓜、南瓜之類。從「芽」到「果」,自古人們攝食蔬菜養分移轉的部位,就是這個道理。「葉」也是在夏天吃。在充分吸收陽光下,夏天也是葉片好吃的季節。
到了秋天,植物總算累積能量,為明年留下種子而結實。柿子、梨子等水果,還有銀杏、栗子……蘊含這些種子的果實中都儲存著養分。果實落地,回歸土壤,或是被其他動物吃掉,移動到陌生土地上等待下一個春天來臨。
到了冬天,地上的植物變成枯葉或種子落地,成了土壤中的養分,讓大地中貯藏養分的蔬菜變得更好吃。蘿蔔、蕪菁、紅蘿蔔,這些根莖類蔬菜,都是在寒冷季節於土壤中孕育生命。
日本人的飲食就是依照這個循環,這也是「吃當季時令」的概念。所謂的日本料理,正是品嚐這日本四季不同的時令。日本料理當然有獨特的技術、樣式,及哲學,但這些幾乎全都是為了突顯「時令」食材真正美味而誕生的。
美味的答案就在大自然之中。在不自然的食材裡,是尋不著美味的。
我所謂的「自然」,除了包括四季、天然之外,有時也指在調理科學上或自然法則的意義。
料理在鍋子裡或砧板上顯現的種種不可思議現象,多數以科學的角度來看都只是再自然不過。為什麼用不同形狀的鍋子燉煮,所需的時間也不同?為什麼只是讓鍋蓋開個縫隙,就能做出細緻滑嫩的茶碗蒸?為什麼用炭烤能夠做出散發美好焦香的燒烤料理?超過二十年,每天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廚房裡的我,見識到種種不可思議──但現在看來都是再自然不過的各種現象,我也想趁機在本書之中,一一介紹給大家。
我年輕時很喜歡夏卡爾(Marc Chagall)跟馬諦斯(Henri Matisse)的油畫,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到了法國。現在我喜歡日本畫,其中又以水墨畫這類簡單構圖最吸引我。我最喜歡的畫家是長澤蘆雪。長澤蘆雪是江戶時期中葉,也就是一七○○年代後期的畫家,特色是使用淡色及墨的畫風。日本畫通常以單一線條來描繪出輪廓,或是光以輪廓的曲線來呈現實體。無論臀部的豐滿或是臉頰的盈潤,都不會繁複細塗,而總是試圖用一條簡潔線條來表現。這樣的作業在塑造出空間的同時,也不容許修改。相對來說,西方繪畫則是不斷重複疊色,總之就是要盡量塗滿,總是給人畫面上沒有空白部分的印象。
油畫與水墨畫的差異,令我聯想到這恰巧就像是法國料理高湯「fond」與日本料理高湯「出汁」的不同。日式高湯幾乎都是水。雖然百分之九十九是水,其中卻有淡淡的柴魚鮮味及香氣,昆布的鮮味及香氣。再加入極少量的鹽、極少量的醬油。另一方面,小牛高湯雖然外觀是液狀,其實成分幾乎是膠質與蛋白質,我認為那並不是液體,而是呈現液狀的固體,小牛高湯放涼之後會像肉凍一樣凝固,就是最好的證明。牛骨先烤過,洋蔥先炒過,紅蘿蔔也要炒再放進去,加入香草,疊上一層又一層的鮮味,熬煮所有材料。
相對地,日式高湯是以水為根本,加入淡淡的鮮味與風味,點到為止。
在水墨畫之中,描繪的部分固然重要,而空白之處也不能有多餘的元素。所以我就想到,這套用在日本料理上也是相同的道理,尤其日式高湯更是類似在一張紙上,一邊思索留白的同時揮灑水墨畫筆。
留白之美。
我認為這才是日本人的美學。不加入必要以外的元素,不是去層層堆疊,甚至將所需的要素控制在最低程度。
我自己也一樣,在二、三十歲時,一心一意想做出前所未有的料理,認為非得打破既有觀念才行,否則就失去自我創作的意義。換句話說,我滿腦子在意的都是自我表現。可是,這種料理做得愈多,自己愈感到厭倦,因為有太多不必要的東西。雖然是自己做出來的,卻仍無法接受,因為自己也清楚得很,其中並不真實。不真實的創作,毫無意義。過了四十歲,我開始會這麼想。而這一轉念,才讓我看到了由日本這個國家豐饒自然產出的食材是多麼豐盛,是多麼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