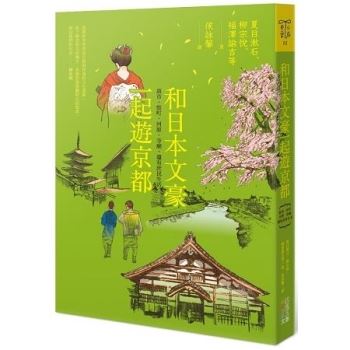◎京都晨市/柳宗悅
我從大正末年至昭和八年(注1:一九三三年),算起來在京都住了近九年的時間。如今回想起來,我應該多看看這古都與周邊的文化遺跡。除了歷史悠久的廟宇,我應該要接觸附近的聚落,親近他們的生活。我還錯過在這古都裡,如今仍然傳承的各種手工藝工房。我應該到處走訪,見識這些技術的工程、完成的作品。工藝品的類別肯定比我見識過的還多吧。關於這一點,再也沒有比京都更強的地方了。 今日依然維持遠古的傳統。我只見識過一小部分,應該充分增廣自己的見聞才是。現在想起來,只覺十分可惜。
不過我可沒有虛度光陰。住在京都的期間,我對晨市產生極大的興趣,學了不少知識。關於這一點,河井寬次郎(注2:一八九○~一九六六,陶藝家)可說是我的前輩。
晨市會在當月的特定日期與地點舉辦,最晚在早上六時許開始的市集。上至二手衣,下至缺角的木梳,什麼都賣的市集。而且晨市不只在一處。諸如弘法晨市、天神晨市、壇王晨市、淡島晨市、北濱晨市(注3:以上皆為京都的地名),會在不同的日子與地點舉辦。要把這些市集全都逛一遍,大大小小加起來,聽了可別驚訝,一個月竟要二十餘日才逛得完。其中最大的是每月為期二十一日的弘法晨市,也就是在東寺的市集,在寬廣的寺內,擺著滿滿的商品。與每月二十五天的天神晨市號稱雙璧,這是在北野天神(注4:北野天滿宮)寺內寺外,擺到無一空處的大型市集。
這些什麼都賣的晨市非常吸引我。直到大正的尾聲,我才聽說晨市的事,最好的時期已經過去了。若是大正初期,甚至是更早的明治時代,賣的商品不知該有多好。隨著時代發展,商品的品質下滑,我們經常聽商人說:「這陣子完全沒好貨。」他們說得肯定沒錯。
不過,既然出了門,還是會買點東西。商人會在五點至六點之間,以手推車將商品送到晨市,雜貨店那幫人早就在那裡等車子,好貨先被他們挑走了。六點出門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最早也是七、八點才能抵達。來逛晨市的都民絕非少數,天氣好的時候,經常都是人潮多到動彈不得的盛況。因此,我們永遠都是排名第二、第三的買家。幸好雜貨店的眼光跟我們相距甚遠。後來到訪的我們,還是可以撿到許多不錯的好貨。那些沒人注意,比市價還低的商品中,經常出現各種好貨。雖然比不上從前的晨市,仍然是錯過可惜的獵場。只要沒下雨,我還是經常光顧大型市集。
大部分的賣家都是老婆婆。這肯定是份不錯的兼差。市集通常在中午結束。買家也早早來報到。我們經常造訪,後來跟老婆婆混熟了,她們還會幫我們留貨。
稍微聊一下,其實我也是聽老婆婆們說,我才知道還有「下手(注5:便宜粗俗)」與「下手物(注6:便宜又粗俗的工藝品)」這類的俗語。也就是說,我們購買的商品,都是老婆婆們口中的「下手物」。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時,我們覺得很有趣,而且還有相對的「上手物(注7:精緻、高級的工藝品)」,可以明確區分品質,也許是特別投緣,我們也覺得這些名詞用起來很方便。「下手」表示普遍又低廉的品質,民器(注8:民生器具)與雜器(注9:雜用器具)都屬於此類。我們可能是第一個用文字記錄這些俗語,描述其性質的人吧。我在大正十五年(注10:一九二六年)九月發行的《越後時代》(越後タイムス)首度以「下手物之美」為題撰稿。
也許是這些俗語的語氣比較強烈,大家覺得新奇,很快就流傳開來,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詞,現在甚至每個人都在使用,字典只好收錄這個名詞。最早把它編進字典的,大概是新村出(注11:一八七六~一九六七,日本語言學家)博士編纂的《辭苑》吧。
隨著這個名詞的普及,它也沒有倖免,被人們誤用,或是故意給它不同的意義,也有人出於興趣,把這個俗語轉用到各種情況,已經偏離我們本來給它的意義了。因此,我們遭到各種誤會與曲解,甚至飽受困擾。於是我們反過來覺得應該避免使用這個俗語,創造另一個取代它的新名詞,最後選定「民藝」(注12:日常使用的工藝品)二字。不過「下手」一詞非常有趣,也有自由、樸實之處,若能正當使用,也是一個不錯的俗語。好像有點離題了,我們在晨市找到最驚豔的商品,就是俗稱的「丹波布」,老婆婆她們都簡稱「丹波」。我們後來才知道這是丹波國佐治地方(注13:今兵庫縣冰上郡)生產的木棉布,當地人稱為「縞貫」,特色是在緯系隨處織入未經染色的玉線(注:用一繭雙蛹的玉繭製成的線)。成色沉穩,織法溫潤,條紋美麗,使我們大感驚奇,這布用的是手紡線,色彩則是草木染。有一段時期,人們只生產這種布。因為它豐富的變化,簡直像茶客特別訂製的產品。第一次見到這布的時候,我就深受吸引,每回見了總是大肆收購。丹波布之所以落入京都的晨市,乃是由於京阪地區的人喜歡用它來製作棉被套。有時會裁製丹前(注14:舖棉的防寒外套),不過還是棉被和墊被居多。現在已經過時了,成了老舊的二手衣,才被丟進市集。據說此布盛產於幕末至明治初期。絲線與染法都是無可比擬,如果能早點認識這布料,也許可以製作茶客們喜歡的提袋或茶袋吧。特別是蚊帳,乃是用剩下的線頭織成的,條紋的色澤極美。我曾經用它裱褙過幾幅大津繪(注15:江戶初期滋賀縣大津市流行的民俗畫)。簡直是天作之合。這布料立刻成了我們這群人的寵兒,販賣的老婆婆們還特地為我們找來許多貨。現在民藏館收藏的,長期陳列的,都是那陣子在晨市找來的寶物。將來若有人編纂日本的棉布史,千萬不可忘記這布料的存在與價值。也許有一天,它會成為人們口中讚不絕口的新名物裂(注16:名物裂為鎌倉時期到江戶初期,由中國傳來的高級絲織品)。
關於它的起源。這布料曾一度停產超過半個世紀,近來以丹波國冰上郡佐治附近的大燈寺為中心,為求復興,再度召集紡線者、染色者、織布者,尋求他們的協助。
我在晨市捕獲的可不只有丹波布。我還買到不少品質精良的和服。有幾件和服甚至比新品更耐穿,作工非常好。有幾件甚至放了三十幾個年頭,直到今日,我還能穿。全都是拜高品質之賜。說是織布者的用心,也許更妥當吧。然而,我購買的不只是這種和服。我收購許多名為裂織(注17:將老舊布料剪成碎塊,以麻線織成的再生布料,又名「舊布織」)或屑絲織(注18:用零碎的絲線紡成的布料,又名「矢鱈縞」)賣的時候都沒有清洗,帶回家後,內人非常嫌棄,直說好髒。還說也不曉得是不是什麼病人穿過的。她說得也有道理,有些衣服的味道特別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吉田璋也(注19: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民藝運動家)醫生很擔心,整批拿去消毒,於是這場家庭糾紛就此落幕。如今,這些布製品全都存放於民藝館。
晨市無所不賣,除了布製品,也有陶瓷器、漆器、金屬製品,還有木材或竹製工藝品,經常遇到吸引我的物品。不消我多說,全都很便宜。拜這些晨市之賜,我更加了解丹波的陶瓷器。不曉得誰說過,和以前相比,這陣子的好貨少多了,不過,我們仍然期待晨市的行程。說不定有預料之外的寶貝,靜待我們光臨。
一般來說,在晨市買不到什麼來頭不少的東西。所以買東西不需要靠名氣。在這樣的地方,人們才能隨心所欲地挑選。這也是晨市的迷人之處。在這種地方,知識完全派不上用場。反而要靠直覺。當你發揮敏銳的直覺時,好貨也會高興地湊過來。(待續)
我從大正末年至昭和八年(注1:一九三三年),算起來在京都住了近九年的時間。如今回想起來,我應該多看看這古都與周邊的文化遺跡。除了歷史悠久的廟宇,我應該要接觸附近的聚落,親近他們的生活。我還錯過在這古都裡,如今仍然傳承的各種手工藝工房。我應該到處走訪,見識這些技術的工程、完成的作品。工藝品的類別肯定比我見識過的還多吧。關於這一點,再也沒有比京都更強的地方了。 今日依然維持遠古的傳統。我只見識過一小部分,應該充分增廣自己的見聞才是。現在想起來,只覺十分可惜。
不過我可沒有虛度光陰。住在京都的期間,我對晨市產生極大的興趣,學了不少知識。關於這一點,河井寬次郎(注2:一八九○~一九六六,陶藝家)可說是我的前輩。
晨市會在當月的特定日期與地點舉辦,最晚在早上六時許開始的市集。上至二手衣,下至缺角的木梳,什麼都賣的市集。而且晨市不只在一處。諸如弘法晨市、天神晨市、壇王晨市、淡島晨市、北濱晨市(注3:以上皆為京都的地名),會在不同的日子與地點舉辦。要把這些市集全都逛一遍,大大小小加起來,聽了可別驚訝,一個月竟要二十餘日才逛得完。其中最大的是每月為期二十一日的弘法晨市,也就是在東寺的市集,在寬廣的寺內,擺著滿滿的商品。與每月二十五天的天神晨市號稱雙璧,這是在北野天神(注4:北野天滿宮)寺內寺外,擺到無一空處的大型市集。
這些什麼都賣的晨市非常吸引我。直到大正的尾聲,我才聽說晨市的事,最好的時期已經過去了。若是大正初期,甚至是更早的明治時代,賣的商品不知該有多好。隨著時代發展,商品的品質下滑,我們經常聽商人說:「這陣子完全沒好貨。」他們說得肯定沒錯。
不過,既然出了門,還是會買點東西。商人會在五點至六點之間,以手推車將商品送到晨市,雜貨店那幫人早就在那裡等車子,好貨先被他們挑走了。六點出門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最早也是七、八點才能抵達。來逛晨市的都民絕非少數,天氣好的時候,經常都是人潮多到動彈不得的盛況。因此,我們永遠都是排名第二、第三的買家。幸好雜貨店的眼光跟我們相距甚遠。後來到訪的我們,還是可以撿到許多不錯的好貨。那些沒人注意,比市價還低的商品中,經常出現各種好貨。雖然比不上從前的晨市,仍然是錯過可惜的獵場。只要沒下雨,我還是經常光顧大型市集。
大部分的賣家都是老婆婆。這肯定是份不錯的兼差。市集通常在中午結束。買家也早早來報到。我們經常造訪,後來跟老婆婆混熟了,她們還會幫我們留貨。
稍微聊一下,其實我也是聽老婆婆們說,我才知道還有「下手(注5:便宜粗俗)」與「下手物(注6:便宜又粗俗的工藝品)」這類的俗語。也就是說,我們購買的商品,都是老婆婆們口中的「下手物」。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時,我們覺得很有趣,而且還有相對的「上手物(注7:精緻、高級的工藝品)」,可以明確區分品質,也許是特別投緣,我們也覺得這些名詞用起來很方便。「下手」表示普遍又低廉的品質,民器(注8:民生器具)與雜器(注9:雜用器具)都屬於此類。我們可能是第一個用文字記錄這些俗語,描述其性質的人吧。我在大正十五年(注10:一九二六年)九月發行的《越後時代》(越後タイムス)首度以「下手物之美」為題撰稿。
也許是這些俗語的語氣比較強烈,大家覺得新奇,很快就流傳開來,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詞,現在甚至每個人都在使用,字典只好收錄這個名詞。最早把它編進字典的,大概是新村出(注11:一八七六~一九六七,日本語言學家)博士編纂的《辭苑》吧。
隨著這個名詞的普及,它也沒有倖免,被人們誤用,或是故意給它不同的意義,也有人出於興趣,把這個俗語轉用到各種情況,已經偏離我們本來給它的意義了。因此,我們遭到各種誤會與曲解,甚至飽受困擾。於是我們反過來覺得應該避免使用這個俗語,創造另一個取代它的新名詞,最後選定「民藝」(注12:日常使用的工藝品)二字。不過「下手」一詞非常有趣,也有自由、樸實之處,若能正當使用,也是一個不錯的俗語。好像有點離題了,我們在晨市找到最驚豔的商品,就是俗稱的「丹波布」,老婆婆她們都簡稱「丹波」。我們後來才知道這是丹波國佐治地方(注13:今兵庫縣冰上郡)生產的木棉布,當地人稱為「縞貫」,特色是在緯系隨處織入未經染色的玉線(注:用一繭雙蛹的玉繭製成的線)。成色沉穩,織法溫潤,條紋美麗,使我們大感驚奇,這布用的是手紡線,色彩則是草木染。有一段時期,人們只生產這種布。因為它豐富的變化,簡直像茶客特別訂製的產品。第一次見到這布的時候,我就深受吸引,每回見了總是大肆收購。丹波布之所以落入京都的晨市,乃是由於京阪地區的人喜歡用它來製作棉被套。有時會裁製丹前(注14:舖棉的防寒外套),不過還是棉被和墊被居多。現在已經過時了,成了老舊的二手衣,才被丟進市集。據說此布盛產於幕末至明治初期。絲線與染法都是無可比擬,如果能早點認識這布料,也許可以製作茶客們喜歡的提袋或茶袋吧。特別是蚊帳,乃是用剩下的線頭織成的,條紋的色澤極美。我曾經用它裱褙過幾幅大津繪(注15:江戶初期滋賀縣大津市流行的民俗畫)。簡直是天作之合。這布料立刻成了我們這群人的寵兒,販賣的老婆婆們還特地為我們找來許多貨。現在民藏館收藏的,長期陳列的,都是那陣子在晨市找來的寶物。將來若有人編纂日本的棉布史,千萬不可忘記這布料的存在與價值。也許有一天,它會成為人們口中讚不絕口的新名物裂(注16:名物裂為鎌倉時期到江戶初期,由中國傳來的高級絲織品)。
關於它的起源。這布料曾一度停產超過半個世紀,近來以丹波國冰上郡佐治附近的大燈寺為中心,為求復興,再度召集紡線者、染色者、織布者,尋求他們的協助。
我在晨市捕獲的可不只有丹波布。我還買到不少品質精良的和服。有幾件和服甚至比新品更耐穿,作工非常好。有幾件甚至放了三十幾個年頭,直到今日,我還能穿。全都是拜高品質之賜。說是織布者的用心,也許更妥當吧。然而,我購買的不只是這種和服。我收購許多名為裂織(注17:將老舊布料剪成碎塊,以麻線織成的再生布料,又名「舊布織」)或屑絲織(注18:用零碎的絲線紡成的布料,又名「矢鱈縞」)賣的時候都沒有清洗,帶回家後,內人非常嫌棄,直說好髒。還說也不曉得是不是什麼病人穿過的。她說得也有道理,有些衣服的味道特別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吉田璋也(注19: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民藝運動家)醫生很擔心,整批拿去消毒,於是這場家庭糾紛就此落幕。如今,這些布製品全都存放於民藝館。
晨市無所不賣,除了布製品,也有陶瓷器、漆器、金屬製品,還有木材或竹製工藝品,經常遇到吸引我的物品。不消我多說,全都很便宜。拜這些晨市之賜,我更加了解丹波的陶瓷器。不曉得誰說過,和以前相比,這陣子的好貨少多了,不過,我們仍然期待晨市的行程。說不定有預料之外的寶貝,靜待我們光臨。
一般來說,在晨市買不到什麼來頭不少的東西。所以買東西不需要靠名氣。在這樣的地方,人們才能隨心所欲地挑選。這也是晨市的迷人之處。在這種地方,知識完全派不上用場。反而要靠直覺。當你發揮敏銳的直覺時,好貨也會高興地湊過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