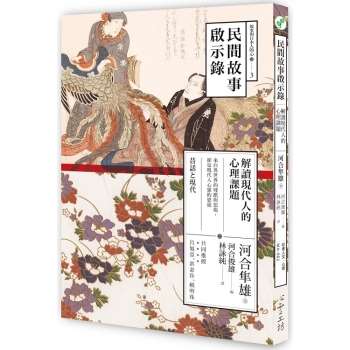第一章、格林童話中的殺害
民間故事中的「殺害」
「殺害」是民間故事中常見的主題,民間故事中經常出現試圖殺人,或是真的殺了人的故事。譬如日本人也很熟悉的格林童話「小紅帽」、「白雪公主」、「糖果屋」、「大野狼與七隻小羊」等,也都是把「殺害」當成重要主題的故事。
有些人秉持「教育者」的想法,認為民間故事中的殺害會讓人感到「殘忍」,並認定不該把這樣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也有人主張應該把故事改編。這樣的意見實在十分荒謬,如果把格林童話中含有「殺害」主題的故事都拿掉,那格林童話就不再是格林童話了吧?格林童話中,光是描述實際「殺害」行為的故事(不是只有殺害的意圖),隨便一數,就多達約四分之一,占了相當多的數量。為什麼民間故事中會提到這麼多的「殺害」呢?而格林童話中的「殺害」,又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呢?本書接下來,就要概括地來看這些問題。
格林童話與日本民間故事
老實說,我之所以會開始探討民間故事中的殺害,是源自於我對日本民間故事的考察。
長久以來,我試著透過日本民間故事,探索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並將結果大致整理成冊發表出來,而在發表之後,我仍持續思考這當中還有什麼未竟的問題,於是「殺害」這個重要的主題,就浮現在腦海中。
比較日本的民間故事與世界各國的民間故事時,可以將「異類婚姻」視為重要的關鍵特徵。民俗文學學者小澤俊夫已經將這個觀點發表在其劃時代的研究當中,而我也順著他的脈絡思考。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猴女婿」(《日本民間故事大成》)等異類女婿的故事中,異類女婿經常遭到殺害。而且這些動物女婿並沒有為非作歹,單單只是因為身為動物,就被人類殺死,而有時殺害的方法,還可說是極為陰險歹毒。然而若對照異類妻子,譬如「鶴娘子」(《大成》),這些妻子就沒有被殺,只是當場離去。因此,殺害異類女婿,可謂日本民間故事極為顯著的特徵。若比較「猴女婿」與格林童話中的「青蛙王子」(《全譯 格林童話集》一),就能發現彼此之間的顯著差異。「青蛙王子」雖然也屬於一種異類婚姻,但是當公主將討厭的青蛙丟向牆壁時(這裡也能看到「殺害」的主題),青蛙變身為王子並與公主結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這個故事,與利用計謀殺死猴女婿的日本民間故事,呈現出鮮明的對比。
關於「殺害」這點,日本還有一則值得注意的民間故事。我想,廣義地解釋「殺害」的話,「自殺」應該也包括在內,而日本民間故事中,就有以下這則令人震驚的故事。這則故事屬於「鬼子小綱」(《大成》二四七A)分類中的某個版本,有些也以「片子」為題。故事是這樣的:鬼把人類的妻子擄走,讓她成為自己的妻子。於是丈夫出發尋找妻子的下落,終於在第十年來到鬼島,他在那裡遇見了鬼與人類妻子生下的孩子,這個孩子自稱為「片子」。後來人類夫妻重逢,並在片子的幫助下回到人界,但所有人都不接納半鬼半人的片子,無處容身的他,最後從大樹上跳下來自殺。這是一則非常令人震驚的故事。為了母親的幸福而拚命奉獻的孩子,卻因為自己身為「半人半鬼」而自責,最後甚至結束自己的性命(關於這點,下一章會再討論)。
我讀到這篇故事時,覺得這篇故事很有日本特色,並與前面提到的異類女婿問題一併做了許多思考。不過,如果將日本民間故事與格林童話進行比較,真的可以斷定格林童話中就「絕對」沒有這樣的情節嗎?當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後,逐漸有些不安。因為我雖然仔細讀過格林童話,卻不是記得那麼清楚,而且故事情節出人意表,可以說是民間故事的特徵。於是我把焦點擺在「殺害」,將格林童話重新讀過一遍,並把所有故事中關於「殺害」(包含自殺)的情節製作成表格。
我最原始的動機,是探討日本民間故事,但我看著自己製作的一覽表時,腦中也浮現了一些頗為有趣的想法。接下來就以格林童話中的「殺害」為主題,敘述我腦中浮現的想法,穿插與日本的民間故事的比較。「殺害」的意義
我有一位個案因為夢見殺人而覺得非常驚恐。或許因為他不知道從哪裡聽來「夢境滿足了願望」之類的說法,才會那麼驚恐吧?我問他:「你是不是為了建立現在的生活方式,而在過去扼殺了某些事物?」他聽到這個問題就心裡有數了,於是我就從這個切入點去分析他的夢境。換句話說,「殺」這個字象徵的意義非常廣泛,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使用「扼殺氣息」或「扼殺味道」來形容「屏息」或「破壞味道」,而運動中也有「殺球」這樣的技巧。
翻開辭典《廣辭苑》,「殺」除了「①結束生命」的意思之外,還有「②壓制,使之氣勢減弱;壓制,使之無法活動。③在競爭中,削弱對手的攻擊力。④在棒球中,使對手出局。⑤(俗語)抵押。⑥將對方迷得神魂顛倒」等意思。即使查的是英文字典,也能從英文的「kill」查到幾乎相同的意思。因此從語言的象徵角度來看,夢境或民間故事中的「殺」,不一定是字面上的「結束生命」,必須像字典一樣,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解讀。換句話說,民間故事中的「殺」,不是字面上的「殺人」。孩子們在心底深處感受到這點,所以即使聽了民間故事,也不會那麼驚訝或害怕。
在思考殺害的象徵性時,也可以完全反過來思考。也就是說,有些人以為他對某件事物所做的,只是單純的壓抑、削弱其氣勢,但其實他的行為已經算是某種「殺害」了。舉例來說,假設有個國中生告訴父親自己想要加入棒球隊,但是父親卻對他說:「你可以打棒球,但是不能加入棒球隊,因為練習的時間太長了,會影響功課。」父親這麼說的時候,往往以為自己只是壓抑了孩子強烈的渴望,但有時候卻是扼殺了孩子的靈魂。這麼一想,我甚至覺得很多父母不僅殺害自己的孩子,還把孩子當成「食物」了,不是嗎?
那些以「甜言蜜語」迷惑孩子,將孩子當成「自己的所有物」或「食物」的父母,或許就和「糖果屋」裡用糖果餅乾做的房子引誘孩子們,最後把孩子們吃掉的巫婆沒什麼兩樣。如果注意到人類現實社會中的各種「殘忍」,尤其是大人對孩子所做的殘忍行為,就會發現沒有必要只把民間故事中的殘忍挑出來說三道四。即使只是處於空想的階段,還不到「想要殺掉那個人」的程度,也應該很少有人能夠拍胸脯自己從未設想過「如果那個人不在的話」或者「要是那個人死掉的話」之類的情形。而且想像的階段愈深入,「殺害」的意思也會愈加深。無論親子關係再怎麼親密,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對父母懷著強烈的抗拒。而且,這樣的情緒甚至可能強烈到不僅止於抗拒或反抗,或許還會在某段時間全面否定父母。如果沒有經歷過這種強烈的否定,孩子就難以成長為能與父母保持適當距離的獨立大人。這樣的過程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孩子必須經歷象徵層次上的「殺父弒母」。
思考民間故事的意義時,隨著孩子成長所帶來的弒親問題是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已經在其他著作中討論過這點。但由於這點在本書中也相當重要,所以在此很簡單地介紹一下。奧地利精神分析學者佛洛伊德注意到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內心糾葛,他認為所有的男性在兒時都有殺死父親,與母親結婚的欲望,但這樣的欲望遭到壓抑,以伊底帕斯情結的狀態留在無意識當中。而瑞士分析心理學者榮格則認為,與其將神話或民間故事中常見的弒親主題視為實際的親子關係,倒不如將其視為個人與存在於個人普遍無意識中的原型──「父親形象」與「母親形象」之間的關係。
榮格的學生艾瑞旭.紐曼(Erich Neumann),更進一步探討西方近代的自我確立過程與弒親的象徵性之間的關聯。紐曼提到,近代西方所確立的自我,屬於世界上的特例,而典型的英雄故事,象徵的就是自我確立的過程。英雄故事可分成英雄的誕生、英雄打敗怪物(龍)、英雄與被怪物抓走的少女結婚等三個階段。他認為英雄的誕生,象徵自我的誕生;打敗怪物則代表自我脫離母親形象與父親形象的束縛,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而後與少女結婚,則象徵獨立的自我再度與世界締結新的關係。
這是極具說服力的想法「之一」,卻不是唯一的正確答案。而且這樣的想法,雖然能夠用來解釋西方故事,對於日本的故事卻不一定適用。不過接下來在探討格林童話時,我覺得應該把這樣的概念放在腦海裡,但並非將紐曼的想法套用到所有的殺害故事中。接下來,希望大家把前面提到的所有關於殺害的內容記在腦中,來進行對格林童話的探討。第八章、民間故事的殘忍性
殘忍之處在哪裡?
不論是東方或是西方的民間故事,都描述了許多「殘忍的情節」。只要稍微翻閱一下格林童話,就能立刻找出殘忍的場景。譬如在「小紅帽」中,小紅帽被大野狼吞下肚;在「沒有手的女孩」中,父親砍下親生女兒的雙手;在「糖果屋」中,父母為了解決飢餓的問題而拋棄孩子。格林兄弟雖然將「糖果屋」的母親改寫成繼母,但在原版的故事裡卻是親生母親。
東方的故事也充滿了殘忍的情節,與西方故事相比,不遑多讓。「喀擦喀擦山」中的狸貓,不僅把老奶奶殺死,還煮成老奶奶湯給老爺爺吃。這段情節過於殘忍,所以很多「喀擦喀擦山」的童書繪本都將這個部分刪去。但有些原始版本的「喀擦喀擦山」在老爺爺喝下老奶奶湯之後就結束了,沒有提到後來兔子幫忙報仇的部分。換句話說,老奶奶湯是這個故事的著眼點,如果把老奶奶湯刪去,故事就無法成立。在「螃蟹與猴子」的故事中,雙方也發生了極為殘忍的交戰,螃蟹被猴子殺掉,小螃蟹為了報仇而把猴子的頭剪下來等等。
類似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但有些人質疑民間故事中的殘忍性,因此在說給孩子聽的時候,擅自將故事改編。話說回來,格林兄弟確實也將「糖果屋」與「白雪公主」中的親生母親改寫為繼母,只不過日本市面上的童書繪本,把內容改編得太過輕描淡寫,不禁令人訝異。譬如原本應該被剪下腦袋的猴子,在改編的故事中卻變成哭著道歉就得到原諒。市面上的繪本很多都以這樣的「和平共處」收尾。關於「改編」的問題我想留待之後討論,在這裡先探討所謂的「殘忍」到底是什麼。那些基於淺薄的「和平」理念而製作出粗糙童書繪本的人,知道孩子的靈魂在讀了、聽了這些淡化處理的故事後,無聊到幾乎要窒息嗎?有些母親「為了孩子好」,而把一些無趣的故事讀給他們聽,這些母親的行為不是與騙老爺爺喝下老奶奶湯的狸貓沒兩樣嗎?大人必須察覺到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對孩子做出了多麼殘忍的事情。如果把民間故事解釋成發生在內心深層之處的真實故事,就會發現民間故事中描述的「殘忍」,就如同家常便飯般發生。嚴格禁止女兒與他人來往的父親,這不是就和「砍下女兒的雙手」一樣嗎?把孩子當成「食物」的父母很多、被封在「水晶棺材」裡的女孩也確實存在。而且孩子為了成長,甚至需要在內在完成「殺父弒母」的儀式。這麼一想就會發現,大人一邊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殘忍」的事情,卻又一邊禁止殘忍的故事,或是將其改寫,這樣的行為就像日本在戰爭時對創作內容進行的審查一樣。無論審查多麼嚴格,最後還是會以更愚蠢的形式露出馬腳。
孩子都知道
前面提到的這些事情,孩子其實都知道得很清楚。但關於這裡的「知道」,必須稍微下點註解。大人一般所謂的「知道」,難免都會過度連結到智能的運作。大人會將新事物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與自己的知識體系相互對照,由此產生「知道」的感受。譬如提到狸貓的時候,大人會對照自己的知識,判斷狸貓是一種動物、與貓差不多大、住在山裡面等等,然後才會說自己「知道」狸貓是什麼。但孩子不一樣,他們對狸貓的反應是全人的,他們知道狸貓單純只是動物不是妖怪,但同時也知道狸貓是狡猾、會騙人的傢伙,而且狸貓不只住在山村,也住在都會,甚至住在自己的心裡。孩子的「知」,靠的不是頭腦,而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受,而且是全人的、有生命的。
當孩子聽到大野狼在可愛的小紅帽面前露出真面目,將她整個吞下肚時,能夠對照自己的經驗,把這件事當成「常有的事情」來體驗。他們也確實能夠透過深入的智慧,看穿很多家庭都經常在晚餐端出「老奶奶湯」。更了不起的是,他們清楚知道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於外在的現實當中。大家應該不曾聽說過有哪個孩子在聽了「喀擦喀擦山」的故事後,想要把老奶奶煮成味噌湯吧?也不曾聽說過有哪個孩子在聽了螃蟹與猴子的故事後,試圖拿剪刀把同學的頭剪下來吧?由此可知,大人可以更放心地信賴孩子的智慧。愈是不安的大人,愈無法信賴孩子。很多「為了孩子好」而把殘忍故事改寫成溫和形式的大人,都沒有發現他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是為了減輕自己在面對內在真實時所產生的不安。無論再怎麼試圖矇混,都無法騙過孩子。前面已經說過,孩子就算聽了殘忍的故事,也不會變得殘忍。那麼完全沒有聽過殘忍故事的孩子,又會變得如何呢?首先可以想到的反應,是孩子自己編造出殘忍的故事。這其實是非常健康的反應,或許也有大人記得自己曾有過這樣的經驗。當父母給的故事全都過於「安全無害」時,孩子就會自己幻想出殘忍的故事,或是從他人之處尋求這樣的殘忍故事。畢竟孩子的靈魂渴求無限的自由。
如果父母給的故事全都過於「安全無害」,而孩子也不具備反彈的能力,並因此被塑造成人為的「好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時候,就會急遽發生反轉現象,對父母施加「殘忍」的暴力。我想各位可以透過最近日本急速增加的家庭暴力事件充分了解到這件事情。
孩子聽到「殘忍」的故事時,可以知道這是發生在內心世界的事情,並且將其意義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就不再需要做出殘忍的舉動。但是對於殘忍沒有任何免疫力的孩子,最後將成為殘忍的犧牲品。
說故事的意義
肯定民間故事中的殘忍,不代表肯定「殘忍」本身。但民間故事中的殘忍,真的如同前面所說的,完全不會刺激孩子的殘忍性嗎?關於這點,我還是必須指出「說故事的方法」,以及「說故事者」的重要性。外在的真實即使是透過書本也能清楚傳達,但是想要清楚傳達內在的真實,只能透過人與人,或是人的靈魂與靈魂的直接對話。所以民間故事只有透過「口耳相傳」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如果說故事的人已經如同前述一般,明確知道殘忍性的意義,那麼不管他說的故事有多麼殘忍,都不會發生問題。這裡的「知道」,指的也是全人意義上的「知」。民間故事只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口耳相傳,才能傳達內在的真實。因為孩子即使被故事中的殘忍與可怕嚇得尖叫,也能以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為基礎,消化聽故事時的恐怖體驗,將其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那麼如果把民間故事寫成書,又會如何呢?民間故事原本應該是口耳相傳的內容,不是閱讀的內容。但如果孩子能夠在閱讀之前獲得支持自己存在的良好人際關係,我想他們即使自己閱讀故事,也彷彿能夠聽見「說故事的聲音」。正因為民間故事是經過漫長歲月形成的內容,所以才具有極高的普遍性,具備某種能在心底深處產生共鳴的性質。
但如果孩子在人際關係上沒有前述穩定的根基,就可能在閱讀民間故事的時候,被強烈的不安襲擊,繼而受到不良的影響。將民間故事寫成書,已經有點困難了,畫成繪本或是做成電視節目,更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因為繪本或電視節目在孩子聽到故事、建立自己內在現實的印象之前,就已經給了他們來自外部的影像,而這些影像將成為一種外在現實。因此製作民間故事的繪本,需要仔細的考量與相當程度的技術。理想的繪本不能灌輸孩子既定的印象,而是要幫助孩子將他們的印象擴充得更加豐富。但到底有多少製作民間故事繪本的人,擁有這樣的自覺呢?
民間故事中的「殺害」
「殺害」是民間故事中常見的主題,民間故事中經常出現試圖殺人,或是真的殺了人的故事。譬如日本人也很熟悉的格林童話「小紅帽」、「白雪公主」、「糖果屋」、「大野狼與七隻小羊」等,也都是把「殺害」當成重要主題的故事。
有些人秉持「教育者」的想法,認為民間故事中的殺害會讓人感到「殘忍」,並認定不該把這樣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也有人主張應該把故事改編。這樣的意見實在十分荒謬,如果把格林童話中含有「殺害」主題的故事都拿掉,那格林童話就不再是格林童話了吧?格林童話中,光是描述實際「殺害」行為的故事(不是只有殺害的意圖),隨便一數,就多達約四分之一,占了相當多的數量。為什麼民間故事中會提到這麼多的「殺害」呢?而格林童話中的「殺害」,又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呢?本書接下來,就要概括地來看這些問題。
格林童話與日本民間故事
老實說,我之所以會開始探討民間故事中的殺害,是源自於我對日本民間故事的考察。
長久以來,我試著透過日本民間故事,探索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並將結果大致整理成冊發表出來,而在發表之後,我仍持續思考這當中還有什麼未竟的問題,於是「殺害」這個重要的主題,就浮現在腦海中。
比較日本的民間故事與世界各國的民間故事時,可以將「異類婚姻」視為重要的關鍵特徵。民俗文學學者小澤俊夫已經將這個觀點發表在其劃時代的研究當中,而我也順著他的脈絡思考。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猴女婿」(《日本民間故事大成》)等異類女婿的故事中,異類女婿經常遭到殺害。而且這些動物女婿並沒有為非作歹,單單只是因為身為動物,就被人類殺死,而有時殺害的方法,還可說是極為陰險歹毒。然而若對照異類妻子,譬如「鶴娘子」(《大成》),這些妻子就沒有被殺,只是當場離去。因此,殺害異類女婿,可謂日本民間故事極為顯著的特徵。若比較「猴女婿」與格林童話中的「青蛙王子」(《全譯 格林童話集》一),就能發現彼此之間的顯著差異。「青蛙王子」雖然也屬於一種異類婚姻,但是當公主將討厭的青蛙丟向牆壁時(這裡也能看到「殺害」的主題),青蛙變身為王子並與公主結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這個故事,與利用計謀殺死猴女婿的日本民間故事,呈現出鮮明的對比。
關於「殺害」這點,日本還有一則值得注意的民間故事。我想,廣義地解釋「殺害」的話,「自殺」應該也包括在內,而日本民間故事中,就有以下這則令人震驚的故事。這則故事屬於「鬼子小綱」(《大成》二四七A)分類中的某個版本,有些也以「片子」為題。故事是這樣的:鬼把人類的妻子擄走,讓她成為自己的妻子。於是丈夫出發尋找妻子的下落,終於在第十年來到鬼島,他在那裡遇見了鬼與人類妻子生下的孩子,這個孩子自稱為「片子」。後來人類夫妻重逢,並在片子的幫助下回到人界,但所有人都不接納半鬼半人的片子,無處容身的他,最後從大樹上跳下來自殺。這是一則非常令人震驚的故事。為了母親的幸福而拚命奉獻的孩子,卻因為自己身為「半人半鬼」而自責,最後甚至結束自己的性命(關於這點,下一章會再討論)。
我讀到這篇故事時,覺得這篇故事很有日本特色,並與前面提到的異類女婿問題一併做了許多思考。不過,如果將日本民間故事與格林童話進行比較,真的可以斷定格林童話中就「絕對」沒有這樣的情節嗎?當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後,逐漸有些不安。因為我雖然仔細讀過格林童話,卻不是記得那麼清楚,而且故事情節出人意表,可以說是民間故事的特徵。於是我把焦點擺在「殺害」,將格林童話重新讀過一遍,並把所有故事中關於「殺害」(包含自殺)的情節製作成表格。
我最原始的動機,是探討日本民間故事,但我看著自己製作的一覽表時,腦中也浮現了一些頗為有趣的想法。接下來就以格林童話中的「殺害」為主題,敘述我腦中浮現的想法,穿插與日本的民間故事的比較。「殺害」的意義
我有一位個案因為夢見殺人而覺得非常驚恐。或許因為他不知道從哪裡聽來「夢境滿足了願望」之類的說法,才會那麼驚恐吧?我問他:「你是不是為了建立現在的生活方式,而在過去扼殺了某些事物?」他聽到這個問題就心裡有數了,於是我就從這個切入點去分析他的夢境。換句話說,「殺」這個字象徵的意義非常廣泛,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使用「扼殺氣息」或「扼殺味道」來形容「屏息」或「破壞味道」,而運動中也有「殺球」這樣的技巧。
翻開辭典《廣辭苑》,「殺」除了「①結束生命」的意思之外,還有「②壓制,使之氣勢減弱;壓制,使之無法活動。③在競爭中,削弱對手的攻擊力。④在棒球中,使對手出局。⑤(俗語)抵押。⑥將對方迷得神魂顛倒」等意思。即使查的是英文字典,也能從英文的「kill」查到幾乎相同的意思。因此從語言的象徵角度來看,夢境或民間故事中的「殺」,不一定是字面上的「結束生命」,必須像字典一樣,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解讀。換句話說,民間故事中的「殺」,不是字面上的「殺人」。孩子們在心底深處感受到這點,所以即使聽了民間故事,也不會那麼驚訝或害怕。
在思考殺害的象徵性時,也可以完全反過來思考。也就是說,有些人以為他對某件事物所做的,只是單純的壓抑、削弱其氣勢,但其實他的行為已經算是某種「殺害」了。舉例來說,假設有個國中生告訴父親自己想要加入棒球隊,但是父親卻對他說:「你可以打棒球,但是不能加入棒球隊,因為練習的時間太長了,會影響功課。」父親這麼說的時候,往往以為自己只是壓抑了孩子強烈的渴望,但有時候卻是扼殺了孩子的靈魂。這麼一想,我甚至覺得很多父母不僅殺害自己的孩子,還把孩子當成「食物」了,不是嗎?
那些以「甜言蜜語」迷惑孩子,將孩子當成「自己的所有物」或「食物」的父母,或許就和「糖果屋」裡用糖果餅乾做的房子引誘孩子們,最後把孩子們吃掉的巫婆沒什麼兩樣。如果注意到人類現實社會中的各種「殘忍」,尤其是大人對孩子所做的殘忍行為,就會發現沒有必要只把民間故事中的殘忍挑出來說三道四。即使只是處於空想的階段,還不到「想要殺掉那個人」的程度,也應該很少有人能夠拍胸脯自己從未設想過「如果那個人不在的話」或者「要是那個人死掉的話」之類的情形。而且想像的階段愈深入,「殺害」的意思也會愈加深。無論親子關係再怎麼親密,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對父母懷著強烈的抗拒。而且,這樣的情緒甚至可能強烈到不僅止於抗拒或反抗,或許還會在某段時間全面否定父母。如果沒有經歷過這種強烈的否定,孩子就難以成長為能與父母保持適當距離的獨立大人。這樣的過程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孩子必須經歷象徵層次上的「殺父弒母」。
思考民間故事的意義時,隨著孩子成長所帶來的弒親問題是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已經在其他著作中討論過這點。但由於這點在本書中也相當重要,所以在此很簡單地介紹一下。奧地利精神分析學者佛洛伊德注意到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內心糾葛,他認為所有的男性在兒時都有殺死父親,與母親結婚的欲望,但這樣的欲望遭到壓抑,以伊底帕斯情結的狀態留在無意識當中。而瑞士分析心理學者榮格則認為,與其將神話或民間故事中常見的弒親主題視為實際的親子關係,倒不如將其視為個人與存在於個人普遍無意識中的原型──「父親形象」與「母親形象」之間的關係。
榮格的學生艾瑞旭.紐曼(Erich Neumann),更進一步探討西方近代的自我確立過程與弒親的象徵性之間的關聯。紐曼提到,近代西方所確立的自我,屬於世界上的特例,而典型的英雄故事,象徵的就是自我確立的過程。英雄故事可分成英雄的誕生、英雄打敗怪物(龍)、英雄與被怪物抓走的少女結婚等三個階段。他認為英雄的誕生,象徵自我的誕生;打敗怪物則代表自我脫離母親形象與父親形象的束縛,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而後與少女結婚,則象徵獨立的自我再度與世界締結新的關係。
這是極具說服力的想法「之一」,卻不是唯一的正確答案。而且這樣的想法,雖然能夠用來解釋西方故事,對於日本的故事卻不一定適用。不過接下來在探討格林童話時,我覺得應該把這樣的概念放在腦海裡,但並非將紐曼的想法套用到所有的殺害故事中。接下來,希望大家把前面提到的所有關於殺害的內容記在腦中,來進行對格林童話的探討。第八章、民間故事的殘忍性
殘忍之處在哪裡?
不論是東方或是西方的民間故事,都描述了許多「殘忍的情節」。只要稍微翻閱一下格林童話,就能立刻找出殘忍的場景。譬如在「小紅帽」中,小紅帽被大野狼吞下肚;在「沒有手的女孩」中,父親砍下親生女兒的雙手;在「糖果屋」中,父母為了解決飢餓的問題而拋棄孩子。格林兄弟雖然將「糖果屋」的母親改寫成繼母,但在原版的故事裡卻是親生母親。
東方的故事也充滿了殘忍的情節,與西方故事相比,不遑多讓。「喀擦喀擦山」中的狸貓,不僅把老奶奶殺死,還煮成老奶奶湯給老爺爺吃。這段情節過於殘忍,所以很多「喀擦喀擦山」的童書繪本都將這個部分刪去。但有些原始版本的「喀擦喀擦山」在老爺爺喝下老奶奶湯之後就結束了,沒有提到後來兔子幫忙報仇的部分。換句話說,老奶奶湯是這個故事的著眼點,如果把老奶奶湯刪去,故事就無法成立。在「螃蟹與猴子」的故事中,雙方也發生了極為殘忍的交戰,螃蟹被猴子殺掉,小螃蟹為了報仇而把猴子的頭剪下來等等。
類似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但有些人質疑民間故事中的殘忍性,因此在說給孩子聽的時候,擅自將故事改編。話說回來,格林兄弟確實也將「糖果屋」與「白雪公主」中的親生母親改寫為繼母,只不過日本市面上的童書繪本,把內容改編得太過輕描淡寫,不禁令人訝異。譬如原本應該被剪下腦袋的猴子,在改編的故事中卻變成哭著道歉就得到原諒。市面上的繪本很多都以這樣的「和平共處」收尾。關於「改編」的問題我想留待之後討論,在這裡先探討所謂的「殘忍」到底是什麼。那些基於淺薄的「和平」理念而製作出粗糙童書繪本的人,知道孩子的靈魂在讀了、聽了這些淡化處理的故事後,無聊到幾乎要窒息嗎?有些母親「為了孩子好」,而把一些無趣的故事讀給他們聽,這些母親的行為不是與騙老爺爺喝下老奶奶湯的狸貓沒兩樣嗎?大人必須察覺到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對孩子做出了多麼殘忍的事情。如果把民間故事解釋成發生在內心深層之處的真實故事,就會發現民間故事中描述的「殘忍」,就如同家常便飯般發生。嚴格禁止女兒與他人來往的父親,這不是就和「砍下女兒的雙手」一樣嗎?把孩子當成「食物」的父母很多、被封在「水晶棺材」裡的女孩也確實存在。而且孩子為了成長,甚至需要在內在完成「殺父弒母」的儀式。這麼一想就會發現,大人一邊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殘忍」的事情,卻又一邊禁止殘忍的故事,或是將其改寫,這樣的行為就像日本在戰爭時對創作內容進行的審查一樣。無論審查多麼嚴格,最後還是會以更愚蠢的形式露出馬腳。
孩子都知道
前面提到的這些事情,孩子其實都知道得很清楚。但關於這裡的「知道」,必須稍微下點註解。大人一般所謂的「知道」,難免都會過度連結到智能的運作。大人會將新事物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與自己的知識體系相互對照,由此產生「知道」的感受。譬如提到狸貓的時候,大人會對照自己的知識,判斷狸貓是一種動物、與貓差不多大、住在山裡面等等,然後才會說自己「知道」狸貓是什麼。但孩子不一樣,他們對狸貓的反應是全人的,他們知道狸貓單純只是動物不是妖怪,但同時也知道狸貓是狡猾、會騙人的傢伙,而且狸貓不只住在山村,也住在都會,甚至住在自己的心裡。孩子的「知」,靠的不是頭腦,而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受,而且是全人的、有生命的。
當孩子聽到大野狼在可愛的小紅帽面前露出真面目,將她整個吞下肚時,能夠對照自己的經驗,把這件事當成「常有的事情」來體驗。他們也確實能夠透過深入的智慧,看穿很多家庭都經常在晚餐端出「老奶奶湯」。更了不起的是,他們清楚知道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於外在的現實當中。大家應該不曾聽說過有哪個孩子在聽了「喀擦喀擦山」的故事後,想要把老奶奶煮成味噌湯吧?也不曾聽說過有哪個孩子在聽了螃蟹與猴子的故事後,試圖拿剪刀把同學的頭剪下來吧?由此可知,大人可以更放心地信賴孩子的智慧。愈是不安的大人,愈無法信賴孩子。很多「為了孩子好」而把殘忍故事改寫成溫和形式的大人,都沒有發現他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是為了減輕自己在面對內在真實時所產生的不安。無論再怎麼試圖矇混,都無法騙過孩子。前面已經說過,孩子就算聽了殘忍的故事,也不會變得殘忍。那麼完全沒有聽過殘忍故事的孩子,又會變得如何呢?首先可以想到的反應,是孩子自己編造出殘忍的故事。這其實是非常健康的反應,或許也有大人記得自己曾有過這樣的經驗。當父母給的故事全都過於「安全無害」時,孩子就會自己幻想出殘忍的故事,或是從他人之處尋求這樣的殘忍故事。畢竟孩子的靈魂渴求無限的自由。
如果父母給的故事全都過於「安全無害」,而孩子也不具備反彈的能力,並因此被塑造成人為的「好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時候,就會急遽發生反轉現象,對父母施加「殘忍」的暴力。我想各位可以透過最近日本急速增加的家庭暴力事件充分了解到這件事情。
孩子聽到「殘忍」的故事時,可以知道這是發生在內心世界的事情,並且將其意義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就不再需要做出殘忍的舉動。但是對於殘忍沒有任何免疫力的孩子,最後將成為殘忍的犧牲品。
說故事的意義
肯定民間故事中的殘忍,不代表肯定「殘忍」本身。但民間故事中的殘忍,真的如同前面所說的,完全不會刺激孩子的殘忍性嗎?關於這點,我還是必須指出「說故事的方法」,以及「說故事者」的重要性。外在的真實即使是透過書本也能清楚傳達,但是想要清楚傳達內在的真實,只能透過人與人,或是人的靈魂與靈魂的直接對話。所以民間故事只有透過「口耳相傳」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如果說故事的人已經如同前述一般,明確知道殘忍性的意義,那麼不管他說的故事有多麼殘忍,都不會發生問題。這裡的「知道」,指的也是全人意義上的「知」。民間故事只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口耳相傳,才能傳達內在的真實。因為孩子即使被故事中的殘忍與可怕嚇得尖叫,也能以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為基礎,消化聽故事時的恐怖體驗,將其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那麼如果把民間故事寫成書,又會如何呢?民間故事原本應該是口耳相傳的內容,不是閱讀的內容。但如果孩子能夠在閱讀之前獲得支持自己存在的良好人際關係,我想他們即使自己閱讀故事,也彷彿能夠聽見「說故事的聲音」。正因為民間故事是經過漫長歲月形成的內容,所以才具有極高的普遍性,具備某種能在心底深處產生共鳴的性質。
但如果孩子在人際關係上沒有前述穩定的根基,就可能在閱讀民間故事的時候,被強烈的不安襲擊,繼而受到不良的影響。將民間故事寫成書,已經有點困難了,畫成繪本或是做成電視節目,更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因為繪本或電視節目在孩子聽到故事、建立自己內在現實的印象之前,就已經給了他們來自外部的影像,而這些影像將成為一種外在現實。因此製作民間故事的繪本,需要仔細的考量與相當程度的技術。理想的繪本不能灌輸孩子既定的印象,而是要幫助孩子將他們的印象擴充得更加豐富。但到底有多少製作民間故事繪本的人,擁有這樣的自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