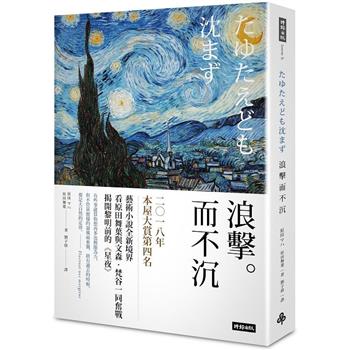收割後已不見任何稻穗的麥田一望無垠,一名男子,獨立交叉路口。
那是空曠的風景。地平線彼方正有積雨雲無聲湧起。高掛中天的太陽發威,從正上方朝他稀薄的白髮射下尖銳的光箭。他的背後已大汗淋漓,白襯衫緊貼在身上。
汗水沿著額頭的皺紋滑落,可他無意抹去,他只是凝視麥梗一望無際的田間小徑。彷彿在苦等不久便會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臨的某人。
狂風在耳邊呼嘯。塵埃飛揚的小路上,落下清晰短小的影子。唯有手裡的亞麻外套在風中搖曳。
宣告正午來臨的教堂鐘聲響起。他向後轉身,挺直腰桿,垂首閉眼。他面對的方向是村子的公墓。他獻上默禱,直至十二響鐘聲結束。
他走向村公所前的拉烏客棧。看似店主的男人站在門口,好像和一個中年東方人起了爭執。
「我不是可疑人物。請你讓我看看樓上的房間,只要一下子就好。」
東方人用生澀的法語懇求。拉烏客棧的老闆挺起啤酒肚,反覆嚷著「跟你說不行就是不行」。
「為什麼?我來自日本。我是梵谷研究者。所以我想參觀梵谷去世的房間。」
他走近二人,「午安,先生。」他用法語說。
「這個人自稱是日本的梵谷研究者。梵谷的確是在這間客棧的三樓去世的吧。雖然沒有對一般大眾公開,但若是研究者,讓他參觀一下應該也無妨?」
他出面說情。並且又補上一句「畢竟人家是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
「你又是甚麼人?」店主流露訝異的眼神轉向他。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在研究者之間很有名喔。」他和顏悅色地回答。
「這樣啊。那我就更要鄭重聲明:『我不答應。』」
店主斬釘截鐵說。
「我這裡也經營供應三餐的出租房。那個房間本來就因為不吉利找不到房客肯租了。現在居然還有甚麼研究者跑來要求參觀。起初我心想無所謂就讓人參觀了,沒想到最近三天兩頭有人上門。如果整天忙著應付這些人,我還怎麼做生意啊。」
店主如此滔滔不絕抱怨後,又說,
「從日本特地來參觀我當然也很感謝啦。畢竟這裡只是鄉下地方。樓上的房間不能開放參觀,但是可以在這兒吃午餐。我們的燉肉很好吃喔。」
他用英語問日本人:「您會英語嗎?」日本人立刻回答:「會,比法語好多了。」
他向日本研究者轉述店主的說詞。研究者很失望,但事已至此莫可奈何,遂決定留下用餐,欣然走進店內。他也尾隨在後,在研究者隔壁的位子坐下。
他點了紅酒與燉肉。隔壁的日本人也點了同樣的東西。研究者從黑色皮包取出筆記本和鉛筆,在桌上攤開後開始寫字。他斜眼偷窺筆記本。
上面寫滿縱行文字,研究者不時拿鉛筆尾巴戳戳滿頭銀髮,由右至左不斷寫出文字。他驀然想起,曾任機械技師的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去日本做技術指導,當時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寫字,這才知道原來日本人是這樣直著寫字,難怪日本的畫也多半是縱向的構圖。
察覺他對筆記本感興趣,研究者停下握鉛筆的手。然後問道:「請問您是從哪來?」
「Nl-Laren。荷蘭的拉倫。」他回答。「從阿姆斯特丹開車約需三、四十分鐘的城鎮。」
「拉倫嗎?我沒去過……」
「荷蘭呢?」
「荷蘭倒是去過。別看我這樣,好歹也是梵谷的研究者。我去過阿姆斯特丹和埃德。」
埃德有梵谷作品的大收藏家克勒勒.米勒夫妻於一九三八年創立的美術館。這位研究者說,在那裡第一次有系統地看到大批梵谷作品。「唉,當時簡直說不出話。只能說,太感動了。」許是又想起當時的記憶,研究者語帶熱切說。
「我知道美國的美術館比法國收藏了更多梵谷的作品,但我現在還無法成行。機票太貴了……我個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死前能夠看到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的《星夜》。」
研究者露出夢幻的神情,
「啊,不過我在羅浮宮也看到囉。《羅納河上的星夜》、《自畫像》、《在亞爾的臥室》、《嘉舍醫生的肖像》,還有……《奧維爾教堂》。」
研究者如數家珍地說出正確的畫名。他不禁微笑。
「日本的美術館沒有梵谷作品嗎?」他問,
「有喔。只有一件。」對方立刻回答。
「是描繪玫瑰的晚年作品。收藏於國立西洋美術館這間戰後成立的美術館中。」
這件名為《玫瑰》的作品,戰前是日本企業家松方幸次郎的收藏品,他在法國買下這幅畫後,就和其他畫家的作品一同保管在法國國內的某處。後來戰爭爆發,日本戰敗,松方名下的那些法國名畫悉數遭到法國政府沒收。戰後日法兩國進行歸還談判,松方多達四百件的收藏品中,除了被指定留在法國的十八件作品,一律以「歸還捐贈品」的名義送還日本。其中一件就是梵谷的《玫瑰》──研究者如此詳細解釋給他聽。
「羅浮宮收藏的那幅《在亞爾的臥室》,本來也是松方的收藏品。但是法國大概也捨不得吧。所以好像被指定留下。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實在不像話,不過,那畢竟是梵谷描繪在亞爾住過的房間嘛。如果留在法國的美術館,而且是舉世聞名的羅浮宮美術館,畫家本人大概也更樂意吧。」
許是紅酒的醉意上來,研究者變得饒舌,用相當流利的英語說個不停。他一邊拿叉子吃燉肉,一邊默默傾聽研究者說話。
「對了,」趁著賬單被放到桌上,他試探地詢問。
「請問您聽說過林這個人物嗎?」
「啊?」研究者反問。「林?」
「對。一位名叫林忠正的日本畫商。是以前的人,十九世紀末據說在巴黎開畫廊販賣日本美術品……」
彷彿聽到甚麼重大問題,研究者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不……很遺憾,我沒聽說過。那個人和梵谷有甚麼關係嗎?」
他苦笑。
「我不是研究梵谷的專家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機械技師。……不,二年前在七十歲時退休了,所以應該說是『曾任』技師。」
他說明自己的身分,
「我曾偶然看到林這個名字……我以為日本研究者或許會知道,所以才問問看。」
「噢?我還以為您也是梵谷專家才跟您說了這麼多呢。畢竟,除了特別狂熱的粉絲或專家,不可能特地在梵谷的忌日專程從荷蘭來到這個小村子吧。」
「咦,原來是這樣啊。」他做出驚訝的表情。「今天是梵谷的忌日啊……」
「不然您怎麼會來這個村子?」
聽到研究者這麼問,他笑答:
「來吃這裡的燉肉呀。」
二人各自結帳,在客棧前握手道別。研究者客氣道歉說:「到現在都還沒自我介紹,真是失禮。」他自稱姓式場,正職是精神科醫生。
「您呢?」式場問。「貴姓大名?」
他在瞬間遲疑,然後才回答:
「我叫文森。」
式場當下開心地發出驚呼。「您和梵谷同名呢。」
如林間篩落陽光的微笑逐漸在他臉上擴大。
「是的,這是荷蘭人常見的名字。」
那是空曠的風景。地平線彼方正有積雨雲無聲湧起。高掛中天的太陽發威,從正上方朝他稀薄的白髮射下尖銳的光箭。他的背後已大汗淋漓,白襯衫緊貼在身上。
汗水沿著額頭的皺紋滑落,可他無意抹去,他只是凝視麥梗一望無際的田間小徑。彷彿在苦等不久便會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臨的某人。
狂風在耳邊呼嘯。塵埃飛揚的小路上,落下清晰短小的影子。唯有手裡的亞麻外套在風中搖曳。
宣告正午來臨的教堂鐘聲響起。他向後轉身,挺直腰桿,垂首閉眼。他面對的方向是村子的公墓。他獻上默禱,直至十二響鐘聲結束。
他走向村公所前的拉烏客棧。看似店主的男人站在門口,好像和一個中年東方人起了爭執。
「我不是可疑人物。請你讓我看看樓上的房間,只要一下子就好。」
東方人用生澀的法語懇求。拉烏客棧的老闆挺起啤酒肚,反覆嚷著「跟你說不行就是不行」。
「為什麼?我來自日本。我是梵谷研究者。所以我想參觀梵谷去世的房間。」
他走近二人,「午安,先生。」他用法語說。
「這個人自稱是日本的梵谷研究者。梵谷的確是在這間客棧的三樓去世的吧。雖然沒有對一般大眾公開,但若是研究者,讓他參觀一下應該也無妨?」
他出面說情。並且又補上一句「畢竟人家是專程從日本遠道而來……」
「你又是甚麼人?」店主流露訝異的眼神轉向他。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在研究者之間很有名喔。」他和顏悅色地回答。
「這樣啊。那我就更要鄭重聲明:『我不答應。』」
店主斬釘截鐵說。
「我這裡也經營供應三餐的出租房。那個房間本來就因為不吉利找不到房客肯租了。現在居然還有甚麼研究者跑來要求參觀。起初我心想無所謂就讓人參觀了,沒想到最近三天兩頭有人上門。如果整天忙著應付這些人,我還怎麼做生意啊。」
店主如此滔滔不絕抱怨後,又說,
「從日本特地來參觀我當然也很感謝啦。畢竟這裡只是鄉下地方。樓上的房間不能開放參觀,但是可以在這兒吃午餐。我們的燉肉很好吃喔。」
他用英語問日本人:「您會英語嗎?」日本人立刻回答:「會,比法語好多了。」
他向日本研究者轉述店主的說詞。研究者很失望,但事已至此莫可奈何,遂決定留下用餐,欣然走進店內。他也尾隨在後,在研究者隔壁的位子坐下。
他點了紅酒與燉肉。隔壁的日本人也點了同樣的東西。研究者從黑色皮包取出筆記本和鉛筆,在桌上攤開後開始寫字。他斜眼偷窺筆記本。
上面寫滿縱行文字,研究者不時拿鉛筆尾巴戳戳滿頭銀髮,由右至左不斷寫出文字。他驀然想起,曾任機械技師的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去日本做技術指導,當時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寫字,這才知道原來日本人是這樣直著寫字,難怪日本的畫也多半是縱向的構圖。
察覺他對筆記本感興趣,研究者停下握鉛筆的手。然後問道:「請問您是從哪來?」
「Nl-Laren。荷蘭的拉倫。」他回答。「從阿姆斯特丹開車約需三、四十分鐘的城鎮。」
「拉倫嗎?我沒去過……」
「荷蘭呢?」
「荷蘭倒是去過。別看我這樣,好歹也是梵谷的研究者。我去過阿姆斯特丹和埃德。」
埃德有梵谷作品的大收藏家克勒勒.米勒夫妻於一九三八年創立的美術館。這位研究者說,在那裡第一次有系統地看到大批梵谷作品。「唉,當時簡直說不出話。只能說,太感動了。」許是又想起當時的記憶,研究者語帶熱切說。
「我知道美國的美術館比法國收藏了更多梵谷的作品,但我現在還無法成行。機票太貴了……我個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死前能夠看到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的《星夜》。」
研究者露出夢幻的神情,
「啊,不過我在羅浮宮也看到囉。《羅納河上的星夜》、《自畫像》、《在亞爾的臥室》、《嘉舍醫生的肖像》,還有……《奧維爾教堂》。」
研究者如數家珍地說出正確的畫名。他不禁微笑。
「日本的美術館沒有梵谷作品嗎?」他問,
「有喔。只有一件。」對方立刻回答。
「是描繪玫瑰的晚年作品。收藏於國立西洋美術館這間戰後成立的美術館中。」
這件名為《玫瑰》的作品,戰前是日本企業家松方幸次郎的收藏品,他在法國買下這幅畫後,就和其他畫家的作品一同保管在法國國內的某處。後來戰爭爆發,日本戰敗,松方名下的那些法國名畫悉數遭到法國政府沒收。戰後日法兩國進行歸還談判,松方多達四百件的收藏品中,除了被指定留在法國的十八件作品,一律以「歸還捐贈品」的名義送還日本。其中一件就是梵谷的《玫瑰》──研究者如此詳細解釋給他聽。
「羅浮宮收藏的那幅《在亞爾的臥室》,本來也是松方的收藏品。但是法國大概也捨不得吧。所以好像被指定留下。在日本人看來這樣做實在不像話,不過,那畢竟是梵谷描繪在亞爾住過的房間嘛。如果留在法國的美術館,而且是舉世聞名的羅浮宮美術館,畫家本人大概也更樂意吧。」
許是紅酒的醉意上來,研究者變得饒舌,用相當流利的英語說個不停。他一邊拿叉子吃燉肉,一邊默默傾聽研究者說話。
「對了,」趁著賬單被放到桌上,他試探地詢問。
「請問您聽說過林這個人物嗎?」
「啊?」研究者反問。「林?」
「對。一位名叫林忠正的日本畫商。是以前的人,十九世紀末據說在巴黎開畫廊販賣日本美術品……」
彷彿聽到甚麼重大問題,研究者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不……很遺憾,我沒聽說過。那個人和梵谷有甚麼關係嗎?」
他苦笑。
「我不是研究梵谷的專家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機械技師。……不,二年前在七十歲時退休了,所以應該說是『曾任』技師。」
他說明自己的身分,
「我曾偶然看到林這個名字……我以為日本研究者或許會知道,所以才問問看。」
「噢?我還以為您也是梵谷專家才跟您說了這麼多呢。畢竟,除了特別狂熱的粉絲或專家,不可能特地在梵谷的忌日專程從荷蘭來到這個小村子吧。」
「咦,原來是這樣啊。」他做出驚訝的表情。「今天是梵谷的忌日啊……」
「不然您怎麼會來這個村子?」
聽到研究者這麼問,他笑答:
「來吃這裡的燉肉呀。」
二人各自結帳,在客棧前握手道別。研究者客氣道歉說:「到現在都還沒自我介紹,真是失禮。」他自稱姓式場,正職是精神科醫生。
「您呢?」式場問。「貴姓大名?」
他在瞬間遲疑,然後才回答:
「我叫文森。」
式場當下開心地發出驚呼。「您和梵谷同名呢。」
如林間篩落陽光的微笑逐漸在他臉上擴大。
「是的,這是荷蘭人常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