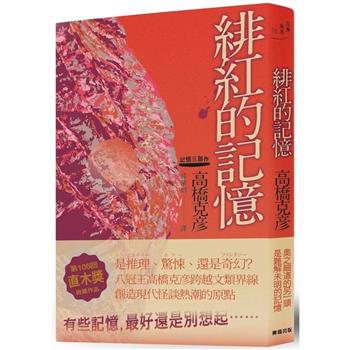1
明明約在彼此學生時代都很常來的新宿,而且是十分好找的咖啡廳,距離約好的時間都已經過了四十分鐘,加藤還不見人影,我只好一個勁兒地猛抽菸。幸好距離下個行程還有很多時間,不用擔心衝到。但都等了這麼久,不禁懷疑是不是我搞錯地點了。是加藤說要見面,時間也配合他來東京出差的空檔,我還記得他說傍晚要和分公司的人開會,萬一遲到,該傷腦筋的其實是他不是我。這時要是有家人可以幫忙傳話就好了,只可惜我雖然四十好幾,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或許加藤打來的電話此時此刻正在我空無一人的家裡響個不停也未可知。
〈話說回來……〉
沒料到咖啡廳會換名字,幸好地址沒變,所以就算名字不同,加藤應該還是能找到這家店……。就算心浮氣躁也沒有其他辦法能聯絡上他,我決定再等三十分鐘。正當我的目光離開時鐘,加藤的身影也同時進入視線範圍,正以飄忽不定的眼神在寬敞的店內四下張望。我朝他頷首,加藤如釋重負地輕輕揮手。
「不好意思。」
加藤把紙袋放在沙發上,用掌心拭去額頭的汗水。他還是老樣子,儘管已經五年沒見,削瘦的體型、黝黑的頭髮、喜歡穿學院風休閒服的習慣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橫看豎看也才三十出頭的樣子。
「格紋襯衫啊……穿這樣去見分公司的人沒問題嗎?」
「導播都是這樣的,總公司的高層還有人留著蘑菇頭髮型呢,雖然看起來很不像樣就是了。」
加藤點了冰咖啡,從紙袋裡拿出岩手的特產——烏賊酒壺,顧名思義就是用曬乾的烏賊製成的酒壺,把酒倒進去喝別有一番風味,喝完以後還可以撕來吃,所以頗受觀光客青睞。
「對你來說可能不是什麼稀奇的玩意兒,剛好在店裡看到就買來了。」
「真是感激不盡啊……不過我一個人住。」
「那又怎樣?」
「你不覺得太空虛了嗎?不知道為什麼,一聽到烏賊酒壺就想到圓形的矮桌,還有昏暗的燈泡。」
加藤哈哈大笑。
「幹嘛不結婚?你現在可是炙手可熱的設計師,像你這麼有名的人,身邊的美女要多少有多少,肯定不愁沒對象吧。還是因為對象太多,難以抉擇?」
「因為我清心寡欲。」
加藤對我開的玩笑笑而不語。
「你才受歡迎吧,有很多女人光是聽到電視台就口水流滿地了。」
「我那裡不比東京,我做的也不是給偶像歌手上的節目,而且我都四十好幾,在這個業界算是老頭子了。」
加藤一口氣用吸管喝掉半杯送上來的冰咖啡。
「可是啊……當我發現自己時間來不及,想打電話告訴你一聲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這家店會改名。」
「我記得半年前還是以前那個名字。」
「急死我了,從神保町到新宿再怎麼趕也要三十分鐘,而且在東京叫計程車也難保不會遇上塞車,但我相信你一定會等我。」
「神保町……」
「因為提早到了,想說去打發一下時間,結果一去到那裡就忘了時間,真是失策。盛岡沒幾家二手書店,害我一下子看得太著迷,每家店都走進去逛了逛。」
「可有發現什麼有趣的書?」
「有,我買了岩手的書。」
「哦,來神保町找岩手的書。」
「倒也不是,那裡有好幾家跟鄉土史有關的專賣店,說不定在這裡可以賣得更好,所以有很多比盛岡還罕見的書,還有盛岡市史。」
我也同意,但不怎麼好奇,所以沒認真找過,印象中像一誠堂這種老字號就設有這樣的專區。
「所以呢?買了什麼樣的書?」
「昭和三十八年版的盛岡住宅地圖。」
「住宅地圖?那是什麼?」
「還能是什麼,就住宅地圖啊!你不知道嗎?」
「跟普通的地圖不一樣嗎?」
「不一樣。應該也有東京的,不過就是普通的那種。這種住宅地圖會仔細地畫出每一戶人家,連屋主的名字也全部寫上去。只要知道地址和名字,靠這本地圖就能知道哪戶人家位在哪裡,所以貨運公司或計程車司機都會利用。」
「全部!就連公寓也是嗎?」
「那當然。如果是社區型大樓,地圖寫不下,會另外寫在後面。比起用說的,直接看比較快,不過整本書充滿黴味就是。」
加藤從紙袋裡掏出B4大小的地圖,放在桌上。聽說是地圖,我原本以為是大面積的紙,結果反而是被厚度嚇了一跳,少說有七、八十頁。
「這些都是盛岡的地圖嗎?」
「那當然。不只是街道的輪廓,還畫上每一戶人家,再加上屋主的名字都要印成足以辨識的大小,一頁頂多只能畫出兩百家左右,所以再怎麼努力,也只塞得進三到四個町。」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這種地圖真的有必要存在嗎?雖說對貨運公司很方便,但是像盛岡這種小地方,多送幾次就能全部摸熟了。
「不只貨運公司有配送業務,賣酒的和報社也有相同的需求。更何況如果是這麼詳細的地圖,就連狹窄的巷弄也一目瞭然,消防隊應該也視若珍寶,要怎麼用全看個人。」
「可是……市容每年都在改變。」
「所以每年都會發行新的版本。如果是普通的市區地圖,可能五或十年才換一次,但這種住宅地圖每年都要更新。而且這本是三十八年的版本,所以只有這麼厚,現在的地圖將近四百頁喔,幾乎跟電話簿一樣了。」
「真難以置信。」
我仰天長嘆。
「還好啦……東京大概不能這麼做吧。像東京這種大都會,地圖會膨脹到無與倫比的地步,光是簡單的分區地圖都要上百頁了,要是以這種方式製作,光新宿至少就要三百頁,二十三區加起來搞不好超過七千頁,只有一個區對工作也沒太大幫助。更何況,你根本也不知道有這種住宅地圖吧。」
再怎麼便宜,七千頁的地圖至少也要賣個二十萬圓,如果每年還要推出新版的話……。
「對吧。盛岡現在發行的住宅地圖就要一千圓以上,東京很難壓在三十萬以下,結果還是錢的問題。」
加藤搖頭。
「問題是……你為什麼要買這種地圖?三十八年的地圖根本沒有用處了吧。」
我感到疑惑。再怎麼便宜也是二十年前的地圖,難道是有價值的古董嗎?
「這是我的興趣啦,興趣。」
「興趣?」
「聽說當初印的就少,連在盛岡也不容易買到。圖書館有是有,但還是希望手邊就有一本,可以細細品味。」
「這有什麼樂趣可言,你還真是個怪人。」
「我說你啊……三十八年的時候,你住在哪一帶?」
加藤以若有所思的表情問我。
「說到三十八年,不就是我們十七歲的時候嗎……」
高中二年級,當時和眼前的加藤是同班同學。
「我住在菜園的祖母家。」
南部藩以前有片野菜田,現在是盛岡的市中心,我高中三年都住在那個區域的祖母家。老家在偏遠的鄉下,得坐一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到盛岡,上學很不方便。
「你還記得詳細的町名嗎?」
「老松町。」
「屋主的名字呢?」
「木村……就連名字也有嗎?」
「這不是廢話嘛,沒有的話還叫什麼地圖。」
加藤苦笑,翻找地圖,不到五分鐘就抬起頭來。
「面向馬路——右手邊是鈴木家,再過去是『坪半』,是那家中菜館吧,現在也還在喔。正對面是田村信一先生的家。左手邊是小原家。原來如此,現在的New Carina飯店就蓋在高橋家的舊址上。」
加藤一字一句喚醒鮮明的記憶,我邊聽邊起一身的雞皮疙瘩。有條涓涓細流流經田村家的黑色木板圍牆前,小時候經常把石頭丟進那條小河裡玩。五歲到小學四年級這段期間,因為父親的工作經常需要調動,我被寄養在祖母家,因此高中的記憶總是與小時候的記憶混在一起。高橋家的院子很大,種滿了鬱鬱蒼蒼的樹木。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沒那麼大,但是對小孩子來說,簡直跟叢林沒兩樣。四周圍著高聳白牆,印象中沒見過那家人,屋裡總是靜悄悄,只有大狗偶爾吠個幾聲。我曾經真的以為怪人二十面相就躲在那裡。
我搶過加藤手中的地圖。
我住過的地方就原封不動地凍結保存在翻開的那一頁。
地圖上還有祖母家後面,現在已經收掉的料亭「音羽」。半夜上廁所時,從小窗可以看到音羽的二樓走廊。我曾經看見一對男女沒發現我在偷窺,靠在走廊的扶手接吻,也看過年輕藝妓敞開胸口吹風。藝妓雪白的肌膚歷歷在目。
〈原來店名叫做Lovely Corner啊……〉
這家店位在走出玄關,面向大馬路轉角的地方,同樣給人淫靡的印象。到了這個歲數回頭去看,或許只是一家再尋常不過的酒吧,但是從我二樓的房間窺探那家店的紅色窗戶時,總是直到三更半夜還能聽見女人的笑聲。到了夏天,我會關掉房裡的電燈,豎起耳朵偷聽客人吵架或女人嬌嗔的調笑聲從店裡敞開的窗戶傳來。猛然想起傍晚才去店裡上班的女人白皙的圓臉。那個女人有點古怪,身材微胖,胸前豐滿,總是穿著銀色高跟鞋,每次在轉角遇到放學回家的我,就會對我說:「快點長大吧你。」因為濃妝豔抹,看起來很成熟,其實只跟我差了三、四歲。我記得她叫正子,也記得自己曾經從二樓臉紅心跳地偷看她喝醉了,有個禿頭男子攬著她的肩,拖著她走進屋裡的模樣。
她請我喝過一次茶。當時我站在書店裡看白書,肩膀被她拍了一下,約我去松竹地下室的富士屋冰果室。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毫不猶豫地跟她走,大概是懷著什麼下流的期待吧……。彼此沒有共通的話題,她問我有什麼興趣,我一個人自顧自地聊起怪談電影。當時我正沉迷於赤座美代子在大映主演的《牡丹燈籠》嗎?不對,再早一點,大概是岡田茉莉子飾演的阿岩大受好評的那年夏天。「你們學校都要剃光頭對吧?」她以對電影毫無興趣的表情對我說:「教國語的老師姓吉本對吧?他是我的老相好喔。」總覺得她很髒,只想趕快離開冰果室。不知是否為當時的流行,眼前浮現她用折成四方形的手帕當扇子搧的動作。
「如何?不覺得有點像是回到過去嗎?」
加藤笑著對死盯著地圖不放的我說。
「這比畢業紀念冊或老唱片更能喚起鮮明的回憶。」
「你說的對,我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我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
「我家有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的住宅地圖,邊喝酒邊看的話,不知不覺還會掉下眼淚來喔。我有個朋友叫小翔,家裡是賣醬油的,小學時家裡發生火災,全家人都死了。三十三年的地圖正好畫出那傢伙的家,找到時我哭得好大聲,感覺小翔還活在那張小小的地圖裡。明明在那之前我早就忘了曾經有過這樣的朋友。」
一把年紀的加藤說得眼眶都紅了。
「從此以後,我便開始收集住宅地圖。我現在住的盛岡並不是真正的盛岡,我居住的城市在這本地圖裡,因此不管再古老的街道被拆掉,我都能無動於衷。不久之前我還致力於保存運動,但現在已經完全放下了,徒具其形的事物再怎麼珍惜也毫無意義。」
「……」
「或許是上了年紀,說了一堆廢話。」
加藤喝光剩下的冰咖啡。
「言歸正傳……下禮拜你有什麼打算?」
「還沒決定。話說回來,安太歲是東北才有的習慣吧。」
尤其是岩手和秋田特別流行。男人到了四十二歲,為了安太歲會集合起來,舉行不亞於婚禮的盛大宴會。通常都在二月底舉行,有人提議既然要辦,不如連同學會也一起辦,於是策劃了集體安太歲,我也收到了通知信。如果只有幾個好朋友還好,搞到同學會的規模,不免讓人有點緊張。我也沒有迷信到非安太歲不可的地步,寄出無法出席的答覆後,接到加藤的電話。他也是主辦人之一。
「我是不會勉強你啦,但是如果你願意來,同學會肯定能更添光彩。你已經好幾年沒回盛岡了吧。」
「十五年有了吧。不過倒是因為工作當天來回過幾次。」
「自從新幹線開通以來,盛岡變了很多。雖說我們每天在這裡過活,比較感覺不到變化就是了。你不想見見初戀情人嗎?」
「初戀?」
我的心湖激起一陣漣漪。
「這就是所謂的成名稅嗎?我認識好幾個自稱和你交往過的女人,都是她們自己提起的,是真是假我就不清楚了。」
「叫什麼名字?」
加藤舉了三、四個名字,裡頭還有當時就讀另一所高中繪畫社的谷藤萬里子,我們單獨看過幾次展覽,其他人我幾乎想不起來。
「萬里子現在是小酒館的媽媽桑,很期待能再見到你說。」
加藤竊笑不已。
「你唯獨對自己的異性關係三緘其口……。害我嚇了一大跳,沒想到那麼多女人都說和你交往過。」
「都不是可以稱得上交往過的關係。」
我主動結束這個話題。別的不說,就說我被萬里子狠狠甩掉那件事,現在就算說我們交往過,湧上心頭的也盡是不愉快的回憶,而無半點懷念。她的才華雖不出眾,但人長得特別標緻,是我們這群搞美術的人心目中的女神,我也曾經對畫布描繪出腦海中的她。她或許很適合當小酒館的媽媽桑也說不定。
「這份地圖借我影印。」
我拜託加藤。比起這些現實的回憶,我有更模糊的記憶想確認一下。
「全部嗎?」
「可以的話。」
「那就先借你看,改天再寄還給我就行了。今天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自是求之不得。
明明約在彼此學生時代都很常來的新宿,而且是十分好找的咖啡廳,距離約好的時間都已經過了四十分鐘,加藤還不見人影,我只好一個勁兒地猛抽菸。幸好距離下個行程還有很多時間,不用擔心衝到。但都等了這麼久,不禁懷疑是不是我搞錯地點了。是加藤說要見面,時間也配合他來東京出差的空檔,我還記得他說傍晚要和分公司的人開會,萬一遲到,該傷腦筋的其實是他不是我。這時要是有家人可以幫忙傳話就好了,只可惜我雖然四十好幾,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或許加藤打來的電話此時此刻正在我空無一人的家裡響個不停也未可知。
〈話說回來……〉
沒料到咖啡廳會換名字,幸好地址沒變,所以就算名字不同,加藤應該還是能找到這家店……。就算心浮氣躁也沒有其他辦法能聯絡上他,我決定再等三十分鐘。正當我的目光離開時鐘,加藤的身影也同時進入視線範圍,正以飄忽不定的眼神在寬敞的店內四下張望。我朝他頷首,加藤如釋重負地輕輕揮手。
「不好意思。」
加藤把紙袋放在沙發上,用掌心拭去額頭的汗水。他還是老樣子,儘管已經五年沒見,削瘦的體型、黝黑的頭髮、喜歡穿學院風休閒服的習慣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橫看豎看也才三十出頭的樣子。
「格紋襯衫啊……穿這樣去見分公司的人沒問題嗎?」
「導播都是這樣的,總公司的高層還有人留著蘑菇頭髮型呢,雖然看起來很不像樣就是了。」
加藤點了冰咖啡,從紙袋裡拿出岩手的特產——烏賊酒壺,顧名思義就是用曬乾的烏賊製成的酒壺,把酒倒進去喝別有一番風味,喝完以後還可以撕來吃,所以頗受觀光客青睞。
「對你來說可能不是什麼稀奇的玩意兒,剛好在店裡看到就買來了。」
「真是感激不盡啊……不過我一個人住。」
「那又怎樣?」
「你不覺得太空虛了嗎?不知道為什麼,一聽到烏賊酒壺就想到圓形的矮桌,還有昏暗的燈泡。」
加藤哈哈大笑。
「幹嘛不結婚?你現在可是炙手可熱的設計師,像你這麼有名的人,身邊的美女要多少有多少,肯定不愁沒對象吧。還是因為對象太多,難以抉擇?」
「因為我清心寡欲。」
加藤對我開的玩笑笑而不語。
「你才受歡迎吧,有很多女人光是聽到電視台就口水流滿地了。」
「我那裡不比東京,我做的也不是給偶像歌手上的節目,而且我都四十好幾,在這個業界算是老頭子了。」
加藤一口氣用吸管喝掉半杯送上來的冰咖啡。
「可是啊……當我發現自己時間來不及,想打電話告訴你一聲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這家店會改名。」
「我記得半年前還是以前那個名字。」
「急死我了,從神保町到新宿再怎麼趕也要三十分鐘,而且在東京叫計程車也難保不會遇上塞車,但我相信你一定會等我。」
「神保町……」
「因為提早到了,想說去打發一下時間,結果一去到那裡就忘了時間,真是失策。盛岡沒幾家二手書店,害我一下子看得太著迷,每家店都走進去逛了逛。」
「可有發現什麼有趣的書?」
「有,我買了岩手的書。」
「哦,來神保町找岩手的書。」
「倒也不是,那裡有好幾家跟鄉土史有關的專賣店,說不定在這裡可以賣得更好,所以有很多比盛岡還罕見的書,還有盛岡市史。」
我也同意,但不怎麼好奇,所以沒認真找過,印象中像一誠堂這種老字號就設有這樣的專區。
「所以呢?買了什麼樣的書?」
「昭和三十八年版的盛岡住宅地圖。」
「住宅地圖?那是什麼?」
「還能是什麼,就住宅地圖啊!你不知道嗎?」
「跟普通的地圖不一樣嗎?」
「不一樣。應該也有東京的,不過就是普通的那種。這種住宅地圖會仔細地畫出每一戶人家,連屋主的名字也全部寫上去。只要知道地址和名字,靠這本地圖就能知道哪戶人家位在哪裡,所以貨運公司或計程車司機都會利用。」
「全部!就連公寓也是嗎?」
「那當然。如果是社區型大樓,地圖寫不下,會另外寫在後面。比起用說的,直接看比較快,不過整本書充滿黴味就是。」
加藤從紙袋裡掏出B4大小的地圖,放在桌上。聽說是地圖,我原本以為是大面積的紙,結果反而是被厚度嚇了一跳,少說有七、八十頁。
「這些都是盛岡的地圖嗎?」
「那當然。不只是街道的輪廓,還畫上每一戶人家,再加上屋主的名字都要印成足以辨識的大小,一頁頂多只能畫出兩百家左右,所以再怎麼努力,也只塞得進三到四個町。」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這種地圖真的有必要存在嗎?雖說對貨運公司很方便,但是像盛岡這種小地方,多送幾次就能全部摸熟了。
「不只貨運公司有配送業務,賣酒的和報社也有相同的需求。更何況如果是這麼詳細的地圖,就連狹窄的巷弄也一目瞭然,消防隊應該也視若珍寶,要怎麼用全看個人。」
「可是……市容每年都在改變。」
「所以每年都會發行新的版本。如果是普通的市區地圖,可能五或十年才換一次,但這種住宅地圖每年都要更新。而且這本是三十八年的版本,所以只有這麼厚,現在的地圖將近四百頁喔,幾乎跟電話簿一樣了。」
「真難以置信。」
我仰天長嘆。
「還好啦……東京大概不能這麼做吧。像東京這種大都會,地圖會膨脹到無與倫比的地步,光是簡單的分區地圖都要上百頁了,要是以這種方式製作,光新宿至少就要三百頁,二十三區加起來搞不好超過七千頁,只有一個區對工作也沒太大幫助。更何況,你根本也不知道有這種住宅地圖吧。」
再怎麼便宜,七千頁的地圖至少也要賣個二十萬圓,如果每年還要推出新版的話……。
「對吧。盛岡現在發行的住宅地圖就要一千圓以上,東京很難壓在三十萬以下,結果還是錢的問題。」
加藤搖頭。
「問題是……你為什麼要買這種地圖?三十八年的地圖根本沒有用處了吧。」
我感到疑惑。再怎麼便宜也是二十年前的地圖,難道是有價值的古董嗎?
「這是我的興趣啦,興趣。」
「興趣?」
「聽說當初印的就少,連在盛岡也不容易買到。圖書館有是有,但還是希望手邊就有一本,可以細細品味。」
「這有什麼樂趣可言,你還真是個怪人。」
「我說你啊……三十八年的時候,你住在哪一帶?」
加藤以若有所思的表情問我。
「說到三十八年,不就是我們十七歲的時候嗎……」
高中二年級,當時和眼前的加藤是同班同學。
「我住在菜園的祖母家。」
南部藩以前有片野菜田,現在是盛岡的市中心,我高中三年都住在那個區域的祖母家。老家在偏遠的鄉下,得坐一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到盛岡,上學很不方便。
「你還記得詳細的町名嗎?」
「老松町。」
「屋主的名字呢?」
「木村……就連名字也有嗎?」
「這不是廢話嘛,沒有的話還叫什麼地圖。」
加藤苦笑,翻找地圖,不到五分鐘就抬起頭來。
「面向馬路——右手邊是鈴木家,再過去是『坪半』,是那家中菜館吧,現在也還在喔。正對面是田村信一先生的家。左手邊是小原家。原來如此,現在的New Carina飯店就蓋在高橋家的舊址上。」
加藤一字一句喚醒鮮明的記憶,我邊聽邊起一身的雞皮疙瘩。有條涓涓細流流經田村家的黑色木板圍牆前,小時候經常把石頭丟進那條小河裡玩。五歲到小學四年級這段期間,因為父親的工作經常需要調動,我被寄養在祖母家,因此高中的記憶總是與小時候的記憶混在一起。高橋家的院子很大,種滿了鬱鬱蒼蒼的樹木。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沒那麼大,但是對小孩子來說,簡直跟叢林沒兩樣。四周圍著高聳白牆,印象中沒見過那家人,屋裡總是靜悄悄,只有大狗偶爾吠個幾聲。我曾經真的以為怪人二十面相就躲在那裡。
我搶過加藤手中的地圖。
我住過的地方就原封不動地凍結保存在翻開的那一頁。
地圖上還有祖母家後面,現在已經收掉的料亭「音羽」。半夜上廁所時,從小窗可以看到音羽的二樓走廊。我曾經看見一對男女沒發現我在偷窺,靠在走廊的扶手接吻,也看過年輕藝妓敞開胸口吹風。藝妓雪白的肌膚歷歷在目。
〈原來店名叫做Lovely Corner啊……〉
這家店位在走出玄關,面向大馬路轉角的地方,同樣給人淫靡的印象。到了這個歲數回頭去看,或許只是一家再尋常不過的酒吧,但是從我二樓的房間窺探那家店的紅色窗戶時,總是直到三更半夜還能聽見女人的笑聲。到了夏天,我會關掉房裡的電燈,豎起耳朵偷聽客人吵架或女人嬌嗔的調笑聲從店裡敞開的窗戶傳來。猛然想起傍晚才去店裡上班的女人白皙的圓臉。那個女人有點古怪,身材微胖,胸前豐滿,總是穿著銀色高跟鞋,每次在轉角遇到放學回家的我,就會對我說:「快點長大吧你。」因為濃妝豔抹,看起來很成熟,其實只跟我差了三、四歲。我記得她叫正子,也記得自己曾經從二樓臉紅心跳地偷看她喝醉了,有個禿頭男子攬著她的肩,拖著她走進屋裡的模樣。
她請我喝過一次茶。當時我站在書店裡看白書,肩膀被她拍了一下,約我去松竹地下室的富士屋冰果室。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毫不猶豫地跟她走,大概是懷著什麼下流的期待吧……。彼此沒有共通的話題,她問我有什麼興趣,我一個人自顧自地聊起怪談電影。當時我正沉迷於赤座美代子在大映主演的《牡丹燈籠》嗎?不對,再早一點,大概是岡田茉莉子飾演的阿岩大受好評的那年夏天。「你們學校都要剃光頭對吧?」她以對電影毫無興趣的表情對我說:「教國語的老師姓吉本對吧?他是我的老相好喔。」總覺得她很髒,只想趕快離開冰果室。不知是否為當時的流行,眼前浮現她用折成四方形的手帕當扇子搧的動作。
「如何?不覺得有點像是回到過去嗎?」
加藤笑著對死盯著地圖不放的我說。
「這比畢業紀念冊或老唱片更能喚起鮮明的回憶。」
「你說的對,我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我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
「我家有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的住宅地圖,邊喝酒邊看的話,不知不覺還會掉下眼淚來喔。我有個朋友叫小翔,家裡是賣醬油的,小學時家裡發生火災,全家人都死了。三十三年的地圖正好畫出那傢伙的家,找到時我哭得好大聲,感覺小翔還活在那張小小的地圖裡。明明在那之前我早就忘了曾經有過這樣的朋友。」
一把年紀的加藤說得眼眶都紅了。
「從此以後,我便開始收集住宅地圖。我現在住的盛岡並不是真正的盛岡,我居住的城市在這本地圖裡,因此不管再古老的街道被拆掉,我都能無動於衷。不久之前我還致力於保存運動,但現在已經完全放下了,徒具其形的事物再怎麼珍惜也毫無意義。」
「……」
「或許是上了年紀,說了一堆廢話。」
加藤喝光剩下的冰咖啡。
「言歸正傳……下禮拜你有什麼打算?」
「還沒決定。話說回來,安太歲是東北才有的習慣吧。」
尤其是岩手和秋田特別流行。男人到了四十二歲,為了安太歲會集合起來,舉行不亞於婚禮的盛大宴會。通常都在二月底舉行,有人提議既然要辦,不如連同學會也一起辦,於是策劃了集體安太歲,我也收到了通知信。如果只有幾個好朋友還好,搞到同學會的規模,不免讓人有點緊張。我也沒有迷信到非安太歲不可的地步,寄出無法出席的答覆後,接到加藤的電話。他也是主辦人之一。
「我是不會勉強你啦,但是如果你願意來,同學會肯定能更添光彩。你已經好幾年沒回盛岡了吧。」
「十五年有了吧。不過倒是因為工作當天來回過幾次。」
「自從新幹線開通以來,盛岡變了很多。雖說我們每天在這裡過活,比較感覺不到變化就是了。你不想見見初戀情人嗎?」
「初戀?」
我的心湖激起一陣漣漪。
「這就是所謂的成名稅嗎?我認識好幾個自稱和你交往過的女人,都是她們自己提起的,是真是假我就不清楚了。」
「叫什麼名字?」
加藤舉了三、四個名字,裡頭還有當時就讀另一所高中繪畫社的谷藤萬里子,我們單獨看過幾次展覽,其他人我幾乎想不起來。
「萬里子現在是小酒館的媽媽桑,很期待能再見到你說。」
加藤竊笑不已。
「你唯獨對自己的異性關係三緘其口……。害我嚇了一大跳,沒想到那麼多女人都說和你交往過。」
「都不是可以稱得上交往過的關係。」
我主動結束這個話題。別的不說,就說我被萬里子狠狠甩掉那件事,現在就算說我們交往過,湧上心頭的也盡是不愉快的回憶,而無半點懷念。她的才華雖不出眾,但人長得特別標緻,是我們這群搞美術的人心目中的女神,我也曾經對畫布描繪出腦海中的她。她或許很適合當小酒館的媽媽桑也說不定。
「這份地圖借我影印。」
我拜託加藤。比起這些現實的回憶,我有更模糊的記憶想確認一下。
「全部嗎?」
「可以的話。」
「那就先借你看,改天再寄還給我就行了。今天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自是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