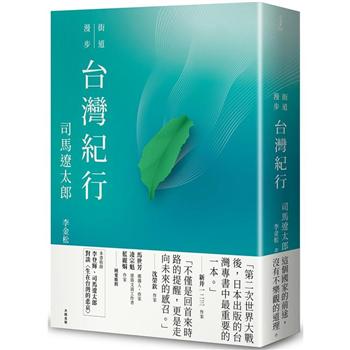流民與榮光
家到底是什麼?
與其說要探討這個話題,倒不如說我是一邊想它的起源論,一邊思考台灣的種種。我認為沒有比台灣這種典型更富魅力的了。
江戶時代的日本,稱這個島為「高砂國」。
各種書本裡,不乏這方面的記述。
據說是「無主」之地。
長崎的作家西川如見,在享保五年(一七二○)刊行的《長崎夜話草》中有如下的記載:
塔伽沙谷位於唐土東南海中,乃一島國,本無主,農民廣種甘蔗,用以製糖。山中住民若年少者,如猿猴然,晨昏持矛獵捕麋鹿,食其肉,持其皮赴市,易酒食,養育妻小並以此為產業。
據說台灣山地的住民具有高貴的心靈,當然不是「像猴子一樣」。總之,台灣古時候是無主之地。
筑前地方福岡藩(黑田家)的儒學家,也是藩醫的貝原益軒(一六三○~一七一四),即對「高砂國」關心過,以下是摘錄自他所寫的《扶桑記勝》。
……位於中華之南。與中華相隔約七十餘日里。
日本的「里」約等於四公里,所以中國大陸與台灣之海相隔七十餘里(二百數十公里)的說法,和實際相差不遠。
……其首都稱台灣城。(中略)通漢字,暖國也。稻作一年二熟。此地往昔原屬無國王之島,未悉始自何時,荷蘭人趁航海前往日本之便,侵佔此島,築城而居,由此地渡海前往日本及各國……
敘述正確得令人折服。
正如益軒所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是在關原之戰(一六○○)後不久的一六○九年,設置洋行於日本的平戶。
這時荷蘭已經以印尼的海港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根據地,他們認為在朝向日本的北航途中,若有個停靠港會較為方便。
這也導致荷蘭於明末的一六二四年,佔領台灣南部的一個港口作為據點。
這期間,西班牙人也活躍起來,有個時期佔據了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不過,也有書上記載,日本人在豐臣秀吉時代以前,就曾以雞籠為根據地。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荷蘭時代則持續了三十幾年。由於台灣深具吸引力,渡海而來的漢人逐漸增加。到了荷蘭時代末期,已有漢人五萬人移入的資料。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東北有非漢族的女真族興起,國號「清」,準備推翻明朝。
另一方面,在海上,有海商—被稱為海獠—的不法勢力。
他們之所以為非法的存在,乃因明朝是海禁的國家。那法令清楚地規定:「寸板不得下海」。明末海盜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一六○四~六一)。
他的兒子,就是被尊稱為「國姓爺」的鄭成功(一六二四~六二)。母親是平戶武士田川氏之女,他才學與武勇兼備,長大之後為了復興明朝,立下勇猛的戰功。在日本也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一劇而為人知。
鄭成功末期,為了據守台灣,率兵二萬五千驅逐了荷蘭人。卻於次年遽逝。
鄭氏佔據台灣是一六六一年。以日本的年號來說是寬文元年,正好是第四代幕府將軍德川家綱的世代。
貝原益軒如此述說:
日本寬文元年之際,國姓爺擁立大明王子,立志反清復明……
有關這個豪爽的人物,不論是在日本、中國大陸或台灣,時至今日仍然受到英雄般的尊崇。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鄭氏佔領台灣僅持續了三代二十二年。
當時,這個島只不過是鄭氏的軍事據點罷了,他並沒有想要在此建立新國家。
很令人遺憾地,鄭家為了要維持大軍,竟把在台灣開拓的漢人農民當作奴隸。
或者,也可以說,鄭氏只是把過去三十八年間,荷蘭人統治這個島時的奴隸農民接收過來而已。
依照史明先生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新泉社出版)的說法。荷蘭統治末期的台灣(台灣海峽側之南部為主)拓墾民數,約達二萬五千戶、十萬人之譜。
不過,鄭家的台灣時代,全軍都成為屯田兵,開闢了農地。
那種農地稱之為「營」。如今台灣地名當中仍保留著這些痕跡,譬如台南縣的平原就有個叫「新營」的小城鎮。在它南邊有「林鳳營」,林鳳營之西也有個叫「下營」的村落,可以說都是鄭氏時代的遺蹟。
鄭家因其後裔歸降清朝而消滅(一六八三)之後,台灣劃入清朝的版圖,但是在另一方面,清朝卻將台灣視為「化外之地」。
清朝沿襲了明朝的海禁,在法律上,台灣是民眾不得渡海前去的島。
已經漂洋過海來到台灣的漢人,也被禁止從大陸攜眷渡台。
就這一點而言,台灣雖被看待為化外之地,但是翻閱《台灣大年表》(台灣經世新報社,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刊)所查得的資料,清朝在一些地方設置了公署,至少西海岸的平原地帶可算是清朝的領土。然而,台灣並非國家的一部分。
日本史上,幕末、幕府之間,有關與日本締結了日本最早的總括性通商條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一八五八年六月)的唐賢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一八○四~七八)的種種,在本叢書的《紐約散步》(第三十九卷)裡已經提過。
哈里斯原本是商人,也曾擔任過市教育局的公職。終生獨身,抱持能對世間有所貢獻的宿願。
四十五歲的時候,拋棄所有,遊遍東洋各地。
他旅居澳門(中國廣東省南部的葡萄牙屬地)期間,對台灣做了調查。其結果知道屬於清國的僅是島的西半部而已,於是寫了「合眾國應該收購台灣的東半部」為主旨的建議書,於一八五四年送呈國防部長,雖未蒙採納,但十九世紀中葉台灣的法律地位由此可明確瞭解。
本篇開頭,我曾談及有關國家起源的問題。
我記得在各派學說中,有一種論調認為,所謂的國家,就是偷偷摸摸地溜進原本已有住民的地方,然後撒網把它網住。
而台灣的情形,既為荷蘭進佔過,又有鄭氏轟轟烈烈地駐紮過。
在那之後,台灣的漢人,憑一把鋤頭耕而耘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結構已見成熟,闢出美麗的田園風貌。
如果哈里斯的意見被採用的話,台灣東部的原住民就會像其後不久夏威夷諸島的玻里尼西亞人一樣,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收編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民了。
這些原住民本來是隨著黑潮漂流過來的。這種將他們漂送過來的黑潮,發自菲律賓東方的海面,有時以流速五節之速度,北上台灣、日本。而菲律賓就像鄰島一樣。
一八六八年亞洲發生一場巨變。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搖身一變成為近代國家。
因為周邊的中國、朝鮮仍然維持所謂儒家傳統的超古代體制,所以這對它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至於近代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國家,乃是將國家的領土,從亞洲式「版圖」概念脫離開來,改以西洋式的領土定義,予以明確定位。但是有關國際法等的法學知識,明治初期政權,則是借重於聘雇的外國人。
比如說琉球,是兩屬(清的版圖與日本的版圖)之地。
碰巧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琉球國的六十六名島民漂流到台灣的東南海岸,其中五十四人被原住民殺了。據說原住民以為是西海岸的漢人。
日本採取了十分乾淨俐落的措施,首先在翌年的明治五年九月,將琉球王國收編為琉球藩,作為國內的一藩。清朝悶不吭聲的,對這件事竟沒提出抗議。
被殺的琉球島民變成了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日本派專使赴北京,向清朝抗議。
清朝這邊因而以口頭答辯說:「台灣之蕃民乃化外之民,大清政教未及於彼」。
此後日本一貫以此口實為由,解釋台灣東半部係無主之地。
之後,清朝改變了態度,於是,兩國之間爭議不休。
這個時候,曾是明治維新主要勢力的舊薩摩藩(鹿兒島縣),因對新政府不滿,維持著半獨立狀態,與其他府縣裡的不滿士族同仇敵愾,衝突之勢一觸即發。
日本政府完全基於內政的考慮,為了排除充滿於國內的不穩氣氛,出兵台灣東部,時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清朝卻仍若無其事。
不久,清朝竟然還支付了這些討伐軍費給日本。清朝並以此作為台灣東部是本國領土的證據。
清朝更進一步為了明確表示台灣是本國領土,於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將台灣升格為台灣省,也就是說成為「國內」。這樣的「國內」持續了十年。
明治二十七、八年(一八九四~五),爆發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台灣省成了日本領土。
日本直到太平洋戰爭戰敗,前後共統治台灣五十年。我是日本人或許難免偏袒日本,可是,當時沒有多餘財力的日本—儘管我不認同殖民地的存在—曾經盡全力去經營,這點當可予以肯定。台灣和日本國內同樣設立帝國大學、設置教育機構、興築水利工程,也創設鐵路與郵政制度。
戰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領土。
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而台灣島至今仍舊是「台灣省」的老樣子。
台灣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中,人民勤奮工作,外匯存底與日本並駕齊驅,號稱世界之最,發展成高水準的經濟社會。
像台灣這樣,能從「流民之國」發展到今日社會這樣的例子,除了美國之外,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吧!
葉盛吉傳
葉盛吉,已故。一九二三年生於台灣,當了二十二年的日本人。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A,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一九五○年被處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今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器、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並沒有自己養乳牛、擠牛乳。(有關牧歌式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此處暫且不提。)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貨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己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業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含蓋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病狀。
這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的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楊威理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B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新營」,前文裡已提到,是十七世紀鄭成功時代由屯田兵所開墾的。
這一趟台灣之旅,我也到過這個市鎮。
在候車室內,靠近天花板的牆壁上,寫著「新營站空襲時期旅客疏散標示圖」的字樣。不由令人想起現今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也就是說,他們擔心中國大陸—我相信不至於—說不定會攻打過來。
日治時代的台灣,因製糖而繁榮。
在新營,就有個「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大糖廠。葉氏的養父葉聰先生是該廠職員,「在人事課服務到六十五歲,還升到課長」,書中是這麼說的。
葉君在糖廠宿舍長大。在他的手記裡,曾這樣寫道:「……每當嗅到淺綠色榻榻米的芳香時,過年就快到了。」這種生活氣氛與我們內地人並沒有兩樣。
就連他在新營公學校時代,所愛讀的《幼年俱樂部》和《少年俱樂部》等雜誌,也和我們一樣。
他進台南一中之後,就以考取內地的舊制高等學校為目標。他之所以能夠有那樣的志向,無疑是拜養父的豐厚薪俸之賜。
重考了兩年,他終於考上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理科乙類。C
在他未出版的自傳中,曾談到:「我是來到日本之後,才產生強烈的民族意識的。」
自修期間,他在高圓寺過著寄宿生活。當時,受到一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向他灌輸民族意識。
在葉先生的自述或手記裡,就常以「雙重生活」來表達他既是漢族又是日本國民的矛盾。
雙重生活是痛苦的……我必須忍受苦楚,使雙方的生活並行。為了這個,忍耐是最要緊的。
大體而言,葉君內心的矛盾,正是戰前整個日本的矛盾。
戰前的日本,跟美利堅合眾國一樣,是個多民族國家。
舉例而言,包括庫頁島的吉利亞克(俄語Gilyak)族,北海道或千島的愛奴(Ainu)人,及第一次大戰後原屬德國領地而受委託統治的南洋廳管轄下的柯納卡(Kanaka)人,查莫洛(Chamorro)人等,再加上日系、朝鮮系、台灣原住民、漢族等多種民族。
只是,戰前的日本,將這些族群視為日裔的從屬,而這就犯了國家政策上的錯誤。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相信同化的葉姓少年,登記為日本式的姓名。那是依據前一年公布的姓名應儘量日本化的法令。據說全台灣更改姓名的人數,推計有十餘萬人。葉君從此成了葉山達雄。
那時,二高的德語教授當中,有一位教授非常熱衷地鼓吹納粹的反猶太論,許多學生對此心存懷疑,而葉君卻傾向這種論調。
那位教授說:整個世界,操縱在猶太人的陰謀裡頭。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的革命是如此,中日戰爭亦因此陰謀而起,俄國的革命也是猶太人策謀的結果,甚至連美國的建國都不例外。
他還說:希特勒驅逐了猶太人,因此比耶穌基督更偉大。
只須將各種事物予以符號化,把邏輯如同模擬數學般地運用,那麼任何邪說異論均可成立。那位教授的論調便是其中之一。
二高那位教授的思想,在那種猶太陰謀論裡加上平田篤胤的神道論,形成極端的右翼思想。那教授稱之為「護國學」。
葉君之所以有一段時期醉心於那種論調,我想是源自前述的「雙重生活」之苦悶,使他想藉此麻痺自己的潛意識作用吧。
在這之前,曾有所謂「學徒出陣」(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文科系的學生,踏出校門出征去了。
葉君所敬愛的,高他一年級的角田秀雄也是其中一位。
在他手記裡記述說:「角田秀雄兄告訴我:要經常保持微笑,好好幹!」
在那個時期,我也從大阪的學校入伍去了。
於戰爭中存活下來的角田氏,之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出版局服務,我在寫這個《街道漫步》連載中的一段時期,他還曾擔任過圖書編輯室長。讀到這本傳記裡的這個部分,我越覺得對葉君有一份親切感。
日美戰爭在第四年陷入不可收拾之局面。在那之前,已打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戰爭,也陷入泥沼。
在大陸的日軍,一方面要和中國政權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國府軍」(國民黨政府軍)作戰,同時也要跟中國共產黨軍戰鬥。
說來,這真是愚蠢的事!依蔣介石的想法,可能希望早日跟日軍談和,而全力去對付共軍吧。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獲有美英—甚至包括蘇聯—的支援,卻因到處肆行劫掠,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相對的,共軍光靠紀律嚴明這一點,便獲得民眾之擁護。
日本投降了。
聯合國太平洋區統帥麥克阿瑟,命令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日軍,向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投降。
當時,蔣介石在重慶。
他派遣陳儀(一八八二~一九五○)率先遣部隊來台灣。
陳儀任福建省主席的時代,曾把整個省搞成貪官汙吏的世界,是惡名昭彰的亞洲型政客。他在任的兩年期間,將台灣私有化,盡其所能地榨取,中飽私囊。
陳儀部下的一兵一卒宛如小陳儀,與中國過去的王朝軍一樣,只知私利私慾,還以「征服軍」的姿態屠殺了無數的台灣人。
後來,陳儀因通敵的罪嫌,於一九五○年遭槍決。然而,在陳儀之後,台灣依舊處在被征服的狀態。
日本戰敗之際,葉君就讀於東大醫學院,其後回到陳儀時代的台灣。
陳儀率領軍隊登陸台灣時,台灣人民以為重投祖國懷抱,無不歡欣鼓舞。
然而,現實可不是那回事。
「日本時代,憲兵雖然佩帶手槍,可是五十年間,從來沒有開過槍,做官的也沒有過貪汙瀆職的」,這一類懷念日本時代的聲音時有所聞。
葉君也因為自己由一個「雙重生活者」,變成一個國民,而雀躍不已。然而,他幻滅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社會結構仍然繼續著。
比起現實的狀況,葉君好像有偏愛德意志式真空內邏輯的傾向。
他在真空中思索,認為只要加入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從「雙重生活者」轉變成一個「真正的自我」。因此,他藉由入黨,在真空內化解了他的苦惱。
一九四九年,他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很快就結婚了。
新娘是台南一中時代同班同學的妹妹邱淑姿小姐,岳父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長老。
不久,失去大陸政權的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
葉先生因黨籍曝光而被逮捕。
他在獄中得知兒子誕生。
正當他覺悟到必死無疑,便從監獄裡寫信給岳父說:「我要將我的一切奉獻給耶穌,感謝神給我的愛。」他臨死前才成了基督徒。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和很多台灣人一同被草草地殺害。
作者楊威理先生本身,也是過了離奇半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不過在此不擬多提。
這位仁兄,為了寫葉先生傳記,曾經四處尋訪葉先生的遺族。一九九○年,知道了他的遺孤葉光毅先生還健在,是成功大學的教授。
據云楊威理先生在電話打通的當兒,這個出生後就未曾見過親父一面的「嬰兒」—葉光毅先生,竟然在電話聽筒的那端,朗聲高唱其亡父的母校—二高的校歌。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情景!
似乎唯有悲情,才能夠超越時間,將人間的傳承傳遞下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