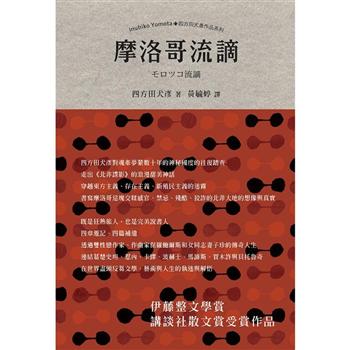終章
我在畫冊上細細玩味馬諦斯的兩張油畫。
第一張油畫,是他在一九一二年春、四十三歲時第一次到丹吉爾,從法蘭西別墅大飯店(Grand Hotel Villa de France)住房窗口眺望的風景。第二張油畫是畫家回到巴黎後,不到一年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丹吉爾,畫下了同一個窗口的景色。
題為「窗外的景色」(Window at Tangier)的第一張油畫,以一扇打開的玻璃窗窗框作為畫框,樹林與全白的建築、坡道上走著的兩頭驢子和白衣的摩洛哥人,在濃烈的藍色和姿態的垂直性基調中描繪而成。窗前有兩只小花瓶,右邊那只的暖色花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油畫的正中央是英國教會,背後是舊城,右方是丹吉爾港最前方的堤防和塔樓;左方依約可見的城堡則是當時的蘇丹宮殿(Dar al Makhzen)。
第二張畫作「丹吉爾的窗外」(Open window at Tangier)則有了顯著的變化。憂鬱深沉的色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柔和的黃色為中心的朦朧景致──不,也許更準確描述的話,莫不如說是個別的建築和樹林、天上的浮雲都已經無法識別、還元成了純粹的色彩,只彷彿一道煙沿著水平軸飄過。英國教會消失了,只留下遠方延展成一片的蘇丹宮殿和舊城區。不僅如此,第一張油畫裡猶認真勾勒出的窗框和蕾絲窗簾也消失不見,只有近前方的幾只花瓶提示出窗子的存在,然而插在瓶中的花塗成了藍色,以某種與窗外的色彩相連的形態登場。如果不作說明,恐怕沒人相信這兩張畫是在同一處空間、同一個視角下繪出的風景。雖然不太符合法文的規則,但我忍不住想把這幅畫的題名「Fenêtre ouverte à Tanger」譯為「開向丹吉爾的窗」。
馬諦斯總令我驚嘆。這位天才畫家嚮往著能像印象派那般把畫布搬到戶外去作畫,卻總為了天候而懊惱,因為他對大自然中實際的色彩變化敏感萬分。當他結束俄羅斯之旅疲憊地回到巴黎,立刻為了追尋恒常的陽光而到了丹吉爾。此時他心中想的應該是八十年前造訪過此地的德拉克洛瓦。到丹吉爾去接受異國情調的洗禮,這在當時的法國畫家當中蔚為風潮,馬諦斯投宿的旅館裡也有多位畫家住在這裡(他們如今都已經沉到遺忘的河裡),卻無人如馬諦斯一般在丹吉爾成就了可說是視線之危機的體驗。相差短短幾個月內所畫的兩張油畫之間橫亙的決定性差異,如實地透露出他已能不受限於事物的形態、全心投入於色彩當中的境地。這是名副其實「開放」的光景、「開放」的繪畫──我不禁想要這樣表達。
同時,我不可能不去思考催生出這件作品的時代。馬諦斯從眼前的風景當中抹除了能夠讓人感受到歐洲近代或殖民地的一切要素,驅逐了一切形態當中的意義。製作這兩張油畫的時間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三年,正值摩洛哥成為法國保護地、利歐堤將軍執掌全權的時刻,想必不是偶然。利歐堤不允許歐洲的近代時間隨意侵入摩洛哥的舊城,試圖將舊城保留、成為它永遠的模樣。
城堡的宮殿如今成了主要展出考古出土品的博物館,與英國教會相隣的建築成了摩洛哥現代美術館,我曾經在那裡參觀阿罕梅得・雅沽比晚年的作品。教會附屬的墓園埋葬著在此地過世的英國人,這裡無人聞問,有次我一時興起走進了這裡,只見雜草叢生,莊嚴的墓碑凋敝殘破,已經沒有一處能夠令人懷想起英國的地方,只有馬諦斯第一張油畫裡驢子緩步走著的坡道還留著「盎格魯街」的名字。這裡很早就設立了巴士轉運站,帶來了熱絡的人潮。我在市場為哈蒂佳買了調理古斯古斯的蒸鍋和特別的奶油。
一九五六年獨立的摩洛哥接管了丹吉爾,列強的共同統治結束後不久,這個城市便急遽地阿拉伯化;與此同時,與利歐堤畢生理念背道而馳地,丹吉爾徹底接受了歐洲的近代化,整個城市朝著混亂的模仿加速前進。因為受到丹吉爾世界一家般的魅力吸引而來的許多西方人離開了這裡,只有喪妻的鮑爾斯留了下來。正因為執意置身事外、從俯瞰城市的尖塔最高處達觀看著一切,才有可能作到吧。事態何以致此,不清楚,到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了──鮑爾斯這麼喃喃自語,對他來說,在眼前的摩洛哥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會令他心底生起半點波瀾。借藤原定家的話來說,就是「非我事」。我有時不禁覺得,就算鮑爾斯不到摩洛哥,他也能從想像中汲取他的摩洛哥編成故事。
接著,惹內來到已經變得混亂猥瑣的丹吉爾。他既無心正視摩洛哥的現狀,也全然無意想要彰顯歐洲的文明,因為他很早以前就已經是歐洲世界的局外人了。如果鮑爾斯是刻意面向世界的外部,當一個享受隱士般生活的作家,那麼惹內相對地就是個不管是不是出於自願,從生下來就被判處了流放之刑、排除在世界之外的人。他對摩洛哥過往的歷史經緯漠不關係,只是被友愛和喜捨的想法牽引著渡過了人生最後的一段歲月。鮑爾斯雖然說要遁世,卻與造訪丹吉爾的藝術家們維持著浮華的社交;至於惹內,除了巴勒斯坦的「同志們」以外,沒有人追踪得到他,他在摩洛哥也不想被人找到。就在他以零星的阿拉伯語和身邊圍繞的孩子們聊天當中,惹內得到了世俗看來平庸至極的幸福,即便如此,他的生涯整體而言極具歷史性,旁人無法輕易複製。
我為這冊散文集的書題給了「流謫」一詞。流謫的人自然不是我,而是鮑爾斯、是惹內,或是布萊恩・瓊斯,換個角度看的話,也是平岡千之與利歐堤將軍,或者是石川三四郎。他們都在自身所屬的都市或國家當中,有的看破了人生,有的嘗盡逃脫不了的疲憊,然後在某個偶然的機會下來到摩洛哥,在這裡等候著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一個瞬間。另一方面,這裡有著等候這些流謫之人的到來,以款待或敵意迎接他們的摩洛哥人,以鮑爾斯而言的話是雅沽比、木拉貝和肖克利;以我短暫的旅程而言,就是拉希德一家、是安德烈亞斯教授。
在種情形下,區別款待和敵待、善意或惡意自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無論是軍事上的侵略或天真的觀光,當一個人造訪別人的社會並且留在當地,這個行為本身在當地人的眼裡看來往往就是無來由的暴力,與之對應的反作用所產生的當地人的回應,不應當以造訪者所揮舞的單方面的道德標準來論斷。我在摩洛哥所到之處都對那些自稱導遊的人的糾纏而困擾不已,然而或許有機會的話,他們的行為也可能轉而促成我在菲斯的家庭所受到的招待。就以我在丹吉爾遇到的那位自稱是教授的謎樣人物為例,已經饒富深意地證明了接納一位異鄉人、或者被接納的行為必然會孕含的雙義性。
因為與鮑爾斯這位流謫之人的相遇,我踏上了追尋鮑爾斯足跡的旅程。半路尋找失踪的人因而展開另一段新的旅程,聽起來簡直就是安東尼奧尼式的主題。我在追尋的路途上知道了其他不少流謫之人的存在,最後便轉換了探求的視角,試著從流謫之人的接納者方的角度談論。我刻意想要倣效的是如《一千零一夜》的敍述者,在敍述當中加入另一段敍述,讓好幾段敍述相互呼應,體現追尋的多元樣態。而我對摩洛哥的關注雖然因為鮑爾斯所啓發,經過十數年之後,也已緩慢但確實地逐步轉向了惹內。
這部長篇的散文集是目前為止第四部我為某片土地所寫的書。這二十年來,我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到處移動,也持續為所到之地撰寫因地而設的故事。首爾、紐約、月島,還有波隆那。在為第一個造訪的首爾所寫的書裡,貫穿全書的是一種對峙的、勇敢注視不逃躲的基本姿態;第二本是為紐約寫的書,構成全書基調的想法是這個世界已經不可能存在所謂的「中心」,只有移動的人群;第三部的月島論,我抹去關於這片土地的刻板印象和神話,以這片成形不過百年的市鎮為跳板,有心想重新檢討日本的現代化之路。將來可能會寫的關於義大利的書,我想主題會是事物的蒐集與時間的經過和懷舊。
摩洛哥在我一系列的書寫當中占有極為異質、特殊的地位。它是少年時透過電影和音樂給我無限憧憬的對象,即便當時從未到過摩洛哥,不管我在地上的任何地方都在我心底的一個角落深信不疑。本書第三章提到的十三世紀哲學家伊本・阿拉比曾經在《旅行的效用解析》寫道:「你是永遠的旅人,不在任何地方落地生根」。我曾住過紐約、波隆那、巴黎和東京,不管我住在哪個城市,當心念一動,我就搭了飛機轉乘到丹吉爾。這部散文集是十多年來這些旅程累積下的成果。
書的終點好似旅行的終點──這句話出自我的文學起點《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強納森.史威夫特。這部以現在式書寫的文本,到了這裡急遽失速,所有的一切都在過去式中娓娓道來。我最近收到了哈蒂佳的來信,信上寫著她近來在貝克特《等待果陀》的舞台劇裡演出了少年小丑的角色。關於鮑爾斯,有位曾經針對他的妻子珍寫過一本詳盡傳記的女性學者,出版了富於同情而優美的鮑爾斯傳。安德烈亞斯教授還是渺無消息,我曾經將照片寄到他給的住址,卻沒有回音。下一次,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回到摩洛哥。
我在畫冊上細細玩味馬諦斯的兩張油畫。
第一張油畫,是他在一九一二年春、四十三歲時第一次到丹吉爾,從法蘭西別墅大飯店(Grand Hotel Villa de France)住房窗口眺望的風景。第二張油畫是畫家回到巴黎後,不到一年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丹吉爾,畫下了同一個窗口的景色。
題為「窗外的景色」(Window at Tangier)的第一張油畫,以一扇打開的玻璃窗窗框作為畫框,樹林與全白的建築、坡道上走著的兩頭驢子和白衣的摩洛哥人,在濃烈的藍色和姿態的垂直性基調中描繪而成。窗前有兩只小花瓶,右邊那只的暖色花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油畫的正中央是英國教會,背後是舊城,右方是丹吉爾港最前方的堤防和塔樓;左方依約可見的城堡則是當時的蘇丹宮殿(Dar al Makhzen)。
第二張畫作「丹吉爾的窗外」(Open window at Tangier)則有了顯著的變化。憂鬱深沉的色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柔和的黃色為中心的朦朧景致──不,也許更準確描述的話,莫不如說是個別的建築和樹林、天上的浮雲都已經無法識別、還元成了純粹的色彩,只彷彿一道煙沿著水平軸飄過。英國教會消失了,只留下遠方延展成一片的蘇丹宮殿和舊城區。不僅如此,第一張油畫裡猶認真勾勒出的窗框和蕾絲窗簾也消失不見,只有近前方的幾只花瓶提示出窗子的存在,然而插在瓶中的花塗成了藍色,以某種與窗外的色彩相連的形態登場。如果不作說明,恐怕沒人相信這兩張畫是在同一處空間、同一個視角下繪出的風景。雖然不太符合法文的規則,但我忍不住想把這幅畫的題名「Fenêtre ouverte à Tanger」譯為「開向丹吉爾的窗」。
馬諦斯總令我驚嘆。這位天才畫家嚮往著能像印象派那般把畫布搬到戶外去作畫,卻總為了天候而懊惱,因為他對大自然中實際的色彩變化敏感萬分。當他結束俄羅斯之旅疲憊地回到巴黎,立刻為了追尋恒常的陽光而到了丹吉爾。此時他心中想的應該是八十年前造訪過此地的德拉克洛瓦。到丹吉爾去接受異國情調的洗禮,這在當時的法國畫家當中蔚為風潮,馬諦斯投宿的旅館裡也有多位畫家住在這裡(他們如今都已經沉到遺忘的河裡),卻無人如馬諦斯一般在丹吉爾成就了可說是視線之危機的體驗。相差短短幾個月內所畫的兩張油畫之間橫亙的決定性差異,如實地透露出他已能不受限於事物的形態、全心投入於色彩當中的境地。這是名副其實「開放」的光景、「開放」的繪畫──我不禁想要這樣表達。
同時,我不可能不去思考催生出這件作品的時代。馬諦斯從眼前的風景當中抹除了能夠讓人感受到歐洲近代或殖民地的一切要素,驅逐了一切形態當中的意義。製作這兩張油畫的時間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三年,正值摩洛哥成為法國保護地、利歐堤將軍執掌全權的時刻,想必不是偶然。利歐堤不允許歐洲的近代時間隨意侵入摩洛哥的舊城,試圖將舊城保留、成為它永遠的模樣。
城堡的宮殿如今成了主要展出考古出土品的博物館,與英國教會相隣的建築成了摩洛哥現代美術館,我曾經在那裡參觀阿罕梅得・雅沽比晚年的作品。教會附屬的墓園埋葬著在此地過世的英國人,這裡無人聞問,有次我一時興起走進了這裡,只見雜草叢生,莊嚴的墓碑凋敝殘破,已經沒有一處能夠令人懷想起英國的地方,只有馬諦斯第一張油畫裡驢子緩步走著的坡道還留著「盎格魯街」的名字。這裡很早就設立了巴士轉運站,帶來了熱絡的人潮。我在市場為哈蒂佳買了調理古斯古斯的蒸鍋和特別的奶油。
一九五六年獨立的摩洛哥接管了丹吉爾,列強的共同統治結束後不久,這個城市便急遽地阿拉伯化;與此同時,與利歐堤畢生理念背道而馳地,丹吉爾徹底接受了歐洲的近代化,整個城市朝著混亂的模仿加速前進。因為受到丹吉爾世界一家般的魅力吸引而來的許多西方人離開了這裡,只有喪妻的鮑爾斯留了下來。正因為執意置身事外、從俯瞰城市的尖塔最高處達觀看著一切,才有可能作到吧。事態何以致此,不清楚,到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了──鮑爾斯這麼喃喃自語,對他來說,在眼前的摩洛哥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會令他心底生起半點波瀾。借藤原定家的話來說,就是「非我事」。我有時不禁覺得,就算鮑爾斯不到摩洛哥,他也能從想像中汲取他的摩洛哥編成故事。
接著,惹內來到已經變得混亂猥瑣的丹吉爾。他既無心正視摩洛哥的現狀,也全然無意想要彰顯歐洲的文明,因為他很早以前就已經是歐洲世界的局外人了。如果鮑爾斯是刻意面向世界的外部,當一個享受隱士般生活的作家,那麼惹內相對地就是個不管是不是出於自願,從生下來就被判處了流放之刑、排除在世界之外的人。他對摩洛哥過往的歷史經緯漠不關係,只是被友愛和喜捨的想法牽引著渡過了人生最後的一段歲月。鮑爾斯雖然說要遁世,卻與造訪丹吉爾的藝術家們維持著浮華的社交;至於惹內,除了巴勒斯坦的「同志們」以外,沒有人追踪得到他,他在摩洛哥也不想被人找到。就在他以零星的阿拉伯語和身邊圍繞的孩子們聊天當中,惹內得到了世俗看來平庸至極的幸福,即便如此,他的生涯整體而言極具歷史性,旁人無法輕易複製。
我為這冊散文集的書題給了「流謫」一詞。流謫的人自然不是我,而是鮑爾斯、是惹內,或是布萊恩・瓊斯,換個角度看的話,也是平岡千之與利歐堤將軍,或者是石川三四郎。他們都在自身所屬的都市或國家當中,有的看破了人生,有的嘗盡逃脫不了的疲憊,然後在某個偶然的機會下來到摩洛哥,在這裡等候著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一個瞬間。另一方面,這裡有著等候這些流謫之人的到來,以款待或敵意迎接他們的摩洛哥人,以鮑爾斯而言的話是雅沽比、木拉貝和肖克利;以我短暫的旅程而言,就是拉希德一家、是安德烈亞斯教授。
在種情形下,區別款待和敵待、善意或惡意自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無論是軍事上的侵略或天真的觀光,當一個人造訪別人的社會並且留在當地,這個行為本身在當地人的眼裡看來往往就是無來由的暴力,與之對應的反作用所產生的當地人的回應,不應當以造訪者所揮舞的單方面的道德標準來論斷。我在摩洛哥所到之處都對那些自稱導遊的人的糾纏而困擾不已,然而或許有機會的話,他們的行為也可能轉而促成我在菲斯的家庭所受到的招待。就以我在丹吉爾遇到的那位自稱是教授的謎樣人物為例,已經饒富深意地證明了接納一位異鄉人、或者被接納的行為必然會孕含的雙義性。
因為與鮑爾斯這位流謫之人的相遇,我踏上了追尋鮑爾斯足跡的旅程。半路尋找失踪的人因而展開另一段新的旅程,聽起來簡直就是安東尼奧尼式的主題。我在追尋的路途上知道了其他不少流謫之人的存在,最後便轉換了探求的視角,試著從流謫之人的接納者方的角度談論。我刻意想要倣效的是如《一千零一夜》的敍述者,在敍述當中加入另一段敍述,讓好幾段敍述相互呼應,體現追尋的多元樣態。而我對摩洛哥的關注雖然因為鮑爾斯所啓發,經過十數年之後,也已緩慢但確實地逐步轉向了惹內。
這部長篇的散文集是目前為止第四部我為某片土地所寫的書。這二十年來,我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到處移動,也持續為所到之地撰寫因地而設的故事。首爾、紐約、月島,還有波隆那。在為第一個造訪的首爾所寫的書裡,貫穿全書的是一種對峙的、勇敢注視不逃躲的基本姿態;第二本是為紐約寫的書,構成全書基調的想法是這個世界已經不可能存在所謂的「中心」,只有移動的人群;第三部的月島論,我抹去關於這片土地的刻板印象和神話,以這片成形不過百年的市鎮為跳板,有心想重新檢討日本的現代化之路。將來可能會寫的關於義大利的書,我想主題會是事物的蒐集與時間的經過和懷舊。
摩洛哥在我一系列的書寫當中占有極為異質、特殊的地位。它是少年時透過電影和音樂給我無限憧憬的對象,即便當時從未到過摩洛哥,不管我在地上的任何地方都在我心底的一個角落深信不疑。本書第三章提到的十三世紀哲學家伊本・阿拉比曾經在《旅行的效用解析》寫道:「你是永遠的旅人,不在任何地方落地生根」。我曾住過紐約、波隆那、巴黎和東京,不管我住在哪個城市,當心念一動,我就搭了飛機轉乘到丹吉爾。這部散文集是十多年來這些旅程累積下的成果。
書的終點好似旅行的終點──這句話出自我的文學起點《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強納森.史威夫特。這部以現在式書寫的文本,到了這裡急遽失速,所有的一切都在過去式中娓娓道來。我最近收到了哈蒂佳的來信,信上寫著她近來在貝克特《等待果陀》的舞台劇裡演出了少年小丑的角色。關於鮑爾斯,有位曾經針對他的妻子珍寫過一本詳盡傳記的女性學者,出版了富於同情而優美的鮑爾斯傳。安德烈亞斯教授還是渺無消息,我曾經將照片寄到他給的住址,卻沒有回音。下一次,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回到摩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