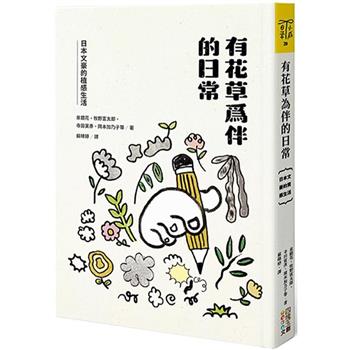〈病房裡的花〉 / 寺田寅彥
發病前的四、五天,我去三越時順道買了一個秋海棠小盆栽。我把它放在書房的桌子上,擺在書架旁,每晚在燈光下觀賞它,想著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還要用它寫生。但這個計畫來不及實施,我就住院了。
入院那天,妻子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畫具,連秋海棠小盆栽也一起帶來了,放在病床旁邊的大理石藥架上。病房被灰色牆壁和純白窗簾團團包圍,只有暗紅色漆櫃和在床頭發亮的黃銅金屬配件為病房增添了一點色彩。然而,這個陰鬱、寒冷的病房卻突然間熱鬧、溫暖了起來。躺在床上,望著彷彿以寶石打造的深紅色花苞,以及天鵝絨般光澤亮麗的翠綠色葉片,雙雙映襯在灰色牆上,令我目眩神迷。
我常常在想,為何再精雕細琢的人造花,與自然花相比仍顯得粗糙不堪?我曾在美國的一間博物館看過由著名工藝家創作的玻璃花,可是與自然花相比,它不僅乏味,甚至令人有些厭惡。這種差異究竟源於何處呢?如果把有關色彩、型態的一切抽象概念和語言當作比較的標準,那麼人造花和真實花朵在外觀上的區別就會非常困難且不得要領。可能有人會說:「一邊是死的,另一邊是有生命的。」但這不過是把同樣的問題抽換詞面而已。照這樣講,豈不是得透過顯微鏡檢查,才能明確地區分兩邊的不同嗎?看看其中一邊是不是不規則且單純的乾燥纖維集合體,或是不規則且凹凹凸凸的非晶體,再看看另一邊是不是複雜但有規律的有機細胞組織?若不是美麗的事物和相似卻不美的事物之間,擁有人類感官所探測不到的細微差異,那就是人類潛意識中隱藏的自我,決定了這件事物美或不美吧。我思考著這個問題,凝視小盆栽裡的秋海棠,覺得彷彿連自己孱弱的肉眼,都看到了每顆花瓣細胞中散發的生命光芒。
住院第二天,A兄帶了一束油菜花來探望我,這裡沒有合適的花瓶,只好暫時擺在金屬臉盆裡。或許是溫室花的緣故,這束油菜花的香氣並不濃郁,很難讓人聯想到總是與油菜花田一同出現的雲雀歌聲。不久後,妻子從家裡帶了一個花瓶來,將油菜花插進去,擺在病房角落的洗手台上。同一天,我的侄子N也帶了一盆西洋蘭花來探望我。磚紅色的小盆栽裡有著茂密的水苔,幾片像青竹匙一樣厚重、寬大的葉子左右對稱伸展,中間佇立著一株微微垂首的蘭花。這株蘭花綠色佔了大部分,只有花冠帶有鮮豔的紫色刷紋,就世俗的審美觀來看並不漂亮,卻散發著極為高雅的沉靜之美。把它和嬌俏可愛、宛如童話故事公主的秋海棠放在一起時,它就像是一位年輕俊美卻憂鬱寡言的貴公子。花冠下半部垂著袋狀花瓣,上面蓋著另一片花瓣,我原本以為這個像蓋子的花瓣遲早會翹起來,讓袋子敞開,但袋子始終沒有打開。
不久後,T先生夫婦又帶了一個更大的秋海棠盆栽來。跟之前從家裡帶來的那一盆比起來,這個盆栽大了好幾倍。大秋海棠一來,小秋海棠頓時相形見拙。大概是家裡那盆小秋海棠的花色也有點黯淡了,一比之下,大秋海棠才真正是豔麗無雙,美得教人目眩神迷。舊的小秋海棠被挪到病房角落的洗手台上,新的大秋海棠則放在床邊,好讓我一遍又一遍欣賞它。奇妙的是,那株清幽的蘭花一點也不比大秋海棠遜色,反而顯得更獨樹一格。我捨不得扔掉舊的小秋海棠,仍時不時轉頭看看那洗手台上花葉都日漸褪色的可憐盆栽。孤伶伶的花瓶裡的油菜花,也總是勾起我淡淡的哀愁。
後來換I兄送了仙客來和聖誕紅給我。我曾在花店見過聖誕紅,但當時並不知道它的名字,這次看了盆栽上貼的標籤才知曉。我將它擺在藥架上,仔細觀賞,發現那火焰似的朱紅色樹冠很像雁來紅,濃烈的色澤一直令人聯想到熱帶。比起花,我覺得那更像是鳥類羽毛的顏色。端詳頂端,會發現那裡長著一叢黃黃的小花,這些小花非常低調,低調到幾乎看不到。大自然裡的植物為何總會有這麼不起眼的生殖器,反倒讓葉子等呼吸器官變得如此顯眼呢?或許植物學家和進化論者可以講出一番學說,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我想像著植物叢生的熱帶雨林,腦海中浮現了前陣子去新加坡旅遊的回憶。馬車穿梭在椰林裡,沿著紅土大道奔馳,當時無以名狀的心情如今清晰地浮現在心頭,只不過細節像夢一樣模糊、斑斕,宛如印在綠色及褐色布料上的花紋。即使如此,對於躺在這張冰冷病床上的我而言,想像著熾烈的陽光和充滿生命力的南國天地,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安慰。
仙客來似乎有些發育不良,花朵看起來沒什麼精神,葉子也有點捲曲,邊緣還變成了褐色。這盆花讓我莫名想起了在柏林的日子,那時我想送花給住在阿卡琴街(Akazien)的語言學老師慶生,便跑到使徒保羅教堂(Apostel-Paulus-Kirche)前的一間小花店挑選,最後買了仙客來盆栽。店員幫我用看似日本進口的粉紅皺紋紙包裝好後,我便立刻送去附近的老師家中。當時老師告訴我這種花叫做阿爾卑斯菫,大概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比仙客來更適合它。我不知道那位女老師現在怎麼樣了,她以前只收日本留學生當門徒,但隨著二戰爆發,留學生全都回國了,柏林市民對日本人的反感也日漸加劇,不知她是否因此遭遇過麻煩?她之後又是如何維生的呢?至今我仍三不五時會想起她。老師剛結婚沒多久,從醫的丈夫就去世了,從此和退役軍人的父親以及丈夫留下的十四歲女兒希德嘉爾特相依為命。我不太清楚老師家的狀況,但她似乎與父親處得並不好。某天我們幾個學生帶著希德嘉爾特一起去路易莎劇院(Luisen-Theater)看童話劇《白雪公主》,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小朋友,令我們這些外國大朋友有些不自在。飾演皇后的演員是一名非常胖的女人,她用美妙的歌喉唱出了「魔鏡啊魔鏡」。兩三天後,我得知當天晚上老師因為腹部嚴重痙攣而飽受折騰,還留下了明顯的黑眼圈。不知為何,我總覺老師會大病一場,責任都在我們身上,從此我再也沒去看過童話劇場。
五歲的雪子跟著姊姊到醫院探望我。剛開始她還會乖乖地看護士的臉色,保持安靜,後來愈來愈調皮,甚至爬到我的床上來。她望著我床邊的花盆,發現了藏在葉子底下的木牌,將片假名寫的花名一字一字大聲朗讀了出來。聽到她怪腔怪調的,大家都笑了。原來她最近學會了片假名,只要看到片假名就會忍不住念出來。從那之後,她每次來都會坐在床邊,不停地念那些花名。這讓我重新思考了「文字」的奧妙,以及人類知識的未來。
我一直很想知道聖誕紅的英文怎麼拼,直到我偶然從丸善書店訂購了《現代美術》一書,看到裡面有一幅由英國畫家羅傑・艾略特所繪製的聖誕紅水彩畫,才終於知道怎麼拼寫。畫下面的解說寫著:「這幅畫堪稱獨一無二的典範,將鮮花原原本本、毫無成見地描繪下來,是近代畫的翹楚。」畫中的背景是一面牆,牆上掛著破布,雜亂地貼著皺紙張,平凡無奇的牛奶瓶裡隨興地插著兩株聖誕紅,整體看起來是很不錯,但與放在我床邊的本尊相比,葉子的排列順序似乎怪怪的。從植物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幅畫肯定畫錯了,但是撰寫該解說的藝術評論家卻像上述一樣讚譽有加。他的評論看似誇大,但仔細一想,確實有幾分道理。
護士每天早上都把這些盆栽帶到戶外澆水,每當她經過走廊,總會有人驚訝地讚嘆「好漂亮的花啊」。相較於朝氣蓬勃的秋海棠和蘭花,聖誕紅則愈來愈虛弱,沿著直挺挺的莖等距生長的翠綠葉片,也逐漸變成了黃綠色。我擔心是澆水過多,特地叮囑了護士和妻子,但我畢竟不是園藝專家,也只能任由它自己生長。不久,聖誕紅的葉子便失去光澤、變成黃色,從底部一片片開始凋零。剩下的葉子也變得極為脆弱,稍微碰一下便掉下來。這些曾經生意盎然、從枝幹上冒出來的強韌葉片,如今居然連一丁點壓力都無法承受,說枯萎就枯萎了,令人感到十分詫異,但我也只能看著它們從底下開始,依序逐漸凋零。
S兄又送來了一盆秋海棠,跟T兄送的一樣大。但與之前的相比,這盆的花朵和葉子的色澤都略顯蒼白,有種淡淡的哀愁,反之卻也洋溢著一股清新的野花風情。想不到同一種花,會因為種植方法和環境不同而產生如此差異。我不禁思考著,土壤性質、肥料與水源、光線及溫度的變化,居然令花也有貴族與平民之分,幸虧花的貴族和平民不會抗議,才能相安無事。
接著,換O君送來了一個大型淺盆栽,裡面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花卉。正中央一樣是秋海棠,四周如綠色薄紗般綿延的是蘆筍葉,下面藏著火焰似的天竺葵,底部則有好幾朵有平糖似的蟹爪蘭垂掛在盆栽邊緣。每一朵花都很美麗,但像這樣以人為方式種在一起總感覺不太自然。不過,整體來說這是一盆非常華麗熱鬧的花,失眠的夜晚有它陪伴著我,讓漫漫長夜感覺縮短許多。失眠時我腦袋轉個不停,想起了得知N老師病重後,我趕去探望他的事。當時,我特別到江戶川大曲的花店買了一盆秋海棠,小心翼翼地用紙張包住花盆,帶在身上,一路徒步至早稻田。當天我的胃已經很不舒服,脹氣極為嚴重,後來才明白那時我的胃已經慢慢開始出血。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還堅持走路過去只為了節省一點點車資。老師病重,任何人都不見,但師母將我送去的花放到了病床旁。後來師母走出病房,告訴我:「他說很漂亮。」如今想來,那便是我從老師那裡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即使只是轉述。老師因為這場病撒手人寰,現在的我則跟老師得了同樣的病住院了,幸運的是,這次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在同樣的季節罹患同一種病,一樣望著床邊的秋海棠……或許這只是單純的巧合,但是仔細想想,其中卻彷彿有種必然的因果關係。很多事物乍看偶然,實則不然。老師和學生之間若有共通點,即使那只是精神上的,也難保不會對身體造成類似的影響。相反的,當共同點在身體上時,也會影響精神,促使兩個陌生人結成師徒緣分。若果真如此,老師和學生患上同樣疾病的機率,便可能素昧平生的人還要高。而一旦患上同樣的疾病,當然也可能在相同的時間點惡化。想著想著,我便愈覺得這個理論是對的。
出院時,蘭花已經枯萎到只剩葉子,聖誕紅也只有頂端的紅葉像鳥羽一樣殘留下來,仙客來也大多凋零了,但三盆秋海棠儘管褪色,卻依然開著花。我打算連同出院的行李,把所有盆栽都放到推車上一起帶回家,但當天不巧下雨了,推車沒有遮雨棚,只好請人力車運送行李。我決定留下所有盆栽,儘管覺得很不好意思,但還是拜託護士代為處理,看到她笑瞇瞇地答應,我便放心了。不過O兄送的什錦盆栽花色仍然鮮豔,妻子說扔掉太可惜了,便將它放在膝蓋上載回家。那盆花在客廳擺了一陣子,後來挪到院子裡的盆栽架上,每晚風吹雨淋。如今,秋海棠已經完全枯萎,莖就像折斷的杉木筷子,蟹爪蘭的花朵和葉片也變得蒼白無力,癱在盆栽上,唯獨蘆筍那薄紗般的葉子仍保持部分翠綠,沒有倒下。
住院三個星期,身旁的人事物和我自己都產生了許多變化。我讀了很多書,思考了很多事情。好多人來看我,在我心中投下光亮,卻也形成陰影。但我並不打算針對這點多說什麼。像現在這樣,只寫寫讓病房變得生意盎然的植物,令我有種整個住院生活都在拈花惹草的錯覺。這些無聊瑣碎的記錄對別人來說可能不值一提,但對我而言卻像寶貴的人生總目錄,令我畢生難忘。
發病前的四、五天,我去三越時順道買了一個秋海棠小盆栽。我把它放在書房的桌子上,擺在書架旁,每晚在燈光下觀賞它,想著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還要用它寫生。但這個計畫來不及實施,我就住院了。
入院那天,妻子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畫具,連秋海棠小盆栽也一起帶來了,放在病床旁邊的大理石藥架上。病房被灰色牆壁和純白窗簾團團包圍,只有暗紅色漆櫃和在床頭發亮的黃銅金屬配件為病房增添了一點色彩。然而,這個陰鬱、寒冷的病房卻突然間熱鬧、溫暖了起來。躺在床上,望著彷彿以寶石打造的深紅色花苞,以及天鵝絨般光澤亮麗的翠綠色葉片,雙雙映襯在灰色牆上,令我目眩神迷。
我常常在想,為何再精雕細琢的人造花,與自然花相比仍顯得粗糙不堪?我曾在美國的一間博物館看過由著名工藝家創作的玻璃花,可是與自然花相比,它不僅乏味,甚至令人有些厭惡。這種差異究竟源於何處呢?如果把有關色彩、型態的一切抽象概念和語言當作比較的標準,那麼人造花和真實花朵在外觀上的區別就會非常困難且不得要領。可能有人會說:「一邊是死的,另一邊是有生命的。」但這不過是把同樣的問題抽換詞面而已。照這樣講,豈不是得透過顯微鏡檢查,才能明確地區分兩邊的不同嗎?看看其中一邊是不是不規則且單純的乾燥纖維集合體,或是不規則且凹凹凸凸的非晶體,再看看另一邊是不是複雜但有規律的有機細胞組織?若不是美麗的事物和相似卻不美的事物之間,擁有人類感官所探測不到的細微差異,那就是人類潛意識中隱藏的自我,決定了這件事物美或不美吧。我思考著這個問題,凝視小盆栽裡的秋海棠,覺得彷彿連自己孱弱的肉眼,都看到了每顆花瓣細胞中散發的生命光芒。
住院第二天,A兄帶了一束油菜花來探望我,這裡沒有合適的花瓶,只好暫時擺在金屬臉盆裡。或許是溫室花的緣故,這束油菜花的香氣並不濃郁,很難讓人聯想到總是與油菜花田一同出現的雲雀歌聲。不久後,妻子從家裡帶了一個花瓶來,將油菜花插進去,擺在病房角落的洗手台上。同一天,我的侄子N也帶了一盆西洋蘭花來探望我。磚紅色的小盆栽裡有著茂密的水苔,幾片像青竹匙一樣厚重、寬大的葉子左右對稱伸展,中間佇立著一株微微垂首的蘭花。這株蘭花綠色佔了大部分,只有花冠帶有鮮豔的紫色刷紋,就世俗的審美觀來看並不漂亮,卻散發著極為高雅的沉靜之美。把它和嬌俏可愛、宛如童話故事公主的秋海棠放在一起時,它就像是一位年輕俊美卻憂鬱寡言的貴公子。花冠下半部垂著袋狀花瓣,上面蓋著另一片花瓣,我原本以為這個像蓋子的花瓣遲早會翹起來,讓袋子敞開,但袋子始終沒有打開。
不久後,T先生夫婦又帶了一個更大的秋海棠盆栽來。跟之前從家裡帶來的那一盆比起來,這個盆栽大了好幾倍。大秋海棠一來,小秋海棠頓時相形見拙。大概是家裡那盆小秋海棠的花色也有點黯淡了,一比之下,大秋海棠才真正是豔麗無雙,美得教人目眩神迷。舊的小秋海棠被挪到病房角落的洗手台上,新的大秋海棠則放在床邊,好讓我一遍又一遍欣賞它。奇妙的是,那株清幽的蘭花一點也不比大秋海棠遜色,反而顯得更獨樹一格。我捨不得扔掉舊的小秋海棠,仍時不時轉頭看看那洗手台上花葉都日漸褪色的可憐盆栽。孤伶伶的花瓶裡的油菜花,也總是勾起我淡淡的哀愁。
後來換I兄送了仙客來和聖誕紅給我。我曾在花店見過聖誕紅,但當時並不知道它的名字,這次看了盆栽上貼的標籤才知曉。我將它擺在藥架上,仔細觀賞,發現那火焰似的朱紅色樹冠很像雁來紅,濃烈的色澤一直令人聯想到熱帶。比起花,我覺得那更像是鳥類羽毛的顏色。端詳頂端,會發現那裡長著一叢黃黃的小花,這些小花非常低調,低調到幾乎看不到。大自然裡的植物為何總會有這麼不起眼的生殖器,反倒讓葉子等呼吸器官變得如此顯眼呢?或許植物學家和進化論者可以講出一番學說,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我想像著植物叢生的熱帶雨林,腦海中浮現了前陣子去新加坡旅遊的回憶。馬車穿梭在椰林裡,沿著紅土大道奔馳,當時無以名狀的心情如今清晰地浮現在心頭,只不過細節像夢一樣模糊、斑斕,宛如印在綠色及褐色布料上的花紋。即使如此,對於躺在這張冰冷病床上的我而言,想像著熾烈的陽光和充滿生命力的南國天地,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安慰。
仙客來似乎有些發育不良,花朵看起來沒什麼精神,葉子也有點捲曲,邊緣還變成了褐色。這盆花讓我莫名想起了在柏林的日子,那時我想送花給住在阿卡琴街(Akazien)的語言學老師慶生,便跑到使徒保羅教堂(Apostel-Paulus-Kirche)前的一間小花店挑選,最後買了仙客來盆栽。店員幫我用看似日本進口的粉紅皺紋紙包裝好後,我便立刻送去附近的老師家中。當時老師告訴我這種花叫做阿爾卑斯菫,大概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比仙客來更適合它。我不知道那位女老師現在怎麼樣了,她以前只收日本留學生當門徒,但隨著二戰爆發,留學生全都回國了,柏林市民對日本人的反感也日漸加劇,不知她是否因此遭遇過麻煩?她之後又是如何維生的呢?至今我仍三不五時會想起她。老師剛結婚沒多久,從醫的丈夫就去世了,從此和退役軍人的父親以及丈夫留下的十四歲女兒希德嘉爾特相依為命。我不太清楚老師家的狀況,但她似乎與父親處得並不好。某天我們幾個學生帶著希德嘉爾特一起去路易莎劇院(Luisen-Theater)看童話劇《白雪公主》,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小朋友,令我們這些外國大朋友有些不自在。飾演皇后的演員是一名非常胖的女人,她用美妙的歌喉唱出了「魔鏡啊魔鏡」。兩三天後,我得知當天晚上老師因為腹部嚴重痙攣而飽受折騰,還留下了明顯的黑眼圈。不知為何,我總覺老師會大病一場,責任都在我們身上,從此我再也沒去看過童話劇場。
五歲的雪子跟著姊姊到醫院探望我。剛開始她還會乖乖地看護士的臉色,保持安靜,後來愈來愈調皮,甚至爬到我的床上來。她望著我床邊的花盆,發現了藏在葉子底下的木牌,將片假名寫的花名一字一字大聲朗讀了出來。聽到她怪腔怪調的,大家都笑了。原來她最近學會了片假名,只要看到片假名就會忍不住念出來。從那之後,她每次來都會坐在床邊,不停地念那些花名。這讓我重新思考了「文字」的奧妙,以及人類知識的未來。
我一直很想知道聖誕紅的英文怎麼拼,直到我偶然從丸善書店訂購了《現代美術》一書,看到裡面有一幅由英國畫家羅傑・艾略特所繪製的聖誕紅水彩畫,才終於知道怎麼拼寫。畫下面的解說寫著:「這幅畫堪稱獨一無二的典範,將鮮花原原本本、毫無成見地描繪下來,是近代畫的翹楚。」畫中的背景是一面牆,牆上掛著破布,雜亂地貼著皺紙張,平凡無奇的牛奶瓶裡隨興地插著兩株聖誕紅,整體看起來是很不錯,但與放在我床邊的本尊相比,葉子的排列順序似乎怪怪的。從植物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幅畫肯定畫錯了,但是撰寫該解說的藝術評論家卻像上述一樣讚譽有加。他的評論看似誇大,但仔細一想,確實有幾分道理。
護士每天早上都把這些盆栽帶到戶外澆水,每當她經過走廊,總會有人驚訝地讚嘆「好漂亮的花啊」。相較於朝氣蓬勃的秋海棠和蘭花,聖誕紅則愈來愈虛弱,沿著直挺挺的莖等距生長的翠綠葉片,也逐漸變成了黃綠色。我擔心是澆水過多,特地叮囑了護士和妻子,但我畢竟不是園藝專家,也只能任由它自己生長。不久,聖誕紅的葉子便失去光澤、變成黃色,從底部一片片開始凋零。剩下的葉子也變得極為脆弱,稍微碰一下便掉下來。這些曾經生意盎然、從枝幹上冒出來的強韌葉片,如今居然連一丁點壓力都無法承受,說枯萎就枯萎了,令人感到十分詫異,但我也只能看著它們從底下開始,依序逐漸凋零。
S兄又送來了一盆秋海棠,跟T兄送的一樣大。但與之前的相比,這盆的花朵和葉子的色澤都略顯蒼白,有種淡淡的哀愁,反之卻也洋溢著一股清新的野花風情。想不到同一種花,會因為種植方法和環境不同而產生如此差異。我不禁思考著,土壤性質、肥料與水源、光線及溫度的變化,居然令花也有貴族與平民之分,幸虧花的貴族和平民不會抗議,才能相安無事。
接著,換O君送來了一個大型淺盆栽,裡面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花卉。正中央一樣是秋海棠,四周如綠色薄紗般綿延的是蘆筍葉,下面藏著火焰似的天竺葵,底部則有好幾朵有平糖似的蟹爪蘭垂掛在盆栽邊緣。每一朵花都很美麗,但像這樣以人為方式種在一起總感覺不太自然。不過,整體來說這是一盆非常華麗熱鬧的花,失眠的夜晚有它陪伴著我,讓漫漫長夜感覺縮短許多。失眠時我腦袋轉個不停,想起了得知N老師病重後,我趕去探望他的事。當時,我特別到江戶川大曲的花店買了一盆秋海棠,小心翼翼地用紙張包住花盆,帶在身上,一路徒步至早稻田。當天我的胃已經很不舒服,脹氣極為嚴重,後來才明白那時我的胃已經慢慢開始出血。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還堅持走路過去只為了節省一點點車資。老師病重,任何人都不見,但師母將我送去的花放到了病床旁。後來師母走出病房,告訴我:「他說很漂亮。」如今想來,那便是我從老師那裡聽到的最後一句話,即使只是轉述。老師因為這場病撒手人寰,現在的我則跟老師得了同樣的病住院了,幸運的是,這次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在同樣的季節罹患同一種病,一樣望著床邊的秋海棠……或許這只是單純的巧合,但是仔細想想,其中卻彷彿有種必然的因果關係。很多事物乍看偶然,實則不然。老師和學生之間若有共通點,即使那只是精神上的,也難保不會對身體造成類似的影響。相反的,當共同點在身體上時,也會影響精神,促使兩個陌生人結成師徒緣分。若果真如此,老師和學生患上同樣疾病的機率,便可能素昧平生的人還要高。而一旦患上同樣的疾病,當然也可能在相同的時間點惡化。想著想著,我便愈覺得這個理論是對的。
出院時,蘭花已經枯萎到只剩葉子,聖誕紅也只有頂端的紅葉像鳥羽一樣殘留下來,仙客來也大多凋零了,但三盆秋海棠儘管褪色,卻依然開著花。我打算連同出院的行李,把所有盆栽都放到推車上一起帶回家,但當天不巧下雨了,推車沒有遮雨棚,只好請人力車運送行李。我決定留下所有盆栽,儘管覺得很不好意思,但還是拜託護士代為處理,看到她笑瞇瞇地答應,我便放心了。不過O兄送的什錦盆栽花色仍然鮮豔,妻子說扔掉太可惜了,便將它放在膝蓋上載回家。那盆花在客廳擺了一陣子,後來挪到院子裡的盆栽架上,每晚風吹雨淋。如今,秋海棠已經完全枯萎,莖就像折斷的杉木筷子,蟹爪蘭的花朵和葉片也變得蒼白無力,癱在盆栽上,唯獨蘆筍那薄紗般的葉子仍保持部分翠綠,沒有倒下。
住院三個星期,身旁的人事物和我自己都產生了許多變化。我讀了很多書,思考了很多事情。好多人來看我,在我心中投下光亮,卻也形成陰影。但我並不打算針對這點多說什麼。像現在這樣,只寫寫讓病房變得生意盎然的植物,令我有種整個住院生活都在拈花惹草的錯覺。這些無聊瑣碎的記錄對別人來說可能不值一提,但對我而言卻像寶貴的人生總目錄,令我畢生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