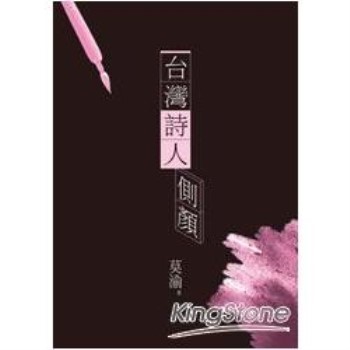散發靜光的銀杏
───懷思巫永福先生的「文學之路」
一、前引
1930年代,日本殖民地出身的數位二十來歲的台灣青年,在東京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印行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即《福爾摩沙》),推動藝術性的詩文學,為新興的台灣文學界掀起里程碑。隨歲月流逝,當年英姿氣盛的一夥文藝憧憬者,逐漸凋零,跨世紀後,碩果僅存的巫永福先生也於今年9月10日離世,全體成員走入歷史,但,文學運動與文學生命並未萎謝。如同落地種子般,它們繼續在這塊土地各自萌芽、長大。文學雜誌的旗幟,仍標記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有力飄揚,巫老生前整理出版全集24冊及未整理的少量文稿,都將成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提供典藏,讓後人欣賞與研究。塵土一坯,朝露人生,引人懷思的是這些足以千秋的詩文學。
2008年10月12日,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告別式場內的輓詞,甚多「典型永存」、「仁風永仰」、「碩德永欽」、「德望所歸」、「駕鶴西歸」等,呈現的是他在社會層面世俗認同的「蓋棺論定」。另一層面,文學界恭送花籃的輓詞,如笠詩社的「詩業永恆」、台灣筆會的「筆劍同光」、文學台灣社的「文學長存」、李敏勇的「時代先鋒」,就突顯並肯定了他在心靈活動的焦點。
跨世紀的「文學長者」巫永福先生,是「國之耆宿」,台灣文學界的頂針,以九六高齡往生,理當有國家級的告別儀式,然環視現場,民間人士居多。讀其詩文,或許能體會家族的低調。再回看巫永福一生文學創作與行誼,他寫下甚多與當時文人交往的記錄,在當事人往生後,記載尤詳。同為台灣藝術研究會的同志王白淵和張文環兩位,巫老的追懷之情,溢於言表。在〈緬懷王白淵〉長文,巫老詳述當年告別式過程與眾親友留下的話語,文章起筆,巫老說「一個人死去,還常能使人緬懷者實在不多,雖已去了二十年,台灣新詩草創期的傑出傷痕詩人王白淵的影子,卻常在腦子裡環繞,談論新詩與美術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於我的面前。」在〈悼張文環兄回首前塵〉文章前,巫老留有一輓聯:
數十載文學運動,春風並坐,夜雨聯床,回首前程悲若夢。
猶著佳構竟未成,一朝永別,典型式望,尚留斯界作巨人。
如今,巫老走了,應有更多的晚輩緬懷他,先敬記數語,謹表感念:
轉型正義未完成,威權餘力強復辟,詩人遺憾深深深。
文學大業堆疊砌,無悔當年志凌雲,魂歸家鄉樂樂樂。
───懷思巫永福先生的「文學之路」
一、前引
1930年代,日本殖民地出身的數位二十來歲的台灣青年,在東京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印行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即《福爾摩沙》),推動藝術性的詩文學,為新興的台灣文學界掀起里程碑。隨歲月流逝,當年英姿氣盛的一夥文藝憧憬者,逐漸凋零,跨世紀後,碩果僅存的巫永福先生也於今年9月10日離世,全體成員走入歷史,但,文學運動與文學生命並未萎謝。如同落地種子般,它們繼續在這塊土地各自萌芽、長大。文學雜誌的旗幟,仍標記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有力飄揚,巫老生前整理出版全集24冊及未整理的少量文稿,都將成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提供典藏,讓後人欣賞與研究。塵土一坯,朝露人生,引人懷思的是這些足以千秋的詩文學。
2008年10月12日,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告別式場內的輓詞,甚多「典型永存」、「仁風永仰」、「碩德永欽」、「德望所歸」、「駕鶴西歸」等,呈現的是他在社會層面世俗認同的「蓋棺論定」。另一層面,文學界恭送花籃的輓詞,如笠詩社的「詩業永恆」、台灣筆會的「筆劍同光」、文學台灣社的「文學長存」、李敏勇的「時代先鋒」,就突顯並肯定了他在心靈活動的焦點。
跨世紀的「文學長者」巫永福先生,是「國之耆宿」,台灣文學界的頂針,以九六高齡往生,理當有國家級的告別儀式,然環視現場,民間人士居多。讀其詩文,或許能體會家族的低調。再回看巫永福一生文學創作與行誼,他寫下甚多與當時文人交往的記錄,在當事人往生後,記載尤詳。同為台灣藝術研究會的同志王白淵和張文環兩位,巫老的追懷之情,溢於言表。在〈緬懷王白淵〉長文,巫老詳述當年告別式過程與眾親友留下的話語,文章起筆,巫老說「一個人死去,還常能使人緬懷者實在不多,雖已去了二十年,台灣新詩草創期的傑出傷痕詩人王白淵的影子,卻常在腦子裡環繞,談論新詩與美術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於我的面前。」在〈悼張文環兄回首前塵〉文章前,巫老留有一輓聯:
數十載文學運動,春風並坐,夜雨聯床,回首前程悲若夢。
猶著佳構竟未成,一朝永別,典型式望,尚留斯界作巨人。
如今,巫老走了,應有更多的晚輩緬懷他,先敬記數語,謹表感念:
轉型正義未完成,威權餘力強復辟,詩人遺憾深深深。
文學大業堆疊砌,無悔當年志凌雲,魂歸家鄉樂樂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