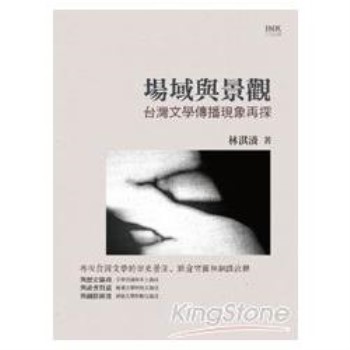壹、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一、緒論:民族‧大眾‧鄉土
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隨著研究的日漸增加,以及戰後台語文學論述與實踐的強化,其過程及其論述內容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但在解釋上則似乎尚未能清楚呈現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1954年廖毓文發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 一文,以大量引文方式回溯了當年起於1922到1933年間台灣文字改革運動的過程,使得戰後台灣文學界得以通過此一文獻,重新認知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語文改革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廖毓文宏觀地從「台灣文字改革」的視角切入,認為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乃是應台灣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後「對於普及的方法,要銳意的予以考慮」的時代要求而生。2 他將日治時期的文字改革運動分為「白話文運動」、「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等三個內容,台灣話文運動下又細分為「台灣話保存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兩者。作為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廖毓文持平地使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台灣話文運動中贊同與反對者的各家論述,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語言主張的鳥瞰圖;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台灣文化作為日本「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
廖毓文並未具體分析台灣「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如何,但是在短短十一年間台灣文學界出現以中國五四白話文學為藍本的主張(白話文運動)、以西方教會羅馬字為範本的主張(羅馬字運動),以及以漢字創造台灣話文的主張,若再加上1937年日本總督府廢除漢文之後展開的全面採用日文書寫,則殖民地台灣的語文狀態就相當複雜地徘徊於中國白話文、西方羅馬拼音文、台灣話文與殖民統治者限制的日本語文之間。採用什麼樣的文字,才能有效發展台灣文化?用什麼樣的語文來創作文學,才是最恰如其分的台灣文學?顯然已經使得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因此陷入「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3 的弔詭困局之中。這使得這個階段的台灣文學界也因此不斷辯爭,白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台灣話文論爭」,乃至於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運動之遭到冷漠以對,都具體說明了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徬徨猶疑。
這種文化認同的徬徨猶疑,之所以複雜,更深層地看,還與台灣知識分子面臨的身分認同有關,我曾從傳播與政治的面向分析此一困境:
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在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仍懷有來自種族身分上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面對著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以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這三種來自不同身分認同的困境,從而……構成了其後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諸多論戰與爭辯的主軸。4
1930年代發生的台灣話文論爭,從身分/文化認同的深層結構看,更足以讓我們看到隱藏在使用何種語文之爭背後,台灣知識分子的民族想像,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話來說,這種民族想像都是被想像出來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是從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出來的結果,5 台灣話文運動中的爭論,因此也是一種民族想像認同的爭論: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這三種民族想像介於其中,使得這場爭論絕不止於使用什麼語文才能有效傳播,或者應該採用何種文字才能表現台灣文學的特性,這樣表面的語詞之爭,有著打造一個全新的民族文學/文化的意涵在內,其中也蘊藏著通過行動,創造民族和維持民族生存的「民族文化」的嚴肅意義。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的另一個複雜性則不只是文化認同,同時還攙雜著意識形態的鬥爭。日本學者松永正義指這個階段的鄉土文學論爭包括了「民族的契機」與「民眾的契機」的矛盾,6 是相當深刻的看法。「民眾的契機」,意味著台灣話文論爭的底層還具有階級性。這與台灣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乃至論爭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有關,如最早提出台灣話文思考的黃石輝,就是當時「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重要刊物《伍人報》的地方委員,7 加上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更使得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深而且鉅」的影響;8 此外,這也與當時台灣政治、文化乃至文學界的思想轉向有關,左翼知識分子在取得政治與文化運動主導權之後,轉向具有階級性的「大眾文化」實踐。9 文藝大眾化,因此成為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根本的基調;大眾路線,也因此進入台灣話文運動的論述中,成為階級路線具體落實的表徵。
右邊是民族文化的標舉,左邊是大眾文化的鼓吹─民族主義的想像和社會主義的主張從而以看似矛盾、實則相諧的意識形態,被「接合」(articulate)在1930年代「鄉土文學」的論述符號下。1930年8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正式揭開了台灣白話文運動的序幕,也促發了其後兩場圍繞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與大眾/民族性與階級性)路線周邊的論爭。
二、台灣想像:土地、人民、語言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陳淑容在她的研究中,指其主張是「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在內容上,描寫台灣的事物;在形式上,以台灣話文來書寫」;10 而其論述重點則有兩個層面,「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11 這個說法相當明確,也有見地,不過仍有深層分析的空間。我們不妨回到黃石輝當時的文本看。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在民族主義的部分充滿了台灣想像,最為膾炙人口,且成為戰後台語文學論述建構基礎的一段話如下: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台灣的文學怎麼寫呢?便是用台灣話作文,用台灣話作詩,用台灣話作小說,用台灣話作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12
在這段論述中,作為「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是論述核心價值所在,前述安德森的民族主義論述,就強調這樣的想像共同體促成了民族的出現,黃石輝的論述中顯然刻意以「台灣」來區辨於日本、中國之外,以「台灣文學」的書寫來區辨於當時的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之外,因此具有相當濃烈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其次,一如安德森的民族意識起源說,民族意識來自三種動力:一是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二是傳播科技(印刷品),三是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種動力,互為作用,形成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s),方才使得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13 黃石輝倡議使用「台灣話作文」,來寫「台灣的文學」,就其意義來說,的確可以使台灣話成為「台灣文」(印刷語言),無形中創造了凝聚台灣想像的民族意識,而此一民族意識正是具體地落實在「台灣天」、「台灣地」、「台灣的狀況」、「台灣的消息」、「台灣的經驗」與「台灣的語言」之上,「台灣」的土地認同也因此具體可感。我們可以說,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核心在「台灣想像」的創造:台灣(土地)是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母體,台灣人(人民)、台灣話(語言)則是此一台灣想像的兩翼。
不過,由於黃石輝的左翼身分,他對「台灣人」的想像顯然有階級上的傾重,那就是源自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觀點。黃石輝強調的鄉土文學要使用台灣話的另一個理由,非關民族主義,而是要「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
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的心理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14
這裡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黃石輝的「大眾文學」觀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意識,在黃石輝的論述中,相對於殖民地國日本的語言、祖國的白話文,都具有階級性,是「支配階級」的語言,不是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語言,台灣勞苦大眾說的台灣話才是。這是以階級意識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鬥爭,黃石輝顯然有意以台灣無產階級(勞苦大眾)使用的語言,建立一個如同霍爾(Stuart Hall)所說具有「反抗的集體形式」和「集群自覺」的新形式15(以大眾為對象的鄉土文學),來與當時由知識分子使用支配階級語言寫成的日本話文學、中國白話文學抗衡;而其目的之一,當然是與資產階級進行決定性的意識形態鬥爭。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到這裡出現了「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雙重面貌,同時也出現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縫隙:鄉土文學如果只為台灣普羅階級而倡,則全世界的普羅階級如何分享?如果鄉土文學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那也就牴觸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無國界論述了。與黃石輝同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賴明弘就提出這樣的質疑,16 黃石輝的答覆很乾脆,他認為無產階級的要求就是要過一個完全的「人」的生活,以台灣的客觀情勢,提倡普羅文學必須「超階級」,「斷然不是限定在某一階級的工作」。17 儘管「超階級」語焉不詳,黃石輝的主張進一步釐清了:以台灣話為勞苦大眾寫作台灣文學,是要把民族主義擺在優先位置,而把階級的社會主義擺於第二順位,來使台灣的勞苦大眾過人的生活。
要建設台灣人的台灣話文學,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語言落實為文字的問題。台灣話要作為文學語言或具備傳播功能的「印刷語言」,就必須打造一套語文規則。對此,1930年黃石輝具體提出「鄉土文學」建設三原則:
(一) 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1)要排除用台灣話說不來的或台灣用不著的語言,如「打馬屁」要改用「扶生泡」;要增加台灣特有的土語,如「我們」,台灣有時用「咱」、有時用「阮」,要分別清楚。
(二) 增讀台灣音。無論什麼字,有必要時便讀土音。
(三) 描寫台灣的事物。使文學家們趨向於寫實的路上跑。18
其後黃石輝又在《台灣新聞》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全文分「一、鄉土文學的功用,二、描寫問題,三、文字的問題,四、言語的整理,五、讀音的問題,六、基礎問題,七、結論」等七節,重申他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在結論的部分,黃石輝進而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19 台灣話文的語文規則到此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
台灣話文運動的另一位戰將郭秋生,也在《台灣新聞》連載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20 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在這篇論述中,郭秋生基於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同化主義」的立場,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他主張以漢字為工具創造台灣話文。針對台灣話如何落實為文字,則提出語文處理的五原則,21 為台灣話如何入文提出建議。
1931年8月29日、9月6日,郭秋生又以〈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為題,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看法。22 他肯定黃石輝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他認為基礎的打建「要找文盲層這所素地」,所以應從歌謠與民歌整理做起。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是關於「本格的建設」的觀點,他針對當時反對台灣話文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作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23 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
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於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24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觸及的乃是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書寫的核心議題,這是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難得的見解,也就是以「現在的台灣話」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來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學。25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最大的意義,除了標舉「台灣人」民族想像之外,就是強調此一「台灣話」的大眾路線。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分進合擊,對象相當清楚,民族想像針對殖民統治的日本,大眾路線則針對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存在於殖民社會中的新日本文化,其目的最終則在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文化認同的台灣文學。用黃石輝在論爭期間答辯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廖毓文26 的話來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27
到這裡,台灣主體意識清楚呈現,以台灣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文學主張,乃是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主軸,應已無庸置疑。林瑞明認為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性之表現,亦即對台灣本體之正視,不以附屬中國白話文的表達方式為限」;28 呂興昌說這個運動「無論是政治抑民族,攏蔔佮中國參日本劃清界線」,建立真正合身於台灣的獨立文化/文學,29 應屬持平且根據歷史事實所下的結論。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
一、緒論:民族‧大眾‧鄉土
發生於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隨著研究的日漸增加,以及戰後台語文學論述與實踐的強化,其過程及其論述內容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但在解釋上則似乎尚未能清楚呈現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1954年廖毓文發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 一文,以大量引文方式回溯了當年起於1922到1933年間台灣文字改革運動的過程,使得戰後台灣文學界得以通過此一文獻,重新認知日治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語文改革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廖毓文宏觀地從「台灣文字改革」的視角切入,認為台灣的文字改革運動乃是應台灣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後「對於普及的方法,要銳意的予以考慮」的時代要求而生。2 他將日治時期的文字改革運動分為「白話文運動」、「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等三個內容,台灣話文運動下又細分為「台灣話保存運動」與「台灣話文運動」兩者。作為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廖毓文持平地使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台灣話文運動中贊同與反對者的各家論述,提供給後來的研究者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語言主張的鳥瞰圖;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台灣文化作為日本「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
廖毓文並未具體分析台灣「殖民地文化」的複雜性如何,但是在短短十一年間台灣文學界出現以中國五四白話文學為藍本的主張(白話文運動)、以西方教會羅馬字為範本的主張(羅馬字運動),以及以漢字創造台灣話文的主張,若再加上1937年日本總督府廢除漢文之後展開的全面採用日文書寫,則殖民地台灣的語文狀態就相當複雜地徘徊於中國白話文、西方羅馬拼音文、台灣話文與殖民統治者限制的日本語文之間。採用什麼樣的文字,才能有效發展台灣文化?用什麼樣的語文來創作文學,才是最恰如其分的台灣文學?顯然已經使得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因此陷入「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3 的弔詭困局之中。這使得這個階段的台灣文學界也因此不斷辯爭,白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話文運動時期出現的「台灣話文論爭」,乃至於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運動之遭到冷漠以對,都具體說明了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徬徨猶疑。
這種文化認同的徬徨猶疑,之所以複雜,更深層地看,還與台灣知識分子面臨的身分認同有關,我曾從傳播與政治的面向分析此一困境:
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在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仍懷有來自種族身分上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面對著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以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這三種來自不同身分認同的困境,從而……構成了其後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諸多論戰與爭辯的主軸。4
1930年代發生的台灣話文論爭,從身分/文化認同的深層結構看,更足以讓我們看到隱藏在使用何種語文之爭背後,台灣知識分子的民族想像,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話來說,這種民族想像都是被想像出來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是從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出來的結果,5 台灣話文運動中的爭論,因此也是一種民族想像認同的爭論: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這三種民族想像介於其中,使得這場爭論絕不止於使用什麼語文才能有效傳播,或者應該採用何種文字才能表現台灣文學的特性,這樣表面的語詞之爭,有著打造一個全新的民族文學/文化的意涵在內,其中也蘊藏著通過行動,創造民族和維持民族生存的「民族文化」的嚴肅意義。
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的另一個複雜性則不只是文化認同,同時還攙雜著意識形態的鬥爭。日本學者松永正義指這個階段的鄉土文學論爭包括了「民族的契機」與「民眾的契機」的矛盾,6 是相當深刻的看法。「民眾的契機」,意味著台灣話文論爭的底層還具有階級性。這與台灣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乃至論爭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有關,如最早提出台灣話文思考的黃石輝,就是當時「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重要刊物《伍人報》的地方委員,7 加上當時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更使得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深而且鉅」的影響;8 此外,這也與當時台灣政治、文化乃至文學界的思想轉向有關,左翼知識分子在取得政治與文化運動主導權之後,轉向具有階級性的「大眾文化」實踐。9 文藝大眾化,因此成為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根本的基調;大眾路線,也因此進入台灣話文運動的論述中,成為階級路線具體落實的表徵。
右邊是民族文化的標舉,左邊是大眾文化的鼓吹─民族主義的想像和社會主義的主張從而以看似矛盾、實則相諧的意識形態,被「接合」(articulate)在1930年代「鄉土文學」的論述符號下。1930年8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正式揭開了台灣白話文運動的序幕,也促發了其後兩場圍繞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與大眾/民族性與階級性)路線周邊的論爭。
二、台灣想像:土地、人民、語言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陳淑容在她的研究中,指其主張是「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在內容上,描寫台灣的事物;在形式上,以台灣話文來書寫」;10 而其論述重點則有兩個層面,「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11 這個說法相當明確,也有見地,不過仍有深層分析的空間。我們不妨回到黃石輝當時的文本看。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在民族主義的部分充滿了台灣想像,最為膾炙人口,且成為戰後台語文學論述建構基礎的一段話如下: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台灣的文學怎麼寫呢?便是用台灣話作文,用台灣話作詩,用台灣話作小說,用台灣話作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12
在這段論述中,作為「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是論述核心價值所在,前述安德森的民族主義論述,就強調這樣的想像共同體促成了民族的出現,黃石輝的論述中顯然刻意以「台灣」來區辨於日本、中國之外,以「台灣文學」的書寫來區辨於當時的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之外,因此具有相當濃烈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其次,一如安德森的民族意識起源說,民族意識來自三種動力:一是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二是傳播科技(印刷品),三是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種動力,互為作用,形成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s),方才使得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13 黃石輝倡議使用「台灣話作文」,來寫「台灣的文學」,就其意義來說,的確可以使台灣話成為「台灣文」(印刷語言),無形中創造了凝聚台灣想像的民族意識,而此一民族意識正是具體地落實在「台灣天」、「台灣地」、「台灣的狀況」、「台灣的消息」、「台灣的經驗」與「台灣的語言」之上,「台灣」的土地認同也因此具體可感。我們可以說,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核心在「台灣想像」的創造:台灣(土地)是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母體,台灣人(人民)、台灣話(語言)則是此一台灣想像的兩翼。
不過,由於黃石輝的左翼身分,他對「台灣人」的想像顯然有階級上的傾重,那就是源自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觀點。黃石輝強調的鄉土文學要使用台灣話的另一個理由,非關民族主義,而是要「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
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的心理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14
這裡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黃石輝的「大眾文學」觀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意識,在黃石輝的論述中,相對於殖民地國日本的語言、祖國的白話文,都具有階級性,是「支配階級」的語言,不是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語言,台灣勞苦大眾說的台灣話才是。這是以階級意識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鬥爭,黃石輝顯然有意以台灣無產階級(勞苦大眾)使用的語言,建立一個如同霍爾(Stuart Hall)所說具有「反抗的集體形式」和「集群自覺」的新形式15(以大眾為對象的鄉土文學),來與當時由知識分子使用支配階級語言寫成的日本話文學、中國白話文學抗衡;而其目的之一,當然是與資產階級進行決定性的意識形態鬥爭。
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到這裡出現了「一是民族的,一是階級的」雙重面貌,同時也出現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縫隙:鄉土文學如果只為台灣普羅階級而倡,則全世界的普羅階級如何分享?如果鄉土文學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那也就牴觸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無國界論述了。與黃石輝同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賴明弘就提出這樣的質疑,16 黃石輝的答覆很乾脆,他認為無產階級的要求就是要過一個完全的「人」的生活,以台灣的客觀情勢,提倡普羅文學必須「超階級」,「斷然不是限定在某一階級的工作」。17 儘管「超階級」語焉不詳,黃石輝的主張進一步釐清了:以台灣話為勞苦大眾寫作台灣文學,是要把民族主義擺在優先位置,而把階級的社會主義擺於第二順位,來使台灣的勞苦大眾過人的生活。
要建設台灣人的台灣話文學,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語言落實為文字的問題。台灣話要作為文學語言或具備傳播功能的「印刷語言」,就必須打造一套語文規則。對此,1930年黃石輝具體提出「鄉土文學」建設三原則:
(一) 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1)要排除用台灣話說不來的或台灣用不著的語言,如「打馬屁」要改用「扶生泡」;要增加台灣特有的土語,如「我們」,台灣有時用「咱」、有時用「阮」,要分別清楚。
(二) 增讀台灣音。無論什麼字,有必要時便讀土音。
(三) 描寫台灣的事物。使文學家們趨向於寫實的路上跑。18
其後黃石輝又在《台灣新聞》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全文分「一、鄉土文學的功用,二、描寫問題,三、文字的問題,四、言語的整理,五、讀音的問題,六、基礎問題,七、結論」等七節,重申他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在結論的部分,黃石輝進而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19 台灣話文的語文規則到此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
台灣話文運動的另一位戰將郭秋生,也在《台灣新聞》連載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20 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在這篇論述中,郭秋生基於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同化主義」的立場,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他主張以漢字為工具創造台灣話文。針對台灣話如何落實為文字,則提出語文處理的五原則,21 為台灣話如何入文提出建議。
1931年8月29日、9月6日,郭秋生又以〈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為題,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看法。22 他肯定黃石輝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他認為基礎的打建「要找文盲層這所素地」,所以應從歌謠與民歌整理做起。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是關於「本格的建設」的觀點,他針對當時反對台灣話文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作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23 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
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於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24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觸及的乃是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書寫的核心議題,這是台灣話文論爭中相當難得的見解,也就是以「現在的台灣話」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來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學。25
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最大的意義,除了標舉「台灣人」民族想像之外,就是強調此一「台灣話」的大眾路線。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分進合擊,對象相當清楚,民族想像針對殖民統治的日本,大眾路線則針對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存在於殖民社會中的新日本文化,其目的最終則在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文化認同的台灣文學。用黃石輝在論爭期間答辯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廖毓文26 的話來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27
到這裡,台灣主體意識清楚呈現,以台灣想像共同體的台灣文學主張,乃是1930年代台灣話文運動的主軸,應已無庸置疑。林瑞明認為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性之表現,亦即對台灣本體之正視,不以附屬中國白話文的表達方式為限」;28 呂興昌說這個運動「無論是政治抑民族,攏蔔佮中國參日本劃清界線」,建立真正合身於台灣的獨立文化/文學,29 應屬持平且根據歷史事實所下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