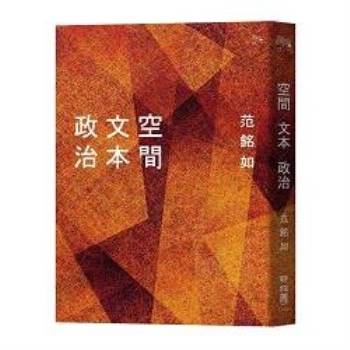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本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鄉鎮、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麗紅、陳淑瑤、凌煙、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陳雪等等,我的同事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即使是上述作家,除了蕭麗紅與陳淑瑤,以都會文化為書寫背景的比例都遠遠超過鄉村。放大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現象格外觸目驚心。十幾年前當我開始爬梳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源流時,我嘗試以一般台灣文學史的分期為經,平行地對比出同時期女性小說的特徵,她們與男性主流文學的類同與差異,以此來建構出台灣女性「自己的文學」。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女作家人數有些不尋常的起伏。在以新近遷移來台的外省女性為主、偏向寫實形式的一九四○、五○年代,作家數高達百人以上,進展到現代主義興盛的一九六○年代時,新進文壇的(外省加本省籍)女性寫手卻銳減至十人以內;當時我認為肇因於台灣女作家對現代主義美學的隔閡陌生,部分也是因為戰後本地女性教育人口還未全面成長,文學養成的時間還不夠久,創作人數大幅下滑倒也合理。到了又是寫實主義形式抬頭但以鄉土素材為內容的一九七○年代,真正以鄉土題材成功進軍文壇的大概只有兩人,而且創作數量不多,以至於我無法專立一章女性鄉土小說去對照台灣文學史裡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雖則有些納悶,我卻不疑有它。反正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們開創出來第一波的婦女寫作黃金年代暫時落幕,一九八○年代的女作家們很快就贏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第二波黃金年代。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間以都會生活、身分議題為主的大量女性創作人才,無論在寫實、現代或後現代等各類形式實驗遊刃有餘,從文學市場到學院口碑上都大獲成功。適逢本地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性女性主義/文學論述相繼在台灣蓬勃發展,三方加持之下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獲得了正典化的地位,一舉將台灣文學界扭轉成女人天下的盛況。直至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鄉土文學又以後鄉土文學的新形式重新稱霸台灣文壇,我赫然發現,此一類型的寫作者全是男性;從一九八○年代以降歷二十年培育出堅強的女性書寫世代竟然在後鄉土文學潮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女性書寫的黃金年代都被鄉土文學終結。台灣女性寫作的黑暗期促使我去思索,此空白的兩頁或者不僅只是歷史性的偶然。
帶著這個疑問轉而檢視其他華文寫作區,我發現,重都會、疏鄉土並非台灣女性文學獨有的現象。香港女性小說家從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陳慧,以迄更年輕一代的謝曉虹、韓麗珠等人,無一不是以都會元素見長,罕見書寫鄉土題材。就連近一百年歷史的中國大陸現代女性小說,專寫鄉土的作家也寥寥可數。一九四九年之前,專以描寫農村經驗或鄉野生活風俗習慣見著文壇者雖有如蕭紅、梅娘、羅淑、羅洪、白朗等東北或左翼陣營女作家,但以總人數來看比例仍舊不高。中共建國以後號稱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與鄉村一躍而成知識分子學習謳歌的對象,下鄉是知青必要的訓練過程甚或是懲罰的手段,鄉土一度變成了文學的主旋律。一九七○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意識型態的管控鬆動,女作家又紛紛轉向都市風華,即使仍有部分篇幅著墨於田野鄉俗。雖然無法做出一個具體的統計表列,總的來說,台港中三個不同地理區域的女作家,不拘一時一地,對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文學趨勢。不爭的現象卻是令人不安的傾向。我可以想像長期以來輕視女性文學的陣營見獵心喜,斷章取義地引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內幕觀察,重彈女人「就是視見狹窄」、「貪圖虛浮奢華的物質文明,不關心廣袤的社會土地」之類的陳腔濫調,或者訕笑嘲弄個一句,原來女人要建造的房間不過是這種小豪宅啊。捍衛女性書寫的同僚則可能會翻出更多寫鄉土背景的女作家人數或文本拉近城鄉的比例,以技術細節的爭議質疑命題的可信度──要是我就會這麼做。不管是針對哪一方的陣營,我都必須鄭重申明,我並沒有贊成或反對都市主義(urbanism)的預設立場;城鄉題材或描寫的空間幅員大小類型更與作品和作家的宏不宏觀、偉不偉大沒有本質性的關聯,無涉其藝術評價。城鄉比重的失衡如果是一個現行女性書寫的特徵,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造成這個傾向的緣由。捫心自問,我不認為這篇專文能夠提供充分完整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性別與空間、書寫與空間,以及性別、書寫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而不管是我個人或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結合空間研究上的累積還相當有限。明知是瞎子摸象,本文仍期許在偌大的問題迷宮中擲下幾條線索,為女性書寫與空間的結構性勾連留下一些思索的足跡。我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空間的偏好以及城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進行討論。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女性書寫為主,也會參照其他中文書寫區域的女作家和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女性文學潮,尤其是幾個女性鄉土書寫熱出現時的歷史條件。我要論證不管是經驗論、生產機制和敘事傳統裡,都市空間皆與女性位置較為親近,除非在特定的狀況下。女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女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管我們習而不察。
本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鄉鎮、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麗紅、陳淑瑤、凌煙、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陳雪等等,我的同事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即使是上述作家,除了蕭麗紅與陳淑瑤,以都會文化為書寫背景的比例都遠遠超過鄉村。放大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現象格外觸目驚心。十幾年前當我開始爬梳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源流時,我嘗試以一般台灣文學史的分期為經,平行地對比出同時期女性小說的特徵,她們與男性主流文學的類同與差異,以此來建構出台灣女性「自己的文學」。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女作家人數有些不尋常的起伏。在以新近遷移來台的外省女性為主、偏向寫實形式的一九四○、五○年代,作家數高達百人以上,進展到現代主義興盛的一九六○年代時,新進文壇的(外省加本省籍)女性寫手卻銳減至十人以內;當時我認為肇因於台灣女作家對現代主義美學的隔閡陌生,部分也是因為戰後本地女性教育人口還未全面成長,文學養成的時間還不夠久,創作人數大幅下滑倒也合理。到了又是寫實主義形式抬頭但以鄉土素材為內容的一九七○年代,真正以鄉土題材成功進軍文壇的大概只有兩人,而且創作數量不多,以至於我無法專立一章女性鄉土小說去對照台灣文學史裡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雖則有些納悶,我卻不疑有它。反正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們開創出來第一波的婦女寫作黃金年代暫時落幕,一九八○年代的女作家們很快就贏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第二波黃金年代。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間以都會生活、身分議題為主的大量女性創作人才,無論在寫實、現代或後現代等各類形式實驗遊刃有餘,從文學市場到學院口碑上都大獲成功。適逢本地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性女性主義/文學論述相繼在台灣蓬勃發展,三方加持之下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獲得了正典化的地位,一舉將台灣文學界扭轉成女人天下的盛況。直至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鄉土文學又以後鄉土文學的新形式重新稱霸台灣文壇,我赫然發現,此一類型的寫作者全是男性;從一九八○年代以降歷二十年培育出堅強的女性書寫世代竟然在後鄉土文學潮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女性書寫的黃金年代都被鄉土文學終結。台灣女性寫作的黑暗期促使我去思索,此空白的兩頁或者不僅只是歷史性的偶然。
帶著這個疑問轉而檢視其他華文寫作區,我發現,重都會、疏鄉土並非台灣女性文學獨有的現象。香港女性小說家從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陳慧,以迄更年輕一代的謝曉虹、韓麗珠等人,無一不是以都會元素見長,罕見書寫鄉土題材。就連近一百年歷史的中國大陸現代女性小說,專寫鄉土的作家也寥寥可數。一九四九年之前,專以描寫農村經驗或鄉野生活風俗習慣見著文壇者雖有如蕭紅、梅娘、羅淑、羅洪、白朗等東北或左翼陣營女作家,但以總人數來看比例仍舊不高。中共建國以後號稱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與鄉村一躍而成知識分子學習謳歌的對象,下鄉是知青必要的訓練過程甚或是懲罰的手段,鄉土一度變成了文學的主旋律。一九七○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意識型態的管控鬆動,女作家又紛紛轉向都市風華,即使仍有部分篇幅著墨於田野鄉俗。雖然無法做出一個具體的統計表列,總的來說,台港中三個不同地理區域的女作家,不拘一時一地,對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文學趨勢。不爭的現象卻是令人不安的傾向。我可以想像長期以來輕視女性文學的陣營見獵心喜,斷章取義地引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內幕觀察,重彈女人「就是視見狹窄」、「貪圖虛浮奢華的物質文明,不關心廣袤的社會土地」之類的陳腔濫調,或者訕笑嘲弄個一句,原來女人要建造的房間不過是這種小豪宅啊。捍衛女性書寫的同僚則可能會翻出更多寫鄉土背景的女作家人數或文本拉近城鄉的比例,以技術細節的爭議質疑命題的可信度──要是我就會這麼做。不管是針對哪一方的陣營,我都必須鄭重申明,我並沒有贊成或反對都市主義(urbanism)的預設立場;城鄉題材或描寫的空間幅員大小類型更與作品和作家的宏不宏觀、偉不偉大沒有本質性的關聯,無涉其藝術評價。城鄉比重的失衡如果是一個現行女性書寫的特徵,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造成這個傾向的緣由。捫心自問,我不認為這篇專文能夠提供充分完整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性別與空間、書寫與空間,以及性別、書寫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而不管是我個人或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結合空間研究上的累積還相當有限。明知是瞎子摸象,本文仍期許在偌大的問題迷宮中擲下幾條線索,為女性書寫與空間的結構性勾連留下一些思索的足跡。我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空間的偏好以及城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進行討論。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女性書寫為主,也會參照其他中文書寫區域的女作家和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女性文學潮,尤其是幾個女性鄉土書寫熱出現時的歷史條件。我要論證不管是經驗論、生產機制和敘事傳統裡,都市空間皆與女性位置較為親近,除非在特定的狀況下。女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女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管我們習而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