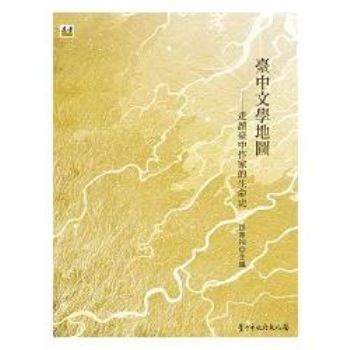走進故事的產房──楊逵與臺中的親密關係
楊翠/文
1906年,楊逵出生於臺南新化(大目降),1924年赴日留學,半工半讀,肉身恆常處於饑餓,精神卻是亢奮貪食。然而,1927年,島內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來自「臺灣文化協會」主幹連溫卿的催告、「臺灣農民組合」同志的促請,不斷呼喚著青年楊逵返鄉。
楊逵覺識到:「同樣是『運動』,在自己家鄉工作才有意義。」決定輟學返鄉,投身運動。1920年代風起雲湧的運動風潮中,大臺中州是核心場域,青年楊逵因而與臺中結了緣。這一結緣,就是五十年,他把雙腳深深踩進城市地景中,以自己的肉身實踐,為城市地圖增添動人的色澤。
楊逵與臺中城市初相識,在今日的柳川與中正路交接處,昔日初音町的「樂舞臺」。1927年歲末,「臺灣農民組合」在這裡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八方風雨會中州,揭開農民運動的全盛時期,青年楊逵在大會中鋒芒畢露,也在這座城市銘刻下他的第一個實踐地點。
1934年,楊逵歷經日本政府的打壓,失去運動舞臺,與妻子葉陶結婚前後,輾轉流徙彰化、臺南、高雄,窮苦度日,借貸為生;然而,同一年,他的成名作〈送報伕〉(〈新聞配達夫〉)獲得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成為首位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運動者楊逵淡出,文學家楊逵誕生。此後,楊逵即使拖著貧病交迫的瘦弱身軀,仍然堅持在現實苦海的縫隙裡,維繫著文學的火種。同年,「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楊逵獲聘為日文版主編,深耕文學田園,從高雄遷居彰化,1935年,移居臺中,此後長年定居臺中。
從1935年定居,到1985年辭世,整整五十年,楊逵的戶籍都在臺中,他的生命年輪也鐫寫在臺中。期間,除了白色恐怖繫獄十二年,被迫遠離家園之外,楊逵的生命足履深深嵌入這塊土地,戰前戰後他的文學作品也大多在這裡產出,他的孩子們在這裡出生,最後,1985年春天,他也在此告別人間。對他而言,臺中城市,既是具體生活空間,也是社會運動與文化實踐場域,更是文學的豐饒產房。臺灣文學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首陽農園」、「一陽農園」、「東海花園」,都是楊逵與臺中親密關係的空間見證。循著楊逵的城市行腳,我們所覽閱的,既是一張城市空間地圖,也是一卷臺灣的記憶之書。青年楊逵落居臺中之後,第一個地點是梅枝町,現在的原子街、中正路、五權路、太平路一帶,他在這裡輾轉搬了幾次家,首先在梅枝町7番地落腳,其後又短暫租住53番地一家民宅二樓,也曾住過後龍仔齋堂一帶。1935年,楊逵離開《臺灣文藝》,另起爐灶,創辦《臺灣新文學》月刊,總計發行一年半,十五期,以及兩期《新文學月報》,這分深具歷史意義的文學雜誌,就發生在這些地點。
遷徙數次,楊逵在臺中第一個較穩定的生活地點,在今日東興市場、五權國中左近,日治時期的梅枝町99番地。1937年,楊逵罹患肺結核,貧病交迫,生活無以為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慷慨濟助,楊逵租賃此地,開闢「首陽農園」。農園入口處是火葬場,天天有人運送屍體進來,生命最終殘餘的氣味,以及周旁豬舍的氣味,混雜成一座豐饒產房,楊逵生活在此,積極生產故事文本。
誕生在首陽農園中的故事,不僅止於文字。1938年,遠方,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島內厲行皇民化,入田春彥同情臺灣人處境,深感精神苦悶,又被舉發「思想有問題」,將被遣返日本,他選擇在臺中市內自殺,留下遺書,說:「這是戰鬥。請不要認為我窩囊。」後事交代楊逵辦理。入田死後,好幾日,在曾經有著入田身影與宏聲的首陽農園,一直都很向陽堅毅的楊逵,寂寞守望摯友的純潔靈魂。
文友口中有著一匹狼、孤鳥性格的楊逵,與一名純摯的日本人性命相交、靈魂相照,因為威權體制陣營中存在著自省者,這段跨越日/臺、統治/被統治的知音故事,就這樣鐫入臺中城市地層深處。
楊翠/文
1906年,楊逵出生於臺南新化(大目降),1924年赴日留學,半工半讀,肉身恆常處於饑餓,精神卻是亢奮貪食。然而,1927年,島內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來自「臺灣文化協會」主幹連溫卿的催告、「臺灣農民組合」同志的促請,不斷呼喚著青年楊逵返鄉。
楊逵覺識到:「同樣是『運動』,在自己家鄉工作才有意義。」決定輟學返鄉,投身運動。1920年代風起雲湧的運動風潮中,大臺中州是核心場域,青年楊逵因而與臺中結了緣。這一結緣,就是五十年,他把雙腳深深踩進城市地景中,以自己的肉身實踐,為城市地圖增添動人的色澤。
楊逵與臺中城市初相識,在今日的柳川與中正路交接處,昔日初音町的「樂舞臺」。1927年歲末,「臺灣農民組合」在這裡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八方風雨會中州,揭開農民運動的全盛時期,青年楊逵在大會中鋒芒畢露,也在這座城市銘刻下他的第一個實踐地點。
1934年,楊逵歷經日本政府的打壓,失去運動舞臺,與妻子葉陶結婚前後,輾轉流徙彰化、臺南、高雄,窮苦度日,借貸為生;然而,同一年,他的成名作〈送報伕〉(〈新聞配達夫〉)獲得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成為首位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運動者楊逵淡出,文學家楊逵誕生。此後,楊逵即使拖著貧病交迫的瘦弱身軀,仍然堅持在現實苦海的縫隙裡,維繫著文學的火種。同年,「臺灣文藝聯盟」成立,楊逵獲聘為日文版主編,深耕文學田園,從高雄遷居彰化,1935年,移居臺中,此後長年定居臺中。
從1935年定居,到1985年辭世,整整五十年,楊逵的戶籍都在臺中,他的生命年輪也鐫寫在臺中。期間,除了白色恐怖繫獄十二年,被迫遠離家園之外,楊逵的生命足履深深嵌入這塊土地,戰前戰後他的文學作品也大多在這裡產出,他的孩子們在這裡出生,最後,1985年春天,他也在此告別人間。對他而言,臺中城市,既是具體生活空間,也是社會運動與文化實踐場域,更是文學的豐饒產房。臺灣文學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首陽農園」、「一陽農園」、「東海花園」,都是楊逵與臺中親密關係的空間見證。循著楊逵的城市行腳,我們所覽閱的,既是一張城市空間地圖,也是一卷臺灣的記憶之書。青年楊逵落居臺中之後,第一個地點是梅枝町,現在的原子街、中正路、五權路、太平路一帶,他在這裡輾轉搬了幾次家,首先在梅枝町7番地落腳,其後又短暫租住53番地一家民宅二樓,也曾住過後龍仔齋堂一帶。1935年,楊逵離開《臺灣文藝》,另起爐灶,創辦《臺灣新文學》月刊,總計發行一年半,十五期,以及兩期《新文學月報》,這分深具歷史意義的文學雜誌,就發生在這些地點。
遷徙數次,楊逵在臺中第一個較穩定的生活地點,在今日東興市場、五權國中左近,日治時期的梅枝町99番地。1937年,楊逵罹患肺結核,貧病交迫,生活無以為繼,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慷慨濟助,楊逵租賃此地,開闢「首陽農園」。農園入口處是火葬場,天天有人運送屍體進來,生命最終殘餘的氣味,以及周旁豬舍的氣味,混雜成一座豐饒產房,楊逵生活在此,積極生產故事文本。
誕生在首陽農園中的故事,不僅止於文字。1938年,遠方,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島內厲行皇民化,入田春彥同情臺灣人處境,深感精神苦悶,又被舉發「思想有問題」,將被遣返日本,他選擇在臺中市內自殺,留下遺書,說:「這是戰鬥。請不要認為我窩囊。」後事交代楊逵辦理。入田死後,好幾日,在曾經有著入田身影與宏聲的首陽農園,一直都很向陽堅毅的楊逵,寂寞守望摯友的純潔靈魂。
文友口中有著一匹狼、孤鳥性格的楊逵,與一名純摯的日本人性命相交、靈魂相照,因為威權體制陣營中存在著自省者,這段跨越日/臺、統治/被統治的知音故事,就這樣鐫入臺中城市地層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