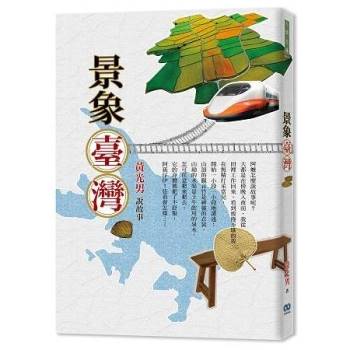試閱壹:
大貝湖的故事
龍母吐珠
順水而潔
逐光而行
帶來了人間福分吉祥
阿孫仔伊
講古囉……
離家已有卅年了,再回到高雄確實可以感受近鄉情怯的情愫。
我已沒有迫不及待尋找親人的心思,也沒有過多的滄桑感,至少在社會丕變之下,人的情感似乎也消散不少,何況至親已離世,兄弟家人四散各地,已無法再敘過往親情,甚至都在預期何日何時才能相聚,有時候只能在幻象中的夢境吚唔幾聲。
倒不是年老情薄,而是現世實境讓人在行動中搖晃不定,是個失去回家方向的杌隉。
在這種情況之下,內心所盼望的家仍然在遠遠呼喚,恰似親人在招手,至親在愛的呢喃中,喚使我伸手銜接那份久已逝去的記憶而能夠再尋求蛛絲馬跡,則是孩童時期阿嬤叮嚀化為故事的神祕力道,或者說阿嬤喜歡用他從廟口或耆老所傳誦的民間故事作為策勵貧窮兒孫的教材,也許也可以說祖先口耳相傳的庭訓,更不同於說教似的教育。
我生長在一個貧窮又封閉的農村中,沒有較多的學習環境,或得到較多的資訊,能夠模仿的都是親人的耳提面命,以及用眼睛多看些他人的行為模式。在這種極度閉塞的環境裡,除了整天為三餐求溫飽而奔波外,能活下來已經不簡單,遑論有餘力求學。因此孩童時期的我,想要得到較多的知識,除了到廟口或一些雜貨店的暫短聽聞為進學外,大多是老人在「有耳無口」的氛圍下,一點一滴學習。
當然,父母不認得字,又忙於農事,沒能教些幼學應知道的事,有關村舍舊聞,或是鄉里傳說,都由還在綁小腳的阿嬤傳述,應該說阿嬤講古,是我最興奮的事,雖然在阿嬤講故事前,必須幫她老人家解開小孩子都說好臭的裹腳布,阿嬤一面舒解腳踝一面說:「阿孫仔伊!你知道嗎?孝順的孩子將來才有做大官的機會!」做大官是天方夜譚,我期待的是阿嬤說故事有神蹟乍現的希望,以一種莫名的喜悅作為「求生過程」中的動力。
阿嬤怎麼說故事呢?大都是在傍晚入夜前,我從田裡工作回來,看到疲倦不堪的我在無精打采當兒,開始一小段一小段地講述,有時已講過好幾遍的內容,卻是興味盎然。
好比阿嬤說:後山長滿菅芒花草的高崗叢山,是被臭頭洪武君殺掉止餓的水牛所化身,每當地動(震)時,就表示祂正在翻身,或者是村民不夠尊重祂,有引人注意的動機!
「真的這麼神奇嗎?那麼山崖土崩石落,隆隆聲是不是祂生氣了」我問。
「應該是吧!好多人提著食物水果向山頭焚香膜拜,就是祈求大家平安」。
阿嬤進一步說,山頂的觀音竹是神靈的衣裳,山坳的水渠是土牛飲用的泉水,怎可任意耙來耙去,祂的身體被耙了不舒服,阿孫仔伊!恁看會怎樣。
語調通暢正經十足地告誡我們不可任意在土山上亂動土,否則牛神常翻身,我們村民就不得安寧了。
說得也是,地震是因為有這樣的神話照應,使我們鄉親不敢隨意在這座山種地瓜或桑麻,因為山崩地裂時小徑封閉,石礫崩裂的困境是很難在一、二天修好原貌,以利農業生產。「還有嗎?阿嬤,請您再說說有土牛山,是不是還有什麼神奇的故事呢?」「有啊!乖乖地把番薯菜(地瓜葉)剁剁吔」,阿嬤一面編竹簍子一面說話的神情令人期待,不知是一種求知的渴望,還是小孩子都喜歡聽故事,尤其在窮鄉僻壤的山腳下,能夠得到一些農事之外的消息就是天大的喜悅。
以最快方式將父母交代的工作完成,就快速窩在阿嬤的房間,等待以搜奇探究的心情等阿嬤開口。
阿嬤指著坡崁後的「黑石山」說:「這座黑石山原本是黑寶石山。但現在都是墓葬地了,住在大貝湖的族人或古早的住民認為這是個寶地風水好,死去的人大都會葬在這裡!」接著說:「寶地必是神鬼必爭之地,壞人會變成鬼,好人會成為神」,提醒要做好人。
當然,這只是個開端,老人家接著說,這座山在夜晚時,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人看到點點閃光忽起忽滅,有人穿過林投小徑時,常看到白布飄零、還有……,我一面愛聽、一面摀耳,想到平日就害怕墓地「奉金缸」的白骨殘肢,總覺得鬼影幢幢,那能再聽阿嬤詳敘下去。
阿嬤卻沒有停止講述的樣子,雖然知道孫兒們已摀嘴閉眼,陷在死懼當中,但她老人家似乎有點講古心情的期許,這個期許挾在示教與神蹟之間,對她來說可能是項傳說文化的責任。
她望著灰濛的星空幽幽地說:「除了土牛山、黑石山之外,尚有金龜仔頭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故事,因為這些先人的墓葬地必是風水絕佳的選擇,叫做福地福人居。庇蔭後代是理所當然的。」她說就在黑石山到金龜仔頭島的水域上,平時湖水泛漣漪,水岸微波籠煙迷漫時,是「上林村」大碑人漁舟唱晚詩情畫意。若是七月風捲起水浪,都是千斤蓋頂的力量。村民有時為了稱便,硬在大風浪時搖槳撞浪回岸,實是件危險的事。有一次村裡有位叫「樹畢仔」的大叔平日就有冒險的習慣,某一天的颱風傍晚為了趕早回家,不顧別人的警告依然駕著竹筏乘風破浪由水路回家,不幸就被凶浪吞噬了。因為他不甘遭此橫禍,便化為厲鬼常在湖邊飄蕩尋找可替身的對象,其中是不諳游泳技術者,或不信邪的村民,一年之中在湖水滅頂的人總有一、二人。所以要小孩子不要晚歸,或有落單的機會,因為這個「樹畢仔」的鬼魂常遊走在湖岸四周,伺機尋找倒楣鬼。
阿嬤說著說著,看到我們縮成一團,乘機教導一些尊天守規的道理,她說:「人在做天在看,做好事神會保護,做邪事鬼魂附身」這一箴言,一直留存在我的心裡。
「乖孫仔!麥擱聽嘸?」要再聽故事,就得改天的閒暇時間,又得為阿嬤搥背打洗腳水,或是撞土豆粉(花生粉)給沒有牙齒的阿嬤食用……我樂意為阿嬤做一切的幫手,阿嬤的故事太引人興趣了。
在斷斷續續講故事的過程中,發現老人家講述的內容,來自廟埕的大戲(歌仔戲)或皮影戲、布袋戲演出的記憶,有些是口耳相傳的情節。例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神農嘗百草、土地公化身為蛇或為窮家老人來試積善人家的真實等等不一而足,更多的是民間傳說吧!
故事充滿著教化義涵,小孩子聽得津津有味,尤其故事就發生在居家旁邊,更覺得新奇有趣。阿嬤說:「大貝湖與湖邊四周圍有很多的故事,要不要聽?」「要!」一陣喧譁後,老人家說,湖的附近有覆鼎金的地方……(未完)
試閱貳:
回不了家
難得有閒,靜默在每天都得坐下來看書的椅上,一時呆呆地想起幾乎忘記的童年過往,哦!是想回家的衝動促發淡淡的憂愁,不為什麼!只是還有記憶,而且說模糊中漸漸清晰的家,竟然看見遠去的父母在門前招手,也沉默在相顧無言的共感上。
母親仍然穿著破舊的簑衣、帶著鋤頭準備到稻田除草。依稀聽到她和父親的談話:今天得一併把香瓜苗種好,以爭取早種早收成的機會。
是啊!看天田,若風調雨順,農時依序,趕早的作業是有利產品的收割,反之,一夜風雨來襲,終年辛苦的菜畦禾田都會化為烏有。
常常是前債未還,後借又來的窘態,父母親已不便出面向有錢人家借貸,只好由小孩倚門求援,常常弄得苦笑連連,依舊空空雙手回程;繼而由近而遠,狀似乞食者向富人求借。那情景不堪回首,否則如我七十歲老翁至今還會淚流滿面。
唯一的告白,包括父母親領進一間叫青雲宮的神農廟,頻頻舉香祈求神農能向玉皇大帝請求降福,使農作物豐收,家人健康。我跟上這個全家唯一可傾訴的神明,倒也相信心誠則靈的動作,我不知道「神」的階段,每當天不從人願時,村裡的人都會怪土地公,為何沒有向神農大帝轉請「天公」,明白眾多老百姓的卑微希望,例如:沒有好收成,是否也能再請小溪來些吳郭魚的成長,因為一根草一點露,若連滴水不下,青苗如何壯大。
母親說不抱怨父親急躁無助的咆哮,她知道大家都是為生活「討賺」,若不勤快什麼都不可能有收穫,何況心急有用嗎?至今我仍然聽到母親說「阿南啊!天運啦,你要努力啊!要快快長大賺錢,幫忙弟妹們成長」的話尾和期待。
於是在「賺錢」的意念下,我撿拾蝸牛、釣青蛙販賣,拾豬糞、牛糞作肥料、斷枝落葉為柴火,撿拾破爛換錢……沒有話說,只有承受母親傳給我此刻如故的心情,不覺又看到母親接受我賺的幾毛錢後雙眼含淚,想說卻沒說出的「這都是命啊!你是老大理當如此」的眼神,並且留下一毛錢給我作為獎勵。隨後又加了一句:「有儉才有底」,意指不得亂花錢。會嗎?節省下來的零用錢,不久又得提供為認命而必須的花費,例如:繳掉因藥包定期需要的開支。
父親是個性情剛烈的人,也是很機警而很有看法的人,他在村子上雖然是個窮困農夫,卻自學了樂器的製作與演奏,一面彈奏月琴,一面念念有詞在唱「孫臏下山」、有時候邊唱邊說「三國演義」。有人說是民間南管曲調的哼唱!有時候也會以「大管琴」和著嗩吶高音吹奏,這又是北管的,「福樂」樂嗎?我不明白父親到底怎樣學來的,印象中這些音樂是他工作之餘的娛樂,也是唯一不發脾氣的時候。
當然,在貧困時代,目不識丁的雙親與人互動往往是謙虛有加,態度極為卑微,尤其有求於別人,事實上常因斷炊在即,必須向鄰人借貸或賒米時那份表情,至今仍令我難忘。猶記母親提著一袋番薯簽勉強下鍋的表情,不知是淚水還是汗水,滿臉憂戚,向我說些叫人聽不懂的話,卻更加固我對家人的敬愛,即使失去生命亦得盡己之力。
這種日子不是一天二天計算,而是經年累月永遠看不到希望,卻還支撐著生存最後力氣的力量,那便是求神拜佛,也得扮笑臉向人打招呼。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暗自祈天拜地,如何改善生活困境,又如何能協助父母親把弟妹帶大呢?
沒有晨昏分野,也不知白天與晚上,工作或休息,凡能求得一份生機,怎能放過。我幾乎借月光接日光在田裡找生存的糧食,甚至除草鏟地之餘,知道泥鰍躲在哪裡,田螺何時長大,有時候小吳郭魚游來游去,也不能欣賞美姿而成為佐餐佳肴,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謝土地公,也謝謝神農大帝指示豬母菜、鳥莧可食用。但有幾次聽到小青蛙半夜呱呱叫時,卻不敢誘釣牠,據說牠向土地公抗議,因為正是牠們的產卵時,牠亦得有天地之靈啊!怎可造次。
鄉人都知道人造孽則殆的道理。聽天由命之餘,仍然抱著「天道酬勤」的意念,不管風雨肆虐、天災蟲害,只要盡心盡力必得福分。
經過一次次的天災,無數次的土地重劃,可以說苦盡甘不來,至少還存到現在。直接的感受好像被火紋身後的灼傷,蔓延在間接的病楚上,永遠驚慌心情。因此我緊張、嘶喊不及的意念,常常閉目求神賜福。結果是靈與不靈都忘記了。但那是一條連接生命存活的臍帶,在田埂邊土地神廟閃光。
除外,黑夜星空是指引回家的亮點,也是鬆解疲憊不堪慰藉,不知從哪時候起,這點亮光也消失在滿城燈光的妨礙干擾,那一份靜謐沉默的片刻,已如生命漸受積塵封閉的歲月,連殘夢碎片的記憶也漸退去。
只記得我尚在等待曙色再現山後的明亮,正是鄉野童伴召喚時刻。如夢醒般想起人在遙遠的臺北,怎有那份漸褪色的彩光,一時間沉默在惶惶不安的殘影晃動上酸鼻。我在等待什麼?是家嗎?還是以為走過厝頭就可以看見阿嬤碎步緩行的熟稔。
不知道如何尋找深烙印痕的田埂,以及摸黑回家的崁石坑路,雖然崎嶇險峻,家是臨時搭建的茅草屋,正被颱風摧毀,剩下的竹竿撐著土牆,比之山坡古墳地還脆弱的現場。但全家人都會圍在一起把可食用的東西填肚。這個既清空又貧困的當兒,我們都知道「家」的意義。家中有一盞微弱煤油燈,勉強提供可移動的方向,卻發現油量只剩一點點,趕緊吹熄它,好使明晚尚可維持天黑時一絲明亮。
我借著月光隱約透出課文來背讀,也堅持不可半途停止課業而允許蚊子嗡嗡飛舞吻身,在抓撓中我明白明天的功課尚能應付,雖然已是深夜眼皮沉重,但看到母親還在斬豬菜的影子就有種欲睡還醒的自覺:「窮鄉困里百姓同,何人可解眼前痛」的嗚咽。
擦擦臉倒頭睡在椅橑上。四周獰猙風影襲來,口中苦痛驚喊喔喔,半睡半醒惡夢中的惶恐似乎至今猶存,究竟是什麼惡魔纏身,還是社會現實糾纏。那是不滅的記憶、驚悚中求生。
說不完的故事,雖漸漸模糊,懸念「家」的安危卻隨時加重心情的紊亂,好想回家一趟,幫幫可能解除危害的方法,或能帶一星點的燈光給「家」的支撐,我願花盡所有,儘管自己受傷流血和童年除草割稻一樣卑微希望稻禾快長!
然而是在夢境中,還是塵埃滿留存身?日漸龜裂如土崩石碎的記憶,為何留存一道道遊絲纏臉,連接著「回家」思念的牽引心緒。抖動就痛,深入心扉,絞碎殘留家鄉的愛戀。
找不到「家」,物換星移?弱肉強食?原有的蒼茫竹篁不再,拾階而上的土石崁路消失!家人無力回望看漏屋,只在鄉音依舊人影稀,漸漸移除前塵記憶。我想回家,卻回不了家!(完)
試閱參:
颱風
五月的梅雨天氣,突然在午後傾盆大雨,淋得全身濕透透,有如兒時記憶中在颱風夜房屋被「吹」毀後的悽慘,冷得發抖,雙手合十祈求家安,幾乎無助哭喊的場景,只是誰又會及時伸出援手撐個傘來接應!心慌步緩,一拐一拐地按鈴回家門。
老妻沒發現力竭志衰的我正無精打采在傷神。啊!是人生的苦難來臨,還是自然界生命消長的必然,或是佛家說的生老病死的不安。都有吧!猶記年少遇荊棘的刺傷,只是抓一把泥土敷上就能自然止痛。而今只是大雨一場,濕衣裳,有何哀傷顧影的自憐,必要嗎?
冷靜是大風雨過後的選擇,對於天候異常是最近常被提起的事,又不是只在臺北發生大雨重擊,世界各地發生的八月雪、二月乾旱的超級異象,都使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徬徨,何況只有雨沒有風算得上什麼?若颱風交加人畜升天,遍地寂然聞腐臭,那才是人間煉獄吧!
至少我能想起兒時的風雨印象深刻,烙印心靈的是天災肆虐,生靈何辜?除了再三膜拜神明保安外,一切的一切重頭再來,雖然辛苦加倍,也不會怨天尤人,因為大家承受的困苦皆然,除了奮起重建工作,以求生機的改善。
猶記民國四十一年有個叫貝絲颱風橫掃高雄,據說是從港灣入境,也叫西北颱的風雨,直撲郊野農家。當時我們家客居在親戚一間柴房。竹頭立的廂房,原本就是土牆、茅草屋頂,建材羸弱,哪經得起使人一推就搖搖欲倒,或風雨沖洗變成籬笆野店的窘境。
那一夜強風暴雨肆虐,有如飛機轟炸、推土機剷地。我驚嚇在阿嬤懷裡哭泣,抖動得不知害怕還是寒冷難當。直到全身濕透,眼前一片狼藉的殘瓦斷梁全沒了,好像是個被剷平的荒地,只留下雙親、家人失神的憔悴。
事實上,大人們正在商討重建的工作,小孩則到處尋覓可食用的糧食,其中有二種被鎖定的對象,一是「風打筍」,拾起正成長卻被打斷的新篁竹,可以削下幼嫩部分燒炒食用;二是落難的斑鳩無處棲息,人們隨手一抓即入袋,當年沒有保護動物的觀念,牠們豈能逃過成為美味佳肴的命運。
當然這是窮壤農家求生的景象,包括滿地的豬母菜、地瓜葉在救急時被青睞,能活命的食物哪能被浪費。尤其颱風來臨時,呼天喚地,直喊土地公的法號,仍然無濟於事時,說大概不是天地不仁,而是人謀不臧,而再三祈求平安。
就是這個颱風改變了我們全家,親戚不允重建借住,父親以堅毅的精神到山上尋地築屋,縱然沒能過著較方便的生活,在環境極度困難下,我們活下來了。也撐過無家可歸的失落,再重建生活的意志。
年輕的時候,雖然知道颱風來臨的恐懼與破壞,損失不只是人民的財富,但都在心理上有個預防災害的方法,幾十年以來,都在年年難過,年年過的苦難中,建立了剛毅的心志,也集合了臺灣民眾的抗災力道,重估因颱風襲臺的各項損益表。
損傷的是農產品被摧毀並流失無影,即房舍倒塌所引發的人畜傷亡更不計其數。其中颱風過後的城貌鄉情,有如飛沙走石,天崩地裂的場景,君不見小林村一夜埋沒亡魂無數。這時的小老百姓呼天搶地又如何?但如我家在屋毀土流之後,過十年也無法恢復舊觀,至今留下片刻記憶「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堅忍中度過。
個人蒙受天災都知道防颱之道,但是不可抗拒的毀傷,並不是以有限的物質可以補救,尤其常忘了自己就是社會組織的一分子、自己就是國家時,動不動就要政府救濟,似乎一點防禦力量都沒有?遑論經國濟世。
就整體而言,颱風過境前後,必有防颱準備,也有損害評估,若不是過於嚴重,對於風大雨勢的吹襲,雖有損毀人之事件發生,但在有備無患的心理準備中,何有懼怕之憂?
倒是颱風名號是魔是俠的屬性,也讓人不置可否,加上「素靈」為戒,因為沒有風不來雨,沒有雨生靈望天。那麼待我們澄心閉目,思想颱風的種種行徑是否也有警鐘作用,例如:風來樹倒、屋毀固然令人生畏,但未倒又重生的樹林其姿態婀娜,其根深葉茂之風情,豈不比之風息搖曳舞樹梢的美妙;又如萬里晴空,千峰開霽,都在煙雲繞樹,狂風暴雨之後的寧靜。
俗語說:「風雨生信心」。臺灣自然環境風雨交加,卻是孕育萬物生命的資源,從農產品到森林、從養殖漁產到高科技育種、從草原花季到高山水果,都是自千錘百鍊後的存菁,它是甘霖,也是靈泉;而人文社會的共同信念則是萬眾一心,寶島臺灣的繁榮等等都來自逐水行舟溯風追影的過程。這個令人著迷的引力,就是每年有那麼多不同名字又是以外國女性命名的颱風造訪。至少給予臺灣一分鮮明的奮鬥力量,或說防禦的訊息如同煙雨瀰漫山澗,臺灣更美。
不論是颱風還是風颱,你是臺灣的記憶,也是臺灣的刻痕,無奈你的吹襲,你的進犯,卻也是因為你,臺灣人更堅強、更明亮,在你來臨前後,迎來送往之間的故事,陸續在增長,衍生了臺灣堅毅不拔的力量。
走筆至此,窗外一片濛濛,似殘夢中飛過的風速五十米,正在加強。(完)
大貝湖的故事
龍母吐珠
順水而潔
逐光而行
帶來了人間福分吉祥
阿孫仔伊
講古囉……
離家已有卅年了,再回到高雄確實可以感受近鄉情怯的情愫。
我已沒有迫不及待尋找親人的心思,也沒有過多的滄桑感,至少在社會丕變之下,人的情感似乎也消散不少,何況至親已離世,兄弟家人四散各地,已無法再敘過往親情,甚至都在預期何日何時才能相聚,有時候只能在幻象中的夢境吚唔幾聲。
倒不是年老情薄,而是現世實境讓人在行動中搖晃不定,是個失去回家方向的杌隉。
在這種情況之下,內心所盼望的家仍然在遠遠呼喚,恰似親人在招手,至親在愛的呢喃中,喚使我伸手銜接那份久已逝去的記憶而能夠再尋求蛛絲馬跡,則是孩童時期阿嬤叮嚀化為故事的神祕力道,或者說阿嬤喜歡用他從廟口或耆老所傳誦的民間故事作為策勵貧窮兒孫的教材,也許也可以說祖先口耳相傳的庭訓,更不同於說教似的教育。
我生長在一個貧窮又封閉的農村中,沒有較多的學習環境,或得到較多的資訊,能夠模仿的都是親人的耳提面命,以及用眼睛多看些他人的行為模式。在這種極度閉塞的環境裡,除了整天為三餐求溫飽而奔波外,能活下來已經不簡單,遑論有餘力求學。因此孩童時期的我,想要得到較多的知識,除了到廟口或一些雜貨店的暫短聽聞為進學外,大多是老人在「有耳無口」的氛圍下,一點一滴學習。
當然,父母不認得字,又忙於農事,沒能教些幼學應知道的事,有關村舍舊聞,或是鄉里傳說,都由還在綁小腳的阿嬤傳述,應該說阿嬤講古,是我最興奮的事,雖然在阿嬤講故事前,必須幫她老人家解開小孩子都說好臭的裹腳布,阿嬤一面舒解腳踝一面說:「阿孫仔伊!你知道嗎?孝順的孩子將來才有做大官的機會!」做大官是天方夜譚,我期待的是阿嬤說故事有神蹟乍現的希望,以一種莫名的喜悅作為「求生過程」中的動力。
阿嬤怎麼說故事呢?大都是在傍晚入夜前,我從田裡工作回來,看到疲倦不堪的我在無精打采當兒,開始一小段一小段地講述,有時已講過好幾遍的內容,卻是興味盎然。
好比阿嬤說:後山長滿菅芒花草的高崗叢山,是被臭頭洪武君殺掉止餓的水牛所化身,每當地動(震)時,就表示祂正在翻身,或者是村民不夠尊重祂,有引人注意的動機!
「真的這麼神奇嗎?那麼山崖土崩石落,隆隆聲是不是祂生氣了」我問。
「應該是吧!好多人提著食物水果向山頭焚香膜拜,就是祈求大家平安」。
阿嬤進一步說,山頂的觀音竹是神靈的衣裳,山坳的水渠是土牛飲用的泉水,怎可任意耙來耙去,祂的身體被耙了不舒服,阿孫仔伊!恁看會怎樣。
語調通暢正經十足地告誡我們不可任意在土山上亂動土,否則牛神常翻身,我們村民就不得安寧了。
說得也是,地震是因為有這樣的神話照應,使我們鄉親不敢隨意在這座山種地瓜或桑麻,因為山崩地裂時小徑封閉,石礫崩裂的困境是很難在一、二天修好原貌,以利農業生產。「還有嗎?阿嬤,請您再說說有土牛山,是不是還有什麼神奇的故事呢?」「有啊!乖乖地把番薯菜(地瓜葉)剁剁吔」,阿嬤一面編竹簍子一面說話的神情令人期待,不知是一種求知的渴望,還是小孩子都喜歡聽故事,尤其在窮鄉僻壤的山腳下,能夠得到一些農事之外的消息就是天大的喜悅。
以最快方式將父母交代的工作完成,就快速窩在阿嬤的房間,等待以搜奇探究的心情等阿嬤開口。
阿嬤指著坡崁後的「黑石山」說:「這座黑石山原本是黑寶石山。但現在都是墓葬地了,住在大貝湖的族人或古早的住民認為這是個寶地風水好,死去的人大都會葬在這裡!」接著說:「寶地必是神鬼必爭之地,壞人會變成鬼,好人會成為神」,提醒要做好人。
當然,這只是個開端,老人家接著說,這座山在夜晚時,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人看到點點閃光忽起忽滅,有人穿過林投小徑時,常看到白布飄零、還有……,我一面愛聽、一面摀耳,想到平日就害怕墓地「奉金缸」的白骨殘肢,總覺得鬼影幢幢,那能再聽阿嬤詳敘下去。
阿嬤卻沒有停止講述的樣子,雖然知道孫兒們已摀嘴閉眼,陷在死懼當中,但她老人家似乎有點講古心情的期許,這個期許挾在示教與神蹟之間,對她來說可能是項傳說文化的責任。
她望著灰濛的星空幽幽地說:「除了土牛山、黑石山之外,尚有金龜仔頭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故事,因為這些先人的墓葬地必是風水絕佳的選擇,叫做福地福人居。庇蔭後代是理所當然的。」她說就在黑石山到金龜仔頭島的水域上,平時湖水泛漣漪,水岸微波籠煙迷漫時,是「上林村」大碑人漁舟唱晚詩情畫意。若是七月風捲起水浪,都是千斤蓋頂的力量。村民有時為了稱便,硬在大風浪時搖槳撞浪回岸,實是件危險的事。有一次村裡有位叫「樹畢仔」的大叔平日就有冒險的習慣,某一天的颱風傍晚為了趕早回家,不顧別人的警告依然駕著竹筏乘風破浪由水路回家,不幸就被凶浪吞噬了。因為他不甘遭此橫禍,便化為厲鬼常在湖邊飄蕩尋找可替身的對象,其中是不諳游泳技術者,或不信邪的村民,一年之中在湖水滅頂的人總有一、二人。所以要小孩子不要晚歸,或有落單的機會,因為這個「樹畢仔」的鬼魂常遊走在湖岸四周,伺機尋找倒楣鬼。
阿嬤說著說著,看到我們縮成一團,乘機教導一些尊天守規的道理,她說:「人在做天在看,做好事神會保護,做邪事鬼魂附身」這一箴言,一直留存在我的心裡。
「乖孫仔!麥擱聽嘸?」要再聽故事,就得改天的閒暇時間,又得為阿嬤搥背打洗腳水,或是撞土豆粉(花生粉)給沒有牙齒的阿嬤食用……我樂意為阿嬤做一切的幫手,阿嬤的故事太引人興趣了。
在斷斷續續講故事的過程中,發現老人家講述的內容,來自廟埕的大戲(歌仔戲)或皮影戲、布袋戲演出的記憶,有些是口耳相傳的情節。例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神農嘗百草、土地公化身為蛇或為窮家老人來試積善人家的真實等等不一而足,更多的是民間傳說吧!
故事充滿著教化義涵,小孩子聽得津津有味,尤其故事就發生在居家旁邊,更覺得新奇有趣。阿嬤說:「大貝湖與湖邊四周圍有很多的故事,要不要聽?」「要!」一陣喧譁後,老人家說,湖的附近有覆鼎金的地方……(未完)
試閱貳:
回不了家
難得有閒,靜默在每天都得坐下來看書的椅上,一時呆呆地想起幾乎忘記的童年過往,哦!是想回家的衝動促發淡淡的憂愁,不為什麼!只是還有記憶,而且說模糊中漸漸清晰的家,竟然看見遠去的父母在門前招手,也沉默在相顧無言的共感上。
母親仍然穿著破舊的簑衣、帶著鋤頭準備到稻田除草。依稀聽到她和父親的談話:今天得一併把香瓜苗種好,以爭取早種早收成的機會。
是啊!看天田,若風調雨順,農時依序,趕早的作業是有利產品的收割,反之,一夜風雨來襲,終年辛苦的菜畦禾田都會化為烏有。
常常是前債未還,後借又來的窘態,父母親已不便出面向有錢人家借貸,只好由小孩倚門求援,常常弄得苦笑連連,依舊空空雙手回程;繼而由近而遠,狀似乞食者向富人求借。那情景不堪回首,否則如我七十歲老翁至今還會淚流滿面。
唯一的告白,包括父母親領進一間叫青雲宮的神農廟,頻頻舉香祈求神農能向玉皇大帝請求降福,使農作物豐收,家人健康。我跟上這個全家唯一可傾訴的神明,倒也相信心誠則靈的動作,我不知道「神」的階段,每當天不從人願時,村裡的人都會怪土地公,為何沒有向神農大帝轉請「天公」,明白眾多老百姓的卑微希望,例如:沒有好收成,是否也能再請小溪來些吳郭魚的成長,因為一根草一點露,若連滴水不下,青苗如何壯大。
母親說不抱怨父親急躁無助的咆哮,她知道大家都是為生活「討賺」,若不勤快什麼都不可能有收穫,何況心急有用嗎?至今我仍然聽到母親說「阿南啊!天運啦,你要努力啊!要快快長大賺錢,幫忙弟妹們成長」的話尾和期待。
於是在「賺錢」的意念下,我撿拾蝸牛、釣青蛙販賣,拾豬糞、牛糞作肥料、斷枝落葉為柴火,撿拾破爛換錢……沒有話說,只有承受母親傳給我此刻如故的心情,不覺又看到母親接受我賺的幾毛錢後雙眼含淚,想說卻沒說出的「這都是命啊!你是老大理當如此」的眼神,並且留下一毛錢給我作為獎勵。隨後又加了一句:「有儉才有底」,意指不得亂花錢。會嗎?節省下來的零用錢,不久又得提供為認命而必須的花費,例如:繳掉因藥包定期需要的開支。
父親是個性情剛烈的人,也是很機警而很有看法的人,他在村子上雖然是個窮困農夫,卻自學了樂器的製作與演奏,一面彈奏月琴,一面念念有詞在唱「孫臏下山」、有時候邊唱邊說「三國演義」。有人說是民間南管曲調的哼唱!有時候也會以「大管琴」和著嗩吶高音吹奏,這又是北管的,「福樂」樂嗎?我不明白父親到底怎樣學來的,印象中這些音樂是他工作之餘的娛樂,也是唯一不發脾氣的時候。
當然,在貧困時代,目不識丁的雙親與人互動往往是謙虛有加,態度極為卑微,尤其有求於別人,事實上常因斷炊在即,必須向鄰人借貸或賒米時那份表情,至今仍令我難忘。猶記母親提著一袋番薯簽勉強下鍋的表情,不知是淚水還是汗水,滿臉憂戚,向我說些叫人聽不懂的話,卻更加固我對家人的敬愛,即使失去生命亦得盡己之力。
這種日子不是一天二天計算,而是經年累月永遠看不到希望,卻還支撐著生存最後力氣的力量,那便是求神拜佛,也得扮笑臉向人打招呼。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暗自祈天拜地,如何改善生活困境,又如何能協助父母親把弟妹帶大呢?
沒有晨昏分野,也不知白天與晚上,工作或休息,凡能求得一份生機,怎能放過。我幾乎借月光接日光在田裡找生存的糧食,甚至除草鏟地之餘,知道泥鰍躲在哪裡,田螺何時長大,有時候小吳郭魚游來游去,也不能欣賞美姿而成為佐餐佳肴,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謝土地公,也謝謝神農大帝指示豬母菜、鳥莧可食用。但有幾次聽到小青蛙半夜呱呱叫時,卻不敢誘釣牠,據說牠向土地公抗議,因為正是牠們的產卵時,牠亦得有天地之靈啊!怎可造次。
鄉人都知道人造孽則殆的道理。聽天由命之餘,仍然抱著「天道酬勤」的意念,不管風雨肆虐、天災蟲害,只要盡心盡力必得福分。
經過一次次的天災,無數次的土地重劃,可以說苦盡甘不來,至少還存到現在。直接的感受好像被火紋身後的灼傷,蔓延在間接的病楚上,永遠驚慌心情。因此我緊張、嘶喊不及的意念,常常閉目求神賜福。結果是靈與不靈都忘記了。但那是一條連接生命存活的臍帶,在田埂邊土地神廟閃光。
除外,黑夜星空是指引回家的亮點,也是鬆解疲憊不堪慰藉,不知從哪時候起,這點亮光也消失在滿城燈光的妨礙干擾,那一份靜謐沉默的片刻,已如生命漸受積塵封閉的歲月,連殘夢碎片的記憶也漸退去。
只記得我尚在等待曙色再現山後的明亮,正是鄉野童伴召喚時刻。如夢醒般想起人在遙遠的臺北,怎有那份漸褪色的彩光,一時間沉默在惶惶不安的殘影晃動上酸鼻。我在等待什麼?是家嗎?還是以為走過厝頭就可以看見阿嬤碎步緩行的熟稔。
不知道如何尋找深烙印痕的田埂,以及摸黑回家的崁石坑路,雖然崎嶇險峻,家是臨時搭建的茅草屋,正被颱風摧毀,剩下的竹竿撐著土牆,比之山坡古墳地還脆弱的現場。但全家人都會圍在一起把可食用的東西填肚。這個既清空又貧困的當兒,我們都知道「家」的意義。家中有一盞微弱煤油燈,勉強提供可移動的方向,卻發現油量只剩一點點,趕緊吹熄它,好使明晚尚可維持天黑時一絲明亮。
我借著月光隱約透出課文來背讀,也堅持不可半途停止課業而允許蚊子嗡嗡飛舞吻身,在抓撓中我明白明天的功課尚能應付,雖然已是深夜眼皮沉重,但看到母親還在斬豬菜的影子就有種欲睡還醒的自覺:「窮鄉困里百姓同,何人可解眼前痛」的嗚咽。
擦擦臉倒頭睡在椅橑上。四周獰猙風影襲來,口中苦痛驚喊喔喔,半睡半醒惡夢中的惶恐似乎至今猶存,究竟是什麼惡魔纏身,還是社會現實糾纏。那是不滅的記憶、驚悚中求生。
說不完的故事,雖漸漸模糊,懸念「家」的安危卻隨時加重心情的紊亂,好想回家一趟,幫幫可能解除危害的方法,或能帶一星點的燈光給「家」的支撐,我願花盡所有,儘管自己受傷流血和童年除草割稻一樣卑微希望稻禾快長!
然而是在夢境中,還是塵埃滿留存身?日漸龜裂如土崩石碎的記憶,為何留存一道道遊絲纏臉,連接著「回家」思念的牽引心緒。抖動就痛,深入心扉,絞碎殘留家鄉的愛戀。
找不到「家」,物換星移?弱肉強食?原有的蒼茫竹篁不再,拾階而上的土石崁路消失!家人無力回望看漏屋,只在鄉音依舊人影稀,漸漸移除前塵記憶。我想回家,卻回不了家!(完)
試閱參:
颱風
五月的梅雨天氣,突然在午後傾盆大雨,淋得全身濕透透,有如兒時記憶中在颱風夜房屋被「吹」毀後的悽慘,冷得發抖,雙手合十祈求家安,幾乎無助哭喊的場景,只是誰又會及時伸出援手撐個傘來接應!心慌步緩,一拐一拐地按鈴回家門。
老妻沒發現力竭志衰的我正無精打采在傷神。啊!是人生的苦難來臨,還是自然界生命消長的必然,或是佛家說的生老病死的不安。都有吧!猶記年少遇荊棘的刺傷,只是抓一把泥土敷上就能自然止痛。而今只是大雨一場,濕衣裳,有何哀傷顧影的自憐,必要嗎?
冷靜是大風雨過後的選擇,對於天候異常是最近常被提起的事,又不是只在臺北發生大雨重擊,世界各地發生的八月雪、二月乾旱的超級異象,都使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徬徨,何況只有雨沒有風算得上什麼?若颱風交加人畜升天,遍地寂然聞腐臭,那才是人間煉獄吧!
至少我能想起兒時的風雨印象深刻,烙印心靈的是天災肆虐,生靈何辜?除了再三膜拜神明保安外,一切的一切重頭再來,雖然辛苦加倍,也不會怨天尤人,因為大家承受的困苦皆然,除了奮起重建工作,以求生機的改善。
猶記民國四十一年有個叫貝絲颱風橫掃高雄,據說是從港灣入境,也叫西北颱的風雨,直撲郊野農家。當時我們家客居在親戚一間柴房。竹頭立的廂房,原本就是土牆、茅草屋頂,建材羸弱,哪經得起使人一推就搖搖欲倒,或風雨沖洗變成籬笆野店的窘境。
那一夜強風暴雨肆虐,有如飛機轟炸、推土機剷地。我驚嚇在阿嬤懷裡哭泣,抖動得不知害怕還是寒冷難當。直到全身濕透,眼前一片狼藉的殘瓦斷梁全沒了,好像是個被剷平的荒地,只留下雙親、家人失神的憔悴。
事實上,大人們正在商討重建的工作,小孩則到處尋覓可食用的糧食,其中有二種被鎖定的對象,一是「風打筍」,拾起正成長卻被打斷的新篁竹,可以削下幼嫩部分燒炒食用;二是落難的斑鳩無處棲息,人們隨手一抓即入袋,當年沒有保護動物的觀念,牠們豈能逃過成為美味佳肴的命運。
當然這是窮壤農家求生的景象,包括滿地的豬母菜、地瓜葉在救急時被青睞,能活命的食物哪能被浪費。尤其颱風來臨時,呼天喚地,直喊土地公的法號,仍然無濟於事時,說大概不是天地不仁,而是人謀不臧,而再三祈求平安。
就是這個颱風改變了我們全家,親戚不允重建借住,父親以堅毅的精神到山上尋地築屋,縱然沒能過著較方便的生活,在環境極度困難下,我們活下來了。也撐過無家可歸的失落,再重建生活的意志。
年輕的時候,雖然知道颱風來臨的恐懼與破壞,損失不只是人民的財富,但都在心理上有個預防災害的方法,幾十年以來,都在年年難過,年年過的苦難中,建立了剛毅的心志,也集合了臺灣民眾的抗災力道,重估因颱風襲臺的各項損益表。
損傷的是農產品被摧毀並流失無影,即房舍倒塌所引發的人畜傷亡更不計其數。其中颱風過後的城貌鄉情,有如飛沙走石,天崩地裂的場景,君不見小林村一夜埋沒亡魂無數。這時的小老百姓呼天搶地又如何?但如我家在屋毀土流之後,過十年也無法恢復舊觀,至今留下片刻記憶「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堅忍中度過。
個人蒙受天災都知道防颱之道,但是不可抗拒的毀傷,並不是以有限的物質可以補救,尤其常忘了自己就是社會組織的一分子、自己就是國家時,動不動就要政府救濟,似乎一點防禦力量都沒有?遑論經國濟世。
就整體而言,颱風過境前後,必有防颱準備,也有損害評估,若不是過於嚴重,對於風大雨勢的吹襲,雖有損毀人之事件發生,但在有備無患的心理準備中,何有懼怕之憂?
倒是颱風名號是魔是俠的屬性,也讓人不置可否,加上「素靈」為戒,因為沒有風不來雨,沒有雨生靈望天。那麼待我們澄心閉目,思想颱風的種種行徑是否也有警鐘作用,例如:風來樹倒、屋毀固然令人生畏,但未倒又重生的樹林其姿態婀娜,其根深葉茂之風情,豈不比之風息搖曳舞樹梢的美妙;又如萬里晴空,千峰開霽,都在煙雲繞樹,狂風暴雨之後的寧靜。
俗語說:「風雨生信心」。臺灣自然環境風雨交加,卻是孕育萬物生命的資源,從農產品到森林、從養殖漁產到高科技育種、從草原花季到高山水果,都是自千錘百鍊後的存菁,它是甘霖,也是靈泉;而人文社會的共同信念則是萬眾一心,寶島臺灣的繁榮等等都來自逐水行舟溯風追影的過程。這個令人著迷的引力,就是每年有那麼多不同名字又是以外國女性命名的颱風造訪。至少給予臺灣一分鮮明的奮鬥力量,或說防禦的訊息如同煙雨瀰漫山澗,臺灣更美。
不論是颱風還是風颱,你是臺灣的記憶,也是臺灣的刻痕,無奈你的吹襲,你的進犯,卻也是因為你,臺灣人更堅強、更明亮,在你來臨前後,迎來送往之間的故事,陸續在增長,衍生了臺灣堅毅不拔的力量。
走筆至此,窗外一片濛濛,似殘夢中飛過的風速五十米,正在加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