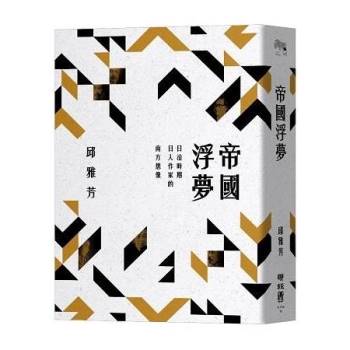南方與蠻荒:中村地平的《臺灣小說集》
一、南方的旅行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村地平如願從日本渡海來到臺灣讀書。這段青春時期的臺灣經驗,無疑為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他在一九四一年所出版的隨筆評論集《工作桌》,有兩篇文章〈往南方的船〉、〈三等船客〉,談到初次赴臺的青澀心情。〈往南方的船〉是描寫作者十八歲那年,要從故鄉前往門司搭船往臺的經過,除了沿途的瑣碎情節之外,也述說了作者出發前忐忑不安的心情。不過,這篇散文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它細膩地傳達出親情的強度。儘管父母極力支持中村的決定,然而隨著啟程日期的漸近,關於自己單獨旅行這件事,還是讓他萌生極大的危機感:「去臺灣的話,說不定我會罹患瘧疾而死。這樣的話,去好嗎?」對於日本人來說,早期來臺的旅遊活動確實帶有「探險」的意味,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以降,臺灣已經逐漸邁向現代化,到臺灣的冒險活動也轉向較具娛樂的觀光性質,這誠然和殖民政權的穩定有密切關聯。但是,其實一般日本國民普遍對臺灣缺乏知識,甚至存有負面的蠻荒印象。父親對兒子的遠行看似信心滿滿,內心卻是忐忑不安,而兒子也為即將離別而心慌,只是兩個男人都壓抑情感。但是,在中村即將出發前,父親向他表示要親自送行到門司。這番舉動,是為了安撫中村神經緊繃的情緒,也是父親的體貼。
父子兩人從故鄉宮崎坐汽車到門司,然後在客棧過夜等待隔天的船期。在用完晚餐的時刻,鄰室的一位房客突然來拜訪他們。這一位客氣的老人,也是要搭船前往臺灣,因此過來打聲招呼。當彼此開始閒聊之後,才發現老先生是因為兒子在臺灣病死,所以此行是要去接回他的骨灰。作者的父親在聆聽之際,神情似乎顯得相當狼狽。在老人告辭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建議,如果想打退堂鼓也無所謂,就再一起回家吧。少年的自尊心,讓他隱忍住內心強烈想和父親回頭的渴望。隔天早晨,他們坐上小艇去轉搭輪船,這也是送行的最後一程。登上大船之後,距離啟航還有一些時間。神經衰弱的中村,這時身體狀況開始出現不適。父親急忙為他安排座位、買飲料解熱,並細心叮嚀他在臺灣可以去洗溫泉來保養身體,學校放長假時也可以返鄉……。忽然,開船的信號響起了。當父親再度坐上小艇返回碼頭時,作者企圖透過小小的船窗搜索父親的身影。然而小艇上擠滿了送行人,隨著漸行漸遠,他再也分不清誰的臉。回到座位躺下後,他的眼睛彷彿一直在追尋父親的背影。
原本嚴厲的父親,在這裡卻展現了異於往常的柔軟身段。父親的愛子之情,隨著〈往南方的船〉的文字不斷地滲透出來。中村地平在文中提到是佐藤春夫的文學讓他對南方產生強烈的憧憬,但是透過書寫的脈絡不難看出他對南方/臺灣還是存有疑慮。對於來自文明世界的旅人而言,亞熱帶縱使風情萬種,卻也難抵風土疾病的威脅。青澀少年的中村,當時即有神經衰弱的傾向。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他的步伐顯得有些躊躇。中村在另一篇隨筆〈三等船客〉,描寫了上船後的際遇。〈三等船客〉可說是〈往南方的船〉的續篇,作者在開頭延續了〈往南方的船〉結束時的感傷筆調。誠然,在前往臺灣的船上,他的寂寞與不安是強烈的。幸運的是,一位同船的年輕女性適時對他伸出友誼之手。而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他竟然在船上遇到一位同鄉。與這些人的邂逅,彷彿是在預言他的臺灣之行還是受到祝福的。
不過,臺灣風土的疾病意象,顯然讓中村印象深刻。收進《臺灣小說集》的短篇小說〈在旅途中〉,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的《行動》,屬於中村早期的創作,是一篇帶有淒美情調的作品。這篇小說的女主角「俊」,最後就是因為感染熱病而死於臺灣。〈在旅途中〉的情節是描寫主角分別在兩次的旅途中,與「俊」短暫交會的情分。主角當時是一位臺北高等學校的日籍學生,可說是作者以自己為形象而塑造的人物。根據岡林稔的研究指出,日本文壇在明治末到大正時期,自然主義小說的創作技巧成為文學青年邁向作家之路的指標。當時許多知名作家在作品中將私人生活以藝術的告白的手法,對中村這些新生代作家是具有相當魅力的。其實在佐藤春夫的臺灣相關作品,就能輕易看到這種表現方式。而中村地平在《臺灣小說集》中,也有多篇作品以此技巧展現。〈在旅途中〉是主角對青春的追憶,其中也包含了他對「俊」的淡淡情愫。縱使如今已無法記起「俊」的真切容貌,但她的白皙身影與執著性格卻是他難以忘懷的。主角回想起與「俊」的初次會面,是某年夏天和友人牧一起到九州健行途中所認識的。「俊」當時在一個鄉村小鎮當小學老師,由於她和牧有親戚關係,所以計畫途經她的小學時叨擾住宿。不料學校當天有青年團的活動,於是「俊」轉而招待他們到旅館過夜。晚上三人聚在房間閒聊,就著窗口穿拂進來的涼風,主角感覺自己似乎被「俊」的浴衣飄散過來的香味所包圍住了。顯然主角對「俊」是頗有好感,然而他只是一位旅人,兩人的緣分或許是短暫的吧。怎知那年秋天,主角竟然在臺北的東門市場裡瞥見「俊」的熟悉身影。向友人查證後才知道她已嫁到臺灣的嘉義,這也開啟了他們在臺灣交會的契機。
隔年寒假沒有回鄉的主角,計畫一個人沿臺灣的西海岸旅行。在旅行途中來到嘉義,他決定順道拜訪「俊」。在尋訪「俊」的住處時,主角獨自走在本島人的街道上,由於種族的隔離性在這種鄉下更加明顯,他不僅受到異樣的眼光,骯髒汙穢的巷弄也讓他寸步難行。彷彿置身在奇異的時空,強烈的疲憊與不安在找到「俊」後才稍稍平息。兩人在異鄉重逢是值得喜悅的,然而主角也察覺到她在此地的處境是落寞的。縱使有丈夫的陪伴,但在日本人稀少的嘉義鄉下,「俊」終須長期忍受孤獨的煎熬。主角和他們夫妻分手之後,「俊」的故事卻還未告一段落。半年後,主角意外接到「俊」感染瘧疾而死亡的通知。「俊」的人生旅途,就在臺灣劃下句點。不難發現小說裡所選擇的場景都「在旅途中」,如果人生是一場漫長的旅程,那麼主角和「俊」的交會只是沿途的短暫景點吧。
依循線性時間的進行,〈在旅途中〉呈現了相互對照的世界;兩趟旅途,兩個地理,兩種人生。死後安息在嘉義的「俊」,生前在她的心目中,臺灣占有多少分量,讀者無從得知。曾向主角自白要採取獨身主義的「俊」,為什麼突然結婚,作者也沒有多加說明。因為「俊」的先生抱定海外雄飛的壯志,立志要往南方發展,所以她才會追隨而來到臺灣。但是置身在臺灣鄉下的「俊」,不僅要適應粗俗惡劣的環境,還要忍受孤獨與寂寥的心情。而主角在兩次旅途中和「俊」交會所激起的火花,最終也映襯了人間的無奈與蒼涼。「俊」如果沒有來臺灣,必定會有不同的人生。臺灣最終成了「俊」長眠的所在,她的死亡似乎是在叩問:「前往南方的可行性?」
然而青春的早逝,也籠罩著一種絕美情調。在死亡的恐懼意象之外,極有可能轉喻為浪漫的想像。在日本與臺灣、文明與落後之間,「俊」之死在南方/臺灣,作者的南方意象還有其辯證之處。縱使中村地平一直對南方懷有渴望,但是親臨與想像還是會有落差。他曾坦言雖然深受佐藤春夫的影響,但是隨著南方之行的漸近,也不免因種種臆測導致神經衰弱。對於熱帶的想像或是恐懼,其實都來自文明思維的訓練。透過中村另一篇作品〈廢港〉,相信可以更為理解中村的南方憧憬。〈廢港〉由兩篇作品組成,發表的時間稍早於〈在旅途中〉,也是中村初期的創作,是屬於紀行文式的短篇小說。小說前半部「安平」,是敘述主角:一位高校生,他和專攻植物學的大學教授夫妻三人偕伴從阿里山旅行到南部的故事。後半部「淡水」,則是主角在前往淡水寫生途中,和一位內地來的畫家之間的對話。
前半部「安平」中人物的對話,可以觀察到旅者的跨文化想像與思鄉情懷。其中,植物學教授提出了他對臺灣植物的分析:「已研究過這裡各形各色的植物,它們全都帶有強烈的性的魅力。」這位教授甚至以動物來比擬,認為亞熱帶植物在夜間所散發出來的氣息與姿態,如同動物的交歡。他的形容儘管很生動,卻不免帶有異色(erotic)的眼光。對植物學者而言,分析臺灣植物的特色,也成為他詮釋臺灣的方式。而少年高校生的心情,卻是把目光放在荒廢美的追尋之上。佐藤春夫在〈女誡扇綺譚〉中對荒廢風景與心境的營造,深深地影響了中村地平。藉由安平與淡水兩個廢港的荒廢意象的震撼,他也期待自我內在能激發出對人生嶄新的覺悟。在前半部「安平」到後半部「淡水」,其實都有這樣的中心思考。追求從荒廢到新生,甚至永恆的美,只有自然界才有如此搖撼人心的力量。因此作者不斷提到法國詩人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一段話:
總之,我就是看到了水、太陽、雲、岩石。―不幸詩人的幸福言語,幾度無意義地在我內心裡不斷地複誦著。對莫泊桑來說,他眼睛要捕捉的水、太陽、雲、岩石,就是最純粹的自然;不涉及文明的一切,只是對原始的渴望。如此單純的情感想必衝擊了中村地平的心靈,他嚮往南方也是為了追求這樣的蠻荒境界。中村在高校期間,就曾經因為神經衰弱的問題而留級一年。中村在此以法國詩人莫泊桑為借鏡,期待南方的光與熱能夠為他治癒精神上的苦惱。
以自然主義文學聞名的莫泊桑,其悲劇性的命運對中村產生無比的魅力。中村常在作品中引用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那段文字,應該也是希望這段話能夠帶給他力量吧。而他在少年時期所閱讀的佐藤春夫的臺灣相關作品,則是對他形成積極影響的效用。當他透過回憶的文字,書寫自己初次的南方經驗時,可以看出兩位作家賦予他創作上的靈與肉。可以說,中村自少年期對南方的憧憬,是經由在臺的高校生活而得以實踐,但是卻也留下了負面的回憶。中村提過和佐藤春夫初次會面時,臺灣的事物是他們倆共同的話題。在這次的對話中,中村向佐藤傾訴,在殖民地的生活並不愉快。佐藤則向他表示,這是因為政治等等原因所造成的。中村在這裡並沒有詳述「不愉快」為何,但是顯然和佐藤春夫所解釋的理由有關。在〈廢港〉後半部「淡水」的人物對話中,也曾討論日本人是否能以人道主義看待殖民地的問題,或者只是漠然以對。由於民族的問題、政治的問題等等,這些複雜因素都有可能影響中村的臺灣觀感。
當一九三九年二月底,中村地平為了蒐集小說材料再度來臺時,他已經成為一位專業作家,也發表過許多作品。除了寫作方面,距離他上次離開臺灣到目前為止,這些年他的人生也有許多重大事件發生。首先,他和真杉靜枝的同居生活已將結束,兩人約定一起來臺,卻是這段感情的分手之旅。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村的大哥戰死在中國戰場,這個事件對中村的打擊相當大。同年的十月,他自己也收到徵召令而進入軍隊,不過後來因為胃病發作而立即退伍。但是隨著戰爭局勢的蔓延,日本全國也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當中。中村在一九三九年到臺灣取材,或許是希望能轉換心情而來的吧。中村地平這次的臺灣之旅,受到總督府以內地文士的特殊身分而被招待,和佐藤春夫當時遊臺的情況相同。他也透過這趟旅行,蒐集到不少寫作的題材。如果要具體說明中村再次造訪後的臺灣觀感,〈旅人之眼:作家觀看下的臺灣〉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之作。中村在這篇隨筆中,描述了他二度來臺旅遊的見聞與心情。比起十年前就讀高校時的景況相比,他明顯感覺到臺北已相當的現代化,不僅外在的事物改變了,連文化等精神層面的內容也有了急速的進步,這些變化令他相當驚訝。此外,他提到自己在臺北停留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去參觀臺北帝大的土俗學教室,期待能瞭解「生蕃」的文化。中村也談到這次旅行受到官方相當的優遇,讓他非常感動。但是,來臺過程中唯一使他無法忍受的,大概就是旅途中所遇到的本島人了。
中村在日本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有很多旅行的機會,他又是一個極愛好庶民旅遊方式的人,所以在交通工具上都會選擇三等車廂。但是在臺灣搭乘三等車廂,卻是一件必須忍耐的苦事。中村指出,除了車體本身的老舊、座位的不舒適之外,臺灣人的衛生習慣還非常低劣。不僅隨地吐痰、大聲談話,還攜帶各種魚肉蔬果上車,因此整個車廂充斥著惡臭與喧譁。而且臺灣各地方的飲食店也都不注重衛生,他只好以香蕉充饑。這些因素終於讓久未復發的胃疾在途中發作。這篇隨筆展現了近代旅者的文化心態,比起高校時期的青澀少年,此時的中村,儼然已具備文明人的批判視野。
然而,中村在〈旅人之眼〉,還是對臺灣沿途的景色讚嘆不已,認為完全沒有令他失望。他甚至建議臺灣應該規劃設立國家公園,將全臺灣國家公園化。他的理由在於:
既然臺灣是軍事、經濟的南進基地,那麼同時更必然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從這一段文字不難看出帝國的視線,中村提出要把臺灣全島國家公園化,以成為南進者可以獲得撫慰的休憩之地。然而,臺灣人的位置在那裡?如果臺灣是慰安之地,那麼臺灣人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從他批判本島人的身段,到提議將臺灣國家公園化,和他六、七年前在作品〈廢港〉中,苦心思索殖民地問題的文字,其間的書寫策略是有極大差異的。具體而言,對於臺灣的南方風土特色,他的態度始終是憧憬的。他在另一篇隨筆〈臺灣的溫泉〉也提到,在他高校時代時,就非常喜歡臺灣的溫泉。臺灣各地的溫泉,除了各有其天然特質之外,還能以極為便宜的價格享用,對中村這樣年輕的學生來說,真是非常快樂的事。因此他認為:「聽起來或許會誇張也說不定,但是我深深地感覺到,臺灣真是旅行者的樂園。」從學生到作家,中村的社會身分已經轉換,然而他對南方的風土之情卻依舊未變。但是在批評本島人時,他所展現的文明視野則顯得非常敏銳。在〈旅人之眼〉的論述當中,臺灣甚至能發展成帝國的新樂園,作者顯然提出他對南進政策的思考。這篇文章是他二度來臺後不久就發表的,所傳達出來的南進觀點與臺灣想像,應該是清晰而深刻的。中村的南方憧憬,也逐漸產生了變貌。
一、南方的旅行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村地平如願從日本渡海來到臺灣讀書。這段青春時期的臺灣經驗,無疑為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他在一九四一年所出版的隨筆評論集《工作桌》,有兩篇文章〈往南方的船〉、〈三等船客〉,談到初次赴臺的青澀心情。〈往南方的船〉是描寫作者十八歲那年,要從故鄉前往門司搭船往臺的經過,除了沿途的瑣碎情節之外,也述說了作者出發前忐忑不安的心情。不過,這篇散文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它細膩地傳達出親情的強度。儘管父母極力支持中村的決定,然而隨著啟程日期的漸近,關於自己單獨旅行這件事,還是讓他萌生極大的危機感:「去臺灣的話,說不定我會罹患瘧疾而死。這樣的話,去好嗎?」對於日本人來說,早期來臺的旅遊活動確實帶有「探險」的意味,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以降,臺灣已經逐漸邁向現代化,到臺灣的冒險活動也轉向較具娛樂的觀光性質,這誠然和殖民政權的穩定有密切關聯。但是,其實一般日本國民普遍對臺灣缺乏知識,甚至存有負面的蠻荒印象。父親對兒子的遠行看似信心滿滿,內心卻是忐忑不安,而兒子也為即將離別而心慌,只是兩個男人都壓抑情感。但是,在中村即將出發前,父親向他表示要親自送行到門司。這番舉動,是為了安撫中村神經緊繃的情緒,也是父親的體貼。
父子兩人從故鄉宮崎坐汽車到門司,然後在客棧過夜等待隔天的船期。在用完晚餐的時刻,鄰室的一位房客突然來拜訪他們。這一位客氣的老人,也是要搭船前往臺灣,因此過來打聲招呼。當彼此開始閒聊之後,才發現老先生是因為兒子在臺灣病死,所以此行是要去接回他的骨灰。作者的父親在聆聽之際,神情似乎顯得相當狼狽。在老人告辭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建議,如果想打退堂鼓也無所謂,就再一起回家吧。少年的自尊心,讓他隱忍住內心強烈想和父親回頭的渴望。隔天早晨,他們坐上小艇去轉搭輪船,這也是送行的最後一程。登上大船之後,距離啟航還有一些時間。神經衰弱的中村,這時身體狀況開始出現不適。父親急忙為他安排座位、買飲料解熱,並細心叮嚀他在臺灣可以去洗溫泉來保養身體,學校放長假時也可以返鄉……。忽然,開船的信號響起了。當父親再度坐上小艇返回碼頭時,作者企圖透過小小的船窗搜索父親的身影。然而小艇上擠滿了送行人,隨著漸行漸遠,他再也分不清誰的臉。回到座位躺下後,他的眼睛彷彿一直在追尋父親的背影。
原本嚴厲的父親,在這裡卻展現了異於往常的柔軟身段。父親的愛子之情,隨著〈往南方的船〉的文字不斷地滲透出來。中村地平在文中提到是佐藤春夫的文學讓他對南方產生強烈的憧憬,但是透過書寫的脈絡不難看出他對南方/臺灣還是存有疑慮。對於來自文明世界的旅人而言,亞熱帶縱使風情萬種,卻也難抵風土疾病的威脅。青澀少年的中村,當時即有神經衰弱的傾向。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他的步伐顯得有些躊躇。中村在另一篇隨筆〈三等船客〉,描寫了上船後的際遇。〈三等船客〉可說是〈往南方的船〉的續篇,作者在開頭延續了〈往南方的船〉結束時的感傷筆調。誠然,在前往臺灣的船上,他的寂寞與不安是強烈的。幸運的是,一位同船的年輕女性適時對他伸出友誼之手。而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他竟然在船上遇到一位同鄉。與這些人的邂逅,彷彿是在預言他的臺灣之行還是受到祝福的。
不過,臺灣風土的疾病意象,顯然讓中村印象深刻。收進《臺灣小說集》的短篇小說〈在旅途中〉,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五月的《行動》,屬於中村早期的創作,是一篇帶有淒美情調的作品。這篇小說的女主角「俊」,最後就是因為感染熱病而死於臺灣。〈在旅途中〉的情節是描寫主角分別在兩次的旅途中,與「俊」短暫交會的情分。主角當時是一位臺北高等學校的日籍學生,可說是作者以自己為形象而塑造的人物。根據岡林稔的研究指出,日本文壇在明治末到大正時期,自然主義小說的創作技巧成為文學青年邁向作家之路的指標。當時許多知名作家在作品中將私人生活以藝術的告白的手法,對中村這些新生代作家是具有相當魅力的。其實在佐藤春夫的臺灣相關作品,就能輕易看到這種表現方式。而中村地平在《臺灣小說集》中,也有多篇作品以此技巧展現。〈在旅途中〉是主角對青春的追憶,其中也包含了他對「俊」的淡淡情愫。縱使如今已無法記起「俊」的真切容貌,但她的白皙身影與執著性格卻是他難以忘懷的。主角回想起與「俊」的初次會面,是某年夏天和友人牧一起到九州健行途中所認識的。「俊」當時在一個鄉村小鎮當小學老師,由於她和牧有親戚關係,所以計畫途經她的小學時叨擾住宿。不料學校當天有青年團的活動,於是「俊」轉而招待他們到旅館過夜。晚上三人聚在房間閒聊,就著窗口穿拂進來的涼風,主角感覺自己似乎被「俊」的浴衣飄散過來的香味所包圍住了。顯然主角對「俊」是頗有好感,然而他只是一位旅人,兩人的緣分或許是短暫的吧。怎知那年秋天,主角竟然在臺北的東門市場裡瞥見「俊」的熟悉身影。向友人查證後才知道她已嫁到臺灣的嘉義,這也開啟了他們在臺灣交會的契機。
隔年寒假沒有回鄉的主角,計畫一個人沿臺灣的西海岸旅行。在旅行途中來到嘉義,他決定順道拜訪「俊」。在尋訪「俊」的住處時,主角獨自走在本島人的街道上,由於種族的隔離性在這種鄉下更加明顯,他不僅受到異樣的眼光,骯髒汙穢的巷弄也讓他寸步難行。彷彿置身在奇異的時空,強烈的疲憊與不安在找到「俊」後才稍稍平息。兩人在異鄉重逢是值得喜悅的,然而主角也察覺到她在此地的處境是落寞的。縱使有丈夫的陪伴,但在日本人稀少的嘉義鄉下,「俊」終須長期忍受孤獨的煎熬。主角和他們夫妻分手之後,「俊」的故事卻還未告一段落。半年後,主角意外接到「俊」感染瘧疾而死亡的通知。「俊」的人生旅途,就在臺灣劃下句點。不難發現小說裡所選擇的場景都「在旅途中」,如果人生是一場漫長的旅程,那麼主角和「俊」的交會只是沿途的短暫景點吧。
依循線性時間的進行,〈在旅途中〉呈現了相互對照的世界;兩趟旅途,兩個地理,兩種人生。死後安息在嘉義的「俊」,生前在她的心目中,臺灣占有多少分量,讀者無從得知。曾向主角自白要採取獨身主義的「俊」,為什麼突然結婚,作者也沒有多加說明。因為「俊」的先生抱定海外雄飛的壯志,立志要往南方發展,所以她才會追隨而來到臺灣。但是置身在臺灣鄉下的「俊」,不僅要適應粗俗惡劣的環境,還要忍受孤獨與寂寥的心情。而主角在兩次旅途中和「俊」交會所激起的火花,最終也映襯了人間的無奈與蒼涼。「俊」如果沒有來臺灣,必定會有不同的人生。臺灣最終成了「俊」長眠的所在,她的死亡似乎是在叩問:「前往南方的可行性?」
然而青春的早逝,也籠罩著一種絕美情調。在死亡的恐懼意象之外,極有可能轉喻為浪漫的想像。在日本與臺灣、文明與落後之間,「俊」之死在南方/臺灣,作者的南方意象還有其辯證之處。縱使中村地平一直對南方懷有渴望,但是親臨與想像還是會有落差。他曾坦言雖然深受佐藤春夫的影響,但是隨著南方之行的漸近,也不免因種種臆測導致神經衰弱。對於熱帶的想像或是恐懼,其實都來自文明思維的訓練。透過中村另一篇作品〈廢港〉,相信可以更為理解中村的南方憧憬。〈廢港〉由兩篇作品組成,發表的時間稍早於〈在旅途中〉,也是中村初期的創作,是屬於紀行文式的短篇小說。小說前半部「安平」,是敘述主角:一位高校生,他和專攻植物學的大學教授夫妻三人偕伴從阿里山旅行到南部的故事。後半部「淡水」,則是主角在前往淡水寫生途中,和一位內地來的畫家之間的對話。
前半部「安平」中人物的對話,可以觀察到旅者的跨文化想像與思鄉情懷。其中,植物學教授提出了他對臺灣植物的分析:「已研究過這裡各形各色的植物,它們全都帶有強烈的性的魅力。」這位教授甚至以動物來比擬,認為亞熱帶植物在夜間所散發出來的氣息與姿態,如同動物的交歡。他的形容儘管很生動,卻不免帶有異色(erotic)的眼光。對植物學者而言,分析臺灣植物的特色,也成為他詮釋臺灣的方式。而少年高校生的心情,卻是把目光放在荒廢美的追尋之上。佐藤春夫在〈女誡扇綺譚〉中對荒廢風景與心境的營造,深深地影響了中村地平。藉由安平與淡水兩個廢港的荒廢意象的震撼,他也期待自我內在能激發出對人生嶄新的覺悟。在前半部「安平」到後半部「淡水」,其實都有這樣的中心思考。追求從荒廢到新生,甚至永恆的美,只有自然界才有如此搖撼人心的力量。因此作者不斷提到法國詩人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一段話:
總之,我就是看到了水、太陽、雲、岩石。―不幸詩人的幸福言語,幾度無意義地在我內心裡不斷地複誦著。對莫泊桑來說,他眼睛要捕捉的水、太陽、雲、岩石,就是最純粹的自然;不涉及文明的一切,只是對原始的渴望。如此單純的情感想必衝擊了中村地平的心靈,他嚮往南方也是為了追求這樣的蠻荒境界。中村在高校期間,就曾經因為神經衰弱的問題而留級一年。中村在此以法國詩人莫泊桑為借鏡,期待南方的光與熱能夠為他治癒精神上的苦惱。
以自然主義文學聞名的莫泊桑,其悲劇性的命運對中村產生無比的魅力。中村常在作品中引用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那段文字,應該也是希望這段話能夠帶給他力量吧。而他在少年時期所閱讀的佐藤春夫的臺灣相關作品,則是對他形成積極影響的效用。當他透過回憶的文字,書寫自己初次的南方經驗時,可以看出兩位作家賦予他創作上的靈與肉。可以說,中村自少年期對南方的憧憬,是經由在臺的高校生活而得以實踐,但是卻也留下了負面的回憶。中村提過和佐藤春夫初次會面時,臺灣的事物是他們倆共同的話題。在這次的對話中,中村向佐藤傾訴,在殖民地的生活並不愉快。佐藤則向他表示,這是因為政治等等原因所造成的。中村在這裡並沒有詳述「不愉快」為何,但是顯然和佐藤春夫所解釋的理由有關。在〈廢港〉後半部「淡水」的人物對話中,也曾討論日本人是否能以人道主義看待殖民地的問題,或者只是漠然以對。由於民族的問題、政治的問題等等,這些複雜因素都有可能影響中村的臺灣觀感。
當一九三九年二月底,中村地平為了蒐集小說材料再度來臺時,他已經成為一位專業作家,也發表過許多作品。除了寫作方面,距離他上次離開臺灣到目前為止,這些年他的人生也有許多重大事件發生。首先,他和真杉靜枝的同居生活已將結束,兩人約定一起來臺,卻是這段感情的分手之旅。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村的大哥戰死在中國戰場,這個事件對中村的打擊相當大。同年的十月,他自己也收到徵召令而進入軍隊,不過後來因為胃病發作而立即退伍。但是隨著戰爭局勢的蔓延,日本全國也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當中。中村在一九三九年到臺灣取材,或許是希望能轉換心情而來的吧。中村地平這次的臺灣之旅,受到總督府以內地文士的特殊身分而被招待,和佐藤春夫當時遊臺的情況相同。他也透過這趟旅行,蒐集到不少寫作的題材。如果要具體說明中村再次造訪後的臺灣觀感,〈旅人之眼:作家觀看下的臺灣〉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之作。中村在這篇隨筆中,描述了他二度來臺旅遊的見聞與心情。比起十年前就讀高校時的景況相比,他明顯感覺到臺北已相當的現代化,不僅外在的事物改變了,連文化等精神層面的內容也有了急速的進步,這些變化令他相當驚訝。此外,他提到自己在臺北停留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去參觀臺北帝大的土俗學教室,期待能瞭解「生蕃」的文化。中村也談到這次旅行受到官方相當的優遇,讓他非常感動。但是,來臺過程中唯一使他無法忍受的,大概就是旅途中所遇到的本島人了。
中村在日本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有很多旅行的機會,他又是一個極愛好庶民旅遊方式的人,所以在交通工具上都會選擇三等車廂。但是在臺灣搭乘三等車廂,卻是一件必須忍耐的苦事。中村指出,除了車體本身的老舊、座位的不舒適之外,臺灣人的衛生習慣還非常低劣。不僅隨地吐痰、大聲談話,還攜帶各種魚肉蔬果上車,因此整個車廂充斥著惡臭與喧譁。而且臺灣各地方的飲食店也都不注重衛生,他只好以香蕉充饑。這些因素終於讓久未復發的胃疾在途中發作。這篇隨筆展現了近代旅者的文化心態,比起高校時期的青澀少年,此時的中村,儼然已具備文明人的批判視野。
然而,中村在〈旅人之眼〉,還是對臺灣沿途的景色讚嘆不已,認為完全沒有令他失望。他甚至建議臺灣應該規劃設立國家公園,將全臺灣國家公園化。他的理由在於:
既然臺灣是軍事、經濟的南進基地,那麼同時更必然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從這一段文字不難看出帝國的視線,中村提出要把臺灣全島國家公園化,以成為南進者可以獲得撫慰的休憩之地。然而,臺灣人的位置在那裡?如果臺灣是慰安之地,那麼臺灣人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從他批判本島人的身段,到提議將臺灣國家公園化,和他六、七年前在作品〈廢港〉中,苦心思索殖民地問題的文字,其間的書寫策略是有極大差異的。具體而言,對於臺灣的南方風土特色,他的態度始終是憧憬的。他在另一篇隨筆〈臺灣的溫泉〉也提到,在他高校時代時,就非常喜歡臺灣的溫泉。臺灣各地的溫泉,除了各有其天然特質之外,還能以極為便宜的價格享用,對中村這樣年輕的學生來說,真是非常快樂的事。因此他認為:「聽起來或許會誇張也說不定,但是我深深地感覺到,臺灣真是旅行者的樂園。」從學生到作家,中村的社會身分已經轉換,然而他對南方的風土之情卻依舊未變。但是在批評本島人時,他所展現的文明視野則顯得非常敏銳。在〈旅人之眼〉的論述當中,臺灣甚至能發展成帝國的新樂園,作者顯然提出他對南進政策的思考。這篇文章是他二度來臺後不久就發表的,所傳達出來的南進觀點與臺灣想像,應該是清晰而深刻的。中村的南方憧憬,也逐漸產生了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