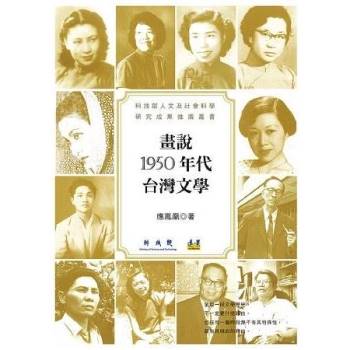第一章1950年代文學環境與文學生態
1-1為什麼「1950年代」?這十年文學發展有何特別?
所謂「1950年代」指的是從1950年到1959年這十年的「一段」,或「一小段」時間。為什麼特別挑選這一段呢?說實在,從時間的長河裡挑出其中一段來檢視、觀察它的歷史──這裡是「文學歷史」,不一定要什麼理由。但任何「一個時段」無不有它的特殊性,都有其精采的理由。把鏡頭拉遠一點看台灣歷史,好比說往前看「四百年台灣歷史」,特徵之一是:面積不大的台灣海島曾被許多「外來政權」所統治,島上人民在不同時期經歷各式各樣「殖民經驗」,包括最早荷蘭、西班牙,接著「明鄭、清領、日治、中華民國」。「1950年代」這一段,正好夾在日本殖民政府離開不久、國民黨政府初來台灣的階段──這時候台灣人剛從日本政府手中,脫離了長達五十年(1895~1945)的殖民統治。1945年二戰結束這年,日本人離開,隨之「接管」台灣的是中國的「南京政府」。
把鏡頭轉到中國大陸。1945年中國對日抗戰剛結束,接著是「國共內戰」。換句話說,日本人離開了中國,戰爭並沒有離開──1945到1949年之間中國依然漫天烽火,國共內戰打得火熱。雖從日本人手中取得「殖民地台灣」,只匆匆指派陳儀去台擔任「行政長官」,1947年二二八事件即爆發在他的任上。實際上蔣介石軍隊此時已自顧不暇,甚至是自身難保了。中國戰場上,國府節節敗退,史書形容蔣軍「兵敗如山倒」。共產黨解放軍在短短四年間贏得中國江山:毛澤東1949年於北京歡聲宣布建國的同時,蔣介石政府全面撤退台灣。國民黨既斷送大好河山,只得渡海求生,同年在台灣島上建立起新政權──說「新政權」似有語病,按後人說法,應是「中華民國到台灣」,1950這一年全台上下都以「民國39年」紀年。蔣氏政府這時也痛定思痛,決心勵精圖治,要以海島為「跳板」,準備「反攻大陸」。這時的聯合國裡仍有「中華民國席位」,當國際都還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時候,它就不能算是流亡政府,不論大陸的政府怎麼認定。必須先簡略鋪陳這一段國共歷史,以它作為「這段文學史」舞台背景,才能更好地認識1950年代台灣文學環境,便於理解十年間文學發展變貌。就宏觀的殖民地歷史來看,1950年代正是如此從一個殖民政府「過渡」到另一個殖民政府,也承續一段從「戰前到戰後」,政經文化都劇烈轉換的時期。學界曾經熱烈討論過戰後台灣是否「(被)殖民」的問題。台灣曾經是「日本殖民地」,有過一段受日本殖民五十年的歷史,這部分大多沒有異議。然而戰後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算不算「殖民台灣」呢?日本政府派一個將軍或親王去治理台灣,這個「台灣總督」雖人在外地,效忠的卻是日本政府,這叫「殖民」,就像英國人「殖民印度」、「殖民香港」;依此標準,戰後初期南京政府派陳儀到台灣成立「行政長官公署」應該可以類比。然而1949年來台灣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的蔣家政權,他撤退來台之後已無退路,沒有另外一個政府可回或效忠。如此境況可以稱得上「殖民者」嗎?問題與答案兩者都很難確認;雖說他已無退路,然而政府時時以「反攻」為念,或許衍生出另類定義的殖民。無論如何,此處先擱置此一疑義,暫且將「殖民」問題或提問,作為我們認識1950年代台灣文學環境的序曲。
從台灣人民的角度看,二次大戰結束,剛送走四十多萬統治台灣的日本人,短短四年後緊接著迎來新的政權,追隨新政府一起入台的還有百萬大陸軍民。可以想像這「十年歲月」夾在兩個不同政權交接的轉折點上,習用的語言與文化不得不跟著轉換調適。以「文學創作」來說,靠的全是「語言文字」,來了新政權必須從頭學習新的語言。本地文人須跨過母語(不論客語或福佬語),以往學習日語,新政權一來馬上禁止日語,趕忙再學習漢語。語言困難是多重的,更別說口語溝通之外,以陌生的中文創作了。儘管表面站在一個「過渡時期」,然而台灣往後數十年的「中文書寫」傳統,卻是從這「第一個十年」開始建立。這段時間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大小文藝政策,強制性語言轉換,定北京話為國語,全面禁止使用日文。加上官方提供經費成立各種作家協會,舉辦文藝獎項,發展軍中文藝活動等等,台灣戰前戰後其它「文學時期」很少像1950年代這樣,將「國家機器」開進文壇並加足馬力「運作」。此「十年文學生態」於是展示了一個「國家體制」與「文學生產」特別密切又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其它年代相比,這一段是很不一樣的文壇史。
1-2「1950年代文學史」如何被書寫?
「文學史」是什麼?一般人以為容易,其實這三個字比想像中困難得多,光一個「定義」就很難說得清楚。你可能會說,這有什麼難?文學史不就是「文學的歷史」嗎?沒錯,只不過何謂「文學的歷史」同樣沒有答案。對於「什麼才是文學」,怎樣才可以算作「文學歷史」,人人看法不同──你認為這部作品很好,另一邊說它很糟。於是,不同的人面對「同一時段文學」,甚至閱讀同一批文學作品,會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文學史」來。這也就是眼前「1950年代文學史」竟讓人「看不清楚」的問題所在。
1980年代以降,海峽兩岸陸續出版十餘部簡詳不一的「台灣文學史」,皆涵蓋「1950年代文學」專章。換句話說,這段「文學史」已經被好多學者作家寫出來,並收進各式各樣文學史著作裡。但對照起來,這段歷史說法不一;不僅各說各話,簡直南轅北轍,評價全然相反。
戰後國民黨主導文藝政策,生產大量「反共文藝作品」,這十年文學於是被史書通稱為「反共文學時期」。此一特徵等到兩岸開放「台灣文學研究」的1980及1990年代,作為「國民黨敵人」的中共學者作家,且不提左右意識形態,光說他們面對的,是一段擺明「反」自家共產黨的「反共」文學作品,不難想像這段文學歷史在大陸人筆下會得到怎樣的評價。
另一方面,「反共文學」也得不到台灣本地史家的肯定:他們對於國民政府在1950年代以威權手段,全面禁止日文、推動戰鬥文學,造成本土作家「失語」或「邊緣化」皆有批評。認為「反共文學」是「壓根兒跟此地民眾扯不上關係的懷鄉文學」。不論題材與內容,反共作品除了生產當時,在往後二、三十年文學史書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正面評價。以下具體列舉「文學史書寫」三方實例,它們代表性地呈現三種不同的歷史評價;對照之下,一方面看到「反共文學」在文學史的輪廓樣貌,一方面也藉此認識所謂「文學史」或「文學史書寫」──我們以為文學史只有一種,其實不然,它也會同時出現好幾種樣貌。
A國民黨/官方的文學史詮釋
──反共文學是大陸來台作家的血淚經驗,表現「志士爭自由」的時代精神
以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中華民國文藝史》為例,聲稱台灣這一段文學史,不但是悠久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更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傳統,是把「中國文學從大陸傳承到台灣最有貢獻的十年」。由於「本省文人」在這之前的五十年一直「呻吟在日本的鐵蹄之下」,無由認識精緻的中華文化,是他們這群來自大陸的文人,在20世紀50年代,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大陸帶到了台灣。
而這「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1950年代,政府提倡的是戰鬥文藝,作家從血淚經驗裡創作出來的是反共文學,如此時代氛圍下,反共文學的正當性是不必懷疑的。「反共」既是最佳代稱也概括這十年的文學特性。同年代評論家充分肯定:反共文學作品既可匡正社會風氣也鞏固民心士氣,給後來的台灣文學歷史奠下良好基礎。
而反共文學何人所寫,為何而寫?師大國文系教授張素貞論文是這麼說的:
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反共抗暴成了50年代新文學的主要思潮。挫辱的慘痛記憶,使無數有文才的人深刻反省……他們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側面,暴露敵人的陰謀詭計與殘暴行為。
若問作者的身分背景,答案是:他們是一群「隨同政府東渡的不甘被奴役的大陸來台志士」;他們「歷經中國空前浩劫,為爭生存爭自由,便不得不反抗共黨暴政」。並且,這一時期的傑出作品,「絕大部分取材於事實,能映現時代精神……顯露出道地的民族色彩。」
1-1為什麼「1950年代」?這十年文學發展有何特別?
所謂「1950年代」指的是從1950年到1959年這十年的「一段」,或「一小段」時間。為什麼特別挑選這一段呢?說實在,從時間的長河裡挑出其中一段來檢視、觀察它的歷史──這裡是「文學歷史」,不一定要什麼理由。但任何「一個時段」無不有它的特殊性,都有其精采的理由。把鏡頭拉遠一點看台灣歷史,好比說往前看「四百年台灣歷史」,特徵之一是:面積不大的台灣海島曾被許多「外來政權」所統治,島上人民在不同時期經歷各式各樣「殖民經驗」,包括最早荷蘭、西班牙,接著「明鄭、清領、日治、中華民國」。「1950年代」這一段,正好夾在日本殖民政府離開不久、國民黨政府初來台灣的階段──這時候台灣人剛從日本政府手中,脫離了長達五十年(1895~1945)的殖民統治。1945年二戰結束這年,日本人離開,隨之「接管」台灣的是中國的「南京政府」。
把鏡頭轉到中國大陸。1945年中國對日抗戰剛結束,接著是「國共內戰」。換句話說,日本人離開了中國,戰爭並沒有離開──1945到1949年之間中國依然漫天烽火,國共內戰打得火熱。雖從日本人手中取得「殖民地台灣」,只匆匆指派陳儀去台擔任「行政長官」,1947年二二八事件即爆發在他的任上。實際上蔣介石軍隊此時已自顧不暇,甚至是自身難保了。中國戰場上,國府節節敗退,史書形容蔣軍「兵敗如山倒」。共產黨解放軍在短短四年間贏得中國江山:毛澤東1949年於北京歡聲宣布建國的同時,蔣介石政府全面撤退台灣。國民黨既斷送大好河山,只得渡海求生,同年在台灣島上建立起新政權──說「新政權」似有語病,按後人說法,應是「中華民國到台灣」,1950這一年全台上下都以「民國39年」紀年。蔣氏政府這時也痛定思痛,決心勵精圖治,要以海島為「跳板」,準備「反攻大陸」。這時的聯合國裡仍有「中華民國席位」,當國際都還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時候,它就不能算是流亡政府,不論大陸的政府怎麼認定。必須先簡略鋪陳這一段國共歷史,以它作為「這段文學史」舞台背景,才能更好地認識1950年代台灣文學環境,便於理解十年間文學發展變貌。就宏觀的殖民地歷史來看,1950年代正是如此從一個殖民政府「過渡」到另一個殖民政府,也承續一段從「戰前到戰後」,政經文化都劇烈轉換的時期。學界曾經熱烈討論過戰後台灣是否「(被)殖民」的問題。台灣曾經是「日本殖民地」,有過一段受日本殖民五十年的歷史,這部分大多沒有異議。然而戰後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算不算「殖民台灣」呢?日本政府派一個將軍或親王去治理台灣,這個「台灣總督」雖人在外地,效忠的卻是日本政府,這叫「殖民」,就像英國人「殖民印度」、「殖民香港」;依此標準,戰後初期南京政府派陳儀到台灣成立「行政長官公署」應該可以類比。然而1949年來台灣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的蔣家政權,他撤退來台之後已無退路,沒有另外一個政府可回或效忠。如此境況可以稱得上「殖民者」嗎?問題與答案兩者都很難確認;雖說他已無退路,然而政府時時以「反攻」為念,或許衍生出另類定義的殖民。無論如何,此處先擱置此一疑義,暫且將「殖民」問題或提問,作為我們認識1950年代台灣文學環境的序曲。
從台灣人民的角度看,二次大戰結束,剛送走四十多萬統治台灣的日本人,短短四年後緊接著迎來新的政權,追隨新政府一起入台的還有百萬大陸軍民。可以想像這「十年歲月」夾在兩個不同政權交接的轉折點上,習用的語言與文化不得不跟著轉換調適。以「文學創作」來說,靠的全是「語言文字」,來了新政權必須從頭學習新的語言。本地文人須跨過母語(不論客語或福佬語),以往學習日語,新政權一來馬上禁止日語,趕忙再學習漢語。語言困難是多重的,更別說口語溝通之外,以陌生的中文創作了。儘管表面站在一個「過渡時期」,然而台灣往後數十年的「中文書寫」傳統,卻是從這「第一個十年」開始建立。這段時間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大小文藝政策,強制性語言轉換,定北京話為國語,全面禁止使用日文。加上官方提供經費成立各種作家協會,舉辦文藝獎項,發展軍中文藝活動等等,台灣戰前戰後其它「文學時期」很少像1950年代這樣,將「國家機器」開進文壇並加足馬力「運作」。此「十年文學生態」於是展示了一個「國家體制」與「文學生產」特別密切又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其它年代相比,這一段是很不一樣的文壇史。
1-2「1950年代文學史」如何被書寫?
「文學史」是什麼?一般人以為容易,其實這三個字比想像中困難得多,光一個「定義」就很難說得清楚。你可能會說,這有什麼難?文學史不就是「文學的歷史」嗎?沒錯,只不過何謂「文學的歷史」同樣沒有答案。對於「什麼才是文學」,怎樣才可以算作「文學歷史」,人人看法不同──你認為這部作品很好,另一邊說它很糟。於是,不同的人面對「同一時段文學」,甚至閱讀同一批文學作品,會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文學史」來。這也就是眼前「1950年代文學史」竟讓人「看不清楚」的問題所在。
1980年代以降,海峽兩岸陸續出版十餘部簡詳不一的「台灣文學史」,皆涵蓋「1950年代文學」專章。換句話說,這段「文學史」已經被好多學者作家寫出來,並收進各式各樣文學史著作裡。但對照起來,這段歷史說法不一;不僅各說各話,簡直南轅北轍,評價全然相反。
戰後國民黨主導文藝政策,生產大量「反共文藝作品」,這十年文學於是被史書通稱為「反共文學時期」。此一特徵等到兩岸開放「台灣文學研究」的1980及1990年代,作為「國民黨敵人」的中共學者作家,且不提左右意識形態,光說他們面對的,是一段擺明「反」自家共產黨的「反共」文學作品,不難想像這段文學歷史在大陸人筆下會得到怎樣的評價。
另一方面,「反共文學」也得不到台灣本地史家的肯定:他們對於國民政府在1950年代以威權手段,全面禁止日文、推動戰鬥文學,造成本土作家「失語」或「邊緣化」皆有批評。認為「反共文學」是「壓根兒跟此地民眾扯不上關係的懷鄉文學」。不論題材與內容,反共作品除了生產當時,在往後二、三十年文學史書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正面評價。以下具體列舉「文學史書寫」三方實例,它們代表性地呈現三種不同的歷史評價;對照之下,一方面看到「反共文學」在文學史的輪廓樣貌,一方面也藉此認識所謂「文學史」或「文學史書寫」──我們以為文學史只有一種,其實不然,它也會同時出現好幾種樣貌。
A國民黨/官方的文學史詮釋
──反共文學是大陸來台作家的血淚經驗,表現「志士爭自由」的時代精神
以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中華民國文藝史》為例,聲稱台灣這一段文學史,不但是悠久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更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傳統,是把「中國文學從大陸傳承到台灣最有貢獻的十年」。由於「本省文人」在這之前的五十年一直「呻吟在日本的鐵蹄之下」,無由認識精緻的中華文化,是他們這群來自大陸的文人,在20世紀50年代,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大陸帶到了台灣。
而這「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1950年代,政府提倡的是戰鬥文藝,作家從血淚經驗裡創作出來的是反共文學,如此時代氛圍下,反共文學的正當性是不必懷疑的。「反共」既是最佳代稱也概括這十年的文學特性。同年代評論家充分肯定:反共文學作品既可匡正社會風氣也鞏固民心士氣,給後來的台灣文學歷史奠下良好基礎。
而反共文學何人所寫,為何而寫?師大國文系教授張素貞論文是這麼說的:
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反共抗暴成了50年代新文學的主要思潮。挫辱的慘痛記憶,使無數有文才的人深刻反省……他們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側面,暴露敵人的陰謀詭計與殘暴行為。
若問作者的身分背景,答案是:他們是一群「隨同政府東渡的不甘被奴役的大陸來台志士」;他們「歷經中國空前浩劫,為爭生存爭自由,便不得不反抗共黨暴政」。並且,這一時期的傑出作品,「絕大部分取材於事實,能映現時代精神……顯露出道地的民族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