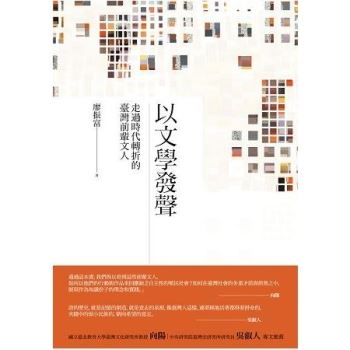時代轉折的見證,臺灣文學史的新發現
─傅錫祺家藏櫟社史料的學術價值
「臺灣文學研究」成為獨立的學科,時間相當短淺,臺灣文學史料的挖掘、整理與建構,乃是臺灣文學研究朝向深刻學術化不可或缺的奠基工作。近十多年來,在臺灣文學的學術範疇,不論原住民文學、母語文學、民間文學、古典文學、日治時期新文學、當代作家文學等諸多領域,不少學者、作家及其家屬、文史工作者、研究生紛紛投入這股挖掘臺灣文學史料的潮流中,提供不同程度的貢獻,出版各類專書或論文,使臺灣文學的研究不斷有新發現,產生新論述,逐步建構更堅實的研究成果。目前臺灣文學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仍如火如荼展開之中,而國立臺灣文學館發行《臺灣文學史料集刊》,提供交流分享的平臺,也可說是以國家資源回應這股新興學術潮流的產物。
筆者專業研究以臺灣古典文學為主,從事櫟社研究多年,並關注近百餘年來臺灣新舊世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傳承、文學活動與創作,社會與政治關懷。2007 年8 月筆者從臺灣師大轉到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任教,偶然得知興大臺文所在職專班學生羅瑰琳(現任臺中市潭子國小教師)為櫟社社長傅錫祺之外曾孫女,筆者經由她的引介,進而結識其母親傅紅蓮女士,透過傅女士之協助,並取得其家族之信任,陸續將其家中珍藏大批櫟社書信、手稿及其他原始文獻提供筆者參考。其資料之豐富、份量之龐大,令筆者大為驚訝。根據這批資料顯示,傅錫祺雖然在1917 年才接任社長,但其實從1906 年櫟社組織化開始,他便擔任櫟社活動的主要聯絡中心,與資料之保管者,因而可以斷言:櫟社相關資料與原始文獻,絕大部分都保存於傅錫祺家中,若能陸續整理,將可提供不少值得研究的新資料。
由於這批資料份量龐大,整理、解讀相當複雜費時,以下筆者初步選錄數件珍貴史料,說明其背景及其學術價值,提供學界及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包括(1)1912 年的櫟社題名錄(2)社員黃旭東,1911 年11 月在青島行醫時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第一手觀察報導(3)1912 年1 月、1930 年3 月,反映連橫與櫟社互動情誼,從親密到決裂的兩張明信片(4)1918年12 月,蔡惠如為發起「臺灣文社」奔走募款,與傅錫祺聯絡之信函(5)1924 年,蔡惠如因意外受傷,回信答謝社友之慰問(6)1947 年1 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櫟社為謀復興,推舉林獻堂接任社長,並吸收新社員的會議紀錄等。
透過這些史料,不但可具體認識櫟社從日治到戰後數十年間的興衰起伏軌跡,也能看出面臨臺灣近百年來多重時代轉折,櫟社社員如何回應?其理想與堅持何在?也能藉此體會社員文學涵養與寬闊視野,乃至成員立場的差異與紛爭的具體細節,從而思索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與政治意涵。這些史料既是時代多重轉折的珍貴見證,也將為臺灣文史學界提供不少新發現。
一、櫟社社友題名錄:櫟社創社初期的一手史料(1912 年)
後圖所示「櫟社社友題名錄」,從字體判斷是傅錫祺的筆跡,題名錄下方註明「以齒為序」,亦即按照年齡大小依序排列,時間是明治45 年(1912),名單上共有二十一人,姓名下方有兩行小字,第一行是本名、字號、地址,第二行是出生年月日(陰曆)。這份資料是考察社員年齡的重要依據,相當珍貴。年齡最長的是生於慶應3 年(1867)的陳基六,其次是張麗俊、王學潛,都生於明治元年(1868)年,其次依序從1871 年出生的賴紹堯,一直到1882 年出生的陳賈,櫟社第一代核心社員,大體上都是在日本領臺之前已完成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
從居住地考察,櫟社社員基本上都是定居臺灣中部,但當時記載的地名,不但與現今頗有差異,日治時期也曾多次更名。如陳瑚、陳貫兩兄弟住苗栗房裡,屬於現在的苑裡,陳基六、蔡惠如住牛罵頭,即臺中清水,而林家的林仲衡、林幼春、林獻堂的地址都寫霧峰舊名「阿罩霧」等,林子瑾居住的「臺中廳臺中街新庄仔」,是現在的臺中市區後火車站大智路附近。至於社員中唯一非出身中部的是臺南人連橫(雅棠),因櫟社創辦人林俊堂邀請而加入該社,1909 年時他受雇於霧峰林家的合昌商會,寓居林家所擁有的「瑞軒」(在現在臺中公園附近,1912 年左右因建公園而拆除)。
名單中較具知名度的人物包括:林俊堂、林幼春、賴紹堯三人是櫟社最初的創辦人,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等人則在1920 年代積極投入臺灣民族運動,櫟社被認定具有強烈的抗日色彩,也肇因於此。傅錫祺在1917 年接替此年去世的賴紹堯擔任櫟社社長,一直到1946 年去世為止,是維繫櫟社運作的靈魂人物之一。林子瑾則是1919 年櫟社創辦臺灣文社的重要人物,臺灣文社發行的《臺灣文藝叢誌》以其臺中住宅為發行地址。而這份1912 年的櫟社社員名單,出身鹿港者計有鄭玉田(汝南)、陳懷澄(槐庭)、莊嵩(太岳)三人,足以反映鹿港向來文風鼎盛的事實。
二、黃旭東致傅錫祺函:辛亥革命後的青島見聞(1911 年11 月)
由於櫟社成員之社會身份,皆屬於當時社會之知識菁英,其中有不少社員曾有豐富的境外旅遊經驗,如林獻堂1927 年至1928 年的歐美之行,著有《環球遊記》,已成為當今學界的熱門研究對象。而在筆者目前所見櫟社信函中,有多件屬於社員旅居日本與中國之見聞,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以下試舉一例說明之。
社員黃旭東(1883 ─ 1913)畢業於臺北醫學校,曾在臺中中央醫院任職,櫟社外團組織「中央金曜會」之例行活動,便是在其任職之醫院舉行。不過,由於他早在1913 年於旅居日本期間意外病故,其事跡並不被後人熟知。而這批信件中,有數封黃旭東旅居中國大連行醫時寫給傅錫祺的信,都是以工整之毛筆小楷書寫。其中一封是1911 年11 月所寫,信紙多達十張,內容約數千字。根據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可知,他大約1911 年8 月下旬離臺赴大連。1911 年11 月23 日黃旭東寫信給傅錫祺報告近況,當時恰好是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大連屬於日本勢力範圍,黃乃得以處在風暴之外,旁觀中國時局之劇烈變遷。信中談到他在大連行醫對大連的觀察,以及與梁啟超、湯覺頓兩人晤談的經過,乃至梁啟超對革命的態度等,摘述片段如下:
近頃革命風潮澎湃全清,大連一地雖不受其影響,而避難來者日有所聞。當盛大臣避難往青島時,亦在此地停船數時間,但不接客耳。約十數日前,任公由日來連,越日往旅順,再越宿赴奉天,在奉天住兩三日,即赴營口,其時擬再回奉天或往北京。後因湯荷庵自北京來連,電促任公來連談話,故任公行程改換來連,二宿即同荷庵乘嘉義丸回神戶矣。
當任公初到時,弟本擬往訪,後思任公際此革命大亂之際,想亦無心與閒人聚談,故不果往。再來之際,因思荷庵亦在,故於夜間挾刺往,則荷庵歡顏出迎,大謂奇遇。弟告以故,始恍然明白,謂彼常來往北京、天津、日本間,每到此地多獨宿旅邸,未有友人聚話,並謂此後來往,有弟在此,可以免寂寞之感矣。
少頃,任公出,亦訝弟南人何以來此?聽彼二人之言,謂此回革命,與彼常時持論不同,固眾所周知者。現時革命乃種族革命,彼主張者乃政治革命,蓋謂種族革命,須大動戈矛,終招外國干涉,則不利莫大於是,政治革命則不然。且此回之亂,因政府不從其平時一黨所主張,虛傳立憲,毋有實行之期,故種族革命一黨,得以藉此肆其所欲為,是以此回之亂,政府亦甚惶恐,已頒十九條新憲法之文,蓋從此息戰,實行憲法,則革命此舉不為無益,但恐革命軍不悟,兵連禍結,則國力消耗,雖有英傑亦難為力耳。
梁啟超與湯覺頓(湯覺頓即信中所提之「荷庵」)兩人,在1911 年4 月曾應林獻堂之邀訪問臺灣,並與櫟社成員在臺中聚會賦詩。黃旭東因為這次機緣,乃有機會在大連與梁、湯兩人敘舊,交換對革命與時局的看法,梁啟超自言擔心激烈動亂與外國干涉,並不贊成革命黨所謂「種族革命」的作為。黃旭東隨後在信中還批評袁世凱,利用革命成功、清廷尚未終結之際,從中取利以遂行掌權之野心。接著,他還談到大連一地之社會狀況:
大連本一漁村,名為青泥窪,露國租借後經營成市,名為グル二―,及改隸日本,改名大連。現時商業甚盛,滿鐵本社設在此處。而此處清人惟商人及勞慟者,多由山東、天津、北京、上海、湖北等處來者,其中山東人十居八九,多獨身者。商人略有上等、中等者,而勞慟者則較吾臺乞丐相似,蓬頭垢面、破衣纏身,無屋可住,且政府設有收容所數處,以收容此等勞慟者。其屋約可六尺高,上蓋草蓆,傍以木板為壁,四壁屋上皆可透光,較吾臺乞丐之屋更不堪甚多。弟曾往觀,訝其冬季不知如何聊生耳。
上文可說是一段相當精采的大連見聞報導。此信的研究價值,在於可多方面考察臺灣人與梁啟超的互動,對晚清、民國政權更送之際的態度,對袁世凱的批判,以及大連被日本佔領後的治理情形與社會面貌等,如下階級的勞動者如乞丐,為數甚多,居住環境簡陋而惡劣。
三、陳懷澄致連橫明信片(1912 年1 月):斷髮風潮漸起
傅錫祺家藏書信,數量最多者仍屬櫟社成員之信函。目前初步清查,幾乎櫟社第一代、第二代社員,與傅錫祺曾有往來書信者至少有三十多人。其中數量尤多者,包括陳槐庭、賴紹堯、陳瑚、陳貫、林癡仙,乃至第二代的莊垂勝、葉榮鐘、林陳琅、張賴玉廉,從上百件到數十件不等。這類信件內容廣泛,從詩社活動、私人事務、友情分享、婚喪慶弔、時局批判、人事臧否,內容無所不包。以下舉陳懷澄與連橫相關之明信片二例,加以說明。
連橫於1908 年移居臺中,1909 年加入櫟社,1912 年赴中國旅遊,1930 年因發表附和總督府鴉片政策之言論而被櫟社除籍。筆者曾發表〈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與決裂─兼論櫟社「抗日」屬性之再評估〉,詳論連橫與櫟社之互動經過。根據這批書信資料可知他與賴紹堯、林癡仙交情匪淺,在臺中時期寄居林家專祠。筆者又根據〈傅錫祺日記〉的相關記載判斷,連橫約1911 年7月,透過傅錫祺介紹進入臺灣新聞社任職,1912 年1 月因準備赴中國旅遊而去職7,連橫擬央請陳懷澄接任,陳懷澄因而寫這張明信片推辭。明信片正面如下:
臺中街林家專祠內
連雅堂先生
惠披
鹿港陳懷澄覆
郵戳日期是明治45 年(1912,大正元年)1 月6 日,內容是:
接示,蒙委匡助錫兄,敢不唯命是聽,奈不譯文,以是裹足。日前痴兄經來書勸往,亦以此意答之。抱歉實甚!現汝南歸家,何不懇於獻、階二兄,請其暫派汝南往助,獻、階二兄必首肯。此舉甚善,兄以為然否?大駕何日發韌耶?仙兄斷髮,弟之辮尾,自此休矣!哈哈!頃抱感風病。匆匆此覆。即侯雅堂兄健安
一月六日 弟懷澄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