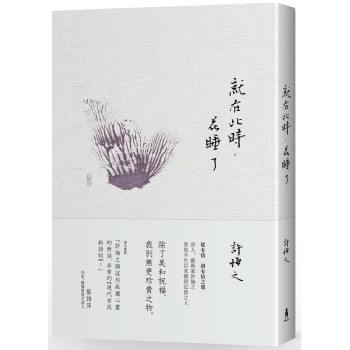〈季札掛劍,韓良露〉
作家韓良露生前是一個熱情多聞的人,於生活生命歷史諸學,博采並且精研,文字溫煦,立論卓然,她是有鹿文化成立之後,我最想邀約出版的作家之一。
2014年6月,有鹿文化出版了她的《文化小露台》和《台北回味》,原因乃依於她對占星之學、生命歷程之中,某一種神秘的感覺和計算;從她給出一個小行李箱的原稿,煜幃、同事和我為之編印成書而出版,其實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編書的過程當中,有一次,她約了我和相關同事到「布拉格咖啡」談工作,卻要求我先到半小時。原因是她覺得那麼緊迫的編輯出書,有鹿的夥伴們都必須加班很多,「悔之,你是老闆,必須認命;而他們是上班的人,為了我的書,這麼認真的拚命加班,所以我包了紅包給他們,表示我的感謝。待會他們來咖啡館,我就會交給他們,但我並不是和你討論,只是向你說明和告知。」
這就是韓良露,依於仁而溫厚,心中總是有人。
之後不久,韓良露和有鹿文化陸續又議定了一些出版的時程,但她的身體開始虛弱不堪,所以她決定去巴黎休假休養。
在她出發去巴黎前兩天,我接到她一通電話,電話中的她,喘著氣說話,説了許多話,包括她已經往生的父親韓時中先生、十普寺、金剛經等諸種心情;其中她也這麼說:「悔之,我要去巴黎渡假了,大概要休養一年之後,再找你討論出書。我原本要出書的還有另外一家出版社,但那是一家大公司,我暫時不出書,並不會影響他們。有鹿是一家小公司,所以我先來告訴你,讓你安排人力和工作⋯⋯」
「悔之,一年後,良露姊會再給你出書;雖然我的書不像某某作家等人,會讓你賺比較多錢;但至少會讓你賺到一些小錢⋯⋯。真是對不起,我必須食言了,我要先休養一年⋯⋯」
聼著電話的我,淚流滿面。
在良露的此生中,我與她見面其實並不多次;她心念的美善真摯,在許多人心中種下種子,包括我。所以良露姊生病、就醫、乃至捨報之時的助念、告別式之佛事種種,我都想到她的一念心,而盡力投入。
春秋時期,吳國季札出使晉國,佩戴寶劍經過徐國,徐國國君雖未言語,但甚愛此劍;季札心裡想著,等出使的任務結束,再經過徐國之時,再將此劍送給徐國國君。未在意料,返經之時,徐國國君病逝,季札將寶劍掛在墓上,以做為默允之心意的踐履。
「南瓜國際公司」這幾年來陸續編整「韓良露生命占星學院」系列,再編印出版幾本,即將齊全圓滿;有鹿文化這四年來,次第出版許多良露的書,而今,《義大利小城小日子》將於今年十月出版,她生前完整、重要的著作,也吿一段落。
追憶昔日電話中的對答——其實大部分都是她在說話,我的心中感念萬千!我不是季札,手中也無天下之名劍,但心中默允之事,竭力編輯良露姊的書,終於大抵完成,我的心情如同季札之掛劍於墓前,故人不在,一死一生。
〈路逢劍客須呈劍〉
「路逢劍客須呈劍」,對一個網路時代興起前就開始寫作的人如我,筆,就宛若是寫作者的劍,透過文字而出的書寫必須藉著筆紙完成。我面對鍵盤打字的速度很慢,因此備受干擾,所以大部分寫作的時間裡,還是習慣用筆書寫。
我這半生,送我最多次筆的人,是林文月老師。以前她每次從國外回來,大概都會送我一支筆,那彷彿是一種不必言語的叮嚀:悔之,用筆好好寫字。
「解劍贈壯士」,每次收到林老師送我的筆,都慨然有壯濶之情;筆,也不再是筆,是一種心意的銘記和付囑。
筆,其形雖小,但其勢其力不可限量,「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緜可付簫」,少年時記住了龔自珍這兩行詩句,愛之不忘,收到贈筆時,總會想起用筆書寫,文字可以洶湧,也可以纏綿。
林文月老師送我諸多支筆,有一次,我取了其中一支,送給有鹿的夥伴施彥如,她也是一位「讀中文系的人」。前年她非常充滿情感投注心力編輯林老師的《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有一天,我慎重的取出一支林老師送我的筆,送給彥如,知道彥如會曉得我的感動和敬意。
我隨身的後背包,總是攜帶了各式各樣的筆,多是朋友所贈,每次選用一支筆來寫字,都起動了緣會的記憶和感激。
最近收到朋友林怡君送的一支鋼筆,看到這支美麗的鋼筆上面,鎸刻了我以前的狗兒之名「尼歐」,知道怡君應該是讀過我寫尼歐的文章;尼歐的名字在一隻鋼筆上被銘記,也在我的心裡被銘記,像葉慈的〈1916年復活節〉那首詩裡,被鄭重銘記的那些人名⋯⋯有一天,在有鹿文化辦公室把看三支筆。這支鎸有尼歐之名的鋼筆,一支袖珍鋼筆,和一支日本「溫恭堂」所製「一掃千軍」長鋒羊毫筆。
臺靜農先生晚年喜用「一掃千軍」寫字,林文月老師以前若去日本時,常常買了帶回台北要送給臺先生,但臺先生總是以做為老師的身份堅持要付錢。這支「一掃千軍」懸在筆架,多年前,畫家于彭到有鹿文化辦公室曾用之而作畫,我則甚少用之,因為寶愛之故。
䄂珍鋼筆則是大兒子含光用他第一筆寫歌的版稅收入買來送我,上面以法文刻字「送給父親」。
那一個下午,我忍不住花了很長的時間,一一把看朋友們送我的各式各樣的筆。「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唐代的臨濟義玄禪師如是道,禪師原來是説證悟之境如人飲水而冷暖自知。
半生的大部分時間以筆書寫,愛筆、敬筆,知道長輩、朋友以筆鼓舞、勉勵我的心意,所以有時候我也會送筆給人。有一次,看到「鴉埠咖啡」的Tina在臉書說恭抄心經且反聞自性的心情,我就敬送了小字抄經會好用的筆給她,正因為人生路上、因緣之中,我們都是贈劍之人也是受劍之人。
〈我的「圓圈日」〉
禪定,「禪」,是外能「離一切諸相」;「定」是內能「不執著」、「不分別」、「依於自性」。定,是禪的基礎,內外都應兼修,到最後也應內外不分。半生以來,關於「禪定」,我渴望學習,最好是「行走坐臥皆是禪」,生活就是禪,但慚愧的是總做得不好,功力很淺,甚至常常連靜心都不可常得常住。
幾年前,參加了一次為期四天三夜的「禪三」,為了禁語、為了止妄,道場收取了大家的手機,斷絕與外界的聯繫,當然依規定也不可以抽菸。那次的禪三,我的心非常平靜,長年的菸癮都沒有犯,甚至隔壁房間的先生晚上把頭伸出窗外,偷偷抽菸,煙飄進了我的室內,我居然也能不為所動所惑!只是下山後不久,覺得世界吵雜,雜事繁多,覺得心不靜定、煩躁,很快的,我又抽菸了。
心,如果能離一切境界,當然最好!像我在那一次的禪三,可以不受菸癮的制約。但修行不夠的我,常常心不能離境,「心」不能離境的時候,我選擇使自己的「身」離境——就是斷絕外緣。
很多年前讀《當和尚遇到鑽石》這本書,深受啟發,除了其中深論「自他不分」的共同成長之外——作者説每周三是他自己一人的「圓圈日」,用來靜休、靜思,使心力恢復、上增,後來並且有「森林日」⋯⋯
年紀過了半百,我看到有鹿文化的夥伴們成熟、互愛,所以在2018年3月1日,將總編輯的工作付託給林煜幃先生,由他帶領夥伴們更煥然的前行。
因為在那段時間,忙著自己第一次手墨個展,諸事忙碌,自知心性不夠澄明自在,我生起了無比強烈的「圓圈日」念頭,覺得是時候了,應該照顧好自己的「心君」。
2018年4月開始,我的「圓圈日」是每天傍晚六點之後,盡量關掉手機或保持靜音;有時擇日,徹底關掉手機,靜休、思惟、創作、思考——包括有鹿與我有關的工作、創作、陪伴因緣之人、爬山、運動、和朋友喝幾盞茶、聼一張唱片、慢慢為自己沖一杯咖啡……,也可能只是若有想、若非有想的嘗試「看到自己」、「陪伴自己」而已。
言語,道斷。
差不多十年了,每年我都會以兩天左右的時間,息交絕遊,什麼事也不做,就靜靜翻讀《法華經》。
慧命無窮,讀法華,變成我每一年的「慧命清洗日」,回到平靜的閱讀和思惟,因為斷絕外緣,遂形同「禁語」,因此略知什麼是不須言語的「妙不可言」!也因之有著淺淺的,超乎喜悅的喜悅。
讀法華,那是我以前除了「一人旅」之外,最「圓圈日」的行為了。
半百過後的我,近來因為「圓圈日」,多了緩慢、靜心,覺得生命的沙漏,流速慢了一些……
作家韓良露生前是一個熱情多聞的人,於生活生命歷史諸學,博采並且精研,文字溫煦,立論卓然,她是有鹿文化成立之後,我最想邀約出版的作家之一。
2014年6月,有鹿文化出版了她的《文化小露台》和《台北回味》,原因乃依於她對占星之學、生命歷程之中,某一種神秘的感覺和計算;從她給出一個小行李箱的原稿,煜幃、同事和我為之編印成書而出版,其實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編書的過程當中,有一次,她約了我和相關同事到「布拉格咖啡」談工作,卻要求我先到半小時。原因是她覺得那麼緊迫的編輯出書,有鹿的夥伴們都必須加班很多,「悔之,你是老闆,必須認命;而他們是上班的人,為了我的書,這麼認真的拚命加班,所以我包了紅包給他們,表示我的感謝。待會他們來咖啡館,我就會交給他們,但我並不是和你討論,只是向你說明和告知。」
這就是韓良露,依於仁而溫厚,心中總是有人。
之後不久,韓良露和有鹿文化陸續又議定了一些出版的時程,但她的身體開始虛弱不堪,所以她決定去巴黎休假休養。
在她出發去巴黎前兩天,我接到她一通電話,電話中的她,喘著氣說話,説了許多話,包括她已經往生的父親韓時中先生、十普寺、金剛經等諸種心情;其中她也這麼說:「悔之,我要去巴黎渡假了,大概要休養一年之後,再找你討論出書。我原本要出書的還有另外一家出版社,但那是一家大公司,我暫時不出書,並不會影響他們。有鹿是一家小公司,所以我先來告訴你,讓你安排人力和工作⋯⋯」
「悔之,一年後,良露姊會再給你出書;雖然我的書不像某某作家等人,會讓你賺比較多錢;但至少會讓你賺到一些小錢⋯⋯。真是對不起,我必須食言了,我要先休養一年⋯⋯」
聼著電話的我,淚流滿面。
在良露的此生中,我與她見面其實並不多次;她心念的美善真摯,在許多人心中種下種子,包括我。所以良露姊生病、就醫、乃至捨報之時的助念、告別式之佛事種種,我都想到她的一念心,而盡力投入。
春秋時期,吳國季札出使晉國,佩戴寶劍經過徐國,徐國國君雖未言語,但甚愛此劍;季札心裡想著,等出使的任務結束,再經過徐國之時,再將此劍送給徐國國君。未在意料,返經之時,徐國國君病逝,季札將寶劍掛在墓上,以做為默允之心意的踐履。
「南瓜國際公司」這幾年來陸續編整「韓良露生命占星學院」系列,再編印出版幾本,即將齊全圓滿;有鹿文化這四年來,次第出版許多良露的書,而今,《義大利小城小日子》將於今年十月出版,她生前完整、重要的著作,也吿一段落。
追憶昔日電話中的對答——其實大部分都是她在說話,我的心中感念萬千!我不是季札,手中也無天下之名劍,但心中默允之事,竭力編輯良露姊的書,終於大抵完成,我的心情如同季札之掛劍於墓前,故人不在,一死一生。
〈路逢劍客須呈劍〉
「路逢劍客須呈劍」,對一個網路時代興起前就開始寫作的人如我,筆,就宛若是寫作者的劍,透過文字而出的書寫必須藉著筆紙完成。我面對鍵盤打字的速度很慢,因此備受干擾,所以大部分寫作的時間裡,還是習慣用筆書寫。
我這半生,送我最多次筆的人,是林文月老師。以前她每次從國外回來,大概都會送我一支筆,那彷彿是一種不必言語的叮嚀:悔之,用筆好好寫字。
「解劍贈壯士」,每次收到林老師送我的筆,都慨然有壯濶之情;筆,也不再是筆,是一種心意的銘記和付囑。
筆,其形雖小,但其勢其力不可限量,「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緜可付簫」,少年時記住了龔自珍這兩行詩句,愛之不忘,收到贈筆時,總會想起用筆書寫,文字可以洶湧,也可以纏綿。
林文月老師送我諸多支筆,有一次,我取了其中一支,送給有鹿的夥伴施彥如,她也是一位「讀中文系的人」。前年她非常充滿情感投注心力編輯林老師的《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有一天,我慎重的取出一支林老師送我的筆,送給彥如,知道彥如會曉得我的感動和敬意。
我隨身的後背包,總是攜帶了各式各樣的筆,多是朋友所贈,每次選用一支筆來寫字,都起動了緣會的記憶和感激。
最近收到朋友林怡君送的一支鋼筆,看到這支美麗的鋼筆上面,鎸刻了我以前的狗兒之名「尼歐」,知道怡君應該是讀過我寫尼歐的文章;尼歐的名字在一隻鋼筆上被銘記,也在我的心裡被銘記,像葉慈的〈1916年復活節〉那首詩裡,被鄭重銘記的那些人名⋯⋯有一天,在有鹿文化辦公室把看三支筆。這支鎸有尼歐之名的鋼筆,一支袖珍鋼筆,和一支日本「溫恭堂」所製「一掃千軍」長鋒羊毫筆。
臺靜農先生晚年喜用「一掃千軍」寫字,林文月老師以前若去日本時,常常買了帶回台北要送給臺先生,但臺先生總是以做為老師的身份堅持要付錢。這支「一掃千軍」懸在筆架,多年前,畫家于彭到有鹿文化辦公室曾用之而作畫,我則甚少用之,因為寶愛之故。
䄂珍鋼筆則是大兒子含光用他第一筆寫歌的版稅收入買來送我,上面以法文刻字「送給父親」。
那一個下午,我忍不住花了很長的時間,一一把看朋友們送我的各式各樣的筆。「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唐代的臨濟義玄禪師如是道,禪師原來是説證悟之境如人飲水而冷暖自知。
半生的大部分時間以筆書寫,愛筆、敬筆,知道長輩、朋友以筆鼓舞、勉勵我的心意,所以有時候我也會送筆給人。有一次,看到「鴉埠咖啡」的Tina在臉書說恭抄心經且反聞自性的心情,我就敬送了小字抄經會好用的筆給她,正因為人生路上、因緣之中,我們都是贈劍之人也是受劍之人。
〈我的「圓圈日」〉
禪定,「禪」,是外能「離一切諸相」;「定」是內能「不執著」、「不分別」、「依於自性」。定,是禪的基礎,內外都應兼修,到最後也應內外不分。半生以來,關於「禪定」,我渴望學習,最好是「行走坐臥皆是禪」,生活就是禪,但慚愧的是總做得不好,功力很淺,甚至常常連靜心都不可常得常住。
幾年前,參加了一次為期四天三夜的「禪三」,為了禁語、為了止妄,道場收取了大家的手機,斷絕與外界的聯繫,當然依規定也不可以抽菸。那次的禪三,我的心非常平靜,長年的菸癮都沒有犯,甚至隔壁房間的先生晚上把頭伸出窗外,偷偷抽菸,煙飄進了我的室內,我居然也能不為所動所惑!只是下山後不久,覺得世界吵雜,雜事繁多,覺得心不靜定、煩躁,很快的,我又抽菸了。
心,如果能離一切境界,當然最好!像我在那一次的禪三,可以不受菸癮的制約。但修行不夠的我,常常心不能離境,「心」不能離境的時候,我選擇使自己的「身」離境——就是斷絕外緣。
很多年前讀《當和尚遇到鑽石》這本書,深受啟發,除了其中深論「自他不分」的共同成長之外——作者説每周三是他自己一人的「圓圈日」,用來靜休、靜思,使心力恢復、上增,後來並且有「森林日」⋯⋯
年紀過了半百,我看到有鹿文化的夥伴們成熟、互愛,所以在2018年3月1日,將總編輯的工作付託給林煜幃先生,由他帶領夥伴們更煥然的前行。
因為在那段時間,忙著自己第一次手墨個展,諸事忙碌,自知心性不夠澄明自在,我生起了無比強烈的「圓圈日」念頭,覺得是時候了,應該照顧好自己的「心君」。
2018年4月開始,我的「圓圈日」是每天傍晚六點之後,盡量關掉手機或保持靜音;有時擇日,徹底關掉手機,靜休、思惟、創作、思考——包括有鹿與我有關的工作、創作、陪伴因緣之人、爬山、運動、和朋友喝幾盞茶、聼一張唱片、慢慢為自己沖一杯咖啡……,也可能只是若有想、若非有想的嘗試「看到自己」、「陪伴自己」而已。
言語,道斷。
差不多十年了,每年我都會以兩天左右的時間,息交絕遊,什麼事也不做,就靜靜翻讀《法華經》。
慧命無窮,讀法華,變成我每一年的「慧命清洗日」,回到平靜的閱讀和思惟,因為斷絕外緣,遂形同「禁語」,因此略知什麼是不須言語的「妙不可言」!也因之有著淺淺的,超乎喜悅的喜悅。
讀法華,那是我以前除了「一人旅」之外,最「圓圈日」的行為了。
半百過後的我,近來因為「圓圈日」,多了緩慢、靜心,覺得生命的沙漏,流速慢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