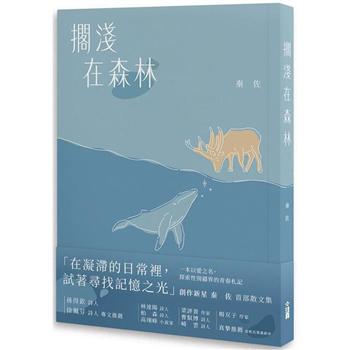01. 墨爾本
親愛的鹿:
那是我在臥鋪夜車上,第一次甦醒。拉開窗是灰藍的草原,從沒辦法想像的,透著光的,青金石色的天空籠罩著大地。
再次睜眼時,已到了南十字星車站,墨爾本的市心穿梭著電車,人群有秩序地移動,適度的吵鬧,待久了,明亮的景色竟顯得清寂。我記得那燦爛的陽光,撫在身上卻是冷。親愛的鹿,我想起高中,妳最討厭的地理課,油墨課本中的圖表讓我提早迷戀了遠方。那一刻,我竟佇立在墨爾本的街頭,南半球的城市,溫帶海洋氣候的二月,高緯度的夏季。
溶著陽光的風,和妳相似,依然微寒。
親愛的鹿,即使走過古老的大教堂、舊監獄、圖書館,喧囂的車站與市 集,我來到墨爾本的目的,卻是荒蕪的野地。攀爬在澳洲大陸邊緣峭壁的一條公路,大洋路。
我此生到過最遠的地方。
至於那些妳能輕易在旅遊手冊上讀到的,被人類硬是冠上某種意志性的名字的巨岩,我就不多說了,沿岸那亙古的美,也非我筆墨能觸及。親愛的鹿, 我想和妳談談意外的海灣,那裏幾近無人。誤打誤撞走進,無柵欄,無阻攔, 我就這麼走入汪洋的臂彎。半身浸在海水中,我知道即使我想,也不能再前進了,那一瞬間,真的覺得死在這裡就好了。
我想起一年前,大一上學期,那時也像現在,一下對未來充滿期望,肯定當前的努力與部分的逃避;一下充滿不安和恐懼,否認生命的一切意義。決定要前往澳洲的那天晚上,我去了詩人任明信的講座,最後有人顫抖著提問:「你詩中的重要主題是『愛』,對你來說愛是什麼?」詩人不多思索地回答:「愛是那一刻你可以為其而死。」
講座結束後,我才知道提問的人是憤怒的,他認為得到一個膚淺而做作的答案。走過高談闊論的提問人,詩人的話語卻越過了時空,到了乍晴的南半 球,流入晶亮而冰冷的海波中的我。我認為那句話非常精準,且美,一句話表現了愛的瞬間和永恆,合一,愛的永恆存於頃刻間,一刻是瞬間,死亡是永 恆,我們可以用瞬間去觸碰永恆。
親愛的鹿,海水慢慢侵蝕我的體溫。我是多久沒有感覺到我是愛著的了, 泥爛的現實早已吞沒我原先的形貌。而我並不害怕了結自己,我怕那只出於單薄的衝動。
我必須用漫長的時間去沉積那絕對的一刻,親愛的鹿,即使那時我們還未認識,或許此刻我也未曾真正認識妳,即使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我們必須走過這一段感情。親愛的鹿,我知道現在啟用的方法很詭異,但既自成為唯一對妳說話的方式,我將在可用按鍵消弭的平台,寫信給妳,讓妳從不會看見,變成可能看見。看見我在無可抑制的黑暗之後,生命裡確實也保有美好的瞬間, 牠們是那麼微小,零碎,卻閃閃發亮。
親愛的鹿,雖然這一切可能終如遠浪般轉化,消解。親愛的鹿,浸在來自南極的寒意中,我感覺溫暖,而無望,感覺平靜,而不必快樂。
02. 雪梨
親愛的鹿:
坐上臥鋪夜車前一天,我在歌劇院的美景前,被怒吼:「滾回中國。」我連解釋自己是台灣人的機會都沒有。
人們拿著水壺,在廣場中央排隊,天色欲雨,巨大的積雲壓扁了人們的耐心,一個白皙巨大的身軀撞過我,插隊上前,我用英語告訴他請排隊,之後不是利刃,是鈍厚血汙的殺豬刀一般,不屑的眼神:「滾回中國。」我第一次希望自己聽不懂對方的語言。親愛的鹿,在思考是什麼賦予他對素未謀面的瘦小亞洲人,說「滾回中國」的權力之前,我思考的是為何想和妳說這件事。寫信給妳,原本是冀望能把生命中美好的瞬間留下(即使微不足道),使我終於,或 許,可以好好向這世界告別。
那究竟為何說這事呢? 恐怕無關美善,這是真的,是「會發生」的,像我必然佇立這回憶裡,寫信給妳,像如此美麗的城市也會忽然暴雨。親愛的鹿, 當妳對我說,世界很爛但妳一點也不想改變。妳放棄改變社會就像放棄改變氣候,有時我也認知自己的渺小。
我們所面對的,不純粹是種族的惡意(即使許多經驗讓我知道自己時常被當成男性)。我耳畔響起經過澳洲入境檢查時,旅伴告誡:「海關盡量排有色人種女性。」旅伴的朋友曾被質疑為性工作者(跨海賣淫)而被攔下,並承受精巧而不犯法的羞辱,我並不想特意指涉,但旅伴朋友所面對的那海關,是白人男性。
「有色人種、女性」,親愛的鹿,那不正是我們的身體?這時我倦於爭辯自己是個非順性別者,就像在歌劇院前我倦於爭辯自己是台灣人。關於生存的不適,身為非異性戀,若再加上貧窮、心理疾病的因素,親愛的鹿,如果沒有足夠自欺欺人的本事,「真的每天起床只想自殺」(套用我朋友的話,他後來也去了),但我們都知道那些因素互相造成。
暴雨終於傾注而下時,我已在雪梨博物館中。展區沉默,關於華工與女性的空間總是太小,太少而且黯淡。當晚,我明知隔天夜裡要搭車前往墨爾本, 我還是在凌晨四點踩著路間積水跳上電車,白日熱鬧的唐人街此時沉睡在黑暗中,我到中央車站搭上第一班火車,在清晨的微光中前往藍山。
在雨後晴暖的山徑中,由渦痕及石色臆想古代的河流,轉角巧遇水聲才知瀑布不遠,用自己的雙手攀爬濕滑的岩石,踏著枯枝越過泥沼。高中課本裡, 讓雪梨多雨的大分水嶺,只是遙遠的概念、虛浮的考題。現下,卻是同時觸及我心靈與身體的無際大地。
那一瞬間,我真正認知自己的渺小,卻不感到悲哀。
在赭紅的巖頭之上,沒有想要保護自己,也沒有一躍而下的慾望。
親愛的鹿,那是我長期的毀滅傾向,突然乍止的一刻。被藍山雲霧環抱, 身體並不存在,有色、女性、瘦弱或任何標籤,都不存在。親愛的鹿,我曾對妳轉述過詩人的話,若當真「愛是那一刻可以為其而死」,或許。
一向太輕視自己的生命,所以愛也稀薄。
我想起年幼的自己,理直氣壯地說想改善這世界。我想起,妳對我說世界很爛的那一刻,我應該抱緊妳,說我們一起努力,無論妳要接納,還是抵抗, 無論結局。
03. 挪威的森林
親愛的鹿:
寫給妳的第三封信,關於告別與,我對記憶的偏執。
那是白色情人節前夕,我們在學校旁最安靜的咖啡廳,漫無邊際的談天伸展於幽暗的香氣。我談起想讀的書,妳說妳曾二小時內讀完《挪威的森林》:
「是周圍非常吵,充滿討人厭的親戚的時候哦!」妳接著解釋自己「一目十 行」的閱讀習慣,我懷著初戀的悸動與剛成為戀人的不安,幾乎是仰望著妳而感到難解的崇拜。我是許久以後才知道,妳花二個小時讀完的小說,我要用二個月的時間,一種充斥著個人風格的,遲緩。
讀一本書很慢,淡化一段記憶很慢。放下一個人,很慢。
妳離開之後,我拿著借來的破破爛爛的小說(館架上有兩本,很難分辨哪一本比較破),佇立於書架之間思考我的大學生活(同時我們知道政大的圖書館和它的藏書一樣破舊),妄想村上春樹式的浪漫與自由(與其反向)。和朋友在酒吧聊到凌晨三點,在無人的路上抽著菸走回宿舍,親愛的鹿,這些都是表 面,我什麼都感覺不到,妳離開之後我空空如也。有段時間我完全沉浸在《挪威的森林》,對不熟的朋友也提起,殊不知對方說:「很有趣的純愛故事呢。」對此我只能半開玩笑地回:「我倒覺得沉重,而且跟戰爭有關。」
那是 60 年代,主角渡邊經歷學運與思潮,關於遙遠而迫近的越戰。跟許多其他作家(我知識所及)比起來,村上的風格「容易被喜歡」,他的小說可以讀淺,可以讀深,不著痕跡地展演整個時代的青年氛圍(與反思,像是綠的社團遭遇凸顯性別仍不平等、號稱新思想青年的偽善)。然而,無論種種與當時社會扣合的巨大暗示,我在第一章,就決定了此生必須把這本書讀完。
只是為了那草原,深藏其中的孤獨的深井,為了其上突然消逝的不再被尋找的人,為了首章的最後一句:「直子甚至沒有愛過我啊。」
我是更久以後才知道,妳讀得那麼快,是因為有些情緒妳太熟悉了。親愛的鹿,《挪威的森林》對我來說最可怕的,是許多裡頭的話語與觀念,妳早警示過我。當他們在精神療養院談論「歪斜」,我想起我們,我突然明白能否一起生活的重點不是歪斜本身,是對歪斜的認知,雙方的差異。那時的妳恐怕像現在的我,自己不能好起來,怎樣都無法得到安慰,直子顧慮不了渡邊,木月顧慮
不了直子,而這不包含任何責怪的意思。縱使我感謝如此仍對我溫柔、耐心的人,我深知他們毫無義務,親愛的鹿,至於我們,會那麼痛並非因為我們曾在一起或那時發生的什麼,是因為我全心喜歡過妳啊。物質世界無法指認的真實籠罩著我,重點不是發生了什麼,是感覺到什麼。
「你需要更健康的愛人。」曾有摯友如此勸我,我下意識回答:「可是健康的人不會想要我。」像漂亮的小女孩穿著乾淨的洋裝,牽著和她一樣漂亮的媽媽的手,不會撿起路邊髒破的爛娃娃。親愛的鹿,妳那時為何選擇了我?或許妳選擇的是「我們」,妳不過從我身上感覺到了什麼,像最終章提起直子自殺後寂寞的喪禮,玲子姊近乎自信地對渡邊說:「我們遲早都會那樣死掉哦。」
我想這封信不能再刺探了,像拿硬石去刮一顆極薄的玻璃球,我意識核心的裂痕,不想記得妳,不能忘記妳,提及《挪威的森林》,我想起了妳,想起死亡,想起愛情。書中那些情節的對話(超越言語的),直子在自己精神的病的醫院;綠在他人身體的病的醫院,永澤與初美的死;渡邊與直子的死,都預示著某種命運。如果說在翻開《挪威的森林》時我就知道直子的結局,對於綠,我一無所知,即使許多人說綠「很世俗很正常」並非全錯,但她不是那麼一個形容能概括。最後主角不知身在何處,選擇「持續呼喚著綠」。
親愛的鹿,身為異常者的我們,或許從一開始就互能感知,回憶著我是怎麼走到今天,此刻聽著 The Beatles 的 Norwegian Wood,內心大為動搖,已知
「挪威的森林」為錯譯的我,莫名想起的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是在伍佰的歌,「挪威的森林」中那句:「我在妳心中是否仍完美無瑕?」從一開始就不是啊,親愛的鹿,但妳的選擇與我們的片刻,確實曾經存在的。
那並非淺薄的體貼與順勢的關懷,那是真正的同情。
「直子甚至沒有愛過我啊。」闔上書之後仍迴盪在我腦海。 親愛的鹿,願妳愛人如同妳被愛,願我們愛人如同我們被愛。
親愛的鹿:
那是我在臥鋪夜車上,第一次甦醒。拉開窗是灰藍的草原,從沒辦法想像的,透著光的,青金石色的天空籠罩著大地。
再次睜眼時,已到了南十字星車站,墨爾本的市心穿梭著電車,人群有秩序地移動,適度的吵鬧,待久了,明亮的景色竟顯得清寂。我記得那燦爛的陽光,撫在身上卻是冷。親愛的鹿,我想起高中,妳最討厭的地理課,油墨課本中的圖表讓我提早迷戀了遠方。那一刻,我竟佇立在墨爾本的街頭,南半球的城市,溫帶海洋氣候的二月,高緯度的夏季。
溶著陽光的風,和妳相似,依然微寒。
親愛的鹿,即使走過古老的大教堂、舊監獄、圖書館,喧囂的車站與市 集,我來到墨爾本的目的,卻是荒蕪的野地。攀爬在澳洲大陸邊緣峭壁的一條公路,大洋路。
我此生到過最遠的地方。
至於那些妳能輕易在旅遊手冊上讀到的,被人類硬是冠上某種意志性的名字的巨岩,我就不多說了,沿岸那亙古的美,也非我筆墨能觸及。親愛的鹿, 我想和妳談談意外的海灣,那裏幾近無人。誤打誤撞走進,無柵欄,無阻攔, 我就這麼走入汪洋的臂彎。半身浸在海水中,我知道即使我想,也不能再前進了,那一瞬間,真的覺得死在這裡就好了。
我想起一年前,大一上學期,那時也像現在,一下對未來充滿期望,肯定當前的努力與部分的逃避;一下充滿不安和恐懼,否認生命的一切意義。決定要前往澳洲的那天晚上,我去了詩人任明信的講座,最後有人顫抖著提問:「你詩中的重要主題是『愛』,對你來說愛是什麼?」詩人不多思索地回答:「愛是那一刻你可以為其而死。」
講座結束後,我才知道提問的人是憤怒的,他認為得到一個膚淺而做作的答案。走過高談闊論的提問人,詩人的話語卻越過了時空,到了乍晴的南半 球,流入晶亮而冰冷的海波中的我。我認為那句話非常精準,且美,一句話表現了愛的瞬間和永恆,合一,愛的永恆存於頃刻間,一刻是瞬間,死亡是永 恆,我們可以用瞬間去觸碰永恆。
親愛的鹿,海水慢慢侵蝕我的體溫。我是多久沒有感覺到我是愛著的了, 泥爛的現實早已吞沒我原先的形貌。而我並不害怕了結自己,我怕那只出於單薄的衝動。
我必須用漫長的時間去沉積那絕對的一刻,親愛的鹿,即使那時我們還未認識,或許此刻我也未曾真正認識妳,即使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我們必須走過這一段感情。親愛的鹿,我知道現在啟用的方法很詭異,但既自成為唯一對妳說話的方式,我將在可用按鍵消弭的平台,寫信給妳,讓妳從不會看見,變成可能看見。看見我在無可抑制的黑暗之後,生命裡確實也保有美好的瞬間, 牠們是那麼微小,零碎,卻閃閃發亮。
親愛的鹿,雖然這一切可能終如遠浪般轉化,消解。親愛的鹿,浸在來自南極的寒意中,我感覺溫暖,而無望,感覺平靜,而不必快樂。
02. 雪梨
親愛的鹿:
坐上臥鋪夜車前一天,我在歌劇院的美景前,被怒吼:「滾回中國。」我連解釋自己是台灣人的機會都沒有。
人們拿著水壺,在廣場中央排隊,天色欲雨,巨大的積雲壓扁了人們的耐心,一個白皙巨大的身軀撞過我,插隊上前,我用英語告訴他請排隊,之後不是利刃,是鈍厚血汙的殺豬刀一般,不屑的眼神:「滾回中國。」我第一次希望自己聽不懂對方的語言。親愛的鹿,在思考是什麼賦予他對素未謀面的瘦小亞洲人,說「滾回中國」的權力之前,我思考的是為何想和妳說這件事。寫信給妳,原本是冀望能把生命中美好的瞬間留下(即使微不足道),使我終於,或 許,可以好好向這世界告別。
那究竟為何說這事呢? 恐怕無關美善,這是真的,是「會發生」的,像我必然佇立這回憶裡,寫信給妳,像如此美麗的城市也會忽然暴雨。親愛的鹿, 當妳對我說,世界很爛但妳一點也不想改變。妳放棄改變社會就像放棄改變氣候,有時我也認知自己的渺小。
我們所面對的,不純粹是種族的惡意(即使許多經驗讓我知道自己時常被當成男性)。我耳畔響起經過澳洲入境檢查時,旅伴告誡:「海關盡量排有色人種女性。」旅伴的朋友曾被質疑為性工作者(跨海賣淫)而被攔下,並承受精巧而不犯法的羞辱,我並不想特意指涉,但旅伴朋友所面對的那海關,是白人男性。
「有色人種、女性」,親愛的鹿,那不正是我們的身體?這時我倦於爭辯自己是個非順性別者,就像在歌劇院前我倦於爭辯自己是台灣人。關於生存的不適,身為非異性戀,若再加上貧窮、心理疾病的因素,親愛的鹿,如果沒有足夠自欺欺人的本事,「真的每天起床只想自殺」(套用我朋友的話,他後來也去了),但我們都知道那些因素互相造成。
暴雨終於傾注而下時,我已在雪梨博物館中。展區沉默,關於華工與女性的空間總是太小,太少而且黯淡。當晚,我明知隔天夜裡要搭車前往墨爾本, 我還是在凌晨四點踩著路間積水跳上電車,白日熱鬧的唐人街此時沉睡在黑暗中,我到中央車站搭上第一班火車,在清晨的微光中前往藍山。
在雨後晴暖的山徑中,由渦痕及石色臆想古代的河流,轉角巧遇水聲才知瀑布不遠,用自己的雙手攀爬濕滑的岩石,踏著枯枝越過泥沼。高中課本裡, 讓雪梨多雨的大分水嶺,只是遙遠的概念、虛浮的考題。現下,卻是同時觸及我心靈與身體的無際大地。
那一瞬間,我真正認知自己的渺小,卻不感到悲哀。
在赭紅的巖頭之上,沒有想要保護自己,也沒有一躍而下的慾望。
親愛的鹿,那是我長期的毀滅傾向,突然乍止的一刻。被藍山雲霧環抱, 身體並不存在,有色、女性、瘦弱或任何標籤,都不存在。親愛的鹿,我曾對妳轉述過詩人的話,若當真「愛是那一刻可以為其而死」,或許。
一向太輕視自己的生命,所以愛也稀薄。
我想起年幼的自己,理直氣壯地說想改善這世界。我想起,妳對我說世界很爛的那一刻,我應該抱緊妳,說我們一起努力,無論妳要接納,還是抵抗, 無論結局。
03. 挪威的森林
親愛的鹿:
寫給妳的第三封信,關於告別與,我對記憶的偏執。
那是白色情人節前夕,我們在學校旁最安靜的咖啡廳,漫無邊際的談天伸展於幽暗的香氣。我談起想讀的書,妳說妳曾二小時內讀完《挪威的森林》:
「是周圍非常吵,充滿討人厭的親戚的時候哦!」妳接著解釋自己「一目十 行」的閱讀習慣,我懷著初戀的悸動與剛成為戀人的不安,幾乎是仰望著妳而感到難解的崇拜。我是許久以後才知道,妳花二個小時讀完的小說,我要用二個月的時間,一種充斥著個人風格的,遲緩。
讀一本書很慢,淡化一段記憶很慢。放下一個人,很慢。
妳離開之後,我拿著借來的破破爛爛的小說(館架上有兩本,很難分辨哪一本比較破),佇立於書架之間思考我的大學生活(同時我們知道政大的圖書館和它的藏書一樣破舊),妄想村上春樹式的浪漫與自由(與其反向)。和朋友在酒吧聊到凌晨三點,在無人的路上抽著菸走回宿舍,親愛的鹿,這些都是表 面,我什麼都感覺不到,妳離開之後我空空如也。有段時間我完全沉浸在《挪威的森林》,對不熟的朋友也提起,殊不知對方說:「很有趣的純愛故事呢。」對此我只能半開玩笑地回:「我倒覺得沉重,而且跟戰爭有關。」
那是 60 年代,主角渡邊經歷學運與思潮,關於遙遠而迫近的越戰。跟許多其他作家(我知識所及)比起來,村上的風格「容易被喜歡」,他的小說可以讀淺,可以讀深,不著痕跡地展演整個時代的青年氛圍(與反思,像是綠的社團遭遇凸顯性別仍不平等、號稱新思想青年的偽善)。然而,無論種種與當時社會扣合的巨大暗示,我在第一章,就決定了此生必須把這本書讀完。
只是為了那草原,深藏其中的孤獨的深井,為了其上突然消逝的不再被尋找的人,為了首章的最後一句:「直子甚至沒有愛過我啊。」
我是更久以後才知道,妳讀得那麼快,是因為有些情緒妳太熟悉了。親愛的鹿,《挪威的森林》對我來說最可怕的,是許多裡頭的話語與觀念,妳早警示過我。當他們在精神療養院談論「歪斜」,我想起我們,我突然明白能否一起生活的重點不是歪斜本身,是對歪斜的認知,雙方的差異。那時的妳恐怕像現在的我,自己不能好起來,怎樣都無法得到安慰,直子顧慮不了渡邊,木月顧慮
不了直子,而這不包含任何責怪的意思。縱使我感謝如此仍對我溫柔、耐心的人,我深知他們毫無義務,親愛的鹿,至於我們,會那麼痛並非因為我們曾在一起或那時發生的什麼,是因為我全心喜歡過妳啊。物質世界無法指認的真實籠罩著我,重點不是發生了什麼,是感覺到什麼。
「你需要更健康的愛人。」曾有摯友如此勸我,我下意識回答:「可是健康的人不會想要我。」像漂亮的小女孩穿著乾淨的洋裝,牽著和她一樣漂亮的媽媽的手,不會撿起路邊髒破的爛娃娃。親愛的鹿,妳那時為何選擇了我?或許妳選擇的是「我們」,妳不過從我身上感覺到了什麼,像最終章提起直子自殺後寂寞的喪禮,玲子姊近乎自信地對渡邊說:「我們遲早都會那樣死掉哦。」
我想這封信不能再刺探了,像拿硬石去刮一顆極薄的玻璃球,我意識核心的裂痕,不想記得妳,不能忘記妳,提及《挪威的森林》,我想起了妳,想起死亡,想起愛情。書中那些情節的對話(超越言語的),直子在自己精神的病的醫院;綠在他人身體的病的醫院,永澤與初美的死;渡邊與直子的死,都預示著某種命運。如果說在翻開《挪威的森林》時我就知道直子的結局,對於綠,我一無所知,即使許多人說綠「很世俗很正常」並非全錯,但她不是那麼一個形容能概括。最後主角不知身在何處,選擇「持續呼喚著綠」。
親愛的鹿,身為異常者的我們,或許從一開始就互能感知,回憶著我是怎麼走到今天,此刻聽著 The Beatles 的 Norwegian Wood,內心大為動搖,已知
「挪威的森林」為錯譯的我,莫名想起的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是在伍佰的歌,「挪威的森林」中那句:「我在妳心中是否仍完美無瑕?」從一開始就不是啊,親愛的鹿,但妳的選擇與我們的片刻,確實曾經存在的。
那並非淺薄的體貼與順勢的關懷,那是真正的同情。
「直子甚至沒有愛過我啊。」闔上書之後仍迴盪在我腦海。 親愛的鹿,願妳愛人如同妳被愛,願我們愛人如同我們被愛。